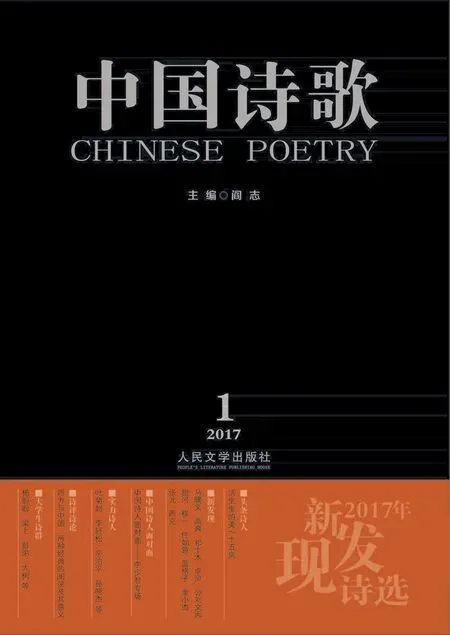诗意的栖息,与诗意的批评
□十五岚
诗意的栖息,与诗意的批评
□十五岚
叶芝在他的《茵纳斯弗利岛》中表达,他要在某个午后,回到一座宁静的岛屿,并在那里搭起一个小屋,筑起泥巴房,支芸豆架,养蜂,多么美好的一幅画卷。而南山的陶渊明呢?是否也厌倦了山水迢迢的仕途,只想回到一片和风送暖之地,举锄种菊,颐养生活。
诗意的栖息,在通往理想的乌托邦,我们必先像先辈一样,具备一颗返璞归真之心。
尽管当下,诗歌这一安静的词语,被无数嘈杂的声音追逐着,拥抱着……甚至使它产生了变异,充满矛盾与疼痛。但是,诗歌终究是要回到其本质上去的,它不以名利作为抛头露面的法器,而取悦大众;也不以媚俗,自甘堕落。它如山涧的流水,林梢之月,给人以清醇与澄澈。
歌德说:“这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是艺术可以向人类最崇高的努力相抗衡的境界。”而诗歌是艺术中的一种,具体到文学范畴,它所凝聚的是人类最高级别的智慧和灵魂。二者相辅相成,才能产生出唯美与和谐。
古今中外的诗人们都在试图按照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进行不同风格的创造,以此,吸引着美学家们的眼球。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保持积极向上的人格精神,才是创作的源泉。
比如唐朝的大诗人李白,我们认定他是诗人,符合他诗人的身份,首先源于他的文字。因为,我们在读他的诗歌的同时,找到了白帝城、月光、桃花潭等一系列美好的景物,并从文字中,我们了解到他是一个游历山川,喜欢以文会友的人。纵观他的作品后,我们才认定他的抒写风格是豪放型的,并以自然的心性在进行创作,然后让文字和我们相遇,我们才有资格,和他一起安顿下内心的世界。
所以,“文如其人”相对于诗人和其作品而言,这种说法还是比较贴切的。
清人叶燮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如果李白生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那么,他一定担当得起胸襟开阔,光明磊落的“我诗写我心”的行为风格,定然不负“诗人是皇冠上的明珠”这一美誉的称颂。
说到底,诗歌还是要回到自然的状态中去的。
而《文学概论》一书中,明确提出文学具备的四个要素:作品、作家、宇宙(自然,生活)、读者。这四要素在进行一系列的活动中,是必须相关联的:生活——作家——作品——读者。当生活在作家的面前展现时,作家不由得就拿起笔,写出作品,而作品最后要到哪里去?最后到了读者那里。读者是什么?读者是肩负起阅读责任的审美者与批判者。他有这个权利,因为作家写出来的作品是在向他传送(灌输)自然、生活中的美与丑。
其实,这个环节比作品诞生还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引导和启示。比如我们小时候在课本里,学到的那首《悯农》,旨在让我们学会感恩,记住恩慈。而生活实则并非处处充满鲜花和掌声。在面对自然与生活时,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有时候真让我们无能为力,惟一能做好的就是选择真理。而真理在的地方,那地方一定是美好的。
美好的东西,在我们的眼里多吗?很多!大到天空的繁星,河流里的浪花;小到眼前的一只鸟,一杯茶,一本书。我们通过这些自然美好的景致,获得内心的安宁。但是,当这种被内心认定美好的事物,有时被意外打破,失去原来的美,怎么办?我们总不能跟着去撕烂书本,摔坏杯子,赶走小鸟吧。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这就好比一面镜子,它破了,有人说好难看,又有人说那是残缺的美。具体到诗歌那块呢(比如骂人事件,评奖的丑闻等)?当真相还原出来后,我们只能以自己的良知去做评估,以自己的批判意识去建立批判。
对于诗歌作品而言,批判是为了亮明观点,起到甄别警示作用;对于诗人而言,批判是在促使其进步,趋于更完美。
席勒的《美学书简》里有一段阐述:“人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受到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束缚,往往得不到自由,总想用剩余的精力,去创造一个自由的天地,这就是游戏。”文学不能成为游戏,诗人更不能成为游戏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