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中国人的道德还需达成哪些“共识”?
编者按:2017年3月26号,北京师范大学在北师大英东学术会堂举办名家圆桌之“文化:焦虑与认同”会议,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高全喜受邀作了发言,从理论分析层面回应了在传统文化复兴背景下如何做有德性的中国人,制度和文化的关系,法律和道德的紧张等现实问题,视野开阔。本刊获得高全喜教授授权发表。
现今中国人的很大忧虑来自道德与法律的紧张关系,或者来自它们之间的张力。
非常高兴参加北师大文化研究院这个圆桌会议。这些年我偏重于宪法学研究,涉及文化的东西不多,但在追溯法律制度上的一些法理正当性时,也会触及到文化与文明的问题。今天正好借这个主题,谈谈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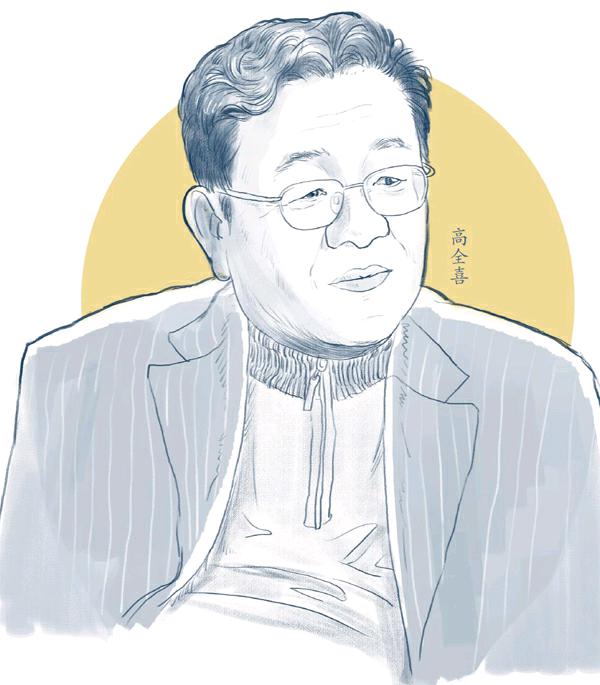
如何做一名有德性的中国人?
10天前, 《南风窗》曾经对我有个访谈,谈到中国社会需要提升道德资源的生产能力。我说关键的问题不在单方面的道德修养,而在于道德的公共化,在于中国人的道德能不能进入公共领域,单纯谈所谓的道德、德性是没有社会意义的。
当今中国的很多问题,我们所面临的忧虑,都跟公共性有关。公共性就是把我们原先日常人伦之间的私人规则,一些个人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平衡机制,包括我们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那些仁义礼智信的美德,放在社会的大格局中予以公开地言说、争议与探讨,由此形成共识和公共遵守的规则,甚至形成制度。
我想到十年前北京大学的张旭东教授写过一篇关于德国哲学与文化认同的著作,谈我们今天如何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记得我当时写过一篇书评,我的问题是,我们今天更应该拷问的是“怎样的制度才能使我们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
回到今天的主题,我同样也还是要说,现在谈所谓的传统文化、文明复兴,等等,这些高调的言辞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呢?当然,推崇传统与德性,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作为中国人谁都有其来有自的传统情感,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道德礼俗我们都感同身受。但是,我们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我们对于这些传统不认同,而是那些制约我们的如影随形的制度,如何使我们能够做成一个有德性的中国人呢?我们现在的焦虑根源主要是来自于制度层面。
现在很少有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了,对于人性中的那些美好的情感,对于传统培育中这些美德,很多人是有强烈的认同的。但问题在于我们生活中所面对的经济、政治、法律等制度上的问题,束缚了我们的道德生活,很难使我们做成一个清明良善的中国人。
我记得张旭东的著作写得很长很大,追溯的是德国文化的传统。德国思想很精粹,我本人也是搞德国哲学的。这些年我深入研究了一些英美的法律制度和政治传统,我觉得德国思想的一个最大短板就是用文化化约政治,高调谈文化,然后用文化把政治的一些根本问题化约了,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上的一些必须予以确立的东西都用文化把它们消解了。
实际上,这些制度层面上的问题最终是消解不了的,尤其是一个现代社会,我们所面临的经济的、宪法的、政策层面的问题,都是文化化约不了的。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必须面对这些问题,这些制度足以使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传统,我们人性中的某些善良天性,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和扭曲。我们的忧虑绝大部分来自这些扭曲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正义的法律制度,只是用一种道德上的高调,用传统文化的标签去遮蔽和化约这种本质性的生存张力,在现实生活中是乏力的,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对此,就像胡适在日记里说的一段很经典的话。他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文明底线与文化多元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美国的刘禾教授在北大出版社主编了一本谈文化多元论的书籍,痛斥西方的文明等级论。对此,我觉得有一定的思想理论价值,但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理论偏见。谈文化多元论,在理论上没有什么问题,尤其是在当今形势下,国际交流日益普遍,多元文化各展其姿,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文化多元论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和普遍接受。
在国际社会,不应该存在文化的歧视,因为种族、肤色、性别、信仰等差异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歧视,理当受到责难,西方传统的文化偏见理应遭到摈弃,这一点是大家都赞同的,甚至成为了西方社会的某种“政治正确”。
但是,问题是我们还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即是否有一个低级文明与高级文明,甚至是野蛮与文明的分野。现在的很多观点在此问题上还是糊涂不堪的。如果一味强调多元论,那就陷于文化相对主义,如果不能区分野蛮与文明,那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的特殊性也就失去了理据。
现实社会的很多使人担忧的问题,往往不全是文化多元引起的纷争,而是野蛮与文明的对峙。我认为这个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是第一位阶的逻辑问题,其次才是文化多元论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第二位阶的问题。
对于这个二阶的文明理论,我们要有充分的了解,其实早在18世纪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中,就有深入的论述。这个时期的理论家们强调文明演进论,赞同文化多元主義。在他们那里,首先要区分一个历史正义的逻辑标准,那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厘清划分。在共享的文明社会之中,才有一个多元并存的问题。
用今天的话来说,穿什么衣服,爱好什么饮食,喜欢昆曲,还是交响乐,甚至生活方式是什么,不同的民族大家彼此相互尊重,多元共享。但是,当我们面对那些野蛮的现代行径,像北美奴役黑人、恐怖主义、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等等,就应该认识到它们与我们诉求的社会生活完全不是文明多元的关系,而是文明与野蛮的对峙关系。
所以,在人类历史的文明演进中,首先要确立有一个文明与野蛮的区分问题,有一个文明演进的历史过程,人类只有把野蛮剔除出去,然后才能有多元的文明并存,文化共享,否则只能是人类文明的最终毁灭。
我觉得很多人把这个问题又给化约了,遮蔽了,由于过分强调文化的多元主义,强调文化平等,这就形成了一个“政治正确”。西方语境下的自由主义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政治正确”,这样一搞,就把野蛮和文明之别化约了。
就我个人来说,我比较赞赏的是苏格兰的启蒙思想,那里有一个文明演进论的历史与文化叙事,有一个区分文明与野蛮,以及不同文明演进和共存的经验主义历史观。遵循这个文明演进论,当然我们不能一昧就认为西方社会就是文明的,东方社会就是野蛮的,西方中心主义显然是错误的偏见。但是,这套文明演进论也不赞同文化相对主义,而是认为不同的文明民族都有各自的历史演变,都有一个从野蛮到文明、从低级文明到高级文明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在后来又都经历了相互的融合与交流,其中不排除对抗,但更多的是相互吸收,并最终化敌为友,共同繁荣。像刘禾她们固执于文明多元论,斥责西方的文明等级论,其实是很小家子气的,有着一种中国文明独断论的焦虑,如果放开胸襟,像古代的大儒那样以天地为怀,像当今的变革论者以时势为命,又何尝不能与西方文明交汇沟通呢?
法律底线和道德直觉
现今中国人的很大忧虑来自道德与法律的紧张关系,或者来自它们之间的张力。传统社会中的生活准则是德性优先,这在业已进入现代生活的很多中国人那里,仍然是获得广泛认可的。
从理想的视角来看,德性优先当然是好的,大家交往中人人都讲道德,岂不是天下太平、公正无私了吗?但那是一个高标准,需要一系列前提预设。
例如,在中国古代社会,能够纳入这一规范标准的人们,基本上都是衣食无忧的人,最低也是所谓士人阶层,他们才讲德性,才配讲德性,士大夫之下的庶民是不具有讲德性的资格的。
在西方古代社会,也是城邦公民才讲德性。德性优先的社会从历史上,必定是一个古代的等级制社会,看似美好,其实与平民百姓没有什么关系。到了现代社会,这个逻辑就变了,现代社会就是正义优先于德性,或者说,是法律优先于德性的社会。这个社会与广大的民众休戚相关,没有什么太高的预设,标准也不高,只要人们遵守法律规则,营生经济,参与公共生活,大致就可以了。上述胡适的那段话说的就是这个现代社会生活的一般道理。
这里又产生了一个人性善恶的问题。前年《文史哲》杂志召开过一个关于人性善还是恶的自由主义与新儒家的对话会议,很多人认为儒家讲究人性善,所以主张德治,自由主义讲究人性恶,所以主张法治,我认为上述所见是皮毛之见,至少不了解自由主义之精髓,也搞偏了儒家的人性论。
儒家的开山圣人孔子就是主张人性亦善亦惡,非善非恶,并不都是性善论,自由主义也不是都主张性恶论,休谟、亚当·斯密就主张亦善亦恶,两派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理论上的假定或预设不同,即儒家假定一个道德上的善治或德治,能够治理好一个社会,君王起到教化万民的作用,而自由主义则假定人性恶,从而防范君主专制,通过法律治理社会。
单纯从哲学上来说,我觉得人性善或人性恶,都是可以成立的,它们与治理社会没有本质性的关系,关键在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究竟何者优先。
对此,亚当·密斯说得很清楚,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他说正义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也就是说,法律或者是规则的治理要比道德的教化更为根本。因为,法律的约束对象不仅仅是民众,更根本的是掌握公权力者。法治的核心不是抓小偷,惩治刑事犯罪,这不是法治的根本含义,法治的根本含义是约束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问题在于,当今的法律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法治不彰,人们反求诸己,开始提倡道德,试图用道德解决法律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样就出现了大量的心理上的焦虑和无奈,甚至愤懑和怨恨。如果当今的社会能够提供一个法律健全的条件,确立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边界,约束有权力的人滥用公权力,那么就会是一个良治的社会,个人的道德感也能够滋生出来,并传承有序。
我觉得自由主义不一定非是预设人性是恶的,也不一定非要预设人性是善的。我觉得正常人性就可以了,这一点,苏格兰启蒙思想早就揭示的很清楚了,每个人都有基本的追求自我利益的自利之心,但还同时也有普遍的同情与仁爱之心,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基本的人性。
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衍生出一种规则,大家按照这个规则处理自己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还没有找到相应的机制,也没有产生真正的共识。于是,产生了诸多的困惑,这些都是在道德和法律、情感和理性、私己性和公共性方面,没有达成社会中的每个人的公共认同的标准所致。
我们看到,有些法律判决并不符合老百姓的道德直觉,感受不到公平正义。不能怪老百姓,他们就认一个“理”。如果把付诸法律救济的最后通道都堵死了,那老百姓怎么办?假如有正常的法律救济途径,这个社会就有基本的秩序与起码的底线。在此基础上,一个具有德性的社会建构是没有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