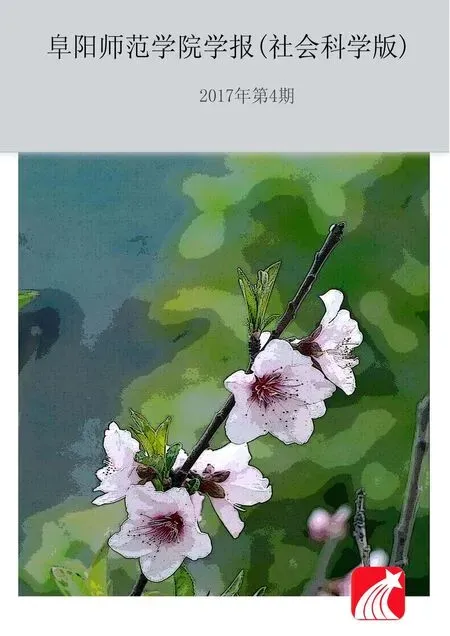移动学习模式下语言形式学习的可行性研究——以“互动假说”为视角
陈中毅,陈 静
移动学习模式下语言形式学习的可行性研究——以“互动假说”为视角
陈中毅1,2,陈 静
(1.上海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部,上海 200083;2.阜阳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在“互动假说”的理论框架下讨论移动学习模式运用于语言形式学习的可行性,发现移动学习模式可以灵活运用文本的编排功能,以及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媒介进行强化型和结构型输入,能够在促进学习者理解意义的同时将其注意力吸引到语言形式上,比教材中单一的文本型输入更加灵活有效。基于网络的移动学习平台不受时间、空间和课堂环境下干扰因素的影响,可以为学习者提供更多、更自由的交流互动机会,当交流以目标语作为媒介时,学习者能够更容易关注到语言形式。移动学习平台为学习者提供了口头和书面输出语言的机会,通过双向交流和集体协作的互动模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学习者口语化输出和正式文体输出的能力。
移动学习;互动假说;语言形式教学;聚焦于形
引言
传统外语教学以语言形式为纲,接受此类教学的学习者善于掌握语法规则,却难以在日常交流中自如运用。二语习得研究发现,不同母语背景的成人二语学习者在学习同一种语言的时候,遵循相同的语言习得顺序,经历相似的语言发展路径[1][2]。这对传统的外语教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不少学者据此认为二语教学无需关注语言形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Krashen[3]提出的“可理解性输入假说”,该假说反对一切语言形式教学,认为有意识“学得”的语言与无意识“习得”的语言分别储存在大脑中不同的位置,只有习得的语言知识能够在线灵活运用,学得的语言规则只能在交际压力不大的情况下对语言运用起到监控作用,使之更加完美。语言习得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是充足的可理解性输入。受此影响,各种轻形式、重意义和交流的语言教学法诞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沉浸式教学,倡导用目的语开设课程、以意义为中心、通过体验的方式来学习目的语。
教学实验研究表明,尽管沉浸式教学能比传统的教学方法更有效地提高学习者语言表达的流利度,但是它在提高语言表达准确度方面却不如传统教学方法有效,易导致严重的中介语石化现象[4]。沉浸式教学实验的失败使语言形式教学再次被重视起来,Long在批判Krashen假说的基础上,提出“聚焦于形”(Focus on Form 简称FOF)的教学方法,即在以意义或交际为中心的课堂上,学生的注意力有时会被某些不经常出现的语言形式吸引,从而开始关注这些语言形式[5]。为便于研究和操作,后来他对这一概念做了重新界定:FOF是指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教师或学生由于理解或表达困难而提出并引起大家对语言形式特征的关注[6]。FOF消除了传统教学中只重视形式不重视意义的弊端,同时也较好地规避了交际教学中只重视意义不重视形式的缺点,成为当前语言形式教学倡导的新模式。
随着语言教学理念的时代变迁,语言教学技术和手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计算机网络的飞速发展“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平等的、自由的、开放的学习环境,而且网络的智能化、交互性特点使学习者可以控制信息、改变信息组合过程,从而更能够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7]。当前,以4G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设备不仅具有传统的通讯功能,还能方便人们随时随地通过无线网络获取各种信息和知识,从而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学习模式——移动学习。移动学习具有移动性、无线性、便携性、资源共享性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学习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局限性[8]。移动学习模式使排队、等车、旅行等一切零碎时间用于学习成为可能,满足了人们在移动过程中随时随地学习的需求。移动学习对传统的课堂教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为语言形式教学带来了许多启示和可能。本文将在“互动假说”(Interaction Hypothesis)的理论框架内,从可理解性语言输入、互动式对话以及可理解性输出三个方面论证移动学习模式用于语言形式教学的可行性。
1 互动假说
Long[9][ 10]提出的“互动假说”理论主要包含输入、互动和输出三个要点,其中可理解性输入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通过对话进行的互动则能增强输入的可理解性,可理解性语言输出能够帮助学习者从语义加工到句法加工的转换。换言之,单纯的语言输入并不能保证语言习得,这也是对Krashen假说的批判。该假说同时强调了互动和输出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产生交际障碍时,交际双方的互动能够促使学习者关注语言形式特征,从而实现意义交流中的“聚焦于形”,并为可理解性的语言输出创造条件。简言之,可理解性语言输入是确保语言流利性的前提,而交际互动中的意义协商则有助于学习者关注语言形式,从而确保语言输出的准确性和可理解性。
1.1 可理解性语言输入
作为互动假说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可理解性语言输入源自Krashen[3]的“可理解性输入假说”它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没有输入,肯定不可能有习得,但不是只要有输入就一定有习得。如果输入的语言难度远远超出了学习者的现有水平,导致学习者无法理解输入的信息,那么这样的输入自然是无法产生习得的;相反,如果输入的语言过于简单,都是学习者已经掌握的知识,也不会产生新的习得。按照Krashen的理论,语言输入应该对学习者现有语言能力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是又不能高出现有水平太多,即所谓的“i+1”(其中“i”代表学习者现有水平,“1”就是对学习者设置的挑战)。尽管该假设因其可操作性受到学界的批评,但是输入的重要性从没有受到质疑。其实,笔者以为对于这个假说的理解不必过于刻板,学习者的现有水平完全可以通过测量工具来获知,教学一线的老师也可以根据教学经验来把握;至于“1”则没必要理解成某个固定的值,可以看成是新的语言形式占总输入的比例,对于不同程度的学习者,不大可能存在一个固定的值。另外,影响可理解性输入的因素也不会局限于新语言形式所占的比例,还包括输入的频次、呈现的方式等等,我们将在后文具体阐述。
1.2互动式对话
对话既是语言学习的目的,也是语言学习的手段。从社会文化理论[11]的角度来看,学习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活动,语言学习尤其如此,因为语言是人际沟通的桥梁,更是调节人际关系的纽带。在以意义为导向的互动式对话中,往往会出现因为语言形式使用不当而引发的理解困难,这种现象会经常发生在本族语者和非本族语者的交流中,在外语课堂中也不鲜见。围绕着理解困难而引发的意义协商以一种多产的方式把语言输入、学习者内在能力和语言输出连接起来[9],能够更好地让学习者在意义交流中习得语言形式。在意义协商的过程中,高水平者为低水平者提供的帮助和提示也构成了可理解性输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低水平者在高水平者的要求下所做的澄清、解释、说明等便成了可理解性输出的重要表现。所以,互动式对话一方面是衔接输入和输出的中间环节,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由输入和输出组成的。
1.3 可理解性输出
除了可理解性输入之外,Long[10]在修订版的“互动假说”中指出,可理解性输出同样可以促进语言习得。从某种意义上说,输出比输入更重要,因为它是检验各种二语习得假说的途径,它能够提高语言的流利度和自动化程度,培养学习者的元语言意识[12]。国内也有学者强调输出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提出“输出驱动假设”[13][14],认为输出比输入对外语能力发展的驱动力更大,能更好地培养学习者的说、写、译等表达技能,以输出为导向的综合教学法比单项技能训练更富有成效。不过输出驱动适用的群体是中、高水平学习者,他们具有一定的语言基础,通过输出可以盘活过去积累的“惰性知识”[15]。总之,输出是语言习得成效的主要体现,也是语言习得的主要目标。
2 移动学习与互动假说的契合
移动学习(M-Learning)是指使用移动设备,利用无线通讯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为学习者提供学习资源并为师生提供双向交流的一种学习方式[16]。由此可见,移动学习强调在交流互动中学习,与互动假说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而且交流互动的主要媒介就是语言,所以移动学习模式也应该适合语言学习。
与课堂学习相比,移动学习具有以下优点:首先,移动学习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灵活性。通过移动学习平台发布的学习资源能长久保存,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地安排学习时间和地点。其次,移动学习具有自主性。没有了老师的监督和家长的督促,移动学习完全由学习者自己掌控,学习资源和任务的使用频率和完成进度都由学习者自己来定。第三,移动学习的交流互动与课堂互动相比,具有延迟性的特点,可以给互动双方更多的思考时间,也能避免面对面交流可能产生的尴尬和紧张情绪。第四,移动学习并不局限于双向互动,也可以进行多向互动,例如微信、QQ等平台可以实现多人同时会话,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多平等交流的机会,打破了课堂教学中互动机会的局限性。第五,移动学习内容可以回访。由于网络的存储功能,学习者可以随时重温先前学习和交流的内容,增强理解,这是即时的课堂互动所无法比拟的。第六,移动学习模式更有利于学习者关注语言形式。移动平台上的互动主要是以文字和语音作为交际媒介,学习者要参与其中必须先理解这些语言形式所表达的意思,然后还要产出恰当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个过程自然会促使他们对语言形式的关注。
总之,移动学习体现了互动假说理论的本质内涵,能够突破课堂互动的局限。移动学习模式下的互动更加便利和自主,更加凸显了语言形式。通过移动设备与人保持沟通和交流是当前人际交往的常态,这也是移动学习模式用于语言形式学习的现实基础,下面我们从互动假说的三个要点出发来分析如何将移动学习模式用于语言形式教学。
2.1移动学习模式中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
在课堂教学中,输入的可理解性可以简单理解为教材的难度,即生词、新的语法结构和用法占总输入的比例,但是决定输入的可理解性绝对不止这一个因素。同样的输入内容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学习者的理解往往并不一样,这也是基于输入的FOF研究的核心内容。根据互动假说,学习者只有注意到目标结构才可能习得相应的语言形式,所以仅有输入是不够的,必须设法让学习者注意到要学习的目标结构,有效的做法有强化型输入(enhanced input)和结构型输入(structured input)等。
强化型输入就是通过加着重号、粗体等手法使目标结构在输入中突显出来,以便学生更容易注意到目标结构[17]。现在部分英语教材已经采用这种方法将课文中出现的生词以粗体的形式呈现以提高学生的注意度。但是教材只能给所有的使用者一个统一的标准,教师很难根据学生的水平和教学的实际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强化型输入。除非教师自己另外印发材料,那么这势必会增加教学的成本,这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很多现实条件的制约。这种课堂教学的窘境在移动学习模式下可以迎刃而解,教师可以通过QQ、微信等公共交流平台来发布学习材料,而学习材料的编排完全由教师掌控,教师可以根据教学需要对输入中的任一目标结构进行强化,不同的目标结构可以用不同的强化手法,或者相同的内容可以多次呈现,但每次强化不同的目标结构。这一切在移动学习模式下都可以轻易实现,而且不受其他现实条件的制约。
结构型输入是指一切促使学习者对目标结构进行加工处理的课堂教学活动[18]。结构型输入就是要让学习者关注和处理目标结构并获取相应的意义。VanPatten[19]认为输入加工策略不受环境因素的影响,所以结构型输入活动也不局限于课堂教学环境,完全可以运用于移动学习模式。常见的结构型输入分指称类(referential)和情感类(affective)两种[20]。指称类活动主要包括对错判断和选择,例如让学生选择一个恰当的名词短语(一个选项为名词的单数形式,另一个选项为名词的复数形式)来描绘一幅图,如果学生能选择正确的选项,则可以说明他们已经注意到名词数的标记并理解其表达的含义。而情感类活动则要求学习者对某事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例如让学生在听/读完一段话后,在“同意”或“不同意”的方框内打勾以表达自己的态度。结构型输入活动大多体现在课文配套练习中,数量有限、形式固定。如果通过移动学习平台进行结构型输入,可以实现输入形式多样化,以微信公众号为例,它可以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以及各种组合来发布信息,增强学习者对目标结构的理解,与课本中以文字为媒介的结构型输入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总之,从提高输入的可理解性来看,基于网络的移动学习模式可以灵活运用文本的编排功能、以及多种媒介进行有针对性的输入,能够在促进学习者理解意义的同时将其注意力吸引到目标结构上,比教材中单一的文本型输入更加灵活有效。
2.2移动学习模式中的交流互动与聚焦于形
课堂教学中的交流互动主要表现为师生互动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两种形式。根据互动假说,互动双方在遇到交际困难时进行意义协商能够使语言输入更容易理解。此时的“输入”既可以指课堂学习的内容(如某篇课文),又可以指主体间进行交流时,各自的讲话内容所构成的语言输入。不论是哪一种情形,交际双方进行意义协商时,必然会关注到语言形式,以及形式与意义之间的联接。但是,课堂教学由于受到时间和教学任务的限制,这种意义协商型的交流互动会非常有限。
移动学习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为意义协商提供机会更多、更自由的交流平台。微信和QQ等社交工具都提供双向交流和群聊的功能,其中双向交流就如同课堂上教师和单个学生之间的互动,或者两个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群聊则如同课堂上的小组讨论。所以,课堂上所有互动类型都可以在移动学习平台上实现。如上所述,移动学习没有课堂环境下的干扰因素,更有利于学生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互动。如果交流使用的文字就是所学习的目标语,学习者在参与互动的时候就必须要先理解语言形式,如果理解出现了偏差,交际的双方就会自然关注到语言形式及其所表达的意义。所以,基于网络的移动学习平台不仅能够为学习者创造更多的、有意义的交流机会,同时也能促使学习者更好地关注语言形式。
2.3移动学习模式中的可理解性输出
语言的输出分口头和书面两种类型,在移动学习模式下,语音和文字都可以作为交流的媒介,所以两种输出类型都可以实现。输出可以表现为独自完成的写作、演讲和翻译等,这些类型的输出显然是语言学习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是由于缺少互动,输出的可理解性得不到检验。最理想的可理解性输出应该出现在交流互动的环节,不过这种语境下的输出多口语化,不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正式文体的表达能力。在移动学习模式下,如何将口语化输出和正式文体输出有效结合起来并让学习者关注语言形式呢?
一种方法是让学习者独自完成习作或翻译等输出型任务,然后将各自完成的作业发送给另外一个同学评阅,评阅的同学如果发现任何表达不当的地方,都可以通过移动学习平台和原作者进行双向互动和协商。如此一来,学习者既经历了正式文体的输出,又通过口语化的输出来协商语言形式及其表达的意义,从而使两种文体的输出能力都得到锻炼。
另一种有效的做法是仿效词语接龙游戏让学生集体创作。该方法与王初明[21][ 22]提倡的“读后续写”法有异曲同工之处,“读后续写”在课堂教学实验中被证明为有效的。但是,该法主要局限于学习者的个体行为。移动学习平台上的集体创作,不仅要求单个学生的“读后续写”,而且还可以促进学习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精神。具体操作起来可以让学习者通过移动学习平台集体完成一篇小说的创作(可以参照“读后续写”法给出故事的开端),按照抽签顺序,每个人写一段,这样一来,每个同学在完成自己任务之前必须要先看懂前面同学的创作,这会促使他们注意到前面创作中的用词、时态、语法结构等,从而会更加注意自己创作中的语言形式。如果某同学对前面同学的创作有理解困难的地方,就应主动去交流协商。所以,这种以任务驱动的输出活动反过来会促进学习者之间为协商意义而进行的交流互动。
结语
综上所述,从“互动假说”的视角来看,通过移动学习平台组织的语言形式学习不仅可行,而且与课堂教学相比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一方面,移动学习平台为语言输入提供了灵活多样的方式,能够有效提高输入的可理解性,为学习者提供更多、更自由的双向和多向交流互动;另一方面,通过移动学习平台组织的各种双向和集体的输出活动,能够综合培养学习者正式文体写作和口语化表达的能力,并能有效促进学习者在进行意义协商的同时关注语言形式。但是移动学习模式缺少了课堂环境下的老师监控,并不能确保学生会用目标语进行交流互动。在群聊的环境中,如果有老师的参与,可以促进学习者使用目标语进行交流,但是这又有可能给学习者造成交际压力。如何确保学习者在移动学习平台上积极使用目标语进行输出和交流,是我们今后研究的新课题。
[1]Dulay, H. & M. Burt. Should we teach children syntax? [J]. Language learning, 1973, 23(2):245-258.
[2]Pienemann, M.,M. Johnston & G. Brindley. Constructing an acquisition-based procedure for second language assessment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88, 10(2):217-243.
[3]Krashen, 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Oxford: Pergamon, 1982.
[4]Hammerly, H. Fluency and accuracy: Toward balance i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and LTD, 1991.
[5]Long, M. Focus on form: A design fea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ology [G]//In de Bot, K., R. Ginsberg & C. Kramsch (eds.).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Amsterdam: John Benjamin. 1991:39-52.
[6]Long, M. & P.Robinson. Focus on form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G]//In Doughty,C. & J. Williams (eds.). Focus on form in classroom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15-41.
[7]戴炜栋,任庆梅. 基于网络技术的词汇习得认知心理环境设计[J].外语电化教学,2005(2):1-6.
[8]刘爱军,刘竹清,褚昭昂. 移动学习的接受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南京的调查[J].开放教育研究,2013 (4):104-111.
[9]Long, M. Native speaker/non-native speaker conversation and the negotiation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J].Applied linguistics, 1983,4(2): 126-141.
[10]Long, M. The Role of th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Chest,1996, 128(3):1836-1852.
[11]Lantolf, J. P.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Swain, M.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Some roles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and comprehensible output in its development [G]//In Gass, S. M.,C.Madden (eds.).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NewYork: NewburyHouse. 1985:235-256.
[13]文秋芳. 输出驱动假设与英语专业技能课程改革[J]. 外语界,2008(2):2-9.
[14]文秋芳. 输出驱动假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思考与建议[J].外语界,2013(6):14-22.
[15]Larsen-Freeman, D. Teaching language: From grammar to grammaring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16]Kukulska-Hulme, A. Mobile learning: A handbook for educators and trainer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17]Ellis, R.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and Language Pedagogy [M].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2.
[18]Nassaji, H. & S. S. Fotos. Teaching grammar in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s: Integrating form-focused instruction in communicative context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19]VanPatten, B. Input processing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G]//In VanPatten, B. (eds.). Processing instruc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commentary .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2004: 5-31.
[20]Vanpatten, B. Input processing and grammar instruction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Norwood, NJ: Ablex, 1996.
[21]王初明.读后续写何以有效促学[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5):753-762.
[22]王初明.读后续写——提高外语学习效率的一种有效方法[J].外语界,2012(5):2-7.
A Feasibility Study on Mobile Learning of Form-Focused Instruction: An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CHEN Zhong-Yi1,2,CHEN Jing
(Graduate School,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83;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Fuyang 236037 Anhui)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Interactive Hypothes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mobile learning to form-focused instruction. With the flexible functions of text management and various media of pictures, sound and video, mobile learning has some advantage in offering enhanced and structured input, which help to focus learners’ attention on linguistic forms and the meaning as well, much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single textual input in the textbooks. The Internet-based mobile learning platforms are free from the restrictions of time and space as well as the distractions in the classroom. They can provide learners with more chances of free interaction, either in oral or written form, where attention to the linguistic forms can be achieved in the target language. Interactions of two-way communication or team work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oral and written output of learners.
mobile learning; the Interactive Hypothesis; form-focused instruction; focus on form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7.04.26
G642
A
1004-4310(2017)04-0135-06
2017-04-18
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移动学习模式在《高级英语》教学中的运用及成效研究”(2015jyxm217)。
陈中毅(1979- ),男,安徽芜湖人,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二语习得和外语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