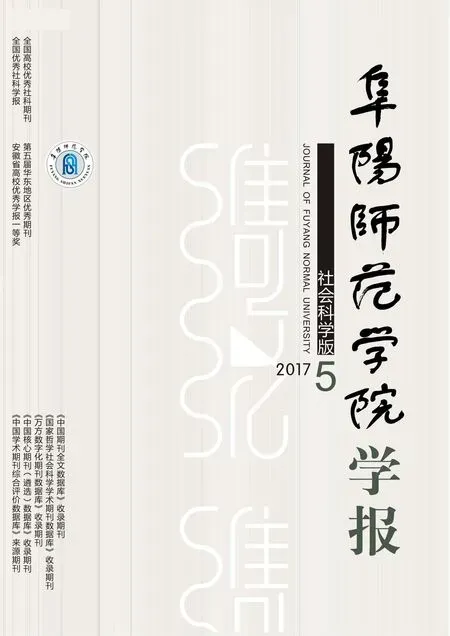文体学视角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建构——以诗歌体教学为例
刘 敏,代晓利
文体学视角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建构——以诗歌体教学为例
刘 敏,代晓利
(阜阳师范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中国古代文学历时久远,内容丰富,文体众多。沿袭传统的教学思路,不仅费时费力,且效率不高,学生对古代文学中常见文体的发展演变更是难言其详,甚至会混淆一些文类的体裁。从文体学的视角切入教学,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诗歌体教学为例,结合相关作品让学生直观感受诗歌体从萌芽产生到逐步成熟的不同体裁类型,梳理演变历程,总结演变规律;再通过阅读代表诗作,品味不同时期代表作家及其作品的风格差异,乃至某一时期的总体风貌,不同流派的风格等,以期让学生全面深入地把握诗歌这一文类。
中国古代文学;文体学;诗歌体
中国古代文学从先秦到明清,历时久远,文体繁多,作家及作品数量庞大,涉及领域广泛,学习古代文学确非易事。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讲授古代文学的教师逐步摸索出一种较为可行的“三段论式”教学模式,即作家生平创作、作品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对于初涉古典文学的学生来说,这种教学方法固然可以较为快速了解古代文学发展演变的历程,把握其中代表性作家、作品等。但是,往往几学期的课程结束后,学生对一些常见文体的发展演变还是一知半解,甚至混淆一些相似的文体。尽管古代文学课程的许多教师不断改革创新课堂教学,诸如参与式教学法[1]、研究性教学模式[2]、合作探究式教学法[3]、实践教学法[4]、地域教学法[5]以及专题式、立体化教学模式[6]等,取得了一些喜人的成效,但还不够彻底。因为改革古代文学教学,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固有的思路,打破王朝分期的局限,以几种主要文体的发展演变为线索,并结合相关作品进行教学。其实,很早就有专家学者提出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要注重文体意识,如胡祥云提出“必须加强文体意识,建立以文体为中心的教学体系”[7];赵义山、万伟成提出:“教师首先要坚持文学本位原则,增强文体意识与文本意识,并在课堂教学中坚持以文本为基础,以文体为纲要,把认知的重点由文学中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文化引向文学自身的体式特征和审美构成。”[8]虽然也出版了《中国分体文学史》,但目前高校通用的文学史教材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这些教材的编写基本还是按王朝分期来阐释文学发展历史,即以时代发展脉络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把作家作品放在特定的时代大背景下,而忽略了各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规律。因此,在当前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中,亟需教师转变教学思路,从文体的角度切入,让学生更清晰地了解我国古代主要文类的发展演变及其风格特征等,进而更全面深入的把握古代文学。
何谓文体?在我国,文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简单的说“文体,指文学的体裁,体制或样式”[9]1。吴承学先生初步归纳“文体”之“体”的六种含义:“体裁或文体类别;具体的语言特征和语言系统;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体要或大体;体性、体貌;文章或文学之本体。”[10]25-26杨旭认为“文体”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里应该有四个层次的涵义,即“文类、体裁、篇体、风格”[11]77。中国古代文体不仅内涵丰富,且种类繁多。《文选》分39类,《文心雕龙》分33类,《文章辨体》有58种,《文体明辨》有121种。面对如此繁多的古代文体类型,在教学中该如何选择呢?“就中国古典文学范畴来说,主要指诗、词、文、小说、戏曲五大门类。从文体意义上讲,诗、文、词、小说、戏曲也可以成为诗体、文体、词体、小说体、和曲体。我们研究古代文体的发展变迁,实质上就是研究这五大文类的发生、发展、鼎盛和终结。考察整部中国文学史,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史实际上就是这五大文类的变迁史,而文学创作上的创新与这五大文类的发展是互相推动的。”[11]78笔者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对这五种文体按照吴承学、杨旭所论文体的涵义出发,每一学期从一、两种文体入手,梳理每一文体从产生、发展到成熟、变迁、衰落等,着重解读每一文体在每一发展阶段的代表性作品,深入理解每一文体的特征,与其他文体的区别以及自身的演变规律等。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以诗歌体教学为例,阐释在教学过程中如何让学生了解并掌握诗歌作为独立文类的体裁体制,体性体貌等。
一、明确诗之体裁体制
文学起源于劳动,而诗歌伴随劳动首先产生。诗歌体的教学可以安排在古代文学学习的第一学期。在讲授古代文学时,如果从朝代的发展顺序来讲,很难让学生对诗歌体的体裁分类及其特征有全面明晰的了解。从文体学的视角出发,先让学生了解诗歌体的渊源,把握诗歌体的体裁分类,通过阅读不同体裁的诗歌,总结出不同体裁类型诗歌的体制特征,有利于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提升学习能力。
诗歌从句型上有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等等,体类有楚辞体、乐府诗、古体诗、近体诗(律诗、绝句),唱和诗、联句诗、集句诗等等。教学时先让学生了解并把握每种诗歌体的渊源流变及其主要特征,辨析相近体裁的诗体,这里难以区别的是古、近体诗,还有乐府与歌行。
诗歌起源于劳动,伴随劳动而产生的原始歌谣,以二言体为主,奠定了后世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性,但由于距离我们年代久远,真伪难辨。从西周末到春秋中叶出现了以四言体为主的《诗经》,成为我国诗歌艺术的光辉起点。《诗经》中赋比兴的手法、重章叠句的运用、风雅精神、优美和谐的语言艺术、用韵方式等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教学时结合一些典型的诗例,让学生感受诗歌体的古朴形态。战国后期,在我国南方楚地产生了一种新的诗体即楚辞,从音律到内容、语言都具有浓郁的楚地风韵,所谓“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校定楚辞序》)。受楚地巫风的影响,多描写人神相恋和天神地祇等故事,宗教气氛和神话色彩浓厚,想象力丰富,善于运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和神话故事,成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楚辞体的教学应注意与《诗经》进行比较。如《天问》《橘颂》的体制与《诗经》四言体接近,其他楚辞作品均以六字句和五字句为基本句式,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对汉赋及五、七言诗影响巨大。
乐府诗,来源于汉代专门设立掌管音乐的机关,后人把这一机关所采集编录的诗歌称为乐府。“所谓‘乐府诗’,主要是指自两汉至南北朝由当时的乐府机关所采集或编制的用来入乐的歌诗,但这只是最初的情况。”[9]102后世把入乐或不入乐模仿乐府旧题或自创新题的文人的仿作都称作乐府诗。从形式上,乐府诗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汉末曹操首开学习乐府诗的风气,用乐府古题写时事,继承并发展了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东晋南北朝,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纵情声乐的需求,乐府机关从民间大量收集民歌俗曲。隋唐之时,很多文人依然喜用乐府体写诗,如李白、杜甫、高适、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等,既有用乐府古题,也有“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句数长短自由,句式参差不齐,也不入乐演唱,只在创作方法、表现手法上继承和模仿汉乐府诗而已。及至后世,甚至把词与曲也称为乐府,实际上混淆了文体的界限,不够科学。
歌行体是汉魏乐府诗产生后,文人模仿乐府诗的风格所写的以五、七言为主,间以杂言的诗体。后人一般把唐前的这类作品称为乐府。自从七言诗在唐代兴起后,这类诗歌往往以七言为主,没有句数限制,句式参差错落,适合表现纵横恣肆的感情,被称为“歌行”“七言歌行”“近体歌行”等,李白喜用歌行体来表达奔放的感情,岑参好奇的个性也喜用长短不齐的歌行句式来描绘边塞奇异之景。关于唐及其以后的乐府和歌行比较难以区分,目前学界也尚无定论,可以安排学生讨论。
古体诗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包括四言体诗、楚辞、乐府诗、五古、七古、杂言古体等。狭义上主要有五、七言古体,句数没有限制,一般不讲求对仗,也不讲平仄,押韵较为自由。其产生也经历了民间流传到文人仿作而逐渐盛行的过程。汉乐府民歌中五言诗居多,而后《古诗十九首》代表着当时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五言诗在魏晋南北朝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诗歌中的一种重要体式。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创作五言诗的文人。七言诗的起源不晚,但兴盛较晚,大概由于其较难驾驭。曹丕《燕歌行》是现存第一首成熟的文人七言诗。刘宋时期的鲍照对七言诗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把句句押韵改为隔句用韵,还可自由换韵,容量大,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之后梁朝一些著名诗人,如四萧、沈约、吴均等都有七言诗流传于世,但直到唐代李白、杜甫、岑参、韩愈、白居易等,七言诗才蔚为大观,蓬勃发展。
近体诗是同古体诗相对而言的,一般认为包括律诗、绝句、排律。每种又分为五言、七言两类。自唐代产生后,历经宋元明清一直都很盛行,体裁上较易识别。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成为律诗定型的标志。在此之前,诗歌的对仗、声律等方面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道路。其中永明体的出现对近体诗的形成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永明体讲求声律和对仗,成为近体诗的先驱。近体诗在句数、字数、平仄、对仗、用韵方面均有严格要求。如每首八句四联,每句五言或七言,只用平声韵,用韵要一韵到底,中间不能换韵,首句可押韵,也可不押,中间两联对仗等。排律,又称长律,也有五七言之分,是指每首超过八句的律诗。从格律上,按照五、七言律诗黏对要求;从对仗上,除首尾两联或尾联不要求外,其他句子都要对仗;从篇幅上,没有限制,从十句到二三百句皆可。写排律的难度较大,因此数量较少,名作不多。绝句,又称律绝,有五言四句和七言四句两种,它是在民间流行的五、七言四句诗的基础上受齐梁时讲求声律的影响,到唐代而逐渐定型,成为近体诗的一种。格律上与律诗基本相近,但不要求对仗,相对律诗更为小巧灵活,易于读诵,但由于容量有限,创作受限制。后来发展到用绝句写成的组诗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受到杜甫、白居易、元好问、杨万里、范成大等人的青睐。
至于诗歌的其他体式三言、六言、杂言,杂句、杂体、唱和诗、联句诗、集句诗等,也可以先溯源再结合相关代表作品进行讲解,让学生全面了解诗歌的不同体式,进而总结出诗歌各体裁的演变规律。句式从原始歌谣的二言体、三言体,发展到《诗经》四言为主的四言体,到汉魏六朝时五言诗兴盛,唐代才迎来了七言诗的繁荣。体制由古体逐步演变为近体,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五、七言近体诗成为百代不易之诗体。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到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新诗成为主流,古典诗歌失去了昔日的繁华,走向衰亡。尽管现当代也不乏有古典诗歌的创作者,但终已成强弩之末。“文体一如人体,是一个整体有生命的机体”[11]78,也有其从产生到衰落的过程。
二、品味诗之体性体貌
明确诗歌作为独立文类的体裁分类及体制特征后,让学生结合作品进一步去品味诗歌体的体性体貌。吴承学先生曾归纳文体的体貌、体性主要有以下含义:“某一类文体的风格;具体作家的风格;具体作品的体貌特征;某一历史时期文章的总体风貌特色;体貌类型或风格类型;流派风貌特征。”[10]26
首先可以按照历时性的发展顺序,让学生阅读不同时期的诗作,进而品味不同诗人、诗作的风格。注意引导学生开阔视野,自主学习,培养创新意识。阅读时不能仅凭个人的喜好,应对诗人不同时期、不同体裁、题材的诗作都有全面深入的解读后,才能比较客观全面地品味并评价诗人的总体风格。比如《诗经》,学生在阅读时比较偏爱《国风》朴实自然的风格,尤其是其中真挚感人的爱情诗,很少愿意读《颂》诗及《大雅》中那些雍容典雅歌功颂德的庙堂乐歌。但如果只片面阅读的话,就不能理解《诗经》为什么是周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不能具体详细地了解当时周代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风貌,更难理解风、雅、颂的分类及其风格的差异。再如陶渊明,在学生心目中更多的是躬耕田园的隐者形象,学生读的较多的是其平淡自然的田园诗,对其咏史、咏怀诗则较少关注。只有当学生读了《读山海经》《咏荆轲》后,才能真正体会陶诗“金刚怒目式”的一面;当读到《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才能体会到陶诗愤激不平的一面,而不全都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悠闲飘然的一面,进而可以全面认识并评价陶渊明其人其诗。就同一诗人而言,由于时代社会、个人生活遭际的不同,其创作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曹植的诗歌创作,以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高扬政治理想,反映社会现实及贵公子的生活,充满了昂扬奋发的少年意气;后期由于受到曹丕的猜忌和迫害,更多的是忧生之嗟,诗风由豪迈乐观转为愤懑悲凉。又如王维,其诗歌创作以张九龄罢相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作品反映了盛唐士人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多游侠诗、边塞诗、政治诗,慷慨英发,风格雄浑博大;后期特别是遭受安史之乱后,消极避世,唯以佛教为慰籍,多山水田园诗,诗歌幽邃空静,充满禅趣。同样,处于同一时代的不同诗人其诗风也有明显不同,或属于同一流派的不同诗人诗风也有差异。如太康诗风的主流代表作家陆机、潘岳,其诗风繁缛,描写繁复,语言华丽,但左思的诗却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传统形成独特的左思风力,笔力矫健,情调高亢,于当时流行的太康诗风外别树一帜。高适和岑参同属盛唐边塞诗人,但高诗慷慨悲壮,而岑诗则雄奇壮丽。这些都需要引导学生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慢慢品味,不断总结概括,才能提升对历代诗人诗作的认识和理解,并形成自己的观点,逐步培养创新意识。
其次,学生读完每一时期的诗作后要引导他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品味该时期的诗歌风貌,并与其它时期进行对比。如《沧浪诗话·诗体》中所谓的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盛唐体、元和体、元祐体等。亦或是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比如在读了三曹、七子、蔡琰等诗作后,学生很容易概括出建安诗风:慷慨悲凉,雄健深沉。既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理想壮志,也有“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时代悲凉;既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雄主义精神,也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现实悲哀。在读完盛唐诗后,学生可以概括盛唐诗歌的总体风貌,博大雄浑超远豪迈,给人以精神的鼓舞和振奋,即使写愁,也愁得有气势有气魄。在读宋诗时,宋代社会积贫积弱的现实使得宋诗深沉内敛,不如唐诗的蕴藉风流,情韵兼善,可以让学生对比汉魏六朝诗歌,尤其是唐诗来读。一是从诗歌体本身的发展演变来看,由古体到永明体、近体,由四言、五言到七言、杂言等;一是从诗歌的总体风貌来看,引导学生通过对比感受汉魏六朝诗的古朴与妍丽、唐诗的雄壮浑厚、宋诗的理性沉稳。
从历时性的角度引导学生读完每一时期的诗作后,接着对此期的诗风进行概括归纳并与其他时期对比,然后进一步理解诗歌体的体貌类型或风格特征。《文心雕龙·体性》:“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这里是把所有文体的体貌类型化了,当然在阅读时可以根据学生自己的理解体会,让他们对所读诗歌的风格进行概括并列举一些风格突出的代表作品。同时也可以和词体的风格进行一些比较,深入体会诗、词体的差异。
最后,还应该让学生对诗歌体的总体风格进行归纳,从辨体的角度来区分诗歌体与其他文体的不同,以明确诗歌体的独特文体特征。如诗歌体与词体的辨体,诗歌体与散文的辨体等。明代胡应麟曰:“诗与文体迥然不类,文尚典实,诗尚清空;诗主风神,文先理道。”(《诗薮》外编卷一)这里指出诗与文相比的突出风格特征。学生通过大量阅读诗歌体、散文体后较易得出诸如诗贵含蓄,重言志抒情,文贵典实,重叙事说理等。
诗歌体的体裁类别不同,其风格也相差明显,比如古体诗和近体诗的差异比较明显,古体诗没有句数、字数的限制,所以比较自然流畅,古朴典雅,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内容;近体诗由于在声律、字句方面的严格要求,风格含蓄蕴藉,音韵和谐,音乐感强。
在教学中,以诗歌体的不同体式发展演变为经,以每种诗体特征和代表作家作品为纬,由文体外部的体裁、体制、体式逐步到文体内部的体性体貌,层层深入剖析诗歌这一文类,让学生全面了解并掌握诗歌体演变历程及文体特征。
总之,在古代文学教学中,从文体学的视角着眼,应从该文体的文类、体裁、篇体、风格出发,阐释不同文类的不同体裁演变,每种文类不同体裁的篇体特征及与相似体裁之间的区别联系,不同文类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风格形成及演进。需要注意的是,各类文体之间并非截然不同,而是相互影响渗透。就诗词而言,诸如韩愈、欧阳修等人的以文为诗,苏轼的以诗为词,辛弃疾的以文为词等等,便是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的结果。在教学中,尤其需要注重回归文本本身,在理清某一文类的发展演变、文体内涵时一定要结合相关作品,不能脱离作品,应让学生在阅读中去体认、感受该文体从萌芽产生到逐步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从同一文体不同体裁的代表作品中总结出该文体的体貌、风格特征等,从同一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去体味作家风格的变化,这样才能更全面深入的把握某一文类,进而提升古代文学的教学质量。
[1]金建锋.古代文学课程参与式教学法的应用研究[J].南昌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101-103.
[2]吴敬玲.古代文学课程研究性学习教学模式的几点思考[J].文学教育,2016(12):71-73.
[3]徐祺娟. 合作探究式教学现状及问题探析——以浙江万里学院为例[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6):99-104.
[4]柯迁娣. 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性教学模式探索——以池州学院为例[J]. 池州学院学报,2016(4):135-137.
[5]陈凯玲.利用地域文化资源探索“中国古代文学”教学[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5):113-116.
[6]王子文. 专题式——立体化: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新探[J]. 萍乡学院学报,2015(2):96-99.
[7]胡祥云.文体意识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89-91.
[8]赵义山,万伟成.让文学课教学回归文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4):50-53.
[9]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 -285.
[10]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J].文学遗产,2005(1):25-26.
[11]杨旭.论“文体”涵义的四个层次 [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77-81.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7.05.29
G642.0
A
1004-4310(2017)05-0153-04
2017-07-12
安徽省教研项目“全面提升三本院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质量的探索与研究”(2014jyxm720);安徽省重大教改项目“全面贯通视野下地方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阜阳师范学院为例”(2013zdjy116);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卓越文科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16zjjh048);阜阳师范学院教研项目“基于中文师范生专业素质培养导向的古典诗歌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2015JYXM54)。
刘敏(1978- ),女,安徽阜阳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代晓利(1990- ),女,安徽临泉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大众传播学等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