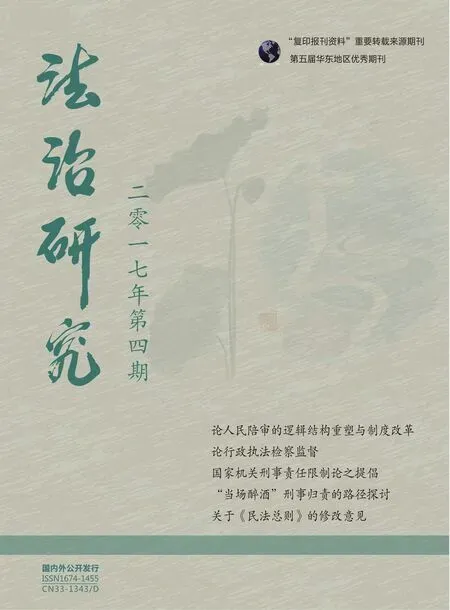国家机关刑事责任限制论之提倡
周振杰
国家机关刑事责任限制论之提倡
周振杰**
从国家机关及其行为内部的区别出发,对国家机关刑事责任不宜简单地予以全部否定或者肯定,而应该采取限制论的立场:国家机关原则上可以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但是其刑事责任应该限制于权利行为与有限的权力行为。从国家刑事责任的角度出发,全国人大、国家主席、国务院等代表国家的国家机关不应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从行为的角度出发,国家机关刑事责任应该限制在不能代表国家的机关所实施的具体权利行为、法律规定其应该承担经济或者行政责任的具体权力行为以及存在具体相对人或具体法律义务的具体权力行为。
单位犯罪 国家机关 刑事责任 限制论
一、引言
传统上,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都以自然人刑事责任为假想对象。20世纪80年代以前颁布的刑事立法都没有单位犯罪。在198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将单位规定为走私犯罪的主体之际,否定单位刑事责任的立场仍然在理论界占据主流,就如有的观点所言:“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本身就是立法回应社会现实的仓促之举,缺乏理论上的深入探讨。”①赵秉志:《外向刑法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页。因此,就单位犯罪,在理论上仍有许多至今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是否应该追究国家机关的刑事责任就是其中之一。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回顾与分析理论界目前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从比较法、国际法与宪法等角度出发,探究国家机关应否承担刑事责任,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二、国家机关刑事责任的否定论与肯定论
根据《刑法》第30条“公司、法人、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之规定,追究国家机关刑事责任在立法层面应该不存在障碍。“既然刑法规定了单位可以成为犯罪的行为主体,事实上国家机关也完全可以实施部分犯罪,故没有理由将国家机关排除在单位犯罪的行为主体之外。”②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1994年山东省乳山市商业局走私案、2000年黑龙江省庆安县人民检察院单位受贿案、③参见周振杰:《比较法视野中的单位犯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页。2015年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教育局单位受贿案④参见毛占宇:《谢家集区教育局单位受贿案引热议,专家认为可作为审案判例起到指导性作用》,载《法制晚报》2015年11月3日。以及2015年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人民政府单位行贿案⑤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向刑初字第168号。表明,在司法实践中,国家机关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虽然较少,但并非不存在。围绕国家机关应否承担刑事责任的理论争议从未停息,2006年的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乌铁中院)单位受贿案更是将这一争议推上了顶峰。⑥2006年7月,昌吉回族自治州中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时,乌铁中院涉嫌单位受贿犯罪成为被告,在国内属首例法院成被告的案例。2006年12月,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变更、补充了起诉书内容,在新的起诉书中,乌铁中院没有成为被告。2007年2月15日,昌吉回族自治州中院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与挪用公款罪对涉案自然人予以定罪处罚,并没有追究乌铁中院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围绕这一案例,众多刑法学者,宪法学、法理学、社会学学者等纷纷投入了争论之中,并形成了肯定论与否定论两大阵营,在如下问题上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立场。
(一)追究国家机关刑事责任是否存在理论依据?
否定国家机关刑事责任的论者认为,追究国家机关刑事责任违反刑事法理。从主观方面而言,国家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宪法规定的管理职能的主体,其在具体活动中体现的是与犯罪意志水火不相容的国家意志,如果国家机关中的个人假借组织的名义集体决策实施犯罪行为,具体行为体现的是个人意志而非集体意志;从客观方面而言,单位的犯罪行为应该由单位决策机构或负责人员的决定行为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实施行为组成,两者紧密相联,缺一不可。而对于“我国国家机关而言,尤其是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司法机关亦存在此种情形)决定者与执行者往往是不一致的,如果强行按照新刑法的规定将之作为单位犯罪来处理,则必然是对犯罪构成理论的悖逆,且造成司法实践中追究刑事责任的困难”⑦胡廷霞:《国家机关作为单位犯罪主体之否定》,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7期(中)。。
肯定论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国家机关也是单位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认为公司、法人等国家机关以外的单位具有自己的意志能力,当然也应该承认国家机关的意志能力。虽然国家意志与犯罪意志不能共存,但是当国家机关集体决策实施犯罪行为之际,体现出来的已经不是国家意志,而是犯罪意志。“犯罪意思与国家意志不能并存的观点正好说明了国家机关为什么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理由。”⑧马克昌:《“机关”不宜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5期。而且,国家机关符合犯罪单位的所有要件。单位要成为犯罪主体,必须具备合法性、组织性、有一定的经费和财产以及有一定的独立性四个特征。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我国国家机关是具备如下特征的法人:依法设立、根据国家编制有本机关的工作人员、拥有国家拨款作为独立的经费以及根据法律规定行使国家权力和从事实现国家职能的活动,具备单位犯罪主体所必须具备的所有特征,能够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⑨郭建华:《国家机关应该成为犯罪主体》,载《宜宾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二)追究国家机关刑事责任是否有国外先例可循?
否定论者继而认为,我国的单位刑事责任是效仿国外,尤其是英美国家的法人刑事责任规定的。国外学者在论述法人的犯罪能力与刑事责任之际,首先是论述法人的本质,并提出了法人拟制说、法人实在说、法人超越说等不同观点,但是“西方学者论述的法人本质,都是就公司、法人而言的,所以西方国家刑法规定的法人犯罪,仅限于公司、法人犯罪,而不包括国家机关。我国规定国家机关为单位犯罪的主体,既无西方国家的理论可以借鉴,事前在学理上也未很好地进行研究,因而可以说我国刑法的这一规定缺乏理论根据”⑩马克昌:《“机关”不宜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21期。。与此同时,主张允许司法机关追究国家机关刑事责任就是允许司法权干预行政权,在国外立法中不存在立法先例,“从国外的立法来看,英、美无国家机关犯罪的规定;德国不承认法人犯罪;法国虽然承认法人犯罪,但是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不可能构成犯罪;日本在行政刑法中规定了法人犯罪,但也没有国家机关犯罪的规定。从法理上讲,国家行政权平行于司法权,两权不能互相干预。司法机关宣布行政机关构成犯罪,实际上就是干预行政权的表现”⑪贾凌、曾粤兴:《国家机关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载《法学》2006年第11期。。
肯定论者则认为,关于法人本质的探讨主要存在于民商法律之中,无论法人的本质是什么,国外立法在肯定法人刑事责任之际,就是已经肯定了法人的犯罪能力,将之放在了与自然人同等的地位,就如美国法官在纽约中央火车站贿赂案中所言:“法律应该尊重包括自然人与法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权利,但是,不能对绝大部分的商业活动,尤其是州与州之间的商业活动由其所控制的事实视而不见,如果因为法人不能犯罪这一腐朽而又陈旧的原则而赋予它们刑事豁免,实质上就是剥夺了唯一能够控制它们、纠正违法的有效工具。”⑫Osvaldo Vazquez (2007).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Corporate Criminality,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978883, p118.也正是基于这一政策追求,在国外的制定法中,近年来已经出现了许多追究国家机关刑事责任的立法例。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英国2007年开始实施的《法人过失致人死亡罪法》(Corporate Manslaughter and Corporate Homicide Act 2007)明确规定,公司、协会、行政机构、警察机关、皇家组织都可以实施该法规定的犯罪,并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议会的解释,可以根据2001年通过的《(工作场所死亡与严重伤害)犯罪法》(Crimes(Workplace Deaths and Serious Injuries) Bill 2001)追究行政机关的责任。在联邦层面,2012年,作为澳大利亚中央金融主管机构的联邦储蓄银行的两家分公司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011年7月之间大肆向东南亚的政府行贿,被联邦法院认定有责。2004年3月31日生效的加拿大C-45号法令也将刑事责任扩展到了所有的“组织”,包括公共组织、公司、社团、工会、地方政府。⑬Zhenjie Zhou (2014).Corporate Crime in China: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London: Routledge, pp.79-80.
虽然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国家接受法人刑事责任的时间较晚,但是,也已经出现了规定国家机关刑事责任的立法例。1994年开始实施的法国新刑法典第121-2条明文规定,除了国家以外,法人可以实施犯罪。这里所谓的“法人”,既包括公司、协会等私法法人,也包括公法法人,即国家以外的地方共同团体。而且,在1997年出现过地方政府因为管理河流不善,导致郊游儿童溺亡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判例。⑭ジャン=ポール·セレ「フランスにおける法人の刑事責任の展開」企業と法創造第3巻第4号(2007)37页。1996年修改的丹麦刑法典第26条和第27条明确规定,如果国家机关与地方政府像私人与法人那样违反了关于污水处理的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可以对之追究刑事责任。芬兰1995年修改的刑法典规定,除行使公共权力的场合,可以追究公共机构的刑事责任。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德国虽然迄今没有承认法人的犯罪能力,但是为了满足欧盟的要求与自身的规制需要,对于公共团体也是可以给予行政性制裁的。⑮同注⑬,第80页。
(三)国家机关刑事责任是否已经被实践否定?
从司法实践与立法适当性的角度,否定论者认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而司法实践常常否定国家机关的刑事责任。在发生在丹东、烟台、海南等地的汽车走私案中,国家机关无一被追究刑事责任;在乌铁中院受贿案中,法院也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国家机关可以构成单位犯罪的规定一直未予实际执行的事实充分说明它的妥当性值得认真考虑。”⑯同注⑩。而且,认定国家机关有罪会带来许多难以解决的难题:“首先,国家机关依照法律设立并行使权力,自上而下呈网状分布,任何一个机关瘫痪,都会使国家权力的运行受阻。其次,公权力的行使,一靠权力主体自身的权威,二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将国家机关作为犯罪处理,将严重损害国家机关的威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关哪还有威信去履行自己的职能?对一个自身被定罪的法院的审判,谁还会认为是正义的审判呢?”⑰同注⑧。
就立法没有得到严格实施的问题,肯定论者则认为,司法上的操作困难与立法本身的妥当性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立法没有得到严格实施,并不必然说明立法本身的妥当性值得反思,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也可能是因为执法环节之中存在亟待解决的缺陷与问题,或者受到了大环境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立法机关不应该否定立法,而应该采取切实而有力的措施,保证刑法规范在实践中能够得到严格遵守与执行。⑱同注③,第87页。同时,虽然总体而言“机关实施单位犯罪的可能性不高,但是客观上仍然存在着实施单位犯罪的可能性。即便司法实务中只出现少量的机关犯罪,法律规定机关作为单位犯罪的主体也是有必要的。而且,惩罚少量的机关犯罪有利于警醒机关、促进机关自律”⑲王良順:《单位犯罪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国家机关权威的丧失殆尽,不是由于国家机关被规定为犯罪主体进而被追究刑事责任造成的,而是由国家机关的犯罪行为造成的。国家机关的犯罪行为本身给社会造成了危害,如果把国家机关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而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无疑是对社会的二次危害,并且这种危害远远大于国家机关犯罪行为本身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因为它破坏了法律赖以存在的基础,使人们失去了对法律的希望和信心。”⑳郭建华:《国家机关应该成为犯罪主体》,载《宜宾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四)追究国家机关刑事责任能否实现刑罚目的?
从刑罚目的的角度出发,否定论者认为,国家机关不能承受刑罚的后果,对之处罚无益于威慑、预防犯罪,因为“国家机关的任务是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机关进行经济处罚,只能损害机关行使职能的能力,最终损害国家和人民自身的利益,因此必然迫使国家追加对机关的经费支出,这无异于国家把金钱从这个口袋装入另一个口袋,没有实际意义,也达不到惩罚教育的目的,而且有损于国家机关的威信”21左振杰:《论国家机关不能成为犯罪主体》,载《西安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继而,否定论者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国有事业单位同样不能成为单位犯罪主体。事业单位是政府创办的提供教育、科研、文化和卫生服务的专门机构。事业单位的管理者和行政官员并没有实质差别,他们都有一定的级别,都可以在不同性质的单位之间互换职位,都是单位仕途的起点和终点。”22高鹏:《论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单位不能成立单位犯罪——以经济分析法学为视角》,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第4期。既然国家机关刑事责任有害无益,则理应予以废除;为了遏制国家机关实施社会危害行为,对相关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即可。
肯定论者则认为,上述主张其实是老生常谈,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就刑法应否将单位规定为犯罪主体的问题进行争论之际已经被反复提及。当时就有学者主张,鉴于在当时几乎所有法人都是国家与集体所有的事实,国家处罚单位即是在处罚自己,无法实现刑罚的报应或威慑目的,23参见高铭瑄、姜伟:《关于法人犯罪的若干问题》,载《中国法学》1986年第6期。同时,刑罚目的的实现以处罚对象能感触到刑罚之苦为前提,而单位不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生物,不能感觉到刑罚之苦,所以,单位处罚对于处罚、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而言,不但无益而且有害。24参见赵秉志:《关于法人不能成为犯罪主体的思考》,载《法学研究》1989年第5期。但是,一方面,上述论点是在刑法仅规定了罚金作为单位犯罪唯一刑罚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如果增加新的刑罚制度,例如资格刑、社区矫正、单位缓刑等,可以避免否定论者所主张的情况。另一方面,从已经发生的案例来看,国家机关所实施的犯罪大多具有规模大、时间长与利益分散化的特点,实际上是在其内部形成了一种具有违法倾向的环境或者文化,仅仅处罚具体行为人是无法改变这种宏观事实的,而且会给有责的国家机关留下责任外化与降低犯罪成本的途径,例如开除具体行为人或者宣布其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从犯罪预防的角度出发,也需要对国家机关这个整体予以谴责与制裁。25See Zhenjie Zhou, Corporate Crime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15, pp.98-101.
(五)追究国家机关刑事责任是否存在宪政障碍?
最后,否定论者认为,将国家机关规定为犯罪主体,将引起宪政上的难题,因为“根据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相应的最高国家机关对外代表国家,对内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管理国家事务与行使国家司法权等。让他们成为犯罪主体并承担刑事责任,与其所承担的角色完全不相符,也会使相应的国家机关和人民群众都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即使是地方国家机关成为犯罪主体,也是极其荒谬的,某个地方的人民可以处于被自己的国家所认定为犯罪的人的行政管理、司法管制之下吗?犯罪人可以管理普通公民吗? 犯罪人如何以及应否行使国家权力? 这是否会产生严重的宪政悖谬? 这一系列问题,必将使单位特别是国家机关作为犯罪主体的刑法规定产生逻辑上、宪政上的难题,……(只要规定了国家机关刑事责任),无论是否将国家机关作为犯罪主体来进行惩处,都会导致一系列的宪政悖谬,都会导致进退两难的尴尬困境与难以言说的困窘。”26朱建华:《单位犯罪主体之质疑》,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30卷第1号。
肯定论者则反驳认为,虽然根据宪法规定,国家机关必须依法行使职能、从事管理工作,但是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不得将国家机关规定为犯罪主体,同时宪法也对国有法人、行业协会、各类学校等作了规定,这些机构无疑也应依法办事。如果将国家机关规定为犯罪主体会带来宪政上的难题,那么将国有法人、高等学校等规定为犯罪主体,也同样会带来宪政上的难题。如果我们不能接受犯罪人的行政管理,难道我们就能接受犯罪人管理我们的财产、给我们提供教育吗?此外,我国的工会、妇联、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在实质上也承当了部分行政管理职能,如果国家机关的犯罪主体资格应该予以否定,这些团体的犯罪主体资格也应该予以否定。而关于国有法人、学校、社会团体等单位能够构成犯罪主体,目前几乎没有从宪政角度提出的否定意见。因此,追究国家机关刑事责任并不会引起宪政难题。27同注③,第87页。
三、否定论与肯定论之评析
在对国家机关刑事责任否定论与肯定论的论据评析之前,必须明确如下事实:第一,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单位刑事责任并非传统刑法理论的自然演绎,而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在19世纪以前,与大陆法系国家一样,英美国家也都基于对法人难以进行道德谴责、法人难以出庭作证、法人对社会生活影响不大等理由否定法人刑事责任。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化向英国全国扩展,英国法院被迫面对大量铁道公司的污染环境等违法行为。为了应对这种局面,英国法院不得不改变立场,认为能够基于不作为对法人提出刑事控诉,就如有的观点所言“:法人已经通过各种方法进入了大部分市民以及其他社会主体的私生活,如果继续让法人享受免责特权,可能会给公众带来危险。”28Guy Stessens(1994),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43: 493-494.1838年的Regina v.Tyler案更是直接表明了“采纳刑事责任是规制法人行为最有效的途径”的态度。29173 Eng.Rep.643 (Assizes 1838).与此类似,“美国法院与立法机关一直在不断地修改法人的法律地位,以应对社会与司法需要。在19世纪初期,这些需要促使法院赋予了法人以自由,后来又促使法院试图将之纳入控制之中,法院所拿起的武器就是刑法”,30Osvaldo Vazquez (2007),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Corporate Criminality, at http://ssrn.com/abstract=978883, p4.因为“仅仅起诉个人不仅是不公正的,也是无效的。即使对法人官员的控诉得以成功,也很难对法人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对一个法人而言,其组织结构的缺陷不会因为成员被审判而消失”31See Guy Stessens(1994).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43, pp.518-19.。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通过修订海关法规定单位犯罪,同样是因为受到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的单位所实施的走私、偷税、污染环境等犯罪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就如有的观点所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关于法人的问题在实务界与理论界都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在经济法、民法以及行政法中已经存在规制法人活动的法规定,但是刑法中尚不存在相应的规定,这是我们研究的弱点所在。”32陈泽宪:《论法人犯罪的刑事法律问题》,载《政治与法律》1985年第6期。
第二,从立法的角度而言,单位在民商、经济法律中被赋予了与自然人相同的主体资格,刑法中的单位与民法中单位的构成要件相同,与自然人一样享有各种权利,其名誉权、财产权等也平等地受到刑法的保护。例如,根据《刑法》第221条之规定,如果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侵犯单位名誉权的行为构成损害商业信誉罪;根据《刑法》第396条之规定,通过私分的形式侵犯国有单位财产的行为,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国家机关作为刑法明确规定的单位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也享受上述权利。既然能够享受刑法上的权利,当然也就能够承担刑法规定的不利后果。
第三,从司法实践中违法事实发生→确定有责个人→处罚相应单位的逻辑出发,可以认为我国的单位刑事责任是以个人刑事责任为基础的,这类似于美国的代理责任(Vicarious Liability)与英国的等同原则(Identification Principle)。这其实是传统刑法理论与现代刑事政策的折中选择:以个人刑事责任为基础,符合了传统刑法理论对个人责任与道义责任的强调;处罚单位,满足了通过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方法预防与打击单位违法行为的政策要求。这一逻辑也表明,我们目前并没有真正将单位刑事责任融入到刑法理论之中,只是以个人刑事责任为基础作了变通规定。33这可能也是刑法在许多问题上缺少一贯立场的原因所在。例如,根据《刑法》第200条的规定,单位可以实施第192条规定的非法集资罪、第194条规定的票据诈骗罪与金融凭证诈骗罪以及第195条规定的信用证诈骗罪,那么,为什么单位不能实施贷款诈骗罪(第193条)与有价证券诈骗罪(第197条),这两个罪名与上述三个单位犯罪的罪名同样规定在第三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侵犯的客体相同,主观方面都是故意,客观方面也都是采取欺诈的方法骗取金融机构。同时,既然单位可能实施特殊法条规定的票据诈骗罪等,为什么不能实施一般法条规定的诈骗罪?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说单位刑事责任是传统刑法理论的有益补充,不如说其是后者肌体上的伤痕。同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刑法理论接受单位刑事责任的被动性。
基于上述事实,从肯定论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单位刑事责任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包括国家机关在内的单位违法行为不但是存在的,而且其危害性是值得发动刑罚的,就如有的观点所言:“一方面,机关并不总是能正确行使国家职能,当地方主义、本位主义作祟时,机关活动就可能脱离其正常轨道而违法犯罪;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大潮下,机关一旦抵制不住诱惑而难守清贫时,其所掌握的权力更为其非法谋利提供直接便利,从而构成违法犯罪。”34张目:《单位犯罪的理论与实务》,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8年第2期。所以,国家机关刑事责任具有实践基础。同时,因为国家机关刑事责任是以其成员的个人责任为基础的,符合传统刑法理论对主客观构成要件的要求,也是具有理论基础的。此外,因为单位刑事责任是参考外国立法制定的,既然现在国外也有立法先例可循,国家机关刑事责任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传统刑法是以个人刑事责任为假想对象的,所以刑法仅规定了罚金作为对单位的处罚,而这是不科学的,应该对单位处罚予以多样化与灵活化;既然对国家机关之外的国有单位进行处罚不违反宪政,符合刑罚目的,对国家机关进行处罚亦是如此。
与此相似,从否定论的角度出发也可以合理地认为,即使国家机关的某些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刑法必须介入,因为刑事责任是刑法的核心内容,刑事责任是以道义主义与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而国家机关作为人的集合与法律的拟制没有自己的故意与过失。同时,既然国家机关刑事责任也是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破坏刑法基本原则对之进行处罚就没有必要,因为处罚有责个人完全可以满足刑罚目的。此外,正是因为刑法强调的是个人责任与道义责任以及国家机关的特殊地位,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国家机关的刑事责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许多案件都是如乌铁中院受贿案一样以处罚直接责任人员而告终。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没有得到贯彻的法律是没有生命的。因此,应该废除国家机关刑事责任。
可见,国家机关刑事责任肯定论与否定论都非空穴来风,各有合理之处,并都能在理论与实践中找到根据。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肯定论是以刑事政策与现实立法,否定论是以传统刑法理论尤其是责任理论为基础,两者的出发点与立足点都是不同的。如上所述,在很大程度上,国家机关刑事责任不是传统刑法理论能解决与解释的,因为其并不是后者自然演绎的产物,而是政策与立法的现实选择。所以,此处的问题不是应该肯定还是否定国家机关刑事责任,而应该是从政策与立法的角度出发,肯定论与否定论之间是否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我们是否必须且只能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以及肯定论或者否定论的观点是否应该完全被接受,或者应该完全被拒绝?答案都是否定的。无论是肯定论还是否定论,都忽略了如下两个基本问题:
其一,国家机关内部是存在区别的。在理论上,就《刑法》第30条中规定的“机关”存在着广义论与狭义论的分歧。广义论认为,在立法没有明确限制的情况下,此处的国家机关应根据《宪法》第三章的规定理解,指以国家预算拨款作为独立活动经费,从事国家管理和行使权力等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组织,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审判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国家军事机关等。与之相对,狭义论认为,此处的“机关”在广义上包括国家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军队、政党等,但国家立法、司法等机关不可能成为单位犯罪主体,所以“机关”应作狭义理解,仅应指地方国家行政机关。35同注⑩。从立法的角度而言,根据《宪法》第三章的规定来界定国家机关范围的主张无疑是恰当的。从该章的规定出发,可以将国家机关分为两类:代表国家的机关,根据宪法与法律行使职权、履行职务的其他国家机关,前者代表国家实施国防、外交、立法等国家行为,后者根据宪法与法律的授权行使具体权力,两者之间存在着实质的区别。
其二,国家机关行为的内部也是存在区别的。例如,从行为主体身份出发,可以将国家机关的行为分为两类:以行使宪法与法律赋予职权的管理者身份实施的权力行为,如颁布各类法律法规、制定治安政策、实施社会管理活动等,与以平等的民事主体身份实施的旨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权利行为,如进行公共采购、管理公共财物。前者又进而可以根据行为对象分为针对不特定管理对象的抽象权力行为与针对特定管理对象的具体权力行为。具体权力行为又可以根据管理相对人的不同,分为针对特定国家机关成员之外的人所实施的权力行为,与针对特定国家机关内部成员实施的权力行为。前者如行政机关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实施行政拘留、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警告,后者如行政机关根据《公务员法》对工作人员进行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等。这些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当然应该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
四、国家机关刑事责任限制论之提倡
从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行为的内部区别出发,对于国家机关刑事责任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与否定,而应该寻找合理的标准,对之进行适当的限制,以在保证国家机关自身权威的同时,有效地预防其在社会生活中可能实施的违法行为,推动刑法规范的贯彻实施。
(一)限制国家机关刑事责任的理由
应该限制国家机关刑事责任的理由,首先,存在于国家机关本身。在理论上,根据现有刑法规定,可以追究包括代表国家的机关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的刑事责任,而追究代表国家的机关的刑事责任,就是追究国家本身的刑事责任。虽然从都是人的集合这一点而言,国家与其他组织具有实质的相似之处,但是迄今为止,国家刑事责任在国际法上仍然是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问题。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争论,始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负责调查破坏战争规则罪行特别委员会曾在一项报告中指出:“德国及其同盟国违反明确制定的规范,以及不容争辩的惯例和人道主义的明显要求,犯下了无数的滔天罪行。”36转引自钱晓萍:《国家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理论争鸣与发展研究》,载《时代法学》2014年第4 期。自此,国际社会掀起了讨论“国家国际犯罪及其国际刑事责任”以及建立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热潮。
在理论上,许多学者都坚持认为国家能够犯罪,尤其是对国际社会危害程度最强烈的犯罪,都是由国家实施或在国家支配下实施的。要想从根本上遏制国家的国际犯罪,必须追究国家的刑事责任。37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外文文献,See Allain Pellet, Can A State Commit A Crime? Definitely, Yes! EJIL, Vol.10, No.2, 425-434;中文文献,参见王虎华:《国家刑事责任的国际法批判》,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年第4期;蒋娜:《国际法视野下国家刑事责任的可能与局限》,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2期。例如,1985年发生在新西兰的著名的彩虹勇士号(Rainbow Warrior)案件中,38彩虹勇士号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所属船只,活跃于各种抗议活动。1985年7月10日,在该船从新西兰的奥克兰港启程去法国抗议核试验之际,被法国特工炸沉。在实施犯罪行为的特工被新西兰法院判处有罪之后,绿色和平组织与法国政府达成协议,将该案交由国际仲裁。仲裁的结果是法国应该向绿色和平组织承担赔偿责任。有的观点明确认为,法国应该被视为国家恐怖主义组织。39Harding, C.(2007).Crime Enterprise, Portland: William Publishing, p135.所以,国家刑事责任获得了非常强烈的理论支持。40See Huls, V.(2002).State Criminal Liabilit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Filling the Justice Gap in the Congo, at www.lawanddevelopment.org/docs/justicegapcongo.pdf(accessed 12 July 2015).为了避免实践中的困境,有的学者提出了以“政府犯罪”代替“国家犯罪”的建议,并认为“在国际法层面,政府行为通常归于国家行为,所以政府犯罪被视为国家犯罪。然而国家犯罪较普通国际犯罪有更严格的判断标准,只有基于政府行为或在政府渎职的情势下才能实现;反之政府犯罪可能因政府行为违反法律,严重伤害本国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而超越国家犯罪,独立存在,所以‘政府犯罪’包含‘国家犯罪’”。41钱晓萍:《“政府犯罪”对“国家犯罪”的替代性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 年第9 期。这其实是变相地主张国家能够成为犯罪主体。
但是,在国际审判实践与国际法文件中,国家刑事责任从未得到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为审判战争罪犯而设立的纽伦堡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虽然控方同时提出了个人刑事责任、组织(或团体)刑事责任及国家刑事责任,并特别指出,国家犯罪比个人犯罪更加可怕,国家对其犯罪行为负责并不是创新,但是特别法庭最后都以国家是抽象实体,受国家主权保护为由,避开了国家刑事责任问题,只让个人承担刑事责任。1948年制定《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87年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1996年一读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文草案》等国际文件都绕开了国家的刑事责任问题;2002年开始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也明确将国家排除在了刑事责任主体之外,该公约第1条明确规定,国际刑事法院“为常设机构,有权就本规约所提到的、受到国际关注的最严重犯罪对个人行使其管辖权”。因此,我们应该对国家机关范围进行限制,避免给外界我国立法已经承认国家刑事责任的印象。
其次,应该限制国家机关刑事责任的理由在于刑法的谦抑性。刑法的谦抑性,在立法阶段,指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其他适当方法可以代替刑罚之即,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刑法应该坚持谦抑性的主要原因,在于“刑罚是达到目的的工具,但是,目的观念要求工具符合目的,并在其使用中尽可能地缩减,因为刑罚是双刃剑,它通过损害法益来保护法益”。“在现代刑事政策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最终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在与犯罪作斗争中,刑罚既非惟一的也非最安全的措施。对刑罚的效能必须批判性进行评估。”42[德]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所以,只有当一般部门法不能充分保护某种社会关系时,才动用刑法来保护;当一般部门法不足以抑制某种危害行为时,才动用刑法来禁止。或许也正因如此,卢梭才会认为“刑法在根本上与其说是一种特别的法律,还不如说是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4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3页。。
从刑法的谦抑性出发,在决定应否以及如何追究国家机关刑事责任之际,应该考虑区分如下三种情况:(1)其他法律并未就某一行为的法律责任进行规定;(2)其他法律已经排除了某一行为的法律责任;(3)其他法律规定了某一行为的法律责任。在第一种情形下,即从刑法二次法、补充法与保障法的性质出发,不宜直接追究该行为的刑事责任。在第二种情形下,也不应追究该行为的刑事责任,因为如果不能追究某一行为的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当然也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主席等代表国家的机关,其根据宪法与法律实施的涉及国防、外交事务行为属于国家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3条已经明确将国家行为排除在了行政诉讼的范围之外。对于此类国家机关行为,当然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在第三种情形下,从刑法保障法的性质出发,在相应法律不足以制裁该行为的情况下,可以将之纳入刑事处罚的范围。
第三,刑法的任务是应该限制国家机关刑事责任的又一理由。考虑到刑罚的严厉性,刑法的任务应该限定于保护法益,即将犯罪限制于侵害法益的行为与导致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这已经成为理论上的共识。我国《刑法》第2条也明确规定,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国家机关实施的某些行为,如制定法律法规、发布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或者命令等抽象权力行为,不会侵害到具体法益,或者导致具体的危险。正因如此,《行政诉讼法》将司法审查的对象限定于具体行政行为,该法第2条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12条对此处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了列举,第13条继而将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范围之外。所以,从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出发,不加区分地将所有国家机关行为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也是不恰当的。
最后,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也应该限制国家机关的刑事责任。在已经明确规定了国家机关刑事责任的国家,立法也都对之进行了一定限制。例如,《法国刑法典》虽然规定了机关法人的刑事责任,但是在第121—2条第2款要求,地方行政部门及其联合团体只在犯罪行为发生在其实施可以签订公共服务委托合同的活动时,才承担刑事责任。也即“地方国家机关的刑事责任并不具有全面性,仅限于与权力活动无关的行为,即受公法人或者私法上的法人委托的行为(例如垃圾回收、泳池管理、公共运输行为以及学校食堂管理行为等),……在公法上的法人根据管理委托,或者通过合同形式接受委托而行为的场合,可以追究公法上的法人的刑事责任。与公权力相关的事项(例如一般的警察活动),并不在刑事责任的范围之内。”44ジャン=ポール·セレ「フランスにおける法人の刑事責任の展開」企業と法創造第3巻第4号(2007)37页。“法国立法者如此规定的主要逻辑在于:地方行政部门管理地方财政的行为属于私法领域的活动,此时他们应当承担与私法法人相同的责任;但是,在地方行政部门进行其公共权力专属性的活动时,即可免除刑事责任。”45陈萍:《法国“机关法人”刑事责任述评及其借鉴》,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11期。英国的2007年《法人过失致人死亡罪法》第1条也是通过“具体义务”要求,对国家机关的刑事责任进行了限制。根据该条规定,只有具备以下两项条件,才可以追究包括国家机关在内的法人的刑事责任:第一,导致了死亡结果;第二,相关组织严重违背了对被害人所承担的注意义务。同时,该法第3条第1款明确规定,在有关公共政策事项的决定之中公共机关所承担的注意义务,尤其是在资源分配以及在衡量具有竞争关系的公共利益的场合,并非本法所规定的注意义务。46参见英国司法部官方网站:http://www.justice.gov.uk/publications/corporatemanslaughter2007.htm。另言之,虽然可以根据该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国家机关的行为,但是仅限于违反具体义务的行为。上述芬兰刑法典也是将国家机关刑事责任限定在了非行使公共权力的场合。
那么,应该如何限制国家机关的刑事责任呢?
(二)限制国家机关刑事责任的途径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从国家机关本身及行为两个角度对其刑事责任进行限制。第一,限制可以承担刑事责任的国家机关的范围,将可以代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象征的国家主席与副主席以及行使最高行政权力的中央政府等排除出单位犯罪的主体范围。因为追究这些国家机关的刑事责任,就等于追究国家的刑事责任。所以,建议立法机关在《刑法》第30条中增加一款,明确规定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等代表国家的机关不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限制实行行为的范围。首先,就国家机关实施的权利行为,因为是发生在平等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设立、变更、终止过程中,与行使国家管理职权无关,如国家机关购买服务、物品以及委托他人从事管理工作等,如果在此过程中国家机关实施了需要以刑法规范予以调整的违法行为,当然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例如,《刑法》第276条之一规定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国家机关也完全可以实施。其次,就制定、发布普遍性行为规范、全国性政策等抽象权力行为,不能够据之追究国家机关的刑事责任,这不仅仅是坚持法益保护主义与刑法谦抑性的需要。而且,如果根据抽象的权力行为追究国家机关的刑事责任,将会严重阻碍其行使宪法与法律赋予的职权,造成管理上的难题与社会秩序的紊乱。最后,就国家机关依据职权实施的有关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具体权力行为,如果符合如下两个条件之一,可以据之追究其刑事责任:(1)相关法律已经规定国家机关应该就特定行为承担行政责任或者经济责任,如《国家赔偿法》第3条规定的5种情形、第4条规定的4种情形与第17条规定的第4种与第5种情形;(2)在具体的权力行为之中,存在具体相对人或者具体法律义务。
所谓“具体相对人”,指因国家机关的具体行为而权益受到影响的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如上所述,国家机关必须依法从事管理活动。因此,如果国家机关超越法律授权,或者以违法的方法展开活动,并因此给相对人造成重大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应该承担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例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有权拘留与逮捕犯罪嫌疑人。同时,根据我国签署的国际公约与现行立法,公安机关与拘留场所的管理机关,非依法律不得侵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与健康权利,而且应该采取合理措施,对之予以妥当保护。如果管理机关或者拘留场所管理机关命令其工作人员殴打、虐待被拘禁者,或者在知情的情况下对其工作人员的上述行为予以放任或者默许,可以根据《刑法》第248条的规定追究拘留场所管理机关虐待被监管人的刑事责任。
同时,在许多场合,尤其是国家机关怠于履行法定义务从而导致重大损失的场合,可能并不存在具体的相对人。针对如此情况,有必要规定即使不存在具体的相对人,只要国家机关违背了其应该承担的具体法律义务,就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8月通过的《水法》第42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本行政区域内水工程,特别是水坝和堤防的安全,限期消除险情。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工程安全的监督管理。”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水利行政部门根据本法管理行为中,可能并不存在具体的相对人。但是,如果相关政府或者主管机关怠于行使管理义务,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可以根据《刑法》第115条的规定追究相应政府或者主管部门的过失决水罪的刑事责任。
五、结语
从实然的角度出发,追究国家机关刑事责任并不存在障碍。但从应然的角度出发,就是否应追究国家机关刑事责任,应该予以具体分析,对于国家机关刑事责任不宜一刀切,应该在原则上肯定国家机关刑事责任的前提下,从行为主体与行为性质两个角度对之进行适当限制,即:对于能够代表国家的机关,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抽象的权力行为,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只能就存在具体相对人或具体法律义务的具体权力行为与权利行为追究国家机关的刑事责任。
此外,本文仅仅论述了国家机关刑事责任中“犯罪”方面的内容,限于文章主旨,并没有论述其“刑罚”方面的内容。从实践来看,仅能适用于犯罪单位的罚金虽然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出发,因为社会成本最低,能够抵消犯罪收益,具有相对优势,但是罚金的缺陷,尤其是溢出效应也不可忽视。因此,在国家机关犯罪的案件中,如何避免罚金的缺陷,将刑罚的预防功能最大化,也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单位贿赂犯罪预防模式研究”(15BFX053)与北京市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北京市企业贿赂犯罪现状与对策研究”(16FXB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周振杰,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