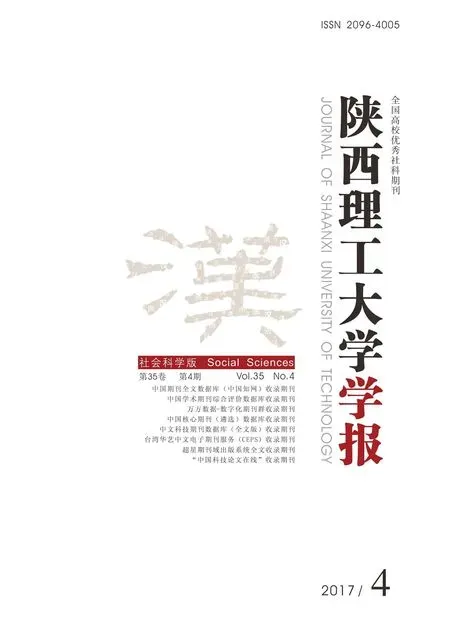阿尔都塞Problematic概念的理解及其多种中译法的选择
潘 志 新
(陕西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阿尔都塞Problematic概念的理解及其多种中译法的选择
潘 志 新
(陕西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problematic是阿尔都塞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可problematic一词有多种中译法,《保卫马克思》和《读lt;资本论gt;》中译为“总问题”,张一兵译为“问题式”,俞吾金译为“问题结构”,冯契、徐孝通主编的《外国哲学大辞典》中译为“问题系”,陈越在《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中译为“难题性”,李智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译为“问题域”,多种中译法的不统一的根源在于对problematic的含义理解上的分歧。problematic是一种提出问题、因而也是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方式,是一个向未来不断敞开的“领域”,与库恩的理性主义的范式概念具有本质上区别,是认识论史上的革命。根据problematic一词涵盖有“不可见的”、“无意识的”等内容并参照夏皮尔的information domain(信息域)的译法,“域”概念是problematic本身所具有的含义,因而选择“问题域”这种译法比较符合阿尔都塞的原意。
Problematic; 问题域; 信息域; 潜意识
problematic是阿尔都塞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1],而这一核心概念中文译名很不统一,有“总问题”、“问题式”、“问题系”、“问题结构”、“问题域”、“理论框架”、“难题性”等多种译法,让许多读者难以理解阿尔都塞的哲学,其根源在于学界对阿尔都塞的problematic概念理解上的差异,而这一问题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本文主要是对problematic概念本身含义进行分析、并将其与库恩的范式(paradigm)概念进行比较,在概念理解的过程中穿插着对这些中文译法的评价。
一、 problematic概念本身的含义
英文problematic由法文problématique而来,是名词probléme的派生形式。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法汉大辞典》中problématique这一词条的解释是这样的,作为形容词有三种意思:“1.成问题的,有疑问的,可疑的,未定的;2.[书]问题的,问题体系的;3.[哲]盖然判断,或然判断。”[2]2803作为名词是指“(科学某个门类所提出的)问题,全部问题,问题体系”。英文中用problematic来翻译problématique这个法语词。在《英汉辞海》中,problematic=problematical,有两类含义,第一类含义又有三种不同的意思“1.(1)成问题的、构成问题或提出问题的;疑难的、难于解决的,难于做出决定的或难于处理的:perplexing使人困惑的,puzzling使人迷惑的lt;a~situation错综复杂的形势gt;;(2)问题多的、问题多得只能做出临时性的或没有把握的解决办法或决定的lt;have arrived at a~impasse陷入难以脱身的绝境gt;。2.不清楚或尚未解决的、全然不明确的:dubious含糊的lt;the future remains~前途未卜gt;。3.有疑问的、值得怀疑或争论的questionablelt;whether we should do it or not is~我们究竟应不应该做还是有疑问的gt;”。第二类含义是逻辑上“盖然的:用以阐述或支持一种可能正确但并不一定正确的假设的lt;a~proposition盖然性的命题gt;lt;~judgments concerning the existence of unicorn and zebras关于是不是存在独角兽和斑马的种种判断gt;”[3]4164。《语言大典》中将汉语中的“问题多的”翻译为:problematic[4]3619。但阿尔都塞在其著作中不是使用problematic这一形容词的本义,而是将这一形容词转化为名词、作为一个特殊概念来使用的,因此根据problematic来翻译肯定不符合阿尔都塞著作中对problematic概念的引申用法和含义。
虽然阿尔都塞早在1948年《论黑格尔思想中的内容概念》中就使用了problematic这个概念,但他并没有对problematic作明确的界定,只是到1960年《论青年马克思》中才对它的作用做了一个描述:“每种思想都是一个真实的整体并由其自己的总问题(problematic)从内部统一起来,因而只要从中抽出一个成分,整体就不能不改变其意义。”[5]48导致很多人都将problematic的这一功能描述看作就是problematic的定义(参见David Mclellan:Marxism after Marx)。不过1976年阿尔都塞在《哲学的改造》演讲中给problematic下的明确定义是:“Philosophy produces a general problematic: that is, a manner of posing, and hence resolving, the problems which may arise.” (“哲学生产一个总的问题域,也就是说生产一种提出问题、因而也是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方式。”)problematic既是“提出问题(posing)的方式”,也是“解决问题(resolving)的方式”。“提出问题的方式”包括产生问题的冲动、思考问题的角度方式和习惯、问题的具体表述、各种问题之间的结构关系,“解决问题的方式”包括问题各种可能的答案和范围以及不可能的答案的界限。因此,problematic涵盖和指代的内容较多,概括起来说,它涵盖和指代了“看得见的东西”和“看不见的东西的结构”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problematic一词涵盖了具体的问题和各种问题之间的结构体系等“看得见的东西”。他说:“What actually distinguishes the concept of the problematic from the subjectivist concepts of an ideal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es is that it brings out within the thought the objective internal reference system of its particular themes, the system of questions commanding the answers given by the ideology.”[6]67中文版的翻译是:“总问题(problematic)的概念与唯心主义地解释思想发展的各种主观主义概念的不同之处,正是总问题(problematic)的概念在思想的内部揭示了由该思想的各个论题组成的一个客观的内在联系体系,也就是决定该思想对问题作何答复的问题体系。”[5]54在这个注释中,“总问题(problematic)的概念在思想的内部揭示了由该思想的各个论题组成的一个客观的内在联系体系,也就是决定该思想对问题作何答复的问题体系。”这是problematic一词涵盖和指代的“看得见的东西”。
另一方面,problematic一词还涵盖和指代了“无意识的”、“看不见的东西的结构”等内容。他说:“This investment of knowledge,conceived as a real part of the real object,in the real structure of the real object,is what constitutes the specific problematic of the empiricist conception of knowledge. Once this has been firmly grasped in its concept, we can draw some important conclusions which will naturally go beyond what this conception says,since it will give us a confession of what it does while denegating it.”[7]38中文版的翻译为:“把被理解为现实对象的现实组成部分的认识纳入这一现实对象的现实结构,这就构成了经验认识论的特殊的总问题(problematic)。只要从概念上牢牢把握这个总问题(problematic),就可以得出重要的结论。这些结论当然超出了这个概念所表达的东西,因为我们从这个概念得到了它只是在否定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才真正承认的它所做的事情。”[8]27在这句话中,阿尔都塞明确地指出problematic“在否定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才真正承认的它所做的事情”,作者紧接着说的话涉及到problematic的实质内涵,他说:“我在这里不去探讨这些结论。这些结论,特别是涉及看得见的东西和看不见的东西的结构时,是很容易阐明的。关于这种结构,我们已经预感到了它的某些重要性。我只想顺便指出,经验主义的范畴是古典哲学总问题(problematic)的中心。在总问题(problematic)的各种变化形式上,包括在它的无声的和否定的变化形式上对总问题(problematic)的再认识,会给哲学史的草图提供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对于这一时期概念的建立是重要的。这个被18世纪洛克和孔狄亚克所承认的总问题(problematic),尽管极其矛盾,却深深植根于黑格尔的哲学之中。基于我们在这里所分析的理由,马克思不得不使用这个总问题(problematic)来思考他已经生产出其结果的那个概念的空缺,以便提出问题即这个概念,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分析中已经对这个概念作出了回答。马克思在利用这个总问题(problematic)的术语(现象和本质,内在和外在,事物的内在本质,表面的运动和现实的运动等等)的同时颠倒、改变并在事实上改造了这一总问题(problematic),不过这一总问题(problematic)在马克思之后仍然存在着。我们在恩格斯、列宁著作的若干地方看到了这个总问题(problematic)。”在这段话中,problematic包含一些“看得见的东西和看不见的东西的结构”,也就是说problematic包含一些能够用语言文字表达的看得见的东西,这实际上是显意识中思考的东西;还包含一些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看不见的、“无声的”东西,这实际上是潜意识中的东西。他说:“哲学家一般并不思考总问题(problematic)本身,而是在总问题(problematic)范围内进行思考。”[5]56“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历史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严格表述所不可缺少的理论(哲学)概念的产生:尚未以概念形式存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哲学概念的产生。”[8]169“确认在哲学史中存在哲学事实,存在着其有历史意义的哲学事变,也就是那些能够使现存的哲学结构关系即现存的理论总问题(problematic)发生现实变化的哲学事实。当然,这些事实并不总是能够看到的,更有甚者,它们有时竟成为真正的倒退现象,成为较长时期内真正的历史退化现象。”[9]90这就使problemetic概念所涵盖和指代的内容非常复杂了,它涵盖了意识和无意识两大领域,作为形容词的problematic“成问题的,有疑问的,可疑的,未定的”就表述了这两层含义:既有明确的问题,还有不明确的在潜意识中的东西。并且“在总问题(problematic)的各种变化形式上,包括在它的无声的和否定的变化形式上对总问题(problematic)的再认识,会给哲学史的草图提供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对于这一时期概念的建立是重要的”。说明problematic可以推演出一些看得见的明确的原则,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可以形成一些基本概念,利用这些基本概念可以建立一个哲学体系,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在改造黑格尔的problematic中建立起来的。他说:“也就是说,没有意识到业已存在但未被承认的总问题(problematic),而这个总问题(problematic)却在思想的内部确定着各具体问题的意义和形式,确定着这些问题的答案。因此,一般说来,总问题(problematic)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它隐藏在思想的深处,在思想的深处起作用,往往需要不顾思想的否认和反抗,才能把总问题(problematic)从思想深处挖掘出来。”[5]56因此,“问题系”、“理论框架”、“问题结构”和“问题框架”几种译法显然不能让读者从中文译文中读出problematic概念还隐含着这么多具有生成性的无意识的东西。
二、 problematic概念与库恩“范式”(paradigm)概念的区别
problematic在每一种思想的内部将这种思想统一起来,“只要从中抽出一个成分,整体就不能不改变其意义。”[5]48阿尔都塞在这里所说的原则,就近似于库恩的“范式(paradigm)”的概念:“‘范式’(paradigm)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9]293所以,范式“是指某一科学家集团围绕某一学科或专业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他们有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科学传统,规定共同的发展方向,限制共同的研究范围”。[10]530它有一些共同的信念、核心的原则,在这些原则下形成一些基本概念,并形成一个思想体系。因而张一兵将problematic译为“问题式”,既考虑到problematic作为形容词的本义,又兼顾了库恩的“范式”概念,克服了“问题系”、“理论框架”、“问题结构”和“问题框架”几种译法的不足。“问题式”的译法表明了problematic的内部结构不是一个简单的“框架”、“结构”或“系列”,而是有着内在关联和层次性的有机生成系统。
但是,阿尔都塞的problematic概念实际上与库恩范式概念并不一样,它们之间的不同表现在:
首先,库恩的范式(paradigm)概念是1959年[11]VIII提出来的,1962年《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1965年7月13日国际科学哲学大会开始讨论库恩的“范式”概念时,其影响逐渐传开。而阿尔都塞的problematic概念是1948年在他的求职资格论文《论黑格尔思想中内容概念》中就正式提出[11]111,随后在1959年的《孟德斯鸠:政治和历史》、1960年的《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等正式出版的文章中连续应用。1964年前《保卫马克思》中7篇文章全部以单篇文章的形式正式发表,1965年汇集成册出版,献给他的亡友马丹(Jacques Martin),并产生广泛影响。可见,阿尔都塞的problematic概念比库恩的范式(paradigm)概念提出的时间早,且problematic概念的公开出版也比库恩的范式(paradigm)早三年。但由于阿尔都塞的求职资格论文在其生前并未公开发表,死后才于1997年正式出版,且由于科技理性的强势地位和西方社会对左派的偏见,阿尔都塞的problematic概念从一开始只在左派等有限的学术圈子里流传,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其次,阿尔都塞本人是一名哲学家和人文学者,他提出problematic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哲学范畴,因此阿尔都塞的problematic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而且适用于自然界、“革命”和社会,还是一个认识论范畴,适用范围要比库恩的范式(paradigm)要广得多,而不像库恩的范式(paradigm)那样,只是一个科学领域中的概念。不过由于库恩范式概念的影响大,后来人们渐渐将这一起源于科学领域中概念推广和扩展到了人文社科领域。但毕竟不是一个哲学概念,一旦扩展到人文领域,范式的内容就模糊不清了,尤其是科学自近代以来能够稳步发展,而哲学却在原地打转、成为堆满死人尸骸的战场(康德语),甚至各种哲学终结论不断涌现,科学的范式是否和哲学中的范式是一回事?否则两者的命运和前途为何如此迥异?这就需要引进范式概念的哲学理论重新界定它。而阿尔都塞的problematic范畴在哲学和科学上的内涵是一致的,阿尔都塞早就明确宣布科学是“整个当代思想中最大的丑闻”[12]348,认识和对象之间是隔着“栅栏(grid)”[7]21和“间隔(dislocation)”[7]17的“症候阅读”,读者不能仅看作者写出来的表层文字,而是要将这些表层文字看作是弗洛依德精神分析意义上的“症候”,起决定作用的是在这些表层症候(如文字、笔误等)下面的、精神分析患者和文章作者等本人无法感知和反思的潜意识,因为它们没有上升到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层次。前面我已经引用过:“哲学家一般并不思考问题域本身,而是在问题域范围内进行思考。”“总问题(problematic)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它隐藏在思想的深处,在思想的深处起作用,往往需要不顾思想的否认和反抗,才能把总问题(problematic)从思想深处挖掘出来。”但潜意识却决定着意识,精神分析师和读者必须采取“症候阅读”的方法理解表层症候下面的problematic,才能理解患者和作者。虽然潜意识(如心率跳动、膝关节反应等潜意识控制行为)属于人体机能,但由于人无法自觉到和反思自己的潜意识,因而不能构成意识和反思的主体,所以阿尔都塞认为认识无主体[14]62。因此,“症候阅读法”和理性主义的主客二分框架内的认识和对象相符合的科学观是南辕北辙的,是认识论史上革命。因而从范围上说,库恩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范式”加上“人文科学的范式”之和才等于阿尔都塞的problematic的范围,并由此导致了阿尔都塞的problematic概念和库恩的范式(paradigm)概念的第三个也是它们之间最根本区别。
最后,阿尔都塞的problematic概念和库恩的范式(paradigm)概念最根本的区别是:它们两者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库恩的范式(paradigm)概念虽然包括了人们的信念、习惯等要素,有“韧性”,但是他是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提出来的,本质上属于经典科学、理性主义的范畴,人们的信念、习惯等非理性因素在库恩那里是隶属于理性的,是理性的组成部分,不具有复杂性、不可回溯性等复杂科学的特征。虽然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但范式是确定和稳定的,甚至成为划分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哲学类型的标准。而阿尔都塞的problematic概念本身属于哲学概念,problematic有一半属于非理性、无法认识、不可见的,不属于理性主义范畴,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它不仅包括库恩“范式(paradigm)”中的原则概念等思想性的东西和在这些原则信念下形成的研究者、研究手段、实验工具等科学共同体,而且包括研究问题、潜意识的或者思想中无意识的内容以及环境中的因素,这就比库恩的范式范围要广。在目前法国中学哲学课程中,每位写论文的中学生都必须陈述自己论文的problématique。因此,阿尔都塞的problematic是一个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相结合在一起的整体,它“揭示了由该思想的各个论题组成的一个客观的内在联系体系,也就是决定该思想对问题作何答复的问题体系。”[5]54Note*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and the Spontaneous Philosophy of Scientists amp; Other Essays. Edited by Gregory Elliot. London,New York: Verso. 1990(259).我在《阿尔都塞的有机理性思想初探》一书的初版中,引用菲兰达·纳威诺(Fernanda Navarro)在 Philosophy and Marxism 的访谈中转述的、经过阿尔都塞本人的审阅和修改、并同意发表的problematic定义:“Philosophy produces a general problematic: that is, a manner of posing, and therefore resolving, any problem that may arise.” 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87. Translated by G.M. Goshgarian. London,New York:Verso. 2006(287).与这里阿尔都塞自己的定义几乎一样。“理论实践、科学性、problematic(它也许间接地来自于海德格尔的Problemstellung,什么时候把它和德勒兹和福柯problematisation的比较一下将会很有意思的)等概念完全有权属于它,且它并不被认作各种观念或思想本身的系统统一体,而是被认作概念具体可能性的系统统一体。”[5]viii-ix海德格尔的problemstellung意思是“问题的提出”,是1919年海德格尔在弗赖堡大学授课过程中提出,是指通过向历史和传统提问以获得“前理论、前世界的‘东西’”的直观体验的对话过程,通过这种对话揭示历史寓含的哲学观念,是一种揭示原初科学的“形式显示”的方法。巴里巴拉说阿尔都塞的problematic“也许间接地来自于”海德格尔的problemstellung(“问题的提出”),但阿尔都塞的problematic不同于海德格尔的problemstellung(“问题的提出”)的地方是,problematic实际上是某一学科或领域中的所有的东西,是理性和非理性集合在一体的有机复合体,而不仅仅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方法”。problematic超出了传统理性的范围,其实质是“有机理性”[14],只不过没有恰当的称呼,所以“阿尔都塞创造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工具群体”[5]viii,虽然形式上有点像库恩的“范式”,实质上要比库恩的“范式”更先进、更符合当代复杂性科学的实际。problematic涵盖的这些非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内涵是“问题式”这一译法所无法表述的内容。看到“问题式”这几个字,读者想到的是problematic是一种模式、方式或范式,一种成形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的东西,不会与非理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联系在一起。因此,陈越在《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中将problematic译为“难题性”,就克服了“问题式”这种译法的理性主义倾向和不足。但是,“难题性”这种译法只是某种特性描述,不能表述problematic所包含的具体问题及结构的内涵。
总之,《保卫马克思》、《读lt;资本论gt;》的“总问题”译法太笼统、空洞,不能包含“问题的结构、模式”和“产生问题的无意识”;冯契主编的《外国哲学大辞典》中译为“问题系”[15]331是根据problematic的本义来翻译的,但是,辞书中的本义不是阿尔都塞在文中使用problematic的意思;徐崇温的“理论框架”、张一兵建议译为“问题式”,俞吾金译为“问题结构”,陈学明的“问题框架”等翻译将problematic一词理解为近似于库恩的“范式”一词了,强调了问题的模式、范式和框架,不能概括“问题的定位”、“产生问题的无意识”,和“概念具体可能性的系统统一体”,理性主义倾向太明显;“问题意识”的译法比“问题式”和“问题结构”的译法更差,不但不能包含problematic中的“无意识”内容,而且丢掉了problematic中“模式”、“框架”的含义。所以我觉得这些译法共同问题是:都不能概括problematic一词中所包含的不可见的、无意识的内容和“概念具体可能性的系统统一体”两方面的内容,不能概括problematic作为形容词的“成问题的,有疑问的,不清楚或尚未解决的,全然不明确的”等含义。
三、 problematic是一个向未来不断敞开的“领域”
《保卫马克思》和《读lt;资本论gt;》的英文编者本·布鲁斯特(Ben Brewster)是这样来解释problematic这个词条的:“problematic是一个不能单独理解、只能在它所在的理论或意识形态的结构框架内才能理解的词语或概念。与此相关的概念可以在福柯的《疯狂与文明》中看到(参见阿尔都塞给译者的信)。problematic强调的重点不是一种世界观,不是通过经验的一般阅读能从文本中推导出来的个体或时代的本质,它强调的是在一个problematic内,问题或概念的不可见的部分与可见的部分一样重要,因而只能根据弗洛依德的对病人的言语的精神分析模式来进行症候阅读才能获得。”[7]316阿尔都塞本人也说problematic是:“一种系统地向世界提问的新方式,一些新原则和一个新方法。”[5]225从这个角度来看,problematic是一个通过诠释学的方法、不断向未来和未知敞开和扩展的“领域”,用阿尔都塞的话说,是通过划界和斗争的方式将那些漂浮着因素不断征询(interpellation)到problematic中的过程。problematic不同于难题(problem)和问题(question)的地方是,问题(question)是一个需要研究和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但它是有答案、可以解决的,比如日常生活中筹集资金、购房等问题;如果一直筹集不到或长时间内无法解决、不知道答案,问题(question)就成为难题(problem),比如,人类目前碰到的癌症和艾滋病的治疗、地震的准确预报等难题(problem)。problematic不仅包括具体的问题和难题,更主要的是指产生这些问题和难题的方式、方法、机制和心理状态,以及解决这些问题和难题的各种可能的答案、范围和方式。比如小孩子对周围事物总有疑问,他的问题(question)很多,如他想知道“宝宝是从哪来的”,他能理解的方式和答案就是“爸爸妈妈捡回来的”等,经过一段时间他才可能明白“爸爸妈妈捡回来的”的含义,而有些问题如“上帝是怎么来的”就成为难题(problem),甚至穷尽其一生精力也不能证明上帝会无中生有。像小孩子这种不断问这问那的这种好奇心态和提问方式、他的那些问题以及在他理解能力范围内能够理解和获得的答案,就是小孩子理解这个陌生世界的problematic。可见problematic包括的东西很多,在某种problematic下,问题是不断出现,而出现的问题越多,人对世界的理解就越深刻,之前那些不理解的漂浮着的要素(外在“自在之物”)也就被征询到自己的problematic中,成为“为我之物”,因而problematic是一个敞开的领域。并且在敞开的过程中,与原有的problematic发生质的飞跃和变化,用阿尔都塞的话说就是“认识论的断裂”。当小孩从不知道“宝宝是从哪里来的”到他青春期获得了性知识的阶段,是其problematic的一次“认识论的断裂”;当他穷其一生精力而无法证明上帝能无中生有时,他的problematic可能发生第二次“认识论的断裂”。“任何科学的理论实践总是同它史前时期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划清界限:这种区分的表现形式是理论上和历史上的‘质的’中断,用巴什拉尔(Bachelard)的话来说,就是‘认识论的断裂’。”[5]159“因为问题域(problematic)的转换就是所谓的‘断裂’。”[14]335problematic的敞开和断裂的过程实质就是problematic征询世界的过程。
但是,“认识论的断裂”并不意味着与旧problematic彻底一刀两断,没有任何联系,而是“不连接之中的连接”[16]290。虽然转变之后新problematic与旧problematic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比如一个人儿童时期的心态和problematic与他青年时期和老年时期的心态和problematic完全不一样,但在“断裂”的过程中是存在着“连接”的。阿尔都塞在《列宁和哲学》中指出,“把哲学和科学、哲学范畴和科学概念加以区分,其核心立意,在于采取一种反对一切形式的经验主义和实证论的激进哲学立场:反对甚至连某些唯物主义者都会有的经验主义和实证论,反对自然主义,反对心理主义、反对历史主义”就是列宁当时碰到的问题[16]152;而“在用经验主义的基本范畴思考和表达自身的同时竟然能够成为反经验主义的,这当然是一件悖论式的业绩,而且必定会给任何准备考察它的真诚的哲学家提出一个小小的‘难题’”[16]153。列宁对这个哲学难题的解决方式是“在一个作为参照的经验主义problematic内采取了这些反对经验主义的立场”[16]153,这是列宁与经验主义problematic的“认识论的断裂”。但在这一“认识论的断裂”过程中,“哲学和科学之间”的“这种特许的联系”是列宁“认识论断裂”中的不连接处却又连接的一号连结点[16]156,而二号连结点“哲学只不过是对于论据的重新考察和沉思冥想,而论据则以范畴形式体现着这些倾向之间的基本冲突”[16]159,则是problematic对漂浮着的要素的征询(interpellation)过程,或者说是“症候阅读”的过程,两个连结点是problematic的两种存在方式和状态。
因此,我们发现李智翻译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用“域”概念来翻译阿尔都塞的problematic的译法比较符合阿尔都塞的原意。首先是因为哲学上已经有“域”的概念。“‘域’这个概念是由夏皮尔提出用于替代传统科学哲学中观察与理论的分离,他以关联主义立场将问题置于‘域’的中心,与其他信息密切相关。”[17]夏佩尔将“信息域”看作是一个具有复杂内在结构的实体。这实体以客观的实体信念为基础,以广阔的背景知识信念为主体,以求解难题为目的,以科学方法为手段,以各“项”的变化和发展为过程,形成了一幅具有高度动态性的科学图景[18]97。“域”概念和“式”概念的不同就在于“域”概念是范围概念,不是某种成型、稳定的“式”,这样就把problematic中包含的未知东西和不确定性表达出来。
其次是因为阿尔都塞problematic本身就包含“域”概念的内涵。
他说:“This is a characteristic phenomenon of the transitions-breaks that constitute the advent of a new problematic. At certain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we see these practical concepts emerge, and typically they are internally unbalanced concepts. In one aspect they belong to the old ideological universe which serves as their ‘theoretical’ reference (humanism); but in the other they concern a new domain, pointing out the displacement to be put into effect to get to it. In the first aspect they retain a ‘theoretical’meaning (the meaning in their universe of reference); in the second their only meaning is as a practical signal, pointing out a direction and a destination, but without giving an adequate concept of it.”[6]244中文版翻译是:“这是新的总问题(problematic)诞生时出现的过渡和断裂所特有的现象。在思想发展史的某些阶段,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以内在不平衡性为特点的实践概念的出现。一方面,它们属于为它们充当‘理论’参考的意识形态的旧领域(人道主义);另一方面,它们又属于为它们指出方向,要它们向实在转移的那个新领域。由于第一方面,它们仍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它们的参考领域的‘理论’意义);由于第二方面,它们只是作为信号而具有指示方向和目的地的实际意义,但不提供恰当的概念。”[5]242-243显然,这里的“总问题”(“problematic”)应译为“问题域”才与后面的“领域”(“domain”)相衔接。
“Not the repetition but the non-repetition of this space is the way out of this circle:the sole theoretically sound flight——which is precisely not a flight, which is always committed to what it is fleeing from, but the radical foundation of a new space,a new problematic which allows the real problem to be posed,the problem misrecognized in the recognition structure in which it is ideologically posed.”[7]53中文译文是:“只有通过这一领域的非重复而不是重复,才能摆脱这一圆圈,只有通过理论上有根据的逃遁——确切地说不是逃遁(逃遁始终是由逃遁的对象所决定的)而是彻底建立新的领域,建立新的总问题(“problematic”),才能够提出被意识形态的提法的再认识结构所歪曲的现实问题。”[8]41这里的“space”在中文版中译为“领域”,说明它是problematic本身具有的含义,因此,这里的problematic应该译为“问题域”。
“So I shall be expounding a limit-situation here,too,just as I did with respect to the ‘historicist’reading of certain passages from Capital, and I shall be defining not so much any particular interpretation(Gramsci, Della Volpe,Colletti, Sartre) as the field of the theoretical problematic which haunts their reflections and which emerges from time to time in certain of their concepts,problems or solutions.”[7]131中文译文是:“这里我仍然像对待《资本论》的某些叙述的历史主义阅读那样仅仅作一个有限的说明,我不想去说明某个个别的解释(葛兰西、德拉沃尔佩、科雷蒂、萨特等人的解释),我只想说明对他们的思考产生影响的总问题(”problematic“)的领域,这个总问题(”problematic“)领域不时出现在他们的某些概念、问题和解答之中。”[8]118这里的field一词是“领域”的意思,就是problematic本身具有的内涵。
因此,“域”概念而不是“式”概念更符合阿尔都塞的本义,所以在problematic的多种名家的译法中,李智的“问题域”译法比较准确。
[1]张一兵.问题式:阿尔都塞的核心理论范式[J].哲学研究,2002(7).
[2]黄新,等.法汉大辞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3]王同亿.英汉辞海[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8.
[4]王同亿.语言大典[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0.
[5]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Louis Althusser. For Marx[M].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London:The Penguin Press.1969.
[7]Louis Althusser. Reading Capital[M].Translated by Ben Brewser. London:Verso.1970.
[8]阿尔都塞.读《资本论》[M].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9]库恩.必要的张力[M].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1]Louis Althusser.The Spectre of Hegel[M].Translated by G.M.Goshgarian.London:Verso,1997.
[12]阿尔都塞.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Ⅰ[M].唐正东,吴静,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3]阿尔都塞.自我批评文集[M].杜章智,沈起予,译.台北:源流出版社,1990.
[14]潘志新.阿尔都塞的有机理性思想初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5]冯契,徐孝通.外国哲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16]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陈越,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7]张立静.问题域在近代科学起源中的作用[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2).
[18]郭富春.当代科学实在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曹 骥]
B089
A
2096-4005(2017)04-0066-07
2017-03-28
2017-06-16
潘志新(1966-),男,江苏泰州人,陕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性等研究。
——重读阿尔都塞的《论青年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