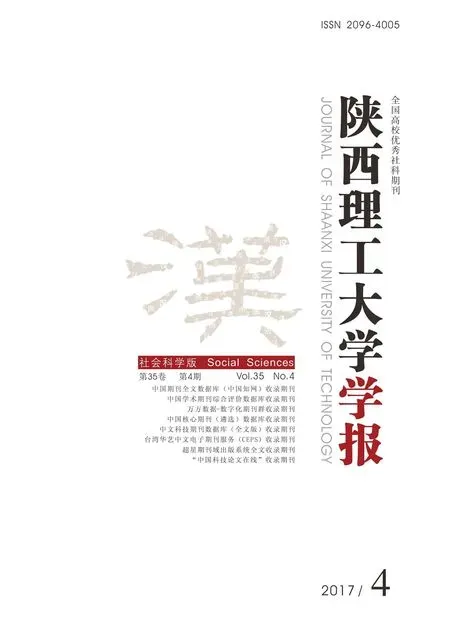变形:格里高尔的成年礼
吴 金 涛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变形:格里高尔的成年礼
吴 金 涛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变形记》的艺术内涵极其丰富,具有解读上的多种可能性。以人类学观点看格里高尔的变形,它既是一个社会问题,又是一个文化问题;既是一个家庭事故,又是一个民俗事件。格里高尔年龄虽已长大,心智却远未成熟。以房间的门为界限,格里高尔通过变形而被分隔出来,以边缘人身份,一步步进行自己的成年礼。变形既是仪式的重要标志,也是仪式的主要内容,它使格里高尔从俗界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神圣的仪式活动主体。在这场仪式中,卡夫卡主要展示了格里高尔在分隔期和边缘期所经受的种种考验,事实证明,格里高尔对这些考验无所适从。进一步看,由于格里高尔个人原因,导致萨姆沙家族逐渐丧失了生命力,作为替罪羊,他必须以自己的献祭与死亡换回家族精神的复活。格里高尔必须接受惩罚并被大家抛弃,而最终无法聚合回到家庭和社会。
格里高尔; 变形; 成年礼; 仪式
卡夫卡的《变形记》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有关它的解释往往关乎整个现代西方文学的评价。而关于格里高尔的变形问题,则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外论者观点不同,方法各异,从不同角度肯定了《变形记》特立高标的审美表达。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首先是奥地利的索克尔[1]205、美国的纳博科夫[2]256等人,他们主要采用所谓“回到文本”的批评方法,对主人公格里高尔变形的原因作出严谨而又深刻的逻辑分析;国内的叶廷芳[3]70、钱满素[4]299等人,他们从作品的家庭和社会联系入手,深刻揭示了格里高尔变形的社会根源。这些观点新颖而又精辟,方法灵活而又独到,形成了卡夫卡研究重要的学术积淀。
不过,正像任何伟大的作品一样,《变形记》具有极其丰富的艺术内涵。迄今为止,对它的研究无论是内容的挖掘还是方法的选择,似乎都还有未尽之意。考虑到卡夫卡复杂的文化出身,对卡夫卡作品的研究就不能画地为牢或排斥异见,那样的话,关于《变形记》的许多问题就难以申明。比如,纳博科夫说,当甲虫格里高尔死去的时候,萨姆沙家族反倒有了虫的灵魂,这是为什么?[2]280-281格里高尔与父亲的关系意味着什么?甲虫格里高尔为什么在春天来临之际悄然死去,而当此时,妹妹却像充过氧气似的,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仔细检读各家学说,始终未能了然。倒是纳博科夫给出一些启示,他以近乎嘲讽的口吻指出,小说中的数字“三”、实物“门”等具有特殊象征意义,尤其是宗教上的象征,而他原本反对这样解释卡夫卡。看来,《变形记》中的问题可能要回到“文化”上来解决,特别是能否考虑用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进行分析。叶舒宪认为:“人类学方法论上的‘求异’思维足以对寻求普遍规律的自然科学式‘求同’思维传统构成有力挑战,……并尝试用不损失其‘原汁原味’的方式将所体认到的真实传达出来”[5]25。格里高尔的变形既是一个社会问题,又是一个文化问题,他(它)用自己的虫身及其死亡换来家族的新生。与其说这是一场现代社会的家庭悲剧,倒不如说,它更像格里高尔走向成年的一个考验,或如弗雷泽阐述过的阿都尼斯死而再生的仪式。这大约就是格里高尔变形的“原汁原味”的真实。因此,笔者循着这条思路,尝试运用人类学仪式理论对《变形记》进行分析,以作抛砖引玉之用。
一
《变形记》故事最打动人的地方,莫过于格里高尔不顾自己遭受无妄之灾,还试图与家人沟通交流,最终却无法得到他们谅解。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刚刚发现自己出了状况,出于善良而又单纯的动机,格里高尔努力打开房门,像小孩子一样表白自己,结果吓晕了母亲,也吓跑了秘书主任;妹妹葛蕾特为房客拉琴,格里高尔被家里难得一见的温馨场景所感染,情不自禁地凑上前来,结果引发一场新的混乱。就这样,《变形记》通篇都写满了格里高尔的莽撞与幼稚。卡夫卡式的悖论出现了,格里高尔越是想解释自己,就越显得不可理喻;越是想承担责任,就越显得幼稚和不可信赖。他年龄虽已长大,心智却远未成熟。然而,“对人来说,最重要的人生课题是成人、亦即怎样学习做人。因为人只有进入成年,才成为真正的人、完整的人,才是自己的主人”[6]169。从一般意义上讲,格里高尔需要完成自己的成年礼,而“变形”就是他的成年礼仪式。
根据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理论和维克多·特纳的阈限学说,格里高尔的成年礼必须经过分隔、边缘、聚合三个阶段以及相应的阈限期,通过与群体(家庭和公司)的分离,他要接受各种严酷的考验,让自己的心智而不单单是身体尽快成熟成长起来,证明自己能够独立承担责任,从而重新加入群体。“在任何社会中,个体生活都是从一个年龄到另一个年龄,从一种职业到另一种职业的过渡”[7]2-3。显然,格里高尔还没有完成这种“过渡”。在变形以前,他的心智还停留在人生初级阶段,而一个人的成年需要脱胎换骨般的改变,这种改变犹如再生,否则就不能“加入”成年行列。“加入(成人)礼仪是一次完成,有时需经过若干阶段。在视新员为死亡的地区,加入礼仪是使其再生,教导他如何过与童年不同的生活”[6]159。因此,要想理解格里高尔变形的含义,就必须小心翼翼地分析和评价他的人生过程。
关于格里高尔早年间的身心成长,小说虽然未作系统介绍,但并非没有暗示。小说第一次提到格里高尔想起过去,是在他吓跑秘书主任而自己受伤以后,“格里高尔从门缝里看到起居室的煤气灯点亮了,可是往日里父亲惯常在白天的这个时间提高嗓门将他的下午出版的报纸读给母亲并且有时也读给妹妹听,而现在人们却听不到一点响声[8]124”,看到这样的场景,他充满内疚。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勾起他对过去的回忆,是父亲颇为得意地向家人公开自己的储蓄所得,父亲“时不时从桌子旁边站起,拿来一份什么凭据或一本什么备忘记事本,这些东西都放在一只小小的保险箱里,这是五年前他的公司破产时保存下来的[8]129”。从父亲的谈话中,格里高尔进一步明白了家道中落与自己辛苦奔波的真正原因,他感到自己被家人欺骗了。从这两段情节当中,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如同妹妹受哥哥保护而生活得单纯幸福,由于受父亲荫蔽,格里高尔的少年时代也是无忧无虑的,只是因为父亲破产,这一切才被改变。
一般而言,卡夫卡的小说中只有“现在”,或者叫“当下”,极少涉及“过去”和“未来”,而《变形记》是很少的例外。“《变形记》的叙事时间中,作者还引入了‘过去’与‘未来’,不过,这两个概念的存在都是为了陪衬或凸显‘当下’的现场感”。[9]60如果说格里高尔和家人过去的生活平静而又温馨,那么,他们家在当下就充满了烦躁情绪和不安全感,而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变形。萨姆沙家族“当下的现场感”,就是大家觉得与一只异形动物生活在一起。他(它)和家人不一样,大家连看他一眼都感到害怕,更别说去触碰它。当家人用恐惧的眼神注视他的时候,他离家人也就越来越远。可以说,正是由于变形,格里高尔被从家人中间分隔出来,他成为一个异类,成为一个边缘人,用范热内普的话说,成为一个“新员”。这正是格里高尔成年礼的第一步骤,现在,他从以往熟悉而又温馨的家人中间分离开来,被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接受各式各样严峻的考验。
有意思的是,卡夫卡在小说中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格里高尔的变形是他完成分隔礼仪的必要步骤,这个证据就是“门”。对格里高尔变成甲虫的情节作了初步介绍以后,故事的中心很快就转到“门”上。这扇门几乎成为故事转折的重要标志,格里高尔细腿与硬腭并用,第一次打开房门,想要对自己的状况作出解释,结果吓退了秘书主任;母亲和妹妹试图搬动他房间的家具,而格里高尔的模样和行为打破了他与家人之间脆弱的平衡,他本能地冲出房门,结果被父亲的苹果炸弹轰进门内;受妹妹琴声的吸引,格里高尔又一次越界来到自己门外的起居室,让刚刚搬来的房客大惊失色,也断送了家人与他之间的最后一丝温情。纳博科夫慧眼识得这扇门的美学价值,认为门的主题反复出现,强化了格里高尔与家人的对立,对故事结构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还有人认为,上述关于门的三段情节其实就是隐含在小说中的所谓“横向结构”,它具有“在展示人们内部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时所具备的层层深入的艺术功能”[10]129。然而,用范热内普过渡礼仪理论看,格里高尔卧室的门主要起的是分隔作用。门内与门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蛰伏门内是格里高尔当下的宿命,虽然孤独,但他必须经历这种考验,之后才有可能回归门外的家庭和社会。
特纳在对赞比亚恩丹布部落年轻人的成长仪式或青春期仪式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后发现,受礼者往往是一无所有的人,他们没有地位、财产,在亲属中也没有他们的位置,“在成长仪式里,有很长一段时间受礼者都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受礼者须得完成少年向成年的“过渡”、个人向社会的聚合,最终获得所谓“相对稳定的状态”。[11]95-96在《变形记》中,通过门的分隔,格里高尔成为一个“受礼者”,不过,这只是形式上的分隔。就其成年礼的实质而言,格里高尔事实上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他失去了人的身份,失去了工作,自己挣的钱分文未留,在家人中间也没有他的位置——既不是儿子,也难称呼哥哥。因此,从成年礼角度看,与其说格里高尔由于重压而致人格扭曲变形,不如说他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成年礼,必须从家庭和社会分离出来,先做一个受礼者;与其说他是一个不得不躲在门内的异类,毋宁说他是一个正在进行成年礼的边缘人。从此,格里高尔进入他的漫长而又难堪的边缘期。
二
在格里高尔成年礼的边缘期,他主要面临三大考验,一是变形的尴尬,二是沟通的困难,三是亲情的消褪。此外,他从世俗家庭分隔出来,暂时成为“神圣”的受礼者,这不仅对他而且对家人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关于成年礼的边缘期,范热内普指出了它的特点:其一是时间较长,其二是受礼者必须“重生”,即他被视为已经死去,其三是对新员的考验。“在某些部落,新员被视为已经死去,直至度过此阶段。这阶段相当长,包含对其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弱化,以使他失去一切童年记忆”,[7]75最终达到“社会成熟”。特纳则更看重过渡礼仪中的阈限期,受礼者作为“阈限人”“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他们在法律、习俗、传统和典礼所指定和安排的那些位置之间的地方”。[11]95同时,在这种通过仪式中,还伴随着力量与权力,受礼者被指定必须完成某些“作业”,以证明自己能够通过这些考验。综合起来看,成人礼仪的核心就是考验,“在许多生命礼仪中,‘考验’与‘受难’是考察和评价‘通过者’必须和必备的功力和课业。是社会布置的‘作业’,完成了便获得社会给予的入社‘通行证’,反之则无法入社”。[12]187就是说,倘若格里高尔不能完成这些考验,他就不能聚合进入社会。
当格里高尔被房门隔开,他就进入一个仪式世界。在这个仪式语境中,他是人也好,是虫也罢,都具有一种神圣性。而且,这种神圣性可以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得到充分证明。作为重要的民俗活动,仪式将世俗生活的一部分分离出来并赋予其神圣性,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仪式当中所包含的“神圣-世俗”二元对立,就成为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关注的重要问题。《过渡礼仪》一书开宗明义地写道:“人生每一变化都是神圣与世俗间之作用与反作用——其作用与反作用需要被统一和监护,以使整个社会不受挫折和伤害”。[7]3杜尔干说:“圣物是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圣物之所以有这种特点,那是因为圣物与俗物是泾渭分明的。……礼仪的职能是防止圣、俗混淆和违反惯例的接近,并阻止圣、俗双方互相侵越”。[13]303与宗教信仰、社会结构有关的一切活动,莫不体现了这种圣俗相隔、泾渭分明的差异性。格里高尔的成年礼仪主要关乎社会结构这一方面,对个人而言,他要成长;对家庭而言,他要承担责任;对社会而言,他要确立自己的角色地位。这一切,需要一个圣俗分隔的神圣礼仪来完成。在仪式进程中,代表世俗社会的家人、房客、公司代表统统不能进入他的世界,反之,格里高尔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想回到家人中间。
毫无疑问,变形是对格里高尔最大的考验,也是他的成年礼的关节所在。关于格里高尔的变形,有人认为是异化所致(叶廷芳,钱满素);有人认为是思想矛盾和人格冲突的结果,“卡夫卡一辈子都处在工作和创作、家庭义务和个人理想的矛盾冲突之中”,变形是一种“成年的焦虑”的反映[14]183;还有人从美学角度指出:格里高尔“一方面要甲虫生活,要具备甲虫的习性,另一方面又跟人一样思维,……这种分裂的意识导致了分裂的文字,所以小说中出现了虫性与人性、大祸临头与拘泥小节的强烈反差”[15]64。依笔者看来,这些观点中包含有某种人类学因素,“成年的焦虑”正是成年礼的考验带给主人公的精神紧张,“虫性与人性的反差”也是成年礼边缘期的受礼者的重要特征之一。包括范热内普在内的许多人类学家通过大量田野作业和文献疏证,证明在成年礼仪进行过程中,受礼者往往被化装成异于常人的形态,有些像兽类,有些像家畜,有些则像植物;伴随仪礼进程的常常还有受礼者的人身痛苦,比如割礼、鞭打之类。
因此,变形是仪式交通与文化理解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变形,仪式的阈限也就无法变通和转换;没有变形,文化的理解、翻译、交流、借鉴也不可能得以顺利进行[16]244”。不仅如此,变形还有重要的叙事功能,“以变形的叙事原则去观照文学创作,‘变形’显然更为丰富:叙述故事的变形,人物性格的内部逻辑变形,叙事的中介性变形价值……”[16]246-247人变虫,这是一个多么富有艺术张力的故事啊!不过,在仪式场合,我们还是应当重点关注格里高尔所受的考验。作为他的成年礼的组成部分,变成甲虫类似于对他的化装,虽然尴尬,但神圣性也随之形成。至于他所遭受的饥饿、呵斥、磕碰、刮创,以及苹果轰炸,则无一不是一个受礼者应当接受的严厉考察。若非如此,他的成年礼仪就无法完整成礼。还有冷暴力——家人的沉默、疏远和横眉冷对,都让格里高尔体验到孤独、寂寞和被遗弃感,这是这场仪式最严肃和严厉的部分。
的确,格里高尔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得不到家人的理解,为此,他忍受了太多的孤独与寂寞。起初,家人觉得他只是一时不小心交了厄运,不是什么不治之症,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好起来的。但时间一长,他们就失去了耐心,甚至觉得他给全家带来了厄运。在家人眼里,格里高尔不仅是一个难以沟通的虫子,它说话瓮声瓮气,浑身浸透肮脏的粘液,喜欢吃腐食而不是新鲜的饭菜。这样一个异类,除了厌恶、恐惧,很难想象家人会对他维系什么感情。“人变成甲虫:甲虫便带着人的视角去看人类,它所看到的是一群多么冷漠、多么空虚的芸芸众生;从人的角度看甲虫,甲虫就显得更加孤独、恐惧和不可理解了”。[17]107格里高尔与家人的关系现在变成了“甲虫与人”的关系,这就注定了他处在弱者地位,而他与家人的感情也必然会渐渐消褪以至于被遗弃。
人变成虫,这是卡夫卡的逻辑,是卡夫卡的叙事策略,其目的是揭示人性的退化和人格的扭曲。卡夫卡主人公的性格特点是“屈辱退让、逆来顺受,对各种黑暗势力缺乏自卫能力,在重大抉择面前总是彷徨不前,迟疑延宕,最后听任命运的安排和摆布”。[18]55“卡夫卡似乎在寻找一种稍为策略一些的、能够部分地保全自我和自由的妥协方式,即把自己尽可能地变小、变弱、变丑、变恶、变成异类,以求龟缩在‘父亲’张开四肢覆盖住的版图之外所剩无几的空间里生存下去”。[19]71然而,在格里高尔成年礼的语境下,人变虫却不单单是一种叙事策略,秉有虫身的格里高尔与家人的沟通困难和感情消褪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性问题,而应该视作他的成年礼必须完成的“作业”。“人类学家了解到,即使像爱慕、恐惧和愤怒这类人类的基本情绪,也不能归咎于种族遗传或所谓共同的人性,它们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20]4就像特纳所描述的非洲人的成年礼,此刻的格里高尔已经而且应该“死去”,因为作为一个没有修毕成年礼的人,他首先应该被遗忘、被抛弃。
三
格里高尔应当被抛弃,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有些残忍,然而事实就是这样,因为他是一个“必须死去的人”。格里高尔是一个重要的家庭成员,他是儿子也是哥哥,依靠他旅行推销员的收入,全家人生活无虞。按道理讲,他出了状况,大家都应该施以援手,帮助他走出困境。但在仪式场合,这样做是不适宜的,会打乱格里高尔成年礼的进程,所以大家只能袖手旁观,听凭甲虫挣扎、自救。不仅如此,换个角度说,由于他的某种过失,比如工作不够卖力啦,精力不济啦,等等,使得家人生活不宽裕,心情不舒畅,整个家庭就像冬季的大地一样,一派沉闷萧瑟。本来,造成目前家庭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父亲的破产,但是,在五年前,格里高尔既然义无反顾地挑起这副担子,那现在他就得承担责任。这样看来,格里高尔是替父亲背了黑锅,他是一只“替罪羊”。因此,在成年礼仪进程中,格里高尔还不知不觉地成了另一个仪式——替罪羊仪式的主角。
在西方文学中,替罪羊母题主要有两个出处,一是旧约故事,一是希腊神话和悲剧。《旧约·利未记》载,拿答和亚比卢不遵圣训,以凡火祭神而被神的圣火烧死,且罪及其父亚伦。此后,亚伦被禁止擅入圣所。若入,他必以公牛献祭赎罪,或从民家选两只公羊,一只献为燔祭,另一只就是替罪羊。祭司手按羊头,将众人的罪归在羊身上,然后将其逐放旷野,那羊便把罪恶带去无人之地。在《圣经》叙事语境中,替罪羊仪式的要旨是“审判∕惩罚∕赎罪”,《变形记》的仪式与此是暗合的。关于俄狄浦斯的神话及其悲剧演出,美国批评家费格生明确指出了它的替罪羊仪式展演性质,“俄狄浦斯本身形象提供了替罪羊的一切条件,被逐的国王或神的形象条件。剧本开始表演的忒拜的处境——生命攸关;它的庄稼,它的畜牧,妇女神秘地无生育能力,是城市遭灾的迹象,神明发怒的表示——像是冬天带来的枯萎,同样需要斗争、放逐、死亡和复活。这些悲剧性的连续事件正是剧本的实质内容”。[21]39这个仪式的关键情节是追查凶手,它犹如圣经替罪羊仪式的“审判”;俄狄浦斯与先知忒瑞西阿斯的暗斗,他的自我放逐,以及忒拜了无生机的灾象,则是赎罪与惩罚。《变形记》的替罪羊仪式叙事与此又是暗合的。
卡夫卡曾经把作家比作替罪羊,他说:“作家……他是人类的替罪羊,他允许人类享受罪愆而不负罪,几乎不负罪。”[22]257一个犹太出身且熟悉犹太经典的作家,他拿替罪羊之说自喻,这一点也不奇怪。此外,卡夫卡熟悉古希腊罗马文学经典,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准此,则卡夫卡赋予他的主人公以替罪羊的属性,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卡夫卡说:“比心理分析学更令我折服的是,与有些人引以为精神食粮的那种恋父情结相关联的不是那无辜的父亲,而是父亲的犹太属性。”[23]420-421卡夫卡把自己亲身体验到的犹太民族的父子关系融进《变形记》,艺术地表现了父亲对儿子生杀予夺的威权,父亲就是剥去圣衣的上帝,儿子就是他的替罪羊,父亲的呵斥、威吓与苹果轰炸就是对格里高尔的审判与裁决。“表面上看,他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儿子’,其实以各种形态出现的‘父亲-上帝’的存在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24]84老萨姆沙本来因为破产而变得一蹶不振,但儿子的变形仿佛给他打了一针兴奋剂,使他精神大振,颇有些神采奕奕的样子。父亲“一双黑眼睛射出活泼、专注的目光”,竟让格里高尔感到陌生,“这还是父亲吗?还是这同一个男子吗?”[8]139所以,当甲虫格里高尔被父亲砸伤后,他很快就领悟了父亲所说的“如果他懂我们的话”的言外之意,并“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痛定思痛,他坚定了“自己必须离开这里”的决心。[8]152-153最终,格里高尔带着对家人的眷恋,更带着自己和家人全部的罪,他无声无息地死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格里高尔与父亲的关系很像亚伦父子与上帝的关系。亚伦和儿子都是上帝审判与惩罚的对象,老萨姆沙则是神圣上帝的世俗显现,儿子格里高尔是由他审判并惩罚致死的。所不同的是,亚伦父子可以让替罪羔羊代自己受罚,而格里高尔只能以替罪羊之身代父亲受罚,其性质是一样的。“当初格里高尔一心只想着要竭尽全力,让家里人尽快忘掉父亲事业崩溃使全家沦于绝望的那场大灾难。所以他以不寻常的热情投入工作,几乎是一夜之间便从一个小办事员变成一个旅行推销员”。[8]129殊不知,从那时起,他就被放上了替罪羊祭坛并随时会遭到祭杀。显然,格里高尔对此并没有充分理解,所以他才会做出那些莽撞行为,用满含愤怒的咝咝声警告妹妹,用毫无遮拦的虫身吓唬母亲,用带有挑衅性的步态对待父亲的追逐。拿答和亚比卢不尊圣训而以凡火奉献上帝,父亲亚伦不予纠正和引导,轻浮之心昭然若揭;格里高尔不忠实履行自己的责任,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想以变形之术逃避责任,其轻慢之态溢于言表。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都犯了“不罪之罪”,也就是原罪,而这样的罪者必须受到惩罚。因为根据《圣经·罗马书》使徒保罗的说法,只要人在思想、言语、行为上不合乎神旨的都是罪,而完全顺服神的就是良善的和无罪的。因此,无论怎么讲,格里高尔都必死无疑。
依格里高尔承担的家庭责任和工作效果而言,他曾经是全家人的救星,是保证家族长盛不衰的监护人,是爱人如己的“国王”。可是,从现状看,格里高尔这个“国王”既力不从心又不够称职。因为在他的“荫蔽”下,整个家庭了无情趣、死气沉沉,父亲疲态日现,母亲病病殃殃,妹妹至今少不更事。这种景象不就是俄狄浦斯治下的忒拜所面临的危机吗?不同的是,俄狄浦斯有清醒的责任意识,而格里高尔对自己的责任却浑然不觉。此外,根据弗雷泽对阿都尼斯“生-死-再生”神话的分析可知,神主阿都尼斯必须一年一度死去,尔后再行复活。“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把死去而又复活的神说成是收割后又长出新芽的谷物。”[25]338神像死而复生的谷物一样,他身上承载着生命的希望。弗雷泽所述的意大利内米湖畔的弑老民俗,其要旨与阿都尼斯死而再生的仪式可谓异曲同工,它“包括了人类对生命在自然律动中的直观性理解,并与国家社稷的长治久安,部落族群的繁衍壮大,黎民百姓的安养生息,万物的丰产收获维系在一起”。[12]267-268显然,格里高尔的身体变形与精神退化,已经妨碍了家族的发展。
结论很清楚,萨姆沙家族是“兴也格里高尔,衰也格里高尔”。当初,父亲破产,家族危难之时,格里高尔意气风发,是他全心全意的劳动奉献赋予家族新生命;如今,家庭成员的生命律动似乎快要窒息,作为拯救者,他只能像俄狄浦斯、阿都尼斯、内米湖畔的祭司一样,以替罪羊之身换取家族精神的复活。正如弗雷泽所说:“既然总是要把他(替罪羊——引者)杀掉的,人们就会想到他们何不抓住这个机会,把他们苦难和罪孽的担子也交给他,让他把这个担子挑到坟墓后面那个不可知的世界里去呢。”[25]576-577格里高尔,这只可怜的替罪羊,当他背负全家“苦难和罪孽的担子”死去,果然带来一片春光明媚,父亲、母亲和妹妹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他们满面春风,兴高采烈,很快便筹划着进行一次忘情的郊游。
要之,“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是一个符号行为,它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依仪式理论看,甲虫身份意味着格里高尔与家庭和社会的分隔。在接下来的漫长的边缘期,他就像非洲部落社会成年礼中的少年一样,没有社会身份,没有行动能力。在仪式场合,对格里高尔最大的考验,就是看他能否摆脱自己的虫性,重新聚合进入社会。结果是他未能经受住这种考验,他虫性依旧,缺乏自信,试图通过变形而蜗居起来,甚至想要逃避责任。这样一来,格里高尔就永远失去了回归社会的可能性,再也无法完成自己的成年礼。
[1]Sokel, Walter. Kafka‘s ’Metamorphosis’:Rebellion and Punishment[J].Monatshefte,1956,48(4).
[2]Nabokov, Vladimir. Lectures on Literature. Ed. Fredson Bowers[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2.
[3]叶廷芳.现代艺术的探险者[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4]钱满素.卡夫卡和异化[M]//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五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5]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7]Van Gennep, Arnold. The Rites of Passage[M].London: Routledge, 1960.
[8]叶廷芳.卡夫卡全集:第1卷[M].洪天富,叶廷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9]胡志明.“变形”的美学——从《变形记》看卡夫卡小说的话语方式[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
[10]阎保平.《变形记》叙事结构解析[J].外国文学研究,1992(3).
[11]Turner, Victor. The Ritual Process: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M].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12]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13]Durkheim, Emile.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Trans. Karen E. Fields[M].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95.
[14]曾艳兵.卡夫卡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5]黄燎宇.卡夫卡的弦外之音——论卡夫卡的叙事风格[J].外国文学评论,1997(4).
[16]彭兆荣.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7]曾艳兵.卡住了吗——卡夫卡论[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2).
[18]曾艳兵.论卡夫卡创作中的后现代特征[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19]昂智慧.倔强的灵魂的独语——论卡夫卡的人生求证[J].外国文学评论,1996(4).
[20]Mead, Margaret. Coming of Age in Samoa[M].New York:William Morrow, 1928.
[21]Fergusson, Francis. The Idea of Theater[M].New York:Anchor Books,1953.
[22]叶廷芳.卡夫卡散文选:下册[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
[23]叶廷芳.卡夫卡全集:第7卷[M].叶廷芳,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4]胡志明.父亲:剥去了圣衣的上帝——试论卡夫卡作品中的父亲形象[J].外国文学评论,2001(1).
[25]Frazer,James.The Golden Bough[M].New York:The Macmillan Press,1990.
[责任编辑:王建科 责任校对:王建科 陈 曦]
I106
A
2096-4005(2017)04-0017-06
2017-08-02
2017-08-13
吴金涛(1961-),男,陕西洋县人,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西方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卡夫卡创作的文学人类学研究”(12JK0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