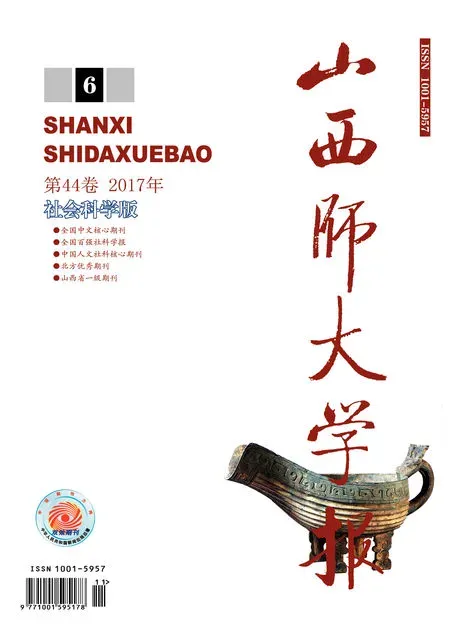西舞东传与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变迁
张 艳
(北京舞蹈学院 思政部,北京100081)
舞会是西方社会进行社交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历史悠久。在近代以前,由于交通不便,商贸不发达,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尤其是舞蹈文化的交流非常有限,所以中国人对西方交际舞非常陌生。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文化也伴随着腥风血雨传入中国,这其中包括西方的各类舞会、各种舞蹈表演等,近代国人的休闲娱乐生活由此增加了新的元素。
本文拟对西方舞蹈传播状况做进一步研究,通过挖掘珍贵的原始资料特别是中国驻外使节的日记、文集等,梳理西方舞蹈传入中国的路径、发展状况及影响等,可以窥其在近代中国传播的风貌。
一、 西舞东传的途径
伴随着近代国门洞开,西方各种新式娱乐传入中国,社会史研究专家严昌洪称之为“新潮娱乐”。西方舞蹈是其中重要的内容。纵观近代西方舞蹈传入中国的方式,其途径是多元的,大致包括以下几种[1]43—48。
一是中国驻外使节的言传和笔记,这是时人认识西方舞蹈的中介桥梁。晚清时期,走向世界的国人特别是驻外使节见识了西方各种级别和类型的舞会,他们的见闻或者通过言传,或者通过文字如日记、文集等传到国内,让国人了解了西方这种交际娱乐方式。
近代中国第一批官派到西方的是1866年斌椿携子并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一行五人考察团,他们是年3月18日到达法国马赛,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等11个国家,时间长达4个多月。他们在英国参加的维多利亚女王专门为中国来访者举办的宫廷舞会,是目前可查有记载的近代国人参加西方国家舞会的最早记录。在白金汉宫,王公贵族1200余人参加的舞会非常豪华,随着乐队的演奏,宾客翩翩起舞, 乐人于楼上奏乐,音节铿锵。男妇跳舞十馀次。武职衣红,文职衣黑,皆饰以金绣。妇人衣红绿杂色,袒肩臂及胸。珠宝钻石,项下累累成串,五色璀璨,光彩耀目。[2]117
斌椿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但他对西方舞会并无贬斥、厌恶之意,相反却称在英国游历大开眼界。
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嵩焘(1818—1891)自1876年起任清政府驻英、法公使。他外交建树不多,但其《伦敦与巴黎日记》在文化思想史上的价值很大。在日记中,他记载了两次应邀参加英国宫廷舞会的场景。第一次是1877年5月12日, “晚赴柏金宫殿看跳舞会。铿伯叱年七十(总督军政)、哈定敦及大太子及俄国公使及太子妃及各公主,各挟所知,相与跳跃而不为非。使中国有此,昏乱何如矣!”[3]234第二次是1878年4月21日,“晚赴柏金宫殿跳舞会。男女杂沓,连臂跳舞,而皆着朝服临之。西洋风俗,有万不可解者。自外宫门以达内厅,卫士植立,皆有常度,无搀越者。跳舞会动至达旦,嬉游之中,规矩仍自秩然。其诸太子及德国太子,皆与跳舞之列。以中国礼法论之,近于荒矣。而其风教实远胜中国,从未闻越礼犯常,正坐猜嫌计较之私实较少也。”[3]580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思想非常开明,对西方交际舞会的认识也颇有识见。他认为西方舞会这种男女连臂跳舞的形式,按照中国的礼教来说是完全荒谬的,但在西方却非常有秩序,少有越礼犯常为非不良之事,说明西方的风俗教化远超中国。但如果这种形式放在中国,将会引起极大的混乱。也正如郭嵩焘所预测的那样,交际舞传入中国后,逐渐失去了西方正常交际娱乐的功能,越来越流于市场化、低俗化,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
然而在早期出使西洋的官员中也有思想极端保守的,其中以刘锡鸿为突出代表。刘锡鸿于1876年12月任出使英国的副使,与正使郭嵩焘性格不合,政见不一,互相参奏。他在其所著《英轺私记》中记载的跳舞会是这样描述的:
跳舞会者,男与女面相向,互为携持。男以一手搂女腰,女以一手握男膊,旋舞于中庭。每四、五偶并舞,皆绕庭数匝而后止。女子袒露,男则衣襟整齐。然彼国男子礼服下裈染成肉色,紧贴腿足,远视之若裸其下体者然,殊不雅观也。云此俗由来最古,西洋类皆为之,国中大小衙门莫不有跳舞庭,以备盛会,若以为公事之要者。四月以来,英人延请赴观者,不下十余家。余以病,皆未往。[4]151—152
从这段记述中,非常明显地体现了刘锡鸿对舞会的态度,他虽然深知舞会在西方由来已久,是西人交际的主要形式,但认为此种形式“殊不雅观也”。因此英人举办舞会多次邀请,他都以身体有病为由拒不参加,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西方交谊舞会的排斥与不认同。
总之,在早期的驻外使节中,大多数人像郭嵩焘、曾纪泽、王韬、徐建寅、张德彝等,初次见到西方舞会都感惊异,如曾纪泽所称“华人乍见,本觉诧异,无怪刘云生之讥笑也”[5]166。但大都抱着宽容、理解甚至欣赏的态度,像刘锡鸿那样顽固排斥的比较少。也正是这些驻外使节的宣传散播,使日后交谊舞会传到中国并被接纳具备了一定的舆论和思想基础。因为这些外交官的出洋日记,有的要交给主管衙门审阅,以便相关衙门了解其出洋经历和外国的情况;有的是当时刊刻以转赠给亲友的;有的是写给自己看的。这其中张德彝先后八次出国,每次都留下一部以“述奇”为名的日记,记载了其在各国的见闻,有些还是未刊稿,共七十余卷,二百多万字。他们在出洋日记中的描述,并不因为西方舞会不符合中国礼教风俗而妄加批判,表明近代国人有相当一部分对交谊舞会这种西方的习俗并不排斥,体现了中华文化包容性的一面。借由他们的笔记和言传,近代国人了解了西方舞蹈。一个很好的例证是,在深宫中的慈禧太后也听说了西方人跳交谊舞的习俗,对此感到非常好奇,曾经让驻法外交官裕庚的女儿著名舞蹈家裕容龄、德龄姐妹专门在宫中表演交谊舞给她看。
二是在华外侨的影响。在一些华洋混居的通商城市,伴随着商贸的繁荣,休闲娱乐性商业也兴旺起来。特别是在这些通商城市居住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带来了西方的娱乐活动。据载,外商在上海进行贸易,赚取了丰厚的利润,生活十分奢侈。他们购建豪宅,在贸易淡季里,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跑马、打猎、打弹子、击剑、划船等,时常举办舞会。某些和外商有联系的中国人借此机会观赏、参加舞会,并由此逐渐影响了华人上流社会的娱乐方式。
三是留洋归国人员的传播,使西方舞蹈在中国日益广泛地流行。近代出洋留学生也是西方舞会的重要见证者和传播者。比如著名的教育家蒋梦麟在1908年被官派赴美留学,在赴美航船上,蒋梦麟第一次看到了西方交谊舞,“船上最使我惊奇的事是跳舞。我生长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里,初次看到男女相偎相依,婆娑起舞的情形,觉得非常不顺眼。旁观了几次之后,我才慢慢开始欣赏跳舞的优美”[6]87。后来在美国学习期间,他常常参加附近居民的家中舞会,随着主人弹奏的提琴曲子婆娑起舞。宋美龄在1907年10岁时被父亲送到美国留学,在美学习11年,接受的完全是美式教育,非常喜欢跳交谊舞。回国后,她便经常举办或者参加上海上流社会的舞会。鲁迅先生在他的散文《藤野先生》中,讲到东京“清国留学生”的生活情况,每到傍晚,在中国留学生会馆里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留学生在国外的见识及经历,使他们成为近代传播西方舞蹈的重要力量之一。
四是外国电影让更多的中国人通过银幕认识了西方舞蹈。1896年8月11日,上海首映西洋影戏。当时演出的电影只是一些活动着的人物和风景,没有故事情节。据时人记载:“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7]8—9外国电影配外国歌舞,是当时的一种通例。这个时期电影放映的内容中包含了专门的舞蹈表演,让国人有机会欣赏到西方舞蹈。
五是西方舞蹈团体、马戏团等在中国的演出,让中国人亲眼见识了西洋舞。1886年西方马戏团首次到中国上海演出,内容包括各种马戏杂技节目以及“鼓人舞蹈”等。1896年6月,法国舞蹈家维多里亚非利来沪演出,《申报》对此专门作了报道,称其“所用衣服,美丽非常,加以舞态歌声,并皆佳妙,以故观者神摇目眩,几讶彩云万朵,降至瑶台”。[8]20世纪20年代之后,西方舞蹈团体到中国的演出活动日益增多,给中国的观众带来了西方的芭蕾舞、现代舞以及外国民间舞等。
正是通过在华西人和华人上流社会为主体的人群在通商城市的传播,近代国人初步认识了西方舞蹈,由此为西方舞蹈在大众社会的流行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成为近代民众生活方式演变的重要突破口。“中国生活方式的近代化演变,带有比较明显的‘西洋化’,或仿效西方的色彩”,[9]696西方舞会的引入,也是国人效仿西方的新生活元素之一,使近代的社会生活呈现出鲜明的“西化”色彩。
同时,由以上的途径可以看出,这种传播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和地域差别,使得近代以来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娱乐方式差异极大,典型地反映出近代中国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首先,阶层差别。当西方文化新质注入中国城市文化之初,往往只有一个或几个阶层与群体感受到其优越性而产生认同及至接受,进而改变自己旧有的生活方式。就交谊舞这种新式娱乐而言,消费主体就呈现明显的阶层差别。最开始是在租界洋场和上流华人社会中流行,后来才逐渐成为大众社会的流行时尚。又由于城市中不同的人们所处的地位、受教育程度、思想价值观念以及受西方文化影响程度等不同,到舞厅跳舞的目的各不相同,选择舞厅进行消费的等级也有高低之分,呈现明显的阶层差异。
其次,地域差别。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必然导致城市文化娱乐生活变迁的不平衡。较大的、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城市首先接受西方文化,引起生活方式的变化,再向次一级城市传播,最后辐射到广大的内陆城市及乡村市镇。交谊舞在近代通商城市的流行也体现了这样一个特征。当大城市的洋派人物洋溢在西洋音乐、舞蹈的氛围里,在烛光摇曳的酒厅中举杯相庆圣诞、复活等洋节时,内地城市的人们却还不知提琴、洋笛为何物,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接受要滞后得多。
二、 舞会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近代国人通过多种途径初步认识了西方舞蹈,但西方舞蹈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播和流行,并且成为国人一种新的娱乐生活方式则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追根溯源,西方舞蹈从清末引入,到民国时期流行,大概经历了80多年的时间。
最初西方舞蹈在中国是作为正式宴会后的余兴节目在外侨中流行。上海最早的舞厅是作为外侨专门的娱乐场所而存在的,在形式上主要是作为饭店、夜总会或俱乐部所属娱乐设施的一部分,并不是独立的对外经营的专门的娱乐场所。据记载,1852年建造的礼查饭店已附设舞厅,可以说是上海近代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家。此后,建于1864年的英国总会,建于1866年的汇中饭店,建于1883年的一品香旅社,建于1910年的大华饭店等都是当时非常豪华的高级饭店,都开设有舞厅、酒吧。这些舞厅每逢周末都要举行茶舞,主要接待各国在沪的侨民、外交官员、海陆军官及少数买办,不对外营业,甚至不让中国人进入。受西方娱乐方式和经营理念的影响,19世纪晚期,中国的一些买办、富商也开始投资开设舞厅。1885年,上海张园内,“安垲第大楼内设舞厅,乃是上海第一家舞厅,也是中国人开设舞厅之始”[10]46—47。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志琴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的记载,1893年,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吴宗濂曾上奏清廷,推广舞会,作为与西方人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后由于甲午战争的爆发,此议被搁置。但从此言论看,舞会已被近代开明人士所接受,并力图推动政府官方的支持,是西舞东传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的一个节点。
据记载,中国官方最早举办的交谊舞会是驻外使节为了入乡随俗,便利外交,在驻外使馆举办的。其中最早的记载是1880年2月5日,曾纪泽在巴黎驻法使馆举行的舞会:
酉正,所请饮宴之客:法国赴华新公使布蕾、外部侍郎热路及爱尔倍尔特夫妇、波斯公使夫妇……德在初,房东力格先后来,戌初二刻入席,亥初散。
送客至楼厅后,即至客厅立迎茶会诸客一千二百余人,丑初以后,来者微稀,诸客跳舞极欢,寅正乃散。[5]310
此次舞会参加的宾客非常多,1200余人,从“诸客跳舞极欢”的记载中,可见舞会举办的效果不错,多年后还有人提及。
在国内,中国官方举行的第一场大型舞会应是1897年11月4日上海道蔡钧为配合慈禧“万寿庆典”,在上海洋务局举办的,“以中国人员而设舞会娱宾,此为嚆矢”。该舞会共发出请柬600封,均“红笺金字,封以华函”。实到500余人,多系在沪外国人、清方官员、社会名流等。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人们对在华举办舞会的兴趣和争议也越来越大。有人投书《格致新报》询问:“西国男女,每于夜间会聚一处,跳舞为乐,殊属陋习……能言有弊与否,请为畅言,以开茅塞。”对此,报馆明确告答:“西人光明磊落,脱略为怀,虽男女聚会跳舞,乐而不淫,与中国之烧香赛会,男女混杂,大有天渊之别。”[8]64—65对西方的跳舞习俗给予了肯定,认识得比较深刻,预示着这种西方风俗将被中国社会所认同。
这样的舞会属于临时性质,在清末也比较少见。民国初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女开始模仿西人,参加或者举办交谊舞会。如1914年阳历元旦的广州按照西方的习俗,“军队休假7日,文员休假3日,庆祝新年。民间多主遵行旧历,故无庆祝者。欧美大学中国毕业生之寓此者于除夕夜开亲睦会,聚宴跳舞,且有妇女与会。”[11]北京的排场更大。2月5日,外交部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开跳舞会,中外宾客到者1000余人。……各国公使皆到,其夫人亦到,国务总理熊君亦到,各部总长及重要人物亦多到,中外报界亦到。”[12]近代著名的记者黄远庸评论外交部茶会上的跳舞:“西洋礼法最佳,此等社交,乐而有礼,男女和合,故最能怡悦心情,较之中国人每会必为牧猪奴等戏者大异矣,故必此等社会发达,而后风俗移易。”[13]376对于交谊舞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及上流社会的提倡,为交谊舞的进一步流行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后,跳舞逐渐在大众社会流行,在大的通商城市,各式舞厅林立,越来越豪华,跳舞人士也越来越多,一度出现了“跳舞热”。《小日报》描述了1928年上海市民跳舞的盛况:“今年上海人的跳舞热,已达沸点,跳舞场之设立,亦如雨后之春笋,滋茁不已。少年淑女竞相学习,颇有不能跳舞,即不能承认为上海人之势。”[13]天津《大公报》也记载:“跳舞一事,在天津已经是很盛行。一般占洋气的饭店,因为想求事业上的发达,经济上的胜利,不得不有极精美的跳舞场,去迎合一般自以为新青年人们的心理,所以这些爱出风头的男男女女们,如癫似狂,争先恐后,去学习跳舞。”[14]跳舞逐渐成为人们一种新的娱乐生活方式。
三、西舞东传的影响
西方舞蹈在中国的传播和流行,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人们的休闲娱乐、价值观念等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归纳起来,可以看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心理由保守向开放演变。对于西式交际舞在近代中国都市中的传播,中国人经历了“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的过程。当西式交际舞刚在中国登陆只在外国人中流行时,中国人对这种礼俗表现出来的是惊愕,只是作壁上观,一个看客而已。然而一旦这一娱乐形式在国人中流行,并被男女青年纷纷效仿的时候,文化上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反对之声甚嚣尘上,一场大辩论在大都市中展开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于天津、上海、北平等大都市的“禁舞风波”,就是典型的文化冲突的例子。对此,左玉河《跳舞与礼教:1927年天津禁舞风波》(《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一文,马军《1948年:上海舞潮案——对一起民国女性集体暴力抗议事件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就当时的禁舞风波和舞潮案做了详尽探讨,在此不赘述。尽管各地的禁舞风波炒得沸沸扬扬,但大多数人对西式交际舞并不反对。尤其是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西式生活方式在中国传播极快,在潮流的推动下,抵制取消交际舞显然是不可能的。相反,经过辩论,人们对交际舞有了观念上、性质上、目的上、影响上的进一步认识,更多的人接受并喜爱这种西式娱乐。
第二,促进了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首先,中国传统男女大防的观念发生重大转变。交际舞传入中国,在很长时间里并不被中国人接受,中国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限制了交际舞在国人中的流行。交际舞只是在使馆区或者租界举行,参加者大多是西人,虽然和中国的礼法相悖,但对中国人的道德伦理尚不构成威胁。然而都市中的男女青年喜欢上了跳交际舞,是对“男女授受不亲”传统礼俗的巨大挑战,守旧者认为这有伤风化,非比寻常,就会跳出来横加指责,由此引起了国人的激烈论争。但是“随着五洲万国文物人事之相接日繁日近,中国固有的传统礼节便‘不得不有所迁就,改良实时势使然’。由此早年认为男女合群手舞足蹈‘有伤风化’避而不观的中国人,随跳舞潮流由领海一带向内陆澎湃涌来,其旧有之念渐次华离犋碎。”[15]115其次,促进了社交公开,男女平等观念逐步建立。在光怪陆离、形形色色的都市文化生活中,夜上海的舞厅成为很多年轻女性沐浴现代生活的场所,为中国树立了男女公开社交的文明生活方式的典范。由于社会日益开放,西式交际舞作为都市一种流行的新式娱乐,并不是男人的专利,也成为都市女性追求的一种时尚。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参与,特别是一些上流社会的年轻女眷打破禁锢,会时常组织一些交际舞会,或者到舞厅跳舞。
第三,助长了崇尚奢靡的社会风气。随着西式娱乐的传入,人们的生活追求日趋奢靡。就舞厅消费来讲,由于跳舞活动日益普及,舞票的价格日趋平民化,在那时1元钱可以购买普通舞票7至10张,有的甚至买到16张,并不会耗费太多的金钱。但在舞厅的其他消费中,可能只是几杯香槟,给舞女一些小费,多了就很难估计,有的舞客在舞女身上花钱不计其数,挥金如土,甚至倾家荡产。舞女的消费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奢靡之风。比如当红舞女的各种消费支出就非常浩大,再加上互相攀比,衣食住行都非常讲究,因此常常入不敷出,就得依靠舞客们的巨额供给,其中的代价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滋生了娱乐色情化的倾向。色情化的娱乐环境是20世纪30年代夜上海的一大特色。除了妓院之外,被变相的各式各样的色情活动所污染的娱乐场所最典型的当属舞厅。作为舞女这一职业,本来是在近代社会变迁的情况下女子为生计而从事的正当职业的一种,依靠的主要是舞技,和妓女是不同的。人们热衷于跳舞,原本是作为追求时尚的一种娱乐方式,但是随着娱乐商业化的发展,特别是舞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商家为了追求利润刻意营造色情化的娱乐氛围。时人曾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迷恋跳舞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它含有神秘性诱惑性习惯性和麻醉性的缘故……半裸的雾谷轻盈,全身的肌肉,隐隐显露在你面前,绯红的樱唇,波纹的黑发,柔媚的双眸,细腻的纤手,混合了一片脂粉,肉和酒的香味,真使人陶醉,使人迷恋”。[16]282由于深陷色情化之中,“舞厅也沦为一个社风日下,色情角逐的黄色境地,完全迷失了其本来的面目。”[16]282因此,“到三十年代,舞厅成了上海城市环境的另一个著名,或说不名誉的标记。”[17]28南橘北枳,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生活方式的变动,是伴随着社会转型发生的。近代中国新与旧、中与西、保守与现代等各种力量和矛盾交织,社会形态发生千年未有之变化,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相伴而变,逐渐由传统走向现代。
西方舞蹈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并成为国人一种新的娱乐生活方式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反映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由陌生、新奇、甚至排拒到交流、融合这样一个大趋势。虽然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但是却打破了中国城市民众精神世界的封闭、单调与宁静,人们逐渐开始接受和仿行西洋生活方式,并顺应中国文化加以改易和创新,传统的娱乐生活方式抑或逐渐衰微、消亡,抑或适时增添了不少新内容而发生着变异。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生活方式由此日益走向西化、多样化和现代化的变迁过程,中国社会呈现出移风易俗的新气象,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1] 王克芬,隆荫培.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
[2] 斌椿.乘槎笔记[A].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一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8.
[3]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A]. 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四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8.
[4] 刘锡鸿.英轺私记[A].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七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8.
[5]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A].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五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8.
[6] 蒋梦麟.西潮与新潮[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7] 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
[8] 刘志琴,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9] 李长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10] 张伟.沪渎旧影[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11] 罗检秋.近代中国社会文华变迁录:第三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2] 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3] 李洪华.都市的“风景线”与“狐步舞”——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公共空间与现代派的文学想象[J].江西社会科学,2007,(3).
[14] 左玉河.跳舞与礼教[J].河北学刊,2005,(5).
[15] 扶小兰.论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生活方式之变迁[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
[16] 楼嘉军.上海城市娱乐研究[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
[17] (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上海:三联书店,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