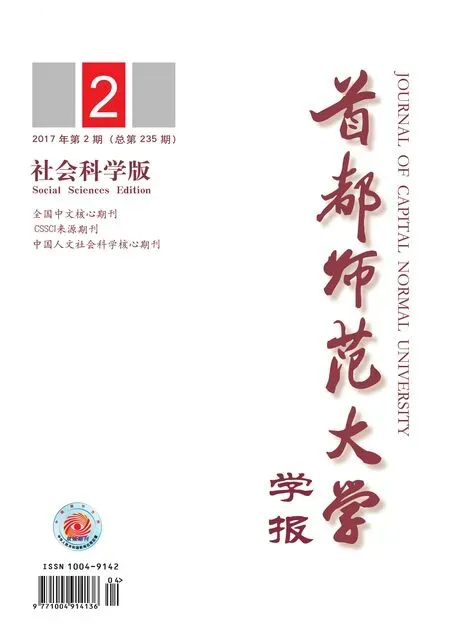学术流派研究平议
周 群
摇曳多姿的学术流派是构成中国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序》中曾有这样形象的比喻:
在黄宗羲看来,探求大道的学术史之浩瀚海洋是由江、淮、河、汉等万派支流的汇注而成的。学派各自不同的特点,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学术史缤纷多彩的篇章,只有将不同学术流派的特点呈现出来,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学术发展的大势。但目前学界对于学术流派研究中的一般性问题鲜有论及,故而对学派研究的价值、问题以及成因进行必要的理性思考,略呈管见,以期能引起对于中国学术史上诸多“江、淮、河、汉”研究的重视。
一、学派研究的价值
学术流派是构建中国学术史的重要单元,学术流派之间以及学派内部的争鸣增强了学术变革的动能。如果说某一个杰出的学术宗师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闪光点,那么,以其为核心的一个学术流派则呈现了面与线的风貌,林林总总的学术流派是构成中国学术史斑斓画卷妍姿各别的扶疏花叶。
学派间的激荡互动及不同学派的意脉赓续是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因。学派通过学术争鸣,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书写了中国古代色彩斑澜的学术发展史。这首先体现在不同学派的论争与互动之中。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就是以不同学派的形式出现的,虽然春秋时儒墨并称显学,但文献又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注]陈广忠译注:《淮南子》第二十一卷《要略》,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67页。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激荡互动增强了学术的创新动力。学派之间的互动与承续隐然存在于学术史的过程之中。如,宋代影响较大的几次讲会就是不同学派宗师或钜子之间的论辩,如,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与张栻在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淳熙五年(1178年)陆九龄和朱熹的铅山崇寿观音院之会等,成为当时的学坛盛事,大大地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当时的东南三贤张栻、朱熹、吕祖谦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湖湘学派、朱子学以及金华学派鼎立而三。三个学派因竞争而相互汲取,使各自的学术思想更臻于成熟,诚如黄宗羲所言:“朱子生平相与切磋得力者,东莱、象山、南轩数人而已。东莱则言其杂,象山则言其禅,惟于南轩,为所佩服,一则曰:‘敬夫见识,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一则曰:‘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表。近读其语,不觉胸中洒然,诚可叹服。’然南轩非与朱子反复辩难,亦焉取斯哉!”[注](清)黄宗原著 全祖望修补,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北京:中华书局本,1986年版,第1635页。湖湘学派的中坚张栻也通过与朱熹的论学而改变了湘学发露有过之失而得从容平正之气象。学派之间或隐或显的历时的因革关系错综复杂,为学术的融铸创新创造了条件,并成为揭示学术发展逻辑进程的线索。如,晚明时期尊坡之风独盛,时人乃至对文坛现象曾有“东坡临御”之喻。尊奉东坡的原因固然因为苏轼与晚明文人都具有通脱灵变的文学主张,漠视陈俗、自铸新词的革新精神,而明人董思白则云:“程苏之学角立于元祐,而苏不能胜,至我明姚江出以良知之说,变动宇内,士人靡然从之,其说非出于苏,而血脉则苏也。”[注]引自(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紫柏评晦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9页。董氏所云洵为的论。虽然明代士人并非直祧苏氏蜀学,但明代后期阳明学的流行正是与文坛“东坡临御”的现象同时出现的。袁宏道赞叹“苏子瞻、欧阳永叔辈见识,真不可及”[注](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江进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15页。。其“见识”,便是与洛学迥绝的人性论、文学观。董氏所论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学术流派历时赓续所呈现出的复杂关系。
学派内同道的相互切劘、补益是学派形成理论张力的重要机制。学派不是学术旨趣完全相同的学人的群体,而是学术观点同异相兼的动态的学人集群。学派的开派宗师往往是首开风气的学术先进,“德不孤必有邻”,这些宗师往往最早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洞察到学术发展的新的进路,这又必然会受到敏锐的学人们的应和。他们或声应气求,激浊扬清,去短集长,共同为学派的肇兴奠定了基础。如汪中、阮元、焦循、任大椿、刘台拱和高邮王氏互相推挹,他们都是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更多的则是在开派宗师立说的基础上,通过设坛讲学,经高第弟子的薪传与新变得以流播,在学坛及社会形成昭著的影响。如,阳明学是因“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注]《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03页。,亦即阳明学的巨大影响与阳明学的弟子王艮(泰州)、王畿(龙溪)等为代表的王门后学的学术活动密切相关。但王门后学则错综复杂,他们在不违阳明良知之教的前提之下,持说各异,辩论甚烈,如,王畿与钱德洪天泉证道时关于“四无”、“四有”的论辩,王畿与聂豹、罗洪先关于良知的寂与感、未发与已发的论辩,王畿与黄绾关于慈湖之学的论辩,聂豹与钱德洪关于后天诚意之学的论辩,季本与王畿、聂豹等人关于“龙惕说”的论辩等等。他们持论各极其至,其情形诚如王畿所说:“良知宗说,同门虽不敢有违,然未免各以性之所近,拟议搀和:有谓良知非觉照,须本于归寂而始得,如镜之照物,明体寂然而妍媸自辨,滞于照,则明反眩矣。有谓良知无见成,由于修证而始全,如金之在矿,非火齐锻炼,则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谓良知是从已发立教,非未发无知之本旨。有谓良知本来无欲,直心以动,无不是道,不待复加销欲之功。有谓学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体用。有谓学贵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无内外,而以致知别始终。”[注]《明儒学案》卷十二《浙中王门学案》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1页。阳阳明学派内部多维度的深入论辩,丰富了阳明学派的理论内涵,共同成就了阳明学的繁盛局面。再如,泰州学派由王心斋开其端,形成了以淮南格物、百姓日用即道、大成学为中心的学术思想。但心斋的表述明快通俗而疏于论证,而克嗣家学的王襞则较清晰地疏理了心斋之学的内在逻辑。心斋是一位平民思想家,其论学的目的在于使“愚夫愚妇能知能行”。心斋虽有“百姓日用即道”之论,但并无笃行之实,乃至“每论世道,便谓自家有愧”[注]《王心斋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泰州后学颜山农、何心隐等人则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施,通过建立“萃和会”、“聚和会”等乡村组织,将王艮儒学的民间化思想付之于实践,并以各自的行谊特征,彰显了泰州学派特有的精神风致。
对学派的评骘态度是蠡测学者为学旨趣的重要依凭。学派成员的别识标准主要是师承关系以及学术旨趣,但由于学者问师可能及于多门,学术旨趣也存在着历时演变与多元并存的特征。学者对学派成员的辨析与厘判也往往会基于各自的学术立场、历史情境而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因此,从学者对于学术流派谱系的描述之中,往往可以窥见其中诸多的学术信息,他们对学术流派的评骘本身即成为学术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对于清代浙东学派,章学诚认为是起自黄宗羲,经万斯同、万斯大,终于全祖望、邵晋涵。梁启超却认为应以章学诚为殿军。而章太炎则认为在章学诚之后尚有黄以周、黄式三。章学诚何以首先描述出浙东学派的基本谱系?钱穆先生认为:“实斋与东原论学异同,溯而上之,即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之异同。其在清初,则为亭林与梨洲;其在南宋,即朱陆之异同也。”[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26页。亦即章学诚描述浙东的学术谱系,目的其实是章氏本人溯浙东学术之源以为奥援,以与戴东原之学相颉颃。同样,章太炎将浙东学派学术史学在对“学派”的描述乃至“建构”的过程中,也清晰地表现了自己的学术祈向,并成为他们学术思想的有机部分而定格于学术史之中。同时,认清学者的学派归属,也有助于理解其学术立场,如,陈淳等人认为湖湘学派中坚张栻之学有得于朱熹,此说不实是因为陈淳乃朱熹晚年弟子,因此而崇朱熹而抑张栻,诚如全祖望所言:“北溪(陈淳)诸子必欲谓南轩(张栻)从晦翁(朱熹)转手,是犹谓横渠之学于程氏者。欲尊其师,而反诬之,斯之谓矣。”[注]《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序录》,第1609页。因此,认识学人的学派归属,也是分析其立论缘由的有效途径。
学派研究有助于理清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逻辑脉络。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源流色彩极浓,尤其是儒林中植矩度绳,斤斤自守者甚众。学术源流,先河后海,自有端绪。阳明的良知说,肇端于孟子;陈白沙所谓静养端倪,显然有得于周敦颐的主静说。学术的承祧与变异形成的内在张力是推进学术史演进的重要动因,因此,明乎学派源流统绪,实乃了解中国学术之津筏。如,对于吕祖谦之后的南宋浙学,全祖望的提示可为我们提供理解浙学诸派的源流概况:“浙学于南宋为极盛,然自东莱(吕祖谦)卒后,则大愚(吕祖俭)守其兄之学,为一家;叶、蔡宗止斋(陈傅良),以绍薛、郑之学,为一家;遂与同甫(陈亮)之学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陆,而自为门庭者。”[注](清)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四《奉临川先生贴子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3-1684页。再如,宋代道南学派的杨时在寓居毗陵时,曾设东林讲舍,讲学达十八年之久。明代的东林书院就是在东林讲舍遗址“建祠宇,立讲堂,仔肩道脉,启迪英贤”[注](清)高廷珍辑:《东林书院志》卷一《建置》,清雍正刻本。。道南祠与书院分列左右,并建于万历年间。东林得道南之意脉,能在姚江之学“风行天下”之时,独以承道南之学相标榜。对于东林承道南之脉,高攀龙在《东林原志序》中有明确的表述:“龟山杨先生上承洛统,下开闽传,其栖止于晋陵梁溪间,浮云流水之迹耳。而吾郡至今言学不畔洛闽,不忍曲学以阿世,于是见先生之精神大而远也。”[注](清)高廷珍辑:《东林书院志》卷十六。使明代晚期学坛呈现出了朱子学与阳明学并置共存的局面。可见,理清学术流派之间的意脉承传与变异,对于理解某些学术现象的产生大有裨益。
二、学派成因蠡测
学术流派一般是以师承关系为纽带,以相似的学术祈向或治学方法为特征而形成的学术群体。学术流派是因应一定社会政治要求、体现学术演进过程中逻辑关系的产物,是与古代教育制度、学术传承方式相关联的历史存在。
时代:学派形成的动因。学术流派是在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下产生,是因学术发展变化的要求而形成的。时代(政治的、学术的)是孕育学术流派的母体,因此,每一种学术流派必然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并因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如,南宋学坛以洛学承传为大宗,尤其是朱熹闽学产生之后,以明理证性为特征的成德之学蔚成风气,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虽然“致广大,尽精微”,但存在着重德性修为而轻事功实际的倾向。南宋政权的一时偏安也滋生了苟且度日,安坐待时的风习。值此而起的永康、永嘉学派则目击时艰,以实事实功相倡,期以改变理学家清谈脱俗,无视现实的学风,提出了与朱、陆理学相异其趣的学说。对于永康之学,黄百家云:“是时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注]《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32页。对永嘉之学,黄宗羲云:“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注]《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96页。他们以事功之学,外王之业作为论学的重点,期以警醒世人,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永康学派的代表陈亮“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注](宋)陈亮撰,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卷之二十八《又甲辰秋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9页。的成人理想,正体现了其恢复中原,大有为于世的时代精神。
儒学既是一种学术思想,同时也是封建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以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学术必然与社会政治絪缊难别,因此,学术流派与时代的关系还体现在政治环境对学术流派的巨大影响。由于传统的学术往往与既有的政治利益集团有关,因此,倡导某种学术思想往往因其新锐而受到正统派斥为伪学。宋崇宁二年(1103)范致虚上疏状告程颐以“邪说诐行,惑乱众听”,洛学便受到政治打压。南宋庆元初年,韩侂冑设伪学之禁,朱子学被斥为伪学。明代东林学派更以一曲“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注]《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75页。的时代悲歌而定格于历史。东林学派中人在“讲会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乃至“朝士慕其风者,皆遥相应和”。[注](清)万斯同撰:《明史》卷三百四十四《顾宪成传》,清钞本。晚明的政治与学术现实,是东林兴起的根本诱因,诚如钱穆先生所说:“盖东林讲学大体,约而述之,厥有两端:一在矫挽王学之末流。一在抨弹政治之现状。”[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章《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页。东林志士在鼎革之际“以血肉撑拒”,书写了学术与政治关系史上最为凄绝的一页。因此,相对自由的政治、学术环境,往往是学术流派产生的春天。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流派纷呈,学术“天下裂”的背景是: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起一统的观念形态。南宋学坛也曾出现诸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这也与南宋乾道、淳熙以来相对宽松的政治、学术环境不无关系。
时代与学术的关系往往是复杂多元的,这从清代乾嘉诸学派产生的背景中即可看出:一方面,在繁密的文网之下,读书人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只得以古书为消遣神明的林囿,他们以训诂考据为学术文化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影响(中)》,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康乾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乾嘉学派的兴起创造了外部条件。同时,还应看到乾嘉之学产生的内在动因:“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虽然理学在清代神脉不绝,但毕竟清人所尚的严考据、辨真伪的笃实学风与晚明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迥然有别。可见,学术流派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之下产生,体现特定学术发展进程的产物。
师承:学派形成与发展的显性纽带。中国古代尊师重教传统独盛,因此,师授也是学术传承的重要方式。古代学术流派源流不同,统绪各别,或本于家法,或基于师承,不同时期的特征亦稍有不同,诚如刘师培所说:“昔周季诸子源远流分,然咸守一师之言以自成其学;汉儒说经最崇家法,宋明讲学必称先师。”[注]刘师培:《左庵外集》卷九《近儒学术系统论》,《刘申叔遗书》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2页。比较而言,师徒授受的讲学传统是中国学术流派形成的重要条件,师承渊源往往决定了学者的治学方向与方式。如,吴派学者江声、余萧客等人对于宗师惠栋的学术笃信不疑,都缀次古义,唯汉学是从。江声受惠栋《古文尚书考》的影响,而成《尚书集注音疏》。余萧客早年曾以《注雅别钞》就正于惠栋,惠栋曰:“陆细、蔡卞乃安石新学,人人知其非,不足辨;罗愿非有宋大儒,亦不必辨。子读书撰著,当务其大者、远者。”[注]引自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余古农先生》,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页。余萧客闻之矍然,遂执贽受业称弟子,并一生服膺惠栋之教。一个学派的绵延发展,往往依靠完整清晰的师承关系得以保证。如,洛学的形成即与谢良佐、吕大临、杨时、游酢、尹焞等程氏高弟门人密切相关,这些门人递相传衍,影响绵远,乃至渐成新的学派系统。对此,真德秀云:“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氏传之延平李氏,李氏传之朱氏,此其一派也;上蔡传之武夷胡氏,胡氏传其子五峰,五峰传之南轩张氏,此又一派也;若周恭叔、刘元承得之为永嘉之学,其源亦同自出。然朱、张之传最得其宗。”[注](宋)真德秀撰:《读书记》卷三十一《张子之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洛学在南宋以清晰的师承关系,渐而分宗衍派,共同组成了南宋学坛的基本格局。同时,师承因方式的不同又分为门人与私淑两类。私淑弟子是未能及门受教而敬仰并传承其师学说者。南宋湖湘学派先驱胡安国虽然与程门弟子过从甚密,但并无及门二程的经历,云:“吾于谢(良佐)、游(酢)、杨(时)三公,义兼师友,实尊信之。若论其传授,却自有来历。据龟山(杨时)所见在《中庸》,自明道(程颢)先生所授;吾所闻在《春秋》,自伊川(程颐)先生所发。”[注]转引自《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56页。同样,罗洪先一般被认为是阳明门人,但罗氏本人则坚称后学,便是因为阳明在世时罗洪先未能及门委贽,罗氏堪称阳明私淑弟子中最为卓荦者,诚如邓定宇所说:“阳明必为圣学无疑,然及门之士,概多矛盾。其私淑而有得者,莫如念庵。”[注]转引自《明儒学案》卷十八《江右王门学案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0页。可见,门人与私淑仅是奉师形式之别,钱德洪因此而将弟子分为“表所闻”与“表所信”两类:“始未有闻,僚也,友也;既得所闻,从而师事之,表所闻也。始而未信师学于存日,晚生也;师没而学明,证于友,形于梦,称弟子焉,表所信也。”[注]引自《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七《答论年谱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2页。门人与私淑,“所闻者”与“所信者”都是学派传承与发展的基本力量。
学术观念与方法:学派的灵魂。仅仅以明晰的学术师承未必能形成一种学术流派,因为没有自身学术特征的学术群体并不能为学术史提供新的成分,一个新的学派的形成往往是开派盟主为首的学者能自张新说,或具有独特的治学方法乃至卓尔不群的人格魅力,才能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之效。如,洛学中的程氏昆仲“自家体贴出”“天理”二字,朱熹谓二程之学“使夫天理之微,人伦之著,事物之众,鬼神之幽,莫不洞然毕贯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传,焕然复明”[注](宋)朱熹撰:《晦庵集·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虽然朱氏之论不无承祧者的溢美之偏,但他们思想之精微细密,恰如牛毛茧丝,无不辨析,使中国思想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这也是其后占据思想史主流地位的重要原因。再如南宋铮铮一时之盛的湖湘学派反对空谈性命,强调“致知力行,知行并进”,集大成者张栻的门人或再传弟子身处偏安之世而多负用世之才,诚如全祖望所说:“南轩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其最显者为吴畏斋、游默斋,而克斋亦其流亚云。”[注]《宋元学案》卷七十一《岳斋诸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83页。全氏在评述张栻高弟彭龟年时又云:“如先生者,有得于宣公(张栻)求仁之学,而施之于经纶之大者,非区区迂儒章句之陋。而其好用善人,则宰相材也。”[注]《宋元学案》卷七十一《岳麓诸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79页。湖湘之学的传人学以致用,成为艰危世况中的一批卓荦之士,其称盛于南宋学坛与其强烈的经世特征密切相关。清代常州学派最初是由庄存与以及刘逢禄、宋翔凤等人而兴,但常州学派后期的学脉流传主要不依师承、里籍,而以治学方法为主。其后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人便不是常州人,与常州学派宗师亦无直接的师承关系,但由于他们论学都以公羊学为核心而期以经世,一改乾嘉脱离现实的考据学风,这也是他们被视为常州学派传人的重要依据。与显性的师承关系相比,学术宗旨更能体现学术流派的本质特征,对此,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列《止修学案》堪称垂范。李材(号见罗)从学于阳明门人邹守益(号东廓),但黄宗羲并未将其与邹东廓一起见列于江右王门,而是另立《止修学案》,云:“见罗从学于邹东廓,固亦王门以下一人也,而别立宗旨,不得不别为一案。”[注]《明儒学案》卷三十一,《止修学案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见,以学派宗师为代表的学术旨趣往往是学派的主要标识,学派向心力的基本内核,以及学派传衍的意脉所系。
家学:学派传衍的稳定因素。家学是师承关系之外中国古代传学的另一个重要途径。这在春秋前“学在官府”时期即已蔚成风气,当时的文化知识掌握在世卿世禄的官吏手中,他们子嗣父业,别人无以染指。汉代经学传承亦复如是,当时的经学家虽门生众多,但都视子孙为传承正脉,克绍箕裘以使家门不坠,家学与士族的形成互为因果,诚如钱穆先生所说:“自东汉以来,因有累世经学,而有累世公卿,于是而有门第之产生,自有门第,于是又有累世之学业。”[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76页。学术流派的传衍亦复如是。如,以昆仲为主体的学派: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洛学,以苏轼、苏辙为代表的“苏氏蜀学”,陆九渊、陆九韶、陆九龄的“三陆之学”等;以吕祖谦为首的东莱学派中吕氏宗亲数量更多,有其弟吕祖俭、从弟吕祖泰,子吕延年、从子吕康年,吕祖俭子吕乔年等。再如,湖湘学派之胡宏、子胡大时与张栻的关系是:“南轩(张栻)从学于五峰(胡宏),先生(胡大时)从学于南轩,南轩以女妻之。”[注]《宋元学案》卷七十一《岳麓诸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69页。常州学派之中的庄存与、弟庄培因、侄庄述祖、外孙刘逢禄,庄培因外孙宋翔凤等,前后相继,使乾隆时期尚为孤家之学的春秋公羊学渐成复兴之势,迄至晚清已蔚成大宗,其中前期庄氏的家学传承起到了主要作用。学术流派中的家学传承因其特有的亲和力,便于成员之间的切磋与交流,如,常州学派的庄述祖尝云:“吾诸甥中,刘申受可以为师,宋虞庭可以为友。”因亲属关系,当晚辈以学问就正时,庄述祖“谆谆诲诱,未尝有所隐也”[注]以上引自(清)宋翔凤:《朴学斋文录》卷四《庄珍艺先生行状》,清浮溪精舍丛书本。。家学传承增强了学派形成时的基本凝聚力以及代际传承时学术特质的恒定性。正因为如此,《宋元学案》于体例之中,专列“家学”一目,以与“讲友”、“学侣”、“同调”并列。当然,这一特征也往往限制了学派的更新与发展,某些学派持论矫激色彩难以消除,亦与家学因素不无关系。清代皖派之所以能够唯是以求,而不墨守成说,这与其宗师江永、戴震都没有家学传统有关。
书院讲学:学派形成的重要平台。宋代理学产生之后,学术流派纷呈。而理学的传播又与书院讲学之风盛行密切相关,尤其是未纳入官办学校系统时期的书院,有较自由的讲学风气,给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场所,诚如吕祖谦所说:“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注](宋)吕祖谦:《东莱集》卷六《白鹿洞书院记》,续金华丛书本。钱穆在论及宋学精神与书院的关系时说:“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章《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页。书院讲学便于学派盟主宣陈学术思想,强化了师生以及同门之间的联系,为形成稳定的学派阵营以及学术传衍提供了重要平台。如,朱熹在复兴白鹿洞书院之后,首登讲台即讲《中庸》,书院成为其传播以“四书”学为本的理学思想的重要场所。湖湘学派张栻讲学于岳麓书院,实乃湖湘之学在乾道、淳熙年间盛极一时的关键因素。而吕氏昆仲在金华明招山丽泽书院的讲学活动,则开启了金华学派的端绪。诚如全祖望所记:“岳麓、白鹿以张宣公、朱子而盛,而东莱之丽泽,陆氏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则又南宋之四大书院也。”[注]《鲒埼亭外编》卷四十五《答张石痴徵士问四大书院帖子》,(清)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3页。对书院重视程度直接关系到学派的兴衰,这从宋代洛学与蜀学的比较中便可以看出。洛学学者十分注重书院讲学以弘传本派学术,如,程颐在河南的伊皋书院讲学二十余年。洛学传人亦秉承这一传统,充分利用书院讲学的机会传扬洛学,二程弟子周行己返里之后,在家乡创置浮沚书院以传关洛之学。而曾与洛学相角的苏氏蜀学则不太重视书院讲学的作用,乃至使传承洛学学脉的谯定等人传道于蜀地书院。其后的洛蜀会同以及蜀学复兴,实际是承传濂洛之学的张栻及门、私淑弟子通过书院在蜀地传学的结果,此时之蜀学已非苏氏蜀学。“程苏之学角立于元祐,而苏不能胜”,不可忽略的原因在于洛、蜀对书院的重视不一。明代前期因科第功利所趋,书院讲学之风一度中衰,但随着湛若水、王阳明的平分讲席,书院讲学又成风行之势,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诸生闻其名纷纷负笈来学,阳明在龙冈山阳明洞开办了龙冈书院,讲学不辍。其后又在府城文明书院首次讲论知行合一说,可见,阳明学的形成与传播,首先是从书院讲学开始的。阳明之后,高弟弟子们四方讲会,促进了阳明学的传播以及阳明后学的分宗衍派,据载:“阳明殁后,绪山、龙溪所在讲学,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庙会,泰州复有心斋讲堂,几乎比户可封矣。”[注]《明儒学案》卷二十五《南中王门学案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9页。书院讲会的盛行是阳明学“风行天下”的重要原因。
三、学派研究的理性思考
历史上存在的诸多学术流派堪称是中国学术史中最具特色的篇章,对各个学派的分别剖析是研究学术史的必要途径。对学术史的宏观把握又是厘定具体学派历史地位的前提。因此,欲全面准确地呈现中国学术的演变史,亟需对学术流派进行系统研究。尽管如此,中国学术史并非诸学术流派的简单累加,学派研究还需要秉持理性的态度,摒除历史迷障,客观认识学派研究价值的相对性。
客观评价的复杂性。学术流派的内容各各有别,在历史上所受到的重视以及社会、学术意义各有不同。学派的影响及命运殊异的原因颇为复杂,但与传统文化中学术理想化、形上化的倾向不无关系。儒学实乃成德之教,尤其作为内圣外王之学的理学形成以来,学人们重内圣而轻外王,亦即重成德而轻事功的倾向十分明显。理学家们重内圣以立本并无不妥,但一味地谭道证性,穷高极远,鹜于空言,必然使学术脱离社会。尤其是理学被悬为功令之后,更成为利禄工具,失去了扶世教、正人心的作用,渐成空洞的道德说教。事实上,这样的取向在宋代即已露出端倪,诚如四库馆臣所言:“盖理宗以后,天下趋朝廷风旨,道学日兴,谈心性者谓之真儒,讲事功者谓之杂霸,人情所竞,在彼不在此。”[注](清)永溶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六《宗忠简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44页,中。这在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那里体现得更加充分。朱熹与陆九渊虽然论辩甚烈,但朱熹对当时主功利的浙学的贬斥更加峻厉,云:“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注](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967页。朱熹之忧乃是基于学术当以研讨德性为本,而不应成为功利实用之学。事实上,理学家们论学都重明体达用,将体用一致发挥到了极致,但忽视了体用之间的差异性,完全以成德代替事功,贬斥功利之学。明代大学士邱浚作《大学衍义补》,以补宋人真德秀《大学衍义》止于格致诚正修齐而未及治国平天下之不足。尽管邱浚闻见甚富,颇资实用,且受到了明神宗的激赏,御制序文,嘉许其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补政治,特命将其刊播天下,以昭示帝王明德新民图治之意,但仍被正统儒者视为“议论不能甚醇”[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三《大学衍义补提要》,第791页,上。。因此,今天对于学术流派的评价,需要摆脱传统思维定势,清除历史迷障,以更平允、客观的心态,正确认识不同学派各自的价值。
学派厘判的相对性。学术流派多是学术史家对于具有独特学术风格,具有师承关系的学者集群的称名,不同的学术史家对于同一学派可能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流派的区别难免存在着主观因素。同时,学术流派虽然往往是学术史上最具风采的篇章,但学术史并不是诸学术流派的总和。虽然历史上不乏坚守各派壁垒的学者,但“君子欲其自得”[注]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离娄章句下》,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89页。,力避因袭雷同乃是学人的基本价值取向。就儒学而言,虽同尊孔孟,阐论性命,但诚如《周易·系辞》所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学人们立言垂教,途辙有别,各抒其独得之妙,诚所谓“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注]《明儒学案序》,《明儒学案》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页。。因此,学者超越于学派之外的学术独创性理应受到重视。还应看到,学派之间交互作用,学者取法多元,超越于门户所囿,汇通而自成其说的现象在中国学术史上也在在可见。不同学派之间的互融互摄是普遍存在的历史事实,如,宋代关学宗师张载去世之后,关学弟子吕大忠、吕大均、吕大临等都成了程门高足。此外,在学术史上仍有一些戛戛独造的学者并不为一定的学派所能涵括,诚如梁启超所说:“其实各派共同之点甚多,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说他们专属哪一派。”[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可见,学术史的多元复杂性并不能仅凭学派疏理得以全面呈现。学派研究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环节,但并非学术史研究的全部。
学派特征的历时变化与价值衰减。如前所述,学术流派的产生是因特定的社会政治、学术环境而产生的,其学术意义往往也与特定的时代情境相关联。但学术流派又是一个历时发展的过程,一般经历数代学者乃至多达数百年的传衍发展。在历时流变过程中,学派特征也随之发生变化,如,金华学派初创于吕祖谦,其与朱熹、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全祖望《北山四先生学案序录》云:“勉斋(黄干)之传,得金华而益昌。说者谓:北山(何基)绝似和靖(尹焞),鲁斋(王柏)绝似上蔡(谢良佐),而金文安公(金履祥)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注]《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25页。尹焞在洛学中为晚出,但“守其师说最醇”[注]《宋元学案》卷二十七《和靖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01页。。谢良佐则被时人推为洛学之魁,谢、尹都是得洛学正脉的学者。可见,当时金华之学乃执守理学矩矱,纯然以道学名世。但其后金华之学则悄然发生了变化,黄百家云:“金华之学,自白云(许谦)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也,犹幸有斯。”[注]《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01页。许谦虽然执守于道学义理的传统,以《四书》为的,云:“圣人之心,具在《四书》。”但又兼及考据:“于《诗》则正其音释,考其名物度数,以补先儒之所未备。”[注]以上引自《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57页。深受其影响的张枢、吴师道等人则“文采足以动众”[注]《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61页。。由道而文的变化至元明之际的宋濂更加明显,虽然对于早年以古文辞为事而悔之、愧之乃至恨之,但宋濂仍然是以“开国文臣第一”见著于历史,被朱元璋“首用文学受知,恒侍左右”[注](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宋濂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784页。。宋濂以辞达而道明相倡,但并不以理学义理分疏见长,文显道薄则是不争的事实。可见,金华学派的学术特征有一个嬗变的过程。学派特征的因时而变,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且有变化而开出一新境界者(如常州学派),但毋庸讳言,大多数学派在流变过程中往往淡化了自身特色,这势必会弱化该学派作为历史存在的价值。摇曳多姿的奇花异卉渐而变成弥望皆是的黄茅白苇,良可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