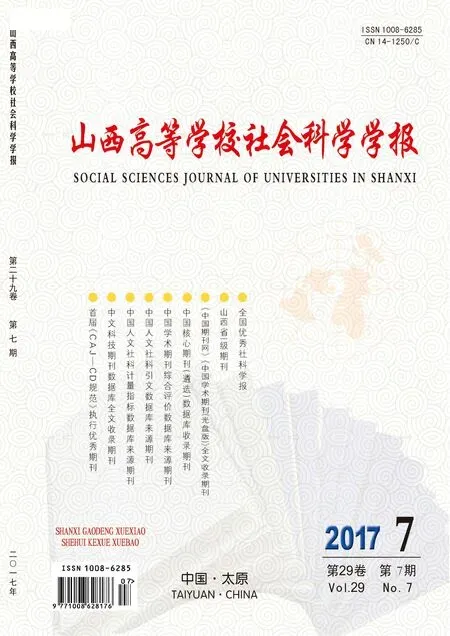中国人缺乏公德现象及其解决之方
——基于梁启超、费孝通、梁漱溟论述的考察
王生云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中国人缺乏公德现象及其解决之方
——基于梁启超、费孝通、梁漱溟论述的考察
王生云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梁启超曾提出中国人缺乏公德的命题,梁漱溟赞同之,费孝通亦有类似之观点。究其原因,梁启超认为因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的儒家经典私德有余而公德不足造成,梁漱溟认为中国过去的社会缺乏集团生活而导致,费孝通认为是中国文化中的消极的差序格局形成自我中心的“私的毛病”。论解决之方,梁启超主张由私德拓展延伸为公德;梁漱溟主张引固有伦理入团体生活;费孝通主张挖掘社区文化培养共同感,由自我中心的消极差序格局变为推己及人的积极差序格局。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欲落实上述三先生的方案,需要注意冯友兰提出的教育工厂化后道德教化归社会精英人物引领的问题以及李泽厚有关价值多元与公德统一性(一道德)问题的思考。
公德;梁启超;梁漱溟;费孝通;积极差序格局;冯友兰;李泽厚
一、公德问题的提出:中国人缺乏公德
中国自古以来有君子小人之辨,是一个非常讲道德讲文明的国度,然而1902年梁启超在《论公德》中劈头赫然提道:“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1]16让我们意识到一个深明君子小人之道,追求高尚道德的中国人,竟然“缺德”——缺公德。梁启超解释了什么是公德。他说:“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此西儒亚里士多德之言)。人而不群,禽兽奚择。而非徒空言高论曰群之群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1]16同时做了公德与私德的区分,并认为公德与私德同源于道之本体,是道的一体两面。他说:“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1]20梁启超认为中国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与西方新伦理(家族、社会、国家)相比较,只有朋友一伦接近社会伦理,其余均属于私德,偏于私德而公德不显,国家社会之团结不能实现;公德的缺失让中国人常常奉行独善寡过主义,“我国民中无一人视国事如己事者”[1]20。因此,要大力提倡公德。
关于缺少公德问题,费孝通先生表述为“私的毛病”。在其《乡土中国》中,提道中国人“各人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中国人性格——私。费孝通通过苏州的村民们对待公家之河态度和方式的例子来说明老百姓对国家的事情不关心或者只想从公家那里占点便宜。他写道:“苏州人家后门常通一条河,听起来是最美丽也没有了,文人笔墨里是中国的威尼思,可是我想天下没有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什么东西可以向这种出路本来不太畅通的小河沟里一倒,有不少人家根本就不必有厕所。明知人家在这河里洗衣洗菜,毫不觉得有什么需要自制的地方。为什么呢?——这种小河是公家的。”[2]30他还接着说“私的毛病”非常之普遍,“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了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2]30。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绪论中概括众人的十个特点之一即是“自私自利”:“身家念重、不讲公德、一盘散沙、不能合作、缺乏组织能力,对国家及共同团体缺乏责任感,徇私废公及贪私等。”[3]27在《中国文化要义》第四章中,梁漱溟把中国人所缺的团体精神概括为四个大方面,即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他说:“这四点亦可以总括以‘公德’一词称之。公德,就是人类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质量。这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3]64
梁启超、费孝通和梁漱溟三位学者都认为中国人缺乏公德,只是他们论述的侧面不一样罢了,当然他们指的并非全部中国人,而是典型的中国人。时至今日诸如“中国人缺公德”之类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只是在批评的同时很少有人去深究其深层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人会缺乏公德或者公德意识呢?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以上三位学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中国人缺乏公德的原因,并给出相应的解决之方。
二、中国人公德缺乏的原因
关于中国人缺乏公德或公德意识的原因,三位学者都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探讨。作为第一个揭示“公德”话题的梁启超指出,作为中国道德文化源头——儒家的经典如《论语》《孟子》所讲的十之八九都是私德,而公德不及一,重私德而废公德。他在《公德论》中如是讲道:“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如《皋陶谟》之九德,《洪范》之三德,《论语》所谓‘温、良、恭、俭、让’,所谓‘克己复礼’,所谓‘忠信笃敬’,所谓‘寡尤寡悔’,所谓‘刚毅木讷’,所谓‘知命知言’,《大学》所谓‘知止,慎独,戒欺,求慊’,《中庸》所谓‘好学,力行,知耻’,所谓‘戒慎恐惧’,所谓‘致曲’,《孟子》所谓‘存心养性’,所谓‘反身、强恕’……凡此之类,关于私德者发挥几无余蕴,于养成私人(私人者对于公人而言,谓一个人不与他人交涉之时也)之资格,庶乎备矣。”[1]16-17然而他并未深入分析为什么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会重私德而废公德。
梁漱溟并没有停留在对塑造国民的经典之分析上,而是将中国人赖以生活的“社会存在”作为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并层层推进,最后归结为中国文化的“理性早启”问题。首先,他指出中国人缺乏公德是因为缺乏公共生活即集团生活。那为什么中国人会缺少这种集团生活呢?他的回答是,中国人走上以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的道路而不是西方的集团生活(社会本位)和阶级分层的道路。然而何以中国人会走上这样道路呢?梁漱溟的回答是中国文化理性早启。因理性早启而走向几乎没有宗教的生活,而西方人是通过宗教即基督教来分解家庭形成集团生活(社会)的,因集团而形成阶级。所以梁漱溟得出结论,中国文明的优点或者缺点全在于此——早熟。早熟就是理性早启。
费孝通认为中国人“私”(即缺乏公德)的问题是一种完全与西洋社会格局(团体格局)不一样的社会格局模式——差序格局——造成的。西洋人个人与团体即群己关系是明晰的,知道自己的界限。他用很形象的捆柴形式来比喻这种社会模式。在其早年(1947年)作品《乡土中国》中写道:“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像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2]31这样一种在社会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叫团体格局。而中国人则很不一样。费孝通指出:“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2]34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2]34这种“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2]38。每个人处于一定网中,但这个网极富有弹性,随时随地以“己”作中心,而成为一种不是个人主义却是自我主义。“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2]38而中国传统中,这些都没有,是一种一切价值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这是自我主义。
三、 解决之方
(一)梁启超方法:由私德拓展延伸为公德
如前所述,梁启超1902年著写《新民说》的“论公德”一节,提出了中国人缺乏公德之问题。第二年(1903年)他指出其前一年作《论公德》时的用意是:“恐中国之旧道德不足以范围今后之人心,而渴望发明一种新道德以补助之。”[1]178但是,后来发现其不可行,他说:“由今以思,此指理想之言,而绝非今日可以见诸实际者也。”[1]178因此,他重新强调私德,用历史上的私德修养的方法来引导大众重视修德,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是《论私德》以及后来的《德育鉴》。其中《论私德》一文论述了私德与公德之间的关系,指出:“私德跟公德,不是两个相互对立的名词,而是两个相互隶属的名词。”[1]162如果从普遍意义上讲,无公德与私德之区分,从辨析意义上讲有私德完善而公德不足之情况。公德是私德之扩展延伸,因此应该重视私德由此拓展为公德,私德是本,而公德是一本而推之扩充。据此,他甚至强调只要“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1]163。他说:“公云私云,不过假立之一名词,以为体验践履之法门。就泛义言之,则德一而已,无所谓公私,就析义而言之,则容有私德淳美,而公德尚多未完者,断无私德浊下,而公德可以袭取者……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在也。”[1]163
因此,梁启超特别重视私德,指出:“私德者,人人之粮,而不可须臾离者也。”[1]176在该文中梁启超从中国历史上先儒的论述中择取了三条义理作为需要之纲要,即正本、慎独、谨小[1]186-194。后来在《德育鉴》中进一步完善为六条,即辨术第一、立志第二、知本第三、存养第四、省克第五、应用第六[4]。
(二)梁漱溟的方法:引固有伦理入团体生活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缺乏公德是因为缺乏团体生活造成的,如今建立团体生活,发挥中国固有伦理精神引入团体组织中以建立良好的组织,并且通过团体运用科学技术。他说:“要建设新中国文化,第一在挥发固有伦理精神引进团体组织,第二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只如此使圆满无缺,更无其他。”但是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他说在旧伦理的五伦之外增加一伦,即“团体对个人”“个人对团体”之相互关系[5]174。
梁漱溟认为英美之路和苏联之路都与建设新中国文化不合宜,只有引入中国固有之伦理精神才能同时对治中国人的两大病根,实现团体的进步。他论述道:“流俗以为中国缺乏民主,其实乃是缺乏进步的团体组织,误为缺乏民主,更误认为是封建。于是把欧洲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自我中心,权利观念,都引到中国来,而不知这些原为他们团体过强,干涉过甚之反动。在他们是对症下药,而在我们缺乏团体生活者恰好药不对症。更且加重其散漫之病,个人主义是团体生活之一种离心倾向,但我们却正需要团体生活之向心力。所以说完全错误。”[5]174-175同时近代西欧思潮于我不合用,东欧之集体主义也是不合用。“抬高团体以压个人者,似乎是加强团体生活之向心力。但要知道中国之病,一在散漫,二在被动。抬高团体之结果,便是专政和统制。专政和统制,更加重中国老百姓被动之病。”[5]174-175他归结说英美之路、苏联之路,皆与我不合,需要“新开一副新药”同时兼治“散漫”与“被动”二病,才可以有进步的团体生活实现。“此药方即是固有伦理精神,适用于团体与个人之间。但是旧伦理是一人对彼一人之关系,例如五伦皆如是,现在我们需要增加一伦,即团体对个人、个人对团体之相互关系。伦理精神在尊重对方,在此,即是团体要尊重个人,个人要尊重团体。”[5]174-175
梁漱溟还提道自己在乡村建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伦理情意,人生向上”来维持团体和鼓舞成员积极努力。关于伦理精神,他说:“伦理关系互以对方为重之精神,适用到团体生活,实在是一个仙方,既使中国人从散漫入组织,又是使中国人从被动变主动。一个进步的团体生活,亦所谓民主的团体生活,于是成功。”关于人生向上,梁漱溟说:“四五十年来,中国举办地方自治所以失败无成,一则误在摹仿西洋个人权利观念,二则误在摹仿西洋人公共福利观念。福利岂能不要,但眼中只知福利,忘了人生向上则不可。按照中国精神,福利应该隶属于人生向上之内。”[5]176他还说:“向上精神提振起来,则地方公益自然兴办,福利自然实现。”[5]17他还进一步指出:“‘伦理情意,人生向上’自周孔以来数千年,早于人心深处大有启发,今天要民族复兴,必从复兴此精神入手。否则精神不振,更何能吸收外来东西?”[5]177
(三)费孝通的方法:挖掘社区文化培养共同感
如前文所述,费孝通先生在早期的著作《乡土中国》中通过观察其家乡苏州村民对待公共之物(河)的态度得出“私”的结论,并用差序格局来解释这一切。但后来,他观察上海的社区,这个看法有所改变,他开始关注社区所形成的认同基础。他建议把“这个文化的基础再拓宽一点,内涵挖深一点,与居民的生活联系搞得更全面一点,作为生活方式的特点更鲜明一点,这样形成的社区认同,作用可以更大”[6]298。他引入了社会学中的“社区”这一概念,根据其词根的含义,“共同的” “一起的” “共享的”等,可以引申出“一群人有共同的感受,有共同的关心的事情,也常常有共同的命运”[6]294。基于这种共同文化心理基础,进一步挖掘和拓展就可以引向公有、共享的氛围。这就由社区的文化基础引向了更加广阔的社会团体的精神并与之相契。
社区相对于家庭,其实它是一个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秩序的维系方式与家庭不同,需要挖掘共同区域内的小文化的认同——价值、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上的共同感觉等,实现共同管理。费孝通说:“社区不可能像单位或家庭一样,因为没有那么直接的经济利益和血缘纽带。在社区里,个人凭什么接受管理或制约,又为什么要‘管闲事’?上海人是很喜欢讲‘关你什么事’和‘关我什么事’的。要让大家接受管理,愿意管,主要还靠文化认同,在价值观、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上找到同一种感觉,共同管起来。”[6]298
这种基于习俗或者共同的文化心理之引申与推广,离不开儒家“推己及人”的精神。至此,费孝通重新重视儒家精神。在《推己及人》一文中,他指出,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7]474。推己及人,最要的是要知己,其次是一以贯之。他说这个“己”,首先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英语里是self,而不是me,也不是I[7]471。虽然费孝通没有明确讲,但不难明白,此处之“己”类似于儒学所讲之良知。他说:“自己觉得对的才去做,自己感觉不对的、不舒服的,就不要那样去对待人家。”[7]472费孝通晚年在与李亦园的对话中,重新诠释了早年提出来的“差序格局”,由“消极的差序格局”走向“积极的差序格局”。他说:“能想到人家,不光是想自己,这是中国在人际关系当中一条很主要的东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我的差序格局出来了。这不是虚的东西,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边的,是从中国文化里边出来的。”[8]
费孝通早年的差序格局(《乡土中国》)推导出“私”的结果,或者说当时他把中国人私的原因归结为儒家经典《大学》中的己—家—国—天下的价值序中的逆向推理(或者消极推理)。此推理的过程是:“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9]130但是,后来即从上文所引的1998年访谈录中,我们可以看出费孝通对于差序格局的意义有了积极的理解,这是一种由己向外推广的善的精神。因此,笔者把它称为“积极的差序格局”,相应地把他早年的差序格局命名为“消极的差序格局”。通过这种积极的差序格局的推己及人,用在社区治理就是把社区的共同感觉挖掘扩充,而用在个人身上就可以推广于共同领域。翻检《费孝通全集》,我们不难发现,他晚年对中国文化有了这种积极的看法之后,就不再提国人“私”的问题了,从中隐含着对“私”的超越和解决。
四、余论
前文提到的三位大师关于中国人缺乏公德以及解决之方的讨论,都是基于西方文化涌进中国、中国文化遭遇时代巨变之际做出的反思。我们今天,一方面要努力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尽量避免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公德不足而出现的社会风气不良的问题。在此,如何落实上述诸贤所提出的公德问题解决方法呢?这里至少要面对两个问题,一个是现代过程中学校教育的工厂化与道德教育困难问题;另一个是现代化的价值引领问题,即源于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让中国的私德资源、伦理精神以及乡土文化产生对公德的积极建设作用。这里涉及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文化价值的多元与公德的统一性(一道德)论问题。在这里,笔者想举冯友兰和李泽厚两位的思考来进一步探讨。
冯友兰曾指出,现代教育的工厂化需要与道德教育之间存在矛盾。冯友兰在《新事论》中有篇专门阐述教化的文章,其主要观点就是教育需要工厂化,而工厂化的教育不可能教会学生做人,做人的学习靠社会的教化,而教化主要依赖于(人师)精英的影响,精英又是在社会中形成。
首先,教育工厂化。冯友兰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差异不是东西的差异而是古今的差异,即西方人发展得快跑到前面去了。他用“乡下人”与“城里人”来比喻中西差异。中国是乡下人,落后,被西方人剥削;西方人是城里人,发达,剥削中国人。中国人要想不被剥削怎么办呢?很简单,就是自己做城里人,方法就是由家庭为本位的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为本位的生产方式亦即是产业革命。冯友兰说,在生产社会化底社会中,教育制度亦需工厂化。他解释道:“教育制度工厂化即是说:在生产社会化底社会里,我们对于教育人材,亦要集中生产,大量生产,细密分工。”[10]85
其次,学校不可能教会做人。冯友兰认为“做人”是主要靠“化”而不是靠“教”[10]930,而学校只不过是一个小社会,其所形成的风气虽然能够影响学生,但学校之外尚有大社会之风尚[10]94。因此学校对学生做人的影响是不会很大的,这与传统社会不一样,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本位社会,人的一辈子可以说是在“家”中,因此家风对其影响深远,而学生求学也似拜师学艺,在师徒父子这样的伦理关系中进行,因此“师”能够言传身教而影响徒弟做人,且这种影响是深远的。
那么生产社会化的社会中做人的事情如何学会呢?在冯友兰看来,做人主要是受“人师”的影响而学会。在生产社会化的社会中,人师已经不是过去教授弟子的师父,而是社会上的精英人士,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更容易受所谓风尚的支配。他论述道:“因为交通方便,所谓‘宣传’,更容易达到人人的心中,使人互相刺激。此人见彼人若何而若何,彼人见此人若何而更若何。如在街上,此人见彼人满街都跑。此是互相刺激,所谓群众心理,即是如此构成底。这些都不是教,这些都是化。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化的力量比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大得多。”[10]98冯友兰说:“所谓‘人师’者,只有政治上社会上底领袖可以当之,而这些领袖实际上亦是各个地方社会的‘人师’。”[10]98冯友兰认为这些人师不可能在现实的学校中培养出来,他说:“我们正需要一种学校,能教育出这种领袖……在实际上这一类学校是不能有底。”[10]98那么这些领袖从哪里来呢?只能来自社会一时的风尚。他说:“一个社会在某一时侯,为适应某种环境,有某种运动。参加这种运动底人,有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即是领袖。其余即是群众。”[10]98他还进一步说,这就是:“所谓英雄造势时,时势造英雄。世界上没有造英雄的学校,也没有造诗人、发明家的学校。”[10]98至此,冯友兰把社会公德教化问题还给社会,就是在社会公共活动中成就榜样人物来引导大众的公德罢了。
面对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呈现出思想的多元性,道德选择的多样性。然而,作为公德必然是协调公共空间的道德行为,需要统一性。如何调节这种“一多关系”,显然会遇到一定的挑战。对此,李泽厚把私德归入宗教性道德而把公德定义为社会性道德,而两者的关系是:宗教性道德对社会性道德具有范导作用,但不决定和规定社会性道德(建构),宗教性道德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是个人自愿的选择,别人不容干涉,而社会性道德是公德,要求广大公民做到,以此试图从中国过去政教合一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同时也让社会性道德的来源有个来自传统道德资源的范导,但又避免被统治者恶意以宗教性道德的名义去压制百姓的生活。李泽厚说:“完全相信并竭力论证存在一种不仅超越人类个体而且也超越人类总体的天意、上帝或者理性,正是他们制定了人类(当然更包括个体)所必须服从的道德律令或伦理规则。因之,此道德律则的理性命令,此天理、良心的普遍性、绝对性,如人是目的、三纲五常,便经常被称之为神意、天道、真理或者历史必然性,即以绝对形式出现,要求放之四海而皆准,历时古今而不变,而成为亿万人群所遵守和履行。这就是所谓绝对主义伦理学,也就是我所谓的宗教性道德。”[11]15他还指出:“宗教性道德源于社会性道德。”[11]18关于社会性道德,李泽厚说:“所谓现代社会性道德,主要是指在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人群交往中,个人在行为活动中所应遵守的自觉原则和标准。”[11]18
两种道德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李泽厚指出:“现代社会性道德以理性的有条件的、相互报偿的个人权利为基础,传统的宗教性道德则经常以情感的、无条件的、非互相报偿的责任义务为特征。人不是机器,在现实中即使循理而行,按社会性道德的公共理性规范而生存而生活,但毕竟有各种情感渗透、影响于其中,人际关系不可能纯理性,而总具有情感方面。两种道德的纠缠渗透,于群体于个人都是非常自然甚至必然的事情。”[11]70李泽厚提出情本论、西体中用来统摄两种道德,既给宗教性道德留下了地盘,又为现代社会的普遍道德要求提供了一种哲学的方法论。但是似乎在李泽厚那里,儒家的传统道德在多大程度上对现代社会的公德产生影响,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度的问题,因此建设社会公德的基础主要还是依赖于西方的自由主义现代社会道德理论,让他本人也承认自由主义以契约为基础的整个社会管理模式基于原子式个人的假设,此种假设是非历史非现实的虚构,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他寻求把社会性道德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社会存在之上而不是原子式个人的假设上。无疑,李泽厚的这种做法,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私德的多样性与公德的统一的矛盾的调节无疑是有利的,但问题是这种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模式,让道德建设成为和处于次要和靠后的次序。
梁启超、梁漱溟与费孝通等,都属于时代的文化英雄人物,他们确实也做出了道德引领的作用,比如梁启超以文章引领年轻人,梁漱溟进行乡村建设,费孝通参政议政。然而,我们看到其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冯友兰式的解决是必要的,李泽厚式的处理方式也值得重视,这些都可以视为对二梁以及费老解决方式的修正和深化。
我们不妨接着上述诸贤的思路,进一步思考。梁启超重视私德,以之为公德之本,充分挖掘传统经典中的私德资源并推广,而梁漱溟以传统伦理精神入团体生活,费孝通挖掘社区的文化后进一步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然而,如何把传统的私德资源、伦理精神、社区文化进一步发挥于今日公德建设中呢?就积极意义而言,冯友兰给我们指出了对精英人物的道德要求以及媒体治理的重要性,而李泽厚告诉我们对社会公德底线意识与价值多元之间协调如何协调的问题,即社会公德宣传和推广过程中如何兼容多元价值的问题。
反过来讲,冯友兰式的把道德教化问题还给社会而不作为,肯定难以解决中国人缺乏公德的问题。李泽厚式的把私德和公德进行分开,在理论上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有丰富的私德(宗教性)资源,个人可以用来修身,同时社会有一套要求全体成员遵循的社会道德,但是社会道德可资开发和建构的资源主要源于西方,这个难免与中国文化不太适应,并且他把社会道德基础建立在社会存在之上,这就容易导致过去三十年出现“经济建设为中心”,虽再三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而实际上却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同时,把传统的宗教性道德完全归于私人领域,缺乏国家开发教化民众的工作,出现传统的宗教性道德被遗忘或者被打倒的局面,而新的所谓的社会性道德又难以建立起来,造成今天道德的不理想状态。
无论是梁启超、梁漱溟,还是费孝通,都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由固有之本推广、引申,冯友兰的办法是交给社会,而李泽厚的办法则更多依赖于西方文化资源。在文化自信力不断增强,国学不断复兴的今天,我们更有信心充分发扬中国固有的优秀文化资源,为提高中国人的公德意识做出积极的努力。就像马克斯·韦伯所言:“没有企业家阶层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道德宪章就没有企业家阶层,没有宗教信念就没有道德宪章。”中国现代化过程应该有自己的伦理道德作为规范和动力。梁漱溟提倡的把传统固有伦理精神引入团体组织,这是一种正确做法,但是具体引进传统的什么伦理精神和如何引进就需要我们下工夫研究;费孝通所谓的社区文化的开发,转化消极的“差序格局”变成积极的“差序格局”,在今天是否还有其相应的社区文化根底是个问题;梁启超所提倡的私德资源,在全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可以引入社会各个领域,尤其是教育领域以及公务员系统;冯友兰的社会教化办法,启发我们要加强精英人物的道德模范引领。同时,李泽厚提出的既保证公德的改善又能兼容多元价值观,这需要挖掘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费孝通晚年也积极倡导。“和”,需要底线思维来保障,“不同”兼容多元文化与价值。
新儒家努力的儒家“内圣”到底能不能开出新“外王”?笔者认为,“内圣”自然能够开出“外王”,民国以来中国出现的一大批科学家不就是在儒家经典教育下,发扬爱国之情,留洋深造科学而得吗?“钱学森之问”就是一个明证。关键是如何从中国传统的道德资源中自然引出能够在公共生活空间起作用的公德。这个公德恐怕是简单的个人与团体、团体与个人互相尊重不能完全包含的。
[1] 梁启超.新民说[M].宋志明,选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2]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4] 梁启超.德育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 梁漱溟. 中国文化命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6]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7卷(2000—2004)[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7]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60卷(1997—1999)[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8] 费孝通,李亦园.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6):87.
[9]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6卷(1948—1949)[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10] 冯友兰.新事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1] 李泽厚.哲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The Phenomenon of Chinese Lack of Public Morality and the Solution——BasedontheexpositionsofLIANGQichao,FEIXiaotongandLIANGShuming
WANG Shengyun
(DepartmentofPhilosophy,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LIANG Qichao once put forward that the present Chinese people lack ethics and the sense of social morality, which was also shared by LIANG Suming and FEI Xiaotong. As for the reason, LIANG Qichao pointed out that it was the result of the overweight of personal morality than public morality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FEI Xiaotong further explored the reasons for the personal morality and believed that the negative structure of differential mode in Chinese culture created self-centred national psychology; in addition, the lack of communit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was considered by LIANG Suming to be an important reason. With regard to solutions to this problem, LIANG Qichao advocated that we could extend personal morality to public morality, and then ethics, while LIANG Suming suggested integrating the established ethics into group life, and FEI Xiaotong argued that the negative structure of differential mode could be developed into a positive mode by putting one in another′s place. If solutions of three scholars are implemented well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wo problems are worth noting: First, FENG Youlan thought that moral education should be lead by the elites after the systematic education, while the other, proposed by LI Zehou, involves the relation between multiple values and public morals unity.
public morality; LIANG Qichao; LIANG Shuming; FEI Xiaotong; the positive structure of differential mode; FENG Youlan; LI Zehou
2017-03-02
王生云(1986-),男,云南普洱人,北京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儒家哲学。
10.16396/j.cnki.sxgxskxb.2017.07.016
D648.3
A
1008-6285(2017)07-0066-07
——概念跨学科移用现象的分析与反思
——概念跨学科移用现象的分析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