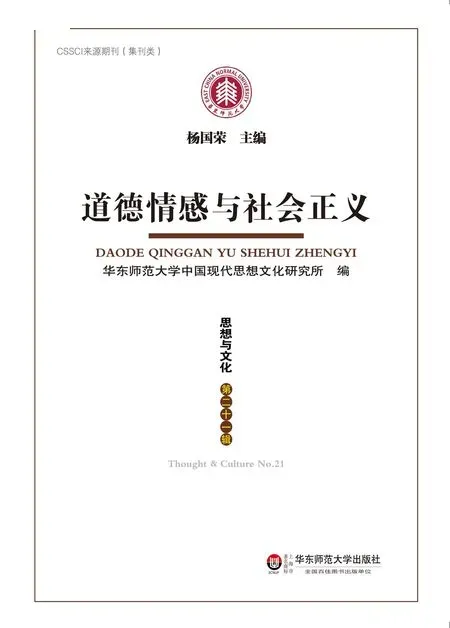法国当代哲学中的空间观念
哲学史上对时间的关注一直胜过对空间的研究,换言之,空间甚至作为时间的反义和对比而出现,这种作为背景式的空间观念可以追溯到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和柏格森。另一方面,近年来在国内社会批判理论中已成风尚的“空间转向”研究,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福柯和列斐伏尔也是法国当代哲学家。尽管空间研究已在社会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但其哲学意义仍有待探究。在这个背景之下,本文在梳理法国当代重要哲学家的空间观念的过程中,试图对空间的哲学意义作出尝试性的回应:空间一方面作为存在的载体和方式,具有被动和消极性;另一方面,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对空间有新的规范和生成,使空间又具有积极的生成性和开放性。
对于追问当代哲学中空间思想的哲学意义,法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意义。首先,当代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福柯和列斐伏尔,而且近代以来有一批法国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空间概念作出重要理论贡献,如笛卡尔、柏格森、梅洛-庞蒂、巴舍拉、德勒兹等。文章分三个部分对以上哲学家的空间思想作出梳理,其中第一部分围绕笛卡尔和柏格森的空间观念,概述了一种属于物质属性或身体的“背景式”空间观念,这种观念至今在科学领域和日常生活中仍占有重要位置;第二部分则介绍了梅洛-庞蒂的知觉空间和巴舍拉的诗学空间,他们开始注意到空间的现象学维度,空间由此开始具有构建能力,并进入人的知觉以及生活活动;第三部分是以福柯、德勒兹为代表的差异性空间理论,该理论一方面表现出了异质空间的理论创造力,另一方面也进一步阐发了空间的方法论意义,进而影响到社会领域的批判理论。
一、笛卡尔和柏格森:背景式空间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笛卡尔将空间与物体等同,他认为它们都是由长度、宽度和深度三个维度的广延而构成的:
“空间或处所,与这个空间所包含的物体之间的差别只在于我们的思想。因为事实上,在长宽高上的相同广延既构成了空间,也构成了物体。二者的区别只在于我们赋予物体一种特殊的广延,每次都跟随物体移动而感受位置的改变;而我们赋予空间的是一种普遍和宽广的广延,把某一空间上的物体移开后,我们并不会认为这个空间的广延也发生了移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空间一直保持着相同的广延,大小相同,形状相同,空间相对于确定它的外围物体并没有改变位置。”*René Descartes,Principes de la philosophie,part.2,art.10,oeuvres et Lettres, 《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 NRF Gallimard,1953,P.616.
物体和空间的同义关系是通过广延来实现的,因为在笛卡尔那里,物体的本质属性是有长宽高的广延,而不是质量*关于物质的本质属性的问题,与笛卡尔把物质的本质属性规定为广延不同,伽利略认为是质量。事实上,质量和广延都是物质的重要性质,而在科学领域内更加成功的概念应该是牛顿的“质点”。质点指物理学中理想化的模型,在考虑物体的运动时,将物体的形状、大小、质地、软硬等性质全部忽略,只用一个几何点和一个质量来代表此物体,这个概念在物理学中沿用至今。、密度、颜色或其他。所以,如果坚持要区分物体和空间的话,就是特殊广延和普遍广延的关系。换句话说,物体和广延都是空间的同义词。众所周知,在笛卡尔的二元论当中,广延是区分思想和物体的标准,即思想是没有广延的,而有广延的则是物体,这个“物体”包括我们的身体(法语词corps既指身体,也有物体之意)。所以在汉语语境中,我们可以把这个同义词组继续扩大为:空间=广延=物体=身体。而且,它们都是“心灵=思想”的反义词。在这个简化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容易理解柏格森认为时间(绵延)是思想的本质的命题,也更容易理解梅洛-庞蒂为何以身体作为阐发空间性的出发点。
笛卡尔的广延概念对后来的空间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一方面强调了广延作为事物本质属性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开启了以数学化的方式对空间进行研究的方法。对此,胡塞尔有深刻的认识,并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对欧洲的科学危机进行了讨伐。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的法语译者Nathalie Depraz在同意胡塞尔观点的基础上,对笛卡尔的广延(res extenso)概念做了一条批判性的注释,他说:“res extenso的字面意思‘广延事物’,是笛卡尔以广延为其本质属性的物质性概念。在这点上,笛卡尔是数学化物理学的源头:定义广延空间的依据是定量和抽象的同质性,而不是定性的可感受的、具体的异质性。”*Edmund Husserl,la crise de l’humanité européenne et la philosophie, trad.par Nathalie Depraz,Edition numérique,la Gaya Scienza,2012,p.102.
把笛卡尔对广延空间的界定看作是数学化的物理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他用数学化的方式来规定物质的本质,由此空间的研究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科学所占领。定量的同质性研究和定性的异质性研究构成了两种空间研究的进路。这两种规定空间的方式可以类比于洛克对物质的两种性质的规定:同质性的空间表现为物体所固有的第一性质,异质性的空间则属于物体所具有的一种能力,与人的知觉感受相关。洛克的区分是针对物质的不同属性而言,但在这里却给出了对空间广延这一性质的两种解读。根据Nathalie Depraz,空间或广延,它不单单是第一性质,而且具有第二性质的潜质。由此,他既反对了笛卡尔,也与洛克的观点有所不同。在他刻画的两条对空间的研究道路中,一条从此被科学研究所占领;另外一条则如下文将要指出的,是由受现象学影响的梅洛-庞蒂和巴舍拉提出的空间概念,以及法国当代哲学代表福柯和他的同代人德勒兹对这种“异质性”空间概念的回溯阐发。
先回到同质性空间概念。笛卡尔将广延归之于物体,并且将空间与思想相对立。与笛卡尔不同,柏格森在《论意识的直接来源》开篇就提到了意识当中的空间性:“我们的表达必然借助于文字,我们最通常的思考借助空间。”*Henri Bergson,avant-propos dans l’Essai sur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 1888.这里的空间指的是我们意识当中的空间性,它像语言文字一样有明确清晰的间隔和区分,表现为物体之间的不连续性。我们对空间的常识理解,大多和笛卡尔一样,将其视为一种对物质世界的看法,空间具有和物类似的性质,比如可区分的多样性和不连续性等。但柏格森指出这种机械论和目的论的观点已经对人们的意识产生了影响,这也是他要进行批判的。他在后来出版的《创造进化论》中再次重申了对意识空间的批判,他说:“论著(指《论意识的直接来源》)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心灵生活既不是一,也不是多,而是对它们的超越,机械和智力的机械论和目的论只有在‘区别的多样性’和‘空间性’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因此它们只是现有存在的整合;‘真正的绵延’则同时意味着不可分的连续性和创造性。”*Henri Bergson,L’évolution créatrice,Paris:Puf,1941,note de base de pp.X-XI.换句话说,尽管柏格森批判的是意识状态中的空间观念,但这观念的来源仍旧是物质性的空间观,或者说,只是进入了意识领域的背景式空间观念。
从形式上来看,在对空间和时间的看法上,柏格森补充了笛卡尔。笛卡尔说空间(广延)是物体的属性,而不是思想的;柏格森则说了这句话的另外一半,即意识(思想)的来源是时间(绵延),而不是空间。在对空间的看法上面,尽管柏格森延续了对机械论空间观的批判,尽管柏格森所批判的空间性不是物质界的空间,而是进入到了意识界的空间,但他对意识空间性的批判,是为了给“时间性”的绵延留出位置,与此同时,他也给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空间研究保留了地盘。如今,时间的哲学意义和空间的科学意义都得到了卓有成效的阐释,而空间的哲学意义则仍有待探索。我们要追寻的正是柏格森和海德格尔对时间原初性和创造性的关注和热忱,进一步探求空间的哲学意义。
二、巴舍拉和梅洛-庞蒂现象学空间观的启发:空间想象和空间知觉
现象学对空间哲学意义的生发很关键。如前所述,在自然哲学传统中,空间被视为背景式的存在,为世界万物的存在提供场所,这种观念的影响极为深远。在现象学之前,康德已经注意到了空间作为人类先天的认识条件的重要性,它将空间的规定性从物的属性转变为了人的认识条件。相应于现象学要求从本质追问回到“现象”本身的主张,空间开始真正地从背景式存在走到舞台前面来。空间现象是在场的现象,这种“在场”是空间图像的即时在场,这些空间图像来自美好的回忆或想象,这是超越时间的在场。这就是巴舍拉所说的“现实的空间”(l’espace vécu):“它是现实的,不在于它的实证性,而在于想象力的全部偏袒。”*Gaston Bachelard,La poétique de l’espace, Paris:Puf,1972,p.17.
巴舍拉的诗学空间针对的是实证主义的空间观,后者追求因果关系,寻求事物背后的本质属性。相反,诗学空间反对因果分析,强调刻画人们的空间感受,主要以家宅中的情感、想象、梦想和回忆为内容。感受是在场的;但与即时感受不同的是,像梦想、想象和回忆等这些感受超越或克服了时间,进而它们带来的是“全部的空间”。这个全部的空间不是包含了所有范围的空间,而是指一种没有了时间限制的空间。在巴舍拉对回忆的分析中,他强调了这种空间相对于时间的优先性,即他认为,“对于回忆来说,空间就是全部,因为时间不喜欢回忆,回忆忘却的超越的就是时间”。*Ibid,p.37.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亲密性的回忆,往往首要的是回忆中的地点定位,其次才是时间定位,因为时间往往是模糊的甚至是被忽略的,而空间记忆往往相对清晰。在回忆中所展现的“全部的空间”,指没有时间的或是时间被忽视了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巴舍拉的回忆是克服了时间的空间,而柏格森的“绵延”则是克服了空间的时间。
在巴舍拉所开启的想象空间中,家屋中的亲密空间与外在的宇宙空间是相对抗的,或者说,正是在与宇宙空间的对抗性力量的对比中,才更加凸显了家庭空间的温暖和快乐。他认为:“家和宇宙这两种空间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在想象的王国里,它们以相反的梦境互相激发。”*Gaston Bachelard,La poétique de l’espace,Paris:Puf,1972,p.69.关于这点,他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外面的风暴越强,则家屋的庇护就越温暖”的体验。这和崇尚自然的中国道家思想有所不同,老子从外在的自然出发,侧重自然之道与人类生活规则之间的相通和关联:“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老子·第二十三》)以天道论人道,其依据便在于二者的统一,正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从理论的出发点来看,巴舍拉显然以人心的感受性和想象力为出发点,这在人类精神能力中可归于非理性能力的范围;而老子所谓崇尚自然之人道则包含了更为广泛的内容,而且多以抽象性的人道原则为主,属于理性的反思内容。与注重内在与外在空间的统一性有所不同,巴舍拉从内在的“想象”出发,侧重外在空间施加给内在空间的对抗性力量(forces adverses)。
福柯赞赏巴舍拉对内在空间的分析,但也强调自己与巴舍拉的一点分别便在于,巴舍拉只关注“内部空间”,他自己则关注外部空间。换言之,巴舍拉的想象空间发掘了空间在想象力中的图景,表现出空间作为“在场图像”的能力,但是这种想象力的空间却囿于内在空间的范围,缺少与外在空间以及主体间的有效沟通和互动。
巴舍拉的诗学空间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超越了时间的“全部的空间”。谓之“诗学”,一是因为这种空间感受往往是诗歌赞颂的主题;一是因为这个空间所表达的是与诗相近的情感,而不同于实证科学的研究。巴舍拉的梦想和想象,可以归入广义的知觉范畴。与此相联系,梅洛-庞蒂以身体的知觉为核心展开了空间知觉的论述。如果说巴舍拉是从内知觉感受出发,那么梅洛-庞蒂所建立的则是身体的外知觉学说。
在知觉空间的构建中,梅洛-庞蒂将身体优先于心灵而存在:“我的身体在我看来不但不只是空间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没有身体的话,在我看来也就没有空间。”*Maurice 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Gallimard,1945,p.119.这同时意味着空间不是靠心灵思考得到的,而是靠身体感受知觉得到的。这一方面秉承了上述笛卡尔“空间=广延=物体=身体”的等式逻辑,将空间性最终落实到了身体的感受性上面,以身体性阐释空间性;但另一方面,在身体与心灵的关系方面,梅洛-庞蒂因为强调身体的优先性而主张“我在故我思”,将意识纳入存在,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截然相对。他分析道:“在命题‘我思故我在’中,两者肯定是等值的,否则就没有我思。但是,还应该在这种等值的意义上取得一致:不是‘我思’完全地包含‘我在’,不是我的存在归结为我对我的存在的意识,恰恰相反,而是‘我思’被纳入‘我在’的超验性的运动,而是意识被纳入存在。”*Ibid.,p.439.
身体的这种优先性为知觉空间提供了理论上的前提。知觉空间区别于客观空间,相对于后者,知觉空间具有一种构成人与世界联系的能力。这种从空间性质到空间能力的转变,在梅洛-庞蒂这里主要表现在“身体的图式”中,如其所言:“身体图式是一种表示我的身体在世界上存在的方式。”*Ibid.,p.117.这就是从存在论上论证了身体空间的能动性,不同于巴舍拉所设想的内在空间图景,梅洛-庞蒂的身体空间积极地构成与世界的关联。因此,它不再是静态的位置空间,而是处在一种关系之中:“身体的空间性不是如同外部物体的空间性或‘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的一种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Ibid.,p.116.处境的空间不仅批判了传统的背景式空间概念,而且也要区别于空间感觉的空间性,后者是包含想象空间在内的对空间的主观感受。
总之,身体的空间性同时体现了存在论、现象学和认知科学的空间思想。梅洛-庞蒂注意到了空间思想的现象学还原与存在论立场的一致性。他说:“如我们所知,现象学还原远不是唯心论哲学的命题,而是存在论哲学的: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之中’只有在现象学还原的基础上才会出现。”*Maurice 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Gallimard,1945,p.IX.如果说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带有浓重的理论抽象性,这在海德格尔那里已经有了改变,现象学与存在论的结合让空间理论真正从抽象走向具体。而且,梅洛-庞蒂以深度空间的分析来阐明空间的存在论性质:“深度比其他空间维度更直接地要求我们摒弃关于世界的偏见和重新发现世界得以显现的最初体验;可以说,深度最具有‘存在的’特征。”*Ibid,p.296.
空间的具体性离不开知觉的形成,这是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基础上的新的理论创设。空间离不开认知,这点在康德那里已经有所注意,但不同于康德,梅洛-庞蒂不认为空间是先天的认识形式,而是后天的认识活动。在空间认知中的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向中,其最为显要的参照和中心就是我们的身体。由此,梅洛-庞蒂融合了认知论、存在论和现象学的思想资源,探讨了一种以知觉和身体为框架的新的空间观。
三、福柯和德勒兹:异质性空间理论
如前文所述,一方面为实体性物质的空间,一方面则是逻辑性的空间,这两者展现在人类的认知和感受性活动当中。与上述两种空间都不同,福柯的空间概念既不是实体性存在,也不是逻辑性存在,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方式或一类方法。他认为现在的时代与其说是时间的时代,不如说是空间的时代。*Michel Foucault,Des espaces autre,Dits et écrits IV(1980-1988),Editions Gallimard,1994,pp.752-762.参见福柯:《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译者似乎遗漏了对该句的翻译。他所指的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世界的存在与其说是一种时间方式的纵向存在,不如说是一种空间方式的横向方式,也就是像一张连接各个点和线束的网络。网络型的世界观并非全然否定时间的存在。福柯亦指出,这只是处理时间和历史的一种方式(une certaine manière)而已。*Michel Foucault,Des espaces autre,Dits et écrits IV(1980-1988),Editions Gallimard,1994,pp.752-762.从哲学上说,结构主义便是在广义上使用空间方式作为研究方法的哲学。
福柯区分了历史上出现的三种不同的空间观念*Michel Foucault,Des espaces autre,Dits et écrits IV(1980-1988),Editions Gallimard,1994,pp.752-762.:一是中世纪时期的“定位空间”(localisation),主要体现于生活经验当中对不同场所的划分,出现了以宗教和政权为核心场所的等级制;接着是18世纪自伽利略开始,由笛卡尔给予哲学确认的“广延空间”(étendue),取代了定位空间,开始以数学的方式测量和计算空间,事物的位置则简化为在运动当中的一个点来表示,也就是后来牛顿的“质点”概念;在当代,取代了广延空间的概念则是“位置关系”(emplacement),它代表的是位置的关系,体现在比邻关系、现代信息的处理,以及广泛意义上的形势分析和处理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广延空间”概念那里,空间是去神圣化的以外,中世纪的定位空间经验和现代的空间位置关系,都包含神圣性,或者说是没有去魅的。如福柯所言,位置关系仍然在“隐藏的神圣性”(une sourde sacralisation)之中。当然,位置关系的神圣性已经与中世纪的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空间隐秘地保留着的神圣性是一种异质性,而不是完全数量化的同质性存在。在位置关系的空间性当中,空间表现出作为方法的性质。
空间现象从实体存在发展到思想和文化存在的过程表明,尽管讨论的范围发生了变化,但思想和文化中的空间性质仍然是从实体的性质而来。比如,思想中的空间元素仍具有物质空间的数量性和不连续性,又如,文化空间现象中以文化作为空间的新场所,这些是具有相同性的方面。反之,从差异性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注意到空间概念本身与思想和文化之间的新的理论张力,以及新的理论生机。值得一提的是从相同到相异的理论追求的转变,通常来说,“异”文化向来不是主流,“同”文化才是人类社会一直坚持不懈的追求理想。福柯站在“异”文化的立场上,在《词与物》中论述了人们惯常使用的四种“相同性文化”的形式:适合、仿效、类推、交感,这些几乎囊括了人类认识和行动中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的最基本原则,同时表现出忽视差异性文化重要性的弊端。在这个背景之下,福柯和德勒兹似乎是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坚持“异”文化的道路。上一节已表明空间不再是实体,而是表现为能力;在此基础上,空间的能力主要展开在新的位置关系当中,表现出异质性的特征。在这点上,福柯和德勒兹是相同的。
德勒兹提出了“平滑空间”概念,它是指空间中没有被“围墙、围栏以及围栏之间的道路”所分层或分化。这些围墙、围栏或道路都是地理空间中的限制,用来喻指知识空间中的几何公理和定理、物理定律,以及生物学上的分类等。“平滑”拒绝这些分化,但“平滑”并不意味着没有变化,它只是没有一种“常规”欧式空间所表现出来的变化。相反,它是“最小偏离的空间”(celui du plus petit écart),它具有多种的可能性。换言之,平滑空间是异质性的,而层化空间是同质性的。尽管层化空间是有分层和分区的,但其基底却是相同且没有变化的;而平滑空间虽没有这些分区,但却是充满多样性的,像“根茎”一样具有多种方向,像“千座高原”一样具有多种形态。就其基底来说,它必定是异质的。
这种异质性的表现之一是其并不能以观察而得到:“它们并不符合从外在于它的空间来进行观察的视觉条件,与欧式空间相对的声音系统或者颜色系统亦如此。”*Gilles Deleuze,Félix Guattari,Mille Plateaux,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80.pp.459-460.欧式空间是依赖视觉的,是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空间形式;与此相反,平滑空间并不是可观察的,它可能是听觉的或者是触觉的,总之不是视觉的。但德勒兹这里给出的颜色系统的论证似乎有自相矛盾之处。对颜色系统与欧式空间的不兼容性似乎可以作如下理解:视觉途径是欧式空间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尽管颜色系统也是依靠视觉观察而得到的,但却是平滑的空间,而不属于欧式空间的系统;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即颜色系统处在平滑空间和层化空间的边界上,体现了二者的相关性。
事实上,在强调差异的同时,德勒兹强调了两种空间的关联性,它们之间并不矛盾。这表现在:平滑空间在形式上与层化空间具有相反或不同的结构组成;但事实上,平滑空间却是作为层化空间一种补充性的存在,两者之间并非是用一种形式取代另一种形式。这种补充性的存在体现在一种“更多”的“增加”上面,如其所言,“新的场域或平滑空间体现为一种‘增加’或盈余,并且置身于这种盈余和偏差中”。*Ibid,p.459.我们要继续追问的是,这种“增加”与原有的空间形式是如何发生作用的,既然不是要相互取代,那又应该如何共存呢?两种不同力量的共存难免是会发生冲突和相互侵犯的,而德勒兹注意到的不是谁侵犯了对方更多些或者更少些,那也许是历史学的任务,而是关注到了这个发生冲突的点——边界,它是“唯一要紧的”*Gilles Deleuze,Félix Guattari,Mille Plateaux,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80.p.455.。因为在边界上,几乎融合了所有的因素与可能性:“两种模式之间的分离和融合,可能的相互渗透,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以及相互交替”*Ibid,p.460.,这些构成了边界最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理由。边界在一定程度上也喻指不同文化之间的界限,与简单的划界和生硬的跨界都不同,边界就是空间的生命力所在。
异质和差异的概念表达了一种叛逆的哲学、反叛的哲学。相对于传统哲学对“同一性”的追求,它们表现出质疑和颠覆性,它们对原有的真理性知识、核心性权力概念进行批判和打击。同一性、统一性、规律性,这些都是自然科学一直信奉和追求的规则,而相反地,差别性、差异性、多样性,则是艺术、文学、诗歌等浪漫主义形式的要求。哲学并不在于作出二选一的选择,以其中一个作为归属之地,而是要能够规避一些理论上的盲点,自觉地、有意识地“不偏执”。这是一股破坏性的力量,这也是一股生发的力量。福柯、德勒兹等继承了尼采所开创的疯狂的精神,而且,他们受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极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哲学与德国哲学有着撇不开的关系。正如福柯所说,道路已经较以往有所改变:“不再问哪条是最确定的真理之路,而要问哪条是有害真理的道路。这是尼采的疑问,这也是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中的疑问。”*Michel Foucault,Questions Michel Foucault sur la géographie,Hérodote,n° 1,janvier-mars 1976,pp.71-85;Dits et Ecrits III texte n° 169,Gallimard,1994,pp.28-40.这当然也是法国当代哲学所自觉继承的问题意识。
鉴于哲学史上对时间的关注一直胜过对空间的研究,以及近年来国内社会批评理论中出现的“空间热”现象,空间哲学意义的探究仍有待发掘。法国当代哲学作为空间思想诞生和发展的重镇,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理论启示。上述三个阶段的划分虽然不能对法国哲学的空间思想做出全面而细致的分析,但却勾勒了一个简要的空间思想的发展路径:背景式的空间观念是以物的空间为主,它长期作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出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限制了对空间哲学意义的探讨;以梅洛-庞蒂和巴舍拉为代表的空间观念则体现了人的空间维度,主要体现于知觉、想象和梦想的空间形态,但还只是以个体的人为关注点,缺乏对个体间的空间思想的讨论;福柯和德勒兹的异质空间思想则在更广的意义上,将空间作为一种理论分析的方法,展开于社会批判的各个方面。可以初步得知,空间一方面作为存在的载体和方式,具有被动和消极性;另一方面,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对空间有新的规范和生成,使空间又具有积极的生成性和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