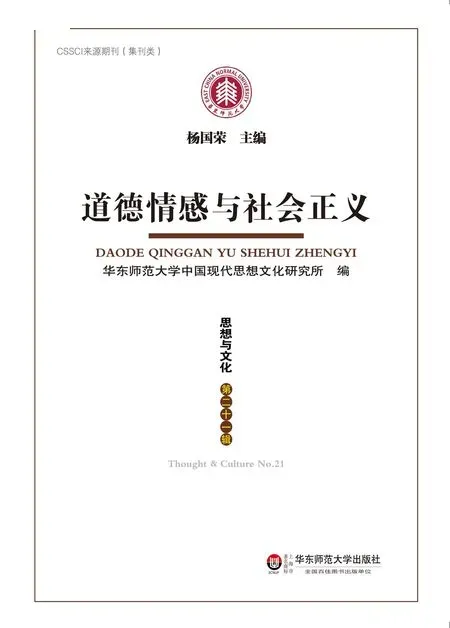道、艺、志的互动:苏轼诗画论中的“文人”探绎
在苏轼的绘画理论中,有较多涉及诗歌与绘画关系的论述,如著名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论画以形似,见与小儿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又跋汉杰画山》)、“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书朱象先画后》引朱氏语)等。这些诗画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学界也依此就诗歌与绘画作为时间性艺术与空间性艺术的异同及相互关系展开了热烈讨论,还有不少学者就苏轼诗画论中的“语—图”互文关系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对于深化苏轼诗画理论认识产生了积极作用。
但是,在苏轼的一系列诗画理论中,隐含着一个潜在的创作主体问题,即谁的诗、谁的画,这个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朱光潜先生曾经提到过此问题,他说:“苏东坡称赞王摩诘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是一句名言,但稍加推敲,似有语病。谁的诗,如果真是诗,里面没有画?谁的画,如果真的是画,里面没有诗?……诗与画同是艺术,而艺术都是情趣的意象化或意象的情趣化。徒有情趣不能成诗,徒有意象也不能成画。情趣与意象相契合融化,诗从此出,画也从此出。”*朱光潜:《诗论》,《朱光潜全集》第五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显而易见,“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中的诗,是作为文人的王维所创作的山水诗,画也是作为文人的王维所创作的山水画;“论画以形似,见与小儿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中的画,则不是专门的画匠之作,而是高度写意化的文人画。也就是说,在苏轼的诗画理论中,隐含着一个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文人”所在。因此,本文欲从作为诗人的文人、作为画家的文人与作为鉴赏者的文人三个层面对苏轼诗画论中这个潜在的“文人”创作主体身份进行探究的基础上,抽绎唐宋时代文人之为文人的综合性因素,并以此透视中国传统社会中文人的身份属性、特点及其艺术审美活动等问题。
一、作为诗人的文人:从“士大夫”到“文人”
在“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中,诗人是王维,诗是王维的山水诗,画也是王维的山水画。虽然,作为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诗人王维,与苏轼一样,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典型的文人士大夫,我们并不陌生。但是,严格说来,从秦汉以来,“文人”与“士大夫”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群体。龚鹏程在《中国文人阶层史论》中曾经指出,中国古代的文人阶层源于士阶层的分化,直到东汉中晚期的时候,文人才具有了与其他阶层不同且足以辨识自身之为一独立阶层的征象。*龚鹏程:《中国文人阶层史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李春青则在考察“文人趣味”的历史生成基础上提出:“所谓‘文人’就是有文才与文采之人,亦即诗词歌赋、棋琴书画样样精通之人。在今天看来‘文人’就是文学家兼艺术家。”*李春青:《“文人”身份的历史生成及其对文论观念之影响》,《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第201页。他还进一步指出,“文人”不等同于“士大夫”:“如果说传统的‘士大夫’是以读书做官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诉求为基本特征的,那么‘文人’就是以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这类关乎‘闲情逸致’的才艺为身份标志的,因此,‘文人’身份的产生必将和其原本的‘士大夫’(政治家)身份发生某种冲突。”*李春青:《在“文人”与“士大夫”之间——略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身份冲突》,《船山学刊》2013年第3期,第75页。这些论述初步勾勒了“文人”与“士大夫”之间的相互关系。
纵观中国历史可以看到,作为一种阶层的形成与发展,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文人”与“士大夫”都有各自漫长的发展形成过程,最后在历史的合力中,才逐步形成了唐宋时代如王维、苏轼这样典型的“文人士大夫”。
《诗经·大雅·江汉》中较早出现了“文人”概念:“厘尔圭瓒,禾巨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天”,按照郑玄的笺注“告其先祖诸有文德见记者”可知,这里的“文人”可以理解为有文德的先祖。这与《尚书·文侯之命》“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中的“文人”同义,他们都同时具有了文化角度与政治角度的复合性身份特点。从文化角度而言,“文人”指有文德的人;从政治角度而言,则“文人”主要是指具有美好品德的先祖。到了汉代,“文人”身份的内涵进一步丰富了,这主要反映在王充的《论衡》中。在《论衡》中,“文人”先后出现26次之多,如:“广陵曲江有涛,文人赋之”(《论衡·书虚》)、“故夫能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论衡·超奇》)、以及“抒其义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论衡·超奇》)等,由此,“文人”开始具备了后世文学意义上的含义,即凡“辞赋之士”、“采掇传书”的文吏以及能够“兴论立说、结连篇章”的文章之士,都属于“文人”的范畴。同时,王充也特别强调“文人”的内在德行要求,如“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论衡·佚文》)、“国之功德,崇于城墙,文人之笔,劲于筑蹈。圣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颂纪载,奚得传驰流去无疆乎”(《论衡·须颂》)等,这也就是要求文人同时还必须自觉主动地承担起与其文人身份相匹配的匡扶正义、惩恶扬善的社会道义责任。可见,从春秋战国到汉代,“文人”的概念内涵逐渐变得多元丰富。从整体上说,就文化角度而言,突出其较高的文化造诣修养;就政治角度而言,则强调其对社会强烈的道义责任担当。
而“士大夫”(也称为“士”、“士人”),则从战国时代诞生开始,直至明清时代,就始终在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文化角度而言,“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页。;从政治角度而言,这群特殊的阶层,“就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功能而言,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构成了中华帝国的统治阶级;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政治形态,自汉代以启,也可以说特别地表现为一种‘士大夫政治’。”*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因此,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自诞生以来,便以对知识的掌握而承担着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彰显其主体身份的重要标志,对“道”的终极追求则始终是“士大夫”阶层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
在对“道”的终极追求过程中,“内圣外王”的目标指向使得士大夫阶层也格外注重对自我心灵世界的内省性操持修养,由此开拓出了一个超越世俗功利性的纯粹精神世界,于是,从德行、言语、政事与文学并重的士大夫阶层中,便逐渐衍生出了一种新的文化身份,即“文人”。他们都通“文”,而在传统中国,“文”又是一个广义的“文化”概念,包括“文学”在内,涵盖了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经义策论等,由此就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文人士大夫”身份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多元多维性,诗人、词人、散文家、画家、书法家等身份,可能同时集中于一人。同时,“士大夫”与“文人”又都特别强调其内在的德行修养,只不过,“士大夫”的德性修养目标更多指向兼济天下的庙堂,而“文人”的德性修养目标则更多指向自我个体的内心修养。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士大夫”都是“文人”,只有士阶层中那些善于著述之人,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辞赋之士”、“采掇传书”的文吏以及能够“兴论立说、结连篇章”的文章之士方可称其为“文人”。到了王维和苏轼所处的唐宋时代,由于科举取士和宋代“重文轻武”政策的实施,文人士大夫的身份变得更加复合多元,特别是宋代,文人、学者和官僚集于一身的文学创作主体,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文人士大夫”。
从相对狭义的文学创作领域而言,当王维、苏轼这样具有复合型文化身份的文人士大夫以诗人身份进行诗歌创作时,其“士大夫”文化身份的先天特点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社会文化惯性心理,决定了作为诗人的他们,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士大夫”的潜意识及价值判断常常占据主导作用。因此,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无论是言志还是抒情,都会不可避免地同时具有其“士大夫”的文化情怀和“文人”的高雅情趣追求两个重要的审美维度。由此,苏轼对王维诗画艺术相融相通的论述,便是王维自身“文人士大夫”复合性文化身份在其诗画艺术领域中的必然呈现。
苏轼所谓的“摩诘诗”,主要是指王维的山水诗。作为政治失意的“士大夫”,王维又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山水早已成为他安放心灵和寻找精神栖居地的所在。其山水诗中那种任运自然、超然恬淡、空灵脱俗的世界,更多表现出的是他从“士大夫”退回“文人”自我内心世界后的一种审美体悟。因而以王维山水诗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山水诗,其最终的精神指向,便是作为“文人士大夫”的诗人在现实世界生活与自我精神世界生活中的一种诗意生存情怀传递,是一种人格化的象征体现,山水也因此被赋予了诗人独特的文人气质而具有无限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中国古代山水诗弥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苏轼说摩诘诗之所以“诗中有画”,主要是立足于王维山水诗与山水画而言的,并不能推衍到中国古代一切诗人的山水诗与山水画,必须是具备像王维这样具有多重文化身份的“文人士大夫”的山水诗,才有可能具备“诗中有画”的审美韵味。因为,在作为“文人士大夫”的王维身上,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身份便是画家——不是专攻绘画艺术的画匠,而是文人画家。在这种双重身份画家眼里的山水,已经不再是具象的山水,而是其精神活动的场所了,其山水诗中那些“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的山水,自然也不再是单纯的模范山水,而是在文人审美思维下高度写意化、人格化了的山水。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便是诗人与画师这种复合身份的审美思维结果,他们共同传递出王维诗画艺术的独特文人气息,只不过,诗歌是通过语言传递其眼中的山水物像,而绘画则是通过笔墨线条与色彩光线传递其眼中的山水物象而已。
二、作为画家的文人:从“志于道”到“游于艺”
作为画师的王维,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画的鼻祖,“文人之画,自王右丞(王维)始”(董其昌《容台别集》),在他身上,由于“文人”身份带来的充溢在绘画艺术意境中的高雅出尘意趣,也体现了苏轼所说的“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苏轼《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的特点。虽然,他们并未从理论上正式提出过“文人画”的概念,但是,王维山水画的创作实践及苏轼“士人画”理念的提出,则直接推动了中国古代“文人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苏轼在《又跋汉杰画山》中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在这里,苏轼用“意气”明确区分了“士人画”与“画工画”的不同。在他看来,士人画之所以比画工画更胜一筹,主要就在于士人画以意取胜,而不纠缠于形似问题,这与他“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绘画理论表达的是同样的思想,即士人画强调的是主观精神的表达。如他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苏轼《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突出的正是画者在模写事物外在形貌之下对自我内在生命世界的表达与关注。正如宗白华先生说的那样:“中国绘画里所表现的最深心灵究竟是什么?答曰:它既不是以世界为有限的圆满的现实而崇拜模仿,也不是向一无尽的世界作无尽的追求,烦恼苦闷,彷徨不安,它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3页。也就是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绘画艺术,其最终是要实现“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的畅神目的,传递的是一种文人审美趣味和文人精神,这也是中国绘画艺术尤其是山水画的写意传统。因此,苏轼诗所谓的“士人画”,其实就是一种充溢着文人意味的文人画。
同时,鉴于唐宋时代“文人”与“士大夫”双重身份合流的事实,以及“书盛于晋,画盛于唐宋,书与画一耳。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元)杨维桢《图绘宝鉴·序》)的实际情况,也可以肯定地说,苏轼这里所谓的“士人画”,就是我们所说的“文人画”。元代董其昌首倡并梳理中国“文人画”的发展脉络道:“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董其昌《容台别集》)从中可以看到,在这些所谓的“文人画”画家队伍中,也主要还是以士大夫为主体身份的。这些具有多重文化身份的文人士大夫进入绘画艺术领域后,使得中国绘画艺术尤其是高度写意化的山水画,成为文人士大夫人格精神与人生理想境界寄托的一种艺术媒介,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文人画的一个重要特点。
“文人画”的本质在于“文”,苏轼强调士人画以“意”为主,这个“意”就是文人士大夫的文德修养、胸襟格调等融入绘画艺术作品中的精神意趣。所以,他把王维的绘画作品与吴道子的绘画作品进行对比时,说:“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犹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苏轼《王维吴道子画》),也是将文人意味作为一个重要的审美判断标准来考量的。也因为文人画的本质在于“文”,宋代“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苏轼《文与可思竹屏风赞》)、“画者,文之极也”((宋)邓椿《画继》)的诗画同源理论才可能获得内在的支撑。近代陈衡恪定义“文人画”为:“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谓文人画。”*陈衡恪:《文人画的价值》,见郎绍君、水中天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61页。由此观之,也可以看出,苏轼所谓的“士人画”,其精神实质仍是“文人画”。
以王维、苏轼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文人士大夫,其身份的多元复合维度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即“道”的问题,这也是由“士”的身份所决定的。只有“志于道”者,才可能成其为“士”,“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因此,在现实社会中,“立德”、“立功”与“立言”便成了士大夫最高的人生价值追求。当“文人”从“士大夫”中衍生出来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依然是文人立身行世的重要方式。“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记·乐记》)的传统观念,使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属于“艺”的绘画艺术,无论如何是不能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的文章相提并论的。“志道”与“游艺”二者必须“据于德”,即以道德修养为先导的基础上和谐融合,“艺”才能成为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方式的选择。因此,苏轼也格外注意和强调画家的道德修养:“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白工通。虽然,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苏轼《书李伯时山庄图后》)费衮也说:“书与画皆一技耳,前辈多能之,特游戏其间,后之好事者争誉其工,而未知所以取书画之法也。夫论书,当论气节;论画,当论风味。……至于学问文章之余,写出无声之诗,玩其萧然笔墨间,足以想见其人,此乃可宝。”((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六)这种否定艺术功利性,强调有道有艺的志道之境,也是中国文人画最为重要的内在美学精神追求。
作为文人士大夫的画师王维,以诗意升华画意,开拓出一个禅意盎然的山水画境,苏轼“画中有诗”就是对他山水绘画作品中表现出的文人精神意趣的肯定:“摩诘本词客,亦自名画师。平生出入辋川上,鸟飞鱼泳嫌人知。山光盎盎著眉睫,水声活活流肝脾。行吟坐咏皆自见,飘然不作世俗辞。”(苏轼《题王维画》)自此之后,“画中有诗无诗,关系到作品能否反映画家个人在生活、现实中的感受;进而创立意境,表现风格,也就是作品中有无个性的问题”*伍蠡甫:《试论画中有诗》,见曹顺庆选编:《中西比较美学文学论文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74页。,便成了文人画尤其是文人山水画的重要审美判断之一。
苏轼的其他许多诗画理论也再次印证了他对“士人画”或说“文人画”的审美理想追求。如他评论燕肃山水画曰:“山水以清雄奇富、变态无穷为难。燕公之笔,浑然天成,烂然日新,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也”(苏轼《跋蒲传正燕公山水》),强调的正是对文人山水画中诗人意气风骨的追求。他对王诜山水画的题诗:“老去君空见画,梦中我亦曾游。桃花纵落谁见,水到人间伏流”(《次韵子由书王晋卿画山水二首》),体现的还是对这种文人山水画所所蕴含的创作主体自我内心世界不俗于世的精神追求。
当然,苏轼之所以如此推崇王维诗画相融的艺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唐宋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普遍受到佛禅文化心理影响而形成的独特审美体验。王维与苏轼都在自己“士大夫”的社会角色失意后寄情山水,并且又都不自觉将自己“文人”所具有的文学气与书卷气入诗入画,把山水诗画推向了一个更加幽远空灵的意境,使其人生境界与艺术境界自然融为一体,无论是山水诗,还是山水画,都是他们抒发情感、回归自我的载体,共同承载着文人士大夫们的精神意趣和审美追求,成为创作主体吟咏性情的游心之所。因此,当苏轼面对王维山水诗画进行审美欣赏时,他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诗歌与绘画作为两种不同艺术类型的固有区别,而是贯注其中的那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整体生命精神。在他的诗画文论中,较好地体现了中国文学批评固有的“人化”或说“生命化”特点:“在我们的文评里,文跟人无分彼此,混同一气,达到《庄子·齐物论》所谓‘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的境界。”*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见《钱钟书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02页。也就是说,作为欣赏者的苏轼,面对充溢着生命情性本体的艺术作品时,其审美思维已经逾越了艺术门类之间的界限,在“破体相参”的审美观照中,实现了“与道为一”的终极审美追求。
三、作为鉴赏者的文人:从“破体相参”到“与道为一”
苏轼各种诗画理论中体现出来的“诗画一律”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唐宋时代能够将诗文书画等多方面的修养融会贯通的文人士大夫的博学深思。诗画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弭,游心于诗情画意的艺术意境之中,作为鉴赏者的苏轼,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其中,在打通诗画艺术内容外表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以艺术为媒介而将外在自然宇宙生命与人的内在精神生命融为一体的“圆览批评”,典型地表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破体相参”的思维方式。
在宋代,“破体相参”本是一个文学内部概念,主要是指在文学内部的各种文体,如诗、词、文之间打破文体间的界限,在创作手法等方面相互参考借鉴。“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文为赋”、“以文为四六”等都是宋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破体相参”现象。“破体相参”在宋代的蔚然成风,深刻影响了宋代文学的整体面貌。然而,从苏轼的“诗画一律”论以及“诗文相生”、“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等论调都可以看出,在宋代,“破体”实际上已经逾越了纯粹文学领域的创作实践,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思维方式,泛化到了整个艺术领域尤其是诗画艺术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在宋代,不单是苏轼,其他文人士大夫亦提倡和认可“诗画一律”论,形成了宋代蔚为壮观的诗书画同源论,如“文者无形之画,画者有形之文,二者异迹而同趣”((宋)孔武仲《宗伯集》卷一《东坡居士画怪石赋》)、“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宋)张舜民《画漫集》卷一《跋百之诗画》)和“终朝颂公有声画,却来看此无声诗”((宋)钱鍪《次袁尚书巫山诗》)等。
从宏观上说,宋代“破体相参”思维得以在诗画艺术之间发生,主要源于《周易》象喻思维传统以来奠定的认知基础。从《周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象天法地思维以来,作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吟咏性情的载体——诗歌与文人画,逐渐在“意象”的基础上实现了界域的融合。伍蠡甫说苏轼所谓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就在于“强调诗寓情于景,画借景写情,要皆以意、情为主”。*伍蠡甫:《中国画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页。作为抒情艺术的诗歌与文人画,都在于通过“象”(语象、画象)的创作来实现文人士大夫抒情悟道的终极目的,以及“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价值追求。在苏轼看来,王维那些字字入禅的山水诗,以及他山水绘画中那些将“素朴而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的自然无为、虚淡玄无审美趣味融于笔墨线条与林泉烟岚之间的情致,使得“诗人与画手,兰菊芳春秋。又恐两皆是,分身来入流”(苏轼《次韵鲁直书伯时画王摩诘》),都是文人士大夫吟咏性情审美理想的完美融合。苏轼自己“诗画一律”的创作实践,也有效地印证了自己的艺术理论。如他题卢鸿一的《草堂图》:“嗟予缚世累,归来有茅屋。江干百亩田,清泉映修竹。”也可以看出,在以苏轼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那里,诗画由于较多融入了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理想和人生意趣,具有强烈的表现性、抒情性和写意性,形成了一个面向生命敞开的情性本体空间,他们浑然一体,引发欣赏者对自然宇宙生命的整体感悟。作为鉴赏者,以虚静之心入乎其内,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对其进行清晰的逻辑分析,而在于在品味、意会、妙悟的过程中超越艺术形式的外在之器而达到对艺术作品本体之道的把握,最终实现精神上的绝对逍遥游。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知音》里说的那样:“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这个审美欣赏过程,也就是“与道为一”的过程。
这种思维方式在宋代的泛化,还与宋代文人士大夫“大都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王水照:《王水照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0页。有着密切关系。宋代,“在士从门阀向文官,再向地方精英的转型中,文化和‘学’始终是作一个士所需的身份属性。”*[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0—81页。对于他们来说,琴棋书画的文人士气综合修养使得文人参与绘画、书法都成为了士大夫诗文才识的自然延伸与拓展,治经纬天下之学、写诗作词赋文之外,绘画、书法也是他们修身养性的日常生活常态。“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黄庭坚《题子瞻画竹石》),“文化”和“学”赋予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的品性、学识、才情与思想,织就了宋代文化整合的内在智慧。在以道贯艺的艺术创作过程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也者,虽志道之士所不能忘,然特游之而已。画亦艺也,进入妙,则不知艺之为道,道之为艺”(《宣和画谱·道释叙论》),在“道”的统领下,不同艺术范畴之间在精神指归上实现了相互补充与融合的内在可能性。
同时,“破体相参”思维方式在宋代的泛化,还与宋代禅宗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周裕锴先生提出:“大乘佛教诸经尤其是《楞严经》中‘六根互用’的观念,在北宋中叶以后士大夫习禅的背景下,逐渐向日常生活和审美活动方面渗透。以苏轼、黄庭坚、惠洪等人为代表,从个人修道体验出发,追求六根通透、一心湛然无染的境界。由此带来三个变化:一是有意混同眼、耳、鼻、舌、身等感官之间的界限,尤其是主张眼听、耳观、目诵,从而形成听觉艺术(诗)与视觉艺术(画)相通的全新意识。二是将六根所接触的现象世界升华为心灵境界,将吟诗、作画、焚香、品茶、赏花、尝食诸多活动当作参禅悟道的途径或方式,从而出现诗禅、画禅、香禅、茶禅等宗教精神渗入世俗生活的现象。”*周裕锴:《“六根互用”与宋代文人的生活、审美及文学表现——兼论其对“通感”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136页。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苏轼“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鉴赏过程中,正是在这种“品”诗与“观”画的“六根互用”感知里,本已就将诗画渗入日常生活常态的文人士大夫生活方式,才使苏轼得以将生命整体贴近艺术范本进行圆览观照,最终达到“与道为一”的最高境界。
因此,当我们站在历史彼岸的今天,以现代学术眼光审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如苏轼、王维这样的文人士大夫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的“文人”,其内涵较今天的文人概念具有更加丰富的意蕴。作为从士大夫群体中分流出来的文人,从汉代到唐宋时代,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直接决定了文人的生命存在状态及价值追求,也深刻影响着文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艺术生命。在中国古代象喻思维方式影响下的文人士大夫艺术创作实践与审美欣赏活动,无论是诗歌还是绘画,在与天地相参的过程中,都隐含着对“文”的伦理道德追求及创作主体高雅脱俗的情趣品味追求,其终极价值都在于在吟咏情性中“与道为一”,实现文人对自我本体生命的美学超越。苏轼的一系列诗画理论中,隐含着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文人”之为“文人”的丰富文化信息,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唐宋诗画艺术相融相通的内在理路。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