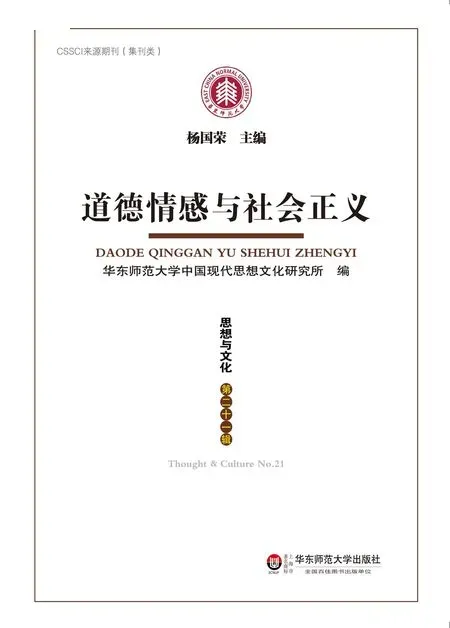论“听”与“道”的关系
——以先秦为中心的考察*
先秦诸子在阐明自身思想的同时,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彰显出“听”与“道”存在的密切关联。听的主体因遵循“听之道”,使得自身得以在闻道的基础上,不断地体味道、践行道,在将“道”行之于实际生活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对“道”的体悟。这既展现出个体通由听体道、得道的可能性,又彰显了“听”的意义与价值。
一、闻道、体道、践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最初的含义为道路,“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经·采薇》)进而引申为行走,“道,行之而成。”(《庄子·齐物论》)这一意义上的“道”与规范性相关,“道路总是通向某处,引申而言,‘道’意味着将人引往某一方向或引导人们达到某一目标。道所蕴含的这种引导性内涵经过提升以后,进一步获得了规范意义。”*杨国荣:《道与中国哲学》,载《道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1页。这种规范性的道,包含天道和人道两个方面的内容。听是获得这一意义上的道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 闻道
在先秦时期,不少典籍将闻与道并提,以“闻道”来表达获得“道”的一种状态。“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下之配也。”(《管子·形势》)“闻”虽不能完全等同于听,但无疑与听密切相关。首先,“闻”乃是“有往有来”的听。《说文解字》中说:“闻,知声也。从耳门声。”*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50页。段玉裁解释说:“知声也。往曰听,来曰闻。大学曰:心不在焉,听而不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92页。从于“耳”部,已说明了它与听的关联。“闻”具体为对声的体知,这需要运用心的作用。它彰显为一个用耳迎来声,并运用心的作用,将其引入人的认知领域,加以体认、感知的过程,这与理性的听相通。应注意的是,一方面,对“闻道”的解读与关注,旨在说明“闻”乃是迎来和获得“道”的重要途径之一,并非是唯一的途径;另一方面,“闻”为个体获得和把握“道”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同时也表明,其他的认知方式在这一点上可能存在局限。秦穆公曾向由余问“道”:“寡人尝闻道而未得目见之也,愿闻古之明主得国失国何常以?”由余答曰:“臣尝得闻之矣,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韩非子·十过》)“道”从久远的过往中走来,具备道的行为已不可见,只能通过别人的讲述,由耳听之的方式得以听闻。由余以其所听,回答穆公所期之闻,便体现出道在一些情况下,已不可得见,却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得以被听取、传递。然而,言在表达道上亦有局限性。“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如果能够用言来表达的道,即不是我们所说的道了。但道毕竟是可闻的,“上士闻道,勤而行之。”(《老子·第四十一章》)换言之,言说虽然对道在表达上有局限性,但道可以通由闻而被获得。应说明的是,这里与听相关的“闻”,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听,因为一旦用某一种方式去听、闻,则道在声上必有固定之声响,从而有所局限,则“道”便不是那个所谓的“常道”,因此,“道”在声上所具备的一切之可能性,唯有通过听无声之道才能获得。“道”因为具备了一切声的可能性,所以,本身是无声的,或者说没有固定的声,所谓“听之不闻其声”(《庄子·天运》),面对这样的无声之道,我们亦不能通由一般意义上的耳去听,而只能通过“听乎无声”(《庄子·天地》),以心听来获得与把握。这种意义上的“闻道”,方能在迎来道的同时,保全道的完整性。“南伯子葵问乎女偊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庄子·大宗师》)女偊之所以能面若幼子,是因为“闻道则任其自生,……闻道故得起全”。*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52页。通过闻,个体能任事物之自性生长,并迎来整全之道,从而保持童之气色、容颜。概而言之,目见与言说在道的迎来与获得上存在局限,与之相对,闻作为一种与听相通的方式,为完整、全面地获得道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二) 体道
个体在闻道的阶段,还仅仅只是迎来道,对其尚未有透彻的了解和把握,故而在闻道后,个体需有一个体道的阶段。所谓“体道”即是指对“道”予以体认,对其内涵进行了解和把握。在这一过程中,听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在寻觅体道的方法上,给予我们启示。换言之,听与体道的关联,具体表现为如何在听的层面,寻找正确的方法,体认和把握道。
首先,聆听来自上天的声音,是主体把握道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一层面的“道”更多地与天道相关联。而要听天之音,把握天道,需先听民之声,把握人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尚书·周书·泰誓中》)。要想聆听来自天的声音,首先要听取百姓的呼声,因为百姓的声音即代表了上天的呼唤,在听民声的时候,自然就从中听取了来自天的声音。从道的层面来看,天道乃在人道中彰显,通由人道的体认可以把握天道的内容,由听民之声进而可以听天之音,便是一个例证。
我们不仅通过聆听来自天、民的声音,体味、把握人道与天道,而且以天为其对象来展开听,这是说,我们依托于天来达成我们的听,并在听的过程中,超越经验性、固定性的听,来完成体道。“人也者,……寄于天聪以听。”(《韩非子·解老》)人在完成听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寄之以“天聪”来听,这与“听天下”相联系,即以天下百姓之耳为己之耳,则可达至“无所不闻”之境地,从而呈现聪的状态。这同时也是遵循天之道而听,遵从天之声音而听,如此方能正确践行听的行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听并不能一味向前,因为“听甚则耳不聪”(《韩非子·解老》),过分听取太多的声音,反而会阻碍聪的到来。一旦如此,则可能导致一系列的后果,“耳不聪则不能别清浊之声,……耳不能别清浊之声则谓之聋,……聋则不能知雷霆之害。”(《韩非子·解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从“人也者”开始,将人之听寄托于“天聪”,正体现着天与人的结合,“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韩非子·解老》)前者关联天道,后者涉及人道。在听上,不断地通由听趋近“动静思虑”,既以“聪明睿智”之天为其指向和寄托,又不断地向之靠拢,个体通由听不断地完善自我,在体味人道的过程中,体认和彰显着天道。
这里对于“听甚”的反思与自觉,值得我们注意,这和道本身的性质有关。“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第四十八章》),对于道的把握相比于学而言,需要“损之又损”(《老子·第四十八章》),由此出发,在由听体认道的过程中,也一样需要对既有的、固定的听予以超越,以听上的“退”来获得“聪”的状态,从而由听“体道”。进言之,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对于道之声,并不执着于某一种固有之声的听闻,而是在整体上,听取、体认、把握道,换言之,道本身所具有的整体性的特点,即要求听者不能执着于固有的听的行为,而应以更为广博的听来迎接、体认、把握它。“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管子·内业》)“道”因为不固定于某一种形质,故而具备成为一切形质之可能,从而为一切事物之根源。基于这一特点,“道”不能以耳听之,但这并不是说通由听无法体认道,而是要求听的施动者对即有之听的超越和转换。如同音一样,从“五音令人耳聋”(《老子·第十二章》)到“大音希声”(《老子·第四十一章》),音不断地从固有的“五音”向“大音”转化,听也需要从固有的、经验性的具体之听向“修心”之听转化,以心之聆听来迎接这“大道”的寂静与可能,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完成由听体道。在听的这一转换过程中,听者自身也对道本身的意义、特点有了了解和把握,如若不然,则这一转换将无法实现。
道常内蕴于一些制度性的规范、条文,如礼、乐之中,“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这里的“天地”可以理解为天地之大道。乐,体现的是天地大道的和谐;礼,则彰显了天地大道在人间的秩序。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些规范性的条文或音乐等,都是人遵循道而制定的,听这些内容,能够帮助主体体认和把握道。
《管子》曾指出:“五和时节……听宫声,八举时节……听角声,七举时节……听羽声,九和时节……听商声,六行时节……听征声。”(《管子·幼官》)这说明,从礼的规定来看,不同的时令应听不同的乐。之所以如此做,乃是因为“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序”在这里具体表现为“时序”,即天地之大道在时间上所表现出的秩序,换言之,遵从天地之时序而听不同之乐,既是对天地之大道的尊重、遵循,又可从中体味天地之大道。进一步说,随着天地之时序的变化,需随之改变听乐的具体内容,这乃是要求听者,通过听此乐,来体味不同时令在天地中的位置,从而感受天地之时间秩序,于此时序中体味天地之道序。由此可见,一方面,礼对于乐的上述规定,体现出礼与道的关联:依据天地之大道来规定人间之秩序,听从这样的礼行事,则可以通过“听礼”而“体道”;另一方面,礼在这里的规定,具体将天地之道序与人间之时序相联,并通过听不同之乐来体现对大道的遵循、尊重,故而在“听乐”的过程中,个体一样通由此听得以体道。概而言之,上述内容体现了通由听礼、乐而体道的过程。
由上所述,不难看到,道包含的两个方面,即天道和人道,并非彼此隔绝,而是相贯、融通的。礼和乐首先与人道相联系,前者规定着人间的秩序,后者则是这一秩序的载体之一,两者既以人道为内在依据,又彰显着人道。因礼、乐与天地之大道的关联,听礼、乐即是要求通由这样的聆听,先体味人道,再通达天道。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认为道很玄远,乃是因为我们常将“道”理解为在上的天道,看不见,摸不着,无有形质,并不实在。事实上,如上一再强调的那样,“道”并不仅指天道,还关涉人道,人道与我们的具体而真实的生活息息相关,而通由人道还能体味天道。“道不远人”(《礼记·中庸》),所谓“不远人”,即是指道内蕴于我们的日用常行之中。立足于听来说,便是通由听即可体认和把握道。听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中最为常用的认知途径和手段之一,具有真实性、实在性等特点,这就摒除了玄虚、抽象等弊端,从而使得由听体道具有可操作性,不再局限于个体自身的感受、体悟,而能依据一定的方式、方法传递给他者。听的这一品质,以及其与体道的关联,证显着“道不远人”。
(三) 践道
闻道、体道之后,还需践道。这是说,在迎来道,体味道之后,道一方面需贯彻于我们的实际行为,另一方面,需通过行为来践行和彰显大道。“上士闻道,勤而行之。”(《老子·第四十一章》)最高境界的“上士”,乃是在闻道之后,积极、勤勉、自觉地践行“道”,通过行将道内化到自我的精神生命中去,从而与道为一。可以看到,闻道的最终归宿乃是行,即践道。同时,在勤勉行道的过程中,个体也逐步对道有了更深的理解和体悟,进一步认可、接受了道,从而更好地将其幻化为自我精神生命的一部分。
由闻道、体道,继而践道的过程,不但关乎对道自身的体认和把握,而且涉及将此道贯彻于实际行为,并在具体行动中,不断体悟道之真谛的实践智慧,换言之,道本身具有规范性,这使得它带有某种抽象性,在践行道的过程中,需要将抽象性的道与实际的生活相连接,进而发挥和落实道的作用,这才是践道。在从抽象性的、规范性的道向具体的践道行为转化的过程中,涉及关乎道的实践智慧。“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管子·形势解》)道从内容上来看,其为“一”,但在践行、使用的过程中,却呈现多样的差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下之配也。”(《管子·形势》)在获得、把握了道之后,能将其贯彻于不同的对象:家、乡、国、天下,便可称为对之有用的人才。“道”作为普遍的规范性原则,需要与不同的作用对象相结合,方能发挥其实际的作用,闻道者之所以能将道与不同对象结合,并成为“一家之人”、“一乡之人”、“一国之人”、“天下之人”,乃是因为掌握了道在践行过程中的实践智慧。唯有具备了从闻道到践道的实践智慧,才能在获得道、体认道的基础上,将其贯彻于实际行为。
掌握“道”之层面的实践智慧的必要性,不仅基于对道的规范性所带来的某种抽象性的考虑,而且在于道本身具有混沌未分、变动不居的特点。如前所述,在老子看来,“道”乃是一切事物之本源,因其自身具有未分化、未定型的特点,使其有可能分化为其他一切可能之形态。从这种未有分化,向各种不同的具体形态转化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关乎道的实践智慧。道同时又作为一种统一的秩序,为动态分化的实现提供指导。“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系辞上》),阴与阳的互动,彰显的是世界的变迁和演化,“作为现实的存在,世界不仅千差万别,而且处于流变过程之中”*杨国荣:《道与中国哲学》,载《道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9页。,要把握这样的“变”,需在万变中把握不变,这一“不变”便是“道”。可见,世界虽变动不居,变化不定,但因道所蕴含的规范性、秩序性,使其本身呈现为一种有序的存在状态。*具体可参见杨国荣:《道与中国哲学》,载《道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8—335页。这一根源于道的有序性为分化的可能性提供了保障。
日常的言行在展开过程中便可彰显道,从这一角度出发,言行的践履便是在践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说“日用即道”。听作为一种日用之行,其在践行的过程中,可以通由其体道,此外,听之行为本身就可以是一种践道的行为。要想达成这一点,则听之主体必须依循正确的听之方法,即所谓“听之道”,如此方能促使听趋近完善。可以看到,这里的“道”又具有了方法论的内涵,具体展现为一种践行听的正确方法。
二、听之道
无论是体道还是践道,都需要遵从“听之道”。这是说,在由听体认、把握、践行道的过程中,要正确运用听的方法。如若不然,则无法正确地体道和践道。
在由听而体道、践道的过程中,道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听需超越一般经验层面的具体行为,达至以心听、以神听、以气听的状态,如此方能听获“无声”之道。
文子问道,老子曰:学问不精,听道不深。凡听者,将以达智也,将以成行也,将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达。(《文子·道德》)
“听道”需深,如此才能通达无碍。要想做到“听道”深入,需要依次经历“以耳听”、“以心听”,最终达至“以神听”(《文子·道德》)。所谓“以神听”既以“以心听”为基础,又超越“以心听”,而具体表现为全神贯注、倾注身心的去听。在听的过程中,不断地通由听将大道迎接到个体的生命中来,实现听者与大道的融贯为一。可以看到,无论是“以心听”还是“以神听”,都根基于听者的自心。以何种状态的心去践行听,决定了“心听”和“神听”达到的程度与效果。“凡听之理,虚心清静,损气无盛,无思无虑,目无妄视,耳无苟听,专精积精,内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长久之。”(《文子·道德》)要想做到“以心听”、“以神听”,需要以“虚静之心”面对、展开听,对思、虑有所保留和反思,自觉克服和节制过多的欲望对心和听的干扰,方能以清静、无欲之本心,专于一事。如此一来,道一旦得之,便可长久固守,这乃是正确的听的方法与道理。可以看到,去除内心的欲望,以清静、虚空之心,展开听的行为,体现出道家思想的倾向。
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管子·心术上》)
这里的“上”显然和心相联系,“下”则与耳、目联结的听、视等认知途径相关联,因为心中有太多欲望的干扰,使其偏离了正道,所以,才会导致“声至而耳不闻”。若做正面的表达,则是若想做到“以耳闻声”,便需要积极消除内心过多的欲望。《管子》中虽有很多表述展现出法家思想的特点,但这里显然与道家的论述有相近之处。在由听闻道、体道、践道的过程中,主体应自觉摒除内心之欲望对于听的干扰。对此,儒家亦有提示,只是它没有直接以“道”来表述,而是借助于“礼”来说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如前所述,礼是制度性的规范,以天下之大道为其内在根据之一,礼是通过条文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规定社会的等级秩序,这本身就是对人的自然性的规约和节制。“非礼勿听”则是要求人们不要去听与礼不符的内容,这即是以礼来规正人的听的行为,使得个体在听上的自然性与自身的社会性得到博弈,从而能够在遵礼的同时,由听礼而闻道、体道、践道。
概而言之,在听的过程中,道家强调的是,对于过多的听之欲望的自觉摒除,儒家则偏向于以一定的规范、标准来范导、规约听的行为。两者的相通之处在于,都对欲望在听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有所自觉和反省,要求听者应以一颗清静、正确之心来展开听的行为,这便是“听之道”的核心,也唯有依循这一方法,才能通由听去接应“道”。
心在达成上述状态的过程中,内蕴了个体修德的内容,德与道通由听密切关联。具而言之,听者若要以清静、少欲或无欲之心,来践行听的行为,从而获得道、践行道,就必须先有一个修己之德的过程,即通过自我的修习,不断地节制自然的欲望,克服自身的不足,从而以正确的方式来践行听的行为,唯有这样的听才能在实际展开的过程中,被看成是一种对道的践行,也唯有通过这样的听,才能由听体道、得道。概而言之,修德(包括修习德性和完善德行)为正确的听提供了有力保障:修德性使得听之心乃为清静、正确之心,善德行使得听之行为逐步成为“道”之体现,唯由此听,方可闻道、体道、践道。也唯有此听,才能接续道,彰显道。*可参见拙文《论“听”与“道”的关系——立足先秦视域的考察》,《应用伦理学》2016年第1期。
“听”不仅可以理解为“聆听”,而且可以诠释为“听从”,从后一意义出发,听与道的关联,表现为唯有得道者的言行才能为天下听从,否则,百姓将叛离而不听。立足于“听之道”来看,要想通由听而得道,进而让天下听之,则必须遵从“听之道”。“失天之道,则民离叛而不听从。”(《管子·形势解》)失去了天道的依托,其言行则是离道、叛道之言行,自然会被天下百姓所离弃,不予听从。进言之,若背离、失去了天之道,则“天下不可得而王也”(《管子·形势解》);与之相对,“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管子·形势》)。若能获得天之大道,则其言行自然会被天下百姓所听从,其成事、称王则十分自然,水到渠成,无需刻意作为。要想得道而使天下听之,从“听之道”来看,则要求主体遵从听的正确方法,如此,方能通由听而得道。当然,这并不是说,听是通达道的唯一途径,而是说,听为得道提供了可能性路径,而要通由这一路径正确、顺利地得道,需要遵从“听之道”。
三、听:在天道与人道之间
“道”所包含的两个方面的意义——人道与天道,并非彼此隔绝,而是密切相关。在听与道关系的展开过程中,听成为了沟通两者的桥梁。
听作为日常的认知途径和方式,常被人使用,个体遵循“听之道”展开听的行为。一方面,唯有如此之听,才能帮助听者闻道、体道;另一方面,这样的听的展开本身即是一个践道的过程,因为“日用即道”,听作为一种“日用”之行,因为符合“听之道”,故能通由听来体味道,这一过程体现出践道与体道的关联:在不断践行道的过程中,实践的主体也加深了对道的体认。在这样一个互动、反复的过程中,听本身也将道贯彻于具体的行为之中,使之成为符合大道的听。如此之听,方能闻道,并进一步帮助听者体味道、践履道。
听作为日常的真实行为,具有“不远人”的特点,内含道的听,或符合道的听,彰显着“道不远人”(《礼记·中庸》)的意义。如前所述,我们之所以认为“道”玄远,难以把捉,乃是因为将“道”理解为天道,但当我们通由听来体认、把握道的时候,道的到来就变得更为切实,同时也具有了可能性和可操作性。道不在远方,就在近处、在当下,在像听这样的具体行为之中,做好它便可以迎来和把握道,这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努力正确地践行听。但应该注意的是,在由听而体味天道的过程中,听者往往是从体味人道开始的,因为听毕竟首先作为一种日常的认知行为存在。礼作为一种制度性的规范,本身内蕴着人间之道。“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乐作为礼的体现,亦彰显着这样的人道,通过“听礼”、“听乐”,个体能够通由礼和乐把握人道。但礼、乐在内蕴人道的同时,还关联着天道,“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乐”体现的是天地万物的和谐,礼则彰显着天地的秩序,这样的“和”与“序”都可视为天道的表现,听者亦由此从人道进而把握天道。此外,“乐”亦与快乐相联,“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荀子·乐记》)音乐所带来的快乐,乃是人不可免除的自然情感,而在这一人情中,即蕴含着天道,“此天之道,人之情也。”(《荀子·君臣下》)天道与人情的联系,从另一个层面彰显了天道与人道的关联,在“听乐”的过程中,人之情感的流露,即内蕴着天道。
除此之外,在听的过程中,主体应“遵道而行”,如若不然,便会导致百姓不听,天下离叛的结果。这里的“道”一方面指向天之道,“失天之道,则民离叛而不听从”(《管子·形势解》),另一方面,亦涉及人之道。因为,在失去了天道的依托之后,人道也会随之失去,换言之,不遵从天道行事,亦会使其违背人道,丢失民心,被百姓叛离。由此可见,遵从了天道,其言行将与道相符,如此方能收获“民心”,为天下所拥护。同时,唯有以人道作为依托,积极听取百姓的声音,才可说听从了天道,因为“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周书·泰誓中》),天的呼唤即在百姓的呼唤之中。听从百姓之声,继而听从天道,是让天下听之的前提。总之,无论从“聆听”之“听”,还是“听从”之“听”来看,天道与人道都在听上得以联系。由此,听成为沟通天道和人道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