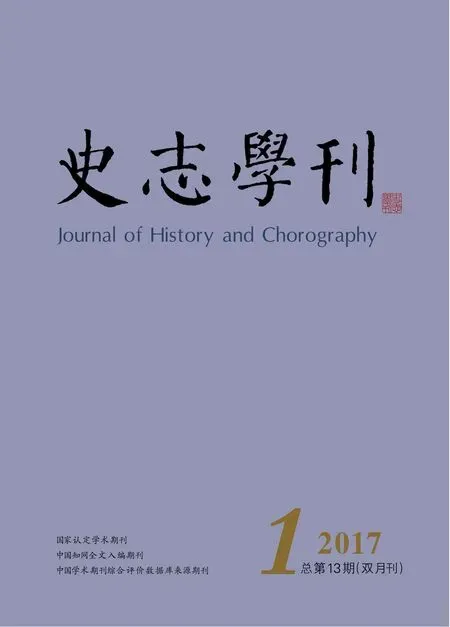中西农业文明下的牛耕与马耕
陈桂权
中西农业文明下的牛耕与马耕
陈桂权
(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秦巴文化产业研究院,四川达州635000)
10世纪前西欧以牛耕为主,之后马耕逐渐推广。欧洲的马耕推广是技术进步、三田制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结果。比较而言,马耕在中华农业文明中始终不太普遍,主要是因为马的军事用途更被看重,犁地主要依靠牛来完成。中西农业文明中对于牛耕与马耕的不同依赖,既是各自不同农业发展结构的体现,也是由不同社会经济特点所决定的。
中西农业文明 牛耕 马耕 犁地
英语中常会用“to work like a horse”表示要努力工作,“work for a dead horse”表示“徒劳无益”;汉语中常用“牛一样的勤劳”“老黄牛一样的精神”来夸奖一个人。牛与马这两种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在东西方文化中有着不同的用途与地位,围绕着它们这种差异也形成了相应的文化寓意。对于牛与马这两种动物,从与农业相关的角度来考察,那就是犁地了。因此,本文就“牛耕”与“马耕”在我国与欧洲农业中的不同地位,做一分析探讨,以期阐释不同农业发展模式下的技术选择问题。对于中西农业发展结构的不同,曾雄生先生在《中西农业结构及其发展问题之比较》一文中已做了精当的阐释,文中称中国农业耕地以牛耕为主,西欧在使用牛耕的同时,也广泛使用马耕,主要原因是三圃制的实施能为马提供更为充足的燕麦饲料[1]曾雄生.中西农业结构及其发展问题之比较[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3).(P49-58)。该文指出了中西方农业在畜力使用方面的差异,是本文进一步阐释的重要参考。除农作制度不同外,还有其他诸如社会经济成本、地缘政治、人地关系等多种因素,导致了中西农业文明下在犁地时对畜力使用的不同。
一、10世纪前欧洲的牛耕
在古典时代与中世纪前期的欧洲,拉犁主要还是公牛的任务,偶尔在一些土壤表层较浅或穷人的地里,能看到用母牛或驴子在耕地的农民。据一份来自1086年的英国农业调查显示,当时各领主土地上“马的比例仅占畜力的5%”[2](美)John Langdon.中世纪英国农业的一场悄悄的革命:公元1100年至1500年的马耕[J].农业考古,1998,(3).(P183),当时的畜力主要包括牛、马、驴子、骡子。这时候,马的主要用途还是充当坐骑及运送旅客。至于为何此时未用马来代替牛耕地?学者们认为可能主要有这样两点原因:
其一,这个时期实行的“两田制”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马。历史上欧洲的田制有一个由“两田制”到“三田制”的变化过程,中世纪是转变期。相比两田制,三田制在作物播种总面积与轮作类型上更多样,其收获物也更多了。因此,利用三田制的农民有足够的粮食与饲草来养家畜。
其二,适合马耕的技术装备尚不健全。那时的马还没有钉马掌,脆弱的马蹄经不起地里各种小石头的折腾,即便不下地,日常运输也不能长途进行。人们通常用一些保护物缠在马蹄上,罗马人还给马穿上了“蹄靴”。另外,在古典时期的欧洲,人们给马戴的轭套是直接套在它的脖颈上。这种轭套勒住了马颈下的主动脉,使得它们极其不舒服,自然就使不出力量来。而牛就不一样了,它们那耸起的肩膀,较适合安放牛轭,即便没有这种肩部的套具,还可以套在牛角上。1170年,一本叫《开心果园》的书中提到,在法国的阿尔萨斯地区,牛角是挽犁的地方。这种挽牛角的做法,相较于勒马脖子的技术要先进些,但仍旧不能使牛发挥出最大的潜力。
所以,欧洲大规模使用马耕的历史是在12世纪以后。美国学者John Langdon在《中世纪英国农业的一场悄悄的革命:公元1100年至1500年的马耕》中,对马耕如何在英国逐渐取代牛耕有比较全面的论述。在他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马耕取代牛耕的过程并不是那么容易。农民对此有成本的计算,还有习惯性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与当时社会经济需求是否适应。欧洲的马耕最终能取代牛耕,是因为它适应了社会的普遍需求。在当时“拥有少于10英亩土地的农民比较偏好使用马耕地,因为他们较轻便的犁头更合适用马拉,而且马在耕地之外还可用作乘骑、拖拉货物”[1](美)克莱顿·罗伯茨,戴维·罗伯茨,道格拉斯·R.比松著.潘兴明等译.英国史上册[M].商务印书馆,2013.(P110)。也就是说,相比于牛,马的用途更广。虽然养马的成本较高,但因农作制度革新之后,粮食的产量也大幅度提高,这就使对马的饲养有了物质基础。同时,马耕的推广又促进了农业总产量的提高。
二、牛耕与马耕之优劣比较
对于牛耕与马耕各自优劣的比较,人们通常从成本与收益角度来进行分析比较。13世纪农学家们对此的看法是“马吃更多的燕麦,马得钉掌,而牛不用这些。因此,养马的费用比牛多4倍。而且牛的脾气更温顺、老了还可以卖给屠夫吃牛肉,而马只能卖皮,甚至有一段时期,马是不允许被宰杀的。所以,马的价值折损费较大,而牛的保值性却较高。”[2](英)波斯坦.剑桥经济史(第1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P125)另外,马更容易生病。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卷六中记:“常系猕猴与马坊,令马不畏,避恶,消百病也”。这就是民间一种防止马生病的措施。吴承恩给猴头孙悟空安个“弼马温”的官衔,其文化寓意就源于此。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广泛的用途上:驼、骑、拉,民用、军用都可以。相比之下,牛在这方面要逊色多了。虽然牛也拉车,但毕竟不如马常用。此外,马在速度与炫耀性消遣上,又比牛有优势。故而,我们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中世纪早期,领主的土地上多用牛耕,而农民反而喜欢马耕的现象了。因为,马对于领主而言是坐骑,是骑士耀武扬威的装备,至于像拉犁、拉磨那些苦活累活还是让牛去干合适些;而农民喜欢用马,除了我们说的马用途更广之外,或许是他们还想在农闲之余,体验下策马奔腾的感觉。
再者,马耕在速度上也具有优势,16世纪的法国农业家们对此给予高度赞扬,他们声称:“马一天干的活是牛的3倍甚至4倍”。对于农民而言,快速犁完地当然是好事。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马耕比牛耕更快的论断,还要视情况而定。耕地是人与动物相互配合的协作式劳动,其效率的高低是两者合力的结果。因此,单看动物劳力大小、速度快慢,或者犁地者技术的好坏,都不足以说明问题。从速度上看,马定是快于牛。只是,耕地时,马的步伐快慢需要与耕地者的步伐协调一致。若马拉的步伐太快,耕地人无法适应,最终也不能保证耕地的效率;而牛的脚步也不可能太慢,因为犁地速度的控制权掌握在人的手中。此外,还有些因素会影响到耕地的速度,如土地平整度,犁平地比犁坡地快;耕者技术的高低;犁头的类型,这也很重要。欧洲常用一种轮犁,这种犁头操作起来更为轻便,且速度更快,能很好地适应马耕;我们中国的多数犁头,既不是为马耕设计,速度自然就快不起来。故,马耕更适合欧洲,这是技术、社会、经济等因素综合的结果。再后来,当现代农业机械化生产要普及时,那些推广耕地机器的宣传者们又把马耕说得一无是处。如苏联上世纪50年苏联作家伊林《五年计划故事》中有段关于工厂与农民所有的“引擎”对比的记录:
谷类工厂有曳引机,农民有什么引擎呢?马。马是所有机器中最贪食,最嘴馋的。他要嚼掉农民田里出产的一半。在乌克兰草原地方,农民为他的马一年要花费五十金镑——跟他给全家人所花费的一样多。
马是一种最贪食的引擎,同时它是一种最孱弱的引擎。一部曳机可以做二十多匹马的工作,并且用马耕地不能像曳机耕得深。但是,连这种孱弱的引擎给农民用还是太强了。普通的马给农民做活,还没有用出全部精力。想一想马全部闲散着的日子吧。一年当中只劳动一百天,可是一年到头,天天都得喂它。曳引机只是在工作的时候才用汽油。并且马做起活来,也太少了。因为在农民的田里并没有充分的工作使得马忙。那又是为什么呢?因为田地太小了。半匹马就够耕穷农民所有的那点土地[1](苏)伊林.五年计划故事[M].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P154)。
这是一段鼓吹集体化农业的文字,其核心观点是说集体农业可以推广机械生产,可以最大限度利用劳动工具。在规模较大的农场上犁地,自动化的农机相较于马更具有优势。这是农业专业化之后的结果,但对于小农而言,马多样化的用途,使他们不愿意轻易地放弃马耕。可以说,在技术史上并没有最好的技术,只有更合适的技术。当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时,原来的最优可能变成次优。
三、“戎马生涯”“放马南山”“却走马以粪”:从常用短语看马在汉民族中的主要用途
《老子》中有这样一句话“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这是对马在农耕社会中的主要功用转化的扼要说明。对于“却走马以粪”的解释,学界前辈有充分的讨论,在此就不赘言。无论何种解释,放马田中去粪地也好[2]曾雄生.“却走马以粪”解[J].中国农史,2003,(1).(P12),用马去运粪也罢[3]游修龄.释“却走马以粪”及其他[J].中国农史,2002,(1).(P103-106),都说明平和期间马的主要功用不在于军事。也就是说,相较于农用,马的军事用途在我国古代是第一位的。我国对于六畜的排列顺序:马、牛、羊、猪、狗、鸡,马之所以居于首位也是因为它的军事用途所决定的,从社会经济角度而言,牛应该居首[4]曾雄生.中西农业结构及其发展问题之比较[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3).(P54)。
在中华农业文明图景中,牛耕是必备元素之一。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强调:“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即强调牛于耕地的重要性。在战国牛耕推行前,土地主要是靠“耦耕”来翻地。学界对于“耦耕”还未形成统一的解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是一种人力的耕地方式。战国时期,耕地主要靠牛力,孔子弟子冉耕、司马耕皆以牛为字,就可为证。到了汉代,在北方关中地区出现“二牛抬杠”的耕地形式。再后来,随着犁具的改进,牛耕的效率越来越高。当然,农民除了用牛耕之外,也还是有用马耕地。据《盐铁论》卷三《未通》称,西汉时:“农夫以马耕载”,同书卷六《散不足》记:马“行则服轭,止则就犁”。只是养马的成本很高,不是普通农家可以支撑的,据《散不足》称当时养马一匹“当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故而中原农耕区少有马耕,其主要是在边缘地区,或者少数民族地区存在。《唐会要》卷一百记载,在突厥北部,距离长安一万四千里的地方,有个“驳马国”。此国拥兵三万,马万匹,地寒积雪,但冬天树木却不凋零,待春天冰雪消融后,当地人“以马耕种五榖,马色并驳,故以为国号”。显然这个国家以斑驳色彩的马来耕地,对于唐朝人来说,这仅是一种域外风情。清代盛京地区的旗人也用马耕,如《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记:“盛京侍郎朝铨奏奉,省所属藉马耕种,兼资旗人当差,嗣后如有偷窃马匹者,民人俱照盗牛及宰杀例治罪”。在此,作为农耕的马与牛的地位相当。当今,在西藏地区的加查县马的主要用途还是:“乘骑和运输,在部分缺牛耕的村用马耕地”[1]加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加查县志[M].藏学出版社,2010.(P314)。可见在藏区马耕也仅是牛耕的一种补充。明代文人徐渭把自己的不得志,说成“于文不幸若马耕”[2](明)徐渭.抄代集小序.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五)[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由此可见马耕在汉文化中的地位。
对于中华农业文明中不普遍使用马耕的原因,排除动物生理特点、技术因素,还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华农耕文明周边是被游牧民族包围着的,从殷商征伐鬼方,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再到秦始皇修筑长城,至汉匈奴战争,五胡乱华,唐代与突厥的战争,宋代与西夏、金、蒙古,明代与漠北蒙古,清代对西北的用兵,桩桩件件都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对抗。这种文明的冲突是地缘政治在扩张中的交织与对抗。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马多数时候充当的是“战车”角色。汉人用骑兵的技术天然不如游牧民族高超。蒙古铁骑能横扫欧亚大陆,靠的就是卓越的骑兵。马是骑兵的关键,没有好马,骑兵的威力会大打折扣。在不同兵役制度下,对马的管理方式也是不同的。马匹,尤其是好的马匹,在战时要被国家征用。不仅如此,历代对马的管理有一套制度,叫“马政”。由此也可体会到马的军事用途更被重视,正如牛的农业用途被重视一样。《商君书·去强》说:“强国知十三之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状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取食之数,利民之数,牛、马、初槀之数。欲强国不知强之三之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3](秦)商鞅.商君书[M].中华书局,2009.(P41)为了强国,政府需掌握确切的“牛、马之数”,这就是“农战”思想的体现。另外在中国农业的结构中,北方农业以旱地为主,南方以水稻田为主,稻田的土壤粘重,犁耕时更费力,而耐力更好的东亚黄牛、水牛能适应耕犁稻田的需要。
且不说马耕了,就连牛耕到后来在南方人口稠密的农业区也不普遍。取而代之的是“人耕”或用“铁塔翻耕”。明人赵统对“人耕”这种形式,表现出惊奇态度的同时,也分析了缘由,他说:“人耕,其法用三人一杠,杠中依于犁,一人柄后,一人掲前,又一人别绳牵牛辕,大抵穷而通牛之变。”[4](明)黄宗羲.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五)[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外还有如:土地零碎化,劳动力够多,养牛成本大,每家拥有耕地少,牧地被侵占、养牛的空间被压缩等。曾雄生先生从“放牛”到“縻牛”的视角,来解读了我国“跛足农业”形成的原因,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明清之后南方农作区人地关系更加紧张,养牛的空间再被压缩。宋代农学家陈旉曾提出在陂塘的埂上种树,用来绑牛的办法。到了明清时,江南地区养牛的农民更少,耕地则要靠铁塔进行。连对空间要求不高的牛的活动空间都不断缩小,就更没有足够的空间与成本来养马。
综上所述,对比中西农业文明下牛耕与马耕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其一,马耕并不是欧洲农业自古以来的特点,10世纪前牛耕才是他们翻地的主要形式。
其二,马耕与牛耕没有更好,只有更合适。工具、使用习惯以及社会文化象征意义都会限制先进技术的推广。
其三,牛耕是中华农业文明的特点之一,这主要是由地缘政治与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模式所形成。
(责编:高生记)
Cattle-plowing and Horse-plowing in Chinese and Wester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Chen Guiquan
陈桂权(1986—),四川平武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农史、秦巴地区社会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