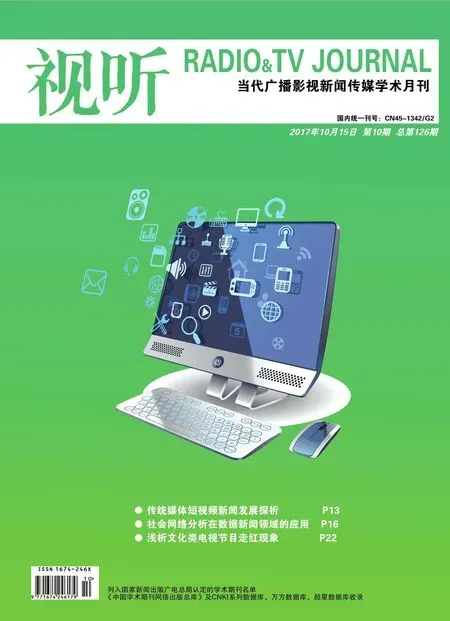新媒介时代下的娱乐至死
□周 倩
新媒介时代下的娱乐至死
□周 倩
媒介融合的拟像数字时代给了大众传播更多的机会。但它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以时迅信息的传播打破时间与空间,连接着多元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另一方面,它也降低了艺术作品中所谓的娱乐性成分的含量与质量。娱乐至死是波兹曼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在如今极速膨胀的娱乐化时代里,则更需要被大众理性思考,端正审美态度,以内容为王的生产标准缓解影视文化传播中艺术作品趋于娱乐化的高饱和现象。
娱乐至死;后现代主义;拟像仿真;娱乐化;把关人理论
根据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的观点来看,“娱乐至死”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娱乐本身,而在于人们日渐失去对社会事物进行严肃思考和理智判断的能力,还在于人们被轻佻的文化环境培养成既无知且无畏的理性文盲却不能够自知的社会群体。在媒介融合的后现代主义社会中,拟像仿真以及数字化的态势已然在影视艺术娱乐化发展的过程中成为推动娱乐至死现象的催化剂。就“娱乐至死”这一观点纵观当下新媒介时代的影像生态圈,观众似乎更容易沉迷在虚拟营造的娱乐幻象中,碎片化信息似乎更容易取代经典的传统规训,综艺节目主宰荧屏的影视风潮似乎更容易削减高雅艺术的渗透。显然,在新媒介大融合的当下,艺术与观众均缺乏对于娱乐本身的躬亲自省,缺少对于在新媒介融合时代下个体精神更容易出现失真失理状态的深度戒备。
一、新媒介时代下影视文化娱乐至死现象深化的原因
在《娱乐至死》的序言中,波兹曼比较了反乌托邦小说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以及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由二者比较可以大胆地将当前我们所处的媒介大融合的时代看作是赫胥黎式的文化逐渐成为滑稽戏的时代,而这里的滑稽戏具体是作为社会娱乐化的表象。随着媒介融合拟像数字化的传播方式的发展,公众话语以娱乐信息方式的出现,更发展成为一种趋向社会文化精神的产物。甚至生活中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在信息爆炸化的当下为了博人眼球也开始成为娱乐的附属。但值得思考与注意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如果文化生活都成为了娱乐消遣的载体,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需要通过娱乐化才能出声,那么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就难以避免被取代的命运。
众所周知,波兹曼提出娱乐至死的判断主要是针对以电视为中心的媒介环境,但其实质却是应用在各个传播领域之中,在媒介融合的拟像数字化的时代里娱乐化的现象就表现得更为鲜明。首先,媒介大融合意味着娱乐传播的多元化。显而易见,架构在网络载体上的媒介传播具有即时的参与性,受众在接受娱乐表现时不仅能够表达出个人的主观意见,甚至还可以成为娱乐信息源,娱乐信息的生产不被圈限与固化,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受众间的交流广泛传播。这也就意味着娱乐信息可以“爆炸式”地产生以及“病毒式”地传播。其次,娱乐信息输送通道的多元化下的新作业模式将传统媒介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与互联网、手机、手持智能终端等新型娱乐传播通道有效整合起来,资源的共享化、信息的集中处理化都使得娱乐化生产被加倍,内容浅薄的娱乐文化更容易被大众所接收。
二、新媒介时代影视文化娱乐至死现象的弊端影响
近年来,在媒介融合的态势下,文化娱乐性的表现愈加明显。首先,媒介娱乐破微化导致媒介娱乐的“草根”化。以当下影视作品的美学欣赏为例说明,影视作品创作的主导者从少数精英阶层向绝大多数“草根”人群转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转变降低了影视作品中的娱乐化成分的质量,根据把关人理论,这种转变也是造成影视格局变化的重要原因。由于媒介融合的出现,影视作品内容创造以及娱乐价值体现的门槛不断降低,渠道不断变宽,以至于出现了近几年更多新的产品形态,例如微电影。娱乐性在各类艺术生产中开始过度充斥,在受众间广泛传播,从而出现人们将过多的娱乐化作为体现艺术生产或个人审美的标志,为了在拟像时代展现作品,以至于愈发追求娱乐生产,当下影视市场作品品质也愈加低劣,最终体现的是肤浅的文化,内容低劣却极具话题的影视文化怪圈现象。其次,以电视剧为例的娱乐化形成病态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的传播。越来越多的电视剧作品过分追求市场份额,放弃理性审美,将粗浅的娱乐文化搬至荧幕,如屡遭诟病的娱乐化穿越系列作品,在消解历史的严肃性与深度性的同时,将观众带入到游戏化、恶搞化里,这样的娱乐表现手法,即便能够有“遁入梦中”的欣赏快感,但也是直接放弃了艺术对美的表达,放弃了对观众善意价值观的指导作用。除此之外,相对于以前红色革命剧大多庄重严肃,如今很多剧为引观众注意,将庄重情感娱化为轻松,将严肃进行调侃处理,离奇荒诞的剧情设计都是为了博彩的恶趣味娱乐化体现。由此可见,这类将影视文化倾附在不节制娱乐化中的艺术作品,会成为提升社会文化良性循环的阻碍因素。
三、“内容为王”缓解新媒介融合时代的娱乐至死
娱乐至死是波兹曼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在如今极速膨胀的娱乐化时代里,会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令我们忧心于社会的未来:一个日渐丧失严肃能力的群体,将如何去创造有建设性价值的未来文化?面对这些现象,我们应该具有基本的人文情怀和理性的审美素养。黑塞说过:“真正的修养艺术不追求任何具体的目的,一如所有为了自我完善而做出的努力,本身便有意义。”基于这一点,在这个已经泛娱乐化的时代,艺术生产以“内容为王”为标准降低大众文化中娱乐化的表现显得尤为重要。
艺术创作者以严谨的艺术态度创作,受众传播者以严肃的态度传播具有内涵的文化,摒弃粗鄙的娱乐化,不再是哗众取宠、强博视听关注的娱乐文化载体。在现代消费大市场环境下,应该有更多“大会系列”(《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及《朗读者》这样的节目,这类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要传播内容的节目类型,把传统文化中的冷知识成功转化成公众关注的热话题的艺术传播。以内容为王更是一种选择,在科技表现与实质内容间的一种选择。波兹曼说:“每一种技术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毋庸置疑,漫无目的的娱乐性解构了文化内容的实质,娱乐固然能够放松身心,但是心灵上的共鸣才是受众内心最主要的需求。以央视为代表的新兴文化类节目经历了引入期,正处在艺术生产的高速成长期,未来同样需要时刻把握受众需求的变化,以不媚俗、不哗众取宠的精致内容赢得受众的长期关注和情感共鸣,以好口碑和高收视持续延长其成熟期。这一现象也足够证明娱乐化的艺术生产最终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不可否认的是,艺术作品的生产需要有娱乐发展的价值,但绝对娱乐化的艺术生产则应该是被有所控制的。以艺术作品的内涵传播为例,现如今越来越多作品的生产已经远不是出于表达艺术寄托情怀,而是想要在媒介融合的浪潮里赢取噱头进而盈利。我们无法在数字时代按照把关人理论对美以及娱乐文化进行清晰且深刻的定义,但我们能够坚守的是发展喜闻乐见的优秀大众文化,以“内容为王”作为艺术创作的实质,抵制粗陋恶搞文化通过大众传播的方式进一步“病毒式”发展。娱乐至死不是娱乐致死,是提醒人们理性思考在多元化文化中思想与审美逐渐变肤浅的原因,再次引用波兹曼的话:“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30.
(作者单位:厦门理工学院数字创意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