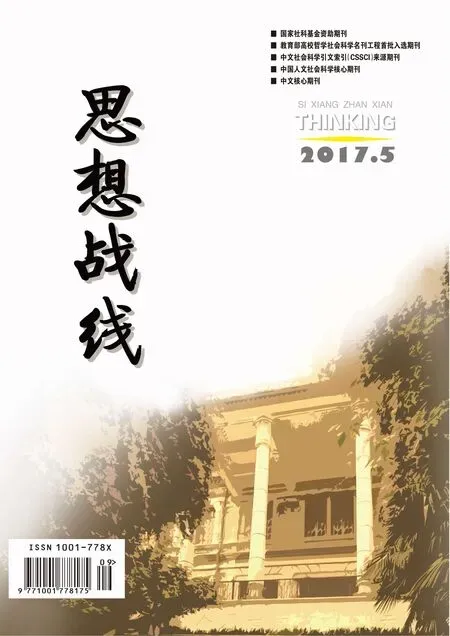清代、民国云南买卖契约中“第三方群体”研究
清代、民国云南买卖契约中“第三方群体”研究
杨志芳
以中人为代表的契约“第三方群体”,是中华法系契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代、民国云南财产买卖活动中的重要法律现象。其广泛存在于清代、民国云南买卖契约中,发挥居中说合、促成交易、见证立约、担保债务履行和解决纠纷等作用。这些功能的生成,与当时云南血缘与地缘结合的宗族共同体社会结构、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本土文化传统,以及习惯法主导契约法领域的法制传统密不可分。这一群体的作用机理对当代契约制度具有借鉴价值,今天我们在相关法律制度的设计中,应培育“第三方群体”的当代意义替代者,紧扣中国本土实际构建当代契约的“第三方群体”制度。
清代、民国;买卖契约;“第三方群体”;功能;机理
一、提出问题
清代、民国云南百姓买卖财产、订立契约时,除双方当事人外,还广泛存在一个由中人、代字人和介绍人等组成的“第三方群体”。这一群体参与契约关系,但不是财产出让方或受让方,而是独立于买卖双方之外的第三方,他们参与买卖和契约行为,受契约当事人倚重。而透过买卖契约,从契约关系内部,“第三方群体”在交易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可得到直接反映和体现。比如,有研究借助清代土地买卖契约,就“契约第三方参与人——中人”对于契约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中人参与契约的传统“影响了契约的形式、内容以及契约实现”。*陈胜强:《中人对清代土地绝卖契约的影响极其借鉴意义》,《法学评论》2010年第3期。又如,通过考察清代的田宅契约,有研究指出,中人等“第三方群体”在契约订立中发挥了以下三方面的功能:“保证交易能够公平进行,尤其是参与议定交易价格”;当“交易双方发生纠纷或者发生交易变更时,承担调解的责任和劝谕的功能”;“在交易纠纷诉讼当中承担证明责任”。*刘高勇,屈 奇:《论清代田宅契约订立中的第三方群体:功能及其意义》,《西部法学评论》2011年第3期。再如,有研究指出,中人对于中国古代契约法秩序的形成,具有“平衡契约双方当事人身份上存在的差异”“降低交易风险”“预防和解决契约纠纷的发生”等作用。*赵丽琴,王荣林:《中国古代契约法秩序探析——以土地契约为例》,《人民论坛》2014年第7期。
契约“第三方群体”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的产物,其功能发挥受社会结构、历史文化传统和法律制度传统的共同作用。正如有研究所认为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乡土社会,中人常常具有某种身份,要么是当事人的朋友、亲戚长辈,要么是村庄领袖或地方精英,给契约加进一些人格化因素使之更为牢固;*李 倩:《民国时期契约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页。而“中人普遍存在于契约中的现象,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在具体制度上的体现,展现了中国文化塑造的传统中国人在‘私法’行为上的旨趣与秩序”。*王帅一:《明清时代的“中人”与契约秩序》,《政法论坛》2016年第3期。
应当说,对“第三方群体”的研究,必须综合考虑契约行为发生时特定环境和影响因素。就此,本文将从契约关系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分析“第三方群体”在清代、民国云南民间财产买卖中出现并发挥作用的机理,并提炼“第三方群体”作用机理对当代契约法律制度的启示。
二、清代、民国云南买卖契约记录的“第三方群体”类型
清代、民国云南买卖契约中的“第三方群体”主要包括中人、代字人、介绍人、过付人和保人,他们参与财产买卖、契约订立过程,发挥着见证契约订立、担保契约履行和定纷止争的作用。从清代到民国,虽然国家政权性质和社会形态都发生了变化,但仅就云南民间买卖契约中所呈现的“第三方群体”之作用而言,两个时期之间并无本质差别。
(一)中人及其作用
据契约记载,清代、民国参与云南民间财产买卖交易的中人有两类:一类是与卖主有一定关系的中人,本文称其为“关系中人”;另一类是具有某种权威身份的中人,本文称其为“权威身份中人”。“关系中人”按其与卖主间的不同关系分为:无特殊关系的“普通中人”、*所谓没有特殊关系是相对的,通观清代、民国云南买卖契约,不难发现,通常情况下中人与卖主之间至少相互认识,并且绝大多数中人虽与卖主不是近邻但至少居住在一个地方,如同村、同甲。有亲属关系的“亲属中人”、有邻里关系的“近邻中人”。“权威身份中人”按其身份权威性质*所谓身份权威性质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身份的来源途径,二是身份权威产生的依据。据此可以把身份权威性质分为:身份来源于官方,如官方任命,身份权威产生依据是官方授权,是官方权威性质的身份;身份来自于民间,如选举,身份权威产生依据是民间共同体成员普遍认同,是民间权威性质的身份。不同分为:“官方权威身份中人”和“民间权威身份中人”。云南买卖契约中,清代以“关系中人”为主,民国除“关系中人”外,大量出现“权威身份中人”,尤以“官方权威身份中人”居多。往往一份契约会同时存在多种类型中人,其中,清代常常是多种关系中人同时存在,民国则是关系中人和权威中人同时存在,还常有两种权威身份中人并存的情况。
关于中人在财产买卖中发挥的具体作用,下面以一件云南宜良的“杜卖水田文约”*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宜良契约文书“社土292”号,载吴晓亮等《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第2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86页。为了方便阅读,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契约原文进行了断句。为例进行说明:
立杜卖水田文约人汤镇,系娄桃营住人,为因缺银正用,情愿请凭中人言明,将自己祖遗水田壹坵,亩积肆分,第叁拾捌号,坐落勒巴埂,东至汤姓田,南至本村公田,西至荒滩,北至汤姓田,四至开明,今当中人立约杜卖与桃花村于受卿员下,实接受杜价洋国币伍佰元正入手应用,当时契银两相交明,中间并无利债转折逼迫等情。自杜之后认由银主照契管业赴官投税颁请契尾,汤姓亲族人等不得异言争论,若有异言争论俱系汤镇一力承担,恐口无凭特立此杜契存照为据。
民国三十年壹月拾伍日 立杜卖水田文约人:汤镇(汤镇之印)
凭中人:张心田
骆锐
杨德清(杨德清印)
代字:陈宏(花押)
杜契为据
从这件契约正文可知,中人在这宗田土买卖中发挥的作用有:第一,帮卖主把缺钱要卖地的想法和所卖土地面积、坐落等信息对外发布出去,寻找、介绍买主;第二,向买主担保自己发布的土地信息真实可靠;*有契约明确记载了中人具有保证买卖标的四至坐落、产权归属等情况真实性的作用,例如:民国文山地区一件杜契中就记录了“四至经凭中证足踏手指分明,界内并未包卖别人寸土,亦未存留立锥之地”。云南省博物馆馆藏文山契约文书“社土217”号,载吴晓亮等《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5页。第三,通过见证契约订立和标的银钱的实际交付,证明买卖关系是自愿、公平、真实的。最后,中人在契约末尾签名画押,证明契约文书记载内容的真实性。
(二)代字人及其作用
代字人指代立约人书写契约之人,在云南契约中被称为“代字人”或“代笔人”。清代、民国云南民间财产买卖对代字人身份没有特别要求,既可以是立约人认识的熟人,也可以是立约人并不熟识的职业代字人。契约记录的两类信息呈现了清代、民国云南存在职业代字人群体。首先,民国昆明和宜良地区有同一地方(同村或同镇)多份契约代字人是同一人的情况,并且时间跨度较长,例如:昆明灵源乡(海源乡)龙院村有12件买卖契约代字人都是“杨述文”,时间跨度6年;宜良有34件买卖契约代字人都是“郭思(斯)香”,时间跨度8年。数量和时间跨度说明,当时昆明和宜良地区存在职业“代字人”群体。其次,清代、民国都有契约明确记载“代字钱一元伍角”*云南省博物馆馆藏保山契约文书“社土624-15”号,载吴晓亮等《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74~375页。笔者仔细辨认契约原件后认为,原件中的“代字钱一元伍角”被误录成了“化字钱一元伍角”。“代字周君用,奉过银五分”,*这件契约形成于清道光年间的丽江地区,收录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一),附录二:纳西族史料汇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88页。说明有代字人代书是有偿的,他们与因人情无偿代书的代字人不同,前者以代书为业,后者代书只是偶尔为之并不以此为业。
清代、民国云南契约记录的代字人作用比较简单,只是代人书写契约。有些契约是立约人“亲笔”书立,有些契约却是代字人依立约人口述记录而成,故通常情况下人们订立买卖契约需要代字人是因为,立约人不识字或不会写字,而代字人则是那些受过教育、识字会写字的人。*代字人应该受过教育,可以从有买卖契约注明代字人是“生”,即“生员”得到证明,见云南省博物馆馆藏保山契约文书“社土624-23”号,载吴晓亮等《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80页。此外,代字人也要在契约落款处签名画押,说明代字人与中人有一些相同的作用。例如证明契约内容真实、见证交易过程等,所以会出现同一宗交易的中人也是代字人的情况,被称为“凭中代字”。
(三)介绍人及其作用
介绍人在清代、民国云南买卖契约中不像中人和代字人那么普遍存在,只是集中出现在民国时期昆明和宜良地区的买卖契约中,可见当时介绍人在云南民间百姓买卖财产活动中并非必需,只在特殊情况下或因特殊原因才会参与财产买卖。
从契约记录的交易细节看,多数介绍人参与的财产买卖都有一个特点:买主、卖主与财产间存在某种“分离”。有时“分离”表现为买主与卖主、财产两者不在同一地域,有时表现为卖主与买主、财产两者不在同一地域,有时则表现为买主、卖主、财产三者都不在同一地域。买主、卖主和财产间存在“分离”,财产买卖就需要介绍人,需要他们在买卖中牵线搭桥、介绍说合,发挥中介桥梁作用,帮助交易双方克服彼此因“分离”导致的陌生与不信任,进而可以聚在一起放心地买卖财产。此外,据云南民国买卖契约记载,介绍人还有见证契约订立的作用。即使契约正文没有记录介绍人具体作用,但他们都在契约末尾签名画押,明确自己交易参与者身份同时,还表明其认可文书记载内容,证明契约内容真实性可靠。
(四)保人及其作用
在清代、民国云南田宅契约中几乎见不到“保人”,可见保人不是田宅买卖必需的“第三方群体”。有一件形成于民国路南地区买卖秋谷的契约,*云南省博物馆馆藏路南契约文书“社土600”号,载吴晓亮等《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37页。记载有保人,买卖双方约定的交易方式是卖方先收钱、秋收后再交货,对卖方到期不“如数清偿”或“欠少”秋粮的违约行为,买方可向保人“是问”,保人对卖方如约交货的契约义务负有担保责任。这件契约记录的交易方式与田宅买卖交易方式不同,清代、民国云南民间田宅买卖基本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方式,即“当即银田两相交明”,契约债务能够即时履行完毕,没有保人存在的必要性。可见,保人只在契约债务不是即时履行的财产交易中有存在的必要性。
而除上述类型的“第三方群体”外,民国新平和文山地区有买卖契约记载了“过付人”这一“第三方群体”。契约对“过付人”在买卖中的具体作用没有记载,但从名称字面含义看,其在财产买卖中负责居中经手交付钱款或财物。过付人也都在契约末尾签名画押,表示他们作为买卖参与者认可文书记载内容,并证明契约真实可靠。
综上,清代、民国云南买卖契约中的“第三方群体”因参与交易的原因、环节、程度、交易标的及方式不同,各自实际发挥的作用存在一定差异。但从总体上讲,“第三方群体”在帮助买卖双方顺利形成交易合意订立契约、顺利完成交易并实现交易目的、防止或减少纠纷,以及帮助解决纠纷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即便纠纷发生,鉴于“第三方群体”见证了契约订立,可以证明契约内容真实性,他们还可以作为调解人甚至证人,促成纠纷各方排除争议达成和解。当然,如果纠纷到了诉讼阶段,他们参与诉讼对于纠纷得到公正解决也是有积极作用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日常生活频繁的契约缔结行为中,当事者双方的相互合意及合同的成立,多多少少总要依靠第三者的居中‘说合’已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构。如果万一在利益分配上出现争执,最早出面进行调解的人也往往是中人。或者不如说,正是考虑到或预期到万一出现争执的情况才事先请求中人参加契约缔结过程的。”*[日]寺田浩明:《明清时期法秩序所“约”的性质》,载[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等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76页。
三、清代、民国云南买卖契约中“第三方群体”的作用机理
从契约关系内部考察“第三方群体”,其在清代、民国云南民间财产买卖契约订立和履行发挥什么作用已基本明晰。然而,如果说“契约的根源是社会”*[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的话,研究“第三方群体”为何能影响买卖契约的订立与履行,则不能只局限在文书记载的契约关系内部,须将买卖行为、买卖契约和“第三方群体”置于清代、民国云南这一具体社会背景中,结合当时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法制传统等因素,才能更有效地阐明“第三方群体”发挥作用的机理。
(一)“第三方群体”强化着宗族共同体社会的契约行为
清朝全面控制云南后,开展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通过积极推行改土归流加强了中央集权,为云南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政治保证。封建地主经济长足发展,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成为云南主导的经济生产方式。而辛亥革命期间爆发“重九起义”,推翻了清朝统治,云南进入民国时期,但并不意味着云南历史和社会进入全新时期。先后主政云南的蔡锷、卢汉等人,对云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改造经营。较清代而言,民国时云南社会血缘与地缘结合的紧密度开始松动。但事实上,传统小农经济生产模式依旧主宰着云南社会经济。小农经济生产模式长期占据主导,云南社会无法彻底冲破传统社会中由血缘与地缘交织结成的网罗,宗族共同体依旧是最主要的社会组织。
而宗族共同体作为一种结构性社会组织,其成员因自身在血缘、经济和政治关系中的地位拥有一定等级身份。*朱 勇:《清代宗族法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9页。人们在宗族共同体中的等级身份,会被带入财产交易,对契约关系产生影响,使契约行为“人格化”。*李 倩:《民国时期契约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2页。交易双方不只从交易本身或一次交易中计算得失,契约关系成为一种多面且长期的互惠关系。这种互惠关系在陌生人之间很难形成和维系,却是宗族成员间常态化关系。宗族成员彼此间在血缘、地缘上千丝万缕的联系,拉扯着他们必须逐渐形成良性互惠关系。成员作为个体一旦破坏互惠,会受到惩罚,严重至被共同体抛弃,且无法立足社会。血缘和地缘关系往往无法选择和逃避,它既无法轻易加入,也无法轻易摆脱。*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71~77页。清代、民国时期云南的传统宗族共同体社会特征,让人们习惯和“自己人”交往,但又不得不与“外人”买卖财产,由此,“第三方群体”参与经济交往,充当人际关系“协调器”,强化契约行为的“人格化”力量。
如果买卖双方相互熟悉信任,欲图结成买卖契约关系时,低强度的外在强制力即可,“关系中人”类的“第三方群体”提供的人格化力量强度已经足够。如果人们要和自己并不熟悉的外村人交易,在一个“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他们很容易找到一个双方都认识的人充当“中人”或“介绍人”,使契约关系间接“人格化”。*赵晓力:《中国近代农村土地交易中的契约、习惯与国家法》,《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1998年,第445页。一方面,“中人”“介绍人”等“第三方群体”能帮助彼此陌生的交易双方变成“熟人”,形成契约产生需要的基本人格化力量;另一方面,那些品德高尚、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第三方群体”,可以为陌生人达成契约关系提供高强度人格化力量。正因如此,在血缘和地缘结合紧密的清代,云南地区买卖契约中人多为“关系中人”,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开始松动的民国,云南地区买卖契约中人大量出现“权威身份中人”;此外,民国的买卖契约有介绍人,而清代的买卖契约却没有介绍人。
(二)“第三方群体”可化解逐利需求与传统道德执念间的矛盾
儒家文化与封建地主经济相伴相生,清代、民国时封建地主经济在云南的发展和繁荣,为儒家文化在云南发展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科举观念深入人心,尊崇孔子之道,儒学教育普及,各州县设置书院,取士入学。私人著述层出不穷,涌现大批经学、史学、文学方面能与全国学界进行交流对话的学者。尤其乾嘉以来,云南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文运大兴,汉宋之辨,今文古文之议,盛极一时,滇之僻壤,皆无与焉”。*夏光南:《云南文化史》,辑于《民国丛书》第5编39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第140页。可见,清代和民国,儒家文化已占据云南本土文化传统核心地位。
传统儒家文化倡导以“礼”调整社会关系,强调道德,忽视权利。美国学者史华兹在《中国的法律观》中认为:“儒家礼的概念与我们对‘个人权利’的态度截然不同。我们把维护个人利益奉为美德,为权利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而他们轻视个人利益,解决权利纠纷的总倾向是让而不是争。这是礼的一些主要特征。”*[美]史华兹:《中国的法律观》,张中秋《中国法律形象的一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5页.“礼”倡导“重义轻利”“和为贵”“礼让”等“君子之道”,这些君子之道如果真能被人们普遍遵循,国家社会无疑会长治久安。但人类道德发展史反映的规律是,“从以品德、德性为特征的协调着近距离人际关系的内在规范,向以规则、原则为特征的调节陌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外在规范的发展”。*甘绍平:《道德:在规则与德性之间》,《思想战线》2015年第1期。而且财产买卖行为终究是逐利行为,争取利益最大化是交易双方的根本目的。逐利过程中,人们尊崇信奉的道德准则必然面临自我私欲的严峻挑战。礼教社会无论是国家还是百姓,都不会轻易背弃固守的道德规范。而“第三方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可化解人们的逐利需求与传统道德执念间的矛盾。
首先,“第三方群体”参与财产买卖,可促成买卖双方的“熟人关系”,使彼此居于具体人际关系网络内,诚信、守礼等道德规范被具体化,不再抽象空洞。在宗族共同体社会,于个人而言,被“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亲朋友邻道德鄙视的威慑力强于被官方惩处的威慑力。在具体人际关系网中,个人名誉决定其在关系网中的地位,有非礼之举的人会因受到关系网中其他人的不齿甚至排斥而“痛不欲生”。买卖双方彼此不熟悉,经中人、介绍人撮合介绍,可以在相互间形成一种“人为的”熟人关系,提升道德规范对彼此的威慑力,推动契约关系良性发展。其次,“第三方群体”中的社会精英和德高望重者,是熟人圈子里的道德“权威”,人们无论是和熟人还是和陌生人买卖财产,有这些“权威”居中说合、见证、担保,就意味着交易一定安全可靠。人们产生买卖财产念头,首先想到的不是寻找买主(卖主),而是寻找可靠的“第三方群体”。“立契有中”的观念深入人心,不仅像孔府这类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秉持,在其订立的契约中留下“本府凭中说合”“同中人……卖于圣府永远为业”字样,*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1~142页。而且地处边疆蛮荒之地、直到民国仍受治于土司甚至还处于原始公社中的少数民族们也都遵循,习惯将中人等第三方引入各类财产交易。例如红河的哈尼族、*云南省博物馆馆藏红河契约文书中普遍存在中人、代字等“第三方群体”。西盟的佤族、*西盟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直到1949年前,还停留在农村公社阶段。佤族在进行土地买卖时,一般要立口头上的契约,并且有“打牙”居间参与。“打牙”应该就属于“第三方群体”中的一种。参见方慧《云南法制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55页。滇川藏毗邻地带的纳西族。*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所编的《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一),附录二:《纳西族史料汇编》中收录了几件民国时期丽江地区纳西族的买卖契约,这些契约当中也有凭中等“第三方群体”。最后,传统中国百姓“面子”观极强,羞于承认和面对面直接表达自己对利益的诉求。即便买卖双方互相认识,清楚财产交易相关信息,也很少会直接向对方表达自己的诉求。再加上买卖双方在交易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利益冲突,如买方想物美价廉,卖方则想价钱越高越好,爱“面子”的习惯却让人们不擅长自己处理这些矛盾,双方越是熟悉,就越不愿冒“撕破脸”当面讨价还价的风险。这些心理因素会一定程度阻却交易形成,这时就需要第三方居中牵线搭桥、传达诉求,为双方利益诉求进行斡旋,调和各种利益冲突,寻找让双方均满意的利益平衡点促成交易。
(三)“第三方群体”弥补了国家权威缺位所致的契约约束力不足
无论清代还是民国,在“官由政法,民从私约”传统法制思想指导下,国家层面法律制度在最大程度保证税收利益前提下,并没对民间契约行为做更深入细致的规范调整。国家和政府在云南契约法律制度中充分让步,习惯法成为调整规范民间契约活动的主体制度。在清代,中央王朝对云南法制建设的原则是有限制的因俗而治和积极移植汉律。有限制的因俗而治,让少数民族以固有习惯法处理内部事务、维护内部秩序。积极移植汉律时,把少数民族进行分类,不同类别使用不同汉律。*《皇朝政典政纂》卷374《刑名·名例律·化外有犯·事例》。但只把重案尤其是命盗案件的准据法规定为汉律,民法等私法领域并没强调汉律移植,而是最大程度接纳和承认云南少数民族固有习惯法。到了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积极进行法制改革,移植西方法律思想和制度。然战乱频繁、政局动荡,新的法律制度尤其是民事法律制度因缺乏国家强制力保障,最终并没能真正产生普遍实效,在云南民间真正发挥作用的契约法律制度,依旧是习惯法。*当然,并不是所有民国时期的国家法律制度都没真正在云南被贯彻和落实,如刑事法律制度和行政法律制度,由于与统治阶级地位稳固与否息息相关,当权者是着重落实的,云南无法在这些领域成为法外之地。但在民事法律等私法领域,国家推行力度不大,再加上国家民事法律制度本身也允许习惯法存在发展,导致一些国家民事法律制度因为与云南社会实际不相契合,并没有被严格遵守。
在这样的条件下,契约的遵守,需要依靠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强制力约束。外部强制力主要来自官方对契约行为的干预调整,而内部强制力则来自于人们对契约内容和习惯的认同、自觉遵守。国家权威在云南契约法律制度中缺位,民间契约关系缺少国家层面制度的调控,再加上民间契约文本难免简略不周全,契约风险发生几率必然增加。因此,对于有效防控契约风险而言,来自内部的强制力就显得至关重要。契约“第三方群体”作为一种被人们广泛接受遵守的契约制度,能有效稳固契约关系。清代、民国云南买卖契约“第三方群体”要么与买卖双方有某种特殊关系,要么具有一定身份、地位或影响力,可以用多种手段,确保契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督促契约的履行和实现,能强化契约行为“人格化”力量,以降低契约风险,弥补国家法缺位造成的契约约束力不足之缺陷。
此外,国家权威在契约纠纷解决中同样缺位,有纠纷的契约关系更多依赖民间习惯法的调解实践来调和。契约“第三方群体”是民间调解中的重要功能角色,能促成契约纠纷顺利解决,保障契约约束力的实现。清代、民国时期,云南民间秉承“政权不下县”的社会治理理念,民事纠纷因是“细故”不被官府重视,更多依靠民间调解解决,“民之有讼,往往处于不得已而告官,官之听讼,往往是不得已而后准,皆非乐于有事”。*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页。云南许多少数民族习惯传统都不看重和依赖官方纠纷解决机制,譬如诉讼,当人们发生纠纷,首先选择由民间权威进行调解。而“第三方群体”充分了解缔约履约过程,具备纠纷调解人资格,其在契约当事人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身份地位,使其公正性和权威性很容易获得纠纷双方认同。
四、结 语
“第三方群体”广泛参与买卖契约,是清代、民国云南地区乃至整个传统中国社会普遍保有的契约习惯之一,其不但在契约订立、履行和纠纷解决中发挥积极作用,且成为了人们心目中一种具有保障契约实施功能的符号。“第三方群体”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依存于特定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法律制度。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虽然发生了根本改变,但文化传统、观念意识、法律制度却与传统中国一脉相承,留存有许多同质性要素。因此,在构建当代中国契约法律制度的过程中,需要着力打造这一“第三方群体”的当代替代者,例如经纪人、中介机构、保险公司、公证机构和民间仲裁机构等。而在构建和完善当代意义上的契约“第三方群体”工作机制时,则需紧扣中国本土社会实际状况,建立民间权威主体培育机制、树立和强化国民诚实守信的道德理念,在确保国家法制统一的同时,给契约领域的民间习惯法留足自我发展空间。只有这样,中国契约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过程才能够避免与传统法制实践的割裂,更为有效地回应来自社会的法律制度需求。
(责任编辑 甘霆浩)
A Study of“Third Party Group”in Contracts of Sale in Yunnan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YANG Zhifang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tract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third party group”represented by middlemen was an important legal phenomenon in the property trading activi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Yunnan. Widespread in sales contracts during those two periods, the third party group in Yunnan acted as go-betweens, helped conclude transactions, witnessed covenants, guaranteed obligation and settled disputes. Those functions of the third party group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en social structure of Yunnan’s clan communities bound by blood and geography, the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 with Confucianism at its core and the legal system in which customary law dominated the the field of contract law. The mechanism of this third party group has referential value for contemporary contract system. In designing related legal system, we should cultivate the contemporary counterparts of the third party group and build a contemporary “third party” system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China.
Qing Dynasty &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ntract of sale, third party group,function, mechanism
杨志芳,云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警官学院法学院讲师(云南 昆明,650091)。
D929
:A
:1001-778X(2017)05-01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