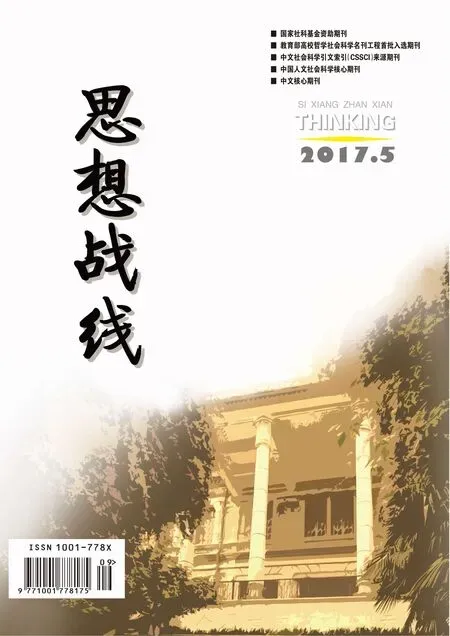论明代前期白银的“双轨”流通及其内涵
论明代前期白银的“双轨”流通及其内涵
邱永志
学界并不熟知明代前期白银的流通状况,实际上可将其归纳为一种因政策阻隔的“双轨”流通状态:在制度层面的“公领域”,政府在极力维持并重申“禁银”政策的同时,在宝钞兑换、赋役课税等诸多领域单向折收白银,赏赐、采办等也不乏行用白银。在民间社会的“私领域”,白银在不少经济发达之地,首先呈现为一种基准计价手段,其后随着宝钞的急速贬值、实物型经济体制的推进等,又与黄金、布帛、米麦等构成了多种通货并存的混杂流通状态,屡禁难止。综合言之,明代前期白银的“双轨”性流通虽显得广泛,但内涵却极为有限:在“公领域”,它仅是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下诸多折色物中的一种,与布帛、丝绢、米麦、黄金等实物区别不大;在私领域,它也仅是多元通货中的一种,属于并非先进的民间实物货币范畴。无论是对于财政体制还是民间经济而言,白银的流通状况折射出明前期浓厚的实物主义特征。
明代前期;禁银政策;白银;双轨;内涵
一、问题的引出
货币白银化问题,是明代货币经济史的基本问题。一直以来,论及明代的货币白银化(抑或白银货币化)问题,不少人认为这是明中后叶才出现的现象。这种观点,其实忽略了白银在明前期*本文所论的明前期主要是指洪武八年至宣德年间(1375~1435年)政府执行“银禁”时期。即存在一定的流通情形。而且,其流通状况、特点、内涵具有不少值得分析的地方。学界之前大体从两个维度对此展开了相关的研究:
其一,从公、私领域整体角度注意到了白银的流通情形。董郁奎对此进行了简单梳理,并认为,政府在出台“禁银”政策同时,却又允许赋税折纳用银、钞法告赏用银,体现了制度规定的内在矛盾,很容易使规定沦为具文。*参见董郁奎《试论明代的白银及其流通》,《浙江学刊》1988年第3期。陈志鹏称这个时期白银存在广泛流通的情形,堪称是“虚拟银本位时期”。*参见陈志鹏《论明代前期的“虚拟银本位”》,《科技信息》2008年第8期。陈氏的判断存在不少问题,忽略了在明初货币经济极度萎缩环境下,当时社会实际应是一个实物本位居主流的多元本位混杂时期。*万志英、邱永志等认为,明前期是多种通货并存时期,财政领域以实物为主,兼收金银、布帛、丝绢、钱钞等,民间社会更是多元货币通行、实物交易充斥,堪称多元本位混杂时期。参见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3章。黄阿明最近也强调,白银在明前期的公、私领域存在不断流通之情形,并认为明代货币白银化的进程首先源自白银自上而下的缓慢开展,尔后才与自下而上的货币白银化趋势汇合。*参见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96~98页。
其二,从民间货币流通实际论及白银的流通情形。傅衣凌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徽州土地契约观察到,白银在明初“禁银”时期实际还在流通。*参见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见《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而后,李若愚、万明等通过对契约资料的进一步挖掘,大致呈现了徽州、福建土地契约交易通货使用状况。*参见李若愚《从明代的契约看明代的币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万 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福建地区契约中货币使用状况,参见福建省钱币学会编著《福建货币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6页;杨国桢等编《闽南契约文书综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增刊;陈支平《明清福建货币地租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他们的研究表明,在明前期地方社会的大额交易事例中存在多种通货并存的局面,白银只是其中的一种。这个状况,在《实录》《明会典》等资料中也有不少记载(详见后文)。
可见,关于明前期白银流通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揭示,但仍存有三点可推进之处:一是白银在赋役财政领域的折纳、流通情形仍欠缺较为翔实的梳理;二是对于白银流通的“双轨性”特点及内涵认识不足,故会断定“禁银”政策规定存在矛盾或明前期存在“虚拟银本位”,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三是对于民间白银流通特点需要放入明初社会经济的大环境下进一步认清,尤其要注意白银在某些地区多执行计价尺度而非交易媒介功能,以及明初实物主义色彩浓厚的特点。鉴于此,本文欲在这些方面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如有不妥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二、禁金银政策及其松弛过程
众所周知,白银在明代经历了一个由非法走向合法的漫长演变过程。但在明初,白银却存在一个由合法转为非法的急速变化过程。史载,朱元璋集团曾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铸造过“银钱”,*俞 本:《明兴野记》,见陈学霖:《史林漫识》附录3,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第412页。此事真伪尚难证明,但在明朝建国前后,白银属于合法流通货币,应是确凿无疑的事情。*参见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95~96页。到了洪武八年(1373年),情况发生改变,朱元璋因铜料缺乏、铸钱无利等因素开始发行宝钞,并同时出台禁止民间金银用于交易的配套措施: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若有以金银易钞者听。*《明太祖实录》卷98,洪武八年三月辛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669~1670页。下引所有实录皆为此版本,不再标注。
很显然,朱元璋是想消除民间诸种通货并存的混杂局面,使货币统一到钱、钞之上,金银只能单向兑换宝钞。国家还以告密补赏的方式来保证禁金银政策的成功。在明初重典治国、商业水平极为低下及大量抑制市场的社会经济制度背景下,禁金银政策似乎能取得不错的成效。
朱元璋为何要出台禁金银政策呢?一般认为,这是为了维护国家钞法运转的需要而立。朱元璋深知,倘若允许民间贵金属自由流通,民众必然会重金属货币而轻无价值的符号货币——宝钞,只有禁止其流通,才能维护国家钞法的顺畅运行。同样因为这个原因,他还于洪武二十七(1394年)年出台严厉的禁钱政策。实际上,朱元璋的禁银政策还有另外两个原因(或目的),而这需要结合明初政权的特性来理解:其一,禁金银政策包含了朱元璋弹压江南地区富商豪强、统制地域经济的目的;其二,该政策体现了朱元璋重本去奢的实物主义逻辑理念。
针对第一点,檀上宽有深入细致的考察。他考察了明初专制国家构建的过程,将宝钞政策与江南重赋、政治大案、迁都计划、科举分卷(南、北)等统摄起来观察,认为明初实行的宝钞政策,是朱元璋为了打破“南人型”政权的封闭特性、欲建立全国型政权的重要经济措施。“国家主导型”宝钞政策的出台,以及严禁“民间主导型”金银的流通,正是为了压制江南“银货”经济、统制地域经济、打击江南豪民富商阶层。*参见檀上宽《明王朝初期的通货政策》,《东洋史研究》1980年第39卷第3期。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重申禁金银令,目标直指杭州地区商人一切以银定价的行为。*《明太祖实录》卷251,洪武三年三月甲子,第3632页。早在之前的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八月,朱元璋宣布禁止铜钱用于民间交易,理由也是两浙、两广、福建等地居民重钱轻钞、“民心刁诈”。*《明太祖实录》卷234,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第3417页。由此可见,朱元璋的货币政策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
关于第二点,史料有不少的相关记载。首先朱元璋不喜爱金银,为此他多次拒绝和排斥民间进献金银的行为。*洪武十五年(1382年),有南京居民挖得地下黄金献给朝廷,朱元璋说:“民得金,而朕有之,甚无谓也,命归之民”。《明太祖实录》卷146,洪武十五年七月丙子,第2295页。而且,他还斥责底下建议开采金银矿的作法,力推封矿罢冶政策。*《明太祖实录》卷27,洪武元年三月甲申,第538页;《明太祖实录》卷180,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第 2724~2725页。可见,朱元璋的禁金银政策与蒙元统治者为了大肆搜刮金银也曾颁行“禁金银”政策不同。朱元璋颁行的禁金银政策多是其重本去奢、重视实物主义的思想体现。明人茅元仪曾深有体察:
洪武间,户部请开中,陕西盐粟不足,则以金银、布帛、马驴、牛羊之类验值准之。今每苦边无粟,又谓开屯患虏,不知边人所需正不止粟如布帛等,每以商人不至,其值甚高。故虽领折色多,而不足以办。使通其法,何物不可中盐?但金银则当禁耳,以金银者准货物之等,子非货物也。太祖深识此意,禁民金银交易,不惟为行钱法,亦深察其本也。*茅元仪:《暇老斋杂记》卷8,见《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2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19页。
茅氏盛赞太祖禁金银的举措是为了保持国家本色富足,而非仅是出于货币制度上的考虑。《明史·食货志》编者也有类似的认识:
明初沿元之旧,钱法不通而用钞,又禁民间以银交易,宜若不便于民。而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昧者多言复通钞法可以富国,不知国初之充裕在勤农桑,而不在行钞法也。*《明史》卷77《食货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77页。
作者称赞明初诸帝王承继太祖劝课农桑、重本轻末之一贯政策,成效显著,并认为疏通钞法不如农桑种植,体现了明前期强烈的实物经济逻辑出发点。
成祖篡位之后,悉数恢复洪武旧制。他深谙太祖“禁金银”的内涵,故于永乐四年(1406年)四月颁布了更为严厉的金银禁令:“以钞法不通,下令禁金银交易,犯者准奸恶论。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银充赏。其两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赏与首捕同。若置造首饰器皿,不在禁例。”*《明成祖实录》卷19,永乐元年四月丙寅,第346页。
此次禁金银令一改太祖时期只治其罪、告发给赏的立场,直接以奸恶死罪论处,但补充规定了民间金银用作饰器不做惩罚。第二年正月,成祖便感此项禁令似乎过于严苛,故改为“诏自今有犯交易银两之禁者,免死,徒家兴州屯戍”。*《明成祖实录》卷27,永乐二年正月戊午,第497页。三月,刑部尚书报告有百姓犯禁:原来湖北江夏县有民众因父亲逝世,用银购买葬具,导致犯禁,理应流放边关,最终成祖以法律不外乎人情的缘由赦免了这位孝子。*《明成祖实录》卷29,永乐二年三月庚戌,第517~518页。可见,禁金银令在明初法令严酷的环境下绝非虚文。同月,有安抚四川地区的御史给事中丁琰,见当地无奸民犯法,于是暗中派遣亲信诱惑百姓用银交易,遭到严惩。*《明成祖实录》卷29,永乐二年三月庚申,第519页。五月,琉球国王朝贡使团“赍白金诣处州市磁器,法当逮问”。永乐帝以怀柔远人的态度赦免他们。*《明成祖实录》卷31,永乐二年五月甲辰,第556页。足见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维持禁银政策不遗余力。永乐十七年(1419年),朝廷再度“申严交易金银之禁”。*《明成祖实录》卷211,永乐十七年夏四月壬寅,第2134页。虽证明金银存在一定的流通,但永乐时期应是该政策执行较为严格的时期。
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仁宗发现“钞法不通,民间交易率用金银、布帛”,于是召集群臣商议,结果是“以金银、布帛交易者,亦暂行禁止”。*《明仁宗实录》卷6下,洪熙元年正月庚寅,第219页。可见,仁宗上台之后,禁金银的政策力度减轻了不少,似乎留有放开金银禁的余地。可惜仁宗很快暴亡。宣宗即位后,针对民间多用金银、钞法不通的情形,勒令“行在都察院,揭榜禁之。凡以金银交易及藏匿货物,高抬价值者,皆罚钞”。*《明宣宗实录》卷19,宣德元年七月癸巳,第493页。禁金银政策的执行从刑徒之罪到罚钞惩治,可以说力度进一步减弱。政府开始改变思维,一是希望维持继续禁银政策,二者希望通过罚钞举措来疏通钞法。罚钞的标准见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的上奏:“近江西鄱阳县民董复安建言,钞法阻滞,请禁使银,不拘旧例。凡交易银一钱者,买者、卖者皆罚钞一千贯,一两者罚钞一万贯,仍各追免罪钞一万贯。”*《明宣宗实录》卷48,宣德三年十一月乙丑,第1170~1171页。
按当时官价:钞1贯折银1分,1千贯折银约10两;民间交易银1钱须罚10两,是成本的100倍,可见惩处力度也不低。
宣德中后期是禁金银政策出现松弛的时期,民间使用金银的频率越来越高。宣德四年(1429年)六月,户部上奏:“比年巨商富民并权贵之家,凡有交易,俱要金银,以致钞不通 行。……及支盐发卖,专要金银,钞愈不行。”结果,宣宗因此次奏报的金银交易罪不明显而没有追究。反映了使用金银的主体大多为豪民、商人、权贵阶层。*《明宣宗实录》卷55,宣德四年六月庚子,第1322页。宣德八年(1433年)闰八月,三法司上报山东一“辱母案”:山东历城县有男子因愤恨邻居辱骂其母,不慎用头一下将邻居撞死,按律当判绞刑。宣宗听完后提出:“既瞽(男子名)又以母故,伤人可宥之,令出银十两付死者家,备葬。”*《明宣宗实录》卷105,宣德八年闰八月壬戌,第2348页。可见,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允许民间金银用于交易。但这不等于国家在货币领域就已经认可金银的法定地位,如宣德七年(1432年)十一月,宣宗针对两广、福建等地银钱兼用的情形,指出“铜钱、银两已有近例。近年以来,广东、广西、福建等处,民间将铜钱、银两相兼行使,往往事发”。*戴金等:《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五刑类·过失杀人罪收赎钞三十三贯六百文铜钱八贯四百文例》,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6页下栏。正统即位之初朝廷还颁令“各处诸色课程旧折收金银者,今后俱照例收钞”。*《明英宗实录》卷1,宣德十年正月壬午,第12页。可见,政府对金银、铜钱依然采取某种限制或打击政策,着力维持的还是宝钞体制。
三、“公领域”的白银流通
政府虽然禁止白银用于民间交易,但并没有在公私领域完全摒弃白银的使用。相反,政府在制度层面规定民间金银兑换宝钞通行,在特定地区使用金银采买物资,在赋役领域允许折纳金银,此外赏赐支用也多有用银之记载,显示出制度规定中“下须通上、上可对下”的单向意味。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在颁行禁金银令时,就曾明确规定告发伪造宝钞赏银250两,并允许“若有以金银易钞者听”。*《明太祖实录》卷98,洪武八年三月辛酉,第1670页。即民众要想金银用于交易,必须先兑换宝钞,否则属于违禁行为。除了货币收兑政策外,在“银禁”时期,白银在诸多公领域中显现其身影。明初统治者在赋役折纳、金银差发、金银课征、税课赃罚输纳、赏赐、采买物资等诸多领域都曾允许使用白银。
田赋折银。银禁政策出台前,朱元璋就曾允许运输不便地区可用金银、钱钞、布帛等折纳税赋。*《明太祖实录》卷88,洪武七年四月甲申,第1568~1569页。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进一步颁令:“命户部、天下郡县税粮除诏免外,余处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明太祖实录》卷105,洪武九年三月己丑,第1756页。明初国家逐步确立了实物为主的两税征收体制,本色为主,少许折色为辅。折色主要是指用金银、钱钞、绢帛等轻赍物来折纳田赋上交,以便减轻百姓的负担,并主要施行于运输条件较差地区或灾害发生地方。折色制是一种以实物为中心、以官定价格开展的赋税缴纳形式。作为国家赋税正额的一部分,折色方式与其说是货币形式,不如说是一种具有颇具实物特征的财政调剂,不仅折纳的物品多样,各地折价也不一。
除了折收钱钞、布帛的事例较多外,折纳金银也多次出现,如洪武十七年(1384年)七月,朱元璋“命苏松嘉湖四府以黄金代输今年田租”,*《明太祖实录》卷163,洪武十七年七月丁巳,第2529页。同年十二月,云南左布政使张紞奏:“今后秋租请以金银、海贝、布、漆、朱砂、水银之属折纳,诏许之。”洪武十九年(1386年)五月,“己未,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往岁仓储,通会其数,凡有军马之处存给二年,并儒学廪膳餋济孤老驿传廪给外,余悉折收金银、布绢、钞锭输京师。”*《明太祖实录》卷178,洪武十九年五月己未,第2692页。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十二月,“鲁府左长史胡秉忠奏,王府岁给米五万石,折收金银、钞锭已移文山东布政使司。”*《明太祖实录》卷198,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午,第2975~2976页。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广西镇安府府民因运输艰难,愿依前例输白金。*《明太祖实录》卷232,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甲寅,第3391页。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朝进兵广西龙州,诏令安南输粮接济,安南国丞相以本国田赋仅够自足、运输艰难为由,只“愿输米一万石,余以金千两、银二万两代输”。*《明太祖实录》卷242,洪武二十八年十月癸卯,第3521页。
至永乐时期,赋税折纳钞、帛的事例较多,但折纳金银的做法也存在。如永乐六年(1408年):“乙卯,诏河南、山东、山西永乐五年以前逋负税银,及追偿未完盐粮、刍豆诸色课程、赃罚悉免。”*《明太宗实录》卷77,永乐六年三月乙卯,第1041页。永乐十三年(1415年),“户部言浙江乌程等四县水伤,田稼九千四百四十三顷税粮请折金帛,从之。”*《明太宗实录》卷165,永乐十三年六月己卯,第1855~1856页。洪宣时期,国家严厉疏通钞法,故赋役折钞、布、绢的事例较多,而折银的事例较少。宣德元年(1426年),山西监察御史于谦见大同田地因逢霜蚤而薄收,故将输边粮“多折金银”。*倪 岳:《少保兵部尚书于公神道碑铭》,见徐竑:《明名臣琬琰续录》卷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影印本,1986年,第344页。宣德五年(1430年),南京监察御史李安揭发地方粮长欺压百姓,有妄自将税粮折收金银、缎匹的情况存在。*《明宣宗实录》卷74,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壬寅,第1721页。折纳金银虽是权宜的暂时行为,但如顾炎武所论:“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顾炎武:《日知录》卷11《银》,见《顾炎武全集》第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2011年,第470页。果不其然,正统之后随着国家允许南方许多地区以金银折纳田赋之例一开,禁金银政策逐渐濒于破产境地。
差发征银。在蒙元时代差发专指赋税徭役,明初承继差发之名,如边地供纳马匹之类。中央王朝虽贯以茶易马之名,实际上成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承纳的特殊赋役负担。*梁方仲有相关介绍,参见氏著:《论差发金银》,《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 278~281页。在云南、安南等地区也存在差发金银的输纳,具体情况《天下郡国利病书》有记载:“城池因高山为砦,无仓廪租赋。每秋冬遣亲信往各甸计房屋征金银,谓之取差发。每屋一楹,输银一两,或二三两。承使从者象马动以千百计,恣其所取,而后输于公家。”*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南贵州交趾备录·种人·僰夷》,见《顾炎武全集》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634页。
除此之外,云南尚有“差发马”“差发海贝”的输纳。永乐元年(1403年),户部尚书夏原吉说:“云南、四川平,宣慰司土官思伦发原输差发六千九百两,续又增办一万八千两。”*《明太宗实录》卷39,永乐三年二月壬申,第311页。明初诸帝即位伊始俱颁令停止金银采办诸项,但云南等地差发金银一直保存下来。至正统初,史料还记载“免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所欠差发银,本司岁征差发银五百两,自宣德元年至七年止纳银一千三百五十两,尚欠二千一百五十两”,*《明英宗实录》卷15,正统元年三月丙子,第282页。安南地区亦有此类金银差发等项。*《明太宗实录》卷60,永乐四年十月乙未,第869页。弘治十五年(1502年),国家正式将云南差发银定为每年8 809.5两的常例。*万历《明会典》卷37《户部二十四·课程六·金银诸课》,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69页。除差发金银外,史料另有永乐时期特殊原因形成的赋役负担银记载:“初永乐间,因征北虏,获羊万余,令顺天府所属州县分牧,岁办羊毛,价银九百六十余两输司设监供用,谓之长生羊毛。”*《明孝宗实录》卷96,弘治八年正月癸丑,第1773~1774页。后因无羊可养,但羊毛银一直存在,直到弘治八年正月才被正式取消。此外,据说永乐初夏原吉治水时曾编有淘河夫银,*参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4《史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1页。永乐后期官场便开始索取皂隶银的现象。*参见李贽《续藏书》卷19《清正名臣·都御史顾公》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09页。
金银课税,主要是在永乐时期大量增加。永乐时期,成祖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但财政大量支用宝钞,同时一改朱元璋最大限度限制金银矿开采的做法,积极在全国各地开采金银矿,并征纳大量金银用于财政支用。建文四年(1402年)十一月,篡位不久的朱棣接受陕西商县的建议,开采旧有八所银矿。*《明太宗实录》卷14,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庚寅,第257页。永乐元年(1403年),“以各处银场银坑岁办科征不实,分遣监察御史及中官核之”。*《明太宗实录》卷17,永乐元年二月丁丑,第316~317页。永乐三年(1405年),开云南大理银冶,命有司督办。*《明太宗实录》卷48,永乐三年十一月丙辰,第734页。永乐五年(1407年),国家允许福建蒲城县开银矿3所,每年可得银1400余两。*《明太宗实录》卷71,永乐五年九月丁巳,第994页。永乐十三年(1415年),成祖又差官到湖广辰州、贵州铜仁等处金银场采办金银课。*万历《明会典》卷37《户部二十四·课程六·金银诸课》,第268页。在这种积极进取型的政策背景下,政府每年征收的金银课收入较洪武时期有了大幅度提高。以白银为例,洪武时期仅有3年的数据,国家每年征收的银课数额从2.98万两下降至2万两左右。到了永乐元年(1403年),白银一下子跃升至8万余两,永乐二年突破10万大关,永乐四年(1406年)更增至20.91多万两,永乐十二年(1414年)一度增至39多万两。整个永乐21年(1404年)的时间,国家每年的银课数大体为23.4多万两,是明代前期金银课额、生产最大幅度的一次扩张和增长。*按,关于明代银矿开设以及废罢的详细情况、开采数额,梁方仲有翔实的考证。他也关注到永乐时期银矿开设之广,金银课铸额之多。参见梁方仲:《明代银矿考》,《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第486~487页。数据统计及计算见全汉昇:《明代的银课和银产额》,《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洪熙上台之后,立马宣布取消这项扰民政策:“各处阐办金银课,除去煎稍见收在官外,自今停止。……其旧额岁办银课并差发金,不在此例。”*《明仁宗实录》卷1上,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丁巳,第17页。
对于金银开展的扩张政策确实是劳民伤财之举,有些地区如浙江温、处二州额办的金银课甚至扩充了40倍以上,百姓难以承受,*《明史》卷158《列传四十六·轩輗传》(第4323页)记载,永乐时此两处的额办数额由0.28万余两,升至8.2万两。故洪熙帝予以取消。因而,自洪熙以后国家每年的征收的银课立马下降至3.7万两左右。不过,宣德后期国家再度大幅度增加金银课,平均每年达到30多万两,可能是由于钞法不畅、财政支用缺乏所致。
课程、赃罚折征银。据《大诰》记载,当时扬州瓜埠河泊所欠鱼课钞四万张,知府令富户追赔,追钞即足,“各人分受入己,变买银两”。*朱元璋:《御制大诰》第50《扬州鱼课》,《续修四库全书》第86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5年,第257页下栏。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下令:“诏天下来朝官员及岁解诸税课赴京者,无间远迩,皆给钞二十锭为道里费,其所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者,许易金银以进。”*《明太祖实录》卷177,洪武十九年三月己巳,第2682页。宣德五年(1430年),浙江温州府知府何文渊透露了一个重要情况:
洪武中商税并三十税一。十七年以前,止收钞及铜钱。十九年于府设税课司,诸县设税课局,及河泊所收商税钱钞,著为定例。若便于起解者解本色,路远费重者许变卖金银,金每两价钞六锭,银每两价钞一锭。至二十四年,本府所属共收钞七百二十八锭四贯,易银七百八两八钱送纳,其后岁办,遂以为例。近虽禁使银,而商税鱼课仍征银,巡拦网户陪纳甚艰。乞自今年始,仍援洪武十九年以前事例纳钞,庶为民便。*《明宣宗实录》卷80,宣德六年六月甲辰,第1853~1854页。
可见,自洪武十九年(1386年)后至宣德五年(1430年),浙江税课司一直将税课钞变卖白银缴纳,大体成为惯例,甚至在禁银时期仍输银。宣德七年(1432年)三月,宣德皇帝颁令:“湖广、广西、浙江商税、鱼课办纳银两者,自宣德七年为始,皆折收钞,每银一两纳钞一百贯。”*《明宣宗实录》卷88,宣德七年三月庚申,第2018页。可见这些地方的商税、鱼课此前多是输银。然改银为钞的规定似乎并没有很好的得到贯彻。宣德九年(1434年),浙江布政司上奏处州府:
所属丽水、青田、松阳、龙泉、缙云、遂昌、庆元七县窑冶、酒醋、铅坑、银坑、碓磨、油榨、砖瓦、窑灶、房地、赁钱、竹木、山租、茶课、税契、茶引、由工墨、果价、儒学山地租契本、工墨岁征课程银三千三百四十一两有奇,民贫,银多负欠,乞依敕谕内商税、鱼课事例,折钞为便,从之。*《明宣宗实录》卷114,宣德九年十一月癸卯,第2576页。
赃罚输银。在宣德元年(1426年)十月前似乎就存在,“赃罚金银诸物,金每两八千贯,银二千贯”。*《明宣宗实录》卷22,宣德元年十月乙亥,第582页。宣德六年(1431年)六月,“行在户部奏,广东琼州府遣人,赍赃罚银五两四钱赴京进纳”,因数额太小,不抵运费,宣德皇帝训斥这个地方官不体察人情,并命令这种小额的赃罚银征收以后收贮在地方官库。*《明宣宗实录》卷80,宣德六年六月乙巳,第1854页。
赏赐金银。明朝建立后便实行过大量的金银赏赐,尤其是对于军士、藩王等人的赏赐,数额有时达一二十万两。国家发行宝钞、禁行金银后,金银依然大量用于赏赐。洪武十九年(1386年),“遣使以钞十五万四千九百锭赐云南各卫军士,白金十二万七千一百四十两赐乌撒各卫军士。”*《明太祖实录》卷177,洪武十九年二月己酉,第2680页。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赐苏州等卫将士二十万九千三百余人,白金十万九千九百余两,钞三万锭,布三十万七千六百匹。”*《明太祖实录》卷190,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辛未,第2869页。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命户部运白金十万两,文绮五千匹往北平;白金五万两,文绮二千匹往山西,俱于王府收贮以备赏赉。”*《明太祖实录》卷201,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乙亥,第3014页。永乐时期,国家金银赏赐更为频繁,多用于对藩王、朝贡使团、官军等人。如朱棣夺位之初,“赐周、楚、齐、蜀、代、肃、辽、庆、宁、岷、谷、韩、沈、安、唐、郢、伊、秦、晋、鲁靖江二十一王各黄金百两、白金千两、彩币四十匹、锦十匹、纱罗各二十匹、钞五千锭。”*《明太宗实录》卷10下,洪武三十五年七月乙巳,第169~170页。洪宣时期,国家对于藩王施行大量金银赏赐,史料不胜枚举。赏赐朝贡使团、军民等事例。如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赐朵甘乌思藏必力工瓦等国师,及其土官,白金三百七十五两、钞千二百五十五锭、彩币四十二表里”,“丁丑,命刑部自今能捕获强盗者赏银五十两。”*《明太宗实录》卷16,永乐元年正月己丑,第293页;卷17,永乐元年二月丁丑,第316页。永乐几次对外战争,如征讨蒙古、征战安南,随军军官征前战后具有大量金银赏赐。*此方面史料很多,可见《明太宗实录》卷154,永乐十二年八月丙辰,第177~184页;卷161,永乐十三年二月戊子,第1826~1831页等。洪、宣时期,国家亦有不小的金银赏赐于藩王、将士等事例,规模不小,实录多有所载。
国家出银采买粮食、马匹及纳银中盐事例。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广西海北白石四盐场,广州东海十一场允许召商纳银。*《明太祖实录》卷96,洪武八年正月甲戌,第1652页。洪武十六年(1383年),朱元璋派遣“内官梁珉以货币往琉球易马,还得马九百八十三匹。”*《明太祖实录》卷156,洪武十六年九月乙未,第2429页。估计此处货币应为金银、丝绢、文绮之属。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命将士几百至千人,携带大量白银往西南番地都买马匹。*《明太祖实录》卷177,洪武十九年正月己丑,第2678页;卷178,洪武十九年五月庚申,第2692页。这年十二月,“命云南布政司以白金二十万两,给各府县籴粮备用”。*《明太祖实录》卷187,洪武十九年十二月壬子,第2802页。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遣使赍白金往湖广思南宣慰使司,籴粮一万二千石,运赴贵州等处以给征南将士。”*《明太祖实录》卷194,洪武二十一年十月甲寅,第2911页。永乐十三年(1415年),国家允许交阯布政司以金、银、钱来中纳官盐“户部定议金一两给盐三十引,银一两、铜钱二千五百文各给盐三引”。*《明太宗实录》卷163,永乐十三年四月庚寅,第1847页。永乐之后,国家用银采买的事例渐少,大部分改为钞、绢、盐、茶等物。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明初政府在诸多领域使用白银作为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的补充。不仅如此,白银在民间交易场合中也一直存在。
四、“私领域”的白银流通
明初专制政府奉行由严至宽的“银禁”政策,且并不断重申此项禁令,侧面透露金银实际不断流通于基层社会。*黄阿明从《逆臣录》《大诰》中梳理出不少民间使用白银交易的案例(俱发生在洪武中后叶),充分说明白银不断参与民间交易的现实。参见氏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第97页。我们知道,白银的货币化在金、元时期得到极大发展,其计价尺度功能日益得到强化。*参见王文成《从“钱楮并用”到“银钞相权”——宋金元时期传统中国的市场结构与货币流通》,《思想战线》2014年第6期;何 平《世界货币视野中明代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等。彭信威、万志英等货币史学者多认为金元之后的白银获得了较为稳定的价值尺度和价值储藏功能,但流通职能尚并未完全获得。对明初某些地区而言,白银的流通现状确实如此。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政府在重申金银禁令时指出:“甲子,禁民间无以金银交易。时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明太祖实录》卷251,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第3632页。
此条史料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国家重申金银禁令的目标直指浙江地区的商人阶层,反映了禁金银政策的政治属性;二是这些地区的人们不论货物贵贱俱以金银“定价”,而非以金银交易,说明在当时的经济发达地区沿海等地,金银主要是作为一种基准计价手段而存在。*足立启二率先进行了这样的解读。参见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p.73。基层社会实际流通的主要还是铜钱或实物货币。*这一点从前后的史料中可以看出,明初浙江、两广、福建等沿海之地主要流通银钱。参见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明初小说《剪灯新话》《剪灯余话》也有多处提及白银用于惠赠、支付、计价等情形。*参见沈伯俊《文学史料的归纳与解读——元代至明初小说和戏曲中白银的使用》(《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再论元代至明初小说戏曲中货币的使用》(《政大中文学报》2006年第6期)。万明在对徽州土地契约交易进行深入分析之后认为,徽州土地契约使用银的情况多是以银议价、谷物支付,抑或支付宝钞、以银作罚,或是以首饰花银、丝银等来支付,体现了白银在交易中主要作为价值尺度,以及法令对其有所限制的特征。*万 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可见,明初白银在某些地区的流通主要表现为一种价值尺度功能。
当然,某些地区白银表现出的计价手段职能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禁银”政策持续的压制以及明初反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展开的背景下,民间的商业经济走向萎缩,交易多陷入实物化、零碎化的境地。*刘光临最近阐述了明前期市场经济的萎缩状况,将其纳入到明初指令性经济体制的框架下考察,认为明初的社会经济并不需要货币,社会交易走向实物化。见氏著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因故,金银与布帛、丝绢、米麦等一道作为一种民间实物货币而流通。如在当时的云南、贵州、四川等偏远之地,多通行茴银及其他的实物货币。*参见黄阿明《明代的货币与货币流通》,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章。洪熙元年,政府发现“民间交易率用金银、布帛”,*《明仁宗实录》卷6下,洪熙元年正月庚寅,第219页。当时钞法出现“不通”的问题,有人建议除金银外,还应“禁止民间毋以布帛、米麦交易”,遭到宣宗的斥责。*《明宣宗实录》卷15,宣德元年三月丁巳,第415页。可见当时的交易媒介不仅多元混杂,且实物气息浓厚。最能体现这个特征的莫过于学界挖掘的土地交易契约货币使用状况(见表1)。

表1:洪武至宣德时期徽州地区土地契约交易使用媒介表*表格来源:转引自万 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由表1可知:其一,自洪武至洪熙时期,宝钞在民间交易中作为主要交易媒介使用。宣德以后,宝钞的使用量大幅度减少,显示其逐步退出民间交易市场的趋势。其二,在明前期的土地交易中,货币多元的现象一直存在,金银、布帛、绢布等大量行用,尤其以洪、宣前后为盛。其三,白银交易在国家“禁银”政策前后一直存在,但在明前期多元通货并存的情形下显然不占优势。
多元实物货币充斥是明初社会的一个鲜明特征。《明会典》记载:“(太祖时期)民间金银、米麦、布帛诸物价钱,并依时值,听从民便。”*万历《明会典》卷164《刑部六·仓库·钱法》,第841页下栏。宣德二年(1427年),巡抚陕西隆平侯张信等说:“陕西西安、凤翔籍府,岁输粮草于宁夏、甘肃洮河、岷州诸卫,道路险阻,运致为艰,民往往赍金、帛就彼市纳。”*《明宣宗实录》卷33,宣德二年十一月癸巳,第841页。足见当时民间交易的货币除了宝钞外,大多为布帛、米谷、金银等实物货币。从《实录》资料反映出的状况看,除钱、钞外,政府也大量使用实物如罗绮、绫帛、茶叶、盐货、金银等前往边地或外国购买马匹、粮食,说明政府上层也大量依赖多元实物交换。一定程度上说,货币的多元混杂状况,反映了市场零碎化、交易不发达的特点。黑田明伸指出,以生活必需品之类的实物充当交易媒介,当其供求出现紧张时,容易导致市场交换出现瘫痪。因为在出现饥馑时,谷物、盐等必需品难以被出售,只会助长混乱。且它们履行货币职能时,会出现超过物品本身的需求预测而过剩地有被储藏的倾向,给生产带来不利影响。*[日]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何 平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页。换言之,即使是在同等交易水平之下,金银与他们的差别仅是自身特性的优势,故容易脱颖而出。
宣德时期,尤其是中后期,白银在民间的流通似乎日益广泛。早在宣德初年,政府就痛斥“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的现象,并下令出榜禁约。*《明宣宗实录》卷19,宣德元年七月癸巳,第493页。宣德四年(1429年)六月,户部发现近年来巨商、富民以及权贵之家交易只用金银,导致钞法不行。*《明宣宗实录》卷55,宣德四年六月庚子,第1322页。可见,在明初萎靡的货币经济状况下,率先突破银禁的群体往往就是这些豪民、富商和权贵阶层。
当时地方势豪借故敲诈财物、科派金银的现象屡禁不止,如宣德五年(1430年),苏州府长洲县官员顾荣报告,卫军百户李让等为了征集少许木料造抗倭船只,下县乡大肆科派排年里长银两、布绢。*况 钟:《况太守集》卷7《备倭船及开浚河道奏》,(吴奈夫等校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6页)载:长吴两县排年里长1万余名被勒令上交银3000两,每名要银0.03两,结果只需要造船1只。江西耆老奏报,地方粮长擅自加倍征粮、折纳棉布以及以官费的名义“每甲首一人别科银二两”。*《明宣宗实录》卷74,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庚戌,第1724~1725页。宣德七年(1432年),粮长杨旭等人串谋科派本区十二里百姓,每里花银3.3两。*况 钟:《况太守集》卷10《提取贪赃逃避官员奏》,第110页。故在生产交易不甚发达的明前期崛起了一批豪商势要之家,积累大量金银财货。如宣德三年至四年(1428~1429年),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刘观受任嘉兴知府,“庇郡豪强,郡民豪富者咸通货贿……观受黄白金动以千数,罗绮不可数计。”其子刘辐收受浙江死刑犯贿赂,“受其白金数百两,白于观,皆听番异,得免死”。*《明宣宗实录》卷56,宣德四年七月庚午,第1343页;《明宣宗实录》卷47,宣德三年十月庚辰,第1151页。江西按察副使李纶“受海盐县豪民白金一百五十两、黄金五两、文绮二十余匹,出其杀人之罪”。*《明宣宗实录》卷74,宣德五年闰五月癸丑,第1726页。宣德六年(1431年),宁阳侯陈懋私遣“军士二十人,人给二马,赍银往杭州市货物”。*《明宣宗实录》卷76,宣德六年二月壬子,第1768页。内官袁琦、内使阮巨队等人以采办为名,大肆敛财,获罪抄家时发现其家藏有“金银以万计,宝货、锦绮诸物称是,又所用金玉器皿,僣侈非法”。*《明宣宗实录》卷85,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第1961页。此外,关于上下官吏、势豪之家收受商民金银贿赂的史料不胜枚举。可见他们手中积累的金银数额不小。
马克思曾说过:“生产越不发达,货币财产就越集中在商人手中,或表现为商人财产的独特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4页。上述例子表明民间社会的金银流通不仅越趋广泛,同时也呈现着社会分层的特点。
五、结 论:白银的“双轨”流通及其内涵
透过前文的分析可知,明前期白银的流通状况,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因制度阻隔的“双轨”流通状态。为了维持钞法的运转、打击江南地区的豪商势力、崇本抑奢的实物主义理念等,明初统治者实行了为时不短的“禁银”政策。政策虽历时代发展日渐松弛,但毕竟在公、私领域造就了一道人为的流通藩篱,使得明前期的白银在公、私领域的各自流通存在明显的割裂特征,相互关联性甚少。
在制度层面的“公领域”,政府并未完全放弃使用白银,如允许某些交通不便或受灾地区的田赋折纳金银上交,某些特殊的赋役名目交抵白银,课程、赃罚等也有不少收银的事例。更为重要的是,自洪武之后国家每年通过金银矿税收缴的白银数不断增加,配合着统治者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朝廷赏赐用白银的例子更是不在少数。从整体来看,“公领域”的白银流通有着更多的单向收兑意味;而采办、赏赐用银也多局限在偏远之地或社会上层。
在民间社会的“私领域”,白银在不少经济发达之地首先表现为一种基准计价手段。其后,随着禁银政策的重申与维持、宝钞的不断贬值、实物型经济体制的推进等,民间交易逐步陷入零碎化、实物化境地,金银遂又与布帛、米麦等构成了多种通货并存的混杂流通状态,屡禁难止。
综合言之,明前期白银的“双轨”性流通虽显得广泛,但内涵却极为有限:
其一,在“公领域”,它仅是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下诸多折色物中的一种,与布帛、棉花、米麦、黄金等实物区别不大。实物主义为本是明初施政逻辑的出发点,典型如洪武后期的一段史料所反映的那样:“凡各处逋租,皆许随土地所便,折收布绢、绵花及金银等物,宜定著其例。于是户部定:每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折十石、银一两折二石、绢一匹折一石二斗、绵布一匹折一石、苎布比绵布减三斗、绵花一斤折米二斗。”*《明太祖实录》卷255,洪武三十年十月癸未,第3682页。
可见,在户部制定的则例中,米石才是所有折色物品的基准手段,深度印证了藤井宏的一个判断:“这一时代(明前期),米为一切物价的基准。”*参见[日]藤井宏《关于<织工对>的诸问题》,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25~126页。
其二,在“私领域”,白银也仅是多元通货中的一种,属于并非先进的民间实物货币范畴。*关于实物货币的分析,参见邱永志《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及其原因——以白银的货币性质为分析视角》,《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故这个时期应称之为实物主义为本的多种通货并存时期,才更为恰当。
因而,无论是对于财政体制的“公领域”还是民间经济的“私领域”而言,此一时期白银的流通状况皆折射出明前期浓厚的实物主义特征。
(责任编辑 张 健)
On the Double-track Silver Circulation in Early Ming Dynasty and its Connotations
QIU Yongzhi
The status of silver circulation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generally unknown to academia, can actually be summarized as a kind of “double-track” circulation caused by the obstruction of government policy. In the institutional public sphere dominated by policies, the government, while striving to maintain and reinforce the “silver prohibition” policy, unilaterally retrieved silver at a discount in such realms as exchange of Baochao paper money, corvée and taxes; silver could also be used as imperial largess and in procurement. In the private sphere of the civil society, silver first became a benchmark in quite a few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 later, following the drastic depreciation of Baochao an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economy, it coexisted with currencies such as cloth, silk, rice and grain, compounding the complex situation of circulation. Silver was still in circulation after repeated prohibition. In sum, although the double-track circulation of silver was widespread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but it was quite limited in its connotations. In the public sphere, silver was but one of the alternative circulation means in an in-kind corvée fiscal institution and was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other forms of kinds--cloth, silk, rice, grain and gold. In the private sphere, it was only one of the many currencies in circulation, belonging to the underdeveloped category of commodity money in the civil society. Whether in fiscal institution or in civil economy, the status of silver circulation reflected marked features of material economy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early Ming Dynasty, silver prohibition policy, silver, double-track, connotation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明变革视野下的明代货币转型研究”阶段性成果(17CZS019)
邱永志,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研究中心讲师、博士(江西 南昌,330013)。
K23
:A
:1001-778X(2017)05-012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