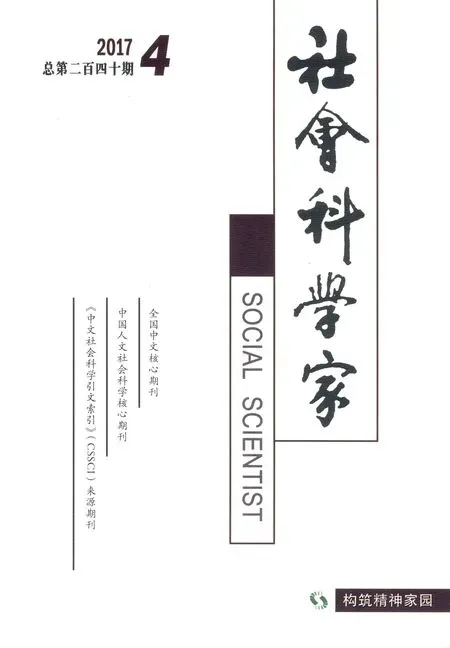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明代京官送别雅集的文化学解读
张高元
(湖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湖北 黄石435002)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明代京官送别雅集的文化学解读
张高元
(湖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湖北 黄石435002)
明代京官送别雅集引入朝隐文化,将预祝出行人取得卓越政绩和设想出行人政暇的娱乐活动结合,创作了表征朝隐意识形态的雅集文本。此类文本充分利用叙事的语言结构,建构意识形态的意指实践,利用普遍化、自然化手段推广意识形态。但送别雅集祝愿的虚化情境和雅集的符号化趋向本身带有乌托邦性,恰好说明了文人的政治处境对意识形态推广的保护作用,显示了中国文人与西方文人对意识形态的不同态度,丰富了文本意识形态批判的内涵。
送别雅集;朝隐;意识形态;乌托邦
中国有悠久的送别文化,文人多在送别之际,用诗歌、图像表达离愁别绪,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据石守谦梳理,早期送别图是“诗图”,如李公麟的《阳关图》是根据王维送别诗而作,到南宋基本定型为水岸送别模式,即一群人在岸边拱手送别将远行的人。这种送别图模式在明代依然存在,戴进、沈周、唐寅、杜琼都绘制过类似送别图。这些图像与相配的诗歌一起,主要表达离别之情,[1]还是处在偏于感伤的送别文化传统中。但明代还出现了另一种送别图。这些图像产生于两京地区官员送别外任京员的饯别会中,参与人数很多,留下了大量诗歌,图像也不是传统的水岸送别式,而是采用宴会形式,却不是参与人物真实活动的再现,而是一些图式组合的结果。送行诗歌的侧重点转向对出行人为政之暇闲适生活的设想和对出行人杰出品性的颂扬。笔者认为这些内涵与明代流行的京官雅集对香山娱乐精神的提倡有密切关系,也说明朝隐文化渗入送别雅集艺术后,将出于性情抒发的隐逸文化转变为意识形态文本的言说,为明代意识形态文化增添了新内涵。①相关研究参看拙文《图像、文本、意识形态》,《观念、文学、图像:明代京官雅集新解》,《王维的雅集图与明初文艺风尚的转变》。分别见《天府新论》,2013年第5期。《鹅湖》(台湾)第38卷,第11期。《西部学刊》,2016年第1期。不同于其他雅集中,送行祝愿本身是一个虚化的结构,既便于利用文化元素强化意识形态的建构性,也能够充分利用诗画的媒介特性,将意识形态转化为意愿,建构文本乌托邦,展示朝隐文化的文本之娱。本文正是在文化学视野下,揭示送别雅集的意识形态内涵,分析意识形态转向乌托邦意愿的过程,及其中采用的修辞策略。
一、明代京官送别雅集图
明代南京是文化、政治的中心,高官和画家云集,送别出佐官员集会很多,也使得赠送诗画合卷的艺术留恋品成为一时特有的文化现象,因此留下了大量南京官员送别外调官员的送别雅集图与诗。由于诗歌的内容和形式都可以在下文见到,图像却很难在行文中展现全貌,这里先介绍一下送别雅集图的情况。目前见到最早的京官送别雅集图是王绂绘制,送别赵友同①赵友同字彦如,长洲人,沈实温雅,有行谊。少笃学,从宋濓游。洪武末任华亭县学训导,永乐初满考当迁,会姚广孝言其深于医,遂授太医院御医。又有言其知水事者,诏从夏原吉治水浙西(1403-1405)。其后大臣数荐其文学,及修永乐大典遂用为副总裁,又与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书成当迁翰林,以母丧去,卒于家。(参见王鏊编:《姑苏志》卷54,《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7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859页。)的《凤城饯别图》。图像表现一舟停在岸边,三人亭中饮酒,亭外盘石高树,亭后两叠山峦。另一幅是吴伟的《词林雅集图》。此图是送别龙霓上任浙江的图像。图中画家截取园林一角,分三组表现雅集场景,右边两人斗棋,一人观看,中间一人观书,一人观画,左边两人写诗,一人抚琴,桌上放着饮用器具。最后一个童子捧书函侍立。园中配置玲珑石、梧桐,一只小鸟正在啄食。从题诗的人数来看,两次雅集的参与人数量均超过画面人物,可知画面不是对实际场景的再现。对照其他雅集图像可知,[2]这些送别雅集图也是采用既定图式完成的。
根据贡布里希图式理论可知,图式既可以是成型的简图,也可以是偶然的墨迹。成型的简图以线条为主,勾勒形态,送别雅集图中通过线条造型,以描绘人物活动为主的图像是成型的图式。偶然的墨迹是不规则形状,艺术家以此为起点,不断矫正、调整,探索现实、处理个体的手段。[3]送别雅集图中以描绘环境为主,侧重笔墨关系,追求表达特殊效果的图像恰是由偶然墨迹发展而来。这里我们不再细致分析中西图式的不同特色,而是回到中国雅集图式传统说明明代送别雅集图式的来源和变化。
从上文对两幅雅集图的描绘可知,两图图式来自文会图传统和书斋山水。历史上著名的文会图很多,西园雅集图是最著名的图像。在西园雅集图像传统中,画家将宴会场景故事化为文艺活动,如饮酒、赋诗、抚琴、题壁,弹阮等。西园雅集图虽然不见宋本真迹,图式内容和人物风采(尤其是李公麟)还是被很多画家传承下来,成为表现雅集人物风采的重要图式。吴伟的词林雅集图正是这种图式在明中期的运用与回响。图中,画家也采用几段故事描绘人物活动,并配有湖石、石案、各种几何形器皿,点明宴会场景。描绘手法以白描线条为主,突出人物的彬彬风采。区别在于,官员都穿着官服,而不是道服,这是明代雅集图比较流行的服装式样(如《杏园雅集图》),显示了官员的特殊身份,也是图像从文人娱乐走向官场应酬的象征,携带大量的政治文化信息。王绂爱好元四家艺术,图中虽表现集会,却没有采用历史上直接表现宴会的著名图式(如赵佶的文会图),而是将宴会镶嵌在元末书斋山水图式中,创立了新图式。图中,画家采用枯淡笔墨皴写山石,后以浓墨点苔,中锋勾树干,浓墨点写叶子,亭中安置点景人物,水面、山体均大量留白,明暗对比强烈,两叠山体浑厚结实,恰如港湾,包围着亭子,图中人物也着官服,但草草勾写,似乎正享受着野外隐居生活,令人想起朝隐的风采。
虽然图像的风格迥异,但图式包含的文化含义都是对一套观念的表征。这要从雅集图的流传来说。雅集在元末非常兴盛,其中顾瑛主持的玉山雅集尤其出名,元四家均参与过他主持的雅集,顾瑛还请张渥绘制了玉山雅集图。根据文献记载,此图就是仿照西园雅集图展示玉山人物风采的图像。而明初流行朝堂的雅集图也恰是在活动于江南的文人到朝廷做官后陆续出现的。图像的持有人也非常乐意请高官题写雅集图,这些行为不仅给官员评价西园雅集图,宣扬他们的雅集观念的机会,也最终导致了明代新雅集图式的出现。此处我们要强调的是,元末隐士和明初官员都对西园人闲适生活充满羡慕,而明初朝中官员为闲适添加了特殊的意识形态内涵,使得闲适成为文化表征。这一点在拙文《杏园雅集图新解》和《图像、文本、意识形态》中已经有论述。我们接着要指出的是,为何送别雅集图也引入意识形态内涵。大家知道,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套观念及其实践,朝堂之上的高官大多功成名就,基本上是朝隐观念的实现者,朝隐中充满对国家的感恩、颂赞,显示了意识形态的修辞性和朝隐生活的象征性的统一,也说明了朝隐包含两个条件:才能的杰出和享受隐逸闲适的生活。然而明代京官非常忙碌,朝隐仅仅是偶然的。根据白居易的说法,朝隐文化实现的理想空间是“留司”,即外任,政务不忙,有充足的时间举行各种娱乐。明代的送别雅集中出行人恰好是外任的京官,显然符合此种情境。又因为白居易及其追随者本身也是杰出政治人才,开拓出一个象征朝隐文化的意象群。送行人抓住这笔文化资源,设想出行人的朝隐生活,预祝他们取得同样的政绩。所以,朝隐的两个条件集中在出行人身上,为送别雅集中朝隐文本的撰写准备了条件。只是根据出行人情况不同,祝愿的偏重点也不同。在凤城饯别中,出行人辅助宰相治理河水,送行人都有江南生活经验,侧重设想归家的生活。在词林雅集中,出行人治理浙江,这里名宦留下太多丰功伟绩,形成政绩的历时丰碑,送行人侧重颂扬出行人的杰出才能和预祝新政绩的取得。显然从深层的朝隐内涵来看,两图是“异貌同质”的朝隐意识形态的表征。
二、“为政文艺”的意识形态
朝隐从私人性情感抒发到意识形态的表征,经历了议论化、名词化的复杂过程。与官场雅集中朝隐文化的表现通过一定观念说明一样,送行雅集也是通过观念来完成意识形态宣扬。从明代京官送别雅集文艺中可知,官员或宣明政治闲暇的乐趣,或颂扬个人杰出才能,或吹捧国家的褒奖等,这些显然与“为政”有密切关系,姑且称为“为政文艺”,其中包含的独特观念,正是他们宣扬的意识形态,简称为“为政文艺”的意识形态。为政文艺意识形态的起源是以闲适的文艺活动表达情怀。白居易不仅是朝隐说的提倡者,①白居易提出“中隐说”,认为隐居朝市太喧闹,不如隐居在“留司官”,混迹出处之间,不忙也不闲,可以使身心吉安。明代京官送别雅集正好是送官员到地方为政,算是中隐。不过,在明代语境下,中隐与朝隐没有什么区别。这些不同位置的官员基本上都有隐居乡间和为官朝廷两种经历,并且中隐文化包含的活动,普遍被这两群人使用,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里我们不去辨析朝隐与中隐的区别,实际上,二者只是处于不同地方,就他们同时服务于国家来说,二者是同质的。为了简便,我还是称之为朝隐主题。也通过一系列的意象创造了朝隐文化。朝隐意象通过象征某种社会身份才转化为意识形态的表征。这种转化是通过评定历史人物、赞美艺术行为、提倡道德行为、颂扬政绩等完成。这里我们借用罗兰·巴特的专有名词概念,将朝隐看成一个集合概念,分析明代送别雅集中意识形态的具体内涵。
专有名词是罗兰·巴特在《普鲁斯特和名字》中使用的概念,主要有三种属性:本质化之力(它只能指示一个所指者),引述之力(人们在说出它时可以为包含在其内的一切本质任意定名)和探索之力(当人展开一个专有名词时有如在进行一次回忆)。所以,专有名词是记忆的一种语言形式。在文艺作品中是意素性形象聚合,包含着若干场景,首先以不连续的、反常的方式产生,然后被聚合为一段小故事,按照换喻把全部场景的若干单元联系起来。[4]送别雅集中,意识形态是一些观念的集合,也是那个所指者,朝隐是其专名。朝隐是开放的,由一些形象化意素来说明,引述其中一些意素自然可以引向本质,也可以得到本质之名。朝隐所涉及的体验也是参与人曾经有,或习得的经验,是一种回忆。这些回忆、片段的意象素也在诗歌中,通过换喻组合,隐喻替换,自然以故事、场景出现,形成完整的意义。意义本身的跳跃性、触发性和开放性,出行人的独特才能,送别雅集提供的未来时空,为新的朝隐实践提供了可能性,并指向未来的朝隐实践。明人正是利用朝隐专名,将意识形态解析为联系的片段,通过包含判断的意象名词实现。
根据白居易的《池上篇》和明代文人对朝隐生活的描绘可知,朝隐展示的是“富贵的快乐”,相对于贫穷的快乐。明代官员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体验朝隐,比如三杨就反复讴歌白式快乐。但针对出外赴任的官员,朝隐成为未来的期许,虽然可以链接往昔的经历,毕竟还是虚化的祝愿。明代官员赴外任职一般有很重要的任务,显示了国家的恩宠和人才的杰出,恰是朝隐的前提。在明人认识中,因杰出而恩宠,才可以有闲暇隐居。送别雅集中,人们正是抓住这一朝隐逻辑,来推送未来的朝隐。所以,他们把目光集中在二者上,用系列专有名词建构送别雅集的朝隐逻辑。凤城饯别是送行朝廷大使赵友同辅助宰相夏原吉治理浙西水患的饯别宴会。送行人将赵友同受到重用评定为“昼锦荣殊甚,归承宠渥优”[5]。侧重点在对国家的颂扬。词林雅集是送中央政府官员龙霓到浙江任职的雅集。罗纪《文会赠言》指出:“豪杰之才得其地与权,真可以有为”②序言引自《词林雅集图》附录文,参见单国强:《吴伟-词林雅集图-卷考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4期。,侧重在对杰出才能的肯定。如果扩大两个关键词的意素,可以发现一系列建构朝隐的专有名词。在凤城饯别中,分别是“使节”、“昼锦”、“宠渥”、“君命”、“誓许国”、“泽灾势怀襄”、“师坚章”、“旧业菱花”、“秋风鸥鹭”、“紫蟹银鱼”、“野桥篱落”。这些专有名词(国有难,承君命,誓许国,锦还乡,闲适生活)构成因果链条,既是时间关系,又充足了朝隐的意义。在词林雅集中,分别是“豪杰士”、“浙大藩”、“佥事宪臣”、“持宪节”、“为之权”、“天下可以为,有一定之势”、“臣节”、“利民”、“贪廉”、“考绩”、“烈魂”、“使君临江看潮戏”,③这些词汇引自《词林雅集图》附录诗歌,参见单国强:《吴伟-词林雅集图-卷考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4期。这些名词围绕着人才杰出、持节出宪、政绩可待、娱乐活动说明朝隐的内涵。两组词汇既在历时中推进雅集叙事,又纵向上聚合人物杰出特性,形成了送别雅集(历时叙事和纵向隐喻)的意指模式。送别表达祝愿本是实情,不一定具有意识形态,但是此处祝愿的内容与意识形态同一,其实现成为意识形态的效果和表征,转为意识形态话语。所以,明代的送别雅集把朝隐的当下快乐,转化为未来的快乐。萦绕在他们心中的朝隐之乐也成为严肃意识形态的虚幻外衣,充盈着虚假与乌托邦的成分。
三、意识形态的意指结构:横组合与纵聚合
根据符号学的观点,意识形态存在于很多阶级社会,不仅表现为一套价值观念,而且是重要的意指实践,已经“自然化”到日常生活中,形成了特殊的符码系统,[6]通过话语叙事发挥作用。这种实践的典型形式是文本。在文本中,意指实践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修辞策略和意指结构。意指结构是基本叙事结构,也是主导意义建构和展开的主要模式。在叙事学语境下,文本主要通过叙事的两种语言结构(横组合和纵聚合,巴特称为组合或切分)发挥作用。在巴特看来,在叙事的语言结构中,横组合是运作,涉及故事的叙述,纵聚合是真正的语义单元,指涉所指,比如人物的品德、故事的环境等。两种结构有典型的文本:民间故事和心理小说。[7]随着文本包含内容的增多和结构的复杂,横纵关系是根据需要,贯穿于文本中。诗歌从叙事或抒情的单一模式下解脱出来后,发展出集叙事、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为一体的文本形态,横纵关系也相应被艺术家用于文本的不同段落,形成了丰富的结构关系。当这种关系是特定的意识形态观念和相应地生活方式的表征时,就开始发挥意识形态的意指作用。明代京官送别雅集的图文对意识形态的表征恰是这两种结构的体现。
凤城饯别的原因是浙西发洪水,朝廷派官员去治理,事件重大,任务艰巨。送别人有意识以横向历时时间展开送别叙事。纵观送别人的题诗,主要有三种叙事时间。一种送别的真实时间,如“孤帆斜日/龙江发/到家/晓发”,“十月/霜降/一夜到/日边回/春色早”,交代送别时间、设想到家和归来时间,保证送别的客观实在性。一种通过因果关系,暗含时间,如“君命-使节-宠渥”,“誓许国-师坚章-昼锦”,从国家任命,官员宣誓,到昼锦归家,显然是互为因果关系,也是政治活动时间,既先于送别时间,又贯穿送别时间,最后引出归家的闲暇活动时间。这种时间是送别雅集的主导时间,也是送别雅集的时间结构,决定了送别雅集叙述的横向组合关系。最后一种是朝隐时间,也是想象性、非真实时间。如“童时/几度秋/旧钓游/旧业/故人/旧隐/耆旧,梦落/想得”。确切地说,这组时间是历史记忆,是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但通过赵友同的回归,即将复活,成为未来时间,并以空间的对立为基础,如“日边-江南”,“宦游-鲈鱼”,①此段词汇均引自《凤城饯别图》题写诗歌,第46页。既是政治隐喻的,又是朝隐的特属标志空间。
词林雅集是送别龙霓到浙江任佥事。佥事在明代是提刑按察使司的属官,处理兵备、提学、抚民、巡海、清军、驿传、水利、屯田、招练、监军等事宜,责任比较重大,但并没有明确任务。②参看明史《职官之四》“提刑按察使司”条。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一人,正三品,副使,正四品,佥事无定员。正五品。浙江二:曰浙东道,曰浙西道。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纠官邪,戢奸暴,平狱讼,雪冤抑,以振扬风纪,而澄清其吏治。大者暨都、布二司会议,告抚、按,以听于部、院。凡朝觐庆吊之礼,具如布政司。副使、佥事,分道巡察,其兵备、提学、抚民、巡海、清军、驿传、水利、屯田、招练、监军,各专事置,并分员巡备京畿。”(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40页。)浙江是明代重要省份,出任佥事足以说明人才才能的突出,所以送别人将龙霓颂称为豪杰,抓住人物的杰出才能进行歌颂。浙江名流辈出,名宦、豪杰留下了大量可歌可泣的事件,也凝定了丰富的文化景观,被后来者膜拜,也成为一个个观念丰碑,警示着后人。这种丰富性为送行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奠定了从纵向聚合结构颂扬豪杰的文本结构。
这些名迹可以分为三类:关乎民生的景点:交通要道(檇李),灌溉要道(鹅池、鉴湖、葛洪川、若耶溪、剡溪),安民定国工程(苏堤、桐江)。警戒士人,颂扬美德和功勋的景点,如惩贪倡廉(明月泉、清风岭、鉴湖),提倡孝道(曹娥江、泰伯祠)。文化娱乐景点,如钱塘、林逋宅、兰亭、和笙台、鹅池、鉴湖、葛洪川、若耶溪、剡溪。这些名迹没有特定的时间顺序,主要是客观留存于浙江东西二道上的历史文化。但它们是豪杰三种能力的隐喻,建构着龙霓豪杰形象的三个特殊维度,也构成了想象的时间维度,增强豪杰形象的厚度和说服力。相应地,送行人也利用词汇的组织关系隐喻性传达了这些意义。整体来看,各组词汇内部既是互相独立的词汇集合,又可以看成横向组合。比如民生景点中的交通要道、灌溉要道和安民定国工程对于浙江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对于龙霓却并不是必然都要做出贡献的,三者在逻辑关系上是独立的,但三者的并列更说明政绩的可观,证明豪杰的杰出政治才能。第二组颂扬才能的景点分别指向清廉和仁孝,二者虽然也是豪杰官员修身的必备美德,但并不构成因果关系,却是豪杰官员的立身为政之本。同理,第三组指向文化娱乐,丰富多彩的活动更增添豪杰洒脱的风韵,也是狭义的朝隐内容。如果将纵聚合词汇看成等值的单位,并具有累计增加的力量效应,它们的并列出现,实际上也可以看作“重复”修辞的使用,这与横组合一样,加强名迹代表的意义的力度。所以,三组词汇的组织关系主体是纵向聚合关系,但又构成了想象性的横组合关系。
接下来我要谈一下想象性横组合关系的结构意义。豪杰三个层面的内涵(为政能力,为宦之本,朝隐风采)是意识形态发挥意指功效的基本要素,将纵向聚合转化为横向组合关系,建构豪杰叙事。想象性叙事的虚化结构特别符合这种语境。送别雅集中,送行人将祝愿转化为未来的行动,将静态的能力颂扬转化为动态的新豪杰建构的行动,以及心理上的认同。正是利用语言结构再造纸上豪杰的表现。
意识形态的意指作用将这种建构纳入整个朝隐过程。其明显的标志是这些事件的“经纬脉络”根据为政的主次关系和必要条件而定。在词林雅集中,最重要的是臣节。出行人到任行礼之后,就是读“表忠观之碑,循苏公堤,拜武穆王之像”,既宣誓忠孝,又激励臣节。其次是倡导清廉之风,出行人拜访泰伯庙,曹娥江,清风岭,中间安排了漫步苏堤,登谢公楼等可以既舒畅心情,又沐浴在清风里的活动,可谓政治隐喻与审美享受合一,是典型的朝隐体验。再次,传统的文艺活动也要联想到道德说教,如钱塘射潮本是民间活动,却把涛声比作“蛟龙怒”,①此段词汇,语句均引自《词林雅集图》题跋诗文。似乎伍子胥的烈魂在发怒,高唱忠诚的颂歌。还有一些名迹栖息在娱乐与为政的两端,如《剡溪》、《葛洪川》通过序、诗同时呈现了灌溉要道和文人遣兴两重含义。若序-诗的主次关系与为政-娱乐重要程度成正比,二者的娱乐性也附属于为政,是政余的娱乐表现。最后是疏通河道,防止豪夺等关系民生的政务,获得人民的爱戴,留下美名。所以,虽然横向叙事是隐含在纵向聚合中,但作为一条主线控制了聚合游览的秩序,也编织了名迹的意义逻辑。也正是“豪杰”的建构不仅仅是某一事件的轰动效应,而是一个星丛式的为政集合,需要块面化的推进,才使得横向组合关系成为内在的主导,又因为没有某一特定事件作为主导,纵向聚合呈现为松散的即兴游览,成为朝隐的未来想象。我们可以说,在词林雅集中,送别叙事的建构是因为“豪杰”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要求累积效应,其结构呈现为块面横向累积结构,所以,纵向聚合结构是“自然化”为叙事表层,受到横向结构的制约,也塑造着横向组合的结构。横向组合结构内含在送别叙事中,主导送别雅集叙事的意义维度,二者如“渔网”共同推进豪杰的建构。
如果说叙事的语言结构是意识形态意指实践的总体结构,目的在于搭建表征意识形态的内在框架,那么修辞策略就是意指实践的重要手段,使得意识形态得以辨识,并合法化、普遍化、自然化其观念,满足统治的需要。[8]
四、意识形态意指策略与乌托邦性
意识形态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具有一定的虚假性和强烈的导向性,受到西方理论界的严厉批判。明代的统治阶级与文人群体均以儒家世界观为主,也具有大体一致的共同利益,类似伊格·尔顿指出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8]但二者还分属于道统与治统的范畴。前者更加理想,后者受到实际利益的影响,发展出许多相应的统治策略和符号化的言说文艺,雅集就是其一。文人对于秉持理想化的儒家观念与遵循统治策略有清醒的认识,并能够在不同的政治时空中,以不同的方式言说。送行人对送别雅集的言说,恰好显示了文人对策略的认识与有意识的使用。学者们认为正是无意识的遵从,显示了意识形态的导向性,意识形态与现实的不符,说明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这也是西方知识分子给予它无情批判的原因。但是,中国古代文人浓烈的精英意识以及出处行藏的政治哲学,使得他们更多以追求自我诗意的生存方式,显示自己的志向,保持独立的人格。所以,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较弱。但正是他们逶迤两间的特殊智慧,助推了意识形态控制策略的实施。此处的送别雅集文图就是一例。
意识形态的目的是全面控制社会,总是以符号化的意象给人以普遍性的假象,弥漫在文艺作品中。送别雅集中的图像也是这种普遍性蔓延的结果。雅集或是官方举行的宴会,或文人官员组织的宴会,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其符号化图式是宴会。此图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与文人逍遥留司的场景有关,一种与文人娱乐朝堂的场景有关。前者比较清雅,主要彰显文人的诗性气质,但经过明代翰林的转化,更具有颂赞性,①参看《王绂的雅集图与明初文艺风尚的转变》的相关论述。后者受到官场的影响,强调由个人能力彰显的外在风采。②参看《杏园雅集图新解》相关论述。《凤城饯咏图》和《词林雅集图》是二种形式的回响,前者把画面焦点放在草亭畅饮,颇有清泠的林下之韵,后者着重刻画了人物的彬彬风采,更增朝堂高士的奕奕之风。但受到送别语境的限定,都没有明显的时空定位,显然以“去时间化”的策略说明两种图式符号的普遍认可性,也顺势将“宴会”推入将来,更制造了宴会模式超越时空的假象。
意识形态本是思想幻觉,却采用一些可信的描写,制造真实感,给人一种自然而然出自本身的印象。送别雅集中能让人信以为真的环节是出行人的行程,以及对沿路风光的欣赏体验。李至刚的送别诗恰是这一过程的描述:
汀洲杜蘅歇,南浦西风生。美人鼓兰楫,路指江南行。南行向何许,东望吴淞去。吴淞秋水多,绿遍芙蓉渚。渚外九龙山,山边三泖湾。人家临水住,日暮采菱还。采菱歌易断,送子愁零乱。愁来可奈何,思满江南岸。江南不可思,动子情依依。③《凤城饯别图》题诗,第46页。
我们知道,这批送行官员都有隐居经历,撰写此类诗歌是对记忆的唤醒。诗人利用舟行,通过景物的不断更新,点出江浦发舟,舟到吴淞所见芙蓉渚、九龙山、三泖湾等地风光,制造视觉的流动感,形成想象的韵律,给视觉带来节奏感。到日暮时分,视觉节奏又被江南采菱的音乐韵律替换,而音乐声断恰恰阻止了韵律的延展,赵友同从归家的沉醉中惊醒,回到送别场景,将归家的喜悦与离别情绪结合,触发对江南的思恋。诗中典型的江南意象让送行队伍经历一次时空错位,完成一次朝隐体验。对照诗歌对灾情的描述和相关史料可知,灾情颇重,水口淹没,一片浑茫。④关于永乐初年的浙西水患危害记载参见何三畏编著《云间志略·治河尚书夏忠靖公传》,《明代传记丛刊》,明文书局,第25-28页。关于浙西水患治理记载可参见太仓县纪念郑和下西洋筹备委员会,苏州大学历史系苏州地方史研究室编《古代刘家港资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第 46-58,64-69页。夏原吉到任后勘察灾情,采用夏禹疏通法治理,虽然解决了主要问题,但支流未妥善处理,形势严峻,后来明廷还继续派人治理,每年都要修理河堤,疏通水道,任务长期而艰巨。送行人作为朝廷重要大臣,对于水患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所以,送行人的祝福也集中在唤起过去的回忆(旧钓游,旧业),增添了朝隐的虚幻性。我们还可以从图像的描绘上发现这种虚幻性。在《凤城饯别图》中,前景草亭与道路处在同一对角线上,草亭左侧紧靠山坡,草亭后两叠平行山遮挡,山下坡陀延伸到右侧,远处淡淡的横山从右向左延伸,江水夹在山坡间,显然是风平浪静的港湾。但画家采用元末隐逸山水图式,山体大量留白,树木萧淡,以点为主,颇写意,给人江南风光的错觉。二者合观可知,诗歌是从时间的角度,通过地点的切换,图像是从空间的角度,采用特殊的江南意象,共同诠释了隐逸生活的幻觉。二者又在情感上与送行人的经验相通,恰如无意识的流露,显得自然而亲切。
明代文人对意识形态的幻觉有自觉,却没有走上批判的道路,而是就送别语境建构朝隐乌托邦,显示了他们助推意识形态幻觉的自觉。根据曼海姆的研究,意识形态内本身有一些不可实现的概念被称作乌托邦。对于阶级成员来说,“乌托邦”取决于人们的视角,与人们的愿望关系密切,或者说是不能实现的愿望。表现在想象的时间或空间中。文化史学者将发生于空间的愿望称为乌托邦。这些意愿本质上是一种组织原则,规范着人们体验时间的方式,处理事件的方式,群体的愿望、目的、渴求都可以直接被理解,所以,愿望也是乌托邦思想的形式,指向具体的思想、行为、感觉、内在关联,是思想的结构。[9]对于参与送别雅集的官员来说,朝隐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祝愿。祝愿设定了虚化的情境,朝隐本是意指实践,包含丰富的图式符号,但祝愿的虚化情境为其限定了想象性的空间。又因为送别祝愿的实施在物理层面上以书画赠送来实现,书画的意指内涵建基于想象性的空间中,所以,朝隐祝愿的能指合并为书画表征,在艺术语言中建构了一个文化乌托邦。这个乌托邦的呈现是朝隐文化符号与意指结构正在发挥作用。所以,从根本上说,送别雅集就是一个文化意识形态机构(ISA),⑤马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机器之一种,参见《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分类,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其内在动力是意识形态控制力。但这并不是说,此处的文化意识形态是完全虚构的,相反,朝隐作为曾经的体验和可能的经历,有充分的现实基础,只是由于赵友同和龙霓不是赫赫有名之人,①赵友同虽然受到姚广孝举荐治理水患,但朝廷派遣官员中没有他的名字,仅在夏原吉《忠靖集》中有《至日述怀简袁少卿赵御医》,提到同行治理水患的事情。可知此次治理水患,赵友同不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也难以称为重臣。夏原吉治理期间,布衣徒步,日夜经营,盛暑出,不张盖,日与役夫同甘苦,虽有题咏,也是扁舟单车,多感慨、客诉之言,恐怕难有联欢之乐。可以想象,赵友同作为陪同治水之人,应该也难以真正逍遥林下。夏原吉题咏、述怀之作《至日述怀简袁少卿赵御医》、《白茅港》,可见夏原吉《忠靖集》,四库全书第1240册,第523,529页。据单国强考证,龙霓到浙江任上治理浙江水事,因得罪刘瑾,不久就被罢官,寓居湖州,与刘麟等人号称“湖南五隐”,也算不得功成名就。(参见《吴伟词林雅集图卷考析》,第87-89页。)也没有特殊的功勋,弱化了朝隐实践的可能性。由弱化反观送别人的言行,恰好暴露了文人助推意识形态扩展的特殊处境。这正是为何中国文人没有像西方知识分子一样超越并批判意识形态的深层原因。众所周知,西方知识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处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语境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革命力量变成了社会霸权的助推者,知识分子是独立于资产阶级的批判者,目的在于揭示虚假性,寻求革命的力量。明代文人是统治参与者,秉持明哲保身的处世观,在政治上受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他们负有责任推行表征国家意识形态的生活方式。作为合谋者,目的在于使用策略保全政治地位。所以,他们是政治文艺文本的修辞使用者,创造了图式化的乌托邦,如《词林雅集图》中人物风度翩翩,举止娴雅,正是明人向往的西园高士风采,这与所到地浙江文化韵味融合,成为未来朝隐风采的想象性表达。这些自觉制造的艺术幻觉,恰是文人游离于朝廷与林下的重要策略,具有特别的象征性。
五、结语
送别雅集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送别文化,形成了以抒写离愁为主的送别文艺。明代京官送别雅集却引入朝隐观念,注重颂扬人物的政绩和才能,突破了送别雅集书写模式。笔者通过研究认为,明代京官送别雅集隶属于明代官员塑造朝隐意识形态的建构进程。由于送别雅集中出行人并不是功勋显赫的政治要人,也不一定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朝隐观念,所以,送别雅集的朝隐建构尤其显示了京官朝隐意识形态建构的虚化特性。送行人也深谙这种祝愿的模糊性,自觉将朝隐阐释定位成纯粹的文本祝愿,在诗画结合的想象性时空中,营造了一个乌托邦的文本,发挥祝词的能指之悦。这一方面暴露了明代京官雅集建构意识形态的游戏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深谙政治艺术的修辞性。从娱乐与为政的矛盾与统一来说,明人在诗画结合的艺术中,找到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交汇的关键点,也理清了二者复杂的依存关系,是明人解决为政与娱乐之矛盾的新途径。反过来,也引起后人思考,他们所颂扬的国家恩惠和人物的杰出才能,都处于政治话语中,与经过传统的修身养性获得的成果具有一定的差异。这必然引起人们对这类修辞文本的有效性进行思考,提醒研究者关注艺术文本的政治文化维度。
[1]石守谦:《雨余春树》与明代中期送别图[A].风格与世变[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3-245.
[2]《图像、文本和意识形态》对西园雅集图式类型的归纳[J].天府新论,2013(5):125-130.
[3]贡布里希,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艺术与错觉——图像再现的心理学研究[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126-127;134.
[4]罗兰·巴特.李幼蒸,写作的零度[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92-94.
[5]《凤城饯咏图》高得旸题诗[A].“台湾故宫博物院”.故宫书画图录(第6册)[C].台北:“台湾故宫博物院”.46.
[6]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幽灵[A].齐泽克.方杰,图绘意识形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0-38.
[7]罗兰·巴特,李幼蒸,叙事结构分析导论[A].符号学的历险[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88-92.
[8]EAGLETON TERRY.Ideology:an Introduction[M].UK:Verso,1991.45;44.
[9]卡尔·曼海姆,黎鸣,李书.琴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00-214.
G02
A
1002-3240(2017)04-0149-07
2016-10-11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宋代美学范畴研究(15BZW030);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项目:明代雅集图的视觉文化研究(16Q168)阶段性研究成果
张高元(1982-),女,文学博士,湖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图像修辞学,明代绘画史。
[责任编校:阳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