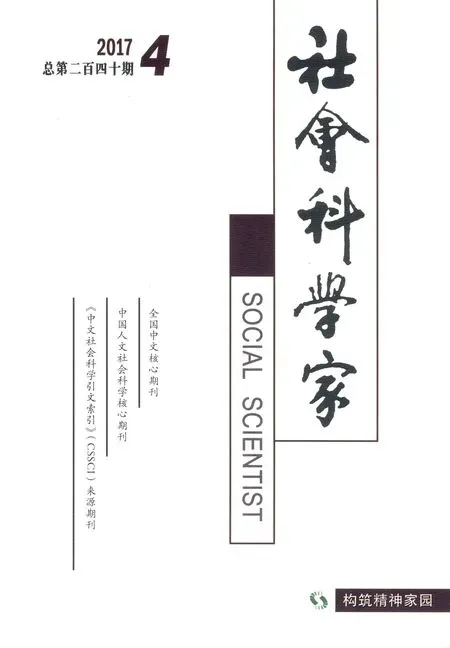超循环:生态美育的生发
秦初生
(1.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2.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育系,广西 桂林 541001)
超循环:生态美育的生发
秦初生1,2
(1.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2.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育系,广西 桂林 541001)
美育是一个历史概念和范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并在发展变化中不断丰富着其内涵和意义,进行着范式的转变和螺旋性的发展,形成超循环的生发特性。美育在其历史性和逻辑性的发展中,依次经历了原始生存性生态美育、古代伦理性的依生美育、近代取得独立地位的竞生美育、现代向生存性复归的共生美育,之后螺旋性地回归和发展到当代整生性的生态美育,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理论体系也呈现出不同的结构模式以及整体变更的超循环态势。
生态美育;依生;竞生;共生;整生
一、问题的提出
美育是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种教育实践,它的历史几乎同人类文明的历史同样悠久。正如人类的发展历史一样,美育的生发、生长历程也是一部不断自我超越的进化史。原始社会时期,美育与原始先民的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紧密融合在一起,具有生态美育的原型,到了古代社会,由于艺术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以艺术教育为中心的美育相应地与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相分离,并具有鲜明的伦理性特征,到了近代,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并列,在教育中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到了现当代,随着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美学的兴起,美育又走向和回归到与人们的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紧密融合。美育的生发和螺旋性回归显示了其超循环的发展历程。在自然和社会领域,超循环有着普遍的适应性,是生态基本规律。作为超循环理论的创立者,艾根认为:“一个催化的超循环,是一个其中的自催化或自复制单元通过循环连接而联系起来的系统。”“在自复制循环之间的耦合必定形成一种重叠的循环,于是只有整个系统才像一个超循环。”[1]在袁鼎生教授看来,超循环是“圈形系统中的各部分以及整体,产生周期性变化与旋升。”[2](前言)既肯定了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圈形运进的超循环的过程,又明确指出了这个过程中既会产生周期性的变化,也会有理论的更新和范式的转变,产生螺旋式的上升。范式是库恩提出的理论,他认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3]即范式就是当某一形态的科学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所形成一定的公认的由若干概念、定律构成的较完备的理论体系。这某一形态范式的发展过程中,会逐渐暴露出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于是,以突破该范式局限性的新形态的科学得到酝酿,并由某位或某些杰出的学者提出了一套挑战旧有范式的科学的新方法与理论的科学体系,并在丰富与深化中成为该科学发展的主流时,科学就发生新一轮的“范式转换”。每一轮范式的转换都是一次芳林新叶催陈叶般的超越过程。本文以超循环理论为视角,同时借鉴库恩的范式理论,把美育的历史发展历程概括为:经历了原始生存性的生态美育、古代伦理性的依生美育、近代取得独立地位的竞生美育、现代向生存性复归的共生性美育,之后螺旋性地回归和发展到当代整生性的生态美育,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理论体系也呈现出不同的结构模式以及整体变更的超循环态势。
二、超循环:美育的历史演进及生态美育的系统生成
(一)原始生存性生态美育
原始生存性美育可以说是生态美育的“原型”。在原始社会,人们认识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弱,生产力水平低,教育未能成为独立的社会实践活动,艺术也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审美形态,因而作为教育有机组成部分的美育,也只能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日常生活中进行。原始先民的认知活动、生产活动和艺术审美活动都处于一种未分化的原始混沌阶段。生产劳动过程也就成了艺术的展演和表现过程,美育的实施过程。因此,原始社会中审美和审美教育是直接服务于生产劳动,是了实践功利目的。另一方面,原始社会的宗教魔法中的艺术活动既是育美的,也是间接地服务于生产的。原始歌舞是原始部族祭礼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了原始先民巫术和图腾崇拜的原始宗教意识,也表达了原始先民渴望通过图腾、歌舞求得本部族生产和繁衍昌盛的意愿。
由此,作为教育有机组成部分的原始社会的美育,是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实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由于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认识能力有限,人类是依于、合于自然的,因而人与自然和谐为主旨、指向生产和生活实践功利目的的生存性美育是这个时期美育的基本特征。原始先民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实践中进行随机性的旨在于促进生产和生活的“互动式”美育或自我美育,在劳动及闲暇时间里进行美的共同创作、共同欣赏,共同接受美的熏陶和化育的美育。这种与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结合,没有明确和固定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身份区别的美育,也没有限定接受美育年龄段而是伴随人一生的美育,正是当今大众美育和终身美育的主要特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原始先民的美育活动与生存性生态活动结合,覆盖了人生全程全域,实现了美育的原始生态化,是原型意义上的生态美育。但由于原始社会生产水平低下,教育及美育实践的内容均较为简单、贫乏,也无法形成美育理论的自觉,为自发、自为性美育阶段。同时由于缺乏纯粹艺术作基础而未能秉承纯粹艺术的精神,缺乏科学技术的支撑而未能深含生态规律,因而这时期的生态美育存在着艺术量不足和质不高的特征。这种原型意义的生态美育,只能为当代的生态美育提供了原始、古朴的范型。
(二)古代伦理性的依生美育
进入古代社会,人类进入农业文明阶段,由于社会发展和生产力水平提高,学校教育产生,艺术也从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获得了相对独立地位。人类不再需要审美直接为认知活动、实践活动服务了,于是审美关系和审美教育获得了相对独立性,审美关系也不再是直接和物质功利关系相结合,于是,以艺术教育为基础和核心的美育也从生产活动和生存活动中分离出来了。虽然在古代中西方都还没有“美育”或“审美教育”这一概念,但文学、音乐等艺术对于人们德行培养、智能发展和情感陶冶的作用已经普遍为人们所认识。于是人们用“艺术教育”、“音乐教育”来表述美育。在西方,古希腊的教育中有缪斯教育,即艺术教育。在欧洲的学校,其教育的内容为“七艺”: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其中的“音乐”即为艺术教育。在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内容“六艺”中的“乐”即艺术教育,“书”也包含着艺术教育。
古代社会阶段的美育虽然不再需要直接为认知活动、生产实践活动服务,获得了相对独立性,但却又依附上了伦理道德教育。如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认为“《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要求艺术教育必须为培养有德行“仁人”服务,在《论语·泰伯》中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要求把“诗教”,即美育,作为育人的起始性环节和使人走向完善的标志性阶段和终极性境界。荀子在《乐记·乐论》中也说:“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美善相乐。”,强调音乐等艺术作品对人的陶冶、教化作用。汉代的《毛诗序》也提出:“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易风俗”进一步阐发了美善相乐的思想。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也强调艺术教育的出发点应该是“对于国家和人生都有效用”,并对音乐的美育作用特别青睐,认为“音乐教育比其他教育都重要得多……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的最深处。”[4]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和美育同城邦的长治久安和人生的终极目是紧密联系的,并提出关于悲剧的“净化”理论,认为悲剧“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净化)。”[5]通过这种“净化”来培养人的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精神品格。
(三)近代取得独立地位的竞生性美育
到了近代社会,人类进入工业文明阶段,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和普及,但也带来了工具理性的泛滥、人的物化、人性的分裂等严重后果。人们意识到美育在促进人的人格发展和人性的完善中有着其他教育无法替代的独特的功能和作用,于是美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得到了普遍的关注和重视。一些大教育家、思想家纷纷对美育及其作用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法国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卢梭反对腐朽、虚伪的封建艺术,认为“一切真正的美的典型都是存在在大自然中的。”[5]提出了“回到自然”的自然主义美育思想,认为儿童只有远离城市,远离封建社会中腐朽的上流社会的恶劣环境,到纯朴的乡村和美丽的大自然中欣赏美、感受美,才能养成对美好事物的兴敏和爱好,成为个性天然、身心和谐的“自然人”。被称为“教育学之父”的赫尔巴特在他的《普通教育学》中把人们的兴趣分为六类,其中一类即为“审美的兴趣”。德国诗人、美学家席勒于1795年撰写出版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美育专著《美育书简》中首次提出“美育”概念,明确提出“有促进健康的教育,有促进认识的教育,有促进道德的教育,还有促进鉴赏力和美的教育。”[6]强调了美育在系统教育中的独立地位和作用,并说:“想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再没有其他的途径。”[6]认为工业社会造成了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分裂,美育的使命就是促进人的感性与理性和谐,从而成为审美的人,人性完整的人。
在中国,率先提出和倡导美育的独立地位和独立价值的人是王国维,他首次把美育和德智体育相提并论,认为由德育、智育、美育组成的“心育”“三者并行逐渐达到真美善的理想,又加上体育,便成为完全之人物。”[7]并倡导美育的独立价值,以解决国民的精神性趣味的匮乏问题。近代杰出的教育家蔡元培则更进一步倡导和推进美育的独立地位和价值,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并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四)现代社会向生存性复归的共生性美育
到了现代社会,美育发展为现代向生存性复归的共生性美育,即美育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紧密结合,与真、善、益、宜相生相长,相竞共赢。共生是指在生态系统和生态结构中,各种事物既相互生发又相互制约,相互平等,互为主体,在对生耦合里达成动态平衡的生态关系与规律。现代社会,随着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和普及,终身教育理念深入人心。教育由过去的精英教育向教育大众化迈进。教育与生产劳动、日常生活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使美育也致力于实现人们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的转化与融合。如杜威提出了“艺术即经验”的重要命题,认为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经验是人类审美经验的源泉,认为要“把经验当作艺术,而把艺术当作是不断地导向所完成和所享受的意义的自然的过程和自然的材料”[8]杜威把艺术归结为经验,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线和阻隔,实现了日常经验向审美经验的转化,使生活走向了艺术,也使艺术走向了生活,为人们实现“艺术生活化”奠定了理论基础。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非常关注和强调美育与人的日常生活和实践结合,认为“假如在学习与劳动旁边,跟它们一起走的不是美——第三种最重要的教育成分,那来学习也好,劳动也好,都会行而不远。”[9]法兰克福学派的赫伯特·马尔库塞基于消费异化的观点,认为发达的工业社会对消费的操纵成为新的控制和压抑人的方式,使人在物欲横流中丧失了批判和超越的思维,成为无个性与思想的“单向度”的人。为此,需要审美教育介入人们的生活和消费活动中,“只有在美的享受中,才能摆脱既有社会对于身心的束缚,才能够完全处于解放的自由之中。”[10]
现代向生存性复归的共生性美育可以说是美育前几个发展形态的综合发展和辩证统一。一方面,共生性美育承继和发展了生存性美育的与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相结合特征,承继和发展了依生性美育的美善相生特征,承继和发展了竞生性美育的坚持美育独立地位的特征。另一方面,共生性美育依据其理论的哲学基础——主体间性的哲学思想和方法,在坚持美育独立地位的同时,使美育与德育、智育,美育活动与其他生态活动的互为主体、相互平等的地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使各部分相生互发,耦合对生并进,并在耦合并进中共生新的质,从而实现了美育前几个发展形态的综合和辩证统一。
(五)当代整生性生态美育
到了当代,人类进入生态文明社会,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生态和谐为主旨。于是,生态文明背景下的美育发展到整生性生态美育形态。即美育作为生态系统整体的有机部分,在与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中系统生存、统生成、系统生长,显现真善美益宜价值整生的格局。当代社会,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理念深入人心,由此推进了教育大众化、美育大众化的步伐,促使美育由阶段性美育向着终生美育转变。另一方面,由于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枯竭和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造成全球性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危机,这催生了致力于改善和美化人生和世界的生态美育。我国学者丁永祥提出了“实施以生态原则为基础,把生态原则上升到审美原则,把生态学、美学、教育学有机结合,重在进行生态观、生态审美观、生存观的生态美育的主张。”[11]这是一种美育生态化的理念和呼唤。袁鼎生教授则明确指出“生态美育的全部意义是生态审美培育,是培育美生人类和美生世界,是培育自然美生场”[12]袁教授所建构的生态美育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基础,以整生论为视角的生态美育,既关注到了人的审美化生存——诗意栖居,又关注到了绿色美生世界的造就。
整生性生态美育,是从共生性生态美育发展而来的,它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超循环为特征和形式的美育。整生是共生方法的发展,强调系统内各种事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网络关联和系统整生。周期性的渐变是超循环的本质特征和要求,生态美育结构的每一次圈走,并不是简单机械地回归到原始的形态,而是各生态位和整体都会较之前一次圈行,形成“似又不似”的递进性渐变,从而螺旋式地提升整体量和质,“似又不似”是超循环结构周期性变化的特性。因此,整生性生态美育是对前面美育形态的正、反、合的辩证发展,是历史空的历史中和与共时空的逻辑中和,是超循环发展。正,是指整生性的生态美育承接了生存性生态美育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紧密联系与融合,贯穿人生始终的特点,承接了依生性美育的美善相生的特点,承接了竞生性美育的保持美育独立性的特点。反,是指它超越了生存性生态美育中美育丧失自身独特性的局限性,超越了依生性美育的依附性,超越了竞生性美育的精英美育和艺术美育的局限。合,是对之前各形态美育的生态中和,即在对之前各形态美育优良质的吸纳、对其局限性的扬弃中超循环地整体生成“似又不似”的新质。因此,整生性生态美育不是简单的线性的对生存性生态美育的“回归”,而是超越性的非线性的回归。在这一超循环中,有对之前美育形态的内容和形式的承续,偏于“似”,形成循环,有对之前美育形态内容和形式的摒弃和创新,偏于“不似”,形成超越。后一生态位较之前一生态位,是中和性的再造,是动态中和,非线性生长。
综上,美育在其历史性和逻辑性合一的超循环的发展轨迹中,在范式的转换中,经历了原始生存性的生态美育、古代伦理性的依生美育、近代取得独立地位的竞生美育、现代向生存性复归的共生性美育后,到了当代,以生态哲学和整生论理论为基础,有了以观照审美人生和审美世界的整生性生态美育的系统生成。
[1](德)艾根,舒斯特尔,曾国屏.超循环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2]袁鼎生.超循环:生态方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3](美)库恩,金吾伦.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5]李天道.西方美育思想简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德)席勒,徐恒醇.美育书简[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7]姚全兴.中国现代美育思想述评[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
[8](美)杜威,高建平.艺术即经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9](苏)苏霍姆林斯基,肖勇.教育的艺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10](德)赫伯特·马尔库塞,刘继.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11]丁永祥,李新生.生态美育[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
[12]袁鼎生.整生论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B83-0
A
1002-3240(2017)04-0133-04
2017-01-01
本文为2015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批准号:15FSH005)、2015年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项目(项目批准号:2015JGA280)的阶段性成果。
秦初生(1968-),广西临桂人,广西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主要从事美育、生态美育研究。
[责任编校:赵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