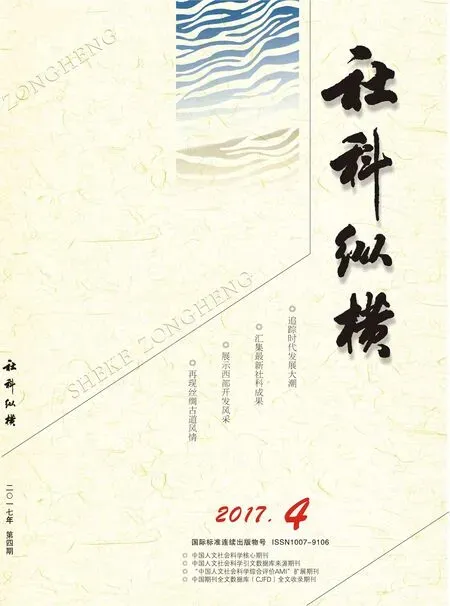南海海洋民俗文化嬗变:历程、特点及成因
——以海南潭门为例
刘士祥 朱兵艳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外语与旅游系 海南琼海 571400)
南海海洋民俗文化嬗变:历程、特点及成因
——以海南潭门为例
刘士祥 朱兵艳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外语与旅游系 海南琼海 571400)
海南潭门渔民是世界历史上唯一连续开发南海的特有群体。自宋元开始,潭门渔民自编自用南海《更路簿》扬帆起航到过西沙、中沙、南沙辛勤耕耘自己的“祖宗海”。自宋元至今,潭门渔民的“耕海”历程酝酿了独具地域特色的热带海洋民俗文化。以海南潭门为切入点,研究南海海洋民俗文化嬗变的历程,分析其特点及成因,对丰富南海海洋多元民俗文化,促进潭门海洋民俗文化对外传播与合作交流,增强潭门海洋民俗文化“软实力”,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南海海洋民俗文化 嬗变历程 海南潭门 特点及成因
潭门镇,地处海南省琼海市东部沿海,东面环海,南邻博鳌镇,西接嘉积镇,北连长坡镇,行政区域面积为89.5平方公里,人口约2.9万人,辖14个村委会,220个村民小组。清人符栋对“会同八景”之一“大海澄潭”(今潭门港)有诗赞曰:“静对澄潭相远映,山明海净画图中”。2004年,潭门港被国家农业部定为一级渔港,是海南岛通往南沙群岛最近的港口之一;2008年6月,潭门镇、文昌渔民自编自用的南海航道《更路簿》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2009年,潭门中心渔港被国家农业部定为一级渔港,成为琼海市唯一国家级中心渔港;2010年8月,首届南海传统文化节在潭门中心渔港举行;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潭门镇考察;2013年8月,专家评审通过《琼海市潭门南海风情小镇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将潭门镇定位为“千年渔港、南海之门”;2015年8月,首届“赶海节”在潭门镇举行,活动当天共吸引了全国各地8万名群众参加赶海;2015年11月,国家南海博物馆建设启动仪式在潭门镇举行,2017年将投入使用;2016年9月,更路簿研究中心在海南大学成立,聚焦潭门等地的南海《更路簿》研究;2016年10月,潭门入选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
一、海洋民俗文化研究综述
海洋民俗文化,是指人类受海洋影响而形成的敬畏海洋和利用海洋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及行为准则。具体而言,就是沿海的人们由于受海洋广阔、宽宏、潮汐、风暴、神秘、流通等特性的影响而衍生的人文特性和精神,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形成的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处世方式[1](P9)。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山东、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香港等地,聚焦海洋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传承,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民俗文化相关性,海洋民俗文化对经济发展、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影响,海洋民俗体育文化等。
海南的海域面积达200万平方公里,但人文研究匮乏,海南既不是海洋经济大省也不是海洋文化强省[2](P10)。海南海洋民俗文化研究归纳如下:
(一)相关论文数量相对较少,研究广度与深度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聚焦:海南海洋民俗文化介绍、海洋民间信仰与祭海民俗、海洋文化发展问题与策略、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开发、陆地与海洋民俗文化关系、海南疍民相关研究、海洋文化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南社会变迁、海洋民俗文化翻译现状与策略等。
(二)南海海洋民俗文化著作逐渐增多:2008年4月,陈智勇的《海南海洋文化》出版,撰述海南海洋文化发展历程、海洋生活生产习俗、海洋信仰等;2015年8月,周伟民、唐玲玲的《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出版,收集南海《更路簿》版本20余个;2016年7月,海南省委宣传部主持编纂的《南海更路簿——中国人经略祖宗海的历史见证》图书发行仪式在潭门镇草塘村举行……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被广泛认可,系统研究南海海洋民俗文化,对充实“海洋民俗学科”的内容,完善海洋国土研究中人文资源学科建设[3],助力“海洋强国”、“海洋强省”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均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潭门南海海洋民俗文化嬗变、特点及成因
经过近千年的“耕海”历程,潭门民俗文化充满典型的海洋性特征,“靠海吃海”、“以海为田”、“以海为商”的生存法则让潭门人由近海到远洋捕捞,孕育了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海洋民俗文化:
(一)汉唐以前,乐会县(今琼海市)以黎族先民聚居为主,主流文化是黎族文化,为潭门海洋民俗文化奠定基础。
先秦时期,百越族在南海有“善水、作舟”的记载,海南黎族的传统民居“船型屋”技艺保留至今。远古时代,黎族祖先可能乘坐独木舟移居海南。据汉朝史籍记载,汉初在海南岛初置郡县,琼海称玳瑁(海龟科的海洋动物,玳瑁的角质板可制手镯等装饰品或镜框、甲片可入药,已成为濒危物种)县,时属琼崖郡,珠崖郡(今海口市)亦含珍珠之意;当时针对海南渔民征收海洋农产税,主要是珍珠等贵重海产品“逢五纳一”,即渔民捕获五颗珍珠就须缴纳一颗,可选择“中等之货”缴税。汉唐以前,乐会县(今琼海市)以黎族先民聚居为主。《汉书·严助传》记载,古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正德琼台志》(卷二)记载,宋太祖开宝五年(972年)将乐会置于琼州县管辖[4](P32);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将新附的黎峒寨五百一十九,民二万余户从乐会分割出来,另置会同县[4](P34)。以上史料暗示,甚至到元朝,琼海文化仍以黎族文化为主,这应该为琼海潭门的海洋民俗文化奠定了基础。唐《新唐书》(卷四十三)记载:“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行三日,至占不劳山”。[5](P1153)根据韩振华先生考证,文中“九州石”即今文昌“七洲列岛”,“象石”为今“西沙群岛”,而“占不劳山”实为今越南“占婆岛”[6](P30-31)。张朔人据此推测,文昌清澜港、琼海博鳌港及陵水港等在“海上丝绸之路”物资补给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影响着东部地区的经济结构”[7]。直到明代,琼海、文昌等沿海地区仍不宜耕种[8]。唐朝末年,移居琼海的一部分福建、广东等地的渔民及商人远渡重洋,赴国外谋生,被称为“去番”[9](P353)。综上,黎族先民的生活方式、“逢五纳一”的征税方式、贫瘠的土地、官方航道的开通等因素为潭门周边地区“耕海”民俗文化的形成奠定了一定基础。
(二)宋元时期,内地来琼人数急剧增多,南海《更路簿》形成雏形,“以海为田”趋于定势,中原、闽越、岭南民俗文化融合,逐渐孕育地域特色的“潭门海洋民俗文化”。
唐代天宝年间(742-756),进入海南的汉族身份多种,有朝廷命官、贬官谪宦、士族世家、将军士兵等,他们将中原文化带入海南,对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民国《海南岛志·人民》描述:“琼东之民朴逊而安土,乐会之民朴野而有礼。”[10](P125)明正德《琼台志·风俗》记载:“琼筦古在荒服之表,历汉及唐,至宣宗朝,文化始洽。”儒学在海南广泛传播,促进了海南民俗文化的迅速发展[11]。唐代中后期,马六甲海峡—海南南部水域—福建泉州航线船只往来有助于增进沿海人们对南海水域海流的认识;元代,人们对南海的地理形势了解渐多[7]。航海知识及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亦为内地来琼移民奠定了技术基础。宋元时期,海南的汉族移民主要来自湖广、闽南地区,岭南民俗文化、闽越民俗文化随之而行,如海神妈祖信仰等,对当地生产、生活影响颇深。据家谱考证,琼海汉族先祖大多来自福建莆田,但受到中原、闽越、岭南等多元民俗文化的影响[9](P10-12)。笔者推测,元代末年以前,潭门周边地区海洋民俗文化大致等同于渔民在大海讨生活过程中的感性经验积的积累;元末明初,更多的海南渔民冒险到南海捕捞,开始认识南海,驾驶船只、记录潮汛、辨别季风及洋流、识别暗礁等感性经验逐渐升华,南海《更路簿》形成雏形[8]。但在感性经验向理性知识升华过程中,浩瀚的大海、丰富的海产、陌生的环境、恶劣的天气等让渔民对南海爱恨交加,对潭门渔民生产、生活及信仰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官方海上丝绸之路及民间远洋捕捞的推进,潭门周边地区“以海为田”的格局趋于定势,中原、闽越、岭南民俗文化逐渐融合,地域特色的“潭门海洋民俗文化”逐渐孕育。
(三)明清时期,内外交流频繁;南海《更路簿》普遍用于导航,潭门“以海为商”初成规模;南海海洋民俗文化空前繁荣,民间海神信仰与祭海仪式臻于完善。
1405至1433年28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必经南海,曾访问东南亚、印度洋沿岸、红海及非洲东海岸国家与地区,内外交流频繁,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官方及民间对南海的认识。明朝唐胄编纂的《正德琼台志》(卷五、卷六)及欧阳璨的《万历琼州府志》(卷三)记载,会同的“冯家港”、乐会的“博敖港”地位重要,可供商船停泊,这都有利于促进潭门、文昌等地借鉴吸收中外文化[7]。据《清史稿》(卷一○、二三、四○、四二、四三、四四)记载,清初,台风、水灾、雨雹、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不断,人们食不果腹、流离失所,沿海居民“靠海吃海”成为必然选择之一[12](P467-474)。乾隆《会同县志·潮汐》(天文志卷一)记载:“会同诸港,潮候皆从乎月。若朔望前后潮大,上下弦前后潮小;‘二至’前后潮大,‘二分’前后潮小;夏至潮大于昼,冬至潮大于夜。晴则望南而吼,人以阴晴之验。”[13](P18)以上足以证明,当地沿海群众应该比较熟悉大海潮汐规律,这为当地渔业生产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清《嘉庆会同县志·堤港埠》(地理志卷二)记载:“港门埠近斗牛,太平都。县治八景之一有‘太海澄潭’,即其处也。”[14](P272)该史料可管窥当时潭门港地形独特,风光旖旎,地理位置重要,应为来往人群聚集地之一。据《琼海县志》记载:“明代,潭门草塘埠一带渔民,常运载西沙、南沙群岛捕捞的海鲜品和贝壳到南洋销售,有少数人随船散居于东南亚各地谋生。”[15](P696)然而,清《嘉庆会同县志·堤港埠》(地理志卷二)记载,“惟东南一带,下至潭门,上至冯家,洋面浩瀚,为海匪渊薮……自乾隆五十年来,贼势愈炽……滨海地方日夜皇皇,奔走不宁,甚受其害……至嘉庆十五年,两广总督百岭遣人招抚……自是海滨始获平安。”[14](P272-273)以上史料暗示,“潭门”港至“冯家”港曾经是官船、商船必经之地,这为琼海潭门“以海为商”提供可能,亦为琼海潭门等地孕育空前繁荣的海洋民俗文化奠定了基础。根据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道光《万州志》记载:“今海外诸国入贡道路,有昔由广东而今由福建、广西省,有径由广东省会者,近均不由琼州”,张朔人梳理得知,由于倭寇、海盗原因,至迟在明代正德年间(1505-1522)之后,南海诸国进贡不再以琼州为中转[7]。但是,无论是康熙三十六年的《广东通志》、雍正九年的《广东通志》、道光二十一年的《琼州府志》、光绪《崖州志》,还是民国时期的《感恩县志》,都有千里长沙(今西沙群岛)、万里石塘(今南沙群岛)的记载,并将之归于琼州府管辖范围[16](P308-309)。宋元时期,墟市多设在城内,明代则设在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据记载,全岛共计一百二十一个较大的墟市,其中会同六个、乐会三个;另据查证发现,康熙五十年,适逢“康乾盛世”之际,乐会县每丁平均占地亩数仅十一,为海南全岛人均最低[17](P133-134)。据此推测,倭寇横行、海盗骚扰、农业耕地面积较少、官方不再借道琼州等因素,迫使部分潭门等地沿海渔民不得不另寻它路,开展远洋捕捞,以避开骚扰、谋取营生,这为南海《更路簿》的完善与普及提供了无限可能。为了祈求航海安全与家人健康,沿海民间海神信仰更加多元,如妈祖、108兄弟公、南海龙王、三江晶信夫人、水尾圣娘、船神等,祭海仪式较为普遍且臻于完善。
(四)近现代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拉开帷幕,移居东南亚的沿海渔民显著增多,海洋民俗文化在夹缝中延续,曲折中求发展。
据《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志六·征榷条》记载,咸丰八年(1858年),复定《英约》:“牛庄、台湾、邓州、潮州、琼州等口,均准开埠通商。”[12]随着海口开埠通商,出洋谋生的群众从琼海东部地区逐渐遍及琼海各乡村[15](P484)。民国时期《海南岛志·人民》描述:“琼东……其民富冒险,务进取,南洋各岛多其足迹。”[10]自19世纪60年代年马六甲太平琼州会馆、槟城琼州会馆建立,尤其是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数万琼海、文昌人移居马来半岛,他们朴逊有识、敢于冒险、奋发图强的性格及内外交流的实践有利于传承并充实潭门的海洋民俗文化。然而,1939年,4月15日,日军攻陷琼东大路墟,下午攻陷嘉积镇;次日上午,日军海陆空三军在乐会县博鳌镇珠塘湾强行登陆,下午进入县城,琼东、乐会大部分沦陷;至1941年底,日军在海南环岛沿海及内陆地区共设360个军事地点,其中,琼东、乐会地区的嘉积为大据点;日军在琼东、乐会地区犯下滔天罪行,烧毁民房2882间、渔船130艘[18](P499-515)。潭门周边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海洋民俗文化在夹缝中延续,曲折中缓慢发展。
(五)新中国成立后,陆地与海洋民俗相互影响,陆地民俗的海洋性特征突出,潭门海洋民俗文化趋于多元;海洋民俗文化的形式、内容及功能正发生变化,由单一向复合演变。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秩序稳定、造船技术省级、航海技术发展、国家政策支持等因素,海南潭门渔民赴南海远洋捕捞更为频繁,渔获更加丰富多样,海产品捕捞、运输、加工、批发、销售等渠道畅通,“亦耕亦渔亦商”的生产生活方式让潭门陆地民俗与海洋民俗相互影响,赋予了潭门陆地民俗更多的海洋性特征[19]。例如,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亦是海南渔家的“平安节”。是日,博鳌、潭门沿海渔民去博鳌玉带滩的“圣公石”,置“三牲”祭石,以求家人平安,该习俗仍延续至今;中午过后,成群结队的人赴海边“洗龙水”(即海里游泳),海滩上人山人海,蔚为壮观。当地人普遍认为,屈原投江后变成了“龙神”,端午节当天的水即为“龙水”,“洗龙水”可以得到“龙神”的保护,保证一年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农历七月十五日,道教称中元节,佛教称为盂兰节,俗称“鬼节”,海南沿海群众有祭海神、“放海灯”习俗。元宵之夜,琼海沿海渔乡“鲤鱼灯闹春”是展现海洋民俗文化的一道风景线,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明朝,历经600余年至今仍常盛不衰。
2009年底,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经国务院批准上升为国家战略,海南的经济社会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为了展现原汁原味的潭门渔民传统民俗、传承南海航道更路簿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力打造特色特色旅游经济文化、宣传潭门渔民勇闯南海的创业精神和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爱国主义精神,潭门镇2010年首次举办南海传统文化节,至今已成功举办七届;2015年8月1日,潭门举办首届赶海节,引入节多项涉海民俗活动,当天共吸引全国各地8万名群众;2016年该活动升级为赶海季,吸引大批海内外游客。无论是南海传统文化节还是赶海节,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民间传统出海祭海仪式,该海洋民俗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随着琼海“就地城镇化”、“全域5A景区建设”推进,该仪式不仅是传统的出海祭海仪式,亦逐渐成为潭门镇展现南海民俗文化、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宣传海南渔民敢闯敢干的精神和国家领土完整的平台,潭门海洋民俗文化的形式、内容及功能正逐渐由单一向复合演变。另一方面,自西汉至今,南海珍贵海产品或海洋工艺品形式与功能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目前,潭门各类贝类工艺品商店已达430余家,成为国内最大的贝类工艺品加工生产交易中心之一。以砗磲为例,曾被用作钱币、清代六品官员的象征、佛教七宝之一,与珍珠、玛瑙、珊瑚一样,被誉为四大有机宝石,但现在主要用于加工海洋工艺品,起到装饰、美化、保健等功能。同样,南海珍珠在封建社会主要用于“实物”缴税,几乎属“官宦专有”,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但现在已根据特定需要深加工,被普遍用于装饰、美容、保健、医药等领域,其最初的功能基本消失。
三、结语
中国南海民俗文化是中国海洋民俗文化的最突出、最典型的代表,潭门等地的海洋民俗文化是中国特色的海洋民俗文化的具体体现。南海是中国最大的海域,潭门渔民成为南海“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活动”的自主开发者。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深挖潭门的海洋民俗文化,对促进海洋民俗文化内外交流、保护与传承南海传统民俗文化、实践“海洋强省”及“海洋强国”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均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戴胜德.中国南海海洋文化传[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3:9.
[2]陈智勇.海南海洋文化[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10.
[3]詹兴文,邢植朝,邓章扬.论民俗学的学科建构与海洋民俗文化研究的发展[J].南海学刊,2016(2).
[4]唐胄.正德琼台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5]欧阳修.新唐书:卷四十三[M].北京:中国书局,1975.
[6]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M].上海:东方出版社,1988.
[7]张朔人.海上丝绸之路变迁与海南社会发展[J].南海学刊,2015(1).
[8]周伟民,唐玲玲.南海“更路簿”的文化意义和价值[J].新东方,2015(5).
[9]梁明江.琼海文化述论[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
[10]陈铭枢,曾蹇.海南岛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125.
[11]符和积.海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构成、发展与特性[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4).
[12]洪寿祥,周伟民.二十五史中的海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13]于煌等.乾隆会同县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18.
[14]陈述芹等.嘉庆会同县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15]甘先琼.琼海县志[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5.
[16]唐玲玲,周伟民.海南史要览[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308-309.
[17]杨德春.海南岛古代简史[M].琼海:琼海市图书馆藏,1982:133-134.
[18]林日举.海南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499-515.
[19]刘士祥,朱兵艳.海南民俗文化的海洋性特征探讨[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K890
A
1007-9106(2017)04-0143-05
*本文为海南省201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就地城镇化进程中潭门的海洋民俗文化保护与传承”[HNSK(ZC)16-22];海南省教育厅2016年度“‘一带一路’背景下南海海洋文化发掘、保护与传播——以海南潭门为例”(Hnky2016-68)。
刘士祥,男,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语言与跨文化交际等;朱兵艳,女,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语言与跨文化交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