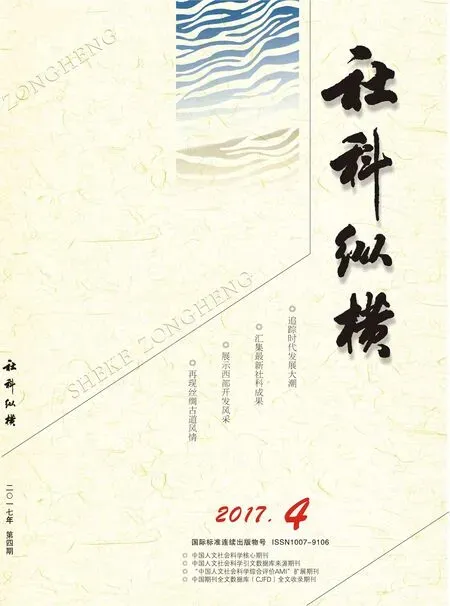论王家卫电影的主题风格
白玉红
(郑州师范学院 河南郑州 450044)
论王家卫电影的主题风格
白玉红
(郑州师范学院 河南郑州 450044)
作为华语影坛大师级的导演,王家卫电影保持着一以贯之的风格化特点,即通过独特的影像语言展现出现代都市中人们的高度抽象化的生存状态:挣扎、逃避、漂泊、孤独,充满不能回避的宿命感的荒谬世界。其电影中所表现的共同主题是以“人的身份”和“人与人的关系”为逻辑起点构建起的完整严密的框架体系,这些主题在其不同作品中的反复出现,在时间轴上形成一条纵向演进的发展轨迹。
主题 系统结构 演变
王家卫凭借着其极端风格化的视觉影像、富有后现代意味的表述方式和对都市人群精神气质的敏锐把握成为香港乃至整个华语影坛最杰出的代表。他用自己独特个性的音像组合方式、颓废暧昧的虚无主义情调成功地建构了一种独特的“王家卫式”的电影美学。他也因此跻身世界一流导演的行列。
纵观王家卫的一系列作品,不难发现,王家卫在多部电影中重复着相似的一套母题:无根与漂泊、追寻与绝望、时间与记忆、疏离与拒避、热情与自由、单恋与错爱……这些母题中各关键词之间还有着紧密的关联并形成了空间上的树型结构系统框架,这个框架的全貌几乎在他每一部作品中都得以完整地呈现,从而构成了其鲜明的主题风格。
一
还是要从“香港”说起。虽然王家卫强调他是不用电影谈政治的,但香港人从未对政治减少过关注,因此香港电影才更具香港特色。
“九七大限”带来的对未来的不安与焦虑是困扰了不止一代人的话题,而中国政府对1997年之后“五十年不变”的承诺虽然暂时缓解了他们焦虑的程度但却永远延长了这一代人焦虑的时间,王家卫这一代人的一生将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度过。因此无论“九七”时代还是“后九七”时代,他们的心理状态是一致的。王家卫的第一部作品就诞生于1988年,作品的主题就被“九七情结”紧紧缠绕。并由此引出了王家卫的两大根本命题:一是人的身份,一是人与人的关系。
王家卫作品的核心内容,围绕的命题就只有这两个。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有浓厚香港特色的艺术经典,就是由于他表现香港人在“九七”与“后九七”时代香港人面对的头等难题:人的身份和关系;而王家卫作品之所以具备如此浓厚的全球性话语色彩,并成为各国人毫无文化差异感和理解障碍顺利接受的作品,也正是由于他讨论了全人类至少是所有生活于后工业都市文明之下的人类都共同面临的两大难题:人的身份和关系。
“主体性的零散化”是不少“后现代”电影的显著特质。在王家卫的影片中,许多人物既没有社会背景,也没有身份内容。《阿飞正传》中的人物,如旭仔就因为身份的不确定而备受困惑。其他人如美美、丽珍都祈求可以得到一个巩固的居所,这些都不失为“九七”前过渡期间香港人心态的反照,对于过去无法定位,对将来又无所适从。王家卫所设计的丽珍,亦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她原本住在澳门表姐的家里,后来因为表姐结婚而失去了栖身之处。她想重新建立一个家的梦想,又因为旭仔把她抛弃而幻破。“家”代表了一个稳定的个体,一个令人拥有归属感的地方,而这正是过渡期间,香港人所缺乏的安稳感觉。
二
王家卫并未直接在电影中提出“人的身份与关系”这个核心命题,而是紧紧围绕这个核心,展开了一系列具体母题的讨论。
无根性,是王家卫电影的一大特征。由于处于主体或母体文化边沿地带,所以不论从历史或文化认知上,香港都因长期受到殖民统治而产生了无法定位的流离、无根感觉,可以说是无根文化。当香港人开始自我认同的思考的时候,先天的身份难题使他们永远套上了“无根感”的枷锁,在都市里被无止境地流放。“无根感”是导致身份难题的直接原因又是具体外化。“寻根”的追问被宿命般地展开。港人这种身份的失落决不是一个回归就可以解决的,历史的永恒缺失和对于回归后前景的种种疑虑将永远延续这种失落。这种无根感和寻根的渴望在《阿飞正传》里是体现得最直接也是最集中的,“有一种小鸟,它可以飞到任何地方,但是,它没有脚,所以,它不可以停留,一旦停下来,它就要死了……”,“无脚鸟”的寓言和旭仔越洋寻母失败的故事立刻成了港人自况的经典。“无根感”的根本现实决定了后工业时代都市个体与都市群体的存在状态。
在“无根感”驱使下的寻根,与寻根的必然结果,引出了“追寻与失望”这一母题。王家卫作品中的人物往往非常偏执地追寻一个目标,可是最终的结果却往往是永恒失落。
长期的殖民统治和与母体文化的脱节使香港人从历史和文化上都产生了无法定位的疏离感和无根感。王家卫的电影根植于香港,展示了过渡期间香港人寻找历史、文化和身位位置的整体心理状态,浸透着现代社会个人生活的无根感与寻求感。
王家卫还擅长用人与人的关系来表现香港人的生存现状。它包括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关系状况和主要的交流方式。其电影中的人物都似乎生活在绝对的孤独之中,他们用毫无逻辑关系的行为和语言,在自己的世界里苦苦挣扎,也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出路。
王家卫电影中所展示的人与人相处于世的普遍关系状况是冷漠与疏离。所有人处都于游荡状态,谁跟谁的关系都是过客,人与人之间都无真情,异乎寻常地冷漠。由冷漠而疏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遥不可及,空间变得十分荒诞,“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就是因为这0.01公分的疏离,代号223的何志武和金发的女毒贩林青霞、代号663的梁朝伟和王菲,才是独立的人。《东邪西毒》的意象是最好的比喻,“人物固守的那个空间是他们内心世界的外化,在茫茫大漠上,各居一方的侠士自占一片自己的黄土蓝天。”[1]
因为人与人隔膜的存在,于是有了交流上的大问题:“拒绝与被拒”和“看与被看”。
首先是“拒绝与被拒”。王家卫在1995年金马奖影展特刊的发言中说:连续五部戏下来,发现自己一直在说的,无非就是里面的一种拒绝,害怕被拒绝,以及被拒绝之后的反应,……而每次发生拒绝,其实都是双方的。旭仔的生母拒绝认亲,于是旭仔也拒绝露面;西毒对情人的不理不睬,最终导致了她嫁给他的哥哥的报复;黎明拒绝了李嘉欣,招致结果是被后者杀害。无论谁先拒绝谁,其结果都是两败俱伤。每个人都不会因拒绝别人而获胜,而每个人都一定会因为拒绝与被拒而受伤。因此每个人都害怕拒绝。
其次是“看与被看”。避免被拒绝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不要采取主动,只看而不说。“看与被看”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主要交流形式,而其实质就是“零交流”。王家卫的每部电影几乎都有旁白,大量的旁白,因为人物们要把看来的世界讲给自己听,而不是别人。旁白的人往往不止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因为每个人都在看人,也都在被看。
害怕被拒绝和只看不说的结果,只能导致人与人之间隔膜的加深和距离的扩大,导致更加冷漠与疏离,更加隔绝与孤独,恶性循环,最终,全体陷入原罪式的孤独的深渊。
三
虽然纵观起来,王家卫电影母题之间形成具有逻辑性的结构体系,但也并不是说从一开始他的思考就是辩证周密的、系统就是完备的。事实上,他的思考是逐渐成熟的,随着对各个母题的视角的不断变换和探讨的逐渐深入,对每次母题系统的变调与重组,它的母题系统逐步完善,并衍生、演化、发展。
处女作《旺角卡门》(台湾名《热血男儿》)的诞生时间已是1988年,距离“九七”只剩下十年。大限之前的港人心态已经十分典型,埋下了他的两大根本命题的伏笔。关于人的身份与关系的思考已经开始了。刘德华饰演的主人公,身为黑社会老大,本应是一个令普通人感到有几分传奇几分浪漫的社会角色,王家卫却为他安排了缺乏起伏升跌的江湖生活,常常单枪匹马,长期处于暴戾、苦闷及无聊的状态,并不断重复着这样的生活直到死亡。影片在对人的身份与生活境况的对比中,因强烈的身份异化感而发出了嘲弄的声音。对生命虚无的体验已经刻骨铭心。
1990年拍摄的《阿飞正传》使母题框架基本成型。“传说中有一种鸟儿是没有脚的,只能一直飞啊飞,飞累了就在风里睡觉,这种鸟一生中落地只有一次,那便是他死的时候。”“无脚鸟”的传说,一个言简意赅的象征,一个高度浪漫化了的流浪者形象,当然这里的流浪者指的不仅是身体的流浪,更是心灵的无依。仅此一个意象已说尽了关于“无根感”的所有母题。生父和生母的缺失,使主人公旭仔的身份成了永远的困惑,并使他体验到了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失落感,这是一种根本的永恒性的失落,任何获取都无法弥补。这比上一部一个黑社会老大混得不够像黑社会老大的身份误差要严重得多。这种失落总在不断地将旭仔推向终极追问与根性寻找的路途。而菲律宾寻母的失败,使这个无脚鸟唯一有可能落地的机会成了泡影,使它原罪式的失落更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无论是阿飞旭仔对工作和人生奋斗的毫无兴趣,还是不负责任地和一个个女人短暂相爱,以及他最经典的对着镜子漫不经心地起舞,都是这种人生态度的典型外化。
《东邪西毒》代表着王家卫的电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母题系统得以更深入仔细地展开和讨论,特别是人与人的关系。比之上一部,人物间的隔膜在加剧,人物通常是在独语。
爱情关系是这部戏里的重点。错爱的关系网变得空前复杂,但并不因为是单恋而是:拒绝。明明是两情相悦,仍然因为害怕对方拒绝而先拒绝对方,以最无中生有的方式扼杀掉一段本应完美的感情。最典型的就是西毒欧阳锋与后来成为他嫂子的女人的爱情。爱情中的替代变得十分普遍,无论是欧阳锋和慕容嫣夜间把对方假想成自己的梦中人,还是盲剑客与欧阳锋对着那个贫女不约而同地都想起自己的所爱。真正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例子几乎绝迹。
由此可以看到,随着王家卫对自己一系列母题的思考的逐渐深入,各个母题之间已经有缝合、交错的辩证关系,逻辑关联性越来越强。
《重庆森林》和《堕落天使》,到这个阶段叙事已经完全摆脱了单线模式,断裂成了几个互不相干的事件。这两部电影也是以讨论人与人的关系为重点的,但与《东邪西毒》不同的是,拒绝与被拒绝已不是最残酷的,最可怕的是人的关系更加隔绝,每个人似乎都处在一个单独的世界,永远无法和任何人交流。故事都变得非常极端,最佳的拍档也完全不见面,父与子也无法交流沟通,人与人的交流要借助机器:点唱机、DV机。
《春光乍泄》,王家卫的新变初露端倪。从身份看,角色的选取更加独具匠心。“同志关系”确立了其典型的城市边缘人的定位,——法律不再明令禁止但又未被伦理普遍认可的灰色地带。而更巧妙的是略去了人的性别差异,这与以往人物身份弱化的惯例一脉相承并且将之发挥到了极致。角色的身份定位鲜明地标注了与其紧密相联的人生状态:漂泊游荡的个体、只活在当下的价值观、醉生梦死的生活态度。
因自由而漂泊,因漂泊而选择,因选择的举棋不定而彷徨,因彷徨而不专一,因不专一而多心,因多心而隔膜,因隔膜而孤独。自由的必然结果就是孤独。可以说这是王家卫把人的身份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所有母题整合得最好的一部。而后黎耀辉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以前一直以为,我和何宝荣很不一样,现在才知道,其实寂寞的时候,每个人都一样。”两类人最后也变成了一类人,到此为止,王家卫的电影世界里的人物第一次不需要再做任何分类,芸芸众生,已经完全相同了。
从《阿飞正传》到《春光乍泄》就是一个完整的圆。《春光乍泄》影片最后黎耀辉的旁白直接交代出了一个重要事实:“终于知道为什么小张可以开心的走来走去,因为他知道这世界上终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对“无根感”的困惑从所有象征比喻暗示中解脱出来做了一次直白的点破,仿佛是对“无脚鸟”人生难题的明确答复。影片结尾处更是盖上了时间戳:邓小平逝世的历史事件。——王家卫完成了他的自问自答之后,“九七”也刚好到站了。
《花样年华》是一部怀旧片,形式更趋向平和,带上了明显中年人的气息。从人的身份上看,最明显的变化是,人变得没有了自由。人到中年,有家有室,道德的枷锁如狭窄弄堂的冰冷墙壁,人在幽闭的空间故作体面地穿行。爱情关系奇特而又富于象征意义,苏丽珍的丈夫和周慕云的太太发生了私通,剩下的两个受害者苏丽珍和周慕云在彼此惺惺相惜之后发现已经爱上对方。但人的身份决定人的关系,周慕云和苏丽珍注定不敢踏出那一步,外在道德的尺度已经深入他们内心,就算没有外人发觉,但自己心里却说“我们决不会像他们一样”。是自己不齿越轨。
《2046》是王家卫对自己几乎全部作品从形式到内容的大总结。从形式上看,它串联了《阿飞正传》和《花样年华》的年代和人物,启用了《东邪西毒》的强大阵容和一个主角串联多个人物故事的散点透视式的叙事,并继续着他一直未曾说尽的人的身份和人的关系的话题。《2046》的重点仍在于拒绝与被拒绝,记忆与遗忘,错爱与替代。正是用爱情中的替代关系,《2046》串联了以往的故事。日本人替代了周慕云,白玲和女机器人甲分别替代了咪咪,王靖雯和女机器人乙替代了重庆森林里的阿菲,浪荡鼓手替代了旭仔,以及巩利所饰的苏丽珍替代了张曼玉所饰的苏丽珍。在不断的身份替代的旋涡里,主人公在不同的情人之间扮演着多情浪子角色却永远走不出感情负伤的阴影。记忆的交织中,过去现在将来又融为一体,循环往复。“2046不只是一个酒店的物理空间,在这个充满味道和颜色的狭窄房间中,……在周慕云的转化过程中,他把2046变成一个寻找失落记忆的想象场所。2046的复杂意义变成了记忆、爱情和主体性的确立点。”[2]影片的最后梁朝伟有一个旁白:“每个去2046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一些失落的记忆,因为在2046没有任何事情会改变,没有人知道这是否是真的,因为曾经去过那里的人,都没有回来,除了我,因为我需要改变。”
王家卫电影的基本主题,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对“香港经验”的艺术表达,体现出他对香港社会充满虚无感、异化感和荒诞感的人生体验。
[1]杨德建.这一坛“醉生梦死”的酒——王家卫的香港故事[A].《香港电影》80年[C].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203-214.
[2]张凤麟.2046:王家卫的映画世界[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165-169.
J905
A
1007-9106(2017)04-0121-04
白玉红(1966—),男,郑州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