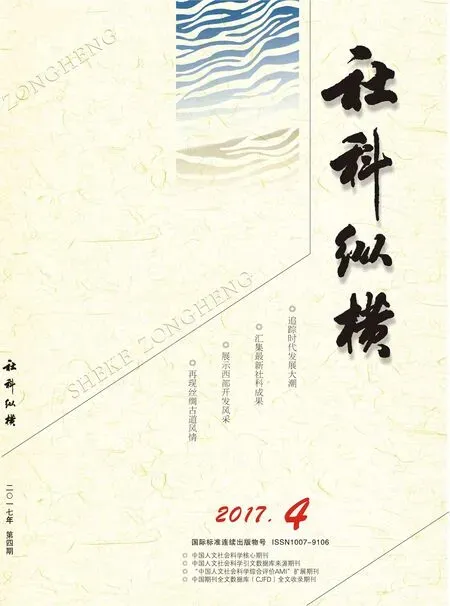天主教激进神学的探讨
——伊格尔顿神学转向的背景研究
刘静
(绥化学院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绥化 152061)
·哲学研究·
天主教激进神学的探讨
——伊格尔顿神学转向的背景研究
刘静
(绥化学院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绥化 152061)
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等著作中,鲜明地表现出了对真理、道德、上帝、死亡、邪恶等问题的关注,他后来在《神圣的恐怖》中自称为形而上学或神学转向或回归。伊格尔顿的神学转向了20世纪60年代的天主教左派政治时期,即以《斜向》为载体所进行的天主教与马克思主义对话,近年来的形而上学或神学探讨体现了对《斜向》时期所开辟的话题的深化和扩展。
天主教左派 激进神学 神学转向
20世纪60年代世俗乐观主义在整个西方世界持续高涨。帝国主义的衰落、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新的政治秩序的建立仿佛就在眼前。约翰二十三世(1958—1963年任教皇)敏锐地意识到了教会与世界的隔离,他下令召开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讨论教会如何“跟上时代”的问题。1962年10月至1965年12月,罗马天主教会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召开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245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主教都聚集在罗马讨论天主教会未来的发展。前后历时三年多,经过反复讨论、辩论甚至争吵,通过了四个宪章、九个法令、三个宣言,共计十六份文件。这是当代罗马天主教会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思想运动、宗教和政治事件,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发表文件最多、涉及范围最广,为教会带来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革。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成为基督教神学发展史上的分水岭。约翰二十三世面向全世界和全人类发表了教皇通谕《世上和平》,向全体天主教会和全世界宣布,罗马天主教会为“适应时代”,决定“对教会实行革新”,“教会向全世界开放”,教会要“与所有一切有良好愿望的人对话”。
罗马天主教会的对话对象也包括无神论唯物主义者,即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这是罗马天主教会反共策略的重大转变。“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后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任何人只要能拼出席勒伯的名字就马上会被加到位于奈梅亨的一些晦涩的神学杂志的编委会上。”[1]1961—1970年间,受梵蒂冈大公会议所带来的宗教改革浪潮的冲击,伊格尔顿主要和剑桥的天主教派别多明我会过从甚密,在劳伦斯·布莱特和赫伯特·麦凯布的启示下,他终于认识到天主教徒和左派身份完全能够统一,这不啻为一次思想大解放。伊格尔顿积极地从事天主教左派政治活动,伊格尔顿在探讨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激进主义可能性的时候,指出了19世纪基督教社会思想中三种错误的观念。其中之一是自由主义的矛盾。基督教会和工人阶级关系的历史反映了一个深层的矛盾,可以看做是英国社会普遍自由主义危机的特别强化。19世纪,教会急切地想和工人阶级进行真正的接触,但是其背后的动机是模棱两可的:一部分是出于对民众福利的真诚关心和渴望;一部分是对自身机制福利和生存的焦虑。这两种因素,正面和负面的情感,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教会对工人阶级一种含糊的态度。而负面的情绪经常作用于正面关注的结果是使同情被异化了,这样恶性循环的后果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呼吁开始变形。自我关注最终凸显在每一次斗争中。教会既不能真正地进行自我批评,也不能洞察工人阶级。整个教会对工人阶级态度上的矛盾,也反映出在教育、文化、民主等方面自由主义的两难困境。教会缺少支持,它必须要赢得支持来证明自身作为福音机构存在的必要。但是矛盾就在于它所急切需要的支持就来自于与它所要证实的价值、观念、思想相悖的阶级。“需要他们的支持但是却抵制他们意识形态的要求,把他们作为一种数量而不是质量的力量。”[2]
可以看出,伊格尔顿这个时期对天主教激进主义已经有了比较客观的看法。天主教左派中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辩论始于迈克尔·达米特在《新黑衣修士》上所发表的《教会有多腐败》(1965),伊格尔顿批评了达米特的改良主义倾向,达米特随后进行了回应,得到了伯纳德·波尔贡齐(Bernard Bergonzi)的支持,伊格尔顿进而回复了波尔贡齐。这是60年代天主教左派著名的论战之一。最终雷蒙德·威廉斯评论维科尔的《文化和神学》时正式提出自由vs激进的问题(1966),维科尔随后的《新左派:基督徒和不可知论者》(1967),继续抵抗任何的定义。最重要的文章是伊格尔顿的《政治和神圣的》(Politicsand the Sacred,1968),在这篇文章中伊格尔顿提出关于作为一个基督徒对社会主义信仰所带来的不同,试图表明基督教神学在一个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深度,并不是一个多余的范畴。
1973年,卡利从教会学的视角,将当今的天主教神学分为四类:(1)激进神学和激进教会学;(2)激进神学和温和教会学;(3)自由主义神学和温和教会学;(4)保守神学和保守教会学。[3]卡利指出伊格尔顿、布莱恩·维科尔和《斜向》小组等天主教左派当属于第一个类别,一种激进的神学和激进的教会学的范畴。
卡利认为这个范畴的天主教神学思想家的激进神学根源于对于传统天主教神学问题的拒绝,对教会官方领导权完整性失去信任以及对变化的文化环境需要重新进行宗教反思的认同,总之,他们的事业根源于一种基本的人文主义,正如罗斯玛丽·卢塞尔所说,激进神学并不是对基督、天国感兴趣,而主要是作为人的表达。因此这种激进神学经常被其他传统天主教神学家加之以偶像破坏的罪名。
伊格尔顿和维科尔等人所领导的《斜向》小组在激进神学的实践中走得足够远,成为60年代独特的政治和文化现象。在这个时期欧洲天主教和马克思主义重要的对话中,多名我教会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康拉德·派普勒、劳伦斯·布莱特、赫伯特·麦凯布,都分别对这种对话做出了贡献。三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事件的促成者(enablers),也就是鼓励别人直接参与,而自己并不发表见解。[4]派普勒作为斯波德屋的主管,为会议提供场地,布莱特是组织者,联系众人并且把他们的讨论付梓,包括发表在《斜向》上。在对话的后期,时任《新黑衣修士》主编的麦凯布在刊物上开辟了专门篇幅供人们自由讨论,自己也发表一些简练的编者按。三人从不同角度对60年代天主教左派论战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劳伦斯·布莱特对伊格尔顿天主教左派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劳伦斯·布莱特是多明我会的修士,十二月小组的发起者和核心人物。如果说布莱特起到了方向上的引领作用,那么麦凯布起到的就是思想的定型作用。伊格尔顿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神学的许多观点都直接来源于麦凯布。
赫伯特·麦凯布,1926年生于约克郡一个爱尔兰的移民家庭。许多爱尔兰天主教徒都蕴含着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情感,麦凯布在正统天主教和左翼政治交织的环境之中长大。1949年大学毕业后,麦凯布加入了多明我会,天主教中的政治左派。当时,法国和比利时的多明我会修士正在进行“工人牧师”运动,青年教士们脱下衣领和教士服到码头和工厂和工人们一起劳作。这场运动在1953年被梵蒂冈所镇压。英国的多明我会修士自来就有激进的传统,他们把梵蒂冈对工人牧师运动和其他进步活动的压制看做是与法西斯主义无异,这些左翼天主教徒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20世纪60年代早期,天主教马克思主义者聚集在牛津大学的黑衣修士厅和斯波德屋,劳伦斯·布莱特主持关于阶级斗争和有关“新神学”(nouvellethéologie)的研讨会。“新的天主教左派在马克思和耶稣,社会主义和福音,革命和回归本源之间安排了一个协定。”[5]
麦凯布1955年受聘教职之后在纽卡斯尔一个教区做了三年牧师,1958年,麦凯布被任命为德拉萨学院(DeLa Salle College)的牧师,伊格尔顿曾经就读的学校。也是在这个时期,麦凯布积极参与斯波德屋的活动。1964年,他的第一部著作《新创造》(The New Creation)发表。麦凯布坚持正统的天主教神学,他对政治的评论都是在对神学问题的思考中出现的。伊格尔顿称麦凯布是一个纯正的托马斯传统主义者。1968年《法律、爱与语言》(Law,Loveand Language)是一部将阿奎那、维特根斯坦、马克思相结合的著作。麦凯布并没有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乐于接受天主教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号。
麦凯布对伊格尔顿的影响深远,“没有和赫伯特·麦凯布长久的友谊,我根本就不会成为今天的我。”[6]2001年麦凯布逝世,他的一些重要的著作在这之后出版,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
麦凯布认为基督教是更进一步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只是讨论劳动导致的异化,基督面对的则既有今生也有死后世界的异化。与麦凯布不同,伊格尔顿导师威廉斯对天主教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持保留的态度。他肯定了天主教左派对共同体的概念的基督教角度的阐释,特别是能够公开地讨论共同体核心的友爱关系,这是其他传统通常不能做到的。另外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也是严厉的,完全令人信服的。预示着激进天主教独立地进行强有力的社会批评的开始,而不再依附于建立在其他分离的术语之上的批评。但是威廉斯认为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两者之间并没有相容的可能性,两者的话语,例如救赎和解放、堕落和异化不可能是一种概念上的并立或甚至是同一,这种努力不过是对可以理解的、可以忍受和个人化的冲突的一种修辞的解决,他不相信这样的天主教徒还是社会主义者。不过,从另外的角度,威廉斯认为天主教徒和社会主义者面对都是共同的危机,可以取得共识,并肩作战。
这一阶段伊格尔顿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者,《斜向》的发起人劳伦斯·布莱特从基督教的视角阐释了革命问题。他认为英国天主教会正处在英国精英统治阶层的控制之下,问题的根源在于基督徒,不管是出自何种派别,都在执行一种错误的基督的教义,加强并支持了这种社会政治机构。布莱特总结了四种这种错误的体现,基要主义、超自然主义、个人主义和精神主义。他主张对圣经的历史性解读,即圣经表现为为改变人类境况的一种新的基督的激进革命。因此正确地解读基督教就在于对它的历史根源的理解,这也是激进主义的真正的含义。“如果能够认识到基督教是是一场革命解放运动而不是一种抽象的教义信仰,也就是宗教的本质是改变人类的实际境况,而且只有通过政治手段才是可行的,那么就可以看到,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在广义上并不是不相容的。”[7]
从两种信仰的统一性出发,《斜向》从一开始就把天主教徒和政治左派的身份紧紧连接在一起,提出了两个主要的文化与共同体的理论主张:一是天主教会在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的复兴,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活动在世界舞台上会具有重要的作用。《斜向》讨论的话题有:怎样把文化分析与政治分析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评和实践行动的充分性;第三世界的革命与西方民主革命的关系;基督教末世论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关系;分析和批评如何变成有效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伊格尔顿作为天主教左派时期的重要的活动就是借助《斜向》促成天主教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
《斜向》致力的读者对象是天主教中产阶级。英国在这之前并没有一个天主教自由主义中产阶级,左派运动对其发展起了很大的助力。这种开创新的神学的可能性对任何的无产阶级天主教意识都太遥远以至于不能做出值得的努力。因此这场运动,必然是一场学术性的,面对的更多是一个完全没有成形成组织的读者群体。《斜向》从一开始就有陷入虚假的伦理约定的危险,既是政治的又是道德的。《斜向》与《新左派评论》有些相似:两者读者的模糊性增加了不加批判的、兼收并蓄的风格和一种自我绝缘的解释学。《斜向》的社会主义理想本质上就是英国世俗新左派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接受了“基督教洗礼”。他们并不太关注政治层面的战略或策略,并没有严肃地思考对于所谈论的革命什么是最中心的问题。《斜向》从最初就显现出来的一大弱点,即词语的替换说明了行动的缺失。[8]
伊格尔顿对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有着清醒的认识。70年代初伊格尔顿承认基督教“永恒革命”或“革命的革命”理论,即革命的基督教在革命的社会之中是具有永久批判的、否定的、超越作用的实践,它象征着一个朝向超越了任何社会现状的终极的社会秩序(天国)的永恒的驱动力。但是他不认为这是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所在,对马克思主义来说革命并不是顶点,而是一个不停的冲突发展、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社会状况的开端。忘记这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斯大林主义。
伊格尔顿认为基督教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模糊的。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对基督教来说必须朝向天国(赫伯特),那么具体的实践是指什么呢?是使用或限制暴力的伦理观点还是提醒人们充分解放还没有实现?伊格尔顿对基督教的革命实践不置可否。他认为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区别不在于革命,而是在于基督教对上帝的天国的信仰,这意味着天国的到来是一定的,而马克思主义除非发展出一套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否则不能够确保人类自由的国度一定会到来。基督徒的信仰使之确信基督的到来,只有通过殉难才能加入天国,因此基督徒比马克思主义者更富有牺牲精神。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未来社会是及其难以确定的,个人之死是一种绝对的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的革命信仰使基督徒成为更好的革命者。[9]在革命的曙光未现的时候,是审时度势还是大无畏的冒险,基督徒更多的是选择了后者。
进入7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左派运动开始衰落。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带来的是上帝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盟的分裂,在《教士身份和列宁主义》(PriesthoodandLeninism)中,伊格尔顿认为天主教牧师应该把自己认同为列宁所称之的革命先锋。伊格尔顿的革命精神借助于信仰得到坦率的体现,但是当梵蒂冈二次大公会议的热潮退去,教会的一系列改革无疾而终,天主教左派活动也随之终结的时候,伊格尔顿所处的境地显得十分艰难,他必须在两种信仰之间做出一个选择,以继续自己的事业。伊格尔顿认为他诚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想看看一个天主教徒在左派的路上能够走多远才会走到边界,实际上,他后来认识到并没有这样的边界。一个人可以既是天主教徒又是左派。“但是这也意味着他在剑桥大学所认识的天主教主义也没有许多其他的优势。这解释了他后来为什么把天主教在他的学术清单上去除了,只留下了文学和政治。”[3]
70年代也标志着伊格尔顿对宗教的幻灭,他不再自称为基督徒。在天主教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归属上,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他此后的批评中,很少见到天主教神学探讨,而是全面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文学分析。他对天主教、神学话题异乎寻常地保持着缄默,从另一方面也显现出早年革命失败的阴影。伊格尔顿本人并不承认曾脱离了神学话题,而认为自己一直保持着对神学伦理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在《理论之后》中以宣言性、纲领性的方式得到了再现和充分的表达。
[1]Eagleton T.Reason,faith,&revolution:reflections on the God debat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2.
[2]Eagleton T.The Roots of the Christian Crisis.Cunningham,Eagleton,Wicker,Redfern and Bright(eds.),1966.
[3]Carey J J.An overview of Catholic theology.Theology Today,1973,30(1):25-41.
[4]W icker B.Justice,Peace and Dom inicans 1216-1999:Viii-Slant,Marxism and the English Dominicans.New Blackfriars,1999,80(944):436.
[5]McCarraher E.Radical,OP.Commonweal,2010,137(17):12.
[6]Eagleton T.Priesthood and Paradox.New Blackfriars,1996,77(906):319.
[7]Corrin J P.The English Catholic New Left and Liberation Theology.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2015:5.
[8]Wall A.'Slant'and the Language of Revolution.New Blackfriars,1975:506-516.
[9]Eagleton T.Faith and Revolution.New Blackfriars,1971,52(611):158-163.
B91
A
1007-9106(2017)04-0072-04
刘静(1978—),女,绥化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西方文论研究。
——《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