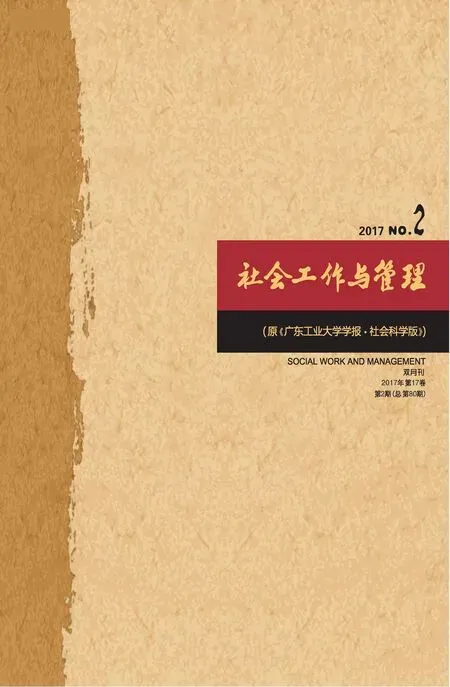化解社区治理中个体化困境的有效途径
李 斌,王镒霏
(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湖南 长沙,410083)
化解社区治理中个体化困境的有效途径
李 斌,王镒霏
(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湖南 长沙,410083)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加速,居民的流动性加快,城乡社区居住空间变动迅速。社区内部居民之间的陌生感难以化解,居民个体化引发的困境日益突出。现有的社区组织(如居委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机构)大多没有认识到以居民之间团结互助为基础的组织化过程的重要性。为化解个体化困境,有效应对即将来临的高龄化浪潮,社区社会组织机构需要着力实施社区居民组织化工程,构建以“助人助他”为理念,组织形式上类似于银行“存储—支付”体系的“跨时空服务提供—跨时空服务提取式的服务传导”式的服务组织体系。在这一组织化建设过程中,社会工作尤其需要在既有提供专业社会服务与角色的基础上,成为建构跨时空服务传递网络系统的主体。
个体化困境;助人助他;组织化;社会工作;服务银行
一、社区治理面临组织化不足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区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城市社区的地理形态发生大规模变迁。因城市宏大规划而引发的社区重组、更生、消失的现象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其次,从社区性质上分析,绝大多数单位制社区已逐步演变为商品房社区。经济逻辑已经成为社区内居民普遍认同的行为逻辑。再次,从社会分层维度看,居住空间阶层化趋势明显,即同一阶层的居民居住在同一社区,不同阶层的居民居住在不同社区。[1]最后,社区内居民的流动性增加,住房易手频率加快,邻居之间的稳定性减少。于是,社区内住房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有人居住自己的房子(独立产权、小产权、集体产权),有人承租他人的住房(直接承租、间接承租)。上述现象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共同加速社区内居民的原子化与碎片化,削减或肢解社区内居民之间的直接联系与时间上的持续性关系。
化解上述困境的有效手段是构建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现代社会组织,让社区组织的持久性存在给社区居民以期待与信心。因为社区组织可以“聚合社区资源,是提高社区治理的手段,增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基本途径,是包容性城市建设的起点”。[2]城乡基层社区一直或多或少有一些组织:有正式的社区组织,如居委会;也有满足居民相关利益需求的社会组织,如业主委员会;还有发挥居民业余兴趣爱好的群众性团体,如老年协会、妇女广场舞协会。近年来,应社会管理创新要求,社会工作机构也逐步进入社区,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支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上述组织机构以及群众团体似乎很难抑制居民原子化、碎片化趋势。原因有三点。
1. 居委会未承担居民群体化、组织化的职责与任务
作为社区组织机构的居委会,其工作范围主要设定在执行党和政府的各项法规政令指示、社区党支部工作、卫生、绿化工作、治安保卫工作、计划生育工作、民政工作、司法调解工作、统战工作、妇联工作、少儿教育工作等。上述这些工作基本没有设置“居民组织化”任务。与滕尼斯意义上的社区包含众多内容尤其强调社会关系及其建构不同[3],在中国城市的行政层面,社区“被设定为我国城市政府为了实现城市区域小型化、管理对象清晰化的目标做出的管理体制选择”[4]。社区成为城市最小行政区划,最小“网格”①。这样的网格管理机构没有被赋予相应职责关注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以及居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建设,更谈不上承担居民组织化职责了。这可以从社区的《社区自治章程》关于社区机构设置职责的规定中得到说明②。在实地调查中笔者发现,各居委会或社区组织工作人员的工作任务大致包括3点:(1)下达上级政府的相关指令,完成政府要求的各项惠民政策,上传本社区政府需要的相关信息;(2)完善本社区物理空间。如解决社区混乱,基础设施不配套,专业物业管理要么欠缺要么变动太快,公共活动场所缺乏,环境恶化等问题;(3)应对逐步显现的难题。如社区居民流动快,人员构成复杂,社会治安差,老年人增加迅速,下岗人员多,困难人员多等难题。
2. 社会组织不承担组织社区居民的职责
在中国行政语境中,社会组织是指在不同级别的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非营利组织。法理上,社会组织并不承担组织社区居民的职责。在走访民政部门发现,类似于志愿者服务、文化传播、残疾人服务、青少年培训等方面的组织比较容易获得注册,注册了的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如调解纠纷、社区巡逻、构建文化、居民自治、和谐督导(拍摄一些不文明行为),发动居民参与社区活动(舞蹈队),使一些癌症病患者娱乐身心,把病人从床上拉起来,把居民从麻将桌上拉下来,参加有意义的社区活动等。社区之间在社会组织建设与发育上存在极大差异:有些社区有多个社会组织。如长沙市雨花区L社区目前有备案的社会组织7个,其中的“H家园”组织相对突出些,他们走家串户,给社区居民经济物质上帮助,开展安抚活动,减少社区居民的失落感。DX社区有登记备案的社会组织8个,他们的服务涉及红白事帮协、居家养老、红袖章志愿者、幸福港湾、老人沙龙、舞蹈队、“四点半课堂”“帮帮团”等。③尽管2000年以后,社会组织发展比较迅速,不过目前还很少有社会组织有意识地将“分散的社区个体重新积聚起来”作为社会组织的主要目标。尽管如此,社区只要有社会组织并且还经常开展活动,其社区粘性度④通常就比较高,居民的满意度也高。在社会科学语境中,社会组织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组织是指人们从事共同活动的所有群体形式,包括氏族、家庭、企业、政府、学校、医院、社会团体等形式。狭义的社区社会组织是“伴随着社区功能逐步完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群众组织形式,是以社区居民为成员,以社区地域为活动范围,以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为目的,由社区成员自发成立或参与,介于社区个体组织(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和居民个体之间的组织”,[5]因此需要将行政语境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科学语境的社会组织关联起来,使其既具有合法性又能够承担起组织社区居民的任务。
3. 社会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不足以承担组织社区居民的职责
截至2015年底,湖南全省社会工作注册机构还不足200家,绝大多数偏僻区县还没有社工机构。[6]尽管一些接受“三区项目”的县已经成立有社工机构,不过其专业化程度仍然不高,他们的运行经费来源方式、从业人员结构、业务范围、工作方法、工作目标都还在摸索之中。⑤与此同时,社会工作专业在大学还没有成为大学生心仪的专业。目前全国民政部门还是采用权宜之计,依靠转化本土人才的方式,即督促社区相关工作人员通过考取社会工作资格证的办法,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在湖南省长沙市调查的社区工作人员中,已经有63.1%的人员参加过社会工作资格证考试,其中有21%的人员取得了助理社会工作师(初级)资格,有12.6%的人员取得社会工作师(中级)资格证。⑥另外,就调查所得以及整理现有文献发现,还没有一个社会工作项目涉及社区居民组织化,即将社区居民组织起来作为社会工作项目在执行。
综上所述,目前基层社区建设的“三社”(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力量自身均不够强大与成熟,其能量还在培育之中。这也许正是“三社”需要联动的原因。[6-8]因此,要提升社区治理水平需要提升社区组织机构之间以及社区居民之间的联动水平与组织化程度。
二、社区治理需要以居民互助为组织化逻辑
为了解决城市社区个体化过度而出现的社区居民原子化问题,以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助性、团结性为核心的“朋友圈”“兴趣群”、志愿者、社会组织等群体形式日益被学界重视,一系列相关研究逐步衍生,如形成“社区效力”“社区能力”“社区粘性”等概念,并迅速成为社区治理研究领域的热词。尽管这些概念均指向积极的社区治理,不过其内涵有各自的独特性。“社区能力”可以综合反映社区居民之间的组织性程度。[9]它由“利益相关者参与社区的能力、评估问题的能力、培育社区领袖的能力、建立或改进组织结构的能力、调动资源的能力、与其他组织和居民建立关系的能力、批判性自省能力、项目战略管理能力以及联结外部机构的能力”构成。[10]“社区粘性”则是指社区居民对所在的社区有归属感、依恋感,社区对居民有吸引力,居民以居住为核心的相关权益能够在社区层面得到保护,权利得到尊重与满足,居民的困境在社区层面可以有效解决,如居民的就医、儿童照看、高龄照护、残疾帮扶等需求能够在社区层面解决。很自然,社区能力、社区效力或社区粘性等的提升是一个综合性工程,不仅需要现有的基层社区组织、社区社会组织以及快速发展的社会工作机构参与,更需要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和付出。因此,社区层面的多方联动(或称“四社联动”)可能是社区层面服务提供与获得的组织性维持的有效策略。多位学者的社区组织化建设实验,比如李强的北京清河实验、沈原的北京大栅栏实验、罗家德的上海嘉定实验、王春光的江苏太仓实验、杨团的山西寨子村实验、蔡禾的广东西部乡贤会实验、李向前的成都金牛区实验、李斌在长沙梅溪湖街道的实验等,正在从多方面探究基层社区的服务组织逻辑以及社区居民的组织化。⑦不过,目前这些实验碰到的共同问题是城市社区居民的组织化建设非常困难,群体性连结很不容易。居民个体化困境所面临的严重后果还没有广泛被社区居民所知晓、理解与警示。于是,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服务型组织体系的建构就面临更多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不少社区还广泛存在政府不支持甚至不允许社会组织建设,绝大多数社区居民参与服务性组织的积极性不高,已经组建起来的社会组织面临资源稀少,居民参与群体活动的兴趣不高,社区能力的重要性被漠视等问题。大多数居民对即将来临的困难不做任何准备,抱着“到哪座山,唱哪支歌”的心态。
正因为社会工作以缓解困难、助人自助为己任,加之所践行的专业化服务,才逐步成为中国政府加强社区治理的有效手段。那么,运用社会工作策略解决社区居民的碎片化问题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其他问题,是依靠培养足够多的社会工作力量分别单个地为每个社区居民提供个案社会工作服务,还是发动社区居民一起参与到形色各异的社会服务中去,以实现他们内部有组织有计划地互助以形成“组织”,进而运用他们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构建温馨的社区呢?我们认为,上述两方面的工作需要共同推进才会有成效。也就是说,社会工作既要承担起既有的专业化服务,又要承担起组织化居民的重任。首先,高校要拓展社会工作人才培养途径,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政府要通过社会工作资格证考试,社会工作实务培训等形式加速现有相关人才向社会工作转轨。类似的努力能够增加社会工作服务量的有效供给。然而完成更多的社会工作服务量,仍然难以抑制因为个体化趋势而增加的个体“无力”与“无助”感。其次,社会工作需要积极推进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提升社区居民的组织性程度,让每个社区居民隶属于某个社区互助组织,贡献自己的资源,同时能够在自己需要的时候通过社区内互助组织获取帮助。
社会工作有两种导向:一是所谓“注重个人困境消除与个人发展”的微观导向,二为“注重社群团结”的宏观导向。[11]中国港台地区及西方国家的主流社会工作以“个人困境免除”导向为主。鉴于中国大陆特定的人文历史环境与现实要求,有学者主张将上述两种存在一定张力的导向结合起来,“社会工作必须在实践中既突出个体位置,又要将塑造个体性作为重建共同体的基础”。[12]如何既凸显个体性以符合市场化工具理性逻辑,又能够构建起有行动能力的社区共同性以抑制孤独无力感,似乎在理论与现实层面都构成了难题。在社区操作层面,希望达成的状态是,社区居民的个体私密空间能够得到尊重与保护,公共空间经由哈贝马斯式的理性讨论[13]后,可以通过居民互助组织建设得到有效构建,进而居民的困难最大程度地在社区层面通过互助组织得以解决。我们认为如果社区社会工作项目围绕上述目标设计、开发与执行,社会工作就需要以社区的组织化为基准,以将社区居民组织起来形成形色各异的互助组织为工作内容。于是,社会工作机构在建设社区居民互助组织的道路上,就需要在三个方面着力。
第一,践行“助人助他”的组织化理念。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理念能够帮助社会工作者在助人的过程“造血”“链接与整合资源”,使受助者能够自力更生,但是它却局限了社会工作的对象范围,容易只注意到困难中的个体;另外还在主观上忽略了案主本身的生产能力,置案主于被动接受的角色。而“助人助他”理念的核心是协助案主提升帮助他人的能力,即社工帮助案主的目的是使案主最终能够再帮助其他的人,置案主于主动角色地位。换言之,社工A(或社区居民A1)帮助B,当B解除困境后再帮助C,C再帮助D,形成助人链条体系,进而实现组织运作,形成人与人之间良好互助关系,建构幸福社会。
第二,实施“跨时空的服务提供与服务提取式传递链条”的组织形式。与学雷锋、志愿服务不同,“跨时空服务提供与服务提取式链条”这一概念借助中国家庭代际反哺“养儿防老”式服务传递关系,即服务提供者不在提供服务后立即获得回报,而是在若干年以后,或到自己年老后的某个时间段才提取自己所需要的“养老照顾”服务量。为了鼓励有能力、有时间提供服务的人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依据等量传递服务原则设计,即自己为他人提供的服务越多,自己在步入困境或年老时可以提取的服务也就越多。“纯”服务量的传递,可以免除货币⑧结算过程中因时间迁移出现的通货膨胀进而导致购买力下降问题,让复杂社会实现实现简单应对,让“以物易物,以服务易服务”成为社区居民组织化的主要逻辑,让不同时段与空间的服务量可以实现等值交换。⑨
第三,构建“银行网络体系”式的社区社工组织体系。为了使“跨时空服务提供与服务提取式链条”这一规划得以广泛实施,需要组建一个类似于银行的网络组织体系。各社区类似的社工服务银行构建起全国性的服务银行体系,服务可以在各银行之间实现转移,以应对流动性社会带来的服务流动的时空问题。让跨时空服务传递的运作方式类似于银行的资金存储与提取形式得以实现组织化运作。社区居民提供服务及其数量需要在专业社工的培训、规划、计划、检查与评估过程中精细地进行,社工将符合要求的服务及服务量记入“服务银行”,[14]并安排相关服务给需要服务的接受者(案主)。对于提供服务的居民来说,其存储与提取是跨时空的;而对于服务银行来说,服务的存储与提取则是同时进行的,作为在服务银行工作的社会工作者来说,匹配服务的存储与提取是其主要的工作。具体的操作规则设计会比较复杂,需要另做大量专题研究。举例说明,如要应对诸如老龄化浪潮带来的高龄长期照顾问题,可以动员60岁至70岁的低龄老年人为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或为行动不方便的人提供服务,社会工作者记录其服务量。给服务提供者的回报就是让他们相信并获得组织保障,当他们步入高龄或行动不方便时,可以到社会工作系统建设好的分布全国的“服务银行”提取他们曾经付出过的等量的服务或照顾。服务银行的运转经费由国家投入解决。一旦出现在服务量的提供与服务量的提取之间存在不对等情况时,可以动用老年人的资金储蓄或财产作为补充支出。
上述互助组织的建设与完善,能够让服务量在时间的流变过程中保持恒定。这一体系能够加强居民之间的团结,增加居民的道德行为,有利于社会信任制度的建设,也能够积极化解个体化困境,增加社区服务所需的人力资源,为应对高龄化社会来临后的养老及照护等一系列问题开辟新路。
三、结语
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传统社会的团结方式依赖于长期稳定形成的血缘、地缘关系,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是“整体性”关系;现代社会以“个体”为特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交换”或者科层制理性规定而形成,建构的更多是“碎片化”的局部关系。法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称前者为“机械团结”,后者为“有机团结”。[15]针对人际关系碎片化变换,现代国家通过诸如行政体系、市场体系、货币体系、教育体系、就业体系、安全体系、保障体系等现代社会设置,让个人从整体意义上脱离于特定群体,游离于差异化明显的组织、群体,而逐渐沦落成“碎片化漂游”的无力感个体。当空间回归到“人的‘存在’,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体验,一种身份认同与情感归依的生成领域以及实现身份认同、产生自我归属感、获取情感归依和本体性安全的场所,一种回归到空间主体的生存的本质性的关注”[16]时,个体的“孤独”与“无力”感可能会朝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要么迅速演变为群体意识,成为群体性体验,突然来临的群体性会使国家结构与社会秩序面临挑战;要么个体走向否定自我之路。布鲁姆曾指出,“正在发生的无数的联合行动……这种联合行动的参与者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处于系统的需要,而是为了参与者的目的”。[17]这意味着,如果整体意义上的社会或社区任由个体性肢解并走向了原子化极端状态,最终无论哪种进路都会形成毁坏性要素。暂时性空间始终时隐时现:有时真实存在,有时虚无缥缈;有时充满游戏和竞争,强者意图维护或强化既有空间秩序,弱者则企图运用“弱者的武器”尽力变动空间秩序,各种策略和行动不断被“创造”,而恒久抵御暂时性、个体性困境则需要走组织化途径。因此,要抑制社区居民的原子化倾向,社区治理就必须以社区居民的组织化为导向,孵化居民互助组织,将居民组织起来,组织居民互相提供服务,用他们自身的力量解决他们自身面临的困境。服务银行网络体系的建构及其内在存储与支付逻辑就是为了回应上述挑战而设置的组织化体系。
马克思和一些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承认“货币是一种社会关系”,是凝汇着人们“集体意向性”的一种制度实在,“一切价值的公分母”“价值的现金化”。然而,正如杰文斯、门格尔、克拉克、马歇尔等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货币值仅仅只指某一时点上以某一时刻所认定的“货币标量”为多少,它既不是指那一币值、财富或经济总量包含多少“抽象劳动”,也不是指那一币值、财富和经济总量代表多少“边际效用”。[18]于是,善于思考的人们就会发现,如果仅仅以货币量(如居民储蓄、各种保险)作为人们养老的支付管道,大量中下阶层居民步入老年前的货币积蓄基本不能支付其年老后的所需服务的货币量。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总量都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迅速增加⑩,这使得居民养老储蓄加养老保险金之和在购买后期服务的能力越来越低。面对这一困境,不少人开始自发地创新养老方式,甚至回归原初社会“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近年来兴起的“抱团养老”■就有纯服务交换的含义。这说明,在老年服务领域,需要非货币化的服务供需途径,实现以“服务时间A”交易“服务时间B”的方式。因此,“服务”的存取既是社区社会组织化的基本需要,也是构建组织化网络的核心。于是乎,社会工作不仅仅要提供“助人自助”“助人助他”式的服务,还需要激励尽可能多的人为了未来所需要的服务量,在现在有时间有精力时贡献自己的服务。精准安排、专业认定与记录居民提供的服务并有效匹配服务者与服务对象也就成为社区治理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与社工机构另一个重要任务。这一重大任务不仅需要社会工作机构自身的组织网络化,以形成“银行网络体系”式的社区组织体系,同时更需要组织所有社区居民参与到社会服务的交换当中去。以服务交换为目的的组织化过程自然也就化解了目前社区治理中广泛存在的个体化、原子化困境。
注释
①所谓网格,就是将城区行政性地划分为一个个的“网格”,使这些网格成为政府管理基层社会的单元。如长沙市各个区均设置有网格化管理系统。
②笔者在2016年实地调研中,从所调研社区取得的《社区自治章程》中规定:社区职责是宣传组织引导居民学习遵守法律,维护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履行义务,美化、净化社区环境,做好社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为社区特殊群体提供社会福利性服务,常住、暂住人员的登记管理工作,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和生活秩序,调节民间纠纷,促进居民家庭和睦,邻里团结。
③⑥笔者在2016年实地调研中,从所调研社区取得相关数据。
④“粘性”原本属于物理学概念,是指“施加于流体的应力和由此产生的变形速率以一定的关系联系起来的流体的一种宏观属性,表现为流体的内摩擦”。后来被运用于网络,“网络粘性”一词“一方面指网站吸引网络用户返回并使之停留在该网站的一种特性,另一方面又是指用户愿意再次访问某网站并延长其停留时间,且愿意有意无意地在该网站持续浏览的一种心理状态”。社区内的“朋友圈”兴趣群体以及各种由居民自己组成的社会组织是衡量社区粘性的基本纬度。(详见巴晶、胡丽娜在《现代管理科学》2012年第5期发表的“虚拟社区粘性对网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一文中的论述。)
⑤数据出自笔者从湖南省民政厅社会工作处获得的内部资料《2015年湖南省社会工作发展总结报告》。社会工作“三区项目”,即在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社会工作人才支持计划的项目。
⑦2016年3月19日至21日参加在清华大学知行楼109举行的第一届“行动—干预社会学(主题:社区实验)”研讨会,获得相关资料。
⑧塞尔哲学式的理解:货币是人类经济活动和交往中一种凝汇着人们集体意向性和“意见约同性”的制度实在。我们最终把货币视作商品与劳务交换、市场运行、经济增长、资源配置和人们生活游戏中体现着人们集体意向性的一种制度建构(a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human intentionality)。(详见韦森在2003年版《经济学如诗》第57~74页中的论述。)
⑧不同时段、空间服务传递在具体精算技术上还需要更复杂的研究、设计、测量与制度设计。
⑨中国货币发行量增长迅速:1952至1957年的增长速度大致在10%左右,1981年至1983年货币增长速度为22%,1994至1998年货币年均增长速度为39%,2002年以后,每年新增货币3万亿以上(详见《中国建国以来货币发行量》中的论述,http://www.360doc.com/ content/10/1117/22/1133289_70280494.shtml)。
⑨“抱团养老”这一概念最先出现在2011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第7版刊载的李增辉《抱团养老就地享福》一文中,是指有一定关联的老年人集中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就养老活动分工合作,各自承担责任与义务,互相服务互相照顾等养老形式。不少媒体判断,“抱团养老”已成新趋势。
[1]李斌.中国城市居住空间阶层化研究[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5-10.
[2]李雪萍,陈艾. 社区组织化:增强社区参与达致社区发展[J]. 贵州社会科学,2013(5):150-155.
[3]TENNIES F. 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7.
[4]王巍. 社区治理精细化转型的实现条件及政策建议[J]. 学术研究,2012(7):51-55.
[5]王名. 社会组织论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
[6]何立军. 深入推进“三社联动”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民政部召开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J].中国民政,2015(20):30-31.
[7]叶南客,陈金城. 我国“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与策略研究[J]. 南京社会科学,2010(12):75-80.
[8]邹鹰, 程激清,陈建平. “三社联动”社会工作专业主体性建构研究——基于江西的经验[J]. 社会工作,2015(6):99-115.
[9]徐延辉,兰林火. 社区能力、社区效能感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能路径研究[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6):131-142.
[10]LABONTE R, LAVERACK G. Capacity building in health promotion, part 1: for whom and for what purpose[J]. Critical public health, 2001, 11 (2): 111-127.
[11]钱宁. 工业社会工作[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4.
[12]江立华,王斌. 个体化时代与我国社会工作的新定位[J]. 社会科学研究,2015(2):124-129.
[13]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M]. 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36.
[14]李斌,王镒霏. 组织化与专业化:中国社会工作的双重演进[J].社会工作,2014(6):3-8.
[15]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8-145.
[16]潘泽泉. 社会、主体性与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8-40.
[17]BLUMER H.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1969: 74-75.
[18]韦森. 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J]. 中国社会科学,2004 (4):61-67.
(文字编辑:徐朝科 责任校对:贾俊兰)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Individualiz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China
LI Bin, WANG Yifei
(Sociology Department,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 China)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spaces have been greatly changed with the New Urbanization Plan in China. Residents are migrating faster than ever, and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are fast becoming unfamiliar. These reasons are deteriorating residents’ individual dilemmas. 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such as residents' committee,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work institutions are not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organizing the residents to help each other when they are in predicaments. In order to solve the individual dilemma and prepare for the coming aging wave, community social workers must organize the dwellers, and develop a kind of institution in which dwellers can help each other, with the ideas of “helping the weak and enabling them to help others”. The logic of the institution should be like the system of bank, but in which the services are deposited and withdrawn instead of money.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need provide professional service in one hand, and build a network system which the human service can inter-exchange across time and space on the other hand.
individual dilemma; helping the weak and enabling them to help others; systematization; social work; service bank
C916
A
1671–623X(2017)02-0052-06
2016-12-08
■ 基金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关系研究”(15ZDA04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居住空间结构化与人口城镇化路径及策略研究”(15ASH007);湖南省智库专项课题“湖南城市化背景下的城乡社区发展研究”(16ZWC24)。
李斌(1963— ),男,汉族,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政策,城乡社区发展。
李斌,王镒霏. 化解社区治理中个体化困境的有效途径[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7,17(2):5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