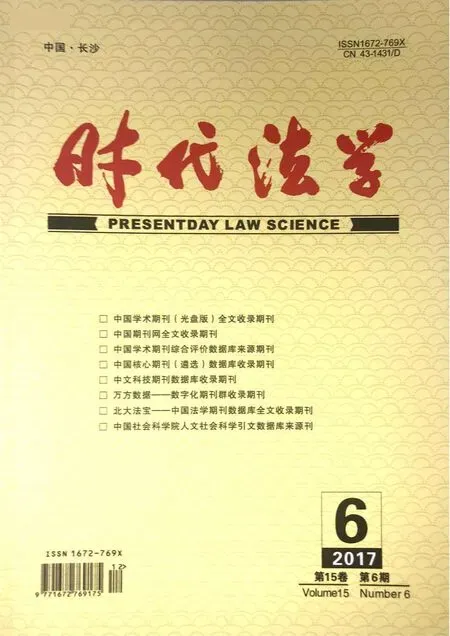《禁止酷刑公约》第3条项下个人来文及其证据问题论析*
李 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2)
《禁止酷刑公约》第3条项下个人来文及其证据问题论析*
李 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2)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依决议开启了人权申诉机制建立和发展的进程,而个人申诉机制则依托国际人权公约得以形成和发展。《禁止酷刑公约》第22条规定了个人来文制度。禁止酷刑委员会所接受和审查的半数来文都涉及第3条项下权利和义务。从来文角度看,有关证据的规则是第3条的核心内容,它规定了委员会证据审查的职责、证明内容和标准以及考察因素范围。从来文审查的实践看,委员会就证明责任、证据真实性以及程序性事宜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逻辑或“先例”。委员会的来文审查致力于寻求保护人权和主权的平衡,其实践丰富着国际人权保护规范,强化着人权执行机制。
禁止酷刑委员会;不推回原则;个人来文;证据问题
关于酷刑的国际法治进程与证据及其规则紧密相关。198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公约》(下称《禁止酷刑公约》或“公约”)*参见联合国大会第39 /46号决议,1984年12月10日。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27条,公约自第20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与联合国秘书长之日起第30天开始生效。公约于1987年6月26日正式生效。。根据公约第1条第1款所含定义,酷刑的客观构成要件是“使…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在现实司法或来文程序中,酷刑所涉“行为”往往属于过去事实的范畴,行为的存在与状态只能依赖相关证据或行为后果来判定。行为所造成的“剧烈疼痛或痛苦”需要以物证、书证、言辞证据、技术鉴定等来加以证明。从未来的角度来看,个人根据潜在的酷刑危险所提出的诉求也必须以符合逻辑且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为基础,《禁止酷刑公约》第3条相关的证据规则主要围绕未来的、个人所面临的、真实的酷刑危险展开。
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17条第1款,公约建立“禁止酷刑委员会”(下称“委员会”)以执行实施公约之职能*具体而言,公约第19~22条分别规定了委员会所执行的缔约国报告制度、调查制度、国家间指控制度以及个人来文制度。。公约第22条规定,委员会有权接受并审查针对宣布承认委员会受理个人来文之权限的缔约国的个人来文,委员会应秘密审议所涉来文并将其意见递交于相关缔约国及个人。基于来文确证之事实,缔约国须承担公约规定的义务,避免将可能面临酷刑危险的人驱逐、遣返或引渡至相关国家*此处为严格意义上的酷刑。如未特指,本文所指“酷刑”不包括其他残忍、不人道待遇。公约第3.2条规定,禁止酷刑委员会应当考察“所有相关因素”,这对证据的全面性和缔约国积极主动履行职责提出了要求。。缔约国履行“不推回”(non-refoulment)*笔者在广义层面上使用此概念,包括公约第3条规定的驱逐、推回和引渡(expel, return/refouler or extradite)。义务以存在“充分理由”为前提,而此等理由须通过缔约方积极、主动的确认加以完成。就公约第3条而言,证据规则关系到酷刑受害者避免再次罹于酷刑、寻求行政或司法程序保护以及获得实质救济的权利。
《禁止酷刑委员会》所建立的个人来文制度是酷刑受害者(或其代理人)与被控实施酷刑的公权力实体(国家或者政府机构)就公约所载之权利与义务进行直接交锋的制度平台,缔约国和个人均会依据自己的逻辑和诉求从各自的“源头”查找并提出证据,并针对对方的证据进行质证和抗辩。个人来文审查过程中,委员会的任务在于依据特定的标准判断证据是否达到要求,以至于国家必须撤回先前针对申诉者所做出的决定或行为。迄今为止,委员会已经处理了多达373项来文,其中做出“裁决”的有282项,而涉及公约第3条项下权利、义务纠纷的又占到大多数,约195项*参见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网站,http://juris.ohchr.org/Search/Results.访问时间:2017年4月5日。。委员会所接受的第3条项下的个人来文虽然事实迥异,对象不同,但委员会有关“证据”的论理却有章可循。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委员会审查来文的方法造成的,即委员会采用类似“遵循先例”的“裁判”方法,对证据的判断因循先前来文所确立或者采纳的规则。对证据规则的论析有助于把握委员会在处理个人来文时的论理逻辑,明确国家在履行禁止酷刑义务过程中应当采取的具体措施,同时,这也会对酷刑受害者权利的有效保护产生一定的启示。
一、国际法层面的个人与人权申诉制度
个人来文(或申诉)制度是国际人权公约赋予遭受特定侵害的个人向公约或附加议定书所设立的机构申请救济的法律制度的总称。一般来讲,个人申诉程序是以《欧洲人权公约》为范本设计的。鉴于申诉程序对国家主权较高的干预程度,人权公约一般采用“来文”(communication)以代替“申诉”(compliant),其目的在于不产生一种有拘束力判决的印象*[奥]曼佛雷·德诺瓦克﹒国际人权制度导论[M].柳文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97.。从国际法角度看,个人来文制度表征个人在国际法层面所秉具的一定程度的行为能力,个人不仅仅是国际法律关系的对象或者后果承受者。传统来讲,除却行为可以归因于国家的外交代表,个人及其行为处于国内法体系的“笼罩”之下,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纵向的权威与服从关系*See Malcolm N. Shaw, International Law (6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6.《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1950)第25条规定,欧洲人权委员会有权接受个人、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团体的申诉。。整体而言,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是间接的,国际法通过对国内法律秩序施加以个人为对象的法律义务来影响个人的利益*对此,凯尔森先生继续评论道:国际法规范大多是不完全规范,它们需要国内规范来完成。See Hans Kelsen, 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State, Anders Wedberg tr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43.。相应地,国际法也被视为原子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复合主义的研究路径被国际法学界引为正典,国家拥有如个人般的自由权力,而个人则几乎完全属于国内法范畴下的概念*立足于国家“原子化”模型的国家主义(statism)认为,国家拥有类似于个人的自主权,政府自然而然地代表着人民,主权无关乎道德性与正当性。See Fernando R. Teson, A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8, pp. 39-43; 静态复合主义之下的国际法禁止对个人权利的考察,人权保护的规范和机制发展一度举步维艰。See Hilary Charlesworth & Jean-Marc Coicaud, Fault Lines of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56-66.。
个人来文制度反映着个人及其权利、义务逐渐被纳入国际法视野的历史性过程。19世纪中期,曾存在有关个人在国际法层面承担责任的动议,但整体而言,国际法仍然排斥个人所扮演的角色,甚至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也是如此。1841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就“麦克劳德案”(The McLeod Case)致函总检察长表示,构成公共权力组成部分并按政府指示行事的个人不应作为私人违法者而被追责,这是文明国家之惯例所支持的一项公法原则*关于“麦克劳德案”及与其相关联的“卡罗琳案”,参见R. Y. Jennings, “The Caroline and McLeod Cas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2, No. 1, 1938, pp. 82-99.,这种思想和思维路径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纳粹依恃主权的遮护和所谓的国内合法性,肆意践踏个人权利,反对暴政、保护人的权利和尊严成为反纳粹力量和同盟国协同行动的道德支撑*See Samuel K. Murumba, “Grappling with a Grotian Moment: Sovereignty and the Quest for a Normative World Order”,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9, 1993, pp. 832-844.。暴政对个人权利和尊严的亵渎震撼着思想界,个人“福祉”与国际问题的密切关系初步显现。诚如学者所言,二战的最初两年,公共讨论中最为闪耀的特征便是思维多样的人们之间所达成的共识,即国家内部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与国际问题密切相关*Julius Stone, “Peace Planning and the Atlantic Charter”, The Australian Quarterly, Vol. 14, No. 2, 1942, p. 17-22.。1941年,《大西洋宪章》(The Atlantic Charter)将个人权利的国内法保障纳入国际秩序(进而也是国际法)视野:个人权利的有效保障被视为国际秩序建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有人(all the men)免于恐惧和匮乏地生活是和平秩序的内在要求*参见《大西洋宪章》第6条。相关措辞为:The two countries “hope to see established a peace which will……afford assurance that all the men in all the lands may live out their lives in freedom from fear and want”.。
国际法对个人权利的规范确认集中体现在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宪章)当中,联合国机构和后续公约所确立的个人来文制度属于对宪章基本权利条款的可操作化发展。宪章将保护个人(human person)基本人权、尊严和价值纳入其宗旨,并将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作为联合国的主要目的之一*《联合国宪章》共有6处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措辞。参见《宪章》序言,第1.3条,第13条,第55条,第62条和第68条。。相对而言,作为国际社会“宪法性文件”的宪章较多地着墨于“共存国际法”所关注的战争、和平与国家间关系问题,个人权利(而非群体权利)的保护机制并未详定于宪章条文,这为后续具体公约从可操作性角度完善国际人权保护法律体系预留了空间*例如,宪章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6处规定中,有4处采用了坚信(faith in)、应当促进(shall promote)等号召性措辞。第62条和第68条属于运行层面的规则,它们分别规定了经社理事会通过建议和设立委员会形式促进人权保护的职权。。从理论上看,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反映了国际法体系规范维度与运行维度的二元分立和时间错位,个人来文制度作为国际人权法之运行维度的重要内容,是人权规范可操作性得以具备并逐步强化的制度表现*规范体系指基于政策或价值而产生的广为接纳的行为标准,其在不同领域表现为或强或弱的行为调整;运行体系则指国际法所提供的调整和管理国际关系的平台或结构。See Paul F. Diehl & Charlotte Ku,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8-46.。
个人来文制度是国际人权规范领域法制化进程的重要内容,它依据联合国职权部门的“赋权”决议或缔约国同意的“授权”得以实现。国际社会的法制化(legalization)进程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规则准确性提升、义务和授权的增加。法制化构成维度的程度与等级各自不同且独立变化,它们的相互组合使特定治理领域的法制化状态呈现出差别性和发展性*Kenneth W. Abbott et al., “The Concept of Leg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3, 2000, pp. 401-402.。整体上看,宪章框架下个人来文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依托宪章所包含之授权性,而非义务性的发挥和强化来实现的。所谓的授权性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员或类似实体赋予一个国际行为体(international body)做出决定或采取行动的权力*Curtis A. Bradley and Judith D. Kelley,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Delegation”,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71, 2008, p. 3.。依据职权对特定主体进行有限范围的授权是个人来文制度得以确立的最初路径,“授权”的强化表现为申诉主体与审查客体的扩大化与个人化以及审查结果效力的增加*根据宪章规定,所有成员国都有义务协助联合国依据宪章采取的行动。为促进人权保护的目的,ECOSOC可以设立专门委员会并做出建议(recommendations)。ECOSOC第1235号决议的“授权”(authorize)是基于宪章规定而做出的,其授权和权限来源于且受制于宪章。因此,ECOSOC及其下属委员会实际上承担着联合国框架下的“人权立法”功能。See Theodor Meron, “Reform of Lawma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Human Rights Instanc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9, No. 3, 1985, pp. 667-672.。与此不同,公约所确定的个人来文程序以义务性为核心确立,缔约国通过接受公约“申诉”或“来文”条款的约束,承诺特定主体可以就公约规定之事项向特定机构提交申诉或来文,并接受该机构的决定、建议或观点。毫无疑问,义务性基础上的授权范围受制于缔约国的同意,因而程序所针对的缔约国主体相对较少*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条规定,ICCPR的缔约国“承认”(非上述“授权”)人权事务委员会接收和考虑来文的权限。第8条与12条分别规定了国家选择签署、批准、加入以及退出的程序。迄今共有116个国家接受ICCPR议定书所规定的来文制度。参见http://indicators.ohchr.org/。。
依职权进行的授权以人权委员会的来文审查机制为典型,该机制的发展经历了由特殊审查向一般审查的转变。联合国经社理事会(ECOSOC)通过第1235号决议(1967),授权人权委员会及其下属部门对大规模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相关信息进行审查。人权委员会的申诉机制主要涉及“国别人权问题”的审议和调查,所针对的问题局限于“一贯”和“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个人虽然可以作为“申诉”程序的“信息源”,但单独个人之权利与自由遭受侵犯的事实或诉求还未成为来文审查的对象*接受和审议来文的主要是人权委员会的下属部门“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90年更名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ECOSOC第1235号决议第2段指出,人权委员会及其下属委员会所审查的信息与“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相关”(information relevant to gros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第3段则采用了“就一贯侵犯人权之情势进行彻底研究”(make a thorough study of situations which reveals consistent pattern of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的措辞。而且,决议通过例证形式确认,来文信息审查主要针对种族隔离和歧视。。ECOSOC第1503号决议(1970)决定建立就“具体的”人权侵犯问题进行审议的秘密申诉程序,但仅仅与特定案件而非“一贯”侵犯人权现象有关的个人申诉仍然不包含在内*ECOSOC第1503号决议授权人权委员会接受来自于团体和个人的,揭示“以一贯方式严重侵犯人权并被可靠证实”(a consistent pattern of gross and reliably attested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的申诉。ECOSOC第2000/3号决议(2000)对“1503程序”进行了修订,但“一般情势”仍然是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申诉审查的对象。对某些学者而言,相对于“1235程序”,第1503号决议只是申诉客体的一般化。参见Thomas Buergenthal, “The Evolving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yste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0. No. 40, 2006, p. 788. 人权理事会(Human Rights Committee)第5(1)号决议(2007)也基本承袭了“1503程序”的规定。。另一方面,以义务性为基础进行的授权表现为国际或区域人权公约所确立的来文或申诉机制,这些机制突破了ECOSOC囿于职权而无法完成的“纵深”建构,将个人来文或申诉机制真正向司法或“准司法”方向加以推进*建立个人申诉或来文机制的典型国际或区域人权公约包括:《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附加议定书(一)》(1981)、《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的公约》、《禁止酷刑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美洲间人权公约》等。国际法实践中,纵向视角(或结构)将国家视作国际法主体而非立法者,国际法体系的建构以授权形式(conferring form)而非限制形式(limiting form)来实现。依据劳特派特的观点,司法功能是国际法作为法律体系所必须的要素。See Jan Anne Vos, The Function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he Hague: T. M. C. Asser Press/Springer, 2013, pp. 1-15.。1981年,根据生效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附加议定书》(议定书),人权委员会开始有权接受遭受缔约国侵害之个人的来文,个人与国家开始处于同一规范和机制层面进行权利与义务的直接交锋。实际上,议定书所设立的个人来文制度致力于促进国内法律体系对国际人权规范的执行,个人在国际层面的申诉权有助于消除国内法律体系(规则或实践)的瑕疵或错误*See Louis B Sohn, Human Rights: Their Implementation and Supervision by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odor Meron ed.,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 Legal and Policy Issues, Clarendon Press, 1986, pp. 384-394.。《禁止酷刑公约》第22条所规定的个人来文制度便是在该层意义上所设立和运行的。
二、公约第3条项下个人来文的规则分析
《禁止酷刑公约》公约第22(1)条规定,缔约国可以宣布接受委员会接受和审查来文的权能(competence)*根据公约第20规定,缔约国需要通过采取否认行为来拒绝委员会接受和审查国家间来文的权限,这与第22条所规定的个人来文制度不同。。对于接受上述条款的缔约国,委员会有权受理并审查任何个人因遭受该缔约国违反公约之侵害而提交的来文。截至2017年3月,公约共有161个缔约国,其中67个缔约国宣布接受第22条规定的个人来文程序。就内容而言,以公约第3条为规范基础提交的来文占到来文总数的半数以上(195/373)*参见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网站,http://indicators.ohchr.org/. 新近接受个人来文程序的国家是圣马力诺,其接受时间是2015年8月4日。。第3条项下的来文提交者面临权利遭受双重否认的局面,来文程序的选择在客观上具有唯一性。来文提交之时,相关个人往往已经(或者宣称)穷尽国内救济,或者国内程序不能提供有效救济。他们置身国外,不愿或不能返回原住国(country of origin),也无法得到原住国司法体系的保护。当其所居住的缔约国拒绝为其提供保护时,委员会的来文程序便成为酷刑受害者可以求助的重要救济途径*公约第22.4条规定,提交来文的个人应当穷尽国内救济(原住国和所在的缔约国),且其他国际调查和解决程序没有处理或没有正在处理来文事项。See Chris Ingelse, “The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One Step Forward, One Step Back”, Netherlands Quarterly of Human Rights, Vol. 18, No. 3, 2000, pp. 307-308.。
缔约国在第3条项下的义务是禁止酷刑的义务性质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公约其他条款所确立之公约义务的自然延伸。一方面,公约序言提到,如《世界人权宣言》(UDHR)第5条和ICCPR第7条所述,所有人都应该免于“酷刑”*UDHR和ICCPR有关禁止酷刑义务的规定都采用否定式表达:任何人都不应罹于酷刑(No one shall be subjected to torture...)。,即禁止酷刑的义务具有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超越国家管辖权的界限,应当被包括缔约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尊重。因而,防止和禁止酷刑法律义务虽以属地性为基础确立,但却不限于对本国公民承担上述义务,在其领土范围内,公约第3条为所有人提供免于遭受酷刑危险的绝对保护(absolute protection)。而且,作为国际法的一般法理,缔约国不能够援引国内关切(domestic concerns)为其不履行第3条项下的义务辩护*Communication 300/2006, Adel Tebourski v. France, paras. 8. 2-8. 3. “符合国内法不能作为其违反国际法之理由”是国际法的一般法理。“纽伦堡原则”(Nuremberg Principles)第二项指出,不违反国内法不能免除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VCLT第27规定,缔约国不得援引国内法条款作为其不执行条约之证明。See John O. Brien, International Law, Cavendish Publishing, 2001, p. 111.。另一方面,公约第2.1条表述了缔约国所应承担的防止酷刑的公约义务,而第2.2条则直接宣示禁止酷刑义务“不可克减”的性质*公约第2.1条实际上是从条约视角对序言保障人权、禁止酷刑等内容的确认。第2.2条并未采用“缔约国承诺、认识到”等措辞,而是采用宣示或说明的形式来进行表达:“任何特殊情况……均不得援引为施行酷刑的理由”,而这属于对“不可克减”的正式表达。。结合序言对禁止酷刑义务之渊源与定位的阐述,第2条所反映的公约义务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CLT)有关国际法强行规范(preemptory norm of international law)的规定*VCLT第53条所规定的国际法强行规范为:被国家构成之国际社会整体接受和承认为“不可克减”(no derogation is permitted)的规范。。禁止酷刑的义务虽然属于强行规范,但如公约所反映,公约的执行仍然依赖于差异巨大的国别执行,这与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存在矛盾之处。不过,“不可克减”的特征为防止国家侵犯人权提供了安全网(safety net),即国家不仅须遵守公约义务,还必须保护公约所致力于保障的人权*See Erika Hennequet, Jus Cogens and Human Rights: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Factors of Harmo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Norman W. Jean & Marc Thouvenin ed., The Influence of Human Rights on International Law, Heidelberg: Springer, 2015, pp. 13-20.。第3条项下个人的权利便是在“强行法”意义上受到保护,同时又具体化到了约文当中。委员会在来文意见中甚至会直接表述第3条项下缔约国义务的绝对特征(absolute character)*See e. g., Communication NOs. 130/1999, 131/1999, VXN & HN v. Sweden, para. 13. 4.。公约第3条的约文如下:
1. 如有充分理由(substantial grounds)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任何缔约国不得将该人驱逐、遣返或引渡至该国。
2. 为了确定这种理由是否存在,有关当局应考虑到所有有关的因素(all relevant considerations),包括在适当情况下,考虑到在有关国家境内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
从委员会来文审查的角度看,公约第3条规则有以下方面值得注意或探讨。第一,第3条项下的来文审查受限于公约其他条款的规定。个人所面临的所谓酷刑危险——尽管还未发生——也应当符合公约所规定的酷刑定义*Communication No. 197/2002, U. S. v. Finland, para. 7. 5; General Commen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3 in the Context of Article 22 (hereinafter General Comment or“一般评论”),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U.N. Doc. A/53/44, annex IX at 52, 1998, para. 3.。在S. V. v. Canada等来文审查中,委员会指出,除非有明确的国家同意,国家并没有义务避免驱逐可能面临非政府实体(non-governmental entities)所施加之酷刑危险的个人。本案中,申诉人以其可能面临反政府武装和其他非政府实体的酷刑为由递交来文,委员会认为该种诉求超出公约第3条的范围,因而不予考虑*公约所规定的酷刑的施加主体是“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参见公约第1.1条;Communication No. 49/1996, S. V. v. Canada, 2001, para. 9. 5; Communication No. 83/1997, G. R. B. v. Sweden, para. 6. 5.。不过,委员会在Elmi v. Australia来文中对酷刑施加主体的论述进行了补充。委员会认为,索马里长期缺乏中央政府,但事实上,交战团体行使着与合法政府相称的(comparable to)职权,因此,上述团体成员可以属于公约第1条所规定的“公务人员和其他以公务身份行事的人”*Communication No. 120/1998, Elmi v. Australia, para. 6. 5.。在HMHI v. Australia来文中,委员会针对类似的案情做出了新的论述。在国家权力机关完善不存在的极端情况下,准政府组织(quasi-governmental authority)符合公约第1条的定义。委员会认为,尽管掌控的领土范围和持久性都存在问题,但索马里全国过渡政府发挥着中央政府的角色。因此,类似Elmi案之情况便不再符合公约有关酷刑的定义*Communication No. 177/2001, H. M. H. I. v. Australia, para. 6. 4.在其他来文中,委员会将“占有(occupy)并行使准政府权力之非政府实体”作为“非政府实体不符合公约第1.1条有关酷刑主体之要求”的例外。参见Communication No. 191/2001, S. S. v. Netherlands, para. 6. 4.。
第二,公约第3条强调,“充分理由”是缔约国承担“不推回”义务的前提,申诉人所持证据应当达到“充分”的水平。实际上,第3条规定包含针对缔约国的“双重义务”,笔者在此称之为程序义务和实体义务。一方面,从约文看,第3.1条表示,缔约国具有一定条件下的实体义务(不推回义务),但缔约国本身拥有判断条件是否成立的独立权力。缔约国首先拥有判断证据充分与否的裁量权,如果个人被认定提供了“充分理由”,即其被返回原住国后将面临酷刑危险,缔约国则须承担第3条所载之义务*第3.1条措辞用了“当缔约国有充分理由相信(believing)”,而相信与否属于自我判断的范畴。。另一方面,第3.2条说明,“充分理由”的认定同时构成缔约国应当履行的程序义务,缔约国不仅有权认定,而且应当“积极认定”*第3.2条措辞用了“为确定这种理由是否存在…当局应当考虑(shall take into account)所有有关因素”,结合前后文,缔约国有义务对相关因素进行积极地确认。同样,“一般评论”第6段指出:“缔约国和委员会有义务(obliged to)审查是否存在充分的理由,以相信申诉人被驱逐、遣返或者引渡之后面临酷刑的危险。”。另外,公约第3.2条规定,当局应当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从语义上讲,这不限于来文程序中申诉人所提交的证据,缔约国当局可以依职权进行收集和补充。当然,如果缔约国当局没有从程序上保障申诉人的相关诉求、证据或信息被充分考虑,那么委员会将会判定缔约国违反公约第3条的规定*例如,在X v. Russian Federation来文中,委员会认为,面对这些情况下(即乌兹别克斯坦的整体人权状况、要求引渡的时间、申诉人被要求引渡前的情况等),缔约国当局和法院有义务合理查证(duly verify)申诉人诉求,评估其所面临的危险,且这种查证和评估应当是充分的(sufficient efforts)。参见Communication No. 542/2013, X v. Russian Federation, para. 11. 8. 当然,除了缔约国依职权应履行的程序义务,相关的程序义务还包括缔约国对申诉人程序权利的保障,这将在下文做出论述。。最后,对于国家整体的人权状况,第3.2条仅仅规定,缔约国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给予考虑,约文并未触及其与个人所面临酷刑风险之间的关系问题。委员会在来文意见中一般会对两者的关系做出措辞几近相同的论述*公约3.2条实际上暗含着个人酷刑风险与国别人权状况之间存在的某种程度的关系。约文措辞是“是否存在…人权侵犯(状况)”。就两者关系,委员会的来文意见一般认为两者存在关系,但并不认为两者间存在互为推导的逻辑关联。几乎所有来文意见都采用了如下(或类似)表述:“the existence of a pattern of gross, flagrant or mas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in a country does not as such constitute sufficient reason for determining that a particular person would be in danger of being subjected to torture on return to that country; additional grounds must be adduced to show that the individual concerned would be personally at risk. Conversely, the absence of a consistent pattern of flagrant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does not mean that a person might not be subjected to torture in his or her specific circumstances”.。
第三,“充分理由”是触发缔约国“不推回”义务的前提,在个人来文程序中,申诉人与缔约国的交锋也主要围绕是否存在“充分理由”展开。从申诉人角度看,充分理由相当于所谓的“充分证据”。充分证据(substantial evidence)与微量证据相对,它为争议事实提供实质性根据,能够使具有理性的人(reasonable mind)相信它足以支持某一结论*See Bryan A. Garner ed., Black’s Law Dictionary (8th ed.), West Group Publishing, 2004, p. 599; 元照英美法律词典[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034.。根据概念,充分证据与所致结论之间存在符合常理的逻辑关联,充分证据本身并不必然完美或完全,关键在于契合拥有理性的人对事情发展规律的判断*委员会的来文意见一般认为,酷刑受害者所提供证据的绝对真实性(absolute authenticity)很难达到,且证据中的不一致或矛盾(inconsistency or contradiction)并不必然损害委员会得出所谓的“充分理由”。。委员会在其“一般评论”中论述了其审查个人来文的证据标准:“酷刑的危险之评价的理由必须超越简单的理论或单纯的怀疑。但是,这种危险也不必符合高度可能性(highly probable)的标准”*General Comment, para. 6.。概括而言,申诉人的诉求不能没有证据支撑,证据所指不能限于微弱的可能性,但也不必达到确证的地步,依据现有证据,只要拥有理性的个人能够预见到此种酷刑危险即可。进言之,第3条项下的所谓“结论”并非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是尚未发生的、公约致力于防止发生的“风险”。风险的防范不同于单纯的证据证明,委员会须要考察“理由”与存在酷刑风险的结论之间的联系是否符合理性,但不能以过高的证明标准“窒息”规避风险的可能,因为“风险”一旦发生便无法逆转*正因为如此,委员会表述个人证明责任时候很少用到“证明”(prove)一词。在Adel Tebourski v. France来文中,委员会甚至用到“暗指”(allude to)来表述个人对未来之酷刑危险的证明。参见Adel Tebourski v. France, para. 8. 3.。
第四,公约第3条确定了缔约国主动考察“相关因素”的职责要求及其范围。根据“一般评论”和来文意见的一般论述,申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应当能够证明其被返回原住国后将会面临“个人”、“可预见”且“现实”(individual, foreseeable and real)的酷刑危险。在美国,个人特定化(personally targeting)是证明存在酷刑“犯意”的手段,也是“遣返”程序的特殊要求。个人只有证明其自身将会被故意且特定地(individually)被选择(singled out)施加严酷待遇(harsh treatment),才能有机会赢得“不推回”诉讼*See Oona A. Hathaway et., “Tortured Reasoning: The Intent to Torture under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Law”,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2, No. 4, 2012, pp. 817-820.。同样,在来文程序中,申诉人所面临的危险不仅须是现实的,还必须“个人化”。例如,委员会就认为,徒有可能被逮捕或者被提起刑事诉讼的事实本身并不能作为面临酷刑危险的证据,因为,其遭受酷刑的危险可能并不存在。申诉人必须进一步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present a convincing case),证明其行为或者身份将会使其在被“返回”后面临真实的酷刑危险*Communication No. 137/1999, G. T. v. Switzerland, para. 4. 8; Communication No. 259/2004, M. N. v. Switzerland, para. 6. 7.。再如,政治、宗教或者族裔等相对敏感的身份(或倾向)并不必然导出存在酷刑危险的结论。委员会指出,尽管申诉人属于某些族群的身份可能会使申诉人招致某些麻烦,但族群身份本身并不足够证实其被遣返后可能面临的酷刑危险*Communication No. 123/1998, Z. Z. v. Canada, para. 8 .5; M. N. v. Switzerland, para. 6. 6.。
特别地,徒有原住国违反人权的事实并不足以使委员会得出申诉人可能将会罹于酷刑危险的结论*Communication No. 519/2012, T. M. v. Republic of Korea, para. 9.7; Communication No. 539/2013, A. B. v. Sweden.。这对缔约国来讲也是如此,即在来文的“控辩”中,缔约国不予施加酷刑的承诺应当针对特定个人,而非群体或全体国民。公约目的在于预防个人所面临的未来的、现实的酷刑危险,缔约国本身作为人权公约成员国、承诺保障个人权利以及其承认委员会接受个人来文之权限的事实并不能构成申诉人安全的足够保障*Communication No. 21/1995, Alan v. Switzerland, para. 8.1-8.2, 11. 5.。不过,相关国家不是公约缔约国、人权状况不佳等“整体”事实很可能增加委员会对申诉人所面临酷刑危险的“忧虑”,从而导致委员会做出有利于申诉人的意见*在Mutombo v. Switzerland来文中,扎依尔不是公约成员国,且人权状况较差,申诉人被“推回”后不仅可能面临酷刑危险,而且也会失去向委员会寻求救济的可能性。参见Communication No. 13/1993, Mutombo v. Switzerland, para. 9. 6.。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委员会审查个人来文的法理发生了变化,这仅仅表明,公约成员国身份及整体人权状况等事实构成委员会“理性判断”的重要因素,但它们本身与个人酷刑危险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关联*委员会清楚指出,扎依尔的整体人权状况只是“强化”(strengthen)了所谓“充分理由”。Mutombo v. Switzerland, para. 9. 4.。
最后,委员会审查第3条项下的来文旨在防范个人被“推回”后将会(would be)面临的酷刑危险,这与公约所规定预防目的一致。首先,虽然未来之酷刑危险是委员会审查来文的焦点,但“一般评论”将过去事实作为相关的(pertinent)信息*General Comment, para. 8(b), (e). 这两项分别规定了申诉人过往遭受酷刑及参加政治活动的历史。,委员会将申诉人过往所遭受的酷刑历史作为整体考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遭受过酷刑的事实并不能单独证成其在公约第3条项下的权利,申诉人被遣返后是否面临潜在的酷刑危险才是委员会考量的“重心”*Communication No. 550/2013, S. K. et al. v. Sweden, para. 7.3.。缺乏对未来酷刑风险的逻辑证明,申诉人将被否认公约第3条项下的权利。在S. A. P. et al. v. Switzerland来文中,申诉人强调其在俄罗斯因发表“异见”文章而遭受的迫害。委员会一方面质疑其所称伤害与酷刑(或迫害)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着重强调申诉人无法证明其被遣返回俄罗斯后仍旧面临类似的境况*Communication No. 565/2013, S. A. P. et al. v. Switzerland, para. 7. 4.。其次,曾经参与政治活动是可能面临酷刑危险的重要“诱因”,但委员会关心申诉人是否因此或因其重要性(significance)而仍旧被相关当局所关注。M. M. et al v. Sweden来文更加具体地分析了过去事实与未来酷刑危险之间的关系。委员会指出,即使相信申诉人过去曾遭受酷刑或参与反对政党,但其现在(currently)是否还面临酷刑威胁,或是否仍然吸引当局的注意并不确定或存在疑问*Communication No. 332/2007, M. M. et al v. Sweden, paras. 7. 4-7. 7; Communication No. 458/ 2011, X v. Denmark, para. 9. 6.。总述之,过去事实不是第3条项下个人来文的独立证据,它们仅能够发挥辅助证明作用。
三、委员会进行个人来文审查的证据论理
(一)证据的提交与审查
个人来文审查中,申诉人须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委员会有权独立审查申诉人及缔约国机关所提交的证据。根据一般意见,对于来文的实体问题,申诉人承担争议事实的举证责任。申诉人举证并非直接引致委员会所做出的结论,而仅仅是奠定充分的事实基础,以至于缔约国可以做出相对应的回应*General Comment, para. 5. 原文强调,申诉人的举证需要充分,以得到缔约国的回应(require a response from the State party)。,因而是“初步的”证明责任。申诉人一般会对证据的可靠性做出论述,如果得到委员会的肯认,则证明责任将转移(shift of burden of proof)到缔约国一方。例如,在M. A. K v. Germany来文中,申诉人和委员会就证据是否足够可靠(sufficiently reliable)存在分歧,委员会不支持申诉人证明责任须转移到缔约国一方的诉求*Communication No. 214/2002, M. A. K v. Germany, paras. 9. 6, 13. 5.。另外,申诉人所须证明的内容与缔约国、委员会类似,只不过视角不同,可以细分为三个内容,即第一,申诉人是否面临酷刑危险(danger);第二,这种危险是否理由充分;第三,危险是否针对个人且现实存在(personal and present)*See General Comment, para. 6-7. 一般评论第7段分三个部分(and that)表述申诉人应当证明的内容。。
作为缔约国所创设的监督机构,委员会将会给予相关缔约国机关所递交之事实以较大的“分量”(considerable weight)。同时,委员会并不会被缔约国所提交的证据约束,相反,根据公约第22条,委员会有权独立审查每个来文案件所涉及的所有情况*Communication No. 583/2014, A. v. Canada, para. 7 .3. General Comment, art. 9 (b).。委员会对“控辩”双方的证据必须同时兼顾,但又有所侧重。委员会认识到,其自身并非司法或上诉机构,因此,对于缔约国所陈述的事实,它必须加以“着重考量”(give considerable weight to),并权衡其对申诉真实性的质疑是否可以被采纳*Communication No. 519/2012, T. M v. Republic of Korea, paras. 9. 4-9. 5.。委员会不会去挑战缔约国所得出的事实,不负责(或者没有权能)调查或解决申诉人论述的不一致问题*Communication No. 135/1999, S. G. v. Netherlands, para. 6. 6.,它的工作是从缔约国和申诉者双方的“诉求”、回应和评论中提取案件事实。如果缔约国没有质疑(dispute)、否认(deny)或者回应申诉者所陈述的事实,委员会则将此等事实作为逻辑说理的基础加以使用*例如,在P. A. v. Netherland来文中,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并未对申诉人所陈述的在哈萨克斯坦曾遭受过酷刑的事实加以回应,因而将论述内容转到与第3条相关的其他方面。参见Communication No. 611/2014, P. A. v. Netherland, paras. 8. 7-8. 9; Elmi v. Australia, paras. 6. 6, 6. 8.。
委员会对权威性、独立性较强的机构或个人提供的证明或信息会给予特别的关注或重视。一方面,对于自身或者独立性较强的第三方机构所做出的一般人权状况评价,委员会一般会赋予较高的证据分量。例如,在R. K. v. Australia的来文中,委员会认为,其在对斯里兰卡所进行的第三和第四轮人权状况观察中认为,内战结束后,在斯里兰卡的许多地区,斯里兰卡军队或者警察等国家行为者都实施着酷刑或不良待遇等行为。委员会还引述了英国、荷兰、特别报告员以及非政府组织所提交的人权状况观察,委员会对这些意见赋予较大的可信度,并以此为基础认定与反政府武装存在个人或者亲属关系的泰米尔族人被返回后可能会面临酷刑危险*Communication No. 609/2016, R. K. v. Australia, para. 8. 6. 相关的文件包括:CAT/C/LKA/CO/3-4, para. 6; CAT/C/GBR/CO/5, para. 20.。另一方面,第三方机构为申诉人所出具的专门证据或意见,如果得不到缔约国的有力回应,将会被委员会接受为做出来文意见的事实基础。在S. J. D. v. Australia来文中,委员会注意到,埃德蒙德﹒莱斯中心(Edmund Rice Center)的报告确认,申诉人的陈述真实可信,其就被遣返后面临酷刑和迫害的担忧理由充分,而缔约国无法反驳报告所载内容。另外,诉求得到酷刑受害者援助机构和全国工人总会的支持,医学报告也证明了申诉人精神伤害和过往经历之间的一致性,缔约国提不出任何有力论据进行回应*Communication No. 387/2009, S. J. D. v. Australia, paras. 10. 6-10. 8.。
(二)证据真实性问题
不寻求取得证据的绝对准确性是委员会审查个人来文的证据法理之一*General Comment No. 1 (2017)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3 of the Convention in the Context of Article 22 (draft),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CAT/C/60/R.2, paras. 44. [General Comment Draft 2017]。如上所述,委员会往往关注缔约国所提出的申诉人陈述中的不一致或矛盾之处,因为这影响到申诉人所举证事实的真实性*Communication No. 156/2000, M. S. v. Switzerland, para. 6 .5.。不过,委员会就个人来文无调查职权,申诉人所提交的某些文件本身无法证明其真实与否。转而,委员会将关注点放置在申诉方所提供文件的可靠性及其是否被充分证实(sufficiently substantiated)方面*Communication No. 34/1995, Aemei v. Switzerland, para. 9. 6; Alan v. Switzerland, para. 11.3; Communication No. 562/2013, J. K. v. Canada, para. 10.4.。申诉人必须有可靠的证据证明被遣返回原籍国所面临的酷刑危险,而所谓“可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证据本身及其提供主体的“资质”。在J. K. v. Canada来文中,委员会就认为,乌干达委员会、同性恋协会所出具的信件是可靠的,其包含的信息可靠且充分,因而证明责任转移到缔约国一方*J. K. v. Canada, para. 10.4.。委员会在Karoui v. Sweden来文中的论理逻辑更加直白。委员会认为,大赦国际(瑞典)所提供的支持信(supporting letter)以及跨国公司Al-Nahdha主席所出具的证词属于可靠的文件,因此,证明责任应该转移,且申诉人的证据应该被相信(be given the benefit of doubt)。另外,委员会直陈其十分重视针对过往酷刑之医学-法律报告(medico-legal report)的证明作用*Communication No. 185/2001, Karoui v. Sweden, para. 10.。
申诉人陈述或者所递交材料中的矛盾或者不一致往往导致缔约国对申诉请求真实性的否认*See Peter Rurns,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and Its Role in the Refugee Protection”, Georgetown Immigration Law Journal, Vol. 15, No. 3, 2001, p. 408.。例如,在F. K. v. Denmark来文审查中,丹麦认为,F. K.申请庇护之事实陈述存在不一致或不协调的地方,因而不可信,故而无法作为其返回土耳其将可能再次遭受酷刑之危险的充分理由*F.K. v. Denmark, paras. 4. 13-4.15.。实际上,依据不要求绝对准确的法理,委员会在早期的来问程序中对陈述的矛盾或者不一致问题相当“宽容”。在Alan v. Switzerland来文审查中,委员会认为,酷刑受害者陈述之绝对准确性不可期待,且这类不一致并非决定性的(material),这不会对申诉人陈述的总体真实性(general veracity)造成疑问*Alan v. Switzerland, para. 11.3.。委员会并非调查机构,只能追求所谓的“书面真实”,而“法律真实”的探求由缔约国公务机构掌握。因此,面对申诉人(国内程序申请人)所提供信息中的不一致,委员会经常强调绝对真实实属罕见,委员会特别重视(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申诉人对不一致问题的解释或者自身对此类不一致的合理化解读*Karoui v. Sweden, para. 10.。
实际上,委员会在辨别不一致问题上拥有一定的裁量权。Kisoko v. Sweden来文中,申诉人对酷刑的前后两次陈述完全相反,但委员会成员深知,酷刑过于残暴,它降低了受害者的注意力和记忆力,受害者不愿再谈起,这是上述不一致的合理解释,而瑞典也接受了上述观点*See Bent Sorensen, CAT and Articles 20 and 22, in Gudmundur Alfredsson et., e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Monitoring Mechanisms: Essays in Honor of Jakob Th. Moller (2nd ed.),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p. 106.委员会在来文意见中并未详述其否认“不一致”影响的逻辑。参见Communication No. 41/1996, Kisoki v. Sweden, para. 9. 3.。同样,委员会在Rios v. Canada来文中以申诉人神经损坏为由否认了陈述模糊或不一致对真实性的影响*Communication No. 133/1999, Rios. v. Canada, para. 8. 5.。当然,这也可能与来文案情的整体“氛围”相关。在K v. Australia来文中,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事实陈述中存在的相对“微小”(而非显著)的不一致,即对申诉人在不同陈述中所声称的被拘禁的时间、地点、天数等细节存在矛盾。作为回应,委员会增加了对过去事实客观性和细节证据的要求*Communication No. 591/2014, K. v. Australia, paras. 10. 6-10. 7.,而这在无形中将委员会审查的视角由“未来”拉回到“过去”。如果申诉人无法提出客观、有力的证据来回应或者弥补此类不一致,其主张权利的进程就将面临相当大的障碍*例如,在G. T. v. Switzerland来文中,针对申诉人离开原住国和达到瑞士的时间争议,申诉人没有做出回应;针对征集令时间的不一致,申诉人未能提供日内瓦土耳其领事所颁发的召集证明,仅有的材料又无法弥补他所声称事实的真实性(truthfulness)。参见Communication No. 137/1999, G. T. v. Switzerland, paras. 6. 5-6. 8.。
(三)有关程序的证据问题
程序是否符合公约要求是委员会审查个人来文的重要内容,缔约国疏于或者怠于履行确认个人所面临的酷刑危险也将构成对公约第3条的违反。程序义务在“一般评论”修改草案(General Comment Draft, 2017)中体现的更为详细,整体而言,委员会对有关程序义务的把握相当严格*See General Comment Draft (2017), paras. 14, 18, 40-43.。在F. K. v. Denmark案中,丹麦“难民上诉委员会”拒绝对F. K.进行医学鉴定。丹麦的解释是,不给予申诉人难民地位的决定符合国内法律程序,且上诉委员会依据国内法有权决定是否进行医学鉴定。况且,F. K.在整个申请程序中的陈述缺乏真实性,所谓的医学鉴定没有必要*Communication No. 580/2014, F. K. v. Denmark, paras. 4 .3-4. 7; 4. 9-4. 11, 4. 13.。对此,委员会表现出对申诉人权利给予周全保护的倾向。委员会认为,难民地位申请人(来文申请人)的确需要提出初步的(prima facie)证据,但这丝毫不会减免缔约国对下述事项应做出重大努力(substantial efforts)的义务,即确认是否存在理由让人相信,申诉人被遣返后会面临酷刑危险*〔82〕F. K. v. Denmark, para. 7. 6; Communication No. 464/2011, K.H. v. Denmark, para. 8.8.。对于申诉人陈述的真实性问题,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未能充分地回应申诉人诉求的根本方面(fundamental aspects),因此,其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真实性结论不足为取,因为,缔约国没有履行第3条所规定的“充分调查”(sufficiently investigate)是否存在酷刑危险的义务〔82〕。
缔约国在公约第3条项下所应履行的(或与第3条相关的)程序义务不仅包括公共权力机构(如警察、出入境管理部门、难民管理部门等)依据职权所采取的行动,也包括对申请人(申诉人)程序权利的保障措施。首先,缔约国的公务部门应妥善地履行公约所载义务,与第3条项下义务相关之公务行为必须受限于公约的规定。言外之意,即使缔约国判定申请人不具有难民或受庇护地位,也不可以对其为所欲为,其合法权利不应被忽视。在上述F. K. v. Denmark来文中,申诉人F. K.认为,自己在丹麦公务人员(包括警察)的执法过程中遭受攻击、被强制按倒、戴上手铐等待遇,而且警察试图在其半裸和流血的状态下将其送交土耳其驻丹麦大使馆。嗣后,丹麦司法部门并未针对被申诉之残忍、不人道待遇展开迅速、公正的调查*F. K. v. Denmark,para. 5. 8. 公约第12条与第16条往往与公约第3条之义务相联系,因为申诉人不仅致力于避免重新陷入原住国可能施加酷刑的危险,也面临缔约国应对难民问题而滥用执法手段的现实危险。公约第12条规定,缔约国应当对受害人申诉之酷刑行为进行迅即和公正的审查;公约第16条规定,缔约国应当防止公务人员实施、鼓动、同意或默许的残忍、不人道或侮辱性的待遇或惩罚。。委员会判定,丹麦警方将申诉人强行送还土耳其使馆的过程构成残忍或不人道待遇,即丹麦警方对待申诉人的方式不符合公约的规定。依据委员会的逻辑,公务部门轻易地接受“表面说辞”(face value of explanation)并不妥当,相反,为确立所涉行为的本质与状况以及相关当事人的身份,应该采取积极的行政、调查和司法行为*F. K. v. Denmark,para. 7. 7.。另一方面,与第3条直接相关的申诉人的程序权利必须得到严格的执行。在Ke Chunrong v. Australia来文中,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提交了足够详细的信息,以证明其与原住国所禁止之政治活动存在密切关联。然而,澳大利亚移民部门对上述诉求和证据未给予充分核实(sufficiently verified),移民部门没有为申诉人提供面谈机会,申诉人也未被通知拥有听证的邀请。因此,澳大利亚没有妥为履行公约第3条项下的程序义务,即通过为申诉人提供有效、独立和公正之审查机会,以保障其程序和实体权利*参见Communications No. 416/2010, Ke Chunrong v. Australia, para. 7.5.。
四、余论:第3条项下个人来文审查的反思
个人来文制度在国际层面为个人直接对抗展示出危害性质的国家公权力提供了平台。委员会虽然不具备强力执行“来文意见”的司法性质,但来文审查反映了全球化和人本化时代人权话语的发展,个人通过公约机制得以和主权观念及其组织表现进行交流或交锋。第3条项下的个人来文案例显示,证据规则为相对“脆弱”之个人增加了程序性“护符”,它通过对国家施加审查证据的实体和程序义务,展现着禁止酷刑之国际义务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同时,如上所述,委员会在来文中所秉持的证据标准和论理表现出谨慎维护处于弱势地位之个人的倾向,即使所涉的基本人权只是处于可能的而非确定的危险当中。整体而言,作为国际人权法的执行机制,委员会不仅代表促进人权遵守的“国际力量”和象征,而且暗示缔约国在促进人权保护中的“服务者”角色。
个人来文的证据论理体现了委员会的法律定位及其功能。委员会不是国际司法机构,只是经由国家同意而建立起来的人权监督机构。第一,个案审查过程中,作为监督机构而非上诉机构的委员会总是在寻求个人权利与国家主权的恰当平衡,即要促进基本人权的保护,又要谨小慎微地维护国家同意的边界。笔者认为,两者的平衡点显著体现在程序方面,即缔约国是否妥为履行公约第3条所规定或隐含的程序义务。第3条项下的个人来文机制从程序上规定缔约国须做出或不做出某些行为,即通过程序义务来保障实体权利,而缔约国本身仍旧保有审查实体条件是否符合的权力。第二,委员会在来文审查的实体问题上并不具有追根究底的权能,现实中,委员会只能进行所谓的“纸面审理”。一方面,这凸显委员会“非司法”性质的一面,也是人权执行机制相对“羸弱”的体现。缔约国可能会质疑,为何委员会的“纸面审理”可以代替和推翻缔约国耗力甚巨的现实审理?委员会成员的回答是,他们更懂得酷刑、酷刑行为及其危害,也更能感觉到酷刑的残忍性*〔87〕Bent Sorensen, CAT and Articles 20 and 22, in Gudmundur Alfredsson et., e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Monitoring Mechanisms: Essays in Honor of Jakob Th. Moller (2nd ed.),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p. 106.105.。另一方面,委员会也形成了审查个人来文的“路径”,如学者所言,委员会在某些案件中会针对相关法律原则做出司法决定或者创造“先例”〔87〕,通过考察具体的来文案例,委员会实际上也贯彻着类似“遵循先例”方法,这不仅体现在行文格式和交互引证,也体现在委员会的证据论理当中。在Rios v. Sweden来文中,委员会指出,在考虑“不一致”问题和形成意见过程中,委员会充分考虑了其确立的实践(established practice),除非构成司法不公,委员会无权质疑缔约国对证据所做出之评估*Kisoki v. Canada, para. 8. 5.。当然,话语之中透漏着委员会的司法色彩,有意无意中,委员会承担着司法“纠偏”的角色。
相对于纯粹的人权监督机构,委员会展示出“准司法性质”,这对寻求第3条项下权利保护的个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3条所涉情况下,酷刑受害者即将面临被“推回”的命运,因此,委员会须具备阻止缔约国做出此种行为的权力。实际上,临时措施不仅在于人权保护机构的管辖权,同时也是有效执行公约义务的必要条件。根据公约第18.2条,委员会在其程序规则第108(9)条中纳入了临时措施条款,委员会在个人来文程序中有权做出临时措施*Oliver De Schutte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Cases, Materials, Comment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7.。委员会实际上通过目的解释达到上述目标。委员会的来文“判例”表明,如果申诉人有可能面临不可弥补之酷刑危险,委员会有权做出其认为合理的临时措施,且相关措施对保护申诉人十分必要;通过接受公约第22条,缔约国承担善意合作的义务,从而赋予个人申诉制度以完全的效力(full effect);如果拒不服从委员会所做出的临时措施,缔约国将违反公约其在公约第22条项下所承担的义务*Communication No. 110/1998, Chipana v. Venezuela, para. 8; Communication No. 195/2002, Mafhoud Brada v. France, paras. 13. 3-13. 4.。从某种程度上讲,此种规则解释手段及其所导致的扩权悄然延伸了国家同意的边界,这是缔约国很难预料和掌控的;同时,委员会以偶现的“判例”或“司法决定”强化了其司法色彩,提升了其在保护人权方面的执行能力。
从保护个人权利的角度来看,委员会在处理第3条项下个人来文方面的“能力”仍旧存在缺陷。第3条项下的个人来文的申诉人往往面临较为紧急的情况,但委员会并不能即时做出回应。委员会并非常设的机构,且委员会回应个人来文的时限长达6个月,这造成了酷刑受害者权利保护的“真空期”*Winston P. Nagan & Lucie Atkins,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orture: From Universal Proscription to Effective Application and Enforcement”, 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 Vol. 14, 2001, pp. 105.。另外,有学者甚至认为,个人申诉机制严重依赖缔约国的自愿配合,且其对普遍存在的酷刑现象并无改观,它表示人权申诉机制只是象征性的存在*F.K. v. Denmark, paras. 4. 13-4.15.。而且,委员会审查个人来文只能得出所谓的“意见”而非“裁决”。笔者认为,上述观点的确反映着国际人权法执行机制相对孱弱的状况,但却是从静止视角出发得出的消极结论。确实,委员会似乎只能通过违法性确认的方法来促使缔约国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但并不代表公约第3条项下来文意见的遵守无法期待。整体而言,缔约国对委员会来文意见都倾向于遵守,这可能源于“约定必守”的力量,也可能是缔约国考虑名誉得失而做出的选择*See Markus Burgstaller, Theories of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Law), Leiden/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4.。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审查第3条项下来文的长期历程积累了相当的“先例”和“决定”,这不仅逐步强化着国际人权执行机制,也构成缔约国(甚至非缔约国)国内法律体系应对酷刑问题时的重要考量因素。而且,通过委员会的来文审查实践,这些“先例”、“决定”或单纯的“必要性”正在通过编纂成为有拘束力的规则*例如,“一般评论”修订草案规定,遣返国(state of deportation)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对权利人提供完全和持续的保护,而且,应当采取国内立法措施,以禁止酷刑,取消酷刑施害者的豁免权。这些规则都是在来文实践基础上,通过委员会的解释和“立法”而即将获得拘束力。参见General Comment Draft 2017, paras. 50-51.。总之,国际人权规范与其执行机制之间存在长期的互动关系,它们经历着虽然缓慢但互为强化的历时性过程。
OntheAspectsofEvidenceinIndividualCommunicationUnderArticle3ofConventionAgainstTorture
LI Jiang
(SchoolofLaw,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ECOSOC established the first global human rights compliant mechanism by its Resolution 1235 in 1967, while individual compliant mechanisms (ICM) were built through sovereign states’ ratification of conventions or their annexed protocol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CAT) laid down ICM in its article 22. Most of communications the Committee has handled concern rights and obligations under article 3 of CAT. Evidence is the core issue of article 3, which stipulates the Committee’s duty to examine, content and standard as well as scope of factors in the process. In the practice, the committee develops its own logic or “precedents” regard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examine, credibility of evidence and procedural aspects under article 3. The committee tries to achieve balance between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maintenance of sovereign power. Its practices help to enrich international norms concerning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nd also serve to strengthen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non-refoulment principle; individual communication; problems of evidence
2017-08-02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2017年10月26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本文系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拔尖创新人才项目资助成果”。
李将,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刑法,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
DF979
A
1672-769X(2017)06-0107-12
DOI.10.19510/j.cnki.43-1431/d.20171026.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