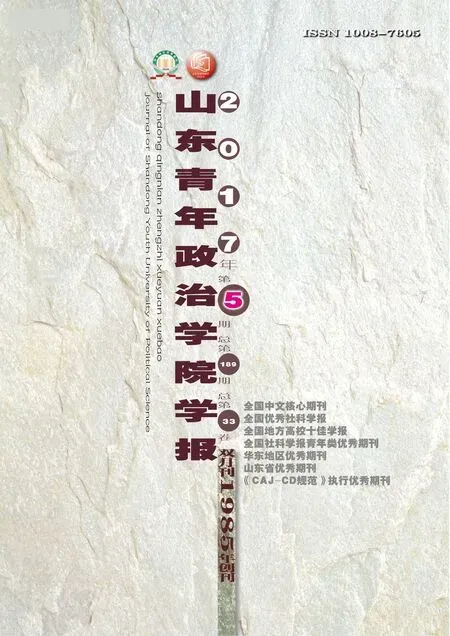试论损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合同效力
顾志伟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苏州 215000)
试论损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合同效力
顾志伟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苏州 215000)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第三人转让股权时,受到原有股东优先购买权的限制;就违反该程序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学术界与实务界的观点已趋于一致,即该类合同为有效合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公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的第27条的裁判规则,结论却大相径庭。正确适用该款司法解释的关键在于重新以股权转让为中心,以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规定否定合同效力,进而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程度的保护。
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效力性强制规定;规范意旨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原则通过了《公司法解释四》,虽然正式文本尚未公布,但其中第27条的施行将会对司法实践产生重大影响,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各级法院关于股权转让合同案件的堆积与延迟裁判。根据《公司法解释四》第27条的规定,未履行公司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订立股权转让合同,其他股东可以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此规则一改先前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定的合同有效但不能履行的裁判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在“新奥特诉华融一案”中确立的裁判规则亦是如此,且该案例已刊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对下级法院具有较大的指引作用。实务中通常的裁判规则是:合同分为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只要合同双方当事人作出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达成合意,原则上合同成立并生效,只有在出现《合同法》第52条或54条所列情形时,合同效力才有瑕疵。传统观点认为,此种情形下合同继续有效,具体履行规则可参照买卖合同“一物多卖”的顺序规则,已经办理登记的优先;均未办理登记的,合同成立在先的优先,其余方可以通过有效的合同主张转让方违约责任。根据物权变动的规则,合同有效不意味着物权当即发生变动,在此基础之上还需履行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易言之,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仅是债权行为,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仅发生债法意义上的效果,即转让方有为受让方办理过户登记的义务,受让方有按约定支付价款的义务,股权本身不会当即发生变动;股权变动还需要将新的股东姓名和出资份额记载于公司名册上,并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另根据我国《物权法》所确立的“区分原则”,股权转让必须基于一个合法有效的合同行为,但股权变动能否发生不影响其原债权合同的效力。然而根据即将生效的《公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第27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有权以转让合同未履行法定程序、损害其优先购买权为由,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合同无效,这实际上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解释路径和裁判规则。因此笔者认为在新的司法解释公布前,有必要回顾传统学说中关于优先购买权的权利属性、损害优先购买权的合同效力状态及第三人的权利救济等问题的研究,以正确适用新的裁判规则。
二、传统观点及评议
(一)请求权、形成权与期待权
“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及其效力不仅决定了自身的行使方式和效力,也深刻地影响到权利人利益受保护的程度。”[1]在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蒋大兴教授较早地对相关学说观点加以梳理和总结。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形成权说、请求权说和期待权说,而形成权说又可以分为绝对形成权说、附条件的形成权说,请求权说可以分为有强制缔约义务的请求权和无强制缔约义务的请求权。[2]目前在学术界占主流的观点是形成权说,如赵旭东教授认为请求权说“实在既无必要,又徒增缔约成本,还拖延契约成立时间,违背经济效率原则,不如采用‘形成权说’既经济又便捷高效。”[3]除了上述交易效力的考虑,从优先购买权的基础性权利的性质,即股权具有物权性、支配性和人合性而言,将优先购买权界定为形成权更为合适。
在关于优先购买权性质的“三国论战”中,多数学者会在选择权和形成权中择一,但仍有不少学者主张期待权说。如郑彧博士认为“就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优先购买权而言,其不是基于物权的形成权,也不是基于债权的请求权,而应是股东基于其作为公司成员而享有的社员权基础上的一种期待权。”[4]在形式上优先购买权符合期待权成立的三个要素,“一是对未来取得某种权利的期待;二是已经具备取得权利的部分要件,尚缺部分要件权利才能成就;三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地位。”[5]不可否认的是,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确实具有期待权的特性,与既得权相对应,但这并不影响其仍符合请求权或者形成权的特征。且期待权说仅是从外部要素来揭示优先购买权特征的,上述三个要素对于认定权利性质或许有意义,但对于认定损害此种权利的合同效力并无实际价值。
通说观点将优先购买权定性为形成权,原因在于更符合立法意图,笔者亦赞同采取形成权说更能够保护原有股东的合法权益及公司的“人合性”。不过,笔者认为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的性质或许可以搁置一旁,讨论是请求权或者是形成权在理论上有意义,但在合同效力认定时中并无实际意义。即使认定优先购买权是形成权,但损害形成权而订立的合同效力与其基础权利的性质并无直接关联;同样,即使认定优先购买权是请求权,合同也并非一定有效。实际上,根据权利的分类,股东优先购买权也并非主权利,而是从属于股权的的从权利,是一种期待权,以优先购买权为中心的传统解释路径并未合理解释基础权利的性质与合同效力间的关联性。
(二)合同效力之“有效说”与“无效说”
对于损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合同,理论上存在“有效说”与“无效说”的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合同有效,合同有效的解释路径以优先购买权为解释中心,遵循着先解释优先购买权的性质,然后从物权请求权或者是债权请求权着手研究损害优先购买权合同的效力,再辅之以立法目的和经济效益,通过在公司、转让方、其他股东和第三人之间取得利益平衡,从保护第三人和交易秩序的角度认定为有效合同。“有效说”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 “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目的在于通过保障其他股东优先获得拟转让股份而维护公司内部信赖关系,因此法律所要否定的是非股东第三人优先于公司其他股东取得公司股份的行为,而不是转让股东与第三人间成立转让协议的行为。”[6]通过将股权变动的发生与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作区分,只要不存在其他效力瑕疵,合同即是有效的。二是“在否定合同效力情况下,第三人只能通过缔约过失的责任机制获得救济,在肯定合同效力情况下,第三人则可以以违约为由追究转让方的责任。”[7]通过赋予第三人的违约救济权利,帮助第三人填补损失。从上述观点来看,合同有效确实能够给予第三人更多的救济,也维护了交易秩序。
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该合同并不能一味认定为有效,而是相对无效或可撤销。如赵俊海教授认为股东优先购买权作为一种法定权利,侵害股东优先购买权订立的合同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不能认定不存在效力瑕疵。但考虑到未来的交易因素均不确定,如原股东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以及是否接受交易价格,因此可认定为可撤销合同。
对于“有效说”,笔者的疑问在于:无论《公司法》还是《合同法》,其均是最大程度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但由于优先购买权是法定权利,法律一经公布即推定所有人因当知晓,即“不知法者不免责”,交易双方应当知晓原有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却仍然擅自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有明显的法律规避的嫌疑,也不排除恶意串通的可能。如果转让方没有履行《公司法》规定的程序,极有可能损害原股东的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此种情况下,是否给予非善意的第三人违约救济措施就值得商榷了。在笔者看来,合同无效的情况下,若第三人为非善意的,则不应当给予违约或缔约过失损害赔偿,而仅是恢复原状;若在特殊情况下,第三人为善意的,则可通过缔约过失责任寻求实际损失的救济,如此一来则更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正义原则。而对于“无效说”,笔者则更为赞同。因为相对无效能够兼顾第三人和受让方的利益,在利益衡量中不存在偏颇之处,也最大程度尊重《公司法》。如果原股东认为行使优先购买权能符合自己的利益,则可以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申请宣告无效,即使股权已经办理变更登记,根据我国《物权法》确定的“区分原则”,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的基础法律关系必须合法有效,否则物权变动仍不能发生。如果原股东在一定期限内未行使优先购买权,则合同仍然有效。不过,“无效说”也存在无法自圆其说的漏洞:第一,撤销权是一种形成权,赋予原股东撤销权应当有法律的明文规定,理论上的赋权并不能为司法实践提供帮助;第二,认定合同无效仅是利益衡量的结果,并未严格遵循法教义学的解释路径,论证路径缺乏严谨性。因此,在传统学说中,无论是“有效说”还是“无效说”,均不能合理解释合同效力的问题,而仅是利益衡量的产物。
三、以股权转让为中心的解释路径
鉴于以优先购买权为中心的传统解释路径无法准确认定合同效力,因此笔者认为,从以优先购买权为中心转向以股权转让为中心的解释路径,更符合法教义学的价值立场。首先,根据《公司法》第71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内可自由转让股权,但对外转让须履行必要的程序,即必须经得其他股东过半数的同意。其次,经过股东过半数同意后的股权可以对外转让,但原有股东可以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此过程可以理解成转让方发出合同内容具体、明确的要约,原股东对此作出承若即可。最后,在未履行上述征求同意和发出要约的义务时,需要思考的是此种义务是否属于法律强制性义务,进而是否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在解释上述路径前,有必要对相关条款作进一步的文义解释,并探求条文的规范意旨,得出合理的解释结论。
(一)文义解释
根据《公司法》71条第2款的规定,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应当首先取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这意味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是一种不完满的权利。股权是成员权和财产权的集合,财产权一般是可以自由转让的,但股权又具有成员权的特征,是一种社员权,为保护公司“人合性”,因此对外转让应当有所限制。《公司法》第71条设置的第一道程序是当股权转让其股权时,应当征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30日内应当做出回复。如果该股权没有经得过半数同意,则是不可转让股权,不具有可让与性,因为其他股东应当购买该股权;第71条第3款设置的第二道程序是在满足过半数同意转让的股权,可对外转让,但此时原有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上述征求原股东的意见可视为第一次通知,在同等条件下通知原股东是否受让股权可视为第二次通知。第二次通知的内容应当包括股权转让的主要交易条件,是转让方向原股东发出的要约,而原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行为即构成对要约的承诺。通过“要约-承诺”的方式订立合同,则无需考虑能够依原股东单方意思表示成立合同的问题,优先购买权的性质争议被巧妙的避免了。另根据71条第3款的规定,优先购买权只发生在同等的交易条件下,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将优先购买权理解成强制接受“同等条件”的义务。
通过对法律条文字面含义的解释,可知《公司法》71条2款,可知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转让的股权是无法对外转让的,属于标的物本身的瑕疵。而转让瑕疵标的物的行为往往是无效的,如根据《物权法》第191条、《担保法》第49条的规定,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擅自转让抵押物的行为无效。因此上述不履行征求过半数股东同意即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应为无效。其次,通过解释第3款,可知《公司法》在股权对外转让时设置的限制性程序,是转让股东应当履行的程序义务,而这种义务则体现为原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的尊重。损害原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也就可以理解成转让股东不履行相关义务,该义务属于法律设定的程序,合同效力的认定即转化为是否属于《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
(二)限制转让条款是否为强制性规范
在认定《公司法》第71条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时,应当先认定它是否为强制性规范。有学者认为“根据《公司法》第71条第4款的规定,明确股东优先购买权并非强制性条款,而是公司可以通过章程修改另行规定的赋权性条款”[8],《公司法》关于限制股权对外转让的条款是任意性条款,但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在章程没有另外规定时,转让方履行通知和征求意见的程序应当是法定义务,是强制性义务;其次,在章程对履行程序有另外规定时,如对具体的时间、通过比例等作出不同要求,应当视为对法定义务的细化或部分变更,但不能据此认定其义务性质的转化,即不能变相否定转让程序。最后,如果章程约定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无需履行上述义务,即可直接与第三人签订转让合同、办理变更登记,即约定是否有效?原股东是否可以请求法院宣告该款无效?很显然,此种约定已经规避了《公司法》关于股权对外限制转让的规定,使得维持公司人合性的立法目的落空,原股东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名存实亡,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等少数群体的合法权益,原股东可以请求法院宣告该条款无效。基于同理,如果章程过度限制股东转让的权利,导致股权实质上不能转让,股东也有权请求法院宣告该条款无效。因此笔者认为,《公司法》第71条第2、3款属于强制性规定,股东优先购买权属于法定权利,其保护力度应当强于意定权利。
(三)“效力性强制规范”之识别
在先前的司法案例中,裁判者认定合同无效往往会遵循以下的推理路径:鉴于某条款是管理性强制规定,因此违反本款不会导致合同无效。对此,有学者鲜明地指出这是一种公式化的思维方式,“先就规范性质做出是否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然后据此推出违反后果。解释结果摇身变成推理前提。”[9]因此“并不是合同因为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而无效,而是某种强制规定令违反者无效故称效力性强制规定。”[10]上述见解矫正了混乱的推理逻辑,笔者亦赞同之。《公司法》第71条第2款是效力性强制规定,是因为违反该款会导致合同无效,合同无效是原因,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结论。对于“效力性强制规范”的识别也不能仅仅依据文义解释,如解释“应当”、“可以”、“不得”等,因为即使立法语词用的是“应当”,但没有明确法律后果,也不能径直认定违反它导致合同无效。合同无效的真正原因则在于行为对规范意旨的违背,即“若想真正对违法合同的效力进行判断,仍然需要去对违反的具体法律的目的进行解释。”[11]
根据上述分析,《公司法》之所以设置必要的程序,是对原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尊重和保护,但《公司法》同样保护交易秩序和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如何精准地平衡二者利益,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公司法》第71条的规范意旨。笔者认为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和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与股东优先购买权具有相似性,通过比较分析的解释方法,识别三者各自的规范意旨。通说认为,赋予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首先是基于其弱势群体地位,体现了“人本”的法律正义;其次是“确保出租人和承租人的租赁法律关系不因出租人的出卖行为而受到影响,从而达到维护交易秩序稳定的目的。”[12]最后,促使用益物权与所有权合二为一,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而法律设置按份共有人享有优先购买权旨在减少按份共有人数量,简化共有关系,促进共有物的有效管理与处分,第三人的介入往往会增加管理成本,降低交易效率。有观点认为,既然最高人民法院对损害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合同效力已作出规定,自然可以类推适用。但笔者认为,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规范意旨在于简化共有关系,而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规范意旨在于实现使用权与所有权合一,二者相差甚远;更为重要的是,按份共有人是基于出资或者家庭关系而形成的,与股东的形成极为相似,规范意旨也趋于一致。此外,在“买卖不破租赁”的保护下,承租人的利益已经实现最大程度得到保障,与此相反的是如果不赋予股东和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强大的法律效力,则该款的规范意旨将会落空。况且在司法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多数合同虽然有效,但陷入履行不能,与合同无效的法律效果差别之处在于第三方可依据有效的合同主张违约损害赔偿,但笔者认为对于非善意的第三人给予违约损害赔偿值得商榷,既无必要,也不应当。
四、结论
不同于《物权法》确立的“区分原则”未能消除关于物权行为理论有因性亦或无因性的争论,《公司法解释四》的生效则会对股权转让合同产生重大影响,这也就意味着此类合同最终将会被认定为无效。笔者认为,待《公司法解释四》正式生效时,也无需对其大加指责或批判其严重违背私法自治理念,是公权力对私权的又一次“干涉”,因为法律解释归根结底是一种价值判断,通过法律解释创造符合价值判断的规范意义,而不是发现其中的规范意义。在新的裁判规则中,《公司法解释四》更加注重对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保护,此种价值取向在司法实践中应当被尊重。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认定损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合同效力为无效无效,原股东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无效;解释路径如下:首先,以股权转让为中心,转让股东发出的通知是包含订立合同的主要内容的要约,原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是对要约的承诺,与优先购买权是何种性质无关;其次,合同效力的认定最终应当回归到能否适用《合同法》第52条相关条款,若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规定,则为无效;最后,从《公司法》第71条着手,通过比较承租人和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规范意旨的不同,进而得出《公司法》第71条的规范意旨与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类似,应当给予股东优先购买权更为有力的保护,而只有否定该类否定合同的效力,方能实现简化共有关系,提高公司决策效率,保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进而符合《公司法》的规范意旨。
[1][3][7]赵旭东.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和效力 [J]. 当代法学,2013,(5).
[2]蒋大兴. 股东优先购买权行使中被忽略的价格形成机制[J].法学,2012,(6).
[4]郑彧.股东优先购买权“穿透效力”的适用与限制[J].中国法学,2015,(5).
[5]申卫星.期待权研究导论[J].清华法学,2002,(1).
[6]潘福仁.股权转让纠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8]胡晓静.论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效力[J].环球法律评论,2015,(4).
[9]朱庆育.《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评注[J].法学家,2016,(3).
[10][11]黄忠.违法合同的效力判定路径至辨识[J].法学家,2010,(5).
[12]曹兴权. 股东优先购买权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5).
(责任编辑:杜婕)
Abstract:when shareholders of a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transfer the shares, the outside-transfer procedures of shares are limited. In the fields of practice and theory, the contract which violated the shareholders preemptive right terms is effective, not voidable.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Judicial Opinion Four Concerning Company Law ( draft)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the conclusion is quite different.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correctly is the way whitch based on the transfer of shares, the validity of the contract is negated by the mandatory provisions. The explanation path can provide a reasonable demonstration process for the invalidity of the contract.
Keywords:stakeholders's preemptive rights;share transfer;normative will;mandatory provisions
OntheContractValidityofViolatingStakeholders'sPreemptiveRights
GU Zhi-wei
( Kenneth Wang School of Law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0, China )
2017-05-16
顾志伟(1992-),男,江苏扬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司法研究。
DF411.91
A
1008-7605(2017)05-007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