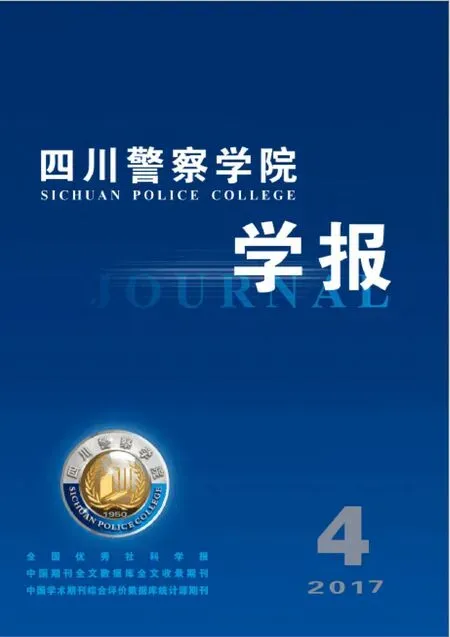从全面取证到规范保管:侦查环节证据运用的法律规制
刘小庆
(成都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四川成都 610207)
从全面取证到规范保管:侦查环节证据运用的法律规制
刘小庆
(成都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四川成都 610207)
刑事证据的全面收集与规范保管是确保侦查质量,实现案件正确定罪量刑的基础,也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就全面取证而言,需扭转传统办案思维,摘掉有色眼镜;需建立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体制;需重新划分警检各自权力范围,探索借鉴“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制度。从规范保管的视角而言,需建立阶段性证据详细记录机制;建立证据调取的规范化机制;需保障证据保管的外部环境和支撑条件。当然,为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依法贯彻无罪推定理念应当贯穿整个办案过程的始终。
审判中心;全面取证;证据保管;检察引导侦查取证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1]。为了实现上述宏伟目标,《决定》明确了公正司法的方向之一在于推进严格司法。为此,“要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2]。
党中央从全局性的战略高度深刻阐释了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为司法实践的积极探索提供了政策支撑,也为今后学界有关证据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和指引。
我国作为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并没有制定专门的证据法典,刑事证据的相关规定往往散见于各种法律、司法解释乃至内部行政性文件。包含刑事证据内容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等。但是,专门以“证据”为文件名称的仅包括《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两部司法解释。在众多的法律法规中,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和实施对刑事证据而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它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法律地位,为刑事证据的审查运用提供了合法性判断依据,同时,明确了侦查取证的全面性有助于无罪推定理念的贯彻实施。立法的进步值得肯定,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目前侦查取证的有罪证据收集的倾向性明显,证据保管规范化机制有待健全。对照全面取证的要求,实践中存在:第一,长期盛行的阶级斗争思想成为刑事案件办案的主导思想导致侦查取证倾向于有“有罪证据”;第二,基于我国社会治安防控压力的增大,三机关流水线办案的模式仍未破除。第三,行政体制原因导致公安机关具有较高的地位,拥有较大的话语权。第四,“警检”权力划分不科学导致检察机关不得不“配合”公安机关的办案需求。侦查实务中证据保管的问题表现为:第一,涉案关键物证由于保管不善造成的遗失。第二,难以杜绝公安机关在少数件中伪造或隐瞒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
为切实提升侦查取证工作的质量,保证关键物证能够得到科学规范的保管。就全面取证而言,需扭转侦查机关传统办案思维,摘掉视“嫌疑人”为“罪犯”的有色眼睛;需探索建立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体制;需重新划分警检各自权力范围,探索借鉴“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制度。从规范保管的视角而言,需建立阶段性证据详细记录机制;建立证据调取的规范化机制;需保障证据保管的外部环境和支撑条件。同时,广大办案民警应当依法贯彻无罪推定理念,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二、全面客观收集证据,避免证据收集的倾向性
证据收集是刑事案件侦查的最基础性的工作,为解决案件事实的认定问题提供客观参考,有助于实现准确案件的准确定罪量刑。证据收集工作的好坏直接决定案件办理的质量和成败。因此,证据的收集工作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应当全面、客观的收集各种与案件有关联性的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立法明确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应当实事求是客观收集证据,不能基于定罪的需要而专门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同时,应当将其无罪或者可能无罪的证据,以及罪轻的证据一并收集。笔者认为,此项要求不仅仅是基于人权保障需要视角下对公检法三机关的具体要求,同时,立法客观证据收集要求也是为了避免上述机关徇私舞弊而放纵罪犯。当然,在现有重打击轻保护的大背景下,立法规定对人权保障的倾向性更加凸显。相类似的规定还要包括《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57条:“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第58条:“公安机关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时,应当告知其必须如实提供证据。”《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61条第三款:“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应当遵循客观公正原则,对被告人有罪、罪重、罪轻的证据都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
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行对应的司法解释均明确要求公检法三机关要全面收集和客观对待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相关证据。但在现实中上述规定能否得到较好的贯彻实施往往是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实践中,侦查机关通常有意或无意识地注重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而对其无罪的证据关注度不足。“近年来暴露出的冤假错案普遍存在偏重于收集、移送有罪证据,疏于收集、移送无罪证据的情况。有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证人提供了指向他人作案的线索,但侦查机关未能引起重视并积极查证”[3]。由于“侦查中心主义”现象的客观存在,部分案件中“真正决定中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命运的程序不是审判,而是侦查”[4]。如有实务工作者通过对73起重大疑难命案的实证分析印证了上述结论[5]。笔者认为,基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条关于三机关应当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规定使得公检法三机关在实践中形成了紧密联系的利益共同体。三者形成了线性结构而非英美西方国家所提倡和贯彻的等腰三角对抗式诉讼模式。三机关往往以流水线式的作业模式办案,注重打击犯罪而忽视人权的保障。针对该条规定,左卫民教授认为,“应当废止相互配合表述,凸出制约的本体性地位”[6]。龙宗智教授认为“条件较为成熟时,应当通过修改宪法和法律,彻底废除这一显然不符合诉讼规律,也有损我国刑事司法公正形象的原则和制度”[7]。
造成上述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社会新旧矛盾的交织,大量进城务工人员未能顺利就业以及城市化进程中拆迁征地导致失地农民增多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每年刑事案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三机关联合共治、相互配合有助于缓解上述案件激增的压力。
为扭转“三机关”的传统办案思维,尤其是公安机关侦查取证的倾向性,有必要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完善:第一,扭转传统办案思维,摘掉有色眼睛。在我国,阶级斗争这一政治思维长期以来盛行并成为刑事案件办案的主导思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划分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对于破坏社会关系的犯罪行为理所应当成为人民打击的对象,犯罪分子被视为阶级敌人,国家有义务惩罚此种危害人民的行为。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和实施明确将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并举,这就要求侦查人员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摘掉先入为主将嫌疑人视为“罪犯”的有色眼镜,全面取证成为基本要求。第二,建立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体制。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在于法院对于案件裁判拥有不受干扰的决定权,“但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司法在实践中异化为侦查决定审判、审判配合检控、审判依附侦查的局面,即侦査职能俨然演化为实质性裁判,法院的审判职能不彰”[8]。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主要推行技术改革路劲,对于司法体制层面的改革关注较少。在我国,行政和司法体制因素往往在各项改革中发挥着关键乃至决定性作用。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本应当作为审判的中心而成为等腰三角诉讼模式的顶点,因而在司法体制中具有较高的权威和地位。反观我国,检察院和法院虽说是由人大选举产生,地位高于一般的同级地方政府的组成部门的公安。但我国较为奇怪的现象是公安机关的“一把手”往往还兼任同级地方人民政府的副职,属于政府党组成员,其官阶和地位高于同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虽然我国出现跨区域的巡回法院的试点设立,但总体而言我国以行政区划来设立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基本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另外,同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赖地方财政供养的局面并未发生体制性改变。基于上述各种原因,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部分案件中不得不全力“配合”公安机关。为确保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成果实现,有必要确立以“法院”为中心司法体制。第三,重新划分警检各自权力范围,探索借鉴“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制度。长期以来由于公安机关的权力过于膨胀,人民检察院和法院不得不在部分案件中寻求公安机关的帮助和支持。如《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上述规定表明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基于案件办理的需要,当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嫌疑人时还需要公安机关予以配合。类似的规定还包括同法第153条:“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机关可以发布通缉令,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归案。各级公安机关在自己管辖的地区以内,可以直接发布通缉令;超出自己管辖的地区,应当报请有权决定的上级机关发布。”当检察院自侦案件犯罪嫌疑人在逃时需要公安机关协助发布通缉令。因此,为进一步保证三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能够客观全面收集案件证据,尤其是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除了进一步加快刑事诉讼法的修法进程外,可以重新划分警检各自权力范围,探索借鉴“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制度”。具体而言,“在审前阶段尤其是在侦查程序中,要发挥检察机关对侦査机关的引导、规范作用”[9]。
三、完善刑事证据保管制度,避免证据遗失或污染
刑事案件的办理其核心是围绕证据来展开,以立案后启动证据的收集工作为起点,以刑事案件认证后的定罪量刑为终点。与言词证据不同,就大部分刑事物证而言均要经过取证、保管、运输、鉴定以及其后的举证、质证、认证等诸多环节。应当说刑事证据的保管是极为重要承上启下的诉讼环节,但保管也是最易被侦查机关忽视。目前,我国对于证据的收集工作有一套相对清晰的工作流程,但对于证据的保管问题在实践中一直饱受诟病,在少数刑事案件中由于侦查机关保管不善而致使关键物证遗失的情况也屡有发生。如著名的“陈满案”之所以能够成功翻案,其核心在于证明陈满当年犯罪的关键物证在一审时均已丢失,而定罪的“口供”高度疑似“刑诉逼供”。类似的案件在司法实务中也屡见不鲜。究其原因在长期以来侦查机关不重视物证的规范保管,庭审又不重视对关键物证的全面审查。
证据保管与证据保全是最容易混同的一对概念。证据保全是对证据的处置行为,在刑事诉讼中通常指侦查机关对涉案物证的扣押,以避免其发生事实或法律上的改变。保管则是对该处置行为发生后的动态管理过程,涉及证据的包装、运输、储藏等环节。
《刑事诉讼法》第139条:“在侦查活动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文件,应当查封、扣押;与案件无关的财物、文件,不得查封、扣押。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要妥善保管或者封存,不得使用、调换或者损毁”上述规定只是原则性的告诉办案机关应当妥善保管,并且对怎样保管做出更进一步的规定。本着基本法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上述规定确实尚且理解,那么,司法解释是否有进一步规定了?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04条:“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犯罪事实、无罪或者罪轻的事实、申辩和反证,以及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证明自己无罪、罪轻的证据,公安机关应当认真核查;对有关证据,无论是否采信,都应当如实记录、妥善保管,并连同核查情况附卷。”《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25条、第226条、第230条均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应对收集到的相关证据加以妥善保管,但并未对公安机关妥善保管证据规定操作层面的具体实施细则。另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38条第三款规定:“对于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录音、录像带、电子数据存储介质,应当记明案由、对象、内容,录取、复制的时间、地点、规格、类别、应用长度、文件格式及长度等,妥为保管,并制作清单,随案移送。”该条规定对证据的保管要求应当制作清单并随案移送,对于保管问题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行要求,具有进步意义。但它只是对检察机关进行要求,并未涉及侦查权的主要运行主体公安机关,且规定较为简单。
笔者认为刑事证据保管相关规定的缺漏在侦查实践中将会造成如下恶果:第一,涉案关键物证由于保管不善造成的遗失。部分刑事案件中关键性物证在案件采信乃至法官认证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公安机关遗失关键物证客观上导致被告质证活动无法当庭展开,同时,法官客观上对于侦查机关未当庭提供实物证据而提供其取证时照片的行为通常给予理解和宽容,因而侦查机关对于证据保管也更加随意。第二,难以杜绝公安机关在少数件中伪造或隐瞒证据。由于未当庭提供实物证据而仅以其照片和其他佐证材料加以代替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该证据的采信,侦查机关客观上获得了伪造证据和隐瞒证据的便利,加之,我国侦查程序较为封闭,律师、检察官和法官客观上并未能对侦查活动给予实时监督,在少数件中公安机关伪造或隐瞒证据难以杜绝。由于“侦查、起诉人员承担控诉职能,其主要目标是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有些侦查、起诉人员可能为了追求控诉成功而对证据进行篡改。此外,有些办案人员可能与案件或案件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因收受当事人的贿赂,而蓄意篡改证据”[10]。
因此,为解决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提高。第一,建立阶段性证据详细记录机制。“证据交付的对象,交付的时间、地点,交付的原因,以及向被交付者索要凭证。接触过该证据的人都要在证据的包装上签名并做好标记,当证据被归还时,原保管人应当签发收条,做好归还时的记录,并且检查证据与当初是否是一致的”[11]第二,建立证据调取的规范化机制,明确两人以上方能调取关键物证。应当通过修法或者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证据收集以后应当建立物证保管的详细记录机制。明确调取物证应当进行详细记录,并且对于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的关键物证应当由两名以上办案民警共同调取和查阅。第三,保证证据保管的外部环境和支撑条件。目前,我国承担大量刑事案件的基层派出所并未建立专门的物证保管室,因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设立物证保管室的方式对证据进行规范管理,强化管理措施。“根据实验室具体情况,设立专用物证保管室和特殊物证贮藏室。物证保管室安全级别设为最高级别,未经授权人员不得擅自进入物证保管室。例如,普通物证保管室保管一般材质物证;DNA等生物物证应设有相应冷藏设备,防止物证腐烂。物证保管室由专人管理,物证的出入要有文字记录,并保存这些记录以备查档”[12]同时,启用监控设备对物证保管室进行实时监控。第四,加强对证据保管的检察监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实施的监督机关理应加强对侦查机关和侦查程序的检察监督,尤其是对证据保管环节检察机关应当定期或不定期抽查侦查机关对证据的保管情况,侦查机关存在不规范、不合法的行为应当当场要求纠正,情节严重的,应当当即排除该证据。
四、依法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切实保障嫌疑人诉讼权利
侦查环节为保证案件办理的质量,确保所有证据都能经得起审判的检验,除前述全面取证和规范保管证据外,还应当进一步从思想层面破除长期形成的办案陋习。笔者认为,广大办案民警应当依法贯彻无罪推定理念,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全面取证、规范保管,确保公诉质量,这也是审判中心主义题中应有之意。无罪推定原则提出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归宿在于保障人权,“被告人是刑事诉讼的中心人物,无论是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活动,还是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活动,都是围绕着被告人进行的,没有被告人,就没有刑事诉讼”[13]代封建社会诉讼模式实行纠问式,被告人成为刑诉追诉的对象,他们被认为是有罪之人,诉讼的进程不是为了查明被告是否有罪的问题,而是被告是怎样作案,作案的经过是什么,正因为如此,被告仅作为诉讼的客体而非诉讼的主体,其不享有公民的一般权利。基于保障人权的迫切需要,无罪推定便应运而生,它的诞生宣告了纠问式诉讼模式的终结,宣告着现代诉讼时代的到来。现代刑事诉目标为复合制,诉讼目的兼顾维护社会稳定、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被告人虽然可能有罪,但只要是“自然人”理应享有一般公民应有的权利。为了保证案件真实的及时查明,在刑诉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理应赋予其充分的权利,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的相关强制措施并不应该是由于犯罪嫌疑人确定有罪,而是基于查明案件的需要和防止嫌疑人逃跑的必要。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有权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因经济问题无法聘请律师的还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有权对侦查机关侵犯人权的行为提出控告;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参加刑事诉讼。”这些权利组成了保障被告人诉讼权益的权利体系,它体现了国家对被告人的尊重和保护,但在刑事诉讼中,尤其是侦查阶段,被告人常常不能充分行使其权利。首先,刑事诉讼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活动,被告人由于法律知识的欠缺,不知道自己有哪些诉讼权利更不知道如何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其次,刑事诉讼是一项费时费力的活动,刑事诉讼活动往往需要一定的人力、财力的投入,如聘请律师等,部分嫌疑人由于经济状况较差,聘请律师维护自己权利的难度陡然增加,即便是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但实践中援助律师通常介入案件时间较晚,难以充分行使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被告在侦查阶段的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且部分法援案件辩护律师普遍资历较浅,难以应付复杂的辩护需求。对此,“除督促律师尽职尽责外还应当从司法体制和诉讼制度上保障律师辩护的机会,确保被告获得有效的辩护”[14];最后,少数侦查人员为了节约办案经费、节省警务人员投入量、加快办案进度,往往阻挠嫌疑人正当权利的行使。无罪推定原则的诞生,认为被告人无论是否在事实上有罪在法院判决以前其都不能被视为罪犯,其理应享有基本的诉讼权利。要求广大办案人员由其是公安机关秉持无罪推定理念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转型必须解决的观念问题,这也是衡量一国诉讼制度文明程度的标尺。
[1][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
[3]沈德咏.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J].中国法学,2015,(3):11.
[4]孙长永.侦査程序与人权[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5.
[5]贺恒扬,吴志良.对73起重大疑难命案的实证分析——从刑事证据的收集、固定、审查判断和运用的角度[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1):129.
[6]左卫民.健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2):28
[7]龙宗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及其限度[J].中外法学,2015,(4):860.
[8]陈卫东.以审判为中心:当代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基点[J].法学家,2016,(4):3.
[9]左卫民.审判如何成为中心:误区与正道[J].法学,2016,(6):9.
[10]陈永生.证据保管链制度研究[J].法学研究,2014,(5):179.
[11]刘 娜.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保管制度[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1):27.
[12]刘 璇,刘 燕,任玉苓.刑事物证中的“保管链”[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9,(3):109.
[13]王美丽.“无罪推定”应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原则[J].公安大学学报,1994,(4).
[14]陈瑞华.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理论反思[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40.
Legal Regulation of Evidence Application in Investigation:from Comprehensive Evidence-obtaining to Standard Evidence-keeping
Liu Xiao-qing
The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and standard keeping of criminal evidence is the basis of ensuring investigation quality and achieving the correct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the case,and the trend of the trial-centered litigation system reform as well.As for comprehensive evidence collection,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court-centered judicial system with investigators’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deas,and also necessary to redraw the power spectrum of police organs and procuratorial organizations to explore the system of procuratorial work guiding evidence collection in investigation.As for standard evidence-keeping,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recording periodization evidence in detail,establish standardized evidence collection system and guarantee its external circumstance and supporting conditions.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should be carried out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handling cases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suspects.
trial Centered;comprehensive evidence collection;keep evidence;procuratorial work guiding evidence collection in investigation
DF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12(2017)04-0061-06
(责任编辑:吴良培)
2017-05-19
刘小庆,(1988- ),男,四川隆昌人,硕士,四川成都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干部,研究方向:刑事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