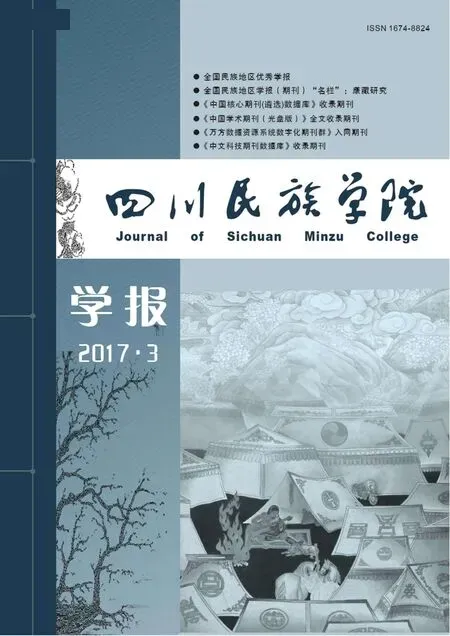我国自愿戒毒制度的失范与规范
靳澜涛
★法律研究★
我国自愿戒毒制度的失范与规范
靳澜涛
自愿戒毒制度由《禁毒法》首次赋予合法地位,又经过《戒毒条例》进一步规范和细化,被单独列为一章,成为我国戒毒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禁毒法》《戒毒条例》等法律规范对于自愿戒毒营利性异化、约束力薄弱、执法避风港等风险给予了充分估计,并做出了相应的制度规制。但是,自愿戒毒措施的立法干预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慎重考查整个戒毒体系的协调和衔接,也需要认真反思自愿戒毒本身的价值和定位。从以上两个维度加以审视,一方面,自愿戒毒与强制隔离戒毒之间的天然紧张关系仍缺乏必要的规范。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过度深入与自愿戒毒充分发挥社会医疗资源的价值理念相悖。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厘清自愿戒毒制度的法律定位,消解戒毒措施之间的内在失范,平衡社会化戒毒理念与行政高权体制的冲突。
自愿戒毒;禁毒法;戒毒条例;强制隔离戒毒
自愿戒毒从狭义上是指,吸毒人员自行到具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这种措施在我国戒毒实践中渊源较为悠久,但直至《禁毒法》出台后,才被落实为成型的法律制度,并在随后颁布的《戒毒条例》中被单独列为一章加以细化。《禁毒法》和《戒毒条例》对于自愿戒毒实践中出现的营利性异化、约束力薄弱、执法避风港等风险给予了充分估计,也完善了相应的制度规制。但是,厘清自愿戒毒的规范框架和运行现状后发现,自愿戒毒与其他戒毒措施在衔接中存在较为明显的冲突,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也难以彰显自愿戒毒的内在价值。对于目前的制度架构需要从立法、政策、措施等多个维度作出修正,方能使其发挥更大的效用。
一、传统自愿戒毒措施的渊源与弊端
《禁毒法》颁布以前,强制性戒毒与自愿戒毒构成了我国传统的戒毒体系的主要框架。但是,在立法中,自愿戒毒作为实践中形成的戒毒措施始终未能得到确认和固化。仅有以下几部法规间接默认了自愿戒毒措施的存在:1995年,国务院发布的《强制戒毒办法》第21条中,允许医疗单位在省级卫生部门批准和同级公安部门备案后开展戒毒脱瘾业务。1996年,公安部在《关于贯彻执行<强制戒毒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第4条第6款中,进一步规范了公安部门对于戒毒医疗单位的监督职责、附属安康医院从事戒毒业务的要求等。同年,卫生部出台《关于加强戒毒医疗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及其所附的《戒毒医疗机构验收标准》,对戒毒医疗机构的具体运行做了细化规范。2000年,公安部发布的《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第47条规定,强制隔离戒毒所可以接受自愿戒毒人员,默示了自愿戒毒现象的存在。这些关于自愿戒毒措施的“法律依据”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都属于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鲜见法律作为渊源;二是发布机关的级别较低,其中级别最高的是国务院,其他均是国务院各部门;三是都没有明确、直接赋予自愿戒毒以法律依据。
自愿戒毒措施在立法定位中的缺失,使得其在规范层面与强制戒毒相抵触,在实践中也呈现弊端迭出的乱象,面临着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质疑。第一,强制戒毒与自愿戒毒存在适用冲突。根据1990年《关于禁毒的决定》第8条、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4条第3款等规定,对吸毒成瘾者一律采取强制戒毒是我国立法机关的基本立场。但是,实践中“自发形成”的自愿戒毒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强制戒毒。一方面,自愿戒毒与强制戒毒或治安处罚的优先适用存在立法空白。另一方面,除医疗机构外,强制戒毒所和劳教戒毒所也允许接收自愿戒毒者,而自愿戒毒过程中呈现的营利性有损强制戒毒等执法活动的权威性。第二,自愿戒毒存在“执法避风港”风险。部分学者在对吸毒人员的访谈中发现,“当禁毒斗争‘风声较紧’时,他们就采取自愿戒毒的方式躲避风头,因为如果被抓获就可能受到拘留、罚款、强制戒毒甚至劳动教养1-3年的处罚,而在自愿戒毒机构里他们自由、安全、‘合算’得多。”[1]第三,由于缺乏相应制度规范,自愿戒毒在管理上存在约束力差、复吸率高等管理漏洞。自愿戒毒人员与戒毒医疗机构之间是病患关系,而非管理关系,其手段的强制性必然受到限制,因而复吸率相对较高。例如,据广东省有关部门对373名吸毒成瘾者的调查,自愿戒毒的复吸率为93.6%。[2]
二、现行自愿戒毒制度的定位与风险
如前所述,自愿戒毒措施在我国戒毒实践中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曾经在合法性与合理性上存在明显的缺陷。《禁毒法》首次赋予了自愿戒毒的合法地位,对医疗机构的资质、治疗活动的要求、治安处罚的豁免等事项做了详细规范。《戒毒条例》在《禁毒法》确认自愿戒毒合法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更为积极的立场,即“国家鼓励吸毒成瘾人员自行解除毒瘾”,并规定了医疗机构协议戒毒的手段和应当履行的义务。
尽管《禁毒法》与《戒毒条例》对于自愿戒毒实践中出现的营利性异化、约束力薄弱、执法避风港等风险给予了充分估计,也完善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予以规制。但是,自愿戒毒措施的立法干预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慎重考查整个戒毒体系的协调和衔接,也需要认真反思自愿戒毒本身的价值和定位。从以上两个维度加以审视,一方面,自愿戒毒与强制隔离戒毒措施之间的天然紧张关系仍缺乏必要的规范,强制隔离戒毒措施的扩大适用也是导致自愿戒毒萎缩趋势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权力过度深入,与自愿戒毒关于充分利用社会医疗资源的价值理念相悖,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自愿戒毒在戒毒体系中呈萎缩趋势
以我国中部H省为例,90年代末自愿戒毒在该省发端时尚有8家开展戒毒业务的医院,如今戒毒科大多并入精神科,缺乏自愿戒毒的病源,自愿戒毒几乎名存实亡。戒毒体系相对较为完善的东部S市,自愿戒毒机构也由4家减少至两家,且其中一家自愿戒毒医院的床位利用率由2008年时的150%锐减到40%,入不敷出,难以维持机构正常运转。
笔者认为,自愿戒毒规模逐步萎缩大体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强制隔离戒毒和美沙酮门诊的收戒力度加大,分流了自愿戒毒病源。以前文提及的H省为例,该省自2007年开始推广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每天一次,每次10元手续费,可以达到24小时内克制毒瘾的效果,对自愿戒毒机构的生存产生较大冲击。另一方面,戒毒费用短缺和合成毒品症状出现较晚也是病源减少的主要原因。以东部S市为例,该市精神卫生中心下设的自愿戒毒中心中,每位病人一个疗程平均1-1.5万元,一个床位一个月平均1万元。而该市近年来月平均工资标准维持在6000-7000元之间,很多吸毒人员难以承担自愿戒毒的高额费用。此外,目前合成毒品的吸食量远远超过传统毒品,合成毒品由于侵蚀中枢神经,成瘾症状出现较晚,也使得大量吸毒人员处于麻痹之中,造成自愿戒毒人员的“断档”。
(二)自愿戒毒与其他戒毒措施衔接不畅
正如前文所述,在《禁毒法》出台以前,自愿戒毒与强制戒毒、治安处罚等存在一定适用冲突。《禁毒法》第62条赋予了自愿戒毒人员治安处罚豁免权,默示其相对于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的优先适用性。《戒毒条例》进一步通过第9条表明了对于自愿戒毒的更为积极的态度,重申对其原吸毒行为不予处罚,并且没有说明“不予处罚”的范围仅限治安处罚。但是,现有禁毒法律框架中对于自愿戒毒与强制隔离戒毒措施之间的天然紧张关系仍缺乏必要的规范,对于因为这种紧张关系所可能产生的潜在风险与困境亦缺乏必要的回应。
一方面,由于强制隔离戒毒以吸毒成瘾严重或社区戒毒为前提,又缺乏与自愿戒毒的转化机制,吸毒成瘾者可以利用立法漏洞,通过申请自愿戒毒而逃避强制隔离戒毒和行政拘留处罚。因此,《禁毒法》出台前的“执法避风港”困境仍未得到根本纠正,前者源于立法的缺失,无法有效规制吸毒人员的投机行为,而后者源于立法未能作出有效界分,使得自愿戒毒与强制性戒毒措施发生适用混同,给吸毒人员逃避执法留下了投机空间。
另一方面,对于自愿到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戒毒的人员如何处理,始终是困扰戒毒实践的问题,立法上存在着是否接收和是否登记的双重困境。[3]一旦登记则可能产生留下“案底”、形成“标签”等负面影响,不利于自愿戒毒者重新回归社会,甚至作为有“吸毒史”的证据,依据《吸毒成瘾认定办法》第7条而被公安机关认定为“吸毒成瘾”;如果不登记则可能与《吸毒人员登记办法》第3条关于必须登记的人员范围规定相抵触。是否接收和是否登记的双重矛盾使得强制隔离戒毒所面临自愿戒毒者往往无所适从。
(三)行政权力过度干预有悖制度价值初衷
关于自愿戒毒措施实践中呈现的营利性异化和约束力薄弱现象,《禁毒法》做出了必要的规制,这主要体现在第36条和37条。具体包括限制戒毒医疗业务市场的准入条件、规范医疗机构戒毒诊疗活动的具体标准、赋予医疗机构检查和保护性约束措施等“准执法权”、明确医疗机构对于吸毒人员复吸行为的报告义务等。为了避免自愿戒毒制度流于形式,行政权力的高度干预有利于统筹戒毒资源配置,规范曾一度混乱的戒毒医疗机构,但是,其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首先,国家对戒毒医疗行业准入条件、诊疗活动、社会宣传等限定颇为苛刻,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民营自愿戒毒机构的成长空间,导致许多机构因为缺乏经费和患者流失而难以为继。受限于《禁毒法》第36条的规定,戒毒治疗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治疗方法不得做广告,客观上也使得自愿戒毒机构不为社会公众和戒毒人员所熟知,因此,当吸毒人员毒瘾症状出现时也未能第一时间选择去戒毒医疗机构。
其次,有学者主张,“将自愿戒毒部分医疗费用纳入医疗保险。”[4]目前,已有个别地区开始将自愿戒毒、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期间因戒毒产生的戒毒诊疗费用纳入医疗保障体系,通过地方财政使用权的倾斜,保障自愿戒毒的正常运行。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戒毒条例》第54条明文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将戒毒治疗项目纳入公共卫生医疗保障体系。”但是,除了一些受诱骗被动吸毒者,大多数吸毒者在初次吸毒时都是在自由意志支配之下的选择,这种自损行为带来的利益损失要由社会承担是否合理,是否会纵容吸毒,似可再做斟酌。现代财政的本质属性是公共财产,与私人财产权应受保护的立场相对,公共财产是一种应受控制的权力。[5]此外,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刚刚起步,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尚未确立,医保控费机制尚不健全,仅仅因吸毒人员被定位为特殊病人,就给予超出普通病人的倾斜性保障,可能会激发民众的不满和反对。
最后,行政权力对于自愿戒毒运行的过度干预可能导致对戒毒人员权利的不当限制。一方面,《禁毒法》第37条赋予医疗机构对于戒毒人员检查、采取保护性措施的“准执法权”。但是,对于戒毒人员的权利保障却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戒毒条例》虽然设置了权利条款,但从唯一的权利条款第7条的排列位置及所适用的术语来看,仍然体现了对吸毒者控制的特征。另一方面,该条规定了医疗及机构发现戒毒人员在治疗期间复吸的报告义务。此处的立法规定面临着一个伦理困境,医疗机构或医生向公安机关报告吸毒人员复吸,是否有违医生职业伦理和医疗保密原则?对此,应当予以充分考虑并妥善平衡。
三、我国自愿戒毒制度的变革与完善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发现,当前自愿戒毒制度既与其他戒毒措施存在天然紧张关系,也背离了充分发挥社会戒毒医疗资源的立法原旨。但是,从运行效用上看,自愿戒毒制度有其不可忽视的正面价值:“药物依赖者的内在戒毒动机是发生改变的真正动力与关键因素。”[6]吸毒人员自行到具有戒毒治疗资质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充分表明吸毒人员自己有戒断毒瘾的决心和意愿,不仅可以消解强制性戒毒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有利于动用社会医疗资源参与戒毒工作。对于目前的制度架构需要从立法、政策、措施等多个维度作出修正,方能使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设置自愿戒毒制度前置许可程序
关于自愿戒毒与强制性戒毒之间的紧张关系,无论是《禁毒法》出台前的立法缺失,还是《禁毒法》出台后的立法缺陷,自愿戒毒之所以极易干扰正常的强制性戒毒执法活动,进而成为吸毒人员逃避法律的避风港,主要源于自愿戒毒制度缺乏前置许可程序,其与强制性戒毒完全分裂于两个独立的系统,前者属于开放化的社会医疗系统,由卫生行政机关主管,后者则由公安机关或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即使公安机关要将吸毒人员进行强制隔离戒毒,也会因为其已经选择进行自愿戒毒而作罢。因此,一方面,为了避免《禁毒法》第38条中的人员通过自愿戒毒脱离强隔离戒毒系统,要对自愿戒毒制度设置一定前置许可程序,由公安机关审查同意后方可进入。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公安机关滥用审查许可权,变相压缩自愿戒毒适用空间,在立法中应设置一定的刚性规范,通过“应当允许”和“可以允许”等立法技术的运用,细化不同类型吸毒人员的处理权限,约束公安机关的许可权。
具体而言,建议进一步细化《禁毒法》第36条、《戒毒条例》第9条关于适用自愿戒毒的规定,既要体现赋予自愿戒毒合法地位,充分利用社会医疗资源发挥其戒毒作用的立法意旨,也要对其存在的病人依从性差、执法“避风港”等负面风险给予充分估计,相应地设置限制性适用规定。具体而言,《禁毒法》第36条和《戒毒条例》第9条应明确为:吸毒成瘾人员主动要求自愿戒毒的,必须由公安机关审查同意后方可进入指定医疗机构。其中,尚未被公安机关发现的,应当允许;对于已被抓获或适用其他戒毒措施期间的吸毒人员,可以允许;对于允许适用自愿戒毒的,应当免除治安处罚和强制隔离戒毒。[7]
(二)允许自愿戒毒者进入强戒所戒毒
《禁毒法》第38条和《戒毒条例》第25条规定,对于自愿戒毒人员,“经公安机关同意,可以进入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戒毒”。虽然立法表述具有一定模糊性,但是,安徽、吉林、湖南等多省份已经允许接收其入所进行戒毒。其中,安徽作为首创自愿强制隔离戒毒模式省份,采取与吸毒成瘾人员签订协议的方式,戒毒期限、措施等均由双方约定。[8]
首先,允许自愿戒毒者进入强戒所戒毒从立法规定落实到具体政策上有一定必要性。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有较好的治疗设备、专业人员、戒毒经验和必要的环境。同意吸毒成瘾人员自愿进入强戒所戒毒,有利于充分利用好、发挥好强戒所在戒毒工作中的作用。[9]但是,一旦同意其进行强制隔离戒毒,即在公民行使选择权后,国家公权力已经做出了意思表示。此时,国家意志应优先于当事人意志得到保障,依法按照强制隔离戒毒的有关规定对其进行戒毒治疗。部分省份采取协议制方式进行强制隔离戒毒,在戒毒期限、措施等事项的决定上混同于普通医疗机构的自愿戒毒模式,这种模式是否值得推广或上升到法规范层面,似可再做斟酌。《禁毒法》关于整合戒毒资源的立法设计,旨在统一国家戒毒康复体系,但是,这种“统一”并非是不同戒毒措施的“完全融合”,恰恰是推动差别较大的戒毒措施的“外在衔接”。
其次,对于自愿到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戒毒的人员,不宜入库登记和动态监管。如果登记管理,纳入“吸毒人员数据库”,有利于实现对重点人群的动态管控,但其不良影响也同样显著。因为,一旦登记入库,该类人员就会被公安机关作为重点监控对象,尤其是会随时受到公安机关“强制尿检”的干扰。“涉毒标签”将对于他们正常生活和回归社会的自信心有极大影响,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刘文忠现象”就是涉毒信息管理模式弊端的最佳实践注脚。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于自愿到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戒毒的人员,应取消对其动态跟踪管理,减少对吸毒者回归社会过程中的歧视。如果将这种价值观念落实在具体制度上,《禁毒法》第38条和《戒毒条例》第25条应明确:主动、自愿到强戒部门进行戒毒的人员,不应该对其进行信息登记,无需纳入“全国吸毒人员动态管控系统”。但是,由于这类涉毒人员毕竟属于“重点人口管理制度”中的“七类重点人员”,为防范完全脱管,可考虑“在公安机关内部专门建立台账,录入自愿戒毒人员信息系统”。该台账不与动态管控系统联网,不会触发警报,可以根据戒毒人员实际的戒毒效果、主观态度、社会危害性等进行“升库”和“出库”。
(三)适度放宽对自愿戒毒的公权干预
我国自愿戒毒制度在过去“一放就乱”,始终面临如何管理医疗单位、规范医疗行为,保障自愿戒毒者作为病人的权利等问题,但是近年来随着各种严管措施到位,又存在“一管就死”即萎缩消亡的危机。
第一,对于自愿戒毒机构的宣传活动确实应该予以干预,防止出现非法刊登广告、虚假宣传等现象。中国二百多年的禁毒史也在警示我们: “毒品经济”及其渗透,不仅难以遏制毒情,反而可能把禁毒工作引入歧途。[10]但是,干预和规制不代表全盘禁止,既然要发挥社会医疗资源在戒毒工作中的作用,必须要尊重和承认社会医疗机构正常的市场运营方式和规律。戒毒医疗机构除地区精神卫生中心下设的自愿戒毒中心、医院、科室外,还有许多民营半公益性质的戒毒医院,在暂不将自愿戒毒纳入医保体系的前提下,应该适度放宽对自愿戒毒市场准入、医疗宣传等限制,以保障戒毒机构在公益性目标的前提下,适度参与市场运作,维持其正常的运营。第二,毒瘾广义上属于精神病范畴,毒品成瘾者、酒精成瘾者在医学上属于精神病患者。但是,我国的药物性精神病患者尚未纳入《精神卫生法》,吸毒人员与精神病患者在政策处遇上也没有通盘考虑。有部分学者指出,自愿戒毒在程序方面与精神病治疗非常相似,对戒毒者可以参照对精神病人的管理办法进行管理,既对其权益予以限制,也加以保障。[11]第三,如前文所述,将自愿戒毒费用纳入公共卫生医疗保障体系,目前尚面临较大的合理性质疑,在尚未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不宜盲目推进。但是,对于自愿戒毒部分医疗费用、替代药品可给予一定幅度的财政补贴,减轻戒毒人员的经济负担,彰显国家鼓励吸毒人员自行戒除毒瘾的基本立场。
四、余论
相较于其他部门法学,禁毒法学在名称上就体现了国家鲜明的态度和立场,彰显了父权主义国家伦理观。简言之,“禁毒”本身就蕴含着“权力”属性。这种行政高权体制会导致公有资源的集中化和公权化,对于打击毒品违法犯罪等工作有较好的效用,但却难以灵活应对戒毒以及毒品预防、宣传、教育等需要社会化的工作。自愿戒毒制度创设初衷在于弱化这种国家强制力,尊重吸毒人员内在的戒毒意愿,利用社会医疗资源进行“自我救赎”,既有利于减少强制性和封闭性的戒毒模式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有利于形成戒毒社会化的氛围。但是,自愿戒毒措施的立法干预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慎重考查整个戒毒体系的协调和衔接,也需要认真反思自愿戒毒本身的价值和定位。禁毒法学作为部门行政法学,自愿戒毒制度发展所面临的艰难转型,恰恰映应了当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变迁,“现代行政法的机制是由双向制约、双向激励和双向协商整合而成的,”[12]既包括权力与权力的平衡,也包括权力与权利的平衡。就自愿戒毒而言,一方面,要确保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平衡,即强制性戒毒制度与自愿戒毒之间不能发生混同,应该有机协调衔接;另一方面,要确保权力与权利的平衡,即国家戒毒强制权不宜过度干涉公民戒毒选择权,避免自愿戒毒的成长空间因过度干涉而萎缩。上述两个方面既是自愿戒毒制度常态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整个戒毒体系内在规范的必然要求。
[1]姚建龙.禁毒法与戒毒制度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p38
[2]郭建安,李荣文.吸毒违法行为的预防与矫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p233
[3]王锐园.吸毒者自愿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情形应如何处理[N].人民公安报,2016-11-7(05)
[4]王瑞山.论我国自愿戒毒的现实困境及制度完善[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p51
[5]刘剑文.理财治国观——财税法的历史担当[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p31
[6]赵敏,张锐敏.戒毒社会工作基础[M].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11年,p103
[7]靳澜涛.现行戒毒体系的运行偏差与本位回归——关于修订《禁毒法》第四章 “戒毒措施”的建议[J].公安研究,2017年第4期,p89
[8]魏亚东,钟虹新.自愿签下“协议”,就能免费戒毒[N].新安晚报,2014-6-9(B02)
[9]安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p114
[10]靳澜涛.我国毒品治理政策的检视与进路——以毒品合法化争议为起点[J]. 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p91
[11]褚宸舸.中国禁毒法治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p116
[12]靳澜涛.行政法平衡理论新探[J].行政与法,2017年第5期,p80-81
[责任编辑:陈光军]
Anomie and Norm of Voluntary Detoxification System in China
JIN Lan-tao
The voluntary detoxification was given the legal status by anti-drug law firstly,which was further refined by drug rehabilitation ordinance and listed as a chapter, becoming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drug rehabilitation system.Anti-drug law and drug rehabilitation ordinance have given sufficient estimates and made corresponding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s. However,the legislative intervention of it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which requires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coordination and cohesion of the whole detoxification system, and also needs a serious reflection on the value and positioning of the system itself. From the above two dimensions, on the one hand, there are no necessary norms about voluntary detoxification and compulsory isolated detoxifi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excessive power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does not accord with the value concept of social medical resourc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legal position of the voluntary detoxification system, straighten out the applicable conflicts between the rehabilitation measures, and balance the concept of socialized drug rehabilitation and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voluntary detoxification; anti-drug law; drug rehabilitation ordinance; compulsory isolated detoxification
D920.4
A
1674-8824(2017)03-0046-06
靳澜涛 ,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海淀,邮编: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