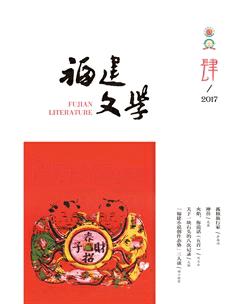火焰,你说话(五首)
刘立云,1954年12月5日生于江西省井冈山市。1972年12月参军至福州军区江西省军区某部服役,1982年毕业于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哲学系。1984年调北京总政解放军文艺社《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工作,历任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解放军出版社文艺图书编辑部主任。在《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十月》等刊物发表大量诗作,出版诗集《红色沼泽》《黑罂粟》《沿火焰上升》《向天堂的蝴蝶》《烤蓝》《生命中最美的部分》《眼睛里有毒》(台湾),长篇纪实小说《瞳人》,长篇纪实文学《血满弓刀》《莫斯科落日》等十余部。曾获《诗刊》“2008年度全国十大优秀诗人”奖、《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十月》年度诗歌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全军新作品特殊贡献奖等。诗集《烤蓝》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慕士塔格峰
从海拔3100米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往回走,是一个接着一个下山的台阶
当苏巴什达坂淡为身后虚无缥缈的
一道辙印,天空和大地各就各位
刚刚还戴着一顶白帽子,在车窗外蹲伏的慕士塔
格峰
拔地而起,顿成天地间的一根银色栋梁
慌忙回头看,慕士塔格峰已高过天堂
高过神话和诗歌的屋脊
而众山匍匐,甘愿当它的座椅
天际飘浮的云被它一手扯来擦汗和束腰
那种当仁不让坐在众山之上
和云朵之上的
气派,告诉我它曾经沧海
曾经把亿万年的积雪,坐成天老地荒
而我想,我顺着它宽阔的肩膀用半个小时
从高处回到低处
它是否视我如一朵飞絮、一粒尘埃
三 亩 江 南
苦心自知。对这片在高寒中孤守的土地
这片冰雪孵化千年也只孵化出
石头和盐碱的冻土
他们说,我要的不多,只要三亩江南
只要有三亩江南,他们说,他们就能用这
三亩江南的绿,治疗眼睛里的那片
无边无际的白;只要有三亩江南的根茎和叶片
还有它们的维生素和叶绿素
他们就能筑一座大坝,挡住身体里的
崩塌、沉陷,和天天到来的水土流失
我的天!连石头都被冻伤冻裂了
土壤因冻得大面积坏死
而需要给它们换一个肾,需要从远方运来新鲜的
泥土
给它们透析,清除血液中的毒素
你说,还有什么能阻挡这群被白雪刺瞎过
眼睛的人?还有什么比被稀缺的氧谋财
害命,更让他们痛彻肺腑
并发誓要推开春天的门?就是这样,他们垒土筑
墙
愚公移山,为这片土地建造了三亩房屋
三亩地热,给菜地穿上了一双保暖的袜子
而作为另一个哨位,那个负责播种的小伙子
那个在高原服役了十八年的士兵
把自己也种植在那座玻璃房子里
常听他独自喃喃,他说:茄子、辣椒、白菜、西
芹……
现在请听好了,现在请你们跟随我的指令
按照江南的节气开花,按照江南的时令结果
后来,那些花果然都开了,那些叫黄瓜
冬瓜、西葫芦……的果实
果然结得像江南那样丰饶和壮硕
再后来,那三亩江南和它蓬蓬勃勃生长的
青翠和碧绿
打败了十万乃至百万亩风雪的怒吼
雪山上的三匹狗
三朵奔跑的雪,三段蠕动的山脊
三团火焰在徐徐燃烧,带来
阳光的消息和祝福
三只降落的鹰收敛翅膀,以慢镜头的速度贴地
而行;或者,我还可以把它们
称为士兵、哨所的侦探
信使,和门客、神秘的第五纵队
只能这样。我在此使用的这些词汇
已經够节制够煞费苦心了
但最终我还必须说它们是三匹
狗,那是因为我被它们的本性
和天性,感动并征服了
我不否认我喜欢它们,对它们充满柔情蜜意
体恤和怜悯,类似一个父亲爱他
苦命的闷声不响的儿子
是因为它们出身卑微,非高贵的黑贝
藏獒、拉不拉,亦非真正意义的
警犬,甚至从未被列入名册吗?
也许吧。但我坚称它们三匹狗,肯定还有
匹夫、匹敌、匹配,或者把它们
比喻为关云长胯下骑着的那匹
赤兔马的意思
不行吗?你看它们毛发光亮,奔前跑后
总是在该出现的时候出现
该消失的时候消失,模范地遵守着
狗的守则;从不摇尾乞怜,也不为争抢一根骨头
咆哮、怒吼、厮杀,相互打得
天翻地覆或抱头鼠窜
更多的时候它们各负其责:一匹
跟着哨兵上哨,另两匹自觉地蹲在营房门前
高高的台阶上,目光里长出两枚钉子
静静地望着远处的雪山、道路
口岸,从天空偶尔飞过的
乌鸦,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居高
临下,整天蹲在法院门口的那对石狮子
我知道高山缺氧,哨所的官兵每三周
轮换一次。要知道驻守在这里即便是
坐着、躺着,胸膛也憋闷得
喘不过气来,如同一只被踩扁的空空的易拉罐
但它们的轮换周期是,从生到死
这让它们的肝肿大,脾肿大
肺叶肿大,退化的听觉、味觉和嗅觉
就像被一把隐秘的刀反复削过
唯有那颗肿大的心脏,让它们不离不弃
保持着狗的气节、尊严
以及永远不用来兑现和交换的忠诚
就像那天,当我们从山那边巡逻归来
它们奔袭三公里赶来迎接
那种别后重逢的亲切,那些眼睛在长久忍受焦灼
之后
盈满的泪水,分明在说:
亲啊,沿途雪深路滑,你们都好吗?
阿米亥,阿米亥
前英军犹太人支队的士兵,后希伯来文
和圣经的卫道士,1942年你趴在
阿尔卑斯山下的哪座街垒
向纳粹射击?当“他们用钢铁制造出更多的炮弹
用我的叔父制造出新的叔父”……
总是如此。你至今还记得浸泡在积满雨水
的战壕里,那些呈各种姿势倒卧的
孩子,尸体已经腐烂,发出一阵阵恶臭
但他们血统高贵,种族优雅
蓝色的眼睛深不可测
一头漂亮的金发,是用源远流长的傲慢染出来的
而搭在扳机上的手指,至死未松开
辨认因此变得更加艰难,更加诡异
比方说,在广场上汹涌的人群中
在皇家大剧院金碧辉煌的包厢里
你能看清谁是心怀鬼胎的
那个?谁是把身体掏空用来装填TNT的那个
或许他们还会借尸还魂,在某一天鬼鬼
祟祟,就像吐着毒信子的蛇
从我们自身的欲望中,探出头来
那么他是谁?长着怎样的一副身子
怎样的一颗脑袋
因为找不出答案,所以你每天都在反躬自问
每天都腾空身体,对世界说:
来啊,来啊,“和平,请进入我的心。”
火焰,你说话
火焰烧着了她的身体、她的头发和她的嗓音
凄絕的美就缺这样一个尾声了
把星空推远
此时她唯一要做的,就是追上她的灵魂
“火焰,你说话!”她孤独地站在舞台中央
以枯树之姿,危岩之姿,一道闪电
劈开乌云,让天空崩裂
说完最后一句台词
台下的每一颗心都在震颤,每一双眼睛都看着她
把彤红的火焰,穿在身上
就像许多年前,她反复把朝露、云霞和海浪
穿在身上
那么老还那么美!她火焰裹着的身体
历经炉火锤打的嗓音
明亮,纯粹
就像一朵花盛开到把自己生生
胀破,一块铁燃烧到融化并汩汩奔流
然后她缓缓倒下,世界寂静如水,黯淡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