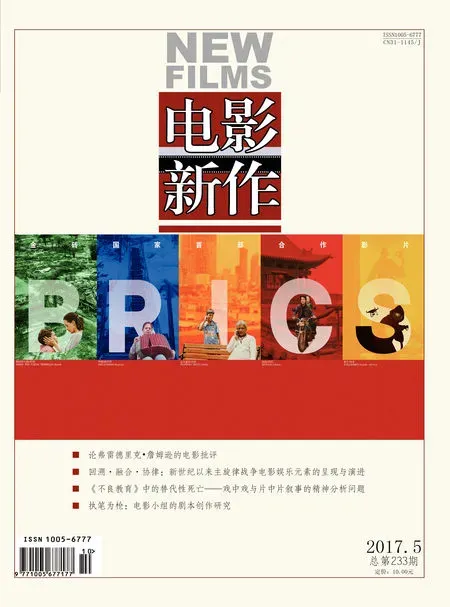从《催眠大师》到《记忆大师》
——叙事风格的延续与类型创作的深化
张婷婷
从2005年个人执导的第一部长片作品《宅变》开始,陈正道就与悬疑类型片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在这之后的近十年间,他凭借《盛夏光年》《幸福额度》《101次求婚》等爱情片给自己贴上了“清新”“温暖”的标签,但始终无法抛却内心对悬疑惊悚类电影的钟爱。2014年,《催眠大师》这部高票房、高评分、斩获多项华语电影大奖的成功之作在这位青年导演的创作历程中书写了浓重的一笔。2017年,带着观众和影评人更多的关注与期待,陈正道携新片《记忆大师》再度披甲归来。自公映伊始,该片所显示出的话题热度就屡增不减,关于导演“个人化”风格的争论和评判也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笔者有鉴于《催眠大师》与《记忆大师》之间的相似点与不同处,试图对导演创作的类型风格做一个细致的鉴定与解析。
一、非复制式延续的叙事风格
从《催眠大师》至《记忆大师》,陈正道执导的悬疑电影愈发具有可辨识的类型风格:表现为对某些叙事方式和造型元素的执著与偏爱。由于两部影片在具体的悬疑类型上的区分度(见后文详述),笔者将这种风格在两部电影中的彰显定义为“非复制式”的延续方式。
(一)梦境编织下的悬疑叙事
对悬疑片来说,“认同”问题是电影与观众进行沟通所依赖的基本方式,并且这种身份认同会分为两种形态:当电影采取全知视角操纵摄影机的运作时,观众只能看到导演安排他们看到的部分,即“客观镜头”;当摄影机以故事内人物的视角表现其所见、所闻、所想,或是以人物的精神状态、心理变化来引领观众,此时观众便获得了指向主人公认同的“主观镜头”①。在大部分悬疑片中,观众往往以“窥视者”的身份,通过导演安排的镜头视角达成对主人公潜意识的认同感,观众掌握的信息与主人公得知的信息持平甚至更少,这种有意为之的“信息截留”所形成的悬念使观众产生强烈的期待意识与情感波动,进而陷入电影编织的“叙事圈套”中去。

图1.《催眠大师》
陈正道的这两部电影都将梦境的编织作为转换情节、推动故事进程的主要方式,并以限制视角为主、全知视角为辅,采用彼此杂糅的套层结构,以视点的多重变幻造成关键信息的延宕,从而处处搭建悬念、制造疑点。《催眠大师》前三分之二的部分主要采用徐瑞宁的主观视角来审视任小妍的病情,即便其中穿插着任小妍被催眠后的梦境,观众也以徐瑞宁的身份对此保持一种旁观者的姿态。与此同时,影片巧妙地安排了一些关于徐瑞宁的细节以铺设悬念,例如方教授坐上汽车副驾驶时他的紧张感、他对水的惧怕、他手臂上的刀疤等,预示着这一人物背后的故事与主干情节之间的神秘关系;影片最后三分之一的部分变为以方教授为中心的治疗团队对男主角施以催眠疗法的全知视角,在实现故事情节大反转的同时,对徐瑞宁的心理疾病、任小妍的身世,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做了完整的交代,使观众从一种朦胧的、不确定的认知状态中脱离出来,获得谜题破解、情绪得以宣泄后的满足感。
相比较《催眠大师》以催眠的外在形式实现碎片化梦境的堆积,《记忆大师》主要依靠梦中记忆重载的方式来控制信息的落差,只不过后者在设置悬念时,故意将两宗发生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对象的罪案以及两个人不同的过往回忆交叉剪辑在一起,造成了视点的重影与疑点的混乱。影片以先入为主的限制视角迫使观众将江丰的经历、思想视为认同对象,这一身份认同在主人公随即遭受到的生命危机中被赋予了自愿与同情的意味,接下来,影片的叙事重点落在了查明真凶这一极具解谜性质的过程上。观众既能代入江丰视角跟随他在睡梦中回忆“自己”杀人的过程,又能切换成外视角看到导演安排的其他事件或细节,例如陈姗姗刻意接近张代晨的行为、沈汉强对待流氓无赖的父亲的态度等,这些零散的信息聚合在一起,在逼近真相的路途中加剧了故事的惊悚氛围与观众的好奇心理。
整体而言,梦境是两部影片相似的特色,在梦境与现实的联系与比照下,导演巧妙地运用视角的转换与并置构造悬念,通过超现实的情景衔接、交叉蒙太奇的画面剪辑,一步步推动情节的发展与真相的露面,也在解疑推理层面与观众实现了积极的互动。
(二)非线性的破碎化叙事
破碎化叙事是源于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创作手法,既可描述外部世界,也可表达主体性感受。它往往将一堆零散的叙事碎片按照已有的叙事目的组合在一起,在看似无序的叙事结构中形成一定的戏剧张力和特殊的艺术风格。与讲究“故事的完整性、时间的连贯性、情节的因果性”②的线性叙事不同,非线性叙事在纷繁复杂的叙事线索、颠倒错置的叙事时空,以及支离破碎的叙事情节背后,包含着对世界的无序性与不确定性的独特演绎。陈正道的这两部电影均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叙事或曰破碎化叙事的特点。
由于“反复催眠”与“记忆重载”的预先设定,两部影片注定将打破线性时间观念,以影像的刻意剪辑与交叉拼贴来组合故事内容,再加上“做梦”这一非理性的潜意识活动,影片不得不摒弃传统电影的戏剧化章程,而采用“拼图式”的情节组合模式。因此,引入反差强烈的色彩作为分割现实与梦境的界限就成为一件必要之事。在《催眠大师》中,导演不仅用色彩的变换来标示不同的时空,还以冷暖色调的区分影射人物的心理倾向与精神状态,而《记忆大师》则更纯粹地使用了黑白与彩色两种色调分别代表现实与梦境两个不同的时空。相同的是,两部电影皆是现实世界采用线性叙事,其中又融入了大量的插叙、倒叙的记忆片段,不论是“催眠”还是“记忆重载”,都需要暂时打断现实中的故事进程而进入另一个时空的叙事层面,且梦境中场景发生的先后并不遵循现实中的时间顺序。它们往往与做梦者的个体经验、情感诉求复杂地缠绕在一起,一些关键性的信息还通过闪回的方式数次再现,导演正是通过破碎化的叙事片段的积累搭建起故事的核心框架,并运用超验结构的逆向叙事挑战传统的审美经验。
如前所述,这种破碎化的叙事方式与后现代主义文化密不可分,正如美国当代理论家哈桑所说:“后现代主义的两个本质倾向,即不确定性和内在性……解构、消解中心、分裂、消解定义、非神话化、零散性、反正统化……”③而在这种反传统、反理性思想的引导下,最先长于破碎化叙事并将其发展成一股电影潮流的,是以张元、王小帅、贾樟柯等人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他们常常以回环、交错或并行的时间结构,缺乏逻辑、视点杂糅的视角安排,以及混沌的、非同质性的空间造型,共同打造出影片不连贯的、破碎化的叙事特征。但二者所具有的本质上的不同在于:在躁动、迷惘的后现代语境中,拒绝乌托邦主义的第六代导演试图以这种看似消极的方式对边缘弱势群体的生活与命运进行表述,从而反映出社会文化结构的不稳定性与人们精神世界的无力感;而陈正道对破碎化叙事的把握显然更具有商业类型片的特征,从悬念的设定、逻辑推理的序列和观众的接受心理上看,这种叙事安排无疑能够最大限度提升影片的紧张气氛与吸引力。
(三)情境化的封闭空间叙事
作为一种时空一体的综合艺术,“时间的流变和空间的转换,在电影中有着无穷的潜力,而这正是电影叙事的重要条件和基本特征。画面是片断的,依靠剪辑技巧构成完整的时空复合体,创造一种非连续的连续性,画面又是整体展现,能指和所指呈共时性存在,空间词语成为主要语言手段。”④换言之,电影不仅依靠时间叙事来构建故事的逻辑,还需要通过直观的空间叙事来表现富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并成为影像的感染形式。在现代电影中,“封闭空间”是电影空间的重要类型,它指一部影片的叙事空间具有相对封闭和隔绝的特点,人物的视野与行动被限制在狭小的场景内,进而营造出一种惊慌、压抑的心理感受。陈正道的“大师”系列电影对封闭空间有着特殊的偏爱与表现,与希区柯克电影对空间含义的情境化处理类似,他也善于利用人类对封闭空间的恐惧感与无力感来烘托影片的悬念气氛。

图2.《催眠大师》
电影中的空间之所以能产生不同于现实空间名称的其他意义,在于它们在情节和表演中被赋予了某种新的实质性内涵。从以下几个空间艺术元素来看,《催眠大师》与《记忆大师》在封闭空间的叙事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光线运用上,二者都布置了大量的阴郁、幽暗的空间,比如《催眠大师》中可以听到弹珠声的阁楼、坠湖后进水的汽车内部,《记忆大师》中警局关押犯人的牢房、李慧兰遭遇丈夫家暴的客厅等等,并都以高反差的光影对比营造出氛围的层次感。在场景布置上,二者都采用了大量具有心理暗示意味的道具或装修风格,比如《催眠大师》中古旧的诊疗室中错落有致地摆放了各类的家饰,营造出一种空间上的局促感与格局上的纵深感,墙面上悬挂着的欧普图案的壁画、带有波纹或几何图形的地砖造成视觉上的眩晕感与闪烁感,天花板上的蜘蛛吊灯、螺旋形状的楼梯、卫生间里被多重切割的镜子均渲染出影片的恐怖氛围;《记忆大师》中设有放满水的大型浴缸、倒地的巨大的女人头像、蜿蜒透明的长廊形监狱、精密复古的发条齿轮,以及屡生不幸的花房(其原型是曼谷著名的鬼屋绿房子),这些都服务于心理恐怖片有关于道德沦丧、人性危机的黑色主题。总之,在陈正道的电影中,封闭空间作为具有意指性的元素是物质与心灵的重叠体,其隐喻性修辞的着力点往往是处于特定情境中的主体的内心世界,以此来加深观众对人物形象和思想道德的认知理解。
二、类型创作的开拓与深化
(一)从心理悬疑片到犯罪悬疑片
根据题材或技巧的差异,电影可以形成歌舞片、喜剧片、西部片、悬疑片、恐怖片等多种形态。其中,悬疑片的兴起与20世纪中后期以来精英文化和古典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型密切相关,由于消费化、娱乐化、平民化代替传统的理性说教成为影视传媒的主要诉求,能够满足观众的好奇心理、释放其负面情绪的商业悬疑类型片便应运而生了。在具体的影视创作中,悬疑往往与惊悚、惊险、犯罪、情感等类型元素相杂糅,形成风格各异的种类,例如惊悚悬疑片《我是证人》、推理悬疑片《嫌疑人X的献身》、犯罪悬疑片《烈日灼心》等。陈正道的两部电影无疑是多种类型元素混合而成的产物,《催眠大师》倾向于心理悬疑片,而《记忆大师》则与犯罪悬疑片的相似度更高,它们共有的类型特征是利用惊险刺激的情节和极具感官冲击力的视听形象来制造惊悚体验,除此之外,前者主要着眼于当下普通人的创伤性记忆,并以梦魇的方式揭开心灵深处那蕴藏着巨大心理危机的伤疤,具有一定的哲学思辨色彩;而后者更多地将梦境利用为寻找真凶的途径与方法,通过还原凶手的人生经历探讨犯罪背后的人格缺陷与社会问题,具有批判现实的意义。
在具体的类型搭配上,如上所述,《记忆大师》与《催眠大师》最大的不同在于引入了科幻、犯罪的类型模式,延展了影片的时代内涵且彰显出一定的问题意识。不同于《催眠大师》将源自于古希腊神话的催眠术作为叙事建构中的关键性一环,以“软科幻”的情节设定作为宣传中心之一的《记忆大师》无可厚非地具有现代科技社会的特征。名为“记忆大师”的2025年未来式医疗中心、具有几何构图特色的明亮的医院大厅、环绕着各类精密仪器的手术台,都作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视觉手段参与调制了影片的科幻色彩,且主人公穿行于梦境与现实的中介是依靠记忆实感手术而非先前借助于催眠这一传统方式,二者在某种程度上便具有质的差异性——后者更多地融入了导演对未来科技发展的向往。

图3.《记忆大师》
不过,《记忆大师》严格来说并非一部合格的科幻片:在最开始主人公被施以记忆删除的手术场景后,影片就近乎放弃了使“记忆大师”大力发挥其科幻性能的机会。其以“软”作修饰的科幻身份除了为记忆重载的情节设定提供合法性基础外,大概只能在影片宣传环节作为吸引观众的附加筹码。相反,影片在故事节奏上可以说是迅速地进入了犯罪、推理的叙事进程:主人公因拿错记忆在梦境中还原出两宗错综复杂的杀人罪案,并使自己和爱人的生命安全暴露在危险之下。在编排剧情线索时,“误导性”机制的设置和“遮蔽性”主观视点的运用使“追查凶手”的过程一波三折,而借助于梦境重现和记忆重载的超现实手段,主人公的生活与经历、罪犯的杀人动机与真实身份也纷纷浮出水面。如果说《催眠大师》对真相的解谜是凭借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和主人公之间高级抽象的智力游戏,那么《记忆大师》除了延续其依靠复杂的叙事结构和叙述视角而建构的叙事迷宫,更多了由犯罪、冒险、性与暴力等商业元素共同打造的视觉奇观。此外,《记忆大师》还通过塑造因为童年阴影和恋母情结导致心理变态的杀人犯——沈汉强的形象,试图对犯罪背后的人性和历史文化因素进行透视和反思,这正印证了希区柯克在1947年的好莱坞新闻发布会上的言论:悬疑电影可以被视为是对“麻木”的人性和“具有保护性的”文明的双重“撞击”⑤。
(二)从被动到主动的情感救赎
电影的类型,总是体现出对不同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心理的影射,而观众对不同类型的电影产生不同的心理体验与情感需求,说到底也是因为它们在题材和艺术表达上的组合能够集中于人类生存中某些悖论式的困境。因此,伦理叙事,作为最直接地展现人与外界之间的社会性关系和人类对道德现象的哲理性思考的产物,就与不同种的类型电影均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好比武侠片一直以来广受国人欢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人们对狂暴武力与血腥场景的偏爱,而在于承载着“侠义精神”的打斗过程向观众提供了“人物成长”“惩恶扬善”“意识觉醒”等积极的情感暗示,所以将能够迎合观众审美需求的伦理表达作为叙事的重要线索便成为这类影片的较好选择。同样,悬疑类电影虽然以情节的跌宕起伏作为主要的内容特点,但正是人物关系、命运等情感信息才是观众期待和关切的因素。在《催眠大师》与《记忆大师》之前,陈正道曾执导过多部爱情片,在电影的情感表达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而在这两部悬疑电影中,对伦理道德和情感的叙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核心要素。不同于大部分国产悬疑片只是简单地展现“疑神疑鬼”式的镜像和惊险刺激的力比多色彩,陈正道善于迎合中国观众传统的情感诉求与审美经验,将人们对于心理疾病和恐怖犯罪的心理体验转化为影片节奏的内在驱动力,并将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潜意识、梦思维、恋母情结等元素与影片的叙事内容结合起来,不断开拓出极具现实伦理意味的超现实主义题材。
从人物设定和情感建构上看,《催眠大师》和《记忆大师》都刻画了深情脉脉的男主人公形象,且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恋爱/婚姻关系成为影响男性的思想与行动的主导因素。徐瑞宁因酒驾致女友与好友死亡而深陷自责、内疚的精神漩涡,置身于不被自己和他人原谅的双重绝望境地,甚至通过自残的极端行为缓解内心的痛苦与压抑,他在现实中自欺欺人地扮演着一名成功的心理治疗师,是为了掩饰自己潜意识中的畏惧感和孤绝感。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讲演》中将此类沉溺于过去创伤经历的人称为“创伤性神经症”患者⑥,我们不妨对这一人物形象做出如下理解:其背后指喻着现代社会人们内心不为外界所察觉的巨大精神危机,而这一危机的根源则来自于个人对约定俗成的伦理、道德的理解(曲解)与尊崇。可以说,徐瑞宁自身并不具备主动驱散心魔的自控力,他是在任小妍的一步步引导和治疗下开始正视过去,是在外力的谋划、推动下实现自我救赎的。令人遗憾的是,影片将大量篇幅用于对悬念的铺垫和渲染,直到最后才以解密的方式披露出部分情感镜头,微弱的感情线索不足以支撑起影片企图揭示的伦理内涵,受害者(任小妍)对犯错者兼忏悔者(徐瑞宁)施予的温情与关怀亦缺乏合理的说服力。

图4.《记忆大师》
同样着眼于困境中的自我解救,《记忆大师》更强调了主人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冲破异己力量的围追堵截的过程,同时在完善影片悬疑、情感的叙事链条上做了更充足的准备。江丰选择接受记忆手术是因为自己的婚姻遭遇到了中产阶级家庭危机的破坏:妻子被迫放弃事业、生育问题对夫妻二人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困扰。然而,医疗中心的突发事故使江丰阴差阳错地错拿了记忆,进而将自己与爱人纷纷推至了危险地带——他必须在脑海里还原出罪案的真相以自证清白,同时需要解救被凶手定为下一个目标的妻子。根据“记忆大师”的操作设定,凶手的记忆是强加于江丰的,江丰进入梦境时虽不是完全的自由人,但由于“自我—他人”两种记忆形态的对立性,他反而能获得一定的自主意识,且这种潜意识中的觉醒程度在清醒时所定目标的驱动下和现实紧急情况的刺激下会进一步加深,因此,江丰在凶手的记忆世界中会逐渐具备对时空、节奏,甚至内容的掌控力和行动力。值得注意的是,记忆力的对调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暴力/柔情对个性的渗透,如江丰表现出的打人、吞刀片等暴力倾向,罪犯沈汉强在最后时刻唤醒了记忆中江丰对妻子的爱而不忍下杀手。总之,正是爱的力量推动着江丰在梦境中主体性意识的显现,并以柔情对暴力的置换阻碍了凶手的杀人行为。在情感叙事上,《记忆大师》也明显比《催眠大师》更胜一筹,影片增强了夫妻情感线索的构建,通过几次恰到好处的闪回镜头基本交代了二人初见、相爱以至婚变的原因,并通过最后“大团圆式”的结局使故事归于秩序和平衡。

图5.《催眠大师》
结语
相较于大部分充斥着阴森恐怖的噱头和粗制滥造的情节的国产悬疑电影,陈正道倾力打造的《催眠大师》与《记忆大师》可谓无愧于观众喜爱的诚意之作。二者最大的价值在于,都能构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异常场面——“入梦”,它不仅可以参与剧情叙事、控制观众的心理走向并调动其观影兴趣,甚至能够在更深层次上影响人们对隐藏在心灵深处的非理性症候的认知。在访谈录中,陈正道曾明确表示过“想做类型片导演”“想每一次都尝试一个新的类型”⑦,《记忆大师》的确也展示出与前作不同的类型元素与主题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国产电影的类型化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贵的参照点。
【注释】
①[法]克里斯蒂安·麦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M],王志敏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52.
②杨世真.重估线性叙事的价值[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51.
③[美]伊哈布·哈桑.后现代主义转折[M].转引自王潮主编.后现代主义的突破——外国后现代主义理论[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29.
④郦苏元.中国早期电影的叙事模式[J].当代电影,1993(06):30-36.
⑤[法]弗朗索瓦·特吕弗.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郑克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67.
⑥详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讲演[M],周泉、严泽胜、赵海强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233.
⑦陈正道,宋华.类型电影的多元化书写[J].当代电影,2014(12):7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