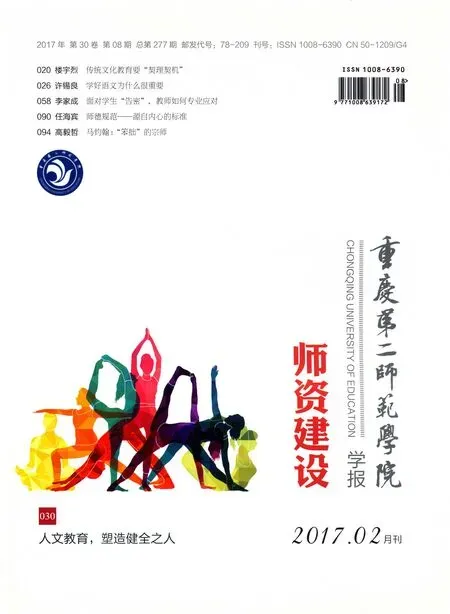明清以来贵州黑神庙分布变迁之成因探析
熊志翔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阳 550025)
明清以来贵州黑神庙分布变迁之成因探析
熊志翔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阳 550025)
明清时期,黑神庙在贵州地区分布广泛。从空间而言,遵义南部、贵阳、黔南一线数量较多;从时间而言,清代黑神庙数量要远多于明代。这种时空分布状况的形成,有多种神灵信仰的冲突、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但国家政权在各地统治的差异所导致的汉文化在各地传播的差异,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贵州;黑神庙;分布变迁;文化认同
黑神庙在贵州地区分布广泛,祭祀唐名将南霁云,“其香火无处无之”。[1]563-564不仅在贵州,其他地区也有关于黑神庙的记载。如湖南安仁县四忠祠,祀唐南霁云等四人;沅陵县南公庙,祀唐南霁云;辰溪县忠臣庙,一在县治东,一在岩屋田,旧名黑神庙,祀唐南霁云;黔阳县南公庙,祀唐南霁云[2]208-253等。明代黑神被纳入国家祀典,谥号“忠烈”。作为一方保护神,黑神在贵州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以致出现了“忠烈桥”[3]35、“忠烈街”[4]275之类的地名。不仅如此,在贵州与中央的互动中,黑神及黑神信仰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目前,关于贵州黑神信仰的研究尚不充分,成果不多。邢飞《贵州黑神信仰初探》一文考察了贵州黑神信仰的原因,认为“诸多记载中提到的南霁云‘显灵’贵州的神异事件”是南霁云在贵州得祀的根本原因。[5]王宏伟《试论明清时期贵州地区的黑神庙信仰》一文不仅考察了贵州黑神信仰的原因,还对贵州黑神信仰的来源进行了分析。王宏伟认为,黑神信仰主要来源于外来移民,是“移民之间文化交流的结果。”[6]高应达在其硕士论文中从黑神的起源、变异和社会效应三方面入手,考察了黑神信仰在国家、地方政府与民间三者之间的重塑,使之成为三者之间文化认同和权力调适的重要契合点。高应达认为黑神庙起源于少数民族的黑色土地崇拜,将黑神信仰文化看作少数民族文化,黑神信仰在传播过程中经过了四次改造、变异,最终达到了国家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统一。[7]而本文则认为,黑神起源于对汉人官员南承嗣的崇拜,黑神信仰主要是贵州区域文化的符号而不仅仅只是代表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当然,上述研究成果对本文的撰写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于贵州地方志的整理,目前在学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张新民先生的《贵州地方志考稿》系统整理了贵州各个地方、各个时代的现存以及亡佚的方志,并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在出版界,2006年巴蜀书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共50册。这些成果为我们研究贵州历史提供了方便。本文在贵州地方志的基础上对黑神庙的情况进行收集与整理,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明清以来贵州地区黑神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状况及其原因。
一、关于黑神身份的讨论
在地方志的记载中,黑神指的就是唐代将领南霁云。但是,从唐到明、清,黑神这一身份是否始终如一呢?这一点是有待商榷的。因此,在分析贵州黑神庙的时空分布之前,有必要先对黑神的身份进行讨论。
史载唐安史之乱中,南霁云在睢阳保卫战中与张巡、许远等人一同殉难。后来张巡、许远二人因为这次保卫战在全国许多地方受到人们的祭祀。但是与张、许不同的是,南霁云在贵州受到普遍祭祀,似乎与他在那场保卫战中的功劳无关。康熙《黔书》记载:“南霁云之得祀于贵阳,以其子承嗣之为清江太守也。”[1]523南承嗣在贵州地区为官时,“德政惠教,深入人心”[8]358-359,“黔之民爱其子而俎豆馨香以祀其父”。[4]266-267或者说,人们为了纪念南承嗣,提出要给他修建生祠,被其拒绝,但是表示可以替他父亲修建庙宇供奉。“人思其德,为立生祠,承嗣辞,命祀其父。后黔省通祀。”[9]79又或者说,南承嗣曾在贵州地区为其父立祠,几百年相沿成俗,“又或以其子曾立庙也,因相沿而俎豆之然”。更有甚者,“谓祀者即承嗣”[10]168,“或又谓神即承嗣也”。[11]128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笔者以为,最后一种说法较为合理。黑神最早是指南承嗣,后来才变成南霁云。首先,按照武雅士的“神、鬼、祖先”的观点,“所有的神都是官僚”,[12]146人们对神的崇拜其实是对官僚的崇拜。反过来说,一个好的官员如果得到百姓爱戴,人们也会对其供奉崇拜。南承嗣在贵州为官期间受百姓爱戴,在其离任之后,百姓为纪念他而立祠祭祀。百姓在生活中遇到不平之事,也愿意祈求清官做主。久而久之,南承嗣就被赋予了各种奇异功能。这种祭祀比单纯的爱屋及乌,因爱其子而祀其父的祭祀更容易使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得到心灵慰藉。其次,南承嗣表示可以为其父立祠也说不通。即使南承嗣有此表示,但是由于当时交通、通讯不发达,这一表示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人所知也是一个问题。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地百姓更想为南承嗣而不是其父立祠。第三,南承嗣在贵州为官时已为其父立祠的说法显然与第二种说法相矛盾。因此,黑神最早祭祀的是南承嗣,后来才转而祭祀南霁云这一说法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黑神的这种身份转换始于何时呢?根据现有资料,笔者认为,当在明景泰年间为南霁云赐谥的时候。尽管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有忠烈庙“洪武间都指挥使程暹建,祀唐忠臣南霁云”,但是事实上这很可能是后人的附会。南霁云景泰年间得谥“忠烈”,不可能在洪武年间就称忠烈庙。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所采用的说法是景泰后的说法。那么,所谓忠烈庙的祀主当然也就是南霁云了。另外,清人陈熙晋《南将军神祠曲》云:“黔人处处祀黑神,昉自何代前未闻。庙门大书忠烈字,人今知有南将军。”[13]370诗里包含两层意思:第一,黑神为黔省通祀,但不知始于何时。我们从以上分析中认为黑神大概始于唐代,“南将军庙曰忠烈,自承嗣始”。[9]79第二,赐谥之后,人们才知道有“南将军”。也就是说,在赐谥忠烈之前,人们不知道或者不确定祀主就是南霁云。由此可见,南霁云应当是在官方赐谥忠烈之后才正式“位列仙班”的。原始的黑神或者就是南承嗣,官方将其塑造为南霁云,原因很明显,南霁云的事迹更符合儒家意识形态的需要。这一点后文将会谈到,此不赘述。所以,本文接下来的讨论,都是在以南霁云为黑神这一前提下进行的。
为何称为黑神,明清以来的官员或地方志编撰者也是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其面黑,故而称为黑神。“土人以其长冠髯而貌之黯也,故曰黑神云。”[1]523-524作为一位生长于唐代且从未到过贵州的中原人士来说,南霁云面黑与否恐怕无人知晓,这很可能只是一种附会。清人张澍在对黑神塑像的描述中写道:“黝面长牙倒竖眉,狰狞怖怖人鼻欲敛。”[1]256唐代文学家韩愈对南霁云也有“勇且壮”[14]76的评价。在想象中,人们很容易将黑脸与威猛勇壮联系到一起,如《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水浒传》中的黑旋风李逵等。在广西,人们也将城破后不屈而死的元朝守城将领也儿吉尼称为黑神而加以祭祀。[15]另一种说法是,贵州简称黔,黔属黑色,故称黑神,即贵州的神。《说文》云:“黔,黎也。从黑,今声,秦谓民黔首,谓黑发也。”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比较有说服力。人们称呼南霁云为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黑神而不愿意称呼其为具有强烈正统文化色彩的“忠烈”,体现的是一种地方认同感,通过黑神这一贵州的神来增强贵州地区的内部凝聚力。
二、贵州黑神庙的空间分布及其成因
通过对贵州地方志的检索,我们发现,明清时期贵州黑神庙分布在贵州各地,共108处(见表1)。其中以遵义、贵阳、黔南这一线居多,三地共58处,占全省总数的一半还多。其他地区共50处,不到总数的一半。

表1 明清以来贵州各地黑神庙数量分布表
通过表1我们可以了解到,黑神庙分布比较密集的地区大部分在贵州中部,而东、西部地区则偏少。当然,这个数据是不完整的。首先,地方志记载不全。很多地方的黑神庙在地方志中没有记载,例如同样位于东部地区的铜仁,黑神庙只记载9处,不到遵义、贵阳、黔南等地的一半。毫无疑问,这是受了文献记载的影响而导致的人为缺失。记载铜仁地区黑神庙的地方志只有5本,而记载黔南、贵阳、遵义地区黑神庙的地方志则都是10本,由此可见,基于文献资料的记载所做出的数据分析,只能是相对的,不完整的。其次,与其他神灵信仰相冲突。以铜仁为例,该地区9座黑神庙仅分布在4县,其他地方没有关于黑神庙的记载。这是因为铜仁地区属于武陵地区,而武陵地区是飞山庙的信仰圈。武陵地区在贵州包括铜仁地区以及遵义的道真、务川、正安、凤冈、湄潭、余庆诸县。这一地区位于湘黔渝交界地带,飞山庙众多。[16]第三,政府政策的影响。黔东南地区的“苗疆六厅”在雍正时期由云贵总督鄂尔泰主持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土归流,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冲击非常大。尤其是大规模建造学宫、会馆等,“反映出‘开辟’苗疆之初,清廷急于改造苗疆的文化冲动”。[17]237因清政府急于推行“王化”政策,故而不可能通过推广黑神庙以达到贵州地域认同进而达到国家认同,而是直接推行能够代表中原文化的神祇,如观音、城隍、关帝等。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在政权统一之后一定要求意识形态的统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便成为历朝历代的官方意识形态,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展开而推行到全国各地。贵州僻处西南,一直与中央政府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羁縻关系。直到明代永乐年间,明朝政府在贵州设立承宣布政使司,贵州才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版图,成为与内地一样的行政区域。随着各级政府机构的建立,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在贵州地区逐渐推行。当然,这种意识形态的推行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需要一定的载体。除了建学校“以用夷变夏”[3]337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收编当地的地方神,将其纳入国家的神祇行列。而南霁云在历史上的忠臣形象正好符合儒家思想的要求,所谓“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18]126南霁云在睢阳保卫战中殉难,成为为国捐躯的忠臣,其在与张巡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义”,[19]5542-5543与儒家思想所宣扬的忠义观念深相契合,于是,黑神庙作为推行正统意识形态的一个很好的载体,便在贵州各地普遍建立起来。
但是,由于贵州地处西南,“皆崇山深箐,鸟道蚕丛,诸蛮种类,嗜淫好杀,畔服不常”。[20]8167在这种复杂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之下,要想推行中原教化,其难度可想而知。由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少数民族分布之间的不均衡,中央政权对贵州地区的统治也因地而异。《清史稿》记载,贵阳、安顺、都匀、镇远、思南、思州、铜仁、遵义、石阡、黎平等地区皆“因明制”而建立府置,其他地区则晚至康雍年间才正式建置设府。①这种将地区纳入国家府厅州县的统治轨道中的时间差异,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国家政权逐渐深入的过程,也是中原文化圈逐步扩大的过程。黑神作为国家祀典所承认的正神,在地域分布中也会呈现不均衡的状态。
在城乡之间,黑神庙也会显出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背后所反映的正是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文化的一种冲突和融合。南霁云在被纳入《祀典》时的谥号是“忠烈”,这两个字实际上包含了非常正统的儒家观念,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有较大的冲突。这种地域文化应对正统的汉文化的侵袭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冲突和融合的过程。“忠烈”这一名称背后所展示的强烈的正统文化色彩并不能深入到乡里社区之中,而只能在政府所在地或者汉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存在。民间对忠烈庙有着自己的称呼,即黑神庙或黔阳宫。
另外,从实用主义角度来看,官方与民间对黑神的祭祀也有着不同的目的。在官方记载中,祭祀南霁云是因其为国尽忠。例如清代贵州巡抚田雯认为,南霁云之所以得祀贵阳,是因其子为清江太守,而南霁云自身亦有可祀者,即“睢阳射贼,临淮借兵”[1]523,强调了南霁云的忠义事迹。“自古忠臣烈士,没而为神,其威灵足以安上全下。”[21]296“忠臣烈士,人人得而敬之,即人人得而祀之也。”[8]358-359而在地方人士看来,之所以祭祀南霁云,是因为其对本地的庇佑。如黔西县“我黔奉为香火,必其流风遗泽及我黔民也”[22]168,“南公忠在唐时,泽及牂牁”[22]169。一个提倡爱国,一个提倡佑民。这就是官方与民间在对待神灵时所体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时人也看到了这一问题,因此想办法将二者进行调和。“南公不食进明之食,归与张睢阳同死,一段勇烈之气,千载犹生。宜其为神而有功于民也……黔苦火患尤剧。南公弭火之功,尤其立祷立应也。”[1]523这段记载说明南霁云因为国尽忠而成神,因成神而佑民,将爱国与佑民联系在了一起。
三、贵州黑神庙的时间分布及其成因
在地方志中,关于黑神庙的修建时间,大都没有详细记载。在108处黑神庙中,明确记载时间的共37处。我们对这37处黑神庙做一时间排比(见表2),以窥一斑而见全豹。

表2 贵州地区黑神庙修建时间分布表
由表2可见,明代修庙不多,只有7处,与清代的30处相比,相差很大。在清代有明确时间记载的黑神庙中我们可以看到,乾嘉道年间与光绪年间是修庙的两个高峰期,分别为17处和11处。明清两代贵州黑神庙数量相差悬殊,所反映的其实是一种文化认同感的时代差异。贵州虽已在明永乐年间建省,但在有明一代,国家政权统治主要及于贵州府、州、县城及交通沿线一带,基层社区仍以少数民族统治为主。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和信仰,作为承载儒家忠义观念的忠烈宫当然很难在这些地区普及。我们从关于黑神庙的称呼上也能看得出来。明代7处黑神庙中,除了贵阳一地的黑神庙称忠烈庙之外,其余地区都称之为南霁云庙或者南公庙。到了清代尤其是雍正年间,贵州开始大规模改土归流,在派设流官进行地方治理的同时,也必然将官方意识形态带入基层。这样,忠烈宫也就能得到官绅的大力倡导而得以广泛分布。
其实,“黑神”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起着一种文化缓和的作用。一方面,黑神在汉文化中是忠臣义士南霁云的化身,符合儒家所倡导的忠义观念;另一方面,黑神作为“贵州福主”,在被不断塑造的过程中赋予了御灾捍患的功能,成为贵州人的保护神,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就像隔着一层未捅破的窗户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在接触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个契合点,从而形成了一种对地方与对国家的认同感。
在贵州地方志中,关于黑神庙记载的最早时间是在洪武年间,共有两处,一在今贵阳市,一在今六盘水市的盘县。当然,这个时候的黑神庙还是属于淫祠,并没有得到官方承认。黑神被纳入《祀典》的时间是景泰二年。史载:“景泰辛未(二年),贵州按察使合肥王公(宪)奉命廉问是邦,肃政之余,祷谒神祠,慨慕神之风节,且有以荫佑于斯土也,其以事闻。朝廷嘉神忠义灵贶,特颁祀典,命有司以春秋行事。”[23]283王宪《请忠烈庙南公祀典疏略》云:“臣闻,以死勤事则祀之,为民御灾则祀之。窃建贵州城中,旧有忠烈庙,祀唐忠臣南霁云。洪武初,都指挥程暹建,至今军民皆称其神灵。每岁春首,风狂境内,常有火灾及水旱、疾疫、虫虎、寇盗,虔祷于神,其应若向,虽神贶久孚人心,而圣代未蒙祀典,臣谨考南霁云在唐天宝末年,安禄山为乱,贼将尹子奇围睢阳,守将张巡、许远与之誓死拒贼。常求救兵于贺兰进明。初啮指示信。已而城陷,霁云死之。兹者显灵八番,阴为御灾捍患,乞追赐美谥,颁祀典,每岁春秋有司致祭,非惟圣恩广布,不遗前代之忠臣,抑使神惠愈彰,永济边方之黎庶。”[24]63从中可以看出两层意思:第一,南霁云与张、许守城,誓死拒贼,已而城陷身死,为国尽忠,这是其之所以进入祀典的理由。第二,“显灵八番”、“御灾捍患”,这是其之所以得祀贵州的理由。明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明代宗即位。于谦临危受命,组织了一场北京保卫战,对抗瓦剌大军的入侵,并最终取得胜利。朝廷对此次保卫战的有功人员进行了封赏,对战死者也进行了抚恤。在这种政治氛围中,追谥前代在围城中战死的人员,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在载入祀典之前,黑神作为贵州的地方保护神,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信仰基础。通过将贵州保护神纳入国家神灵行列,在某种程度上也象征着将整个贵州地区一同纳入了国家统治的行列。尽管贵州在明永乐十一年已经建省,但要使一个地区融入国家这个整体当中,并不是单靠行政法令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除了政治认同以外,还需要一种文化认同。
当然,南霁云在景泰年间载入《祀典》,获谥“忠烈”,这是其之所以能够得到官绅阶层拥护的原因。在众多文人士大夫的话语中,南霁云都是忠臣义士的榜样。都御史邓廷瓒诗云:“烈烈轰轰此丈夫,艰危志在灭强胡。孤城受敌丹心壮,大厦虽倾赤手扶。正气满腔凌日月,清明千古振寰区。我持斧钺来霄汉,愿借英风扫叛徒。”[3]23兵部尚书伍文定诗云:“忠孝能全始是夫,不然中土亦林胡。城孤无赖刚肠在,板荡终归大义扶。气压山潮巍血食,名同巡远振寰区。英灵尚助堂堂阵,唾手天戈靖乱徒。”[25]286-287作为一种民间信仰,被祀者一定要符合普通民众的心理需求,这样才能形成一种稳定的信仰关系。南霁云作为贵州地区的保护神,被民众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神异功能。这些功能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御灾”“捍患”两个方面。
一是御灾方面。《播州道中谒南将军庙诗》写道:“居民求雨复求晴,高香一炷插前楹。神果有灵风雨节,种禾种黍多欢声。”[1]564这是南霁云被赋予保障农业丰收的功能,关系着老百姓的吃;康熙《黔书》记载:“黔苦火患尤剧。南公弭火之功,尤其立祷立应也。”“今禳火之役,祷而祭之,而遂无不应。火灾以弭,而民受其赐,盖黑神之灵焉。”这是南霁云被赋予了灭火的功能,关系着老百姓的住。可见,南霁云不仅关系着百姓个人吃、住的生存需要,更关系到地方的稳定与国家的兴亡。这是南霁云之所以成为地方保护神的根本原因。
二是捍患方面。贵州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与汉族交往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利益与文化差异的关系,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甚至演化为武装斗争。汉人以及地方政府的势力主要集中于城市,一旦发生武装斗争,便是各地的少数民族武装陆续包围城池,给地方官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便祈祷神灵,祈求解围。方志中记载了许多南霁云解围的事迹。陈熙晋《南将军神祠曲》云:“老巫说明天启朝,蟊飞蚁聚攒叛苗。重围垂陷袛炊黍,万人恸哭苍天高。忽见皂纛半空黑,青蛇丈八城头立,妖徒辟易灵旗归。铁马无声汗尤湿,黔中人感全城功。……生前恨未灭贺兰,身后犹能摄罗鬼。”[13]370吴纪《忠烈南将军庙信士捐置祭田碑记》云:“恭惟大将军南公殉节于唐,忠肝义胆,具载史册,历代褒封,迄今庙食千余年。不惟睢阳尊奉甚谨,即江右三楚滇蜀亦无不重其志节而修其禋祀,而我黔之爱戴为尤甚者,以元明以来寇盗充斥,干戈迭起,兵民进不能战,退不能守,公屡显神灵以拥护,乃得城郭无恙,汉夷相安。此黔人既重公生前奇节而更感公殁后威灵。”[21]296可见,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也是南霁云香火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由于南霁云被不断赋予神异功能,不断适应各个阶层人群需要,从而成为整个贵州的保护神。这也可以解释黑神庙在清代的数量为何这么多。有研究表明,“明代276年中,贵州发生大小战事的年份共有145年,占有明一代一半以上时间;清代267年历史中,贵州发生大小战争的年份更达227年,占清代年份的85%。”[26]社会的不稳定,加剧了人们的危机感,对现实的无助促使人们转而寻求心灵的慰藉,这就是历朝历代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神灵崇拜的普遍原因之所在。
四、结语
通过上述对黑神身份的讨论,我们发现,在贵州地区黑神庙中所祀的黑神经历了从南承嗣到南霁云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在黑神“正统化”的过程中,南霁云的事迹更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
在时空分布上,贵州黑神庙的分布在空间上以中部居多,在时间上以清中后期居多。这种分布状况的形成既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总而言之,文献记载的详细与否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明清贵州各地黑神庙数量的直接因素。但是,在空间分布上,多种神灵信仰的冲突以及政府推行的政策是造成各地黑神庙数量差异的两大原因。当然,国家政权在各地统治的差异所导致的汉文化在各地传播的差异,是黑神庙在空间分布上不均衡的主要原因。中原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或者说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反映在对黑神庙的称呼上,则是在前者话语下称之为“忠烈宫”,在后者话语下则称之为“黑神庙”。
在时间分布上,清代黑神庙数量远多于明代,其主要原因是清代在贵州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随着基层统治的流官化,汉文化也随着流官的到来而得以传播,这就使得承载了儒家忠义观念的南霁云信仰得以在官方支持下逐渐推广。但是作为贵州地区的地方神灵,还必须符合普通民众的心理需求才能被普遍认同。南霁云在被官方和民间不断塑造的过程中具备了各种各样的神异功能,正是这些功能使南霁云得以在“黔省通祀”,成为整个贵州地区认同的地域文化符号。
注释:
①据中华书局1977版赵尔巽《清史稿·地理志二十二·贵州》第2351-2352页记载:“康熙三年,增置黔西、平远、大定、威宁四府。二十二年,大定、平远、黔西降州,隶威宁府。雍正五年,增置南笼府。六年,割四川遵义来属。七年复升大定,降威宁。乾隆四十一年,升仁怀,嘉庆二年,升松桃,均为直隶厅,改南笼为兴义府。三年,降平越为直隶州。十四年,升普安为直隶州。十六年,改厅。”
[1]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03)[M].成都:巴蜀书社,2006.
[2]《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光绪湖南通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01)[M].成都:巴蜀书社,2006.
[4]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5)[M].成都:巴蜀书社,2006.
[5]邢飞.贵州黑神信仰初探[J].毕节学院学报,2012(9):101-104.
[6]王宏伟.试论明清时期贵州地区的黑神庙信仰[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2):42-45.
[7]高应达.国家控制与民间信仰的冲突与调适——以明清时代贵州黑神信仰为例[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4.
[8]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6)[M].成都:巴蜀书社,2006.
[9]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34)[M].成都:巴蜀书社,2006.
[10]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5)[M].成都:巴蜀书社,2006.
[11]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7)[M].成都:巴蜀书社,2006.
[12]武雅士.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M].彭泽安,邵铁峰,郭潇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146.
[13]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39)[M].成都:巴蜀书社,2006:370.
[14]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6.
[15]郝浴.康熙广西通志·坛庙[M].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近卫本),2000.
[16]廖玲.明清以来武陵地区飞山庙与飞山神崇拜研究[J].宗教学研究,2014(4):165-172.
[17]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37.
[18]邬国义,胡果文,李晓路.国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26.
[1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忠义传·南霁云传[M].北京:中华书局,5542-5543.
[20]张廷玉.明史·贵州土司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8167.
[21]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9)[M].成都:巴蜀书社,2006.
[22]黔西县志办公室编.黔西楹联碑记集萃[M].内部印行本,1992.
[23]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08)[M].成都:巴蜀书社,2006.
[24]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05)[M].成都:巴蜀书社,2006.
[25]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02)[M].成都:巴蜀书社,2006.
[26]刘学洙.明清贵州沉重的军事负担[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62-65.
[责任编辑 文 川]
2016-11-18
熊志翔(1992— ),男,江西南昌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社会史。
K
A
1008-6390(2017)02-003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