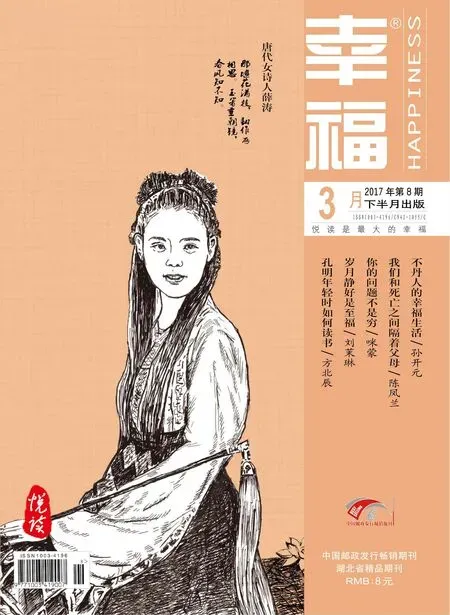摘尽枇杷一树金
文/董改正
摘尽枇杷一树金
文/董改正
吴昌硕是浙人,却喜画枇杷,阔叶圆果,叶垂果举,粒粒金黄,果头点一点黑,生动明媚。枝干修长披拂,旁有鸟雀惊飞。其中一幅有题词曰:“鸟疑金弹不敢啄,忍饥向东林间飞”。“金弹”是枇杷的别称,因其明艳,竟把鸟吓飞了。也有画松鼠缘枝攀援,来就枚枚橙黄的,将坠未坠,引人担忧。
白石也爱画枇杷。大笔绘就叶片,随意点就叶脉,簇簇枇杷轻举,枝干大多略过,而不可少的,却是蚱蜢,不是绿色的,是微红的,翅膀、触须、长腿纤毫毕现。这是夏天了。枇杷号为“初夏第一果”,是入得画的,线条、色彩都好,适合国画写意,它有乡趣,有情趣。
枇杷树是常见的,形貌颇似广玉兰。秋日蕾,冬日花,春日子,夏日挂果,枇杷结子须得走过四季,累累金黄固然惊羡,而首先要感激的是大片的叶,藏着花,护着子,直到簇簇向阳一树金。这时候的树上,还结着几个小脑袋,扬着脸,在肥大的叶子里找:明明在树下看到了,咋一上树就不见了呢?树下扬着的小脸,急得不行:“笨!不就在这边吗?诶,这边一点,对,再来一点!”上面忽地又大叫一声:“在了,在了!”树枝摇动起来,吓得邻树上的鸟惊叫飞远。
坐在枝头吃枇杷,也是入得画的。优哉游哉,清风吹我襟。有的站着,随着风的节律晃动。底下的小屁孩不高兴了:“阿丑哥,还是我们帮你指的呢,只顾自己吃!”一群小的都应和:“就是!”腆着脸摘一把,将撒未撒地作势,底下的孩子双脚岔开,做出瞬移的动态。待一片金雨洒落,底下哄地抢开了。上面的看到谁弯腰露出了黑臀,笑不可遏;而有的不但没抢到,还给绊倒了,就揉着眼睛哭回去了。可是,这场景,有几个画家能注意到呢?
“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微黄尚带酸。”这是苏轼写山僧的诗,卢橘就是枇杷。枇杷即使黄到发软,依然是略酸的,更何况我们等不及--那时候却不觉得酸。但也有酷爱枇杷酸的,高启在冬日飘雪时,就叮嘱僧人老友:“居僧记取南风后,留个金丸待我尝。”诗人尤侗有《枇杷》诗云:“恨不江南一骑收。”那岂不要酸掉牙了?真是痴了!
一个人的童年经过了枇杷,越走得远,味蕾的记忆会越清晰,那绿、那一树金黄、那仰脸的馋,那树冠里的老屋,都历历在目,却氤氲如水墨,如一句诗。我的邻居周太公定居香港前,送我曾祖一幅写意枇杷。后来他写信来,说道:“异乡寂寞难耐,思乡紧,久咳难愈。我兄可寄枇杷叶来否?”他院内枇杷盛极,鸟雀啄落一地。我家院内也有,曾祖非让我父亲翻墙进了周家,说:“他认得!”但包裹没寄到,他就去世了。
我还记得枇杷摘尽后,枇杷树只剩一色,深沉地绿着,鸟也安闲下来。小伙伴走过,下意识抬头,又低头急急走过。夏日的阳光很好,一丝不苟地画下枇杷树影,一只鸡恰好经过,迟疑了一会儿,这情景,远看,还是大写意。

摘自《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