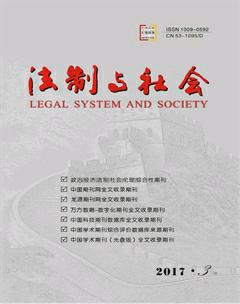浅析利用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之“结婚避债”
摘 要 2012年,成都商报报道了一起海归女婚后两个月被丈夫负担500万债务的案件,原案之判决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成为争议焦点。该司法解释确定的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过于笼统,给了不法分子借婚姻避债的机会。本文将以本案为出发点,考查该司法解释的理论基础,探讨解决同类问题的现行法方案,以及完善相关制度之可能。
关键词 婚姻法 夫妻 共同债务 无效合同
作者简介:江旻哲,南京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法学系本科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3.174
据成都商报报道,2012年2月15日,海归董女士与王某结婚。在婚后的两个月时间内,王某便向多人举债共500多万元,紧接着便难寻踪迹。董女士同年6月发起离婚之诉,却直到2014年才被法院判决离婚。然而在此期间,多位债权人已经联合将董女士与其丈夫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法院依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认定王某的个人名义之债为夫妻共同债务,判决董女士承担连带责任。2017年初,董女士就此案再度起诉,杭州中院现已立案调查。
该案自被报道以来,引发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而原判决之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确定的“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则成为了争议焦点。其实,因该条司法解释引起的争议案件并非个例,2016年以其为依据的判决多达30484份,大量的受害者已经成立互助群以呼吁国家修法。在这一系列案件中,均是丈夫以个人名义对外举债,或直接以妻子名义对外举债,为妻子负担上不知情的债务后逃之夭夭。行为人明显的利用了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进行“结婚避债”。
笔者在本文中将尝试探究《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理论基础,并分别从婚姻法和合同法视角分析为妻子解除债务负担的方式,最后讨论该条司法解释的完善可能。
一、《司法解释(二)》第24条之立法目的和理论基础
传统理论认为夫妻共同生活包括两部分关系: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而财产关系除了积极的夫妻共同财产,就是消极的夫妻共同债务。我国立法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选择曾长期处于变化中,最早的规定见于1981年《婚姻法》第41条,即离婚时才可适用的以“共同生活所负”为标准的认定规则。接着在1993年,最高院颁布《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将共同债务范围从“共同生活所负”扩大到“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并列举了属于个人债务的例外情形。2001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一)没有直接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但是其中第17条对夫妻共同财产平等處理权的解释,提出了夫妻一方由于日常生活需要对财产享有的独立处理权。到2003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二)颁布,将共同债务问题的探讨从离婚时扩展到从婚前至离婚的整个过程,第23条针对婚前债务,第25、26条针对离婚后债务(双方生存时离婚/因一方死亡而离婚)。而第24条则是针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之债务,其直截了当的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之债务原则上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且只规定了债务人与债权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以及债权人明知债务人与其配偶实行分别财产制两个例外。
对于制度的一系列变迁,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目的解释:
(一)保护交易安全,促进利益平衡
认定规则的更改,体现的是婚姻法保护对象倾向的变化。八十年代,我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立法以保护婚姻关系的和睦为第一要务,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极为模糊,导致了九十年代大量夫妻以内部约定、离婚等方式逃避债务。1993年《若干意见》在列举夫妻个人债务时,曾有“夫妻双方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 但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除外”的规定,已经在对症下药。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立法当然要顺应时代潮流。虽说保护交易安全,促进交易便捷是商法的任务,但是传统的民法也必须与其协调以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司法解释(二)确定的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毫无疑问的是在保护外部债权人的利益,鼓励他们与夫妻进行经济上的往来。
除此之外,推定规则中的“举证倒置”也反映立法者认为相比于夫妻共同生活之外的债权人,夫或妻对于其配偶的债务有更大的知悉可能,距离证据更为接近,承担举证责任自然较为合理。可以说,该规则的选定也是立法者基于夫妻与债权人利益平衡考量的结果。
(二)对域外法夫妻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的借鉴
夫妻日常家事代理制度,指夫妻一方在日常生活范围内与第三人为一定行为,其配偶承担连带责任,即一种身份权的代理。该制度起源于古罗马,大陆法系国家多有继承,但因为早期夫妻地位不平等,家事代理制度只是丈夫对妻子的一种授权规定。二次大战后,社会结构变化和平权运动确定夫妻互相享有家事代理权,1965年修订版的《法国民法典》和现行日本民法典就是典型的代表,英美法则进一步发展出同居代理制度。
上文将并未直接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纳入债务认定规则的变化历程,其实是认为该条规定的财产独立处理权,是我国学习家事代理制度的信号。这种借鉴在《司法解释(二)》第24条里体现的更加彻底,“连带责任”的描述与域外关于家事代理制度的规定不谋而合。
立法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上述两点理由均存在缺陷。在利益平衡方面,立法者虽然照顾了债权人的利益,但却高估了夫妻关系的和睦程度。当夫妻处于分居状态时,夫或妻对其配偶的行为并不易获知,举证还没有债权人来的轻松。至于家事代理制度,史尚宽先生曾指出日常家事一般包括“为夫妻共同生活所必要的一切事项,一家之食物、光热、衣着等之购买,保健(正当)娱乐、医疗,子女之教养,家具及日常用品之购置,女仆、家庭教师之雇佣,亲友之馈赠,报纸之订购等”,即并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或妻一方所负全部之债务均要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应分情况讨论,《司法解释(二)》第24条笼统的将全部债务囊括进共同债务,并没有恰当的学习域外立法的经验。
二、现行法解决方式之探究
(一)婚姻法之视角:《司法解释(二)》第24条之例外
既然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引发的问题,我们当然应该从原判决依据的法条本身出发,即其本身规定的例外:
一是由债务人或配偶举证证明,债务人与债权人在签订合同时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该案中原债务人王某早已下落不明,债权人叶某在本案中处于有利地位,就算在签订合同时与王某约定为个人债务,也不可能将情况告知董女士。二是由债务人或其配偶证明债权人知晓夫妻间实行分别财产制。根据案情,夫妻二人间并未实行分别财产制,就算实行,由妻子证明债权人知晓内部约定也十分困难。
由此可以看出,《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的两个例外并未考虑到夫妻感情不合时由债务人配偶举证的难度。类似“结婚避债”案件中,女方想通过婚姻法规定解除债务负担,可能性微乎其微。
(二) 合同法之视角:证明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
从婚姻法角度走不通,我们可以尝试通过直接否定债务存在的基础——原借款合同来为女方解除债务负担。就该案而言,丈夫是以自己名义外借债务,董女士若希望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则必须证明存在以下情形之一:
1.丈夫王某与债权人叶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恶意”指合同当事人双方明知或应知某种行为将造成对第三者的损害而故意为之,而“串通”则是当事人双方都希望以合同损害第三人利益。串通不一定是双方事先达成的协议,也可以是一方做出的意思表示,对方在明知目的非法情形下,默示接受。本案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即在董女士丈夫向叶某所借前款未还情况下,两个月时间里他仍先后6次向叶某借款逾百万。前款未还再放新贷,对于信誉情况不算良好的王某实属异常。董女士及其律师可以以此为出发点探索进一步的证据去证明叶某与其丈夫恶意串通的可能。
2.丈夫王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所谓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指当事人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上合法,但在内容和目的上却非法。本案中,王某和叶某的借款合同形式固然合法,但联系到短时间内借款的高频率以及王某不相称的还债能力,该合同的目的和内容真实性难免让人怀疑。当事人王某明显的是在利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以借款合同的形式故意為其新婚妻子负担债务,使自己规避债务。通过证明此情形的存在,也能否认合同的效力。
三、制度完善之建议
现如今大量不法分子“依葫芦画瓢”一般利用《司法解释(二)》第24条逃避债务、损人利己,而上文提及的解决方式在证明上又存在一定困难,这就对修法提出了要求。综合前人研究,笔者认为第24条仍要继续针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之债,但可以做如下修改:
(一)夫妻同居期间:划分生活性债务和经营性债务后适用推定规则
前文提及,域外立法中的家事代理制度绝非武断的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一切债务均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是分情况进行处理。《司法解释(一)》第17条的两情形划分其实就是珠玉在前,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作为有无独立处理权的判断标准,第24条的修改也可以以此为参照划分生活性债务和经营性债务,并只对生活性债务适用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
(二)夫妻分居期间:推定为夫妻个人债务
举证规则的设置是为了平衡当事人双方之利益,而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必然在获取证据上更具优势。在夫妻分居期间,双方感情不和,对对方之经济事务一般不再过问,而借款合同双方多存在合作关系,债权人相比债务人之配偶,自然能获知更多信息。在规则基础上,分居期间即使发生生活性债务,只要配偶能证明双方已经分居长达一定时间,就不应再背上债务之负担。
综上,笔者认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设置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已经造成了极为不良的社会效应,律师固然应竭尽全力为当事人解除负担,但修改该解释也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唐羽虹.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的缺陷及重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之检讨.行政与法.2008(7).
[2]张素凤.论夫妻共同债务纠纷的举证规则——兼论《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的不足与完善.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4(6).
[3]史浩明.论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政治与法律.2005(3).
[4]孙鹏.民法上信赖保护制度及其法的构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7).
[5]郦诗远.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重构.时代金融.2012(11).
[6]史尚宽.亲属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7]迪特尔·施瓦布著.王葆莳译.德国家庭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8]蒋月.夫妻的权利与义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9]王利明、房绍坤、王轶.合同法(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