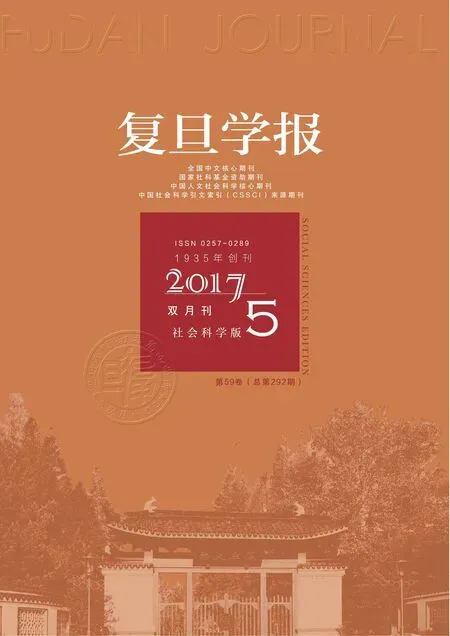一般人格权形成路径的宪法学分析
刘志刚
(复旦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438)
法学研究
一般人格权形成路径的宪法学分析
刘志刚
(复旦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438)
瑞士和德国确立一般人格权的方式代表了一般人格权形成的两种典型路径。德国的一般人格权是联邦最高法院直接依据基本法、通过司法判例的形式形成的。德国保护一般人格权的模式是“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我国“一般人格权”的形成路径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人格权本质上是一种宪法权利和自然权利,人格权应该通过法定主义的方式加以设立,但不适合在民法典中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人格要素分解之后在民法中确立的具体人格权的性质是民事权利,但一般人格权的宪法权利性质不会因为规定于民法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仿效德国采行“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的模式存在许多弊端,应当借鉴瑞士的做法,采取“具体人格权+保护人格权一般条款”的模式,该种模式具有宪法层面的价值。
一般人格权 形成路径 宪法学分析
近代民法对自然人一般人格权的法律保护,发端于《瑞士民法典》,*1907年12月10日经瑞士联邦会议通过,于1912年1月1日正式生效。该法第28条第1项*《瑞士民法典》第28条第1项规定:“人格受到不法侵害时,为了寻求保护,可以向法官起诉任何加害人。”对一般人格权作了明确规定。其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判例确立了一般人格权的概念。一般人格权拓展了人格权益的范围,加强了对人格权的保护力度。但是,由于一般人格权在内涵上的高度不确定性,学界围绕其性质认定、形成路径等问题产生了许多争议,司法实践中还产生了对侵害一般人格权行为之违法性判断的难题。以上这些,对我国在民法典中确立或者完善一般人格权的路径问题产生了许多传导性影响,学界对此存在一些理解上的歧义。在本文中,笔者意欲不揣浅陋,对民法中一般人格权的形成路径做一宪法学分析,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德国一般人格权的形成路径
人格权的概念肇始于近代,在人格权概念的发展过程中,学界对人格权概念始终存在争议。由于人格权通常被理解为权利人针对自己本身的权利,因此经常遭到一些人的质疑,认为人格权的主体与客体是同一的,因而在权利逻辑上是荒谬的。*对此问题的详细阐述,可参见马俊驹、张翔:《论人格权的理论基础及其立法体例》,《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薛军:《人格权的两种基本理论模式与中国人格权立法》,《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该种观点最早由德国学者萨维尼提出,*萨维尼虽然承认每个人独立支配自己意思领域的权利,但却否认对自己自身的实定法上的支配权:并由此引申为:对自己身体支配权的承认等同于对自杀的正当化。萨维尼认为,自然人对于其自身的合法权利不需要实定法予以承认,它受到旨在保护生命、名誉等免受侵害、免受欺骗及暴力等损害的刑法以及大量的民法规范的保护。参见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田士永译:《萨维尼论法律关系》,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七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8页。其观点对德国以及其他国家民法学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近代社会人格权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反对人格权的声音一直存在。该种观念对《德国民法典》的制定产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人格权的观念在《德国民法典》制定时并未被广泛接受。立法者认为,人格利益不应归属于主观性权利,不要试图超越刑法的规范去保护它们。(See Enneccerus, Nipperdey,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egerlichen Rechts,15.Aufl.1959,S.841.)《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立法理由书认为,虽然基于故意或过失通过违反行为侵犯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和名誉等法益,对此应承担损害赔偿义务。这并不表明认可了对人本身的权利,关于这一问题还是交由法学界探讨后决定。(See Motive zu dem Entwurfe eines Büegerlichen Gesetzbuches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Amtliche Ausgabe, Berlin Guttentag, 1888, Bd.I, S.274.)该法典中并未规定一般的保护人格权的条款,仅仅列举性地规定了一些应当受到保护的人格权益。依据《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该款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健康、身体、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者,对他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义务。”的规定,“生命、健康、身体、自由”等四种人格权益是应当受到保护的,但是除此之外的“其他权利”究竟包括哪些人格权益,该条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此外,依据该法第12条*《德国民法典》第12条规定:“有权使用某一姓名的人,因另一方争夺该姓名的使用权,或者因无权使用同一姓名的人使用此姓名,以致其利益受到损害的,可以要求消除此侵害。如果有继续受到侵害之虞时,权利人可以提起停止侵害之诉。”的规定,姓名权应当受到保护;依据该法第823条第2款*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者,负相同的义务。如果根据法律的内容并无过失也可能违反此种法律的,仅在有过失的情况下,始负赔偿义务。的规定,名誉也可以受到有限的保护。总体来看,《德国民法典》所保护的人格权益范围是非常狭窄的。*“人们普遍认为,《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中所提到的以及其他为法律(包括保护名誉的刑法条款)所认可的具体人格权,对于人在人格上应受保护的利益,并没有完全包括齐全,即通过上述的特别人格权仍不足保护所有各方面的人格。”参见卡尔·拉伦茨著,王晓晔等译:《德国民法通论》(上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70~171页。二战结束之前,德国帝国最高法院在保护人格的司法判决中,恪守人格保护的法定主义规则,并未创设一般人格权来拓展人格权益的保护范围。*帝国最高法院认为,“一项一般的、主观的人格权,是为现行的民法所排斥的。民法中只存在特别的、由成文法所规制的人格权利,如姓名权、商标权、对人格形象的权利以及著作权中的人格权的内容”。参见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著,齐晓琨译:《侵权行为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50页。二战结束之后,德国人开始反思以往纳粹政权践踏人权的惨痛历史,逐渐认识到了人格权保护的深层意义。同时,由于战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格遭受侵害的可能性急剧增加。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德国民法典》中一般人格权条款的缺失与侵权行为法列举式规定所导致的封闭性越来越显现出其缺陷和不足,人们迫切需要拓展人格权益的范围。1954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以“读者来信案”为契机,依据德国《基本法》第1条*《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项规定:“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和第2条*《德国基本法》第2条规定,人人有自由发展其人格之权利,但以不侵害他人之权利或不违犯宪政秩序或道德规范者为限。人人有生命与身体之不可侵犯权。个人之自由不可侵犯。此等权利唯根据法律始得干预之。的规定确立了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将其称为“由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作为被现行法合理承认了的,并将之等同于第823条第1款所指的‘其他权利’,从而填补了重大的空白”。*卡尔·拉伦茨著,王晓晔等译:《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第171页。“读者来信案”裁决作出之后,其法律后果经由判例法规则被实质性地扩大。*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806页。经由“骑士案”、“人参案”、“索拉娅案”等一系列人格案判决,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不断地阐释其相关立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当今的基本法已经确认,人有权要求其尊严得到尊重,只要不损害其他人的权利并不违反道德规范,就有权要求自由地发展其人格,这作为一项私权,应当得到所有人的尊重。这些内容在基本法中被确立后,一般人格权也就应当被视为由宪法予以保障的一项基本权利。”参见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著,齐晓琨译:《侵权行为法》,第51页。一般人格权理论逐步趋向于成熟。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直接援引《基本法》创设一般人格权的做法,为其他后进主义国家确立一般人格权制度提供了一种可资参考的路径。
总观德国一般人格权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它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其一,德国一般人格权不是通过立法的形式在民法典中明确予以规定的,而是法院通过司法判例的形式加以创立的;其二,德国一般人格权由以创设的依据是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2条的规定,而不是德国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其三,一般人格权属于一种“框架性权利”,它究竟承载了什么内容,是无法通过某种规范化的方式推导出来的;其四,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中所规定的“其他权利”是一般人格权的载体,它和该条第1款所罗列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构成了“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的人格权保护模式。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直接援引基本法中人格尊严的规定创设民法一般人格权的做法,受到了各国法学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客观上也弥补了德国民法典对人格利益规定的不足。但是,该种一般人格权的形成路径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几乎从“读者来信案”裁决作出之日起,围绕该种创设路径的质疑之声就不绝于耳。总体来看,德国“一般人格权”形成路径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其一,有违法律的安定性,错误适用基本法;*德国法院通过司法审判创设一般人格权之后,“一些学者提出了批评,认为在法学方法上,法院的此种做法超越了法院的职权,影响了法律的安定性;《基本法》第1条及第2条属于公法的规定,不具有私法的性质,不能直接创设人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参见王泽鉴:《人格权之保护与非财产损害赔偿》,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6页。其二,一般人格权本质上并非权利。国内外均有学者表达了该种立场。*参见冉克平:《一般人格权理论的反思与我国人格权立法》,《法学》2009年第8期;迪特尔·施瓦布著,郑冲译:《民法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
二、 中国民法中一般人格权的形成路径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颁布实施的三部正式宪法中均未规定公民的人格权。现行宪法基于对以往践踏人权现象的深刻反思,在第37条*现行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8条*现行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中对公民人格权作了规定。国内有民法学者指出,宪法第38条前半部分所规定的其实就是公民的一般人格权。*杨立新著:《人格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120页。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第98条~第101条具体列举了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具体人格权。其中,第101条*《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包含有公民“人格尊严”的字眼。有民法学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01条所规定的人格尊严其实就是一般人格权方面的内容。*杨立新著:《人格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120页。对此,王利明教授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民法通则》并没有规定一般人格权的概念。*王利明著:《人格权法》(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6页。王泽鉴先生在评价我国《民法通则》时似乎也秉持后种立场。*王泽鉴先生在评价我国《民法通则》时曾经指出,“此种列举方式对人格权的保护较欠周全,由于无一般人格权制度,因而在自由、贞操、隐私等人格利益遭受侵害时应如何处理尚缺乏依据。”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6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3页。对此,笔者同样秉持后种立场。笔者认为,从字面来看,《民法通则》第101条似乎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但是,它是和公民的名誉权关联在一起的,不能将其等同为一般人格权。《民法通则》对人格尊严的规定有严重缺陷,对此,已经有民法学者作过相关的阐述。*杨立新教授指出,“《民法通则》对人格尊严的规定有严重缺陷。将人格尊严规定在名誉权的条文之内,降低了人格尊严这个一般人格权核心的法律地位,使之看起来似乎是名誉权的内容”。杨立新著:《人格权法》,第121页。因此,不能因为《民法通则》第101条中出现了“人格尊严”的字眼,就认为其规定了公民的一般人格权。从我国的司法审判实践来看,法院是通过类推适用保护名誉权的方式来保护公民的“一般人格权”的,并未直接依据《民法通则》第101条关于公民“人格尊严”的规定对“一般人格权”加以保护,这足以说明,我国《民法通则》实际上并未确定公民的“一般人格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4月2日。法办发【1988】6号。第140条就是典型例证。该条第1款*该条第1款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所规定的宣扬他人隐私是侵犯公民具体人格权的行为,丑化他人人格是侵犯公民一般人格权的行为。但是,由于《民法通则》第120条第1款只规定“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可以寻求法律救济,并未规定侵害“隐私权”、“一般人格权”的法律救济,因而最高审判机关只好采取类推方法,适用保护公民名誉权的方法进行救济。*王利明:《人格权法》(第二版),第81页。该种方式固然拓展了人格权益的保护范围,保护了公民的“一般人格权”。但是,由于它将“一般人格权”和“名誉权”结构性关联在一起,因此,不仅“一般人格权”的范围受到较大程度的限制,而且将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之间的关系颠倒了。2001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61次会议通过,自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法释【2001】7号。对此做了修正。该解释第1条*该解释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依法应当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第1款第3项规定了“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第2款规定了“其他人格利益”。有学者认为,该条中所规定的“人格尊严”实质上就是“一般人格权”,具有补充法律规定的具体人格权类型不足的重要作用。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可以通过一般人格权保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以补充具体人格权的不足。*参见陈现杰:《人格权司法保护的重大进步和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报》2001年3月8日。对此,笔者秉持不同立场。笔者认为,该条所规定的“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以及“其他人格利益”实际上都属于公民的一般人格权,它实际上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将现行宪法第37条、第38条关于公民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的规定进行了转化,确立了公民在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但是,该条存在的问题是:将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与两类具体人格权(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并列使用,混淆了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之间的关系。此外,“人格尊严权”与“其他人格利益”之间的界限无法划分,由此导致该条第1款所规定的“违法侵权”与该条第2款所规定的“背俗侵权”之间的界限模糊,进而影响到司法实践。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和2011年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发【2008】11号;法【2011】41号。均将一般人格权纠纷作为一项独立的案由,但是,司法实践中法院受理的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件数量很少,而且,法院所受理的该类案件绝大多数实际上并不属于一般人格权纠纷。*方金华:《一般人格权理论分析及我国的立法选择》,《法律科学》2015年第4期。个中原因,耐人寻味。2010年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中对其保护的民事权益做了规定,但该条并未作类同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那样的规定,将“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以及“其他人格权益”明确规定为《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益。2017年通过的《民法总则》第109条确立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将其置于其他诸项具体人格权之前。这一点与前述司法解释中的做法不甚相同。
总观我国一般人格权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它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其一,《民法总则》颁布之前,我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一直没有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确立,而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加以创立的;其二,我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和宪法第37条、第38条所规定的“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关联性,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所作司法解释中并未做具体的说明,其宪法依据不甚明显;其三,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人格尊严权”与“其他人格权益”的内涵不甚清楚,难以通过某种规范化的方式加以划定,类同于德国民法理论中所说的“框架性权利”;其四,我国“一般人格权”的民法载体不甚清楚,《民法通则》第101条所规定的“人格尊严”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确立的“一般人格权”有些形似,但实质上不甚相同;其五,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之间的关系不甚清楚。依据《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款的规定,“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一般人格权”与该条罗列的两类具体人格权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关系;依据该解释第1条第2款的规定,作为“一般人格权”的“其他人格利益”与两类具体人格权之间的关系似乎又成了补充与被补充的关系。
三、 对我国民法中确立人格权
制度方式的宪法学分析 一般人格权是人格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人格权的形成路径是和人格权制度的确立方式关联在一起的。因此,在对我国一般人格权形成之应然路径进行前瞻性分析前,有必要对作为其前端的人格权制度在我国民法中的确立方式做出学理上的定位。
与公法权利相比,私法权利的设定并不单一地采取法定主义的设定方式,同时还有意定主义的设定方式。*诚如民法学者所言,“全部民事法律关系从调整方法角度可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法律关系可直接借助法定主义确认其权利义务内容并直接得以实现,另一部分法律关系则必须通过法律行为制度才能完成其内容确定和实现过程。”参见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前言。对于人格权而言,尽管其不可能通过意定主义的方式加以设定,但是,基于其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性质,学界固然并不认为可以通过意定的方式来设定人格权,但是,对是否可以、或者是否有必要通过法定的方式来设定人格权却存在诸多理解上的歧义,有法定说*有民法学者认为,人格权的设定应当采取法定主义的模式,其原因是:首先,权利和利益存在区别,侵权法对权利与利益的保护力度存在差异,利益不具有公开性、公示性,行为人往往事先并不知道某种行为是否会妨害他人的利益,若对利益保护太宽,会在一定程度上防碍人们的行为自由。其次,如果实行非法定主义,人格权法就没有必要列举人格权类型,完全由法官来判断是否应保护人格利益,必将使人格权的保护存在很大的随意性。最后,实行法定主义,在法律上尽可能地规定经过我国立法经验以及判例学说认可的可以类型化的人格权,有助于人们了解他们究竟享有哪些人格权。参见王利明、易军:《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前沿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6~200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14~315页。和非法定说*有民法学者认为,法律不可以也不可能对人格权实行穷尽性列举,所以绝对不能像物权那样采取法定主义的立场。参见江平:《民法的回顾与展望》,《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2期。两种立场。对此,笔者秉持前种立场。笔者认为,人格权本质上是一种宪法权利,而且,具有自然权利的性质。作为自然权利,它具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性,不可能通过民事主体之间的私下协商来创设或者确认某种人格权;作为宪法权利,该种权利指向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公权机关,后者担负着尊重、保障并不得侵犯人格权的宪法责任。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决定了它不可能对人格权作过于细密的规定,形成其内容、框定其范围、厘定其界限的责任主要是由法律来承担的。民法中关涉人格权的规定就是国家落实其宪法责任的重要表现形式。基于人格权的宪法权利性质,人格权指向的义务主体不可能包括民事主体,因此,他们并不承担通过合意形成人格权的宪法责任,意定主义对于民法人格权的设定来说自然也就无从说起。对此,人们有可能提出的理解上的困惑是:既然民法中的人格权应当通过法定主义的方式加以设定,为什么德国民法典中却并没有规定详尽的人格权内容呢?
笔者认为,这主要和我们对人格权在民法典中所处地位的理解有关。在我国民法典制定的过程中,围绕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中所处的地位,学界存在理解上的分歧。有学者认为,人格权法是二战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民法制度,由于历史的原因,该种制度在传统民法中规定得非常简略,甚至并不存在,但是,人格权法的内容是物权、债权等民法制度所无法包容的。有必要在未来制定的民法典中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以最大限度地丰富和发展人格权的内容。这不仅符合丰富和发展民法典体系的需要,也符合民法典体系发展的科学规律。*王利明:《人格权法》(第二版),第62页。对此,国内一些民法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参见梁慧星:《制定民法典的设想》,《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笔者认为,民法中的人格权应当规定于侵权责任法部分,不应当独立成编。主要理由是:人格权的本质是宪法权利,不是民事权利;人格权固然是法定权利,但它同时也是自然权利;人格权之宪法权利、自然权利的性质决定了不应当、也不可能在民法典中通过独立成编的形式作出详细规定。德国民法典之所以没有采取正面罗列的方式规定具体人格权的类型、确立一般人格权制度,并将前述内容独立成编,形成一种与物权、债权等民事权利相平行的部分,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德国民法典编撰者并未将人格权真正视为民事权利类型之一种,否则,在存在充分的抽象材料(人格要素的具体分解)的条件下,具有‘抽象化偏好’的德国人没有理由不去建构其内容如此丰富的‘人格权’的权利体系。”“德国民法之所以回避对人格权作出赋权性规范而仅作出保护性规范,原因便在于人格权是一种应当由基本法(宪法)直接规定的权利,民法可以‘分解’这种权利并加以具体保护,但民法不是‘创设’这种权利的上帝”,*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民法中的人格权仅仅是宪法上的人格权在民法中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已。当然,由于人格要素的可分解性,民法中的人格权往往被分解为生命、健康、身体、自由、姓名、名誉等诸种具体人格权,这些具体人格权涉及自然人民事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它们的侵犯将导致民事后果的发生。如果将这些权利的性质定性为宪法权利,这在逻辑上是很难解释清楚的。笔者认为,这涉及对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关系的理解问题。
从文本上来看,宪法和民法中均有人格权,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宪法中所规定的人格权是总体意义上的人格权,而民法中所规定的人格权却往往是分解后的诸种具体人格权。二者在逻辑上的关系是:宪法中所规定的人格权属于宪法权利,其指向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公权机关;民法中所规定的诸项具体人格权是宪法上人格权之内容在民法场域的展开,其性质属于民事权利,指向的义务主体是民事主体。对此,人们容易产生的质疑是:前述逻辑关系不仅适用于人格权,对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其他民事权利也同样适用。既然如此,为什么民法中的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可以专编的形式加以规定,而民法中的人格权却不可以独立成编呢?诚然,民法中的人格权和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本质上和宪法上的某种权利均存在逻辑关联性,都是对某种宪法权利之内容的展开和具体化,但我们不能仅仅依据这种逻辑上的关联性将它们的性质界定为宪法权利,并由此推导出必须由担负尊重、保护宪法权利责任的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的形式来设定该种权利,甚至必须通过独立成编的方式来框定其内容的结论。而且,必须注意到的问题是:人格权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的内容及秉性是完全不同的,具体人格权是这样,一般人格权更是如此!人格权是以民事主体依法固有的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权利,它与财产权的重要区别在于:人格权并不以财产利益为内容,且原则上不得转让和抛弃;*马特、袁雪石:《人格权法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页。人格权是一种专属性权利,它与个人的人格始终伴随、不可分离。说到底,人格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不是一种为法律所创设的权利。当然,笔者此处的意思并不是说,作为自然权利的人格权不需要法律、甚至不需要宪法加以确认和保障。笔者意图申明的立场是:人格权是自然权利,但同时也是需要通过法律予以实证化保护的权利,人格权的法定化对于作为自然权利的人格权的实现具有重要价值。“如果应有权利不能转化为现有权利,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的形态,那么就会防碍应有权利自身的现实化,妨碍人的价值的充分实现。”*公丕祥著:《法哲学与法制现代化》,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8~249页。反过来,如果片面强调法律对作为自然权利之人格权实现的重要价值,力求通过在民法典中将人格权制度独立成编的形式来强化对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凸显民法所张扬的尊重人格和保护人格的时代精神”,*薛军:《人格权的两种基本理论模式与中国人格权立法》,《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就从根本上背离了人格权之自然权利的本质属性,将其混同为一般的民事权利。因此,无论我们如何偏好法律相较于人格实现的重要价值,我们都不能置人格权之自然权利的秉性于不顾,片面强调乃至无限扩大人格权制度在民法中的空间场域。
统合前述,笔者认为,在我国民法典中确立人格权制度有其必要性。但是,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中并不需要独立成编。较为妥当的方式是仿效德国的做法,将其规定在侵权法中。采行这种方式,既可以确保人格权制度的法定性,又可以恪守其自然权利的本质特征;既可以正视人格要素分解之后具体人格权之民事权利性质的现实,又不从根本上偏离人格权之宪法权利的本质。
四、 我国民法中一般人格权形成之
应然路径的宪法学分析 与具体人格权相比,一般人格权具有拓展具体人格权范围的功能。然而,从实在法的内容来看,我国《民法通则》中仅仅规定了几项具体人格权,并未规定一般人格权。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民法学界开始借鉴德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理论,逐步接受了一般人格权的思想,并将其引入了司法审判实践。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所作《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作为一般人格权核心的“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作了确认,从而形成了我国的一般人格权制度。但是,正如笔者在分析前述第二个问题中所指出的那样,由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确立的一般人格权制度存在许多缺陷,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在我国民法典制定的过程中,多数学者主张建立一般人格权制度。但是,对于如何建立该项制度,学界的理解不甚相同。国内一些学者提出,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中应当独立成编,*参见王利明:《试论人格权的新发展》,《法商研究》2006年第5期;袁雪石:《人格权不宜独立成编?——与米健先生商榷》,《人民法院报》2004年11月12日;薛军:《人格权立法的两种基本理论模式与中国人格权立法》,《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马俊驹、张翔:《人格权的理论基础及其立法体例》,《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一般人格权制度应当规定于其中。对此,笔者秉持否定立场(理由见前述)。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民法中确立一般人格权的方式有两种:其一,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模式。该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德国。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直接依据基本法第1条、第2条的规定,经由《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中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将一般人格权注入人格权纠纷的审判之中,从而形成“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模式;其二,具体人格权+人格权保护的一般条款模式。该模式的典型代表是瑞士。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第28条*《瑞士民法典》第28条规定,“任何人在其人格受到不法侵害时,可诉请排除侵害”;“诉请损害赔偿或给付一定数额的抚慰金,只有在本法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始得允许。”首次从立法层面确定了保护人格权的一般条款,*参见马俊驹、余延满著:《民法原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将具体人格权之外的一般人格权注入其中,由此形成了具体人格权+人格权保护的一般条款模式。目前,我国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应当采行“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模式。但国内也有学者秉持后种立场。*有学者认为,“在我国人格权立法中,不应该采用特别人格权结合一般人格权的结构形式,而应该采纳特别人格权结合人格权保护一般条款的结构形式”,具体理由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一般人格权制度是通过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判例创设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弥补《德国民法典》关于特别人格权规定的数量不足与立法漏洞,其实质是法官通过司法途径与个案判断的方式保护人格权益。但是,在我国则不存在这一前提”;其二,“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创立,与德国侵权法对权利与利益的区分保护的立法模式密切相关。由于我国侵权法采取的是与之不同的抽象概括的立法模式,因此一般人格权在我国现行立法上难以发挥作用”;其三,“一般人格权由于没有明确的界限,难以被认定为民事权利。不仅如此,由于我国民法理论广泛接受人格权这一概念,如果再采纳一般人格权,则人格权、一般人格权以及具体人格权之间必然产生逻辑上的冲突与矛盾”。参见冉克平:《一般人格权理论的反思与我国人格权立法》,《法学》2009年第8期;薛军:《揭开“一般人格权”的面纱——兼论比较法研究中的“体系意识”》,《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5期。对此,笔者秉持后种立场。其原因在于:我国当下人格权立法的重要发展趋势是:通过民事立法的形式确立一般人格权,2017年出台的《民法总则》第109条的规定已然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立场,这与此前我国一般人格权的生成历史不甚相同。前述两种方式相比较而言,后者即《瑞士民法典》确立一般人格权的方式具有如下特点:其一,《瑞士民法典》是通过立法的形式直接规定一般人格权的,而《德国民法典》本身并未直接规定一般人格权,它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经由《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中所规定的“其他权利”、通过司法判例的形式挖掘出来的;其二,《瑞士民法典》首先在其“人法”编“自然人”一章规定了一般人格权,进而通过《瑞士债法典》中的侵权行为法*《瑞士债法典》第一章第二节“侵权之债”中的第41条。加以保护。与之相比,《德国民法典》在总则民事主体部分并无关于一般人格权的规定,而是在其侵权法部分间接规定了一般人格权。目前,世界范围内采取后种方式的国家不乏其例,代表性国家和地区如法国、日本、葡萄牙、瑞典、俄罗斯、巴西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等。尽管各个国家确立一般人格权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它们的共性在于:在列举诸种具体人格权的同时,通过人格权保护一般条款的方式对其他人格权益加以保护。相比之下,以瑞士为代表的后种方式显然更契合当前我国人格权立法的发展趋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模式对于中国毫无价值可言。恰恰相反,德国模式的最大价值在于为基本权利实现其对民法人格权保障的价值统合提供了制度性管道,在不危及民法自身体系完整和逻辑自洽的前提下实现了宪法与民法在人格权保障问题上的无缝对接。这对于厘清当下国内学界热议的宪法与民法典的关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笔者的完整立场是:立法上采行以瑞士为代表的后种模式确立一般人格权,司法实践中借鉴德国的相关经验和做法,最大限度实现宪法与民法在人格权保障问题上的无缝衔接。笔者认为,人格权本质上是一种宪法权利,而不是民事权利。基于人格要素的可分解性,人格权固然可以在民法中分解为生命、身体、健康、名誉等具体人格权,并由此使后者的性质实现由宪法权利向民事权利的结构性转变。但是,一般人格权却迥然不同。一般人格权不是对各种具体的人格要素的保护,它是对具有高度抽象性的一般人格的保护。一般人格权在立法层面无法或者暂时不能作进一步的分解,其宪法权利的性质不会因为规定于民法而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如果将一般人格权明定于民法中,实际上意味着作为私法的民法中确立了一种迥然相异于民事权利的宪法权利,这不仅矮化了作为宪法权利的一般人格权,而且造成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在民事场域的混同。诚然,民事权利与宪法权利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关联性,但是,这种关联性并不足以导致抹煞二者之间的界限、在民法场域混同适用的结果。更加之,混同适用无论对于民法自身,还是对于宪法来说,都是有害无利的。
从法理上来说,民事权利是法律为保护民事主体的某种特定利益而设定的权利,但是,该种权利本质上不是一种仅仅表征归属关系的静态权利,而是一种可以将民事主体关联在一起的动态的权利,推动该权利运行的动能源于其固有的请求权能,该种权能是“温德沙伊德从罗马法和普通法中的诉的概念中发展出来的”,*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第67页。在立法上为《德国民法典》所首创。“请求权的产生,保障了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为权利的实现和权利人利益的维护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制度工具。同时,请求权理论的发现还为当事人提供了在权利竞合时的选择自由,增强了权利人实现和保护其权利行为的可选择性。因此,请求权所提供的权利保障机制,强化了私法自治的理念,使私法自治具有了充分的条件和广泛的空间。”*辜明安:《论请求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当代法学》2007年第4期。就一般人格权而言,由于它本质上并不是民事权利,而是一种宪法权利,因此,原则上它不应当具有民事权利所固有的请求权能。就一般人格权的宪法权利属性来说,它应该属于自由权的范畴。作为自由权,一般人格权固然也有正向请求的功能,但是其权利的重心主要是指向于国家的消极防御。而且,即便是确认乃至拓展其正向请求权功能,其指向的义务主体也只能是国家公权机关,而不能是民事主体。如果泯灭一般人格权的宪法权利性质,对其不加思辨地作出民事权利的性质定位,赋予其类同于民事权利那样的请求权功能,那么,权利人就由此拥有了向民事义务主体提出保护其一般人格权的请求权能。由于一般人格权在内涵上的高度不确定性,加之其在民法场域所具有的绝对权属性,社会公众将由此承担过当的尊重和保护他人“一般人格权”的民事责任,处于一种动辄得咎的状态,其充分挥洒自由的民事行为空间被大大压缩。因此,采行“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模式不适合中国。诚然,德国民法确立一般人格权的模式就是“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而且,在德国的法治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不可忘记的是,德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是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判例的形式创立的,而不是《德国民法典》直接规定的,其在民法中的依托是《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中的“其他权利”。这与我国在民法中直接规定一般人格权的做法完全不同。其原因在于:从宪法法理上来说,宪法权利是指向于国家公权机关的一种权利,原则上不能适用于民法场域。基于民事主体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现象的现实存在,德国创造了宪法权利的“第三者效力”理论。依据该理论,宪法权利如果确实有必要适用于民法场域的,应当通过民法中的相关条款(如公序良俗原则)实现其对民法场域的效力涵摄,但是不能直接适用于民法场域。如此设计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避免宪法价值在民法场域的过当注入,避免由此对私法自治造成的制度性损害。这不仅是确保民法自身逻辑自洽的需要,同时也是维护宪法由以存在之市民社会基础的需要。由此观之,德国民法确立一般人格权的方式似乎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具体人格权在保护人格权益方面的局限性,它同时还有联结民法与宪法的功效。
对于中国来说,由于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通过立法、而不是司法的方式在民法中直接规定一般人格权,因此,德国的模式并不适合中国。与“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模式相比,采行“具体人格权+人格权保护一般条款”的方式似乎更适合于中国。其原因在于:在该种模式下,民法中并未直接规定“一般人格权”的概念,而是通过“人格”*例如,《瑞士民法典》第28条规定:“任何人在其人格受到不法侵害时,可诉请排除侵害”;“诉请损害赔偿或给付一定数额的抚慰金,只有在本法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始得允许。”、“身体或精神”*例如,《葡萄牙民法典》第70条第1款规定:“本法保护任何人之身体或精神不受任何非法伤害或将来之伤害。”、“其他人格法益”*例如,1999年修正后的“台湾民法典”债编第195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健康、名誉、自由、信用、隐私、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节重大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其名誉被侵害者,并得请求恢复名誉之适当处分。”等具有高度抽象性的范畴来承载“一般人格权”的。该种模式相较于“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模式的特点及其在民法层面的优势,国内有民法学者已经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参见冉克平:《一般人格权理论的反思与我国人格权立法》,《法学》2009年第8期。此处笔者意图进一步指出的是该种模式在宪法层面的价值。笔者认为,该种模式的宪法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民法的性质迥然相异于宪法,它是私法,而不是公法。私法自治是民法由以存在的基础,宪法是在此基础上的展开并反过来通过对国家权力的构筑来支撑私法自治的空间。私法自治内在地要求民法典的价值中立,以此来维护其体系的完整和逻辑上的自洽。该种模式避免了作为宪法权利的一般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的直接植入,缓解了民事主体承担的过当的宪法责任,在较大程度上维持了民法技术性自治规范的体系完整,夯实了私法自治的基础,并进而加固了宪法由以生成和顺畅实施的社会基础;其二,宪法权利固然指向于国家公权机关,原则上不能适用于私法场域,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彻底否认了民事主体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现实可能性。民事审判实践中具体人格权在保护公民人格权益范围方面的局限性已经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一方面,基于人格要素的可分解性,人格权在民法场域已经分解为生命、健康、身体、姓名、名誉等诸项具体人格权,但是,它们所涵盖的范围显然不足以包容公民人格权的全部空间场域,作为宪法权利的人格权面临着来自民事主体的现实侵害。在“具体人格权+人格权保护一般条款”模式下,法院经由“人格权保护一般条款”,将一般人格权通过法官的制度性搅拌,合乎逻辑地注入到民事审判之中,在不危及私法自治的前提下,实现了对作为宪法权利的一般人格权的民法保护。令人遗憾的是,2017年通过的《民法总则》第五章却首先在第109条规定了“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继而在其他条文中规定了“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个人信息权”等具体人格权,它所采行的确立一般人格权的模式显然属于“一般人格权+具体人格权”模式。由于“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等一般人格权在内涵上的高度不确定性,不仅其在民法场域的诸种缺陷将逐步显现出来,而且,其原本有可能承载的衔接宪法与民法的功能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如何在新的民事立法背景下,基于宪法解释制度在短期内难以实现根本性改观的现实,最大限度地确保宪法和民法之间的衔接流畅就成为此后宪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ConstitutionalAnalysisonFormationPathoftheGeneralPersonalityRightinCivilLaw
LIU Zhi-gang
(LawSchool,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8,China)
The general personality system in Switzerland and Germany represents respectively the two typical formation paths of general personality right. It is directly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basic law and the judicial precedent in the Supreme Court of Germany. The protection mode in Germany is “specific personality right and general personality right.” Chinese general personality right’s formation path requires further improvement. The right of personality is a constitutional and natural right, although it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a legal way, it is not suitable for being compiled independently in civil code. After the decomposition of personality factors, the specific personality right in civil law is civil right, but the nature of constitutional right of general personality right should not be changed. The mode of “specific personality right and general provis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ity right,” following the Swiss mode,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China. This kind of mode has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private law, and it also has constitutional value.
general personality right in civil law; formation path;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责任编辑刘慧]
刘志刚,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是教育部2015年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特色人权观及人权理论研究”(项目批准号:15JZD00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