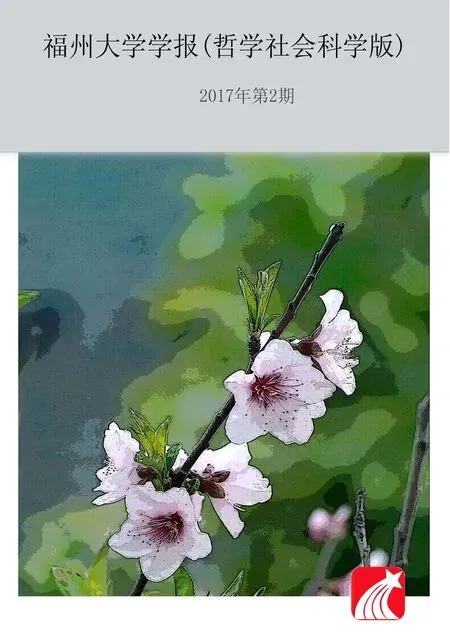麦卡锡西部小说中少年形象的历史之重
李碧芳
(福州大学跨文化话语研究中心, 福建福州 350116)
麦卡锡西部小说中少年形象的历史之重
李碧芳
(福州大学跨文化话语研究中心, 福建福州 350116)
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科马克·麦卡锡迄今为止创作了六部西部小说,这些西部小说中有一个特殊群体即未成年人,他们都以主人公的角色出现且贯穿故事情节始末,对故事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少年在麦卡锡的西部小说中都是寓言式的人物,他们深陷现代文明的污泥浊水之中,不能自主命运。暴力、欺诈、背叛、冷漠、暗算等是他们生活世界里的常态,失落、伤感、迷茫、创伤、绝望是他们的生活状态,与伊甸园的美好图景迥异。从他们的故事中,我们听见了美国伟大历史背后的野蛮之声,看见了美国西部神话的破碎,接收到了人类末日的预警。他们承载着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和宗教热情,在见证美国野蛮发展历史的过程中反省美国文明,同时向美国社会发出拯救美国梦的呼声。
科马克·麦卡锡; 西部小说; 美国文学
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1933-)1985年出版的《血色子午线》标志着他的创作由南方小说向西部小说的转型。此后,他相继发表了《骏马》(1992)、《穿越》(1994)、《平原上的城市》(1998)以及《老无所依》(2005)、《路》(2006)等五部西部小说,其中多部小说都被改编成电影,在世界文学领域影响甚广。麦卡锡西部小说中有一个特殊群体,即未成年人,他们几乎都以主人公的角色出现在麦卡锡所有的西部小说之中,而且他们的行迹贯穿故事情节始终,对故事叙事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人们的意识中,少年往往与“天真”“纯洁”等意象联系在一起,他们展现给人们的是净土之上天使般的干净和愉悦。然而,在麦卡锡的小说中,这些少年却深陷现代文明的污泥浊水之中。暴力、欺诈、背叛、冷漠、暗算等是他们生活世界里的常态,失落、伤感、迷茫、创伤、绝望是他们的生活状态,与伊甸园的美好图景迥异。从他们的故事中,我们听见了美国伟大历史背后的野蛮之声,看见了美国西部神话的破碎,接收到了人类末日的预警。从宗教和历史的视角不难发现,麦卡锡小说中的少年们,无论有名无名,其实都是寓言式的人物。他们承载着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在见证美国野蛮发展历史的过程中反省美国文明,同时向美国社会发出拯救美国梦的呼声。
一、《血色子午线》中深陷暴力漩涡的少年:美国发展历史镜面
《血色子午线》中的暴力是一道最刺眼的风景。小说描写的暴力不仅场面极端血腥,而且手段极端残酷,令许多读者望而却步,有些读者甚至因为暴力叙事而将麦卡锡作品列入糟糕作品之列。其实,麦卡锡并非为了暴力而暴力。他小说中的暴力叙事都是由其叙事内容决定的。《血色子午线》描写美墨战争结束后1849到1850年间的一段历史,小说中描写的基于史实的几个事件本身就充满血腥,只不过有别与历史学家平缓的叙述语气,作家采用聚焦、夸张、重复等小说修辞手法将历史与虚构有机杂糅,从而凸显了人物的残暴以及场景的惨烈,使事件更具震撼力,使读者获得与阅读历史迥异的阅读效果,让其产生恶心呕吐等不适感以此引发他们对历史和现实的再思考。
小说中一个无名少年贯穿始终。作者对他的身世只是简单带过,读者只知道他是田纳西人,生来丧母,没受过教育,14岁时离家游荡,常与人斗殴。这说明他是谁不重要。阅读全书,他无处不在,作者看似主要描述他少年时期的经历,因此读者会认为他就是故事的主人公。但如果细细品读,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他不是作者主要描述的对象。笔者认为,少年是个影子人物,他牵着一根线索的引线引领读者从他16岁一步步走到他45岁,期间时间横跨28年(1849-1878)。在他的引领下,读者认识了一个个形态各异的人物,经历了一桩桩惊心动魄的事件,而这些人物和事件才是作者的重墨所在,因为《血色子午线》的震撼力就来源于这些人物和事件。换句话说,少年是被作者作为历史见证人和解说者的身份虚构出来的,他的使命就是将历史再现于读者面前。无名少年在游荡过程中无意间被拉去加入美国的军事阻扰队伍,前往墨西哥,出师不久,便遭到了印第安人的致命打击。而后因为偶然,他又加入受雇于奇瓦瓦州州长的头皮猎人队伍,这个队伍在墨西哥境内四处游荡,大肆屠杀,以遇害人的头皮为收据换取黄金,最后在尤马人的报复中这个队伍几乎全军覆没,而他幸运逃脱,但最终在格里芬的蜂巢酒馆被法官杀害。以上虚构的少年故事牵扯出了诸多基于史实的历史事件。
首先是美墨战争。美墨战争发生于1864年9月,是美国西进大战略中的一环,战后作为战胜国的美国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以及科罗拉多、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等大片土地。如前所述,《血色子午线》描写的是美墨战争结束后1849到1850年间的一段历史,因此美墨战争就是该小说的历史大背景。其次,小说中头皮猎人队伍在墨西哥境内大肆屠杀印第安人的事件在拉尔夫·史密斯《印第安人》一文中也有记录。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曾在1896年的文章《西部问题》中总结道:“西部问题实际上就是美国发展的问题。”他认为迄今为止,美国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大西部的殖民史。[1]美国西进运动的目的就是寻求经济发展的空间,而在美国不断向西扩张领土的过程中,与土著印第安人的冲突就在所难免,而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使边疆成为了文明与野蛮的交汇点。小说提到的美墨战争老兵格兰顿率领的头皮猎人队伍与奇瓦州州长达成协议,不加区分地屠杀各种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以遇害者的头皮为收据换取黄金就是典型的例子。不过,对于美国人在西进过程中对待印第安人的野蛮行径,有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人认为是理所当然正当合理的行为,弗里德里克﹒帕克森在其专著《最后的美国边疆》中就阐述了这类美国人的观点:“这些领地是从大自然和野蛮人手中获得的,是勇气和远见逐步将其从荒野变成充满生机的联邦的。”[2]这个观点活脱脱地展现了美国殖民者“命定夸张说”和“美国优越论”的主张。最后,许多学者认为《血色子午线》不仅仅描述了美国西进运动时期的殖民本色,同时也影射了美国现代殖民者身份,因为该小说完成时间正好在越南战争(1955-1975)之后。越战是美国暴力侵略的又一段不光彩历史,曾引发国内的反战高潮。如果因为国家大肆宣扬的神话般英雄气概和国家进步使美国民众无视西部神话中灭杀他族的暴力之事实的话,那么这种全民的历史失忆症却被越战治愈,因为越战让美国民众深刻认识到了美国骨子里的暴力倾向,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和麦卡尔·华勒斯在其合著的《美国暴力》一书中这样说道:“ 毫无疑问,将来我们会更加关注我们的暴力。今天我们不仅认识了我们自身的暴力,我们还被此暴力惊吓到了。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从历史承继更多的是暴力而非我们民族形象所能承受的自豪感或自命不凡。”[3]许多学者认为越南战争其实是西部殖民战争的翻版,它使人们重新审视美国民族主义精神的残酷性。
除虚构事件与历史事件的契合外,《血色子午线》中一些人物也有历史人物原型可追溯,比如小说中两位主要人物约翰·乔尔·格兰顿将军和霍尔顿法官均出现在赛缪尔·张伯伦1861年写的自传《我的忏悔》中,只不过虚构的人物和情节与史实人物和事件交错使故事虚实相间,情节也因此扑朔迷离,跌宕起伏,令人回味无穷。格兰顿将军就是小说中头皮猎人队伍的头目,是个美墨战争的老兵。一路上他率领军队杀入各个村庄,他们“拖出鲜血淋漓的受害者,砍死垂死的人,砍下跪地求饶者的头”[4],“他们穿行在死尸中,用刀子收割黑色的长发,受害者们秃着头颅,如同戴着怪异的血淋淋的胎膜”[5]。他的形象就是一个自负残暴的美国殖民者的形象,他的残暴引来了印第安人的英勇抵抗,他最终也惨死在印第安人手中,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与格兰顿将军相比,霍尔顿法官形象的虚拟元素应该更多一些。霍尔顿法官形象是基于塞缪尔·张伯伦的自传《我的忏悔》一书中关于“法官霍尔顿”的历史性描述,而在《血色子午线》中作者对他的塑造颇费一番心思。作者保留了《我的忏悔》中这个人物多才多艺的人物特点,但其他许多方面就是作者根据创造意图进行的再塑造。从外表上看,法官 “他头如秃石,无须无眉也无睫毛”[6],他身长近七尺,“巨大、苍白、无发、如同一巨婴”[7],形象令人惊悚,而从人物特点上看,他即有超人的一面,又有非人的一面,集智慧和邪恶于一身。他通晓多门语言,身兼各种身份,精通各类技艺,精力异常充沛,是个战争狂人,奸杀人不分性别老幼。法官的形象特殊而又矛盾,引起了许多学者关注,有学者认为从他对知识的热切渴望和极强的求知欲方面看,他反映了一种知性的美德,但从他用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获得至高的权利以及他毫无人性的杀人行为来看,他又是恶人[8]。如果我们将法官形象与美国国家形象联系起来,那么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看,法官霍尔顿是个十分丰富的喻体。笔者认为他象征年轻的美国,象征美国人好战的性格,象征美国霸权主义思想。也许人们从他的冷漠暴虐中感觉到的是一个无耻狂徒,但从政治的角度解读,他或许就是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只是这个“英雄”形象仅局限于一个民族,附带太多的政治隐喻。
二、《边境三部曲》中“反英雄” 牛仔少年:美国西部神话破灭的亲历者
美国西部小说是构成美国民族性和文化价值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西部小说中的牛仔形象更是随着西部小说的发展成为美国人心目中不可替代的英雄。牛仔之所以备受美国人民喜爱,是因为他们热爱自由,坚持正义且勇敢勤劳,而这些品质也正是美国人民共同拥有的高尚品质。此外,牛仔受人爱戴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故事与美国宪法“人人生来平等”的理念相吻合。从“皮袜子”开始,牛仔多是被描写成“具有高贵品质的底层人物”,他们虽出身低贱,但通过个人奋斗,许多从帮工这一社会底层进入上流社会,从而实现自己的美国梦,最有代表性的是欧文·威斯特描写的来自弗吉尼亚的牛仔杰夫,他大胆提出了牛仔“和真正的贵族同类”的宣言。威斯特创造的这个“从木屋到白宫”的神话类型的牛仔杰夫,更使牛仔充满了浪漫神秘的色彩。可以说,传统的牛仔承载着诸如美国梦、个人主义、独立、自由、民主等丰富的美国文化内涵。可是,在麦卡锡的西部小说《边境三部曲》中,神话般的牛仔传奇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反英雄”牛仔形象。
首先,《边境三部曲》中的少年所向往的牛仔生活被残酷的现实打击,在家乡,他们失去了牧场也失去了马,而牧场和马是牛仔身份的两个重要标志,因此他们其实是落没的牛仔。《边境三部曲》所描述的时代是二次大战后的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前,西部虽然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经过近百年的开发,已经完成了边疆农业、牧业、矿业的开发,但许多地区因人口稀少,不能支撑地方工业的发展,所以西部绝大多数地区的产业结构依然以传统的农业和原材料加工业为主,与东部经济相比,西部经济在整体上处于劣势。可是到了二战期间,美国政府看重了西部广袤的土地,开始超常规地倾注资金在西部发展新型工业和军事工业、开辟科研场所,充分挖掘了西部的战时经济价值,使西部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个发展在战后得到不断的深入。而西部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工业化替代了农业畜牧业,城市化消解了广袤的大平原。[9]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麦卡锡《边境三部曲》中的牛仔们的命运自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牛仔们遭遇到的第一个沉重打击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牧场正逐渐消失。三部曲中第一部《骏马》一开始就为我们展示了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工业对美国西部的侵蚀,少年牛仔约翰·格雷迪因此失去了在得克萨斯州的家乡牧场。那个曾经被他的父亲视为“仅次于死后进天堂的乐事”的田园牧场生活,在国家政治的权威之下,进入了历史的尾声。格雷迪家乡牧场的命运绝非个案。在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平原上的城市》中,虽然格雷迪和比利还有麦克牧场容纳他们的牛仔梦,但每况愈下的牧场经济使得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艰难贫穷,到后来比利离开麦克牧场四处流浪时,他途中所见的都是西部牧场的没落,“到处牧场的大门都敞开着无人看管,砂石被风吹出来,大路都给埋没了。没几年,整个草原几乎看不到牛羊的踪影了。”[10]再来说说马。三部曲中的少年们都爱马如命。比利和博伊德为了寻找家里被盗的马,不辞辛苦从新墨西哥州策马挺进墨西哥,冒着生命危险在森林和荒原中与亡命之徒盗马贼和马贩子周旋,几经遭遇,博伊德差点丢了性命。因被牧场主出卖而入狱的约翰·格雷迪和罗林斯,他们的马就被上尉占为己有。而格雷迪在墨西哥遇见的另一个少年布莱文斯则为了夺回钟爱的小红马被夺马人陷害入狱,最终遭人暗算,客死他乡。比利在墨西哥几次找回自己的马又几次被马贩子用武力夺走。这些牛仔们争夺马的过程,其实是在捍卫自己作为牛仔的身份。他们夺回马所经历的种种艰辛和危险说明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牛仔已经失去了立身之本。
其次,《边境三部曲》中的牛仔与经典牛仔不仅形象反差很大,命运也截然不同。牛仔的经典形象是高大强健智勇双全的成年人,他们替天行道,扬善除恶,不仅深得人们拥戴,还终能抱得美人归。而麦卡锡笔下的牛仔多是瘦弱单薄被动接受命运的未成年少年。他们也追求自由正义,也勇猛果敢,但面对黑暗势力,他们始终处于弱势,即无能施救于人,爱情路上还得披荆斩棘,甚至牺牲生命。《骏马》中少年格雷迪失去家乡牧场后不甘梦想轻易破碎而策马南下进入墨西哥领土寻找新的牧场,继续他的牛仔梦的追求。他在墨西哥科阿维拉州的普利西玛圣母马利亚牧场找到工作,过上了一段美好的理想牛仔生活,但好景不常在,他与农场主女儿的恋情险些给他带来杀身之祸,他最终只得惆怅离开。而当他在三部曲最后一部《平原的城市》再次出现时,他与妓女玛格达琳娜的恋情却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三部曲的第二部《穿越》同样描写了命运不济的少年。主人公比利为了不同目的两次穿越墨西哥边境,第一次是带着一只被追猎的怀有身孕的母狼回到故土,本想放其回归自然,却不幸落入一群恶徒之手,他在街边舞台上与玩弄母狼以牟取暴利的那群恶徒对抗无果,最终忍痛击杀母狼以结束其悲惨遭遇,逃回家后却发现家人惨遭杀害弟弟下落不明。第二次他穿越墨西哥边境的目的是寻找失散的弟弟。他在墨西哥境内与弟弟相见,但兄弟俩一路遭遇各类恶徒,最终他弟弟在追求自由的亡命天涯中死亡,比利将其尸体艰难运回家乡。到第三部时,比利成为格雷格的朋友再次出现,格雷格死后,他便沦落为流浪汉,浪迹天涯。可以这么说,这些少年们一路追随自己的牛仔自由独立之梦想而努力奋斗,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成功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三、《路》中“问题”少年:世界末日的预警
末世情结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来源于宗教信仰。美国人相信上帝,敬畏上帝,是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美国思想界权威诺瓦克(Michael Novak)曾说过,在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体系中,文化系统是以基督教文化精神为核心的,而末世情结便是《圣经》之《启示录》对美国人民最直接的影响。《启示录》预示人类发展的各个时期将要发生的、多为悲剧性的事件,其终局是人们熟悉的所谓“最后审判”,它是西方文化中关于世界末日预言的一个重要源头。《启示录》的末世说是人们对世界末日的担忧和恐惧,其主要起因是人们的时代焦虑感,在西方,每发生一件大事都有人在《启示录》中对号入座,并寻求解释,这也是美国末世文学和电影作品繁荣的主要原因。麦卡锡的小说《路》就是这繁花丛中耀眼的一朵。小说背景是一次世界性核爆之后的世界,烟尘遮蔽了阳光,植物无法生长,四处皆是漆黑的小溪与灰濛濛的荒草地。面临绝境,人类本性中的恶被无限放大,回归为最原始的兽性,恶之花在荒野里无限衍生。此时,地球成了一片废墟,所有的一切都是虚无,只有死亡才是真实的存在。小说的主人公,一对幸存下来的父子在此背景下开始一次漫长而无望的历险。男人带着孩子上路,想要到达想象中充满希望的南方海岸。这部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泛恐怖年代的后启示录,一是由于整部小说弥漫末世的绝望和寻求希望的不确定性,二是由于作者赋予小说中那位少年(父子中的儿子)代表人性正能量的纯真善良秉性及其潜意识中强烈的救世愿望。一路上,少年被所见所闻惊吓,不停地向其父发问,而少年之问其实就是作者之问,也是所有美国人之问。
少年的问题归纳起来有四类。第一类问题是“我们去哪?”“我们该怎么办?”大灾难造成死亡无数,人们失去了家园,四处荒芜一片,到哪去?该怎么办?这些成了想活下去的幸存者共同的疑问。父亲给儿子指明了一个方向,向南方去。虽然小说里南方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父亲坚信,那里就是未来世界的希望。儿子显然有些将信将疑,但他选择相信父亲。第二类问题是“他(们)是好人吗?”灾难给人性带来了极大考验。父子一路上遇见各色各样的人,他们以不同方式逃难求生。小偷,杀人者,吃人者,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这世界还有好人吗?少年疑惑,因为在他童真的眼里,他遇见的人应该都是好人。但他知道,他父亲时刻都在防着坏人,对见到的人都持怀疑态度。这就是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不同。儿子反复问父亲“还有好人,他们都到哪去了?”父亲肯定地告诉他还有好人,只是不知道他们在哪。如果还有好人,那么遇见的人就有可能是好人吧。这是少年的逻辑,所以他对路上遇见之人都想伸出救援之手。他想救路边垂死之人,他想救饥饿的小狗,他想救偷他们东西的小孩,他想救对他们显然心怀芥蒂的老人,总之他想帮助他见到的每个落难者,父亲反对,他甚至生父亲的气。“该不该救?”的问题一路折磨着少年。第三类问题是“我们是好人吗?”儿子问的这个问题最折磨父亲,因为父亲出于父爱防着所有人,他身上带的枪会随时射向可能威胁他们生命的任何人。第四类问题是“我们会死吗?”大灾难面前谁也绕不开死亡的阴影。随时随处可见的尸体让人觉得死亡随时将至。少年虽小却也能深刻感觉死亡的威胁,他最害怕的是父亲会死去,他会失去依靠。尽管父亲对他们的前途也不确定,但就这个问题他给了儿子确定的回答,即少年不会死,到了南方他就会获救。他总不失时机教儿子自救的办法,以备自己不在时儿子还能继续活下去。临死前他告诉儿子,希望之火就在儿子的身上,并暗示儿子他所带着的希望之火就是未来世界的希望。
观察以上少年的四类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其实都是关乎人类世界及人性的大问题。麦卡锡一开始就直述灾难的场景而忽略灾难的起因,这说明他认为灾难起因不言自明,懂得美国历史,人们就懂得灾难会如何发生。他先前的小说也已经暗示了这一点。此外,他也更加关注灾难过后人类如何拯救自己。就在父子的问答之中,作者展现了人性恶之花所能制造的恐怖世界,同时也提示人性之善是制恶之本,是拯救世界之源。
四、结语
伟大的作品大多反映其所处时代的特点,而作者的想象尽管深远,但正如Sam Shepard所言,“它不能超出你的经验范畴”[11﹞。麦卡锡曾说过,没有流血的人生是不多见的,而不关注生死的小说同样算不上是真正的文学。基于此观点,麦卡锡的小说更多关注的是历史与现实的残酷性。从《血色子午线》到《路》,麦卡锡一直抚摸着美国历史的创伤。在《血色子午线》中,他从美国人自视辉煌的西部神话中看见了美国民族血液中的暴力基因,它像把双刃剑,带来美国历史进步的同时也为美国未来留下后患,这部小说提醒美国人正视自身的暴力基因,并通过无名少年毫无意义的生存与死亡说明国家意志如何主宰国人命运;在《边境三部曲》中,他通过反英雄的少年牛仔故事再次挑拨美国人神经,他无情地打破美国人引以为豪的西部神话,将美国人从历史的辉煌之梦境硬拽入严酷的现实,而在《路》中,那对貌似《圣经》中圣父圣子的父子在末世之中对希望的求索和少年肩负的普罗米修斯希望火种的传递之责则向美国人发出预警:暴力不除,神话不再,末世因此即将来临。在 “后911”时代的今天,经济危机与恐怖袭击一再上演,末日恐慌隐伏于每个美国人的内心。如何突围?正如《路》中所描述的那样,末日就像是一种冷酷的黑,始终伴随着荒原上一点点飘摇不定的微暗之火。身随少年的那点星星火苗就是小说里惟一的亮色,隐喻着未来世界的希望。麦卡锡眼中的世界,阴冷有之,黑暗有之,却绝不缺少希望。他用清醒一次次揭开现实的丑陋疮疤。但他揭露黑暗的目的不是置人民于恐慌之中而使其悲观绝望,而是协同人们一起正视现实,寻找光明,寻找救赎。
注释:
[1] 罗小云:《美国西部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2] Frederic Logan Paxson,TheLastAmericanFrontier,New York: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Inc. , 1970,p.1.
[3][11] Barley Owens,CormacMcCarthy’sWesternNovels,Arizona: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Tuscon, 2000,pp.32,21.
[4][5][6][7] 科马克·麦卡锡:《血色子午线》,冯 伟译,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13年,第176,177,5,372页。
[8] Brent Edwin Cusher, “Cormac McCarthy’s Definition of Evil: Blood Meridian and the Case of Judge Holden”,PerspectivesonPoliticalScience,No.4 (April 2014),pp.223,230.
[9] 高芳英:《二战期间美国西部经济地位的转变》,《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
[10] 科马克·麦卡锡:《平原上的城市》,李 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
[责任编辑:陈未鹏]
2016-11-08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科马克·麦卡锡小说中的美国现代文化寓意”(FJ2016B183); 福州大学研究生院优质课程建设项目(52004641)。
李碧芳, 女, 福建闽侯人, 福州大学跨文化话语研究中心副教授。
I106.4
A
1002-3321(2017)02-006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