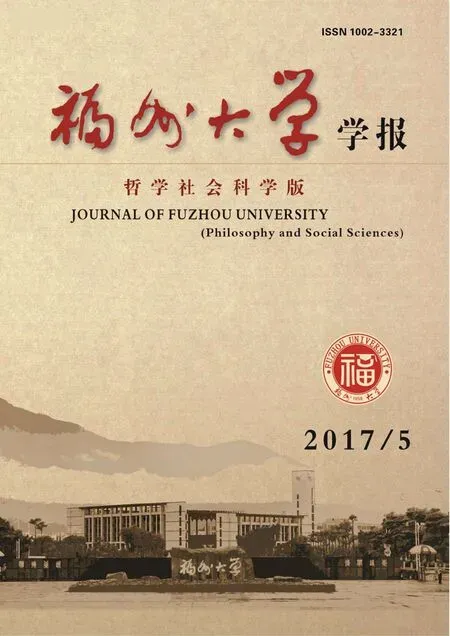1920年代台湾左翼思想的兴起及
孔苏颜 刘小新, 2
(1. 福建社会科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1;2. 两岸协创中心福建师范大学两岸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福建福州 350007)
1920年代台湾左翼思想的兴起及
孔苏颜1刘小新1, 2
(1. 福建社会科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1;2. 两岸协创中心福建师范大学两岸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福建福州 350007)
左翼思想在1920年代台湾的兴起是台湾现代文学的重要现象。但对这一时期台湾左翼思想的研究成果仍存在一定的盲视:一方面大陆学界未将1920年代台湾左翼思潮纳入中国左翼运动的整体视野之中予以思考与论述,另一方面台湾学界也未能在两岸视野以及东亚视野之中对台湾左翼思潮进行整体性论述与建构,从而遮蔽了台湾左翼思潮在跨域文化地景中“重层而丰厚的面貌”。因此,重返1920年代的历史现场,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与整体性视野中论述1920年代台湾左翼思潮的兴起、发展及其知识圈的建构与交流互动及其相关问题显得尤为必要。
台湾左翼; 文化启蒙; 前进东京; 东亚知识圈; 建构; 互动
左翼思想在1920年代台湾的兴起是台湾现代文学的重要现象。[1]正如陈芳明所言:“要看待台湾左翼文学的发展,不能抽离历史脉络而予以孤立地考察。从当时的世界文学地图来观察,就可发现台湾作家的创作与思考,其实与三○年代全球性的左翼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2]左翼文学在台湾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台湾知识分子在觉醒之后所采取的文学行动,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建立了优良的传统。叶石涛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中将这一时期称之为“摇篮期”,1920年代的台湾文学家“所担负播种的使命,在意义上可以说远超过他们收获的任务”[3]。事实上,台湾左翼文学直到1927年才蓬勃发展起来,这是由于台湾受到日据时期客观环境的制约。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从1927年至1931年,台湾左翼政治运动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工友协助会、台湾工友联合会、台湾农民组合、台湾民众党、台湾共产党、台湾左翼文化联盟等组织相继成立,为当时台湾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与震撼。然而,当前大陆对这一时期台湾左翼思想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盲视,现有的研究成果并未将1920年代台湾左翼思潮纳入中国左翼运动的整体视野之中予以思考与论述,而台湾学界也未能在两岸视野以及东亚视野之中对台湾左翼思潮进行整体性论述与建构,从而遮蔽了台湾左翼思潮在跨国文化地景中“重层而丰厚的面貌”。因此,我们有必要重返1920年代的历史现场,拨开历史迷雾,再次探寻以下一系列问题:台湾左翼思潮是如何产生的?它吸收了哪些方面的思想资源?台湾左翼思潮与大陆左翼思潮之间的关系如何?日本作为台湾左翼思潮的中转站,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与评价它的历史意义?苏联的左翼思想在台湾左翼思潮中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台湾左翼青年如何与东亚各国、殖民地青年连结、合作?台湾左翼思潮与在祖国大陆、日本以及整个东亚左翼思想交流与互动过程中,又是如何形塑与建构了东亚左翼知识圈?在思索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本文意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与整体性视野中论述1920年代台湾左翼思潮的兴起、发展及其知识圈的建构与交流互动。
一、台湾左翼思潮的三个来源
(一)大陆左翼思想的传播与影响
1.文化启蒙之旨趣
关于日据时期台湾左翼思潮的起源,台湾学者陈芳明认为有两个途径,一是留日台湾青年学生的传播;二是祖国大陆新文学运动的影响。[4]《台湾社会运动史》亦记录了左翼思想进入台湾的两个主要途径:其一为东京留学生在东京与共产主义者交往并受其影响者,其二为就学祖国大陆的台湾学生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影响与吸收。[5]但这种看法明显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留日的台湾知识青年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心仪其实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在日本留学的台湾青年知识分子深受触动。 1919年秋,蔡惠如、林呈禄、蔡培火等人联络大陆留学生马伯援、吴有容等人,成立“应声会”。 1920年1 月,蔡惠如组织成立“新民会”,以取代组织涣散的“应声会”,林献堂、蔡惠如分别担任正、副会长,于1920年7月16日创办了“新民会”刊物《台湾青年》。无论是“应声会”“新民会”还是《台湾青年》,在命名上明显蕴涵着与五四运动遥相呼应的深刻意味。最初传播左翼思想的《台湾青年》不仅在命名上与《新青年》相呼应,而且在创刊理念上,也与五四新文化精神高度一致,这些新知新觉的台湾知识青年显然把自己的文化活动视为五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从其发刊词就可以看出,发表在《台湾青年》创刊号的《发刊之旨趣》如是而言:“国民之荣辱,不在乎国力之强弱,而在乎文化程度之高低”[6]。同期刊登的陈炘《文学与职务》一文直接把“启发文化、振兴民族”视为文学的责任,主张文学“当以传播文明思想,警醒愚蒙,鼓吹人道之感情,促社会之革新为己任”,“励行其职务,以打破陋习,击醒惰民,面就今日之文明思想,以为百般革新之先导,为急务也。”[7]不言而喻,文化启蒙构成了《台湾青年》的基本主题。在祖国大陆就学的学生团体由于受到环境的影响,即使“标榜民族主义,乃至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或反帝国主义斗争,但视其运动的实绩,不如说在这些斗争目标下所扮演的是启蒙的角色较为恰当”[8]。台湾的“文化发展时日尚浅,大多数的民众还未脱离蒙昧无知的境界,欧美从企图发展以近代思想为背景的社会运动,作为其前提的启蒙运动所具有的意义极为重大,其影响力亦恰是开拓处女地一般的强大。就是不论其为民族主义系统或共产主义系统,都以文化运动为先驱而发展。即使在具体化的各种政治、革命、劳动、农民运动方面,亦多带上启蒙运动的浓厚色彩。”[9]
2. 新文学运动的兴起
20世纪初,台湾青年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文学是文化启蒙的先锋,文学也必须承担启蒙的历史使命,所以文艺大众化是历史的大势所趋,是实践启蒙思想的重要途径。从1922年陈端明《日用文鼓吹论》到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黄朝琴《汉文改革论》,台湾文学界开始提倡白话文运动。《台湾青年》主要执笔者之一黄呈聪在1923年指出:“‘中国’就是我们的祖国,我们未受日本之前就构成‘中国’的一部分……若就文化而论,‘中国’是母我们是子,母子生活的关系情浓不待我多说”,“台湾统治的方针,要用日本固有的文化来同化我们的缘故,这岂不是我们社会不发达的原因么?”[10]他亲赴祖国大陆考察白话文普及情况,并依据胡适的研究,强力主张白话文的使命在于文化普及,让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人的价值而过文化生活,并达到国民团结的目的。黄朝琴也在《汉文改革论》一文中主张,文化普及多数大众是改良社会的基础,而使用白话文则是达成这个基础的基础。毋宁说《台湾青年》上刊载的文章讨论焦点是文字的改革与白话文的使用,不如说这些讨论事实上有效连结了新文化运动,成为台湾现代文学的先声。1923年开始,《台湾民报》完全改用白话文来发行,“这对于今后的文学运动,无论在创作方法,或者在阅读方面,都与了很大的方便”,还开设了“文艺”专栏,用于介绍鲁迅、胡适、郭沫若、冰心等中国新文学作家作品以及外国作品的翻译。
1924年,张我军在《台湾民报》上刊载胡适的《文学革命运动》,并且连续发表《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糟糕的台湾文学界》《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等犀利的评论直接批判台湾旧文学界,从而引起了新旧文学论争。张我军的论述对台湾新文学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一是对台湾文学的属性定位:“台湾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11]其二是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确立:“西洋自古典主义而浪漫主义而自然主义,到现在,自然主义的时运也已去了,所谓新理想主义、新现实主义,已布满了全世界的文坛……总之,现在的时代,无论什么都以世界为目标。我们不是好高骛远趋新弃旧之徒,人喜欢我也喜欢,人厌弃我也厌弃。但事实上像古典主义(如台湾现在的文学)之当废,已成为一个绝对的真理了,不容余喙的真理了,如地球是圆的,人是要死的一样的真理了。他们不但不能脱却旧文学的迷梦,踏入新文学的路上,简直懂得文学是什么的人,恐百中不能求一,(照这样结论起来,他们死守古典主义也是难怪的,老实说一句,他们或许不自知其是守在古典主义吧。)”[12]第三,是对台湾旧文学的尖锐批判,他把旧诗文视为“一种臭不可闻的恶哭”,指控其“陷害了不少活泼泼的青年”。第四,从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高度来提倡白话文运动,“依傍中国的国语来改造台湾的土话,换句话说,我们欲把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再换句话说,是把我们现在所用的话改成与中国语合致的。”[13]这种新文学语言观显然与胡适建设“国语的文学”精神相一致,而且张我军所倡导的包括白话文和诗体解放等主张在内的文学革命论也是对胡适新文学思想的直接继承。1925年,蔡孝干加入新旧文学的论争,在《中国新文学概观》一文中,他以中国新文学为例,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文艺”取代“为艺术而艺术”是一战后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必然结果,他甚至认为“为新社会的艺术”取代“为人生的艺术”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3. 三次历史性对话的影响
1907年、1913年与1926年,这三个关键时刻的历史性对话历来为人所津津乐道。第一次历史性对话是“林梁之会”:台湾青年林献堂与流亡日本的革命家梁启超之间的会面。1907年秋,林献堂在日本奈良旅店中巧遇梁启超,林献堂向梁启超请教了“台民如何争取自由”的严肃问题,此次会谈对林献堂日后的抗日策略与政治立场影响巨大。据叶荣钟回忆:“任公这一夕话极有分量,确实给与该运动的领袖人物灌老以重大而又切实的启示,无疑地也是发生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14]第二次是1913年,林献堂派遣秘书甘得中在东京会见戴季陶,再次请教台湾问题。除了“林梁之会”,台湾知识青年与大陆知识人、革命家在岛外的历史性邂逅,最常被提起的当属张我军与鲁迅的“北京之会”。1926年8月11日,张我军前往鲁迅北京寓所求教台湾问题。张我军请教道:“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太提到。”鲁迅则回答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时放下。”[15]鲁迅对台湾新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从1923年以后,《台湾民报》开始刊载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人作品,对台湾知识阶层、青年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鲁迅对台湾青年张秀哲有关台湾民族问题的请教,以及鲁迅声援张秀哲等人从事的广东革命青年团并为之作序,足见台湾青年当时受到如鲁迅等中国左翼人士的潜在影响。[16]此外,诸如郭沫若等旅日左翼作家亦从理念上对台湾左翼青年进行了指导,对台湾岛内的左翼思想文化运动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4. 台湾青年在祖国大陆的思想运动
在祖国大陆各地就学的台湾青年受到当时革命热潮的影响,也开始投入台湾解放运动,尤其是在上海、北京、广东和闽南地区的台湾青年,更意识到民族解放及共产主义革命的迫切性。随着台湾人民的民族觉醒,台湾青年赴大陆就学的学生数目有遽增趋势,1921年前后台湾到厦门游学的人数已达195人之多,1922年在北京就学的台湾青年就有32人,在上海的台湾青年亦有数十人之多。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左翼运动更为蓬勃。1920年代上海大学汇集了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等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通过创办平民学校与工人夜校,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一个平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乃至中国的传播。[17]上海大学的台湾学生如蔡孝干、翁泽生、谢雪红、林木顺等日后皆成为台湾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据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的史料记载,台湾青年学生在中国大陆的思想运动主要有蔡惠如等的民族自决运动、上海台湾青年的各种运动、北京台湾青年的各种运动、闽南地区的学生运动以及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的运动等。上海台湾青年成立的团体组织主要有上海留学生的台湾青年会、台湾自治协会、平社、台韩同志会、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和读书会等,它们大多转变为以共产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学生联合会的形态。
(二)“前进东京”:日本作为台湾左翼思想的中转站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为亚洲各国取法的对象,各国纷纷派遣留学生前往取经,学习西方近代知识、军事、典章、制度与思想,尤其是东京更成为了当时西方知识、思想交流传播的重要窗口。1918年以降,欧洲思想界被高扬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左翼思想所风靡,日本亦成为了左翼思想资源的中转站。日本尤其是东京,在当时台湾的文学创作中被形象化为进步的、年轻纯洁的革命烽火之城。台湾革命青年往往标举“前进东京”以寻求“革命的烽火”的大旗,他们对日本左翼充满信赖与憧憬。无论是谢春木的“前进东京”的影子,还是杨逵式追求台湾左翼运动与日本左翼运动结成联合战线的前进形态,还是龙瑛宗向往台日学者跨越不平等的平等交流的前进形态,东京的存在“仿佛都先验性地提供了一个困境脱出之道”[18]。“前进东京”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自我的解救,这并非仅仅台湾知识分子单方朝向日本左翼所勾勒的世界倾斜,也是觉醒的知识分子在破茧而出之后犹如“精灵的蝴蝶”般选择自己的去向。
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台湾中高等教育体系匮乏、教育机会不均等,加之时代潮流的刺激,台湾青年赴岛外的留学教育日渐蓬勃。尽管也有赴欧美、祖国大陆的青年,但是因为语言、殖民体制之便,赴日升学的人数远多于其他地区。据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记载:台湾上流阶级将子弟送至日本留学的风气始于1901年左右,而且数量逐年递增,日本还于1907年左右专门设立了东京府辖内的留学生指导监督。1908年,台湾在东京的留学生为六十名之多,至1915年,台湾留学生总数已达三百余名,1922年则激增至二千四百余名。[19]正是台湾留学生在日本的大量集结,促使他们逐渐“以批判的眼光来看事物的态度”,“酿成了唤醒民族意识、集合团结提高台湾人地位,谋求其自由和解放的运动趋势”。[20]大正时期的日本东京作为知识传播中心,吸引了亚洲各国青年前往取经,也提供了反帝、反殖民人士经验交换与组织集结的机会。在前赴后继的旅日浪潮之中,1920年代或因留学或因工作先后赴日的台湾青年主要有谢春木、王白渊、陈来旺、林添进、林兑、陈在葵、陈植棋、苏维霖、赖富贵、张文环、吴坤煌、巫永福、吴天赏、刘捷、翁闹、何德旺等人。诚如谢春木“在他热切投入文协诸运动的时候,他所扮演的正是把文明与改革的火种从东京输往故乡,同时把故乡的改革请愿传达到东京的中介性角色。”[21]“对他来说,东京更重要的意味或许是,它是在他青春岁月中扬起波澜的台湾民族运动的前线。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在谢的认知中,东京的‘进步’之所以对他有意义,那是因为它具有文化启蒙(启蒙台湾)、社会改造(改造台湾)、甚至是反殖民(解救台湾)的效能。”[22]随着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加深,他逐渐意识到了“前进东京”的局限,因此1925年诀别东京,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分水岭。他意识到,革命的火种“期待于东京但不尽于东京”,他不眷恋东京,“经验东京”之后,他的思想、行动所产生的蜕变显示了东京作为其工具性的角色与阶段性的场所之作用。
1919年,在林献堂、蔡惠如等先驱的统帅下,留学日本的台湾青年学生结成团体并开启了实践运动的途径——“新民会”:“表面所揭示的纲领是‘专门研讨台湾所有的应革新事项以图提升其文化’为目的,但实践则依据民族自决主义立场,进行岛民启蒙运动,同时以合法的谋求民权的伸张为主要工作。”[23]1920年以留学日本为主的青年知识分子组织“台湾青年会”,创办《台湾青年》,最早开始介绍社会主义理论与思潮。“自东京台湾青年会的活动开展以后,东京留学生对社会问题,思想运动的关心明显地升高了。不单止于民族自决主义的主张,更受到当时发展期的刺激,或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或信奉共产主义等人士辈出,以致台湾青年会内部也渐次产生思想上的对立,随之而有了和青年会站在不同立场,组成各种团体的倾向。”[24]中山启的《生物学上之爱国者与危险思想家》和蔡铁生的《论中国将来之兴亡》等文章已经触及“社会主义”概念,隐约意识到社会主义思潮对中日两国社会的影响。1921年5月,彭华英在《台湾青年》二卷四号发表《社会主义の概说》一文,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概括介绍“社会主义”。此后《台湾青年》、《台湾》(1922)持续深入引介“社会主义”:蔡复春的《阶级斗争の研究》对左翼阶级斗争理论的集中阐述;蔡以信的《战后思潮の倾向》则从一战后思潮的变迁背景出发介绍世界左翼思想的兴起;许乃昌的文章《台湾议会の无产阶级》第一次建立了台湾社会观察的左翼思想视域。1923年创刊的《台湾民报》的左翼色彩更为浓厚,不仅全面介绍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还从阶级理论和唯物史观出发讨论农民运动、妇女解放和殖民地解放运动,初步建立了左翼的知识启蒙立场。以许乃昌、商满生、高天成等为首的台湾留学生定期聚会,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进而实践共产主义的行动倾向。1923年以后,共产主义思想在东京思想界已经明显地抬头,掀起了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潮。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则深受影响,逐渐兴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的社会科学热潮,致使台湾青年会内部产生了分化与对立,左翼逐渐成为主流。尤其是台湾共产党东京特别支部的成立,对台湾左翼运动的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三)苏联左翼思想的导入与影响
尽管台湾左翼思想的导入源自祖国大陆和日本,但是苏联以及“第三国际”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来源。左翼理论传入台湾的路径有二:一、苏联—中国大陆—台湾;二、苏联—日本—台湾。这两个路径都共同指向了一个源头:苏联。因此,苏联以及第三国际的左翼思想对台湾左翼的影响是一个值得发掘的重要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三国际”以实际行动支援各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潮蓬勃开展也激励了台湾青年知识分子。台湾知识分子受到俄国革命的鼓舞,向往通过马克思主义来“走俄国人的路”。
王白渊在《我的回忆录》说:“俄国有一种传说,说‘俄国有一个地方的山野,至深秋青叶落尽的时候,不知从何处漂来一种难说的花香,但是这‘妖魔之花’的本体。是不容易看到的。但是不幸一见到。那人就要发狂了!这是俄国帝制时代的传说,我觉得很有带着人生的深意……俄国青年好像发狂一样向着革命前进。我想这班青年都是不幸看着这‘妖魔之花’的人。”[25]“妖魔之花”正是共产主义思想的隐喻。当时苏联专门开办了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全称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台湾的许乃昌曾于1924年8月到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大学研究共产主义运动;林木顺、谢雪红夫妇因在上海抗日示威游行表现活跃而受到共产国际东方局的注意,被吸收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就读,同时安排两人赴莫斯科深造。林木顺进入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谢雪红则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7年9月,两人完成训练离开莫斯科,返回上海。他们“经由翁泽生的安排,集合了台湾学生联合会的左倾分子江水得、杨金泉、林松水、刘守鸿、张茂良、陈粗皮、陈氏美玉、黄和气等人,以‘研究社会科学,学习中国语’为表面理由,实则进行台湾共产党组党的准备行动,从事党员的养成及训练工作。”[26]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法国租界区内秘密举行建党大会。从一系列的史料可以发现,台湾左翼青年已直接连结苏联并取得了左翼思想的国际火种,并在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指导与声援下成立了台湾支部。
二、左翼的流动及东亚左翼知识圈的建构与互动
台湾左翼运动并非是孤立的,它不仅是中国左翼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东亚左翼运动乃至整个世界左翼运动的重要一环。
(一)台湾左翼运动是中国左翼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左翼运动作为中国左翼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将其置于祖国大陆左翼运动的整体性视野中加以考察,才能更好地理解祖国大陆左翼思潮与台湾左翼思潮之间的复杂历史脉动。祖国大陆对于台湾左翼青年而言,远非只是一个地域的概念, 更是他们生存与活动其间的一个社会环境、一种文化环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掀起的民族自决声浪,对台湾产生了非比寻常的影响。以蔡惠如为代表的台湾民族自决运动者早在1920年就以演讲报告,抨击日本殖民台湾后的统治手段。他联络并参加林献堂协商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运动后又赴祖国大陆,游历了北京、天津、上海、广东,与各地的台湾青年会面,报告东京的运动经过,并鼓励他们奋起响应,分发《台湾青年》杂志。蔡惠如、林呈禄、彭华英等人与在上海的印度、朝鲜、菲律宾等地的民族运动人士聚集开会,或列席太平洋和会、太平洋会议研究会等会议,商讨反抗殖民统治运动。以台湾青年学生为中心,以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为诉求的各种运动,迅速高昂地推展开来,以致各地以启蒙为目的的各种团体也层出不穷。[27]诸如1919年末,以马伯援、吴有容、刘木琳为代表的中华青年会与台湾的的林呈禄、蔡培火、蔡惠如等人协议成立了“声应会”。尽管“声应会”在创立后未及推行预期活动便已离散,但是它与祖国大陆的思想团体保持着密切联系,致力于指导台湾青年的思想,深刻地支配着青年学生的意识。1922年1月,旅居北京的台湾青年创立了北京台湾青年会,并且聘请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为名誉会员。其后,上海、厦门、广东等地的台湾籍学生也相继在各地成立青年会、学生联合会,有力地推动与支持了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
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上海,已经成为了“台湾爱国青年反日活动的大舞台”。[28]一大批台湾爱国青年在上海学习祖国文化,并参与祖国大陆风起云涌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实践,这既促使他们成长为一代革命者,也使祖国大陆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增添了丰富内容。“上海大学”尽管只创办五个年头,但是它为培养台湾左翼青年做出过特殊贡献。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和社会学系主任,他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台籍爱国青年。如前所述,翁泽生、谢雪红、林木顺、蔡孝乾、庄泗川、李晓峰、洪朝宗等一批台湾爱国青年都曾在“上海大学”学习并开展左翼运动。1925年12月20日,由翁泽生、洪朝宗、蔡孝乾等人发起的“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在法租界的南光中学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台湾学生达100多人。而1928年台湾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则标志着台湾人民的反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台湾左翼青年在祖国大陆学习与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实践,既锤炼了他们的革命才干与思想水平,亦使他们能够自觉地将台湾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在祖国大陆已经积累丰富左翼斗争实践的青年返回家乡,则有力地推动了台湾地区左翼运动的发展。
(二)台湾左翼运动是东亚乃至世界左翼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左翼思潮亦与亚洲思想运动同步,它紧扣1920年代东亚局势的发展,只有将其置于东亚左翼运动的整体性框架下加以探究,我们才能进一步把握台湾左翼思潮的形成与历史位置,亦有助于我们理解台湾左翼青年从事左翼文化运动的跨域路径,以及东亚左翼知识圈的建构与互动等问题。诚如柳书琴所言:“日治时期的台湾左翼运动,与东亚左翼运动共同生成,它具有与东亚左翼运动结盟、具体掌握台湾农工问题症结和殖民地社会实况的特征。”[29]在这样的视野观照中,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台湾左翼知识青年从“台北—上海—东京”的跨域文化场域的转换与连结,进一步探究旅居东京的台湾左翼青年如何凭藉殖民地作家身份,进入日本左翼文化界并连结海峡两岸、朝鲜的左翼人士,共同建造东亚跨域的左翼文艺网络,并在其中以多角结盟的游击战略为台湾文艺界争取到国际左翼资源。
台湾学者柳书琴的《荆棘之道:台湾旅日青年的文学活动与文化抗争》一书对我们深化1920-1930年代台湾左翼运动的认识大有助益。1921年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为旅日的台湾青年与日本、祖国大陆左翼人士的具体交流提供了平台,也为台湾左翼青年作家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提供了契机。中、日左翼文学交流自1920年中后期已渐具规模,而1930年代中、日政府压制左派运动进一步加速了弱者的跨域联合。文联东京支部与左联东京支盟的交流,构筑了台湾文坛、旅日祖国大陆左翼文学者以及东京左翼诗坛之间的多边互动。随后,以东京支部为接触舞台,以作品投稿为途径,吴坤煌、雷石榆二人的交流,开启了祖国大陆旅日左翼作家与他们所陌生的台湾文坛一段难得的接触。台湾左翼青年与祖国大陆、日本左翼文学者之间的跨域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台湾文艺》的关键性人物张深切在《“台湾文艺”的使命》一文中充满期待地勾勒了台湾文艺运动的新蓝图:“《台湾文艺》自出版以来,得诸同志们的鼎力,逐号内容充实,嘉义支部的奋斗,东京支部的努力,台湾支部的组织活动等等,咱们的工作时时刻刻在扩大化,最近上海又决定组织支部,以王白渊、张庆璋、张芳洲诸同志为中心,在进行活活泼泼地活跃,台南方面也开始着手组织支部,厦门方面已有几位同志来函要求本部准许设置支部,咱们的工作渐由文墨运动而进展于行动运动了。”[30]从台湾到东京再到上海,不难发现台湾左翼青年们“尽管边缘但却富含国际精神的诗性抵抗路线”。事实上,台湾与祖国大陆、日本三地已经在交通渠道、人员流动、组织团体结盟等方面构筑起了“留学走廊”与“政治走廊”,进而催生了三地互通的“文化走廊”。柳书琴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文化走廊与政治、留学走廊共生”。旅日台湾青年透过与祖国大陆、日本、朝鲜的文学团体或左翼组织的结合,开启了台湾文学史上罕见的跨域活动。“尽管这些互动并不广阔频繁,没有共同组织或固定活动,严格来说只不过是旅日青年以私人人际构联的一个不甚稳定的交流网络。但是在这样的文学网络中,却闪烁了旅日文学菁英跨域文学运动的思维……台湾旅日作家不仅与日本左翼文化运动人士进行交流,也进一步与祖国大陆左翼文化人士,乃至朝鲜、伪满洲国作家有所接触。”事实上,“令人炫目的不只是这些交流本身,亦是隐藏在这些互动背后,坚守理想、勉力为之的价值视野和行动模式,流露的野心和远见。”[31]或许,左翼思想的涓涓细流已经开始渗透于台湾左翼知识人士的精神结构之中并化为实践运动的动能。
事实上,在柳书琴的“台湾旅日青年的文学活动与文化抗争”的论述视域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即“旅台日本左翼人士所进行的左翼思想传播与艺文活动”。据载,1929年台湾地区的日本人已超过20万,而且他们掌握着绝大多数的资源与资本。尤其是1928年“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建立,促使了1920年代末期至1930年代初期日本左翼运动达到了高峰,也使得台湾地区的日本左翼人士建立起了自己的左翼文化团体,而且这些具有左翼倾向的团体对其后台湾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开展具有奠基性的影响。例如,以藤原泉三郎、上清哉等人为核心的日本左翼文学青年在台湾地区发行同人杂志《无轨道时代》,同时计划在台湾地区设立战旗社的台湾分社并举行《战旗》读书会。1931年6月31日,台湾地区的左翼文学青年重新集结起来,成立了“台湾文艺作家协会”。“台湾文艺作家协会”以日本帝国大学经济部出身的左翼青年井手薰以及《无轨道时代》的同人上清哉、藤原千三郎等为中心,创立时会员共39名,其中日本左翼人士29人,台湾地区左翼人士10人。[32]不言而喻,台湾地区的日本左翼人士推动左翼思想在台湾地区的盛行功不可没。
此外,台湾与日本之间的左翼戏剧的传播与交流亦是这一时期左翼运动跨域交流的重要领域。1920年代,台湾现代戏剧运动风起云涌,陆续出现了许多新剧团与新剧作品,目的都在于进行社会改造运动与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剧场艺术的先驱们明显具有社会主义倾向,他们大多是参加过左翼组织或无政府主义的留日知识分子。日本的左翼剧场、筑地小剧场、新筑地剧团等剧场和戏剧团体所从事的无产阶级演剧活动,对台湾现代戏剧的创作与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张维贤、简国贤先后进入东京“筑地小剧场”学习戏剧,张深切、杨逵在日本参与戏剧活动,林搏秋也曾受过东京“新磨坊剧团”磨练并学习了电影制作。[33]左翼戏剧作为一种激进的艺术形式,它传递给观众一种反叛与颠覆的思想观念,台湾左翼知识分子寄望以新剧所展现的剧场活力抗争日本殖民统治。左翼戏剧作为左翼思想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利器之一,它推动了现代戏剧向着无产阶级戏剧运动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增进了与日本左翼文化的跨域互动。
在持续进展的祖国大陆、日本以及整个东亚甚或第三国际的左翼文学、文化交流中,台湾左翼思潮从一开始便种下了与这个网络接轨的契机,从而开启了台湾左翼文化运动的跨域路径。“以东京台湾留学生为中心的东京台湾人知识阶级,随着时代潮流而起的风气的变迁,必然招致具有相同民族渊源和风俗习惯的祖国大陆留学生及知识阶级的接近,并招来具有相同境遇的朝鲜人与他们汇合的倾向。”[34]因此,台湾左翼青年与东亚各国各区域、尤其是殖民地青年连结与合作的战略是:尽可能扩大联合对象,左派走国际主义路线,与日本、朝鲜、菲律宾、印度等亚洲各国人士互动,更与朝鲜、祖国大陆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携手组织团体;右派也与朝鲜人合作办刊物、相互声援。蔡培火、林呈禄等人与朝鲜人的若干团体保持密切关系,对“亚细亚公论社”频繁地投稿,以及在郑泰玉所主持的《青年朝鲜》上屡次发表意见。根据已有的史料可以发现,事实上1920年代的反殖民运动中的左翼跨域合作情形已超乎想象。而左翼思想的流动以及跨域互动,则为东亚区域左翼思潮与运动实践的结盟奠定了基础,同时,东亚区域左翼思想的形成与互动,亦有效建构了“东京—上海—台北”左翼知识圈及其互动。
注释:
[1] 曾天富在《日据时期台湾左翼文学研究》一书中从形成期(1920-1926)、定著期(1927-1932)、深化期(1933-1936)、萎缩期(1937-1944)四个时期考察台湾左翼文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其与左翼社会运动之间的消长关系。见曾天富:《日据时期台湾左翼文学研究》,韩国:世宗出版社,2000年。
[2][3][4] 陈芳明:《左翼台湾——殖民地文学运动史论》,台北:麦田出版社,1998年,第15,31,15页。
[5][26] 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员会:《台湾社会运动史·共产主义运动》第三册,王乃信译,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6年,第1,8-9页。
[6] 台湾青年编委会:《发刊之旨趣》,《台湾青年》一卷一号,1920年7月16日。
[7] 陈 炘:《文学与职务》,《台湾青年》一卷一号,1920年7月16日。
[8][9][19][20][23][24][27][32] [34] 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员会:《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第一册,王乃信译,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6年,第1,2, 18-19,19,20,31,82,408-409,19页。
[10] 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台湾》四卷一号,1923年 1月 1日, 第12页。
[11] 张我军:《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台湾民报》1925年1月1日。
[12] 张我军:《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台湾民报》2卷24号,1924年11月24日。
[13] 张我军:《新文学运动的意义》,《台湾民报》第67号,1925 年8 月26日。
[14] 叶荣钟:《林献堂与梁启超》,《叶荣钟全集》第2卷,台中:晨星出版公司,2000年8月,第199-203页。
[15] 鲁 迅:《写在“劳动问题”之前》,《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4页。
[16][18][21][22][29][31] 柳书琴:《荆棘之道:台湾旅日青年的文学活动与文化抗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145-147,30,40,46,385-386,295-296页。
[17] 王家贵、蔡锡瑶:《上海大学:1922—1927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8页。
[25] 王白渊:《我的回忆录》,《政经报》1卷2号,1945年11月10日,第17页。
[28] 何 池:《1920至1930年代的上海——台湾爱国青年反日活动的大舞台》,《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年9月。
[30] 张深切:《〈台湾文艺〉的使命》,《台湾文艺》2卷5号,1935年5月5日,第19页。
[33] 参见石光生:《跨文化剧场:传播与诠释》,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9月,第25页。
2017-05-3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台湾左翼文艺思潮与创作研究”(12BZW088)
孔苏颜, 女, 山东济宁人, 福建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刘小新, 男, 两岸协创中心福建师范大学两岸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文学博士。
与东亚左翼知识圈的互动
I206.6
A
1002-3321(2017)05-0026-07
[责任编辑:陈未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