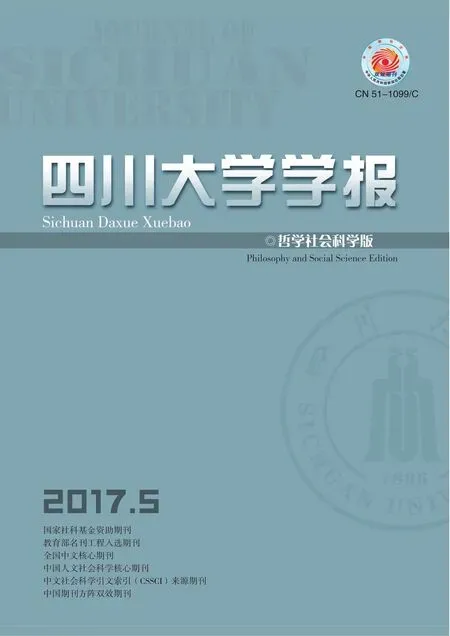儒学现代价值新反思
——基于竞争与相对进步观念的研究
§儒学争鸣§
儒学现代价值新反思
——基于竞争与相对进步观念的研究
邓曦泽
人类各大文明都有过愚昧、野蛮时期,但唯有西方发展出了更高级的形态。以此为基本背景,基于竞争视角,并运用程度区分法与相对价值法,可以发现:儒家虽然在中国古代发挥过巨大正面作用,但在涵盖社会生活的五个基本方面都远远落后于现代文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毫无价值,它可作为道德儒学和心灵儒学而发挥作用。
儒学;竞争;程度区分法;相对价值法;道德儒学;心灵儒学
引言:当前文化思潮提出的问题
近年来,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境遇日佳,似乎形成文化复兴小潮流。前些年,笔者也曾专力论证传统文化尚有巨大价值。但是,近几年来,笔者越来越怀疑:儒家究竟是否还有价值?它又应否复兴?能否复兴?笔者的答案越来越倾向于否定。其实,在根本上,这种否定不是对儒家的否定,而是对我自己过去的立场、观点和思考的否定。一个真正的思想者和学者,不应立场优先,尤其是不应固守立场,把学术作为立场的注脚,而应理智优先,遵循学术和真理本身的逻辑。如果学术和真理的推进推翻了原来的立场和观点,则应追随或引领学术和真理本身。
一、问题反思、研究方法与判断标准
(一)问题反思
关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价值,笔者曾有长期和专门的研究,主要包括对既有文化复兴方案的批判(《现代古典学批判》)和提出自己的文化复兴方案(《文化复兴论》)。*邓曦泽:《现代古典学批判——以“中国哲学”为中心》,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邓曦泽:《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的进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前者是批判,写作在先,但出版在后。《文化复兴论》从公共交往视角论证了两大基本观点:第一,任何国家、民族都需要一个基础的公共交往平台,而传统文化就是这个基础公共交往平台的重要构成。第二,儒学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正是作为中华民族的思想共源和公共交往平台,在现代社会,儒家通过损益,能够继续作为思想共源和公共交往平台,因而能够复兴。
但后来(始于2010年),我发现上述论证存在逻辑问题。因为,上面的第一点,只是一般地论证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我迄今仍然坚持。但是,由之无法逻辑有效地得出第二点。在语义上,“重要”不等于“好”。从传统文化很重要这一命题和一般规律,能够得出一个必然命题(并且是价值命题):我们应该改革传统文化,使之成为更好的公共交往平台,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公共交往。传统文化很重要,是说它是影响社会状况的重要变量,但不能由此得出某种具体的传统文化(如儒家、道家、法家、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此相当于变量的具体赋值)是好还是坏。同时,虽然《文化复兴论》下篇论证了:在历史上,儒家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共源和公共交往平台,但由此命题推不出儒学必然是或永远是。这意味着,儒学在现代社会究竟还有无价值,又应否和能否复兴,就需重新考察。
(二)研究视角与方法
竞争是本文的基本视角,本文的研究方法便来自竞争原理。*邓曦泽:《劣向选择成本——论竞争原理及其解释力》,《中山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可以说,没有《劣向选择成本》的竞争原理,就没有本文。反效用最大化不可能、效用最大化是本土观念、负价值,均来自该文。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详细阐释。另,本文系基于笔者以前一系列研究的再研究,故自引较多。独特的研究方法是本文最大的创新,也是把握儒家价值的关键。本文在文献上毫无新意,如果没有新的研究方法,则本文只能陷入重复研究,毫无价值。
人类甚至生物界,一直都在进行竞争。虽然中国古代总是强调和(和谐),而不主张争(竞争),但这只是表面。其实,古人是希望用和谐来弱化竞争,但这种希望本身就表明了竞争的客观存在。在现代社会,竞争则是公开、明确和有序的,其有序表现为将法治作为竞争的公共平台。竞争意味着追求效用最大化。效用最大化是普适原则,也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甚至是动物行为的基本原则,而反效用最大化是不可能的。同时,效用最大化也是中国本有的观念。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新方法不断产生,所以,很难说某种方法就是完美的,一种方法的优劣总是相对的。基于竞争视角,衍生出两种方法:
第一,相对价值法。一个事物的价值取决于它与其他同类事物价值的竞争状况。也就是说,一个事物的价值乃是它的相对价值或比较价值。这个命题不但是对价值的定义,并且可以作为一个推理规则,此规则是基础规则。如果选项B比选项A更能实现行为者的目标,行为者显然会选择B。在A与B之间选择,就是A与B竞争,胜出者被采用。这意味着,高级的东西(产品、知识、工具、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等)可以让低级的东西衰落,甚至报废。这又意味着,一个通常看起来是正价值的事物可能沦为负价值。简要论证如下:在竞争中,对于一个问题,如果有两种方案A与B,其价值关系为:0 第二,程度区分法。从相对价值法可以衍生出程度区分法。一个事物对解决问题的价值即有效性程度(x)可以在-100%和100%之间,即-100%≤x≤100%。负值就是负效果。程度区分法比二分法(有用无用)更能有效地衡量事物的价值,明晰不同事物之间的优劣及比较优势,并有助于推动事物的有限进步,避免完美主义倾向。 基于这两个方法,才能且就能更客观、科学地理解和评价儒家。如果方法错了,理解和评价就一定不客观和科学。根据该二方法,可以建立0 上述方法适用于一切基于竞争的优劣的比较和分析。 (三)判断标准 即便有了科学的研究方法,而无科学的判断标准,仍然无法判断儒家的价值。本文以五个基本方面来判断一种文化的价值:知识生产与创新;社会治理手段;公共交往与社会治理效率;社会秩序;教育与人格塑造。这五大方面显然很重要,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相应地,由这五大方面延伸的具体判断标准为:在知识生产与创新方面,越鼓励知识生产和创新的文化,越有价值;反之,则越无价值(其余几方面,同理)。本来,这个价值谱系是可以论证的,但这里无法详细讨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同这个价值谱系。 研究方法与判断标准不是一回事。本文的两个研究方法是普适的、非历史的,凡要判断优劣,都适用。但是,判断标准则不能一般地说是普适的,而是历史的。文艺复兴之前,人类并未形成上述价值标准。或许再过几百年,这些标准也会有所调整。虽然这个价值谱系也有不足,但人类尚未找到比之更优的价值谱系。本文的判断标准即上述价值谱系是现代标准而非西方标准。因为,虽然这些现代标准(或现代性)产生于西方,但西方并非天然是现代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原祖杰:《东方与西方,还是传统与现代?——论“东西方”两分法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误区》,《文史哲》2015年第6期。 此外,(1)本文涉及中西比较,这种比较无所谓时间对称,因为两种文化进行比较/竞争,是拿各自最优秀的文化相比较,而不是一定要拿同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相比较。(2)每个理论体系都有其核心观念和次要观念,每个理论的支流学派都必须承认其核心观念。评论一种学说,评论其核心观念是最有效的。本文针对的便是儒家的核心观念即最大公约数(的一部分)。罗素对基督教的批评也采取了这种做法,而未考虑基督教内部各支流学派的差异。*罗素:《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沈海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下面,本文从五大方面论证儒家的缺陷。 (一)知识生产和创新方面:儒家鼓励因循守旧,不鼓励创新 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是知识生产。知识被生产,决定用知识去生产。任何个体只有先掌握一定的知识,才能用知识去生产。行为者掌握什么样的知识,决定了他有什么样的计划性以及相应的实现手段。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生产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邓曦泽:《发现理论还是验证理论——现代科学视域下历史研究的困境及出路》,《学术月刊》2013年第4期;邓曦泽:《冲突与协调——以春秋战争与会盟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8-23页。 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前,世界几大文明的知识生产方式和水平大体都处于同一水平。甚至,如李约瑟的看法,中国的许多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个时期,不能说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生产是落后的。 但是,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彻底改变了几大文明在知识生产方面的均势,西方在知识生产方面远远领先于其他文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明所遭遇挑战的本质,是以现代科学为代表的西方先进知识生产方式对中华文明落后知识生产方式的挑战。*邓曦泽:《中华文明的断裂与赓续——基于知识生产的视角》,《江海学刊》2014年第6期。关于中国知识生产落后的原因,本文只强调一点:在文化层面,以儒学为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根本不鼓励知识生产与创新,而是鼓励因循守旧。儒家在知识生产上的问题不是它没有和不能生产许多具体知识,而是它对知识的态度即价值导向不当。这种价值导向是二阶(second-order)的,即它不是具体地做x,而是鼓励或反对做x。 儒学的圣人观念与经典观念,是知识进步的巨大障碍。因为,儒学认为(尤其是在儒术独尊以后),圣人和经典代表着不可超越、永恒不变的真理(绝对真理)。儒学认为,对道(作为真理的代名词)的探索、理解和表述,已经是完成了的,并体现在特定的人(圣人)身上,而圣人对道的探索与获得表现为他的言论。出于流传(传道)的方便,圣人的言论最终由圣人本人书写或他人记录而形成书面语言,亦即经典。儒家的道、圣人、经典与生活这四者之间的关系,被刘勰相当准确地概括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文心雕龙·原道》)。因此,经典=圣人思想=道=应然的生活。而圣人之外的其他人,即便刘向、班固、郑玄、孔颖达、朱熹这样的大学者,所能做的工作,也只是去理解、解释、阐发和传播经典(即圣人之言,亦即道),论证经典确确实实是永远正确的。这种研究属于典型的文本研究。即便被后世称为圣人的孔子,他也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中庸》也说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意味着,孔子本人就已经认为,道已经完成了,他所能做的工作,只是整理文献(如删诗书定礼乐)、解释文献(如作《易》传)和传播文献(开门授学)。而后来的学者几乎完全停留于解释经典,并有“注不离经,疏不破注”这样的学术教条。无论是孔子的述而不作观念,还是后世学者的经典解释观念,都远离于知识创新,更没有人敢宣称他能超越圣人和经典。而这种情况到后来就变成了,没有人试图超越历史上的圣人和经典。于是,知识进步变得极其艰难。即便有些微进步,也只是在不违背经典的条件下做细小修补,而较大的知识创新几乎是不可能的。儒学喜欢告诉人们如何做,而不重视论证,从来没有形成对概念精确性和对论证严格性的要求,反而把论证视作喋喋不休、低级、不切心性的东西。 儒学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缺陷,不在于它的错误,而在于它的低级。正确与错误,跟高级与低级,不是同一序列的概念。正确的未必是高级的,错误的未必是低级的(低级、高级是中性词,是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如低等动物和高等动物之区分)。传统文化中有许多观点也是对的,但是,即便这些观点正确,也是低级的正确。因为这些观点非常缺乏论证,起点就是终点,前提就是结论,即从A到A。譬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诸如此类起点就是终点的毫无论证的断言,在《论语》及中国传统著作中比比皆是。不要说与西方现代文明相比,即便与古希腊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也是非常缺乏论证的。这导致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非常缺乏讲道理或讲论证的自觉意识,也非常缺乏讲道理或讲论证的能力(人类文明积累的论证方式、能力和水平,在不断发展、提高)。 不可否认,古代那些被称为圣贤的人的确获得了部分真理,对改善当时人民生活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若把圣人视作真理的化身,把经典视作真理的终结,那就大错特错了,而这种观念势必沦为知识进步与创新的桎梏,成为真理的牢笼。凡是认为某种具体思想、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的观念,都是反科学、反知识进步和反知识创新的;同时,凡是认为存在圣人、上帝观念的知识观念,也都是反科学、反知识进步和反知识创新的——概言之,反智主义。因为这些观念都否定了超越经典(经典代表圣人和上帝的旨意)的可能性。五四以来,儒学也号称它主张科学,甚至浪漫地认为可以从儒学发展出科学,但直至今天,许多儒家学者仍然在主观上不重视论证,在客观上很不善于论证,甚至抵制论证,其抵制理由与古代完全相同。由此可见,儒学关于知识生产与创新以及关于真理的观念,与科学完全对立,势必成为科学的敌人,阻碍科学发展。 也不可否认,西方也有把经典当作绝对真理的历史(如中世纪把亚里士多德和《圣经》视作绝对真理),也打压学术创新尤其是打压近代科学。*罗素:《宗教与科学》,徐奕春、林国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5、19、131页。中世纪的学者也跟中国古代儒家学者一样,其任务就是进行文本研究(或经典诠释),论证经典的确是永远正确的。但是,西方走出了这段历史,并在文艺复兴时期以伽利略开创近代科学为标志,进入了知识大创造时期,迄今仍远远领先于其他文明。比较文化之间的优劣,关键不是比较谁更低劣,而是比较谁更优秀。中西文化都有很低劣的东西(即双方都在某个时期有A状态),区别在于,西方发展出了更优秀的文化(B状态,B优于A),而中国没有。如果中国仍停留在自己的传统中,那么,它不是获得了价值A,而是损失了价值P(B与A的差)。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异军突起,中国文化的确也是不错的,几大文明大体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没有谁有明显优势(都是A)。但是,当西方文化发展得更为优秀后(成为B),它在文化竞争(及广义的文明竞争)中就占有优势,其他文明就不可避免地因要支付竞争成本(P)而处于劣势。 小结:中国与西方最根本和最大的差异都在于知识生产方式不同,西方发展出了现代科学这种知识生产方式,而中国没有(关于此点,学界讨论较少)。中西知识生产方式之差异和差距,衍生出其他种种差异和差距。这一部分采取的论证方法,下文还会重复使用。 (二)社会治理方面:儒家崇尚人治和专制,反对法治与民主 如何才能有效地管理一个社会或国家?这是古今中外的政治与政治学的重大问题,而中国古代学术最核心和最直接的问题正是如何治理国家,此如司马谈所言:“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 那么,中国古代的治国方案(尤其是儒学)是否有效?这里的回答是:在现代法治模式产生之前,中国古代的人治模式也是比较有效的。但有了法治模式后,人治模式就是无效的,甚至是负效的。 本文首先强调的是法治,其次才是民主。因为,(1)唯有法治才能实现长久的和平交往。*邓曦泽:《论和平函数与和平系数——关于和平程度的计算法》,《江海学刊》2012年第5期。人治也有一定的规则,也能实现一定程度的和平,但只有法治才能实现长久的和平。而在历史实践中,法治产生的效果远比人治好。(2)如果民主不基于法治,就会沦为民粹民主,走向自身的对立面,沦为暴政、独裁政治,而独裁政治是人治的极端表现。(3)法治对人类智力发展程度的要求远远高于民主,因为它需要一套相当严密且比较合理的规则系统。*邓曦泽:《中华文明的断裂与赓续——基于知识生产的视角》,《江海学刊》2014年第6期。新儒家的经典命题“内圣开出新外王”,强调的是民主,而不是法治,其方向有重大歧误,给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造成了严重误导,这是思想界、学术界不可推卸的责任。 儒家认为,法律是附属于道德的,其作用是次要的,此即德主法辅(或德主刑辅)。儒家总体上反对法治,主张人治。虽然儒家没说自己主张人治,而明确主张德治,但德治其实是人治的一种特殊类型。人治的外延大于德治,人治有好的人治和坏的人治,德治是好的人治。法治与人治的刚性区别是:是否存在超越于法律的个人或集团,如果有,则是人治;如果没有,则是法治。这意味着,在理论上,法治与德治是矛盾的,但在现实社会治理中,二者可以兼容,即将二者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域和权重进行适当分布(某些事务施行法治,某些事务施行人治,这是可能的)。不过,即便在现实社会治理中,德主法辅与法主德辅也是矛盾的。这乃是说,虽然一个社会的治理完全可以同时采用法治与德治,但一个社会的治理不可能同时是法主德辅与德主法辅的(即就统计出来的整体状况而言,何者为主,是不可能兼容的)。 儒家反对法治,无论从言论还是实践,都有许多证据。王充的看法比较有意思,此予辨析。王充说:“韩子之术,明法尚功。贤,无益于国不加赏;不肖,无害于治不施罚”(《论衡·非韩》)。其实,王充所批评的法家的缺点,在现代法治观念看来,恰恰是优点。如果无益于国也要加赏,还有什么行为不应该奖赏呢?而无害不施罪,更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法家这一主张是对个人自由的肯定和保护(虽然不能说是现代意义的),只要个人不危害他人,其行为就是允许的。而儒家以所谓的道德、礼仪来管制人,连平民衣装不合儒家的要求,也要以伤风败俗之类的道德大棒来压制。王充认为,仁义比法度更重要,但实际上,由于动机论困境的存在,*邓曦泽:《动机论及其困境——关于道德判断根据的考察之一》,《哲学动态》2013年第1期。使人们很难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仁义,且仁义作为个人道德,也是很不可靠的。 从历史实践看,古代人治具有一个权力、道德与真理的内在逻辑。(1)由于一个人有没有德,很难判断。(2)并且,在位者(即官员,也就是统治阶级或其代表)掌握权力和由之衍生的话语权。(3)这就导致,有权者就成为有德者,或者说,虽然有权者实际上是借助权力(因)而占据话语权(果)而自封为有德者(果),但是,在公开的宣传中,官员会倒果为因,说自己是因为有德而掌握着权力。(4)于是,官员向人民宣称,他们是应该掌握权力的。(5)因此,官员的言行都是正确的。(6)进而,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权力与真理是合一的,最高权力就是最高真理。中国古代政治实践验证了上述逻辑。 儒家德治存在严重缺陷。 第一,在逻辑上,混淆了假设和现实,圣人(或君子)治国完全不可靠。儒家认为,圣人(或君子,下同)治国,天下大治。但是,这只是一种假设意义的理念,即:如果圣人治国,那么天下大治。而在逻辑上,从假设推不出存在(即:从“如果p,那么q”推不出存在p)。这意味着,从“如果圣人治国”推不出“事实上存在圣人”,也推不出圣人是容易产生的。如果“圣人治国,天下大治”成立,那么还可以说,“上帝/孙悟空治国,天下大治”。但实际上,上帝/孙悟空根本不存在。儒家德治理念混淆假设与存在,应然与实然,乃是儒家的智力发展程度很低的缘故。 第二,儒家提不出可以大体保证统治者素质的理论和措施。把治国的希望寄托于个人品质,非常不可靠,因为这会面对三大困难:(1)如果真的存在君子(包括贤君和贤臣),如何才能将他们从大众中识别和遴选出来?(2)如果君王(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统治者)的品质败坏,靠什么来纠正?(3)如何才能让君王(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统治者)的继任者也保持品质优良,从而使统治者的品质具有连续性和可持续性?儒家无法比较有效地解决这三个问题。但是,现代的法治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因此,儒家又是相形见绌。 第三,颠倒了法律与道德的实施难易关系及相应应遵守的优先性关系。儒家认为,道德应该处于主要地位,而法律应处于次要地位,于是主张德主法辅(德主刑辅可以理解为德主法辅)。儒家这种主张误导了国家政策的制定,使国家决策走上德主法辅的错误道路。譬如,儒家不重视法治,却很重视道德上的诚信。这看似不错,但其逻辑仍是假设,即“如果能做到诚信,社会信任将增加,社会冲突将减少”,因此,儒家仍旧犯了将假设与现实混淆的错误,且颠倒了道德与法律的优先顺序。关于诚信与法治的关系,法治是最基本、最底线的诚信,是国家信用,它不是一个社会的高级信用,而是最低级的底线信用,即首先和更应该做到的信用;而通常说的诚信是道德诚信(或道德信用),是高级信用,即在实施上次于法律的信用。法律通过立法机关制定和颁行,最终代表的是国家意志。法律是更应该实施的,如果法律不能严格执行,则是国家丧失信用。如果国家违背信用,则道德信用就根本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这意味着,儒家所倡导的诚信因法治不昌、国家信用丧失而走向它自己的对立面,沦为空洞的说教,根本不可能可持续地实现,整个社会的诚信度就会越来越低。 儒家不去要求国家法律应该坚决保证底线信用,却要求人民或个体官员讲信用,这是不可能的。言而无信,无法预期,是人治的必然特征。这不是说,道德建设不重要。相反,道德建设很重要,但更重要、更基础的是法治建设。法治搞不好,社会道德建设就搞不好。*较详细的讨论,参见邓曦泽:《唯思想不可随波逐流》第四章之7“道德,拿什么来拯救你”,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年,第195-201页。 在中国,至今仍有许多人轻视法治,认为法治繁琐、麻烦。但是,在现代社会,公共交往尤其是经济交往日益呈现出六大基本特征:陌生化、远距离、长时段、大规模、高频率、全球化。这六大特征决定了,法治是保障经济活动和各种公共交往有效进行的最基础、最重要的手段,它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活动和各种公共交往的平均交往费用。 本来,儒家已经非常轻视法治了。即便如此,在有限的法治成分中,儒家也要用所谓的道德对有限的法治进行侵蚀,从而使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几乎看不到法治的痕迹。虽然中国古代社会也有法律,但是,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在执行时是人人平等的。对同类情况,儒家常用情有可原(具体如经权、权变、变通、时宜、情有可原、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情况特殊)来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法律待遇。情有可原势必沦为为特权阶层辩护,为其特殊利益服务的理论和工具。同时,在儒家的权变观念下,法律、规则几乎毫无威信可言,许多人都漠视规则,都希望绕开规则办事,而整个社会的诚信度也变得极低。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权力不讲规则与腐败及中国人做事不讲规则,儒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较详细的讨论,参见邓曦泽:《唯思想不可随波逐流》第五章之2“情有可原:权势者的护身符”,第167-169页。 因此,在社会治理方面,儒家无法适应现代社会。 (三)公共交往与社会治理效率方面:儒家繁文缛节,效率低下 一个社会,无论是对内治理,还是对外竞争,都必须讲究效率。但是,在诸子百家中,儒家的主张最为繁文缛节,效率低下,因为它设计了太多无效的非产出性(non-output)的繁文缛节,造成巨大的交往成本,却几乎没有实效。此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言:“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淮南子》指出,墨子正是讨厌儒家的繁文缛节,成本高昂,才创立了墨家。墨子所言“久服伤生而害事”,就是批评儒家这一套繁文缛节的成本太高,长久下去,就会影响人们的正常事务和生活。墨家“节财、薄葬、闲服”(《淮南子·要略》),“强本节用”(《史记·太史公自序》)。在这一点上,儒家的价值不如墨家。 儒家的繁文缛节是一套礼仪,也是一套制度和程序。儒家试图通过繁文缛节来培养德行,但是,这套程序完全无关权力制约,也完全无关德行修养。儒家的繁文缛节与德行、才能没有任何相关性。繁文缛节随时随地都可能是虚伪的,并且虚伪是大概率事件。由于动机论困境的存在,导致这种虚伪无法被分辨。班固就批评了儒家的虚伪,“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此辟儒之患”(《汉书·艺文志》)。可悲的是,儒家根本不试图跳出以“仁”为核心的动机论,通过制度的建构与执行来解决问题。然而,儒家苦心经营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却被现代法治较好地解决了。法治社会基本不管动机,而是为官员和民众设定一套行为规则,尤其是权力约束规则。只要一个人遵守规则,不论他持有何种动机,都是允许的;反之,只要他不遵守规则,不论他持有何种动机,都是不允许的。与之相比,儒家又相形见绌。 儒家这套繁文缛节不但对权力没有任何约束,对道德修养没有任何促进,反而因其高成本而对普通民众形成一种强大的约束,并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阻碍社会进步。 因此,在效率方面,儒家无法适应现代社会。 (四)社会秩序方面:儒家主张等级,反对平等与自由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平等,所有社会成员在政治、法律和人格方面都是平等的。虽然不否认,现代西方仍有许多事实上的不平等,但是,现代西方至少在法理上是主张平等的。而儒家在理论上就反对平等,明确主张等级区分。在事实上,中国古代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因此,儒家的社会等级理念与现代社会是对立的。 儒家对等级的明确主张,最经典的表述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周易·系辞》)。这两句话,不管是不是孔子本人写的,都不能否定它是儒家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核心,也是儒家社会观念(包括社会等级观念和基于等级观念的社会治理理论)的最终理论根据。这两句话可谓旗帜鲜明、直截了当地阐明了儒家的等级观念,令儒家的捍卫者无论如何也无法为儒家矫饰和辩护。另外,孔子说:“贵贱不愆,所谓度也……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子此言与与《系辞》完全吻合。陈寅恪也指出,三纲六纪是儒家的核心,*陈寅恪:《陈寅恪诗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11页。而三纲六纪正是儒家等级观念衍生出来的最基本的等级框架。儒家主张等级,毋庸置疑。但是,在现代,平等已经成为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 在儒家的社会秩序观念中,等级观念体现在一切交往关系中,没有任何一种人际关系是平等的,这种等级制可以称为无限细分的等级制,即便同一阶层内的成员也有尊卑或贵贱,因此,在理论上,没有任何两个人是完全平等的,总有或强或弱的等级区分。这导致在实践上,任何两个人对事件的影响力都不相等(或者说话语权不相等),尊者或贵者的影响力更强,卑者或贱者的影响力更弱。由于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参与民主的成员之间的平等,所以,儒家决不允许参与者不分尊卑、贵贱、长幼而平等地展开民主讨论与决策。这意味着,儒家伦理不满足民主的必要条件。本来,不满足并不意味着反对,B对A未必是反对,但A对A却是反对。民主要求平等(A),但儒家反对平等(A),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是反民主的。儒家对民主的反对,是定性的,只不过在不同的情况下,程度可能有所变化。这是儒家伦理对政治的副作用。 在儒家的等级观念下,不同身份的人享有的社会权利大不相同,在法律上的待遇也不同。这是儒家伦理对法治的副作用。*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53页。 虽然可以继续为儒家辩护,说儒家的开放等级制总比西方施行了很久的封闭等级制(世袭制)更好。这没问题,但如前所论,近代西方发展出了平等观念和平等社会这种更优的形态,而儒家没有发展出更优形态。 在儒家理论中,普通民众的自由主要是守礼的自由。守礼是软性约束民众的(或半刚性半软性)。有人把守礼与现代意义的守法相提并论,其实二者迥乎不同。虽然法律与礼都是行为规则,但是,现代意义的法律是人人平等的法律,它反对一切身份和特权。而儒家的礼非常明确地将人区分为不同身份和等级,再据之制定行为规则。并且,这些规则都是日常行为规制,几乎没有对公权力的制约规则。因此,守礼完全不同于守法。守礼的自由就是要把民众束缚在狭小的范围内,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权和统治。 因此,在社会秩序方面,儒家对等级的主张使它无法适应现代社会。 (五)教育与人格塑造方面:儒家强调服从与因循,鼓励奴性,反对独立 由于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是知识生产,人类的行为状况取决于其所掌握的知识状况,而绝大多数人所掌握的知识的主要来源是教育,因此,教育具有极端重要性。 儒家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设计了一套教育理念、规范和内容,而其核心就是奴性教育,也可以称为顺从教育、听话教育。 儒家教育的几乎全部内容都是做人教育,儒家的知识几乎全是如何做人即直接提供行动指示。在儒家的做人教育中,关键又是服从。儒家给出一些行为规范(礼),让人们服从。儒家只管叫人服从,很少探究“为什么”和“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只管执行,不讲道理,因而在其做人教育中,也从不教学生如何做真正的知识(或知性)的思考。因此,儒家的服从是盲从。例如,根据孔子与其学生的对话,《论语》中学生的问仁,都是以“如何行仁”为问题方式的,而孔子的回答也是针对“如何行仁”这一问题。孔子师徒从不关心“仁是什么”、“为什么要行仁”、“是否可以不这样”这样的知性问题,而只关心“如何行仁”这个行为问题。既然儒家只关心如何行为,那么,教育者就要求被教育者服从那个“如何”,同时不希望甚至不准被教育者思考、追问“是什么”和“为什么”;进而,对“如何”的执行、遵守或服从,就势必诱导受教育者走向盲从。若有不盲从者,势必受到打压。 儒家的盲从教育必然导致的另一特征就是反对独立人格。此点完全可以从上文推论出来。因此,缺乏独立人格,乃是儒家教育之下的必然结果。儒家式的清高不是独立人格,因为清高必须淡泊名利,某些应该要的利益都不要。但是,独立人格根本不要求淡泊名利。争取自己的合法、合理的权利和利益,恰恰是独立人格的表现,而这显然不是清高。即便承认海瑞这样的人有独立人格,由于中国古代没有一套制度来保障个人权利,使得独立人格(以及清高、有志)变得极为困难。此外,人格依附是奴性教育的必要蕴含和结果之一。 儒家奴性教育的另一个表达就是听话教育——“要听x的话”。在家要听父母的话,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不管听谁的话,“听话”都是关键,是万变不离其宗者。于是,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中国的教育对受教育者构成全方面的听话教育(奴性教育)。这种奴性教育绝不是近代以后的创举,它就是儒家教育的核心和“精髓”。所以,说儒家教育的本质是奴性教育绝不是对儒家的歪曲和侮辱,而就是事实。 同理,绝不否认,西方也有长时间的奴性教育(如罗素所批评的)。但是,西方走出了奴性教育,发展出了更高级的教育形态。 因此,在教育与人格塑造方面,儒家也无法适应现代社会。 上述五点结合起来,看似与胡适的“百事不如人”观点差不多,但其实大不相同,因为本文有规范和严格的论证,而胡适等没有。本文并不追求特定的结论和立场。关于论证、结论与立场的关系,本文认为论证高于一切,是严格的论证得出特定的可靠的结论,而不是先设定结论或立场。通过严格的论证,得出什么结论就是什么结论,凡是与论证相违背的预先设定的结论和立场,都必须予以摈弃。本文以论证的方式批判儒学,但非简单地因为西方更强大而鄙薄儒学,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可谓甲午战争以来对儒学最强烈也最切中肯綮的批评。 五四以来,儒家面对许多批评,而儒家的捍卫者也有不少辩护。这里探讨六种辩护。 (一)种子说能否挽救儒家? 牟宗三等认为,“我们不能承认中国之文化思想,没有民主思想之种子,其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不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亦不能承认中国文化是反科学的,自古即轻视科学实用技术的。”*黄克剑、钟小霖编:《唐君毅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501页。这个辩护可以称为“种子说”,但此说是个乌龙。因为,即便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科学与民主的内容,但这些东西也仅仅处于种子阶段,即较低水平(A);同时,新儒学也承认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发展到了很高的阶段(B);那么,根据相对价值法,A的相对价值就不再是A,而是-P。再根据前文的“高级的东西可以让低级的东西衰落,甚至报废”这一规则,如果继续坚持A,就永远比西方落后P,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牟宗三等认为,种子说是对儒学的有效辩护(笔者以前也认为此说是有效辩护),但他们决计想不到,他们居然摆了个乌龙,种子说对儒家是明褒暗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相对价值法,误以为过去有价值的东西现在仍应该有价值。 (二)礼有损益说能否挽救儒家? 或许有人会如此为儒家辩护:儒家认为,礼有损益,儒家难道不可以通过改变自身,实现自我革新,从而延续甚至扩大其生命力?此说可以称为“礼有损益说”。本文认为,礼有损益说并不能挽救儒家。 首先,就礼仪本身即狭义的礼仪看,儒家的礼仪是可以作一些精简,但这只是在量上的精简,它无法根本改变礼仪观念。古代儒家从来就没有把礼仪仅仅视作一种形式,而是把礼仪视作儒家社会等级观念的体现。儒家强调等级,而礼仪是对等级的体现,如果没有具有等级蕴含的礼仪,等级就无法体现。古代的礼仪,绝大多数都蕴含有等级区分,几乎没有平等的礼仪。这就意味着,儒家无法通过改变等级观来改变其礼仪观,进而将礼仪改进为现代意义的礼仪。现代礼仪是基于平等关系的。 其次,将损益观念扩大化,运用到整个儒家,又能否挽救儒家呢?除了礼仪,以下几者都是儒家的核心内容:(1)圣人观念;(2)等级观念;(3)德主刑辅观念;(4)三纲六纪(这是儒家等级观念的具体化和规范化)。 任何理论都必须有边界,这个命题的意思是说,任何理论都有一些核心内容区别于其他理论,如果去掉这些内容,该理论就丧失独立性而不再是它自身。儒家的上述核心内容与现代社会都是不兼容的,如果去掉这些核心内容,儒家还是儒家吗?于是,儒家势必面对两难困境:要么摈弃与现代社会不兼容的核心内容,以自我否定精神推动社会发展,若此,儒家将不再是儒家,并且它必将全面而迅速地退出生活;要么儒家竭力维护其核心内容,儒家固然仍旧是儒家,但它势必阻碍中国社会发展。无论儒家多么真诚地捍卫自己,也无论多少外力支持儒家,儒家的命运只能被很有限地延缓,而不可能可持续地长期维持。这是因为,由于与现代文化相比,儒家整体落后,如果提高儒家的地位,扩大儒家的影响,那么,儒家必将构成对中国的更大阻碍,从而使中国在全球竞争中落败。这种落败不是中国(汉族政权)遭遇蒙古族、满族而导致的失败类型。面对更先进的现代文化,休想指望,中国落败后,外来的新统治者会象满族那样不得不汉化,从而让儒家在异族统治下生存和发展。这意味着,中国一旦落败,儒家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也会被淘汰。所以,儒家的两难困境都只有一个结局:儒家必定衰亡。而差别只在于:儒家或者为了推动国家发展与进步而主动否定、摈弃自身;或者为维护自身地位而负隅顽抗,阻碍国家发展。 因此,礼有损益说,并不能为儒家辩护,挽救儒家。 (三)工具说能否挽救儒家? 有一种观点认为,“儒家被历代统治者利用,成为统治者的帮凶,从而阻碍了中国的改革和前进”。针对这一观点,有人为儒家辩护,认为儒家只不过是工具,工具本身是没错的,错在利用者即统治者。这种观点可概括为“儒学工具说”(我以前算是这种观点的一个代表,但现在摈弃了这种观点)。*邓曦泽:《反古思潮的“反古逻辑”批判:附论经济决定论的“崇古逻辑”》,《儒教文化研究》(国际版)第7辑,韩国:成均馆大学,2007年;删节稿载《齐鲁学刊》2008年第2期。 的确,儒学是被利用的,儒学是工具。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儒学仍然可以流行于世。虽然工具是被动的,但工具并非无差别的,不同工具的效用并不相同。所以,人们对不同工具可以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措施。而选择不同态度和措施的标准,是看工具的功能或利弊有多大。例如,同样是成瘾品,人们对香烟就比对海洛因宽容很多。如果一个工具被行为者使用而产生的危害越大,它就越应该被禁止,尽管工具本身是被动的。也就是说,一个工具被禁止程度与其被使用而产生的危害大小成正相关关系。如果因为工具是被动的,就免于禁止而可以放任自流,那么,一切器物都不能禁止。这显然是荒谬的。 对于一种理论的效用,判断标准是以人民利益和社会发展为至上标准,而非以统治者。在上述五大方面,儒家总体上较利于统治者,而较不利于人民和社会,所以,只要论证出儒家是更有利于统治者而更不利于人民和社会的工具,不管它是不是被动的,它都应该在某种程度上被禁止或废弃。除非有谁证明,儒家是一种比其他理论更有利于人民和社会而更不利于统治者的工具(理论)。 因此,工具说也不能挽救儒家。 (四)美好主张说能否挽救儒家? 有人说,儒家提出了不少美好的主张,尤其是对社会秩序的设想,这些主张的价值不容否定。此说可以称为“美好主张说”。 的确,儒家有不少美好的主张,但提出美好的主张太容易,要找到实现美好主张的有效手段,却相当难。手段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它甚至比目的更重要,且其获得与实施一定需要成本。目标的价值与其值得向往的程度成正相关关系,但也与其实现的可能性成正相关关系。用数学来表达,则有目标价值函数—— G=la(-100%≤l≤100%,0≤a≤100%) G(goal)表示目标的价值,l(longing)表示目标值得向往的程度,a(achieve)表示目标可实现的程度。这个函数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也完全符合经验。如果目标不可能实现,无论它看起来多么美好,也毫无价值,而目标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就是方法的有效性。*邓曦泽:《冲突与协调——以春秋战争与会盟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3页。 儒家的问题不在于它提出的社会理想不对,而在于它没有找到有效的实现手段(即a值很低)。与儒家相比,西方也不缺乏美好的主张和社会理想,因此,在这一点上,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占优势。但是,西方找到了比较有效的治理手段,而儒学没有找到,所以,儒学又相形见绌,缺乏竞争力。 所以,美好主张说也不能挽救儒家。 (五)历史功绩说能否挽救儒家? 还有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以儒家为主的治理理论及其治理实践曾产生过不菲的治理效果,使古代中国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因此,儒家的治理理论是有重大价值的。此说可以称为“历史功绩说”。 对此,本文决不否认中国古代曾有的治理业绩,也决不认为儒家从来就是没有价值的。在西方现代治理理论形成及其实践以前,儒家的治理理论及其实践是很优秀的,但是,运用程度区分法和相对价值法,如果面对更高级的治理理念和方式(法治+民主),儒家的价值就相形见绌,而必须予以淘汰。过去很有价值的东西,现在或未来未必有价值。 所以,历史功绩说也不能挽救儒家。 (六)历史合理说能否能否挽救儒家?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儒家在古代是适应当时的历史状况的,因而是合理的(准确说在当时是合理的)。历史状况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尤其是交通通讯技术、教育水平、观念状况等。这种观点可以称为“历史合理说”。我本人也曾持有此见。 作为一个孤立的观点,历史合理说大体是成立的。但是,此说面对一些疑难。 第一,从儒学在历史上是合理的,完全推不出它现在仍是合理的,更推不出它永远、必然合理。同理,从奴隶制是适应当时历史状况且合理的,推不出它现在仍合理。 第二,任何事物的合理性都是变迁的,在古代合理的在现代未必合理,在古代不合理的在现代未必不合理。根据此点,若儒家的捍卫者要证明儒家在现代仍是总体合理的,根本不需要证明儒家在古代是合理的,而只需要直接证明儒家在现代是合理的。若要证明儒家在现代是合理的,则需要证明儒家所蕴含的治理方式、思想观念等的合理性不低于“科学+法治+民主”。但是,儒家的捍卫者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尽管“科学+法治+民主”也有缺点,但在整体上至少比儒家更优。 所以,历史合理说也不能挽救儒家。 第二节的五大方面乃是一个社会体系能否正常运行的基本方面,它们的优劣也决定着一种文化的优劣(“一种文化”的尺度可大可小,大者如欧洲文明、中华文明,小者如儒家、法家)。由于儒家在上述五大方面都远远落后于现代文化,所以,儒家整体上没有价值了,更准确地说,儒家整体上是负价值的。儒家之所以是负价值的,是从相对价值法推导出来的。以1840年为分水岭,无论中国是否自愿,它都卷入了世界体系。各大文明之间(及其内部)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并且都必须明确意识到竞争乃是不可避免的生存环境,因而必须主动、积极地参与竞争,尽可能克敌制胜。这意味着,再也不能仅以儒家自身的价值来衡量其价值(即它与0相比较的价值),而必须与其他文化相比较。在这种比较/竞争中,儒家的价值(A)与现代文化的价值(B)相形见绌,因而,儒家不但不再具有正价值(A),反而具有负价值(-P,即A与B的差)。 但是,能否说儒家毫无价值了呢?不能。判断儒学是否还有价值,需要明确两个基本区分,第一是将生活领域划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第二是将公共领域划分为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在三个领域中,政治领域是最重要的,它决定其他两个领域的边界和基本的行为方式与规则。根据三个领域的划分,儒家必须完全退出政治领域,并且大幅退出社会领域(因为现代的社会领域作为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几乎完全反对等级区分)。但在私人领域,儒家可以局部存在。其实,基督教的许多观念也不适应现代社会,也大范围退出西方人的生活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今天的基督教已退化、收缩为一种道德宗教和精神宗教,生存于私人领域和社会领域。与过去相比,基督教不再具有强制的约束力,民众对基督教的选择完全是自愿的,可以自由加入和退出。凡是法律规定的,宗教都不得介入。凡是与法律相冲突的宗教教条,都必须让步或废除。即便法律的某些规定与宗教的某些教条相近或相同,人们遵守的也是法律,而不是宗教。概言之,在现代社会,法律优先于宗教。只不过,由于现代化发源于西方,基督教与现代性的亲缘关系,可能比儒家与现代性的亲缘关系要近,所以,基督教在西方人生活中的退出程度可能不如儒家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退出程度。 总的说来,在价值上,与现代文化相比,儒家的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错误的;另一类是比较正确但低级的,如修身、仁爱、诚信、谦让等。不过,不要误解“低级”这一概念。欧几里得几何、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牛顿力学,在特定的预设内是正确的,但它们已经由最初的最高级、最先进变得低级。例如,儒家的诚信,当然有价值,但是,与现代西方的诚信相比,儒家的诚信是低级的,因为现代西方已经设计出了一套相当完善的规则体系(信用体系)来保障诚信的实现,但儒家没有这一套规则系统。 对应于上述五大方面,儒学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也可分五大方面来考察。 第一,在知识生产和创新方面,与现代科学这种知识生产方式相比,儒家毫无价值。 第二,在社会治理方面,儒家的德主法辅观念也无价值,但在确立法治基础地位的条件下,德治(人治)观念还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德治存在的必要性在于:人类至今甚至永远无法建立起一套能完美规范人类行为和协调冲突的法律体系及其执行体系。而德治存在的界限是,一切裁决者对分歧和冲突的调控都不得超越法律规定的边界。在这个前提下,裁决者可以并且应该运用自己的良知和道德,使自己对分歧和冲突的裁量更倾向于维护人类的基本价值。当然,很可能出现,某些裁决者的裁量会违背人类的基本价值。但是,只要裁决者的裁量没有越出法律的边界,那么,即便其裁量违背了人类的基本价值,不能让公众满意,其后果也是可容忍的。在这个意义上,还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裁量权,每个人都可以运用自己的良知与道德,使自己的行为更少地损害他人,更多地有利于他人。 第三,在效率方面,儒家也基本上完全不再有价值。只不过,在遵守法治的前提下,且在个人良知和道德的支配下,如果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个人可以更多地为他人提供方便,从而可以提高交往效率,有效促进公共交往。如果锱铢必较,有些本可达成的交往和共赢,反而就不可能了。 的确,儒家含有的一些内容属于人类文明有效存量中的最基础部分,这部分内容永远不会过时,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诚信、自律。但是,这些基础内容各大文明都有,而非儒家的专利。例如,所有文明都或明确或不明确地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诚信、修身、自律。因此,在竞争中,儒家无法以各个文化共通的内容对其他文化构成优势。 第四,在社会秩序方面,儒家的价值也很低,因为它无法打破等级区分,适应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不过,在遵守法治的前提下,且在个人良知和道德的支配下,尊老爱幼,谦让他人等,总是积极的。 儒家的少数礼仪具有正价值。人与人的日常交往,需要一些礼仪或规范。儒家的礼绝大多数是累赘,具有负价值,但少数具有正价值。不过,这里也有两点值得注意。(1)日常交往中的礼仪和规范,在促进沟通、理解和交往以及弱化冲突方面的价值本来就很低,因而在文化竞争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大。所以,既不要否定这些礼仪和规范的价值,更不要夸大其价值。(2)各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交往礼仪和规范,几乎所有文化都不会以自己的交往礼仪和规范而对其他文化构成竞争优势。 第五,在教育和人格塑造方面,因为儒家教育的奴性本质,使其教育理念、规范和内容必须整体地退出教育领域,但儒家的部分修身内容,还有价值。虽然逆来顺受、盲目服从的奴性不可取,但是,宽容、谦让等,总是积极的人格;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这些理念,也可以转化为对知识的追求和创新。 概言之,对竞争力影响的大小,是判断一种文化形式的价值及是否应该维护它的重要标准。基于此标准,可以概括儒家在现代社会的功能与地位:儒家的根本出路是道德儒学和心灵儒学,而不可能再次政治化而成为政治儒学,也不可能再次法律化而成为法律儒学。但即便如此,也要限定两点:第一,中国人的道德思想源和心灵思想源,是多元的,且可自由选择,而儒学只是其一。第二,即便作为中国人道德思想源和心灵思想源的备选项之一,儒学也需要摈弃许多陈腐观念,尤其是等级观念。*邓曦泽:《中华文明的断裂与赓续——基于知识生产的视角》,《江海学刊》2014年第6期。 儒家全面、大幅退出中国人的生活后,其现实价值仍有,但大幅衰减,而主要作为人类历史、人类古老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成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的对象。这就是列文森所言的儒家的博物馆化。*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38、372页。 许多人都有文化情感,这是应该的。但是,理智告诉我们,文化情感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民族的最高目标,不是不可动摇的情感立场。人类的最高目标是幸福,而一切具体的文化形式,都是增进幸福的手段。如果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能增进幸福,那么,用前者替代后者,就是正常的和应该的。如果一种文化面对更高级文化的竞争,却不能自我更新,发展出更高级的形式,从而保持不败,那么,它就只能被淘汰。没有一种文化形式是天命的、永恒的。儒家所言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本身也就承认了文化竞争和更替的逻辑,因而也承认了自己衰亡的可能性。在本质上,这与用一种生产工具替代另一种生存工具,是同样的道理。认识到此点,有助于我们实现文化的升级换代,形成新的文化传统,从而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幸福。 NewReflectionsontheModernValueofConfucianism—AResearchontheConceptsofCompetitionandRelativeProgress Deng Xize All human civilizations have evolved from the period of ignorance and brutality, but only the West has developed a more advanced for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petition, and using degree distinction and relative-value method,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Confucianism had played a huge positive role in ancient China, but in five basic aspects of social life, Confucianism is now far behind the modern culture. Howeve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Confucianism is worthless; it can be used as moral Confucianism and spiritual Confucianism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Confucianism, competition, degree distinction, relative-value method, moral Confucianism, spiritual Confucianism B222 :A :1006-0766(2017)05-0058-13 (责任编辑:曹玉华) 邓曦泽(本名邓勇),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成都61006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冲突与协调——以春秋战争与会盟为中心”(13FZZ006)、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编号:skqx201101)二、儒家的五大缺陷
三、关于对儒家的六个辩护的辨析
四、道德儒学与心灵儒学:儒学的当代价值与定位
结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