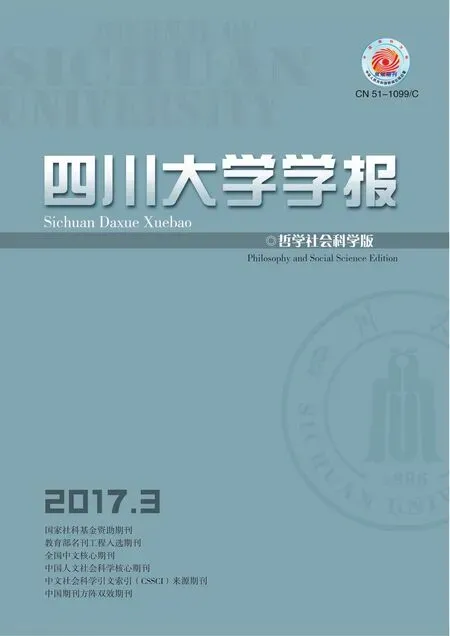迈向生命政治与生命诗学:阿甘本的姿态论及其转向
支运波
迈向生命政治与生命诗学:阿甘本的姿态论及其转向
支运波
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美学家阿甘本提出并系统论述了文学批评概念——姿态。阿甘本的姿态论思想存在着由美学向生命政治以及生命诗学转变的潜在线索。在美学领域,阿甘本把姿态置于语言范畴,认为姿态是一种始源性的语言与交流方式;过渡到生命政治领域,他则从近代资产阶级“丧失姿态”并“不断沦为姿态的命运”的意义上,认为这引发了一种人类的景观化过程。最终,阿甘本倡导以生命诗学拯救姿态丢失后所造成的去主体化命运,从而“复魅”经验世界,实现人之诗意的栖居。
阿甘本;姿态批评;生命政治;生命诗学;理论转向
在由亚里士多德所开启,到了尼采那里达至顶峰,再途经福柯、德勒兹,一直到南希的姿态(Gesture)*该词或译为“姿势”。本文出现两种译法互用的情况,是遵从引文处的翻译。论的历史中;或者从古罗马瓦罗到现代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姿态论的脉络中;抑或者,在由本雅明、科莫雷尔、里维埃尔、费内翁以及孔蒂尼*吉奥乔·阿甘本:《潜能》,王立秋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第252页。等为数不多的20世纪伟大文学批评家们所构筑的姿态论批评范畴中,可以说,没有谁能像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美学家阿甘本那样,对“姿态”这一范畴做出过如此系统的论述。不仅如此,阿甘本的姿态观还大大突破了文学、艺术、电影以及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诸学科界限,并且以其极敏锐的嗅觉探触到了当今世界尖锐的现实问题,因而显得十分独特和富有创见。目前,阿甘本已然成了国内外思想界“新的理论时尚”,*Fredric Jameson, “Symptoms of Theory or Symptoms for Theory?” Critical Inquiry, Vol.30, No.2, 2004, pp.403-408.身处这一学术语境,探索阿甘本的姿态思想便显得尤为迫切和关键了。
一、批评范畴与姿态语言
阿甘本是凭借其卓越的政治哲学思想而被人知晓的。但事实上,他早年却是从事文学、语言学、诗学和美学——或者可以用我们所谓的“文艺学”来概括——研究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阿甘本是如何看待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呢?在其集中论述姿态的三篇重要文献——《关于姿态的笔记》《科莫雷尔,或论姿势》和《作为姿态的作者》中,阿甘本从姿态概念出发,认为文学本质上就是姿态,批评就是将作品化约到姿态的领域。*吉奥乔·阿甘本:《潜能》,第253、257页。他以“作为姿态的作者”来回应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中所提出的疑问,指出作者“在文本中仅作为使表达成为可能的姿态而在场”,并且认为读者和作者一样都是属于“在文本中借以把自身置入游戏并在同时,无限地从游戏中抽身而退的那个姿态”。*吉奥乔·阿甘本:《渎神》,王立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0、120页。可见,“姿态”是阿甘本对文学活动及其批评实践的本质性界定。尽管有学者认为,或许阿甘本不太可能会因为论文学、美学而被人铭记。*Jon Simons, From Agamben to Žižek: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ist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6.但他的“姿态论”却注定将会是一个例外。因为,在诸如电影理论等一些领域内,它业已被视为“不朽的”*Adrian Martin, Last Day Every Day: Figural Thinking from Auerbach and Kracauer to Agamben and Brenez, New York: Punctum Books, 2012, p.29.贡献了。而在文学理论领域内,姿态批评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批判效力,且不断占据了显耀的位置。
姿态是阿甘本密切关注的几个重要主题之一。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丁、尼采、康德、维特根斯坦、施密特、海德格尔、阿伦特、本雅明到福柯、德勒兹、德波等一大批著名思想家那里,以及从艺术、语言到哲学再到法律以及政治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内,阿甘本对相关学说都多有吸收,可他却常常以“姿态”这一术语阐释或置换其他思想家的核心概念。*Jenny Doussan, Time, Language, and Visuality in Agamben's Philosoph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当然,从更为直接的来源来看,阿甘本的姿态论则主要来自瓦罗的“空无”姿态说、科莫雷尔的“纯粹姿态”说、德勒兹的“运动-影像”说、福柯的“作者缺席”说、德波的景观理论以及本雅明的“情节中断”说等多条线索。其中,尤其是本雅明的思想,一直是阿甘本理论首要的潜在对话者和阐释对象。阿甘本有关于姿态论的相关界定,或受本雅明论卡夫卡和布莱希特的影响,比如,阿甘本对卡夫卡作品所做的姿态批评和政治学阐释;*Anke Snoek, Agamben's Joyful Kafka: Finding Freedom Beyond Subordination,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2.或直接就是本雅明原话的转述,比如,阿甘本所说的“批评就是把作品化约到纯粹姿态的领域”,便是来自本雅明的原话:“批评是作品的禁欲(mortification)”。*Walter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57.
阿甘本在不少著述中都对姿态做过界定。比如,在他最为著名的《关于姿态的笔记》中,沿着亚里士多德对制造(poiesis)/实践(praxis)的区分,以及瓦罗对“某种东西在其中持续和维持着”的“执”(gerit)的论述,阿甘本提出“姿态是对可交流性的交流”;*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5-85页。在《科莫雷尔,或论姿态》中,他追随科莫雷尔,提出姿态是一种“在语言中本身之中的有力的在场”和语言的“塞口”(gag);*吉奥乔·阿甘本:《潜能》,第252页。而在《作为姿态的作者》中,他则通过阐释福柯《什么是作者?》一文,提出姿态是指“在每个表达行动中的未得到表达之物”*吉奥乔·阿甘本:《渎神》,第110页。的观点。基于对已有姿态说的创造性阐释,并结合自身对于文学和政治学著作——特别是其中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关论述——的独特理解和精准把握,阿甘本提出了自己极具特色的姿态观。
阿甘本论姿态,首要特征就是将姿态置于语言领域,提出姿态的语言观。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语言问题是阿甘本始终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他一直都在探求一种新的语言体验与语言本体论哲学。从其语言哲学出发,阿甘本认为姿态是一个“原语言”或“前语言”的范畴,姿态是语言中的沉默部分和先于语言的“更为古老也更为源始的在场”。*吉奥乔·阿甘本:《潜能》,第252页。那个内置于语言但却无法言说的东西,即无言、“哑口”或“塞口”,而姿态就是以这种无言的方式“迷失在语言之中”。也就是说,姿态(即语言中的“无”的一面)与语言(语言中可言说的部分)共属于语言,它们是语言的两个面向。这里的“迷失”,既意味着姿态专属于语言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或被翻译成语言,也意味着无法言说,或者语言中断的时刻,由此人类是在语言中存在的这一基本事实便被姿态展示出来。*René ten Bos, “On the Possibility of Formless Life: Agamben's Politics of the Gesture,” Ephemera: Theory and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 Vol.5, No.1, 2005, p.42.一方面,姿态只是作为交流之可能性,以无任何诉求的纯粹媒介性“持续和维持着”某种行止领域;*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第76页。另一方面,通过姿态的敞开,语言(尽管是丧失了经验的语言)以及人类之潜能也便自动地呈现了。
姿态作为内置于语言的“无言”,使得它与“塞口”和暂时的“空无”联系起来,并直接作为纯粹媒介而在场。“姿态是无言”表明姿态既是“无”,也是“言”,是关于“无”或传达“无”的景观或沟通方式。因此,姿态既非“目的”,也非“手段”,而仅仅是“无目的的手段”或“交流”方式。这种“交流”所展示的是作为“在-语言中-存在”的,失去生活经验和自然联系之后的,人的“不可言传性”,以及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拒绝给出的部分,福柯称之为“空无”。简言之,姿态就是填补语言之间裂隙的部分。然而,文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无目的的手段”呢?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让-吕克·南希在其《无用的共同体》一书中就“文学的共产主义”所做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部分解答。南希在该作中较为详细地展现了故事讲述者是如何以文学(主要是以故事、神话、传说等)将个体汇集起来并进而构成共同体的历史历程的。他指出,在那些演说场合聚集的听众并不清楚,或并不关心演说者讲述的故事内容及其真假,也不关心故事中的人物究竟是谁,甚至在大多数场合他们完全没有聆听到故事的内容,就自动地汇集起来。这些听众只是被讲述者的文学才华、演讲口才及其姿态所吸引。由此,南希认为:“文学的本质不是‘文学的事情’(la chose littéraire),也不是‘召唤’这个词语所包含的诉求、宣称、宣告,也不是庄严主体性的流露,文学的本质只是一个姿态(geste)。”*让-吕克·南希:《无用的共同体》,郭建玲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6页。或者,更准确地说,此时的文学只是一个“事件”(event)而已。再者,沿着福柯《什么是作者?》一文的思路,阿甘本提出在作品中,作者并不再现、表征、重塑或诉求什么,而仅仅是使作品的叙述成为可能的手段而在场。他说作者是“通过在这个表达内部建立表达中心的空无(a central emptiness)来使表达成为可能的”。*吉奥乔·阿甘本:《渎神》,第110页。这样一来,作品的内在现实性也因由激发审美愉悦的目的而被抹杀,而有关作品的诗学也不过是到处宣讲着“艺术品脱离其自身本质”的命运。因此在阿甘本看来,“无论批评选择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作品——它也只是用无生命部件拼成的骸骨替代了活生生的肉体而已。……不仅如此,它还把我们引向艺术之外的别的地方,同时将艺术的现实呈现为纯粹的无”。*Giorgio Agamben, The Man Without Content, Trans. by Georgia Alber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pp.27,41.上述两种情况清晰地呈现了文学作为“手段”(或媒介)的无目的性。
然而,阿甘本最看重的却是从姿态的语言关系中窥视到的,只是作为交流之可能性却无任何诉求的纯粹媒介性,即“纯粹姿态”(pure gesture)。这也是阿甘本姿态论的最大贡献所在。根据科莫雷尔的阐释,“纯粹姿态”是指内置于语言结构却从来不能用语言完全表达的一种存在。就像姿态的拉丁语源gestura所意涵的那样,只是作为“承受”(bearing),“执行方式”(way of carrying),或“行为方式”(mode of action)存在。科莫雷尔认为,“纯粹姿态不是表达、说出某物的形式;它没有在内部与外部之间、特殊与普遍之间、能指与所知之间建立任何关系。纯粹姿态根本就不是一个符号。它不属于符号秩序本身,因为它只是‘言说自身的纯粹可能性’。纯粹姿态不是用语言言说某物,毋宁说,它就是言说的可能性”。*Paul Fleming, “The Crisis of Art: Max Kommerell and Jean Paul's Gestures,” Modern Language Notes, Vol.115, No.3, 2000, pp.519-543.也就是说,纯粹姿态是一种有别于正常姿态的例外姿态,它不承担语言交流性的功能,也不能起到衔接语言之间断裂的作用,而单纯地就是一种姿态。因此,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纯粹姿态展现了阿甘本姿态说的根本特性,即“在于在其中既无东西被产出,也无东西被演作,而毋宁说,是某种东西在其中持续和维持着。换言之,姿态打开了行止(ethos)的领域,这个领域是人之为人更为本己的领域”。*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第76页。
姿态打开的“行止的领域”是一个既不“做”(facere),也不“作”(agree),而只是“持续或维持着”(enduring or supporting)某种状态的纯粹交流性领域。这使姿态被赋予了得以克服手段和目的“二决一”难题的可能。突出手段又不忽视“无目的”的“纯粹媒介”性,就这一特性而言,阿甘本认为姿态“别无他名”,姿态即“政治”——“人类最完整的、绝对的姿势性(gestualità)领域”。*吉奥乔·阿甘本:《潜能》,第265页。对此,阿甘本援引瓦罗的话解释说,诗人创造但不表演,演员表演但不创造,而一个国王既不创造国家、也不执行(perform)什么,他仅仅承担和履行某种职责,维持着一种结构性存在。这表明姿态具有鲜明而激进的政治意涵,同时也是人们进入政治共同体的美学途径。基于此,阿甘本主要讨论了姿态的静止性运动、敞开性沟通、维持性支撑这三方面的内容及其美学,并尝试以此整合与建构哲学、文学、政治伦理的一体性。
立足于其哲学、政治与文学统合的观念,阿甘本称姿态批评是超越了其他任何阐释方式(如心理学的、美学的)的最高的批评。这种姿态批评既疏离于文学的历史,也拒斥其他关于文体的理论,它保持了“现实与虚幻、生活与艺术、个体与种属之间的”恰当关系,并借此展示一种“记忆的缺乏”和无可挽回的“无言的塞口”。对阿甘本而言,“姿态发生于所有确定的界定——生命与艺术、文本与实践、现实与虚幻、权力与行动、个人事迹与客观事件——都被悬置时”,它“是一种特殊的行为,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而)属于第三种行为概念,把它描述为执行(carrying)、承担(enduring)和支撑(supporting)。它是既不同于任何先验定义(如生命或艺术),也不同于任何终极定义(telos),包括一切美学定义(如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实践’(pure praxis)”。*Alex Murray, Jessica Whyte,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79.简言之,姿态批评的根本作用就如同“国王的行事”一般:悬置一切既往法则,重新协商、勘定与再平衡现实与思想的多重边界,以此进行并维持着解域与再辖域化。
二、姿态的生命政治学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与福柯一样,都是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一种政治动物的界定开始的。但阿甘本对这一本质性界定的理解要比福柯更为激进。阿甘本认为这里的“政治的”一词并非是形容词,而是标定了种属的差异,并且认为西方政治从一开始就是生命政治的,而并非福柯所认为的始于现代社会。也就是说,在阿甘本那里,人从一开始就与其他生物之间存在着基本的本质不同。这种不同表现为:人作为系着在语言之上的政治动物,还有着情感、伦理以及正义等诸内容。因此,人以自身的行为(实践),以及联系于这些日常行为之经验的思想、哲学和文化都是“政治的假名”,亦是“绝对而完全的姿态领域”。*参见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第81页。由此,阿甘本的姿态概念提供了一个图绘其从美学转向政治的路标,也提供了一个清晰理解生命政治现代性的引线,*Alex Murry, Giorgio Agambe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86-87.这也标志着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文学批评范式的真正诞生。
姿态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天然关系。在被认为是关于“媒介与生命政治的笔记”的《关于姿态的笔记》中,*Deborah Levitt, “Notes on Media and Biopolitics: ‘Notes on Gesture’,” in Alex Murray, Nicholas Heron and Justin Clemens, eds, The Work of Giorgio Agamben: Law, Literature, Lif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93.阿甘本大段援引瓦罗的话阐明了姿态区别于“做”(facit)与“作”(agit)的“执”(gerit)的内涵。紧接着,阿甘本便解蔽了姿态与政治之间的隐秘关系:“姿态的特性即在于在其中既无东西被产出,也无东西被演作,而毋宁说,是某种东西在其中持续和维持着。”*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第76页。也就是说,姿态是外在于“做”(act)之外的,是“做”的否定性。据博思的考察,古罗马帝国时期在城邦议政厅或圆形露天剧场进行的政治演讲,往往并不能使声音有效地传递到听众那里,而杰出的演说家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姿态便成了他们政治表演的最好方式了。*Bos, “On the Possibility of Formless Life,” pp.26-44.事实上,姿态作为纯粹政治的现代例证,也并不鲜见。例如,在当今世界各地,静坐、绝食一类的民众抵抗运动时有发生。在这些事件中,人们仅仅是静坐、绝食,既无政治申诉,也不游行呐喊,但这种姿态却实实在在地是一种政治行为。抑或者,更进一步地说,某些底层行为艺术、哲学思潮,乃至于此消彼长、林林总总的诸多所谓“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视为一种政治行为。但这种种“姿态”显然与日常性的身体姿态(比如,单纯的坐立、行走、身体造型等)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
阿甘本集中论述姿态批评的三篇文献中,有两篇都以“政治是人类最完整的、绝对的姿势性领域”这样的话语结尾。尤其是在《关于姿态的笔记》中,他单列这句结论性的话作为第五部分,并且拒绝给出任何阐释,显得与前面四个部分格格不入。这或许是他认为政治已经内置于其所提供的“姿态的谱系”*Levitt, “Notes on Media and Biopolitics,” p.194.之中了,又或者他无意于重复前人的姿态政治学。但更为可能的或许是阿甘本希望将姿态推进到现代生命政治维度去探视姿态的装置秘密。因为,其一,这种单一性的限定从根本上来说就直接是生命政治的。它通过排除姿态的身体活动的非政治部分将之从自然肉体中抽离出来;其二,作为当代最为杰出的生命政治理论家,阿甘本的许多著作都是在诊断主体遭受极端惩戒与暴力而沦为“赤裸生命”(bare life,或称为神圣生命)时的生命政治现代性的灾难化状况。姿态对他而言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契合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急剧裂变的趋势与生命的极端现实,即姿态相对于身体正常行为的例外性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将生命制造成“赤裸生命”的管治技术亦步亦趋。
事实上,从姿态与语言的始源性关系,以及姿态作为语言的无言和语言的中止之处的行为中,我们已经隐约察觉到姿态与语言之间的第一次裂变。从此,语言与意义之间的整体性关系被打破。沿着这一断裂的路径,阿甘本将他的逻辑起点安置在现代社会人与姿态之间的第二次断裂处,并对此做了极富创见的阐释。在《关于姿态的笔记》中,阿甘本将此第二次断裂规约为:姿态被权力征用。在该“笔记”的第一部分,阿甘本以“西方资产阶级丧失姿态”为主题,呈现了拥有经验的身体是如何被纳入到现代影像技术之中的这一生命政治问题。他以“姿态的丢失”这一表述,表明了可理解的、在人类意义上的身体运动向被科技分析所捕获的可知觉的姿态(姿态的医学和心理学分析)转向。在阿甘本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技把姿态征用为影像、把身体部署为技术与知识系统的方式制造了种种生命政治形式。阿甘本认为,姿态产生于影像的科技分析,彰显了生命遭受权力(power)渗透、经验领域被击碎的现代政治。巧合的是电影的出现和生命分析技术的诞生几乎是同步的。作为医学、法律和工业技术分析对象的身体——之前由姿态驻足的私人领域,借助影像而被公开展示了。现代技术与科学知识(包括影像)的姿态分析打碎和瓦解了自然状态下的、整体性的身体,它将以往属于个体的私人领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使之成为一种被凝视和被展示的政治景观。通过影像科技的索引式痕迹、叙述性细节或摄影师的辅光技巧,身体私域被带入公共领域,自然实现政治化。以此,完成了人的自然状态经由姿态丧失而过渡到景观社会的政治过程。
对于阿甘本的“姿态的丧失”这一判断,莫里将之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就主体性而言,它意味着作为整体和连续性的资产阶级主体身份的丧失。主体化过程是身份错觉的一部分,它通过“去主体化”——由现代生命政治技术所造成的自我的倒塌,使身份受到侵蚀。第二,就艺术而言,它意味着影像灵韵的丧失。影像未被看作完整、绝对和被捕获的姿态,电影仍是碎片化的。第三,就语言与意义而言,它意味着某种完整、内在于意义的自然语言观念的丧失。*Murry, Giorgio Agamben, p.87.这是种对复合义的“姿态的丧失”的理解,在此之外,还存在着单纯义的理解。比如,如今的西方领导人选举,人们大都是在电视屏幕上看政治家对着麦克风和摄像机演讲,看到的是头像而不是其完整的身体及行为。于是,人们也不再折服于演讲者的口才、魅力与热情——即身体本来的自然姿态,而是更在乎他的施政方案与政治目标——即作为纯粹媒介的姿态。而阿甘本更强调的是后者,一种外在的姿态。由此来看,阿甘本对姿态丧失的反思,无论是在字面义上,还是在隐喻义上都意味着人与其生存世界的间离,即现代人失去了姿态的能力,人们沉迷于景观的东西而不再被姿态的美(本然的姿态)所打动。
如前文所述,姿态以其纯粹性交流的语言维度而与“塞口”联系起来,这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塞住其口以阻止其说话,即无言状态;另一个则联系于艺术模仿或戏剧性(如哑剧),即姿态的变异。与此类似,阿甘本认为现代人的姿态丧失也会导致两种情境:一是“生命变得不可辨认”或“生活变得不可解读”,*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第68页。另一个是使姿态变得外异,进而使人的身体变得“神圣”与“不可穿透”。亦即,悬置生命使其变得神圣或赤裸,以便为解除生命的合法性扫除障碍。可一旦生命变得外异于自身,阿甘本断言:这也“就为大屠杀做好了准备”。*吉奥乔·阿甘本:《潜能》,第262页。也就是说,上述两种情境共同指向了姿态的生命政治宿命。以此,阿甘本成功地赋予了姿态以卓越的政治任务,并“将批评问题直接联系到他后期的生命政治主权问题”。*Catherine Mills, The Philosophy of Agamben, Québec: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54.事实上,阿甘本对生命政治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也正在于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典范存在形式——集中营(camp),以及现代生命的典范存在形态——赤裸生命的批判性分析。对于前者,阿甘本认为它是一种无区分的和完全不确定的地带;对于后者,阿甘本视其为一种被悬置于法律之外,未被带入神圣地带的生命,即一种“不能被祭祀但可以被杀死的生命”。*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17页。二者在同一行动领域中,表现为处于临界与无区分地带的生命溢出了生物范畴而沦为随时可被处置却既非祭祀,也非渎神,更非违法的一种常见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
回视姿态的两次历史性变革与断裂,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姿态在废除主体权力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姿态就像是生命之砂砾被丢入法律和政治机器齿轮的一个间隙。*Snoek, Agamben's Joyful Kafka, p.89.或许,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说,“姿态是生活与艺术、行动与权力、普遍与特殊、剧本与演绎之间交叉点的文字。它是被剔除了个人生活史语境的生命瞬间,也是被剥除了审美无利害的艺术瞬间:它是纯粹实践”。*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第108-109页。依据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实践的解读,“纯粹实践”所表明的便是纯粹的行动本身,是没有目的的手段。因此,姿态所涉及的也就是某种生命的形式,亦即没有固定身份、功能和例外的共同体。这使得姿态以其现代形式出现在生命与法律、公共与私下、身体与想象等诸多不可分辨的区域,以居间的方式使手段变得更加可见。故此,姿态是媒介性(mediality)的范例,并且超越了美学、语言和主体性而进入到伦理与政治的现代典范王国。
三、生命诗学的再转向
在姿态的拉丁语源及其最初含义中,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公共场合政治言说之不足的补充中,在现代人和现实社会沦为景观的情境中,以及在南希的关于作为姿态的文学对现代政治共同体形成的考察中,都清晰而连贯地透露出一个被严重遮蔽的关键意涵,那就是:姿态是导向个体幸福和“一种有质量的生活”的可能与手段。作为一种政治或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姿态要求“生命必须自我转变成善好生活”,*以上引文参见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第3、11页。即是说,姿态是一种有关生命实际存在的诗学。缘于此,阿甘本对姿态的沉思并没有满足于语言姿态的美学研究,也没有止步于现代社会“姿态丧失”的政治学意涵,其更大目标则是要进入到不断被超越的生活形式及其现代化的潜能中去重新思考生命,进而建构一种新的生活诗学。所以,曾有学者主张以“诗学”(poethis)来概括阿甘本的思想,*Murray, Heron, Clemens, eds, The Work of Giorgio Agamben, p.55.应该说是不无道理的。
事实上,在生命政治理论领域内,生命、政治、诗学以及生存美学的许多问题还是有区隔的,阿甘本也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些“思想还没有彼此遭逢”给研究造成的困难与阻力。于是,如何修复对西方政治之根源有决定性作用的“生命(zoē)与生活(bios)之间、活着(zēn)与政治上有质量的生活(eu zēn)之间的对立”,*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第97页。成为了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试图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而姿态,尤其是它的居间性(现实与虚构、行与止、权力与行为、普遍与特殊等)和无可区分性的独特品质使其承担了从生命政治向生命诗学转向的关键节点。*Asbjorn Gronstad, Cinema and Agamben Ethics, Biopolitics and the Moving Image,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p.8.就此,我们可以说姿态就如同阿甘本所阐释的色情明星无表情的脸一样,它“打破了生活经验和表达领域之间的一切关联;它不再表达任何事物而只是把自身展示为一种没有表达迹象的场所,展示为一种纯粹的手段”。*吉奥乔·阿甘本:《渎神》,第129页。姿态拆解了生命政治的枷锁,并抓住了现代人类作为一个赤裸生命的潜能,为突破权力的逻各斯而创造了一种新诗学。或者说,在当代,姿态批评提供了“承接先知的拯救工作”。*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第186页。
当人类决计以哲学、舞蹈、小说、诗作以及无声电影等方式来记录并唤回丧失的姿态时,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何阿甘本以姿态作为生命政治批评范式,并把它视为最高的“超越了所有的阐释”的新阐释,也就理解了为何他毫无征兆地将科莫雷尔视为第一流的姿态论作家——甚至超过了本雅明的原因。*Anthony Curtis Adler, “The Intermedial Gesture: Agamben And Kommerel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Humanities, Vol.12, No.3, 2007, pp.57-63.因为,姿态在阿甘本那里被视为一种新的潜能。这从阿甘本所看重和希望重建的,是最普通平常但却凝聚了整个存在的意义的日常生活姿态,就可见一斑,他是要恢复姿态的存在意义。不过,现实中人们所看到的却往往是身体的外观和麻木的世界,而非生命本身及其情感的生命诗学,这多少有些令人心生感伤。
姿态作为维持着行为的中间区域,它使得真实与虚无变得难以区分,而每当这种区分失去意义和必要的时候,就会产生对其实际存在的疑惑,从而使姿态具有一种生命政治的模棱两可性。或者,如同阿甘本所认为的“集中营”(或收容所)那样,以排他与纳入的不确定性表征为:存在的临界与生命的赤裸。亦即,此空间中的生命存在是以保护自由之名而被悬置起来的赤裸生命,生命随时可以例外的规则被中断(杀死)又免于法律的制裁。或者说,此中的生命是通过排除生命的法律正当性而被纳入到一种例外规则中的特殊生命:存在的模糊与终结的随时。与之类似,正是这种模糊性或不确定性才使得姿态具有了有别于传统诗学对诸如形式与内容、真实与虚构、实践与维持所做的确定性结论。如阿甘本所说的那样,“我们已经逐渐习惯于在身体与位置、内与外、无言之物与可言表之物、受奴役之物与自由之物、必须之物与可欲之物之间的这种混淆之中去思想与写作”,而姿态所开启的生命诗学“再也不可能在不可交流与不可言说的事物与可言说并可交流的事物之间做出区分了”。*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第186、185页。生命以姿态存活于当下。而作为“隐秘之谜”的人类内在性生产一部分的艺术,既阻止姿态性身体的日常交流,也抵抗塑性的机械身体作为生命政治调查装置的布置。因此,批评就在于揭示艺术的这种生命政治与真理内涵,或维持着艺术以现代的方式持存,或展示着艺术的“事件”属性。而阿甘本的姿态论不仅呈现了艺术及其与生命政治间的关系,而且还揭示了姿态消失与意义重新被召回到身体内部的这一历史趋势,也就是说人类内在性在阿甘本那里被赋予为真理的处所,这就如同海德格尔说“艺术是真理的自行置入”*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56页。一样具有“弥撒亚”的革命性。
阿甘本说:“朝向艺术家的一面是活生生的现实,他从中读取到‘幸福的承诺’;但朝向观赏者的一面却是一团无生命元素的堆积,只能在审美判断反射回来的倒影里照见自己的样子。”*Agamben, The Man Without Content, pp.70-71.然而,如何弥合这两个断裂面向,阻滞观众不断稀薄的存在感与趣味的精巧化,遏止艺术家远离社会活生生的肌体组织进入美学的无人地带;如何抵抗现代以来的去主体化过程,挽回当今世界进入“博物馆化”(museificazione),*吉奥乔·阿甘本:《渎神》,第145页。重新复魅充满经验的无区隔世界,这些都将是姿态论所必须面对与认真审视的急迫问题,当然,也是思考生命政治批评之可能所必须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因为,不可否认,第一,阿甘本提出姿态的语言哑口论,相应地造就了一个不需要完全用语言来阅读的姿态;第二,阿甘本认为现代社会姿态丧失的是沟通行为能力,所以姿态就成了一个情感表达或一个人的可知真理的知觉表达,或者一个虚假的品质表达;第三,与“在语言中,人把他自己同其自身的赤裸生命分隔开来、并对立起来”*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第12页。相一致,在实存中,人也以姿态将自身与自然生命分隔并对立起来。这样一来,姿态被悬置到一个缺乏根基性的空间之中。尽管,阿甘本以抵抗艺术的生命政治意图转向生命诗学乃是一次自我的突破——这一突破是借助奠基于西方政治根基性的二元对立范畴:排除/纳入来实现的,其根本旨趣或许在于他要沿着海德格尔所开创的“本有”(Ereignis)路径,以致力于从原始起源和内在固有本质的维度上重新找回人类在大地上诗意栖居的内在性本质,但其所遭遇的困境实在是不容乐观。
结 语
阿甘本的姿态批评概念,正如莫里等人所指出的,它表明了姿态领域是:“从与某个目的的相对性中解放了自身而又仍保持为手段的那些手段所构成的领域”;指明了理解姿态领域的可行性路径:“只有通过主权权力(sovereign power)与赤裸生命之间关系的视角对我们政治传统中全部范畴的进行重思,才能获得它们的真正意义”。*Murray, Heron and Clemens, eds, The Work of Giorgio Agamben, p.54.不仅如此,阿甘本姿态论的建设性还在于它破解了去主体化以及姿态丧失和“沉迷于姿态”的困境,重构了现代人精神安防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阿甘本的姿态论承继了西方政治中的政治与生命的纽带,在批评理论领域内首次成功地修复了迄今为止西方政治都未能缝合的“生命与生活、嗓音与语言之间”*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第16页。存在的断裂。就最低限度而言,它也将大大拓展和引发诸如批评的身体维度、形式维度以及无主体维度的新转向,*Snoek, Agamben's Joyful Kafka, pp.87-88.启发人们思考理论批判的当代新维度。
(责任编辑:庞 礴)
Towards Biopolitics and Biopoetics:Agamben's Gestural Ciriticism and Its Turn of Direction
Zhi Yunbo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amous contemporary politic philosopher and aesthetician Agamben's literary criticism concept of gesture. Through study, we find that there is a latent thread running from aesthetics to biopolitics and biopoetics among his gestural idea. In aesthetics, after putting the gesture into linguistic category, Agamben thinks that it belongs to a primitive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media. In biopolitics, however, in the sense that the bourgeoisie has lost gesture or is constantly becoming gesture, which, Agamben maintains, has caused a certain landscape process. At last, Agamben sparkplugs using biopoetics as method of saving de-subjectification caused by the loss of gesture, so as to re-enchant the world, making it again a poetic dwelling for mankind.
Agamben, gestural criticism, biopolitics, biopoetics, turn of direction
支运波,南京大学哲学系在站博士后(南京 210046),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研究所副教授(上海 200040)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生命政治理论视阈下的生存美学研究”(2016M590433)、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项目“生命政治理论视阈下的生存美学研究”(1601126C)、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高原学科建设计划Ⅱ项目“高原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理论”
I06;B546
A
1006-0766(2017)03-0099-08
§文艺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