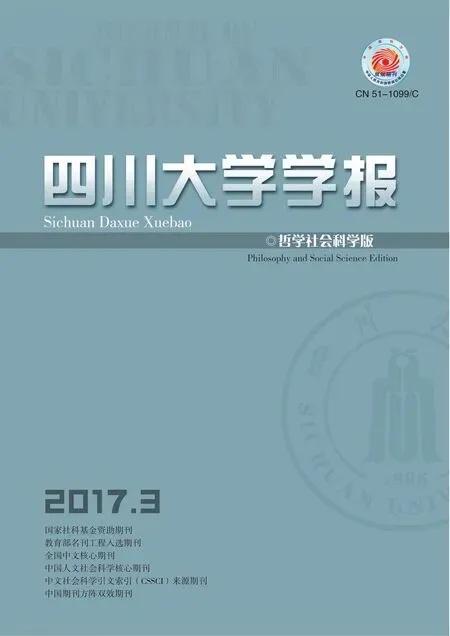“造新因”:胡适对建构“社会重心”的省思
章 清
§胡适研究§
“造新因”:胡适对建构“社会重心”的省思
章 清
“社会”作为理解近代中国变动的关键性概念,早已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值得辨析的是,类似于“社会”这样的概念,对其的清晰把握自是重要的一面,没有认知上的转变,势必影响到对其的接纳;而“社会”概念的另一面同样值得关注,那就是其所映射的“巨变”具有实质性意义,构成把握近代中国历史的枢机所在。对此加以探讨,对于重新认识近代中国以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或不无裨益。胡适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读书人,其如何使用“社会”这一概念并基于此规划自己的角色,如何认识与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架构,又如何阐明“社会重心”的建构乃中国所面临的最突出、最急迫的问题,皆构成揭示“社会”这一概念重要的维度。
社会;社会重心;合群;省界;业界
1932年胡适撰文检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失败,集中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中国这六七十年之所以一事无成,一切工作都成虚掷而不能永久,只是因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在其看来,帝制时代的重心当在帝室,但经过太平天国早已失去政治重心的资格。自此以后,无论是“中兴”将相、戊戌维新领袖还是后来的国民党,都曾努力造成新的社会重心,然往往只一二年或三五年,又渐渐失去担纲社会重心的资格了。*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11页。注意到此一问题,非自胡适始,章太炎1918年在一次演讲中对民国成立以来“中坚主干”之虚位也曾阐述其看法:“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一国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坚主干之位遂虚矣”。*章太炎心目中能成伟大人物的乃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辈,“今世果有如曾、胡、左者,则人自依倚以为主干,就不能然,但得张之洞辈,亦可保任数岁,赖以支持。而偏观近世人物,如此数君者无有也”。参见章太炎:《在四川学界之演说》(1918年春讲于重庆),《章太炎全集》之《演讲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9-270页。研究者也注意到近代中国失去重心的这一现象。参见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149-192页。
胡适勾画近代中国追求“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的历史,并以此为最突出、最急迫的问题,对于检讨胡适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自是提供了值得重视的视角。显而易见,胡适试图表明,他与他的朋友们为之奋斗的,正是致力于为中国创造一个“社会重心”。这样的关切,既浓缩了胡适省思中国问题的心路历程,也昭示了“国难”之际读书人的自我担当。那么,胡适所理解的“社会重心”有哪些具体的体现呢?同时,胡适在30年代形成这样的思考,回溯过往,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呢?这正是本文期望略加申论的。
有必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笔者针对“社会”进行概念史分析的个案之一。“社会”作为理解近代中国变动的关键性概念,早已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从语词的翻译来说,论者颇为关注由“群”到“社会”的转变。*王汎森指明:“‘群’与‘社会’虽然几乎同时出现,但两个观念有一更迭期。大体上从甲午之后到义和团之间是‘群’流行的时期,此后有一段时间,‘群’与‘社会’交迭使用;大致要到辛亥革命前四、五年,‘社会’一词才渐流行。”金观涛、刘青峰也指出,戊戌前后以“社会”翻译society已从日本引入中国,但流行的是“群”,鲜少用“社会”指称society。从“群”到“社会”的转变,大致发生在1901至1904年间。参见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从两份未刊残稿谈起》,《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第203-212页;金观涛、刘青峰:《从“群”、“社会”到“社会主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5期(2000年6月),第1-66页。新近的研究还分别立足于中国和日本,对“社会”作为概念的成长有所解析。*参见冯凯:《中国“社会”:一个扰人概念的历史》、木村直惠:《“社会”概念翻译始末——明治日本的社会概念与社会想象》,见孙江、陈力卫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2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99-137、138-153页。拙文《“社会”的从无到有——晚清中国新名词、新概念的另面历史》对此亦有分析,该文曾提交德国汉堡大学于2015年7月17-18日举办的工作坊“Conceptu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Recent Trends in East Asian Studies”,待刊。笔者针对“社会”这一概念展开分析,是试图揭示“社会”对塑造近代中国的历史图景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其一,“社会”概念的成长,其语境紧扣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的浮现,“国家-社会”架构的形成,也表明此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其二,“社会”的成长有其基本的标识——“合群”,有别于以往的组织形态,这也成为“社会”由“虚”转向“实”的象征所在。其三,“话语”之外,“社会”概念也构成近代历史演进的基本呈现,映射出“各界”所表征的“社会力量”逐渐浮出水面。其四,个人之“入”社会,同样是“社会”成长的写照,并成为检验“社会”之实质性意义的基础。换言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期望能揭示概念成长的另一面。依拙见,类似于“社会”这样的概念,对其的清晰把握固然是重要的一面,没有认知上的转变,势必影响到对其的接纳;然而,“社会”概念的另一面同样值得关注,那就是其所映射的“巨变”具有实质性意义,构成把握近代中国历史的枢机所在。对此加以探讨,对于重新认识近代中国以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或不无裨益。胡适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读书人,其如何使用“社会”这一概念并基于此规划自己的角色,如何认识与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架构,又如何阐明“社会重心”的建构乃中国所面临的最突出、最急迫的问题,凡此种种,皆构成揭示“社会”这一概念重要的维度。
一、“社会”浮现的意义及影响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一词在晚清的浮现,已为相关研究者所揭示。透过晚清读书人的言说,不难了解“社会”概念的浮现所映射的是读书人对“合群”的关注。耐人寻味的是,尽管读书人对于“合群”从各个方面都予以肯定,但如何“合群”,却未必能找到合适的办法。大致说来,学会、学校与报章成为此一时期思考如何“合群”的主要载体,经历种种曲折,固然有其原因,但关键在于,“社会”的缺失导致了“合群”难以找到依凭,进而将各种组织或团体置于相应架构中,赋予其地位。而“社会”的成长,则与形成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观念密切相关;缺乏对“国家”的认知,所谓“社会”也难以有所依托。可以说,基于“合群”进一步产生对“国家”与“社会”新的认知,影响深远;正是有了近代意义的国家观念,对“社会”的认知才有逐步清晰的呈现。
“合群”的主张固然推动着对“社会”与“国家”的认知,不过,仅由此言之,仍不能完全揭示“社会”成长的实质性意义。这里值得强调的是,社会重新组织后形成的“业界”,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也成为社会力量成长的写照。亦可以说,正是“社会”概念的浮现,促成斯时的读书人思考中国应该如何组织起来。换言之,立足于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认识“社会”,并辨析“国家”与“社会”的分野,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进一步的,在获得“社会”概念后,“社会”如何组织,也成为时人所关注的焦点。正是这样的思考,推动了“社会”构成实质性的概念,由“虚”走向“实”,成为近代中国发生深刻变动的象征。结合另一汉语新词“~界”或“~~界”的浮现,即大致可理解其中之枢机。“~界”同样构成把握中国如何重新组织的关键所在,它昭示着这是用与以往不同的方式描绘中国,并推动所谓的“社会”按照“业界”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这方面的讨论参见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形成及其困局》,《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界”的虚与实——略论汉语新词与晚清社会的演进》,《东亚文化交涉研究》别册第7号(2011年3月),日本关西大学,第55-76页。
略说“社会”浮现的意义及影响,检讨胡适如何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中成长,并结合“社会”这一概念思考与之相关的问题,也有了相应的基础。从时间上说,“社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浮现于中文世界,并构成揭示重大转变的关键性概念,自也会影响到正处于成长中的年轻人。胡适1904年春天来到上海,就深深卷入读书人所积极推动的“合群”的潮流中,而“~界”“社会”这些概念也构成其思考的重要符号。
胡适最初留下的日记,就显示出其所受到的影响。1906年3月4日记:“今日为本斋自治会第一次开会之纪念日。”*胡适:《澄衷日记》,“1906年3月4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7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页。3月18日的日记又说明有一茶社,每当星期日,“学生至者极多,几为学界中一会集之所焉”。也正是这一天,胡适在日记中还表示:“与余君及赵君敬承等议发起一阅书社,赞成者颇多。”*胡适:《澄衷日记》,“1906年3月18日”,次日又记“批阅阅报社章程稿”,《胡适全集》第27卷,第3页。过了几日,胡适在日记中又说明:“西四学生前议发起一讲书会。幼稚学生具社会思想诚不易得,故杨师于集益会曾提议,此事请举一代表人为厘定章程。”*胡适:《澄衷日记》,“1906年3月26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7页。这是目前所知胡适最早使用“社会”一词的例证,也许更重要的是,“社会”成为其参与各种集会,以及组织“阅书社”等活动的形象说明。
不惟如此,胡适之介入“社会”,还体现在对于同乡会的活动表现出浓厚兴趣。1906年5月6日记:“得悉吾皖旅沪同乡组织‘安徽旅沪学会’,此为吾皖人创举,闻之大快意。闻此事主动者为方君守六,定今开会,布告章程。余本欲赴会,后读《时报》,知已缓期(日未定),乃罢。”*胡适:《澄衷日记》,“1906年5月6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26页。5月13日,胡适出席了安徽旅沪学会第一次活动,该会吸引了百数十人参加,“到会者皆签名,颇形踊跃也”。*胡适:《澄衷日记》,“1906年5月13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28-29页。正类似于1903年发刊的《湖北学生界》成为斯时由“省界”向“业界”过渡的象征,显示超越“省界”之“业界”逐渐成为读书人聚集起来的标志,胡适参与的“安徽旅沪学会”也具有类似的属性。参与其中,胡适对如何汇聚安徽在沪人士也有所思考,并且对于各界别中之“学界”尤为看重:
旅沪学会章程,原文注重“学界”,故曰“本会为在上海各学校之安徽人组织而成”,嗣由会员改定,将“各学校”三字除去。范围诚广矣,然吾皖人除学界外,流品至杂,程度至不齐,即以商界而论,非特不能相团结相维持,甚且相嫉也,相害也,以此等资格而欲与之办事,其偾事也必矣。故余欲先从学界着手,拟执此说以驳此章程,俟一有暇,即当从事于此也。*胡适:《澄衷日记》,“1906年5月14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29页。
为此,胡适也向该会之组织者明确表达其异议。日记中写道:“寄方守六及学会发起诸人之书成,凡三千言。”其中特别阐明“先就学界入手,不羼他界”;“学界外,各业各举一代表,每次与会旁听”。*胡适:《澄衷日记》,“1906年5月25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36页。只是,胡适的主张并未被安徽旅沪学会的组织者所接纳,该会第二次开会时,之前所议改之处,“均未改正”。*胡适:《澄衷日记》,“1906年5月27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37页。胡适对此显然是颇为失望的,稍后,方守六提议每县各举代表一人,胡适就“不表同情”,为此还致书方辩论此事。胡适阐明“不能举”之理由:“代表必深悉选举者之利害。今商、学界不分,则利害不同,趋向异宜。苟一县之人,二界皆有之,则举学界人乎?抑举商界人乎?故不能举。”其主张“当用二界分举法”:“学界:各校分举”,“商界:各业分举”。*胡适:《澄衷日记》,“1906年6月1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42页。胡适对家乡事务之关切,此一时期已有充分体现。在与家乡同学的通信中就显示胡适在思考创办《绩溪报》事,并向同学借阅《绩溪县志》一书。令其颇感欣慰的是,“吾邑来沪诸人无不争自濯磨,争自树立,殊足为桑梓庆”。而在留学西洋研究文学还只是妄想之际,胡适也表示愿意继续留在上海,益处即体现在“可为吾绩旅沪旅淞诸人作一机关部”。参见胡适:《致春度》(1908年12月30日),《胡适全集》第23卷,第11-12页。在未来的日子里,“同乡”因素也成为胡适重要的“社会资源”。
1906年2-7月间胡适留下的《澄衷日记》,记录了其对于如何“合群”的思考,“社会”之用例并不多。进入中国公学后,胡适加入竞业学会,成为《竞业旬报》主要撰稿人。胡适在该报发表的文字,即显示出“社会”成为其思考相关问题的重要概念。
1906年9月创刊的《竞业旬报》,其《凡例》明确阐明“本报发生之原因”:“愚智既殊,文野斯判,社会阶级之差别尚已。本报意在通行于下等社会,故措词不欲其奥,陈义无取甚高,街谈巷议,樵唱渔歌,皆本报之材料也。”对于“本报注意之重点”,则有这样的阐述:一,振兴教育;二,提倡民气;三,改良社会;四,主张自治。*《凡例》,《竞业旬报》第1期(1906年9月11日),第5-9页。该报第2期登载的《竞业学会章程》又表示:“本会由学界同志所组成,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还要求其会员“一言一行,一动一静,必于公理有合,于社会有益”。*《竞业学会章程》,《竞业旬报》第2期(1906年11月7日),第45-46页。《竞业旬报》《竞业学会章程》中频频出现的“社会”字眼,算不上特殊,当时创办报章、组织学会的活动往往都致力于表达类似的诉求,于此也可见“社会”这一概念具有的影响,它业已成为体现读书人关切的基本话语。胡适考入中国公学后不久就经人介绍加入了竞业学会,在《竞业旬报》1908年停刊之前,胡适对该刊的介入程度颇深,甚至有时整期的文字差不多全出自其手笔,这些文字中也包含不少“社会”的用例。
从胡适在《竞业旬报》发表的近百篇诗文来看,其思想路数是自觉追随梁启超的思想主张,尤其注重于“破除迷信,开通民智”的工作。*最能体现胡适此种关切的,无过于其所撰写的《真如岛》。这是胡适写的第一部章回小说,从《竞业旬报》第3期开始登载,以后断断续续刊登至第37期,计11回,未完。胡适悲叹中国处于迷信状态,“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世界”!*胡适:《无鬼丛话》(二),《竞业旬报》第26期(1908年9月6日),第29-30页。在这一时期一篇重要文章《论毁除神佛》中,胡适就将公共与个人生活中迷信的盛行揭露出来:
现在文明世界,只可怜我国上至皇帝下至小官,都是重重迷信的。什么拈香哪!大庙哪!黄河安澜哪!祈雪哪!祭社稷哪!日蚀哪!月蚀哪!还是缠一个不清楚。就是上海,那真是极文明的了,然而那些上海道哪,上海县哪,遇着什么上元节、中元节、日蚀、月蚀,依旧守他野蛮的风俗。*胡适:《论毁除神佛》,《竞业旬报》第28期(1908年9月25日),第5页。
也许是不经意间,胡适所描绘的正是过去日常生活中“会”“社”的情形,只是并没有明确阐明“会”“社”与“社会”之区别。*《申报》创刊后不久刊发的文字即有“社会”的用例,但往往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与“会”的表述。如1875年9月8日刊发的《闹社会》一文,描绘的即是中元鬼节期间所举办的近似于庙会的活动。在《论承继之不近人情》这篇文章中,胡适倒是产生了对“社会”较为朦胧的认识。文章将“人死无后,把兄弟之子来承继”一事,作为“最伤天理最伤伦理”的风俗,为此表示:“我如今要荐一个极孝顺永远孝顺的儿子给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这个儿子是谁呢?便是社会。”文章试图回答“社会是大家公共结合成功的,怎么可以做我的儿子呢”这一问题,为此还举例说明,孔子死后许多年了,仍得到人们的敬重,一直纪念他,“这可并不是因为孔子的子孙的原故,都只为孔子发明许多道理,有益于社会,所以社会都感谢他,纪念他。这不是把全社会都做他的子孙了么”?不独孔子如此,那些英雄豪杰、仁人义士,之所以能万古流传,同样是缘于他们“有功于社会”。因此,“一个人能做许多有益于大众有功于大众的事业,便可以把全社会都成了我的孝子贤孙”。*铁儿:《论承继之不近人情》,《竞业旬报》第29期(1908年10月5日),第1-5页。该文又题作《论承继之非理》,刊《安徽白话报》第1期(1908年10月5日),第4-7页。文字略有差异。胡适批判家族承继中的陋习,成为其十年后鼓吹“大我”观念的滥觞。也许更重要的是,此时的胡适已立足于“社会”,重新思考人的“不朽”。
必须承认,此一时期的胡适对于“社会”并没有更多论述,相较说来,“爱国”是这一时期其言说的重心所在。他有一篇《爱国》的文字,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一个人本分内第一件要事,便是爱国。”文中还引述了荷马史诗的一句格言:“为祖国而战者,最高尚之事业也。”*铁儿:《白话(一)爱国》,《竞业旬报》第34期(1908年11月24日),第6页。亦有论者阐明:这一时期胡适所崇尚的美德之本,“一言以蔽之,就是爱国”。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1部《璞玉成璧,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138页。在《本报周年之大纪念》中,胡适又集中阐述了面对时势的危机、国民的愚暗,他和朋友们宁可劳心劳力来办这份报,正是寄望于国民“革除从前种种恶习惯”,“革除从前种种野蛮思想”,“要爱我们的祖国”,“要讲道德”,“要有独立的精神”。*胡适:《本报周年之大纪念》,《竞业旬报》第37期(1908年12月23日),第4-5页。
胡适投身《竞业旬报》的编辑、撰文工作,使他成为“民国前革命报人”的代表之一。*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1页。但就当时的社会改革与思想启蒙事业来说,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不过,对胡适本人来说,这段经历倒是非同一般。也许最重要的是,胡适在这些文章中把他后来思想成熟后的基本倾向预现出来了,以至他在撰写《四十自述》时,还不无感叹:
今年回头看看这些文字,真有如同隔世之感。但我很诧异的是有一些思想后来成为我的重要出发点的,在那十七八岁的时期已有了很明白的倾向了。*胡适:《四十自述》,《胡适作品集》第1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第71页。
二、“造新因”:“社会改良”主张之酝酿
1910年后在美7年的留学生活,是胡适思想与志业的定型期。到异域留学,首先意味着横跨两种文化,参与两种文化的冲突与对立,这是留学生定位于边缘人的基础。此种在个人价值体系中产生的两面性,文化人类学家许烺光曾作过这样的自省:“我自承是一个‘边缘人’(marginal man)。因为我是在一种不尚变而大半人生都可以全然预测的文化中出生和成长,但我却又在一个好变,并以变为进步的文化中生活和工作。介于这两种完全不同文化生活中的人……可以体会出两种不同文化面在内心相互摩擦的边界。”*许烺光:《中国人与美国人》,徐德隆译,台北:巨流出版公司,1988年,第20页。对此的检讨参见章清:《近代中国留学生发言位置转换的学术意义——兼析近代中国知识样式的转型》,《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许的这番自省,有助于认清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在接触到两种不同文化时所产生的“问题意识”。紧扣“社会”这一概念,也可发现胡适围绕此是如何思考相关问题的。
“余每居一地,辄视其地之政治社会事业如吾乡吾邑之政治社会事业,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动,社会改良之事,辄喜与闻之。不独与闻之也,又将投身其中,研究其利害是非,自附于吾所以为近是之一派,与之同其得失喜惧,……此种阅历,可养成一种留心公益事业之习惯。今人身居一地,乃视其地之利害得失若不相关,则其人他日归国,岂遽尔便能热心于其一乡一邑之利害得失乎”?*《留学日记》卷十五,“1916年11月9日”,《胡适全集》第28卷,第481页。这是胡适对自己在美国生活的概括,很显然,来到一个不一样的“社会”,胡适除了获得观察新社会的机会外,还意味着其思想与志业也正是在这样随时随地潜心观察中得以成型。*胡适这些经历所获得的启示是他在上海的经历所无法比拟的,正像1915年他离开寄居五年之久的绮色佳时在日记中所说明的:“吾尝谓绮色佳为‘第二故乡’,……此五年之岁月,在吾生为最有关系之时代。其间所交朋友,所受待遇,所结人士,所得感遇,所得阅历,所求学问,皆吾所自为,与自外来之梓桑观念不可同日而语。其影响于将来之行实,亦当较儿时阅历更大。”见《留学日记》卷十一,“1915年9月21日”,《胡适全集》第28卷,第271页。到美国后不久,胡适在一通信函中,对读书人之介入“社会”于成长大有意义就有这样的描绘:
天下学问不必即在校舍讲堂之中,不必即在书中纸上,凡社会交际,观人论世,教人授学,治一乡一国,皆是学问也。社会乃吾人之讲坛,人类皆吾人之导师,国家即吾人之实验室也。*胡适:《致章希吕》(1911年12月15日),《胡适全集》第23卷,第35-36页。
基于可以理解的缘由,留美时期胡适更为关注“国家主义”的问题;他对此也有不少检讨,并以“大同主义”进行对抗。换言之,胡适所思考的问题,居于国家层面的较多。不过在此期间,“社会”也同样构成胡适思考问题之重点所在。在一则札记中胡适描绘了其如何逐步走向“社会”。他先是表示:“吾之去妇人之社会也,为日久矣。”这里所谓的“社会”,显然指向其幼时之生活环境,指明其所受教益全系“诸妇人(吾母、吾外祖母、诸姨、大姐)陶冶之功”。进一步的,他将进入澄衷学堂,视作“投身社会之始”。原因在于,“居澄衷之第二年,已敢结会演说,是为投身社会之始”。而最近之十年,“遂令余成一社会中人,深于世故,思想颇锐,而未尝不用权术,天真未全漓,而无高尚纯洁之思想,亦无灵敏之感情”。*《留学日记》卷四,“1914年6月8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329-330页。这里传达的对“社会”的看法,是外在于“家庭”的。而且,言语之间其对于“社会”不无负面的看法。前日的一则日记,胡适即指明“吾国之家庭对于社会,俨若一敌国然”。*《留学日记》卷四,“1914年6月7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329页。与此相应的,这一时期胡适留下的文字,也对中国社会如何组织起来有所考量,并揭示出其中之流弊。在《政党概论》这篇文字中,胡适述及其在美国之感受,就指出政党之功用正体现在:“遂令人人心目都知有国家,而暂忘其省界、府界、县界,种种界限。”*胡适:《政党概论》,《留美学生年报》第3年本(1914年1月),第60页。对于“省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胡适在一则日记中也有所反省:“留学之广东学生每每自成一党,不与他处人来往,最是恶习。”*《留学日记》卷七,“1914年9月28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518页。
更为重要的是,留学期间胡适对于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已结合“社会”这一因素有大致的定位,并不断进行反省。一则札记里胡适就表示:“余近来读书多所涉猎而不专精,泛滥无方而无所专注,所得皆皮毛也,可以入世而不足以用世,可以欺人而无以益人,可以自欺而非所以自修也。后此宜痛改之。”*《留学日记》卷三,“1914年1月25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261页。这里所谓之“入世”“用世”,乃过去时代的读书人思考问题的常用语,与“社会”意思相近。*有必要强调的是,在获得“社会”概念之前,中国读书人并非没有相关问题的论述,也有与所谓的“社会”发生关联的一幕。尤有甚者,与“社会”密切相关的“天下”与“世”,还堪称构成中国读书人思考的重心所在。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及宋儒围绕“格致诚正,修齐治平”阐述的看法,凡此种种,皆构成读书人成就功业的关键所在。相应的,所谓“入世”与“出世”,也构成检讨中国文化、分析过去读书人的焦点所在。参见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4年。不过,无论是“天下”,还是“入世”与“出世”之“世”,所指向的“外部世界”往往是虚指,与“社会”概念的具象化,不可相提并论。两年以后,胡适在日记中,即立足于“社会”规划其未来的角色。一则日记就表示:“自今以往,当屏绝万事,专治哲学,中西兼治,此吾所择业也。”为此还特别强调:“吾所贡献于社会者,惟在吾所择业耳。吾之天职,吾对于社会之责任,唯在竭吾所能,为吾所能为。吾所不能,人其舍诸?”*《留学日记》卷九,“1915年5月28日”,《胡适全集》第28卷,第148页。后面这段话,稍后胡适在日记中又再录了一遍,以自警。*《留学日记》卷十,“1915年6月16日”,《胡适全集》第28卷,第159页。
可以说,胡适在美国进行着“为他日国人导师之预备”时,“社会”已构成关键性的概念。尤其重要的是,胡适对于中国之变革当立足于“社会革命”展开,也有所认识。“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语出《孟子·离娄》,胡适在日记中多次引述这句话,也成为其解决中国问题所确立的基本信念的写照:当致力于探索治本之道,惟有在“社会”层面多下功夫,才能慢慢地为中国造下“不能亡之因”,造下能产生新的结果的新的原因。
在《论“造新因”》这篇英文札记中,胡适就表达了其所关注的重点,强调吾辈之职责,体现在准备必要的先决条件——即“造新因”(create new causes)。*《留学日记》卷十二,“1916年1月11日”,《胡适全集》第28卷,第297-298页。只是这样的“新因”,这里并没有清楚论述。接下来的《再论造因》札记(给老友许怡荪的信)中,胡适就阐述了所谓“造因”的含义:“适近来劝人,不但勿以帝制撄心,即外患亡国亦不足顾虑。倘祖国有不能亡之资,则祖国决不致亡。倘其无之,则吾辈今日之纷纷,亦不能阻其不亡。不如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庶几犹有虽亡而终存之一日耳。”在其看来,面对当下的危机,青年学生纷纷扰扰,也于事无补,重点应思考如何从“根本”下手,“造不能亡之因”。为此胡适也给出了其对此的基本方针:“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又重复原来的话说:“明知树人乃最迂远之图,然近来洞见国事与天下事,均非捷径所能为功。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为迂远而不为,则终亦必亡而已矣。”*《留学日记》卷十二,“1916年1月25日”,《胡适全集》第28卷,第306页。
对于如何“造新因”,此时的胡适显然不能说已了然于胸,但其中留下值得观察的重点,那就是胡适确信这个“新因”,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为此,他也更偏向于在思想文化层面做长期的努力。胡适对晚清以降思想演进的评价,就体现出这样的用心。
在梁启超结束14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归国之际,胡适即感慨地说:“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他还表示:“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留学日记》卷四,“1912年11月10日”,《胡适全集》第27卷,第222-223页。像这样颂扬梁氏之功而轻视孙中山、黄克强诸人之力,并把文字之功尽归梁氏一人,实属偏宕,但正反映出胡适已深信对中国问题的解决,观念的变革当是比武力更根本的措施。正是秉持这样的认知,在《非留学篇》这篇也许是胡适留学时期最重要的文章中,他就严厉批评中国的留学政策偏重实业而轻视文科是“忘本而逐末”:“吾国人所受梁任公、严几道之影响为大乎?抑受詹天佑、胡栋朝之影响为大乎?晚近革命之功,成于言论家、理想家乎?抑成于工程之师、机械之匠乎?吾国苟深思其故,当有憬然于实业之不当偏重,而文科之不可轻视者矣。”因为有这样的自觉,胡适对其角色也有这样的期许:“留学生不独有求学之责,亦有观风问政之责。”*胡适:《非留学篇》,《留美学生年报》第3年本(1914年1月),第13、20页。
以思想文化建设作为“造新因”的基础,成为胡适留学期间最主要的收获。胡适在日记中还曾记录他与英文教师的一段对话,老师问“中国有大学乎”,胡适“无以对也”。老师表示:“如中国欲保全固有之文明而创造新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识皆无所附丽。国之先务,莫大于是。”这正是胡适当日考虑最多的,他也发愿说:“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撰写好此一札记的第二日,胡适仍难以平静,为此再表感叹:“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留学日记》卷九,“1915年2月20-21日”,《胡适全集》第28卷,第56-57页。不仅如此,胡适还将思想文化建设视作政治改革的基础。在给一位大学教授的信中,他就写道:“通向开明而有效之政治,无捷径可走。”其个人对此的态度是,不管怎样,总该以教育民众为基础,惟其如此,才能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之基础”。*《留学日记》卷十二,“1916年1月31日”,《胡适全集》第28卷,第315-316页。
胡适在留学期间一再言及“七年病求三年之艾也”,正可以看出其思想与志业是如何进行定位的。其一再论述的所谓的“造新因”,也是确信惟有通过教育使民众逐步觉悟而后实行缓慢的改革,才是治本的不二法门。尽管没有立足“社会”进行更多论辩,但结合胡适在留美期间的所思所想,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其对此的基本考量:中国之病在于“社会”,拯救之道也须着眼于“社会”。
三、“恶社会”下守望“不朽”
胡适在留学最后阶段留下这样的记录:“吾数月以来,但安排归去后之建设事业,以为破坏事业已粗粗就绪,可不须吾与闻矣。何意日来国中警电纷至,南北之纷争已成事实。时势似不许我归来作建设事。”*《留学日记》卷十七,“1917年6月9日-7月10日”,《胡适全集》第28卷,第565页。胡适有这样的担忧,也算不辜负其获得的“知国内情形最悉”的赞誉。在他留学美国这段时间,中国正经历着一场重大变革。在人们还没有从旧王朝覆灭的“震惊”中走出时,热闹非凡的民主宪政很快如昙花一现。白鲁恂(Lucian W. Pye)曾形象地用“共和幻像”(phantom republic)描绘革命光辉的式微,揭示出甫经成立的中华民国,不仅未能重建社会秩序,反倒加速了社会整合的危机。*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Ed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p.3.这也难怪,一个古老帝国在以往行之有效的统治方式随着王权的崩溃骤然失去效应后,要在较短的时间重建社会秩序,既不可能,也不现实。聚焦于“社会”这一关键词,也可看出危机的具体表现。在“社会”已构成中心话语之际,“恶社会”这一提法频频出现,就显示出对于“社会”往往偏向负面的评价。影响所及,用心于“社会”的改造,也成为主导性的思潮。归国后的胡适,在此背景下“暴得大名”,成为受各方关注的人物,其对于“社会”的思考也不乏值得检讨的地方。
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办一向被视作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陈独秀发表的作为发刊词的《敬告青年》,就言明之所以将目光投向青年,是缘于惟有青年“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文章谨陈六义,供青年抉择,其中之一为“进取的而非退隐的”,明确阐明:“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第4页。陈鼓励青年向“恶社会”进行抗争,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人,也随处感受到“恶社会”施加的种种压力,1920年顾颉刚致函罗家伦,就表示自己的事业能否顺利开展,有赖于相应的“境遇”,“倘使因为生计的逼迫,世俗的牵掣,埋首在恶社会里头,便永远没有这种的希望了”。*顾颉刚:《致罗家伦》(1920年5月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附录一”,第520页。鲁迅小说《端午节》中也曾描绘身处“恶社会”下的读书人,不免时时疑心“自己没有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所以瞒心昧己的故意造出的一条逃路,很近于‘无是非之心’,不如改正了好”。*鲁迅:《端午节》,《小说月报》第13卷第9号(1922年9月10日),第1页。
针对“恶社会”的指控甚嚣尘上,胡适也不例外。1918年6月《新青年》出版的“易卜生专号”上,其撰写的《易卜生主义》,同样立足于“社会”的负面意义阐述了看法,充满对“社会”的控诉:“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故此,“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第490-507页。针对当时的学生卷入种种运动,胡适也视作是“变态的社会”硬逼出来。*胡适、蒋梦麟:《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新教育》第2卷第5期(1920年1月),第592页。此外,他还表彰吴虞对于斯时社会所做的示范,是敢于向“恶社会”宣战:
先生廿年来日与恶社会宣战,恶社会现在借刀报复,自是意中之事。但此乃我们必不可免的牺牲——我们若怕社会的报复,决不来干这种与社会宣战的事了。*胡适:《致吴虞》(1920年9月3日),《胡适全集》第23卷,第309-310页。
如同1924年一篇短文发出的感叹:“恶社会,恶社会,这种声浪简直成了廿世纪的一句口头禅了。好好的一个社会,为何这样不满人们的意,是诚令人大费思索。”作者为此也强调:“社会的不良,就是人们不善的结果。社会是人们的影子,人们是社会的根源。先有人们的不善,后有社会的罪恶。”*程觉非:《恶社会》,《近思》第17期(1924年4月),第21页。很显然,“恶社会”之说广泛流行,很大程度上是现实政治之令人失望所造就。但不管原因如何,这毕竟影响到读书人的角色定位,所谓“打破政治救国的迷梦而从事于社会事业”,也成为读书人普遍的追求。*燕生:《反动中的思想界》,《晨报副镌》1922年5月25日,第1-2版。发表于《新潮》杂志的文章,尽管将“思想改造”作为优先的选择,但也明确将“社会改造”作为长远的目标。参见吴康:《从思想改造到社会改造》,《新潮》第3卷第1号(1921年10月1日),第27页。
1915年中华书局聘请梁启超任《大中华》杂志主任撰述,梁所撰《发刊辞》就试图说明政治不是事业的全部,“政治者,社会之产物也,社会凡百现象皆凝滞窳败,而独欲求政治之充实而有光辉,此又大惑也”。相应的,梁也将该杂志定位于“赞助我国民从事个人事业社会事业者于万一”。*梁启超:《发刊辞》,《大中华》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20日),第14-16页。次年在与记者谈话中,梁又明确指出:“非亟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此着虽似迂远,却是必要的。为此他同样引述了孟子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畜,终身不得”。《纪梁任公先生谈话》,《大中华》第2卷第8期(1916年8月16日),“附录”,第1页。又见《与报馆记者谈话》,《饮冰室合集》第4册,“专集之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3页。成立于1919年7月1日的少年中国学会,更清楚地昭示了类似的选择。作为学会灵魂的王光祈,区分出不同的改革方案,明确说明“吾辈所主张者”有二:其一,就政治改革论,则为“社会的政治改革”,反对“政治的政治改革”;其二,就社会改革论,则为“社会的社会改革”,反对“政治的社会改革”。*内中还指出:“知第一义者”,今日在野人物中共有四例:黄炎培与胡适之,另二人梁启超与汪精卫,属“知之而不能守者”。“知第二义者”,求之于邻国,亦共有四例:一为创造帝国基础之福泽谕吉、嘉纳治五郎;一为树立劳农根基之托尔斯泰、俄国大学生。王光祈:《“社会的政治改革”与“社会的社会改革”》,《少年中国》第3卷第8期(1922年3月1日),第53页。该会对于会员也提出不可与“政党接近”的要求,王光祈为此还明确表示:“本会主张社会活动,反对政治活动,为本会精神之所在。”*《少年中国学会规约修正案》,《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第62-63页。这也成为当时读书人普遍的坚守。翻阅吴虞的日记即可发现饶有兴味的一幕,此一时期吴每年在日记中差不多都要宣示其宗旨乃“专主研究学术,不问政治”。*1917年吴就写道:“余去年即有不入党、不任主笔之宣言,今年又加不谈政事一条。处此乱世,总以不开罪于人、少与人交涉、和光共尘、不露头角为要。”1920年他又强调:“予平日宗旨不入党,不任主笔,不以文字谈法律、政治,近年尤以不涉足政界为要件。”参见《吴虞日记》上册,“1917年6月11日”“1920年9月25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5、557页。杨树达则以个人的经验表明,当日读书人每以从政为畏途,“见纯洁士人一涉宦途,便腐坏堕落,不可挽救,遂畏政治如蛇蝎”。*杨树达:《杨树达文集之十七——积微翁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页。
将目光聚焦于“社会”,也引出时人对中国现状的思考。傅斯年发表在《新潮》第1卷第2号上的一篇短文《社会——群众》,就提供了独特的视野——直指中国实际处于“无社会”的状态,“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际的绝少,大多数的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凡名副其实的“社会”,体现在有“密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对比中西就不难看出:“西洋人所凭托的社会,是健全的,所以个人的能力,有机会发展;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只是有名无实,所以个人的能力,就无从发展”。*傅斯年:《社会——群众》,《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第345-347页。这里傅区分“社会”与“群众”,尤其强调中国实际处于“社会其名,群众其实”的情形,正是试图阐明就中国来说仍系“无社会”之状。当然,与其说傅指称中国“无社会”,毋宁说其更为关切应该建构一个怎样的“社会”。实际上,差不多同时傅留下的另一份文稿,就说明“社会”如何受到读书人特别的关注:“中国人从发明世界以后,这觉悟是一串的:第一层是国力的觉悟;第二层是政治的觉悟;现在是文化的觉悟,将来是社会的觉悟。”文中尤其强调:“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了。”*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原件藏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此据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第203-221页。
在“社会”成为广为关注的话语之际,胡适又阐述了怎样的见解呢?有一点值得重视,尽管胡适对国内的情形不算陌生,但毕竟甫回国不久,尤其还缺乏对现实社会更多的体验,因此这一时期胡适对“社会”的讨论更多是在“表达”层面,较为突出的是,他在价值的追求上颇为重视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前述《易卜生主义》,堪称斯时宣扬个人主义最倾动一时的文章,就显示出胡适所关注的,集中于“社会”对“个人”的摧残:“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individuality),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耐人寻味的是,这篇高扬个人主义的文章,并没有把个人的价值视作目的本身,相反胡适在论证中仍将“社会”置于更高地位,而“个人”只是作为再造“新社会”的分子:“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文章还借用易卜生的话指明“个人”价值是如何通过“社会”得以实现:“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第490-507页。
到1919年胡适所写的《不朽——我的宗教》,又进一步阐述了有关个人与社会的观点。文章特别阐明了对“社会的性质”的认知——“社会是一种有机的组织”,无论是从纵剖面,还是横截面,都可看出“社会”这一特质:从纵剖面看,“没有我们的祖宗和那无数的古人,又哪里有今日的我和你?没有今日的我和你,又哪里有将来的后人”;从横截面看,“若没有那样这样的社会,决不会有这样那样的我和你;若没有无数的我和你,社会决不是这个样子”。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胡适声称其宗教信仰是“社会不朽论”,从而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他用“小我”与“大我”来表述,建立起不可分的观念:
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能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胡适:《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第96-106页。
这段时间胡适对“社会”的论述,大致皆围绕此展开。1919年3月筹备中的少年中国学会安排胡适发表讲演,他也强调“少年中国的人生观”当以“社会的公共幸福”为重心,“须要有社会协进的观念”。认识到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和“社会”相关,“自然不肯为社会造恶因,自然要努力为社会种善果”。*胡适:《中国少年之精神》,原刊《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1期(1919年3月1日),此据《胡适全集》第21卷,第165-169页。在为好友许怡荪作传时,胡适也特别表彰许“处处把‘救国’作前提”,其思想也因此不断调整:“从第一时代的‘政治中心’论变为第二时代的‘领袖人才’论”;再由此走向“第三个时代”:“完全承认政治的改良须从‘社会事业’下手。”*胡适:《许怡荪传》,《新中国》第1卷第4号(1919年8月15日),第17-25页。对于好友后来“完全是一个社会革命家”,胡适显然是赞许的。这也映射出不少同时代人的心路历程,胡适自己的走向亦未尝不是如此。
进一步的,胡适还倡导一种“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他明确表示:其所主张的是“‘社会的’新生活”——“变旧社会为新社会”的生活。胡适特别指明有一种所谓“独善的个人主义”,“很受人崇敬”,却“格外危险”,其共同性质是:“不满意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如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文章将此归纳为四类:一,宗教家的极乐国;二,神仙生活;三,山林隐逸的生活;四,近代的“新村生活”。在胡适看来,这种种“个人主义”,“根本错误在于把‘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分作两截;在于把个人看作一个可以提到社会外去改造的东西”。为此他也强调须秉持这样的“根本观念”:“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从改造这些造成社会、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新潮》第2卷第3号(1920年4月1日),第467-477页。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也表示:“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因此,须立足于“政治上的影响”“社会上的影响”“思想上的影响”对“主义”进行评估。参见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7月20日),第1版;《四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7号(1919年8月31日),第1-2版。
尚可补充的是,正是对“社会”颇为重视,这一时期胡适也曾针对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阐述其看法。1920年5月,他在北平社会实进会发表演讲时就特别指出:“社会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知道要等到社会里某种制度有了毛病,问题才能发生出来。”这里也延续了对于“社会有机体”的认知:“社会问题不是独立的,他有两种性质:一种是社会的,是成法的,非个人的。比方纳妾问题,决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做成,乃是根于社会制度或祖宗成法而来。一种是个人的,社会问题的发生,虽不在乎个人,然而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他与个人自然有关系。”尤其重要的是,胡适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阐述了来自西洋的经验,那就是“社会的立法”(Social Legislation)。显然,他将之视作最有效的办法,只是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还“不配讲”。对此的检讨,也寄托了胡适的期望:
社会的立法,就是用社会的权力,教政府立一种好的法度。这事我们还不配讲,因为有些地方,不能由下面做上来,还要由上面做下去,……我们由历史方面看,国家是一种最有用的工具,用的好就可以替社会造福。社会改良家一定要利用它,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好些事。*胡适:《研究社会问题底方法》,此系1920年5月15日胡适在北平社会实进会的演讲,许地山记录,原载《晨报副镌》1920年5月26-29日,此据《胡适全集》第21卷,第229-243页。
在“恶社会”下仍守望于“社会不朽”,这也算是胡适自诩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写照。不过,由于此时的胡适对于“社会”的介入并不算深,因此,对“社会”的阐述更多还是在“表达”层面。也正因为如此,这还算不上胡适所固守的主张,相反他还不断在进行修正。最明显的是,到1930年编辑《胡适文选》时,胡适对于《不朽》一文中区分“小我”与“大我”所表达的看法,就作了修正:“这样说法,并不是推崇社会而抹杀个人。这正是极力抬高个人的重要。个人虽渺小,而他的一言一动都在社会上留下不朽的痕迹,芳不止流百世,臭也不止遗万年,这不是绝对承认个人的重要吗?”*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前言”,第12页;又载《新月》第3卷第4号(1931年6月10日),第6-7页。之所以在差不多十年之后修正其对于“个人”与“社会”的看法,原因必多。最基本的是当胡适更多介入到“社会”中,对“社会”自然有不一样的看法。为此也有必要进一步辨析在“实践”层面胡适对“社会”的介入,以及由此催生的其对“社会”的省思。
四、读书人如何介入“社会”
将“社会”作为把握近代历史的关键性概念,除了其作为“话语”得到广泛关注,构成理解这场变局的基本维度,“社会”概念成长的实践意义同样值得重视。原因在于,这些新词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揭示出这个世界的实质,也促成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据此按照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审视外部世界,规划自己的晋升之路。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就描绘了这样的情形:“幼而处家庭,长而入社会”。*梁启超:《论政治能力》,《新民说》24,《新民丛报》第49号(1904年6月28日),第11页。这一直至今日仍在延续的表达方式,正揭示出“社会”对于个体之意义所在。在这个意义上,透过具体的例证揭示“社会”呈现的意义,不无裨益。甚至可以说,开展概念史的研究,值得在这样的“实践”层面多加探索,毕竟包括“社会”之类的新概念,昭示出生活世界的改变。根据一向认为自己不谙社会事务的顾颉刚在日记中的梳理,可知当日读书人所涉足的各种事务,实属不少。*1924年在日记中顾颉刚即曾抱怨“兼职实在太多”,并列举出这样的内容:(1)北大研究所(承担本所事务、纪念册、《国学季刊》、编书等工作);(2)努力社;(3)孔德学校;(4)商务印书馆;(5)亚东图书馆;(6)朴社;(7)北京印书局。在该年12月的一则日记中,顾还列出“我的事务14”:《国学季刊》《歌谣周刊》《学术年表》、清宫整理事务、亚东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北京印书局、孔德学校、朴社、《语丝》周刊、研究所杂事、师友间杂事、家庭杂事、自己读书。(北大纪念册)、(古物报告)。而1925年一则日记中其所列“事务”,更是多达数十项。此外,顾在一则日记中还述及:“以前印了一盒名片,总要用一年多。近三个月来,两盒名片都完了,可见予之渐入世也。”见《顾颉刚日记》第1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1924年3月21日”“1924年12月19日”“1925年8月15日”“1926年6月23日”,第467、562、653-654、760页。而且,顾还提出值得重视的总结,那就是“已为社会上的人”,则身不由己。*《顾颉刚日记》第2卷,“1931年2月7日”,第492页。胡适之介入“社会”,同样值得重视。有论者刻画“民初社会中的胡适”,就致力于在思想史的诠释之外,另辟蹊径,检讨胡适是在怎样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从事学术文化的活动。*沈松侨:《一代宗师的塑造——胡适与民初的文化、社会》,周策纵等著:《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第131-168页。这里要进一步检讨当胡适介入到实际政治中,是否改变其对于“社会”的认知。
胡适归国后抱定“二十年不谈政治,要为中国的政治变革奠定思想文化的基础”,这样的自我期许,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伴随《新青年》的“分裂”,包括胡适在内的原《新青年》杂志一群人,再汇聚知识圈及政治圈中的其他力量,同样走上“谈政治”的“歧路”。1922年5月问世的以“努力”命名的一份杂志,就明确指向对政治事业的图谋。
《努力周报》缘起于胡适、丁文江等于1921年5月组成的“努力会”,目标定位于“谋中国政治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3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74-375页。1921年8月胡适演讲《好政府主义》时,即结合“社会”的改良思考政府的改善:“政府何由而来呢?乃由人民的组织渐渐扩大而来。社会中有家族有乡党,凡团体中之利害,与个人的利害,小团体与小团体的利害,或大团体与其他大团体的利害,均不免时有冲突。”为此,他也将“政府”视作“社会”进步的重心:“政府是指挥大众的公共机关,可使社会上的人减少惰力,而增加社会全体进步的速率;有些个人所不能为的事,一入政府手中,便有绝大的效果。”胡适甚至对“政府”表达了这样的期待:“政府的组织及权力,如果用之得当,必能得着最大的效果;不但可免社会间交互的冲突,而且可促社会全体的进步。”*胡适:《好政府主义》,这篇演讲由甘蛰仙记录,《晨报副镌》1921年11月17、18日,第1版。
胡适之所以创办《努力周报》,除了出于对政府善意的期待之外,还将问题的症结归于“社会”之“中坚”未能尽职。1922年在给罗文幹的信中,谈到北京的秩序已很难维持,胡适就表示:“社会的秩序全靠中级人士为中坚,今中级人士已无守秩序的能力。”*胡适:《致罗文幹》(1922年9月6日),《胡适全集》第23卷,第393页。1923年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胡适也述及此:“我也以为国中中坚人物绝少;系全国重望,而思想属于进取的……尤不可多得。”*《日记》,“1923年5月24日”,《胡适全集》第30卷,第15页。稍后,胡适有机会见到一群浙江二师军官,这些军官向胡适请教该如何做事,他就指出当致力于“组织同志,作个中坚,作个参谋本部”,具体目标即体现在“替社会造一种顺从民意,适应时代潮流的实力”。*《日记》,“1923年9月20日”,《胡适全集》第30卷,第48页。
胡适对于作为“社会”之“中坚”的失望与期待,展现出其对“社会”力量的关切。《努力周报》第2号发表的由16位知名学者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由胡适起草),除了阐明谈论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之外,还明确针对“国内的优异分子”表达了期望,将好人介入政治作为改革当下政治的第一步:“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以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胡适等:《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第2期(1922年5月14日),第1版。以“好人”出来奋斗作为筹码,寄予了那个年代的读书人对于改变丑恶政治的且似乎是最后的努力。这也代表着那个年代读书人共同的识见。早在1917年,梁漱溟即曾写就《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并印成小册子,分送他人。到1918年,梁又将此文通过《学艺》刊发出来。由此可见,“生民之祸亟矣,吾曹其安之乎”是梁漱溟不断追问的问题。*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学艺》第3号(1918年5月),第34-40页。以后梁又将此文重刊于《村治》第1卷第1期(1930年6月1日),“附录”,第1-14页。其晚年口述也以此为题。梁漱溟、艾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此时在给胡适的信中,梁则进一步表示:“今日人民太无生气,好人太无生气,故闹到如此地步。吾曹好人须谋所以发挥吾曹之好者,谋所以发挥人民生气者,则今日恶局势乃有转移,否则将长此终古矣。”*梁漱溟:《致胡适》(约1922年上半年),《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76-177页。
不过,对于自己如何介入“政治”,胡适却是有所保留的。在紧接着发表的文字中,胡适区分出服从政党、表率政党与监督舆论的政论家,就特别褒扬了监督舆论的政论家,强调“社会上确然不应该没有一派超然的政论”,立于各党各派之上,“这种独立的政论家,越多越益,越发达越好”。在其心目中,监督政党的政论家之所以值得特别褒扬,是因为他们是超然的、独立的,“只认社会国家,不认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胡适:《政论家与政党》(误标为“政论家政与党”),《努力周报》第5期(1922年6月4日),第1版。不难看出,这也正是胡适对于自己介入实际政治所做的定位,仍坚守于读书人立足于“社会”的身份。为此,胡适还努力建立起当下读书人与历史上的士大夫密切联系的谱系。这期间他所写的一篇文字,就特别以东汉、两宋的太学生以及明末的东林和复社、几社为例说:“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膊上。”*胡适:《这一周·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努力周报》第38期(1923年1月21日),第1版。1928年5月4日胡适在光华大学演讲,对于五四运动也做了类似评述,并重复其之前反复阐明的看法:“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如果在常态的社会与国家内,国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末,青年学生就无需干预政治了,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班中年人的身上去了”。胡适:《五四运动纪念》,《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觉悟”副刊,第1版。这样也以深文周纳的方式阐明,他与他的同道正是在一个毫无秩序可言的社会,担纲干预政治与主持正谊的责任。
《努力周报》只维持了一年半的时间,该刊1923年10月停刊时,胡适表示只是暂时停办,还道出了其未来的打算:“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胡适:《致高一涵、陶孟和等》(1923年10月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16-218页。但这是未曾实现的目标。接下来的日子,胡适对“社会”的思考又有所调整,尤其是1926年他有机会再度西行,所见所闻,更引发其关注“社会化”问题。
1926年9月,胡适在巴黎与傅斯年相聚,谈及政治就不免有所分歧。胡适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他总希望中国能有一个有能力的Dictator who will impose some order & civilization on us [能整饬社会秩序、再造文明的独裁者]。我说,此与唐明皇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有何区别?况Dictator[独裁者]如Mussolini[墨索里尼]之流,势不能不靠流氓与暴民作事,亦正非吾辈所能堪。德国可学,美国可学,他们的基础皆靠知识与学问。此途虽迂缓,然实唯一之大路也。”*《日记》,“1926年9月18日”,《胡适全集》第30卷,第324页。这里胡适强调德国、美国的基础乃“知识与学问”,虽迂缓,却是“唯一之大路”,可以说延续了其一贯之主张。尽管没有明确表示基于“社会”用力,但其思考的重心却渐渐逼近于此。
在英国时,胡适曾打算将他所写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作为引论,再做九篇文章,汇成一本叫做《西洋文明》的书。内中所涉及的各方面,大致就是胡适斯时心目中的西洋文明。最后一章题作“社会化的世界”,并以此作为思考西洋文明之终结,大有意味。*《日记》,“1926年9月23日”,《胡适全集》第30卷,第342-343页。随后胡适到了美国,在纽约时他曾被邀请参加一个讨论会,听到一个劳工代表说“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好的最伟大的时代,最可惊叹的时代”,胡适也大受感动:“这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向来被压迫的社会分子,能站在大庭广众之下颂扬他的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胡适:《漫游的感想》,原刊《现代评论》第6卷第140、141、145期(1927年8月13日、8月20日、9月17日),此据《胡适全集》第3卷,第36-41页。在给国内朋友的信中,谈及当今世界改造社会的方法,胡适也鲜明表达了对“社会化”方法的肯定:
认真说来,我是主张“那比较平和些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为简单说来,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个方法,我想叫做“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这些信当时分别题作《一个态度》《“新自由主义”》,刊《晨报副镌》1926年9月11日、12月8日;以后又题作《欧游道中寄书》,收入《胡适文存》第3集第1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第73-90页。
“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这些命名,都包含着对“社会化”方法的认同。*《日记》,“1926年8月3日”,《胡适全集》第30卷,第223页。稍后在给太虚的信中,胡适还表示:“先生此次若决计去西方,我很盼望先生先打消一切‘精神文明’的我执,存一个虚怀求学的宗旨,打定主意,不但要观察教堂教会中的组织与社会服务,还要考察各国家庭、社会、法律、政治里的道德生活。”*胡适:《致太虚》(1926年10月8日),《胡适全集》第23卷,第538页。胡适建议太虚将视野拓展到对整个“社会”的观察,显然也是其认同于“社会化”改革的写照。只是,中国如何进行“社会化”的改革,胡适并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看法。这也不难理解,在基本的社会秩序尚未能建立的中国,“社会化”改革自然还难以提上日程。
五、“社会重心”如何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无疑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于胡适来说,《努力周报》阐述的那些诉求,尤其是对社会秩序的重视,此时随着这个新政权的建立,皆部分得以实现。相应的,胡适对“社会”的审视也走向新的一步。一方面,其自我意识中愈发有作为“社会”中人的责任担当;另一方面,在“建国问题”浮出水面之际他也在积极考量如何建设“社会重心”。这期间胡适在《新月》和《独立评论》上发表的论述,即将此呈现出来。
《新月》月刊最初只是偏重文艺性质的刊物,为此胡适等人计划另创办一份《平论》周刊,发表政治方面的一些主张。该刊最终未能刊行,不过《新月》从第2卷第2期起一改过去面目,政论文章占据了重要位置。胡适为计划中的《平论》撰写的一篇文字,也明确点出其用心:“第一,是要想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第二,是要借此提倡一点新风气,引起国内的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胡适:《我们要我们的自由》,《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第25-33页。而在“九一八”引发的“国难”背景下创刊的《独立评论》,更是鲜明表达了这样的期望: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胡适:《引言》,《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第1页。
胡适上述言说,体现出立足于“社会”以立言成为其自觉的选择。因为在《新月》上的文字得到张元济的赞许,胡适就表示:“我的那篇文字,承先生赞许,又蒙恳切警告,使我十分感激。我也很想缄默,但有时终觉有点忍不住,终觉得社会给了我一个说话的地位,若不说点公道话,未免对不住社会。”*胡适:《致张元济》(1929年6月2日),《胡适全集》第24卷,第13页。
守望于“社会”的定位,也促使胡适进一步考量“社会”应有的担当。在蔡元培70寿辰之际,胡适与几位朋友共同商议赠送蔡一处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之所以有此考虑,胡适特别做了说明:“这也可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我们还希望先生的子孙和我们的子孙,都知道社会对于一位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胡适:《致蔡元培》(1935年9月7日),《胡适全集》第24卷,第254页。稍后胡适还曾对汤尔和说起:“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a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胡适:《致汤尔和》(1936年1月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94页。所谓“公人”也成为胡适基本的角色定位,为此他还将创办刊物理解为是对“公家”尽责。主编《独立评论》时胡适经常是一人独立支撑刊物,一直延续了差不多三年时间,但他对此却毫无怨言,反倒乐此不疲,因为这是为“公家做工”,令其“心里最舒服”。*1936年1月9日胡适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就写道:“三年多以来,每星期一晚编撰《独立评论》,往往到早晨三四点钟,妻子每每见怪,我总对她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是我为公家做工,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你可曾看见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吗?’她后来看惯了,也就不怪我了。”胡适:《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96-300页。
胡适自觉守护于“社会”的位置,更突出体现在其婉谢了任职政府部门的邀请。1933年3月,因为翁文灏决计不就教育部长,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思之再三转求胡适担任此职,“明知此是不情之情,但你如果体念国难的严重,教育前途的关系重大,度亦不能不恻然有动于中”。*汪精卫:《致胡适》(1932年3月3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04页。胡适很快回了信,列举了诸多不能就任的理由,特别指明其适合扮演的角色是立于“政府外边”为国家效力。所谓“政府外边”,指的自然是“社会”:
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胡适:《致汪精卫》(1932年4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08-209页。
不仅对个人的规划基于“社会”进行考量,进一步的,胡适也据此出发走向对“社会重心”的思考。《独立评论》围绕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即涉及对“社会力量”的思考。针对丁文江《中国政治的出路》,季廉发表文章进行商榷,提出“要自动组织一个能够肩荷政治责任的团体,要自动设置一个代表民意的机关”。胡适对此主张表示了同情,但他对于现有的“社会力量”却存有疑问:其一,“我们的‘全国各种有信用有实力的职业团体’究竟在哪里”?其二,“现有的各种职业团体又往往是四分五裂,不能合作的”。第三,“现在所谓‘公团’,哪一个不是在党部的箝制之下的”?相对说来,胡适更信任的还是读书人,为此他也表示:“我们只能希望在最近几年之内国中的智识阶级和职业阶级的优秀人才,能组织一个可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并且援助政府的干政团体。”他还具体指明“学术团体”“商人团体”和“技术职业团体”当构成这个“干政团体”的中坚,并且认为“把国中的知识、技术、职业的人才组织起来,也许就是中国政治的一条出路罢”?*胡适:《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独立评论》第17号(1932年9月11日),第1-5页。
紧接着,胡适针对杨公达在《国难政府应强力化》中阐述的主张,又引述一位上海老辈的话:“近年政治不上轨道,当然政府之过,亦因社会宽纵过甚。”对此,胡适也表示:“我们自命负言论之责的人,都应该领受这种很忠厚的劝告。”*胡适:《〈一个时代错误的意见〉附记》,《独立评论》第20号(1932年10月2日),第3-4页。稍后在《国民参政会应该如何组织》一文中,胡适即主张“应该用智识程度较高的法团代表来做预选机关”。在其看来,省市党部代表、省市商会代表、省市教育会代表、省立大学(或国立大学在省区内者)教授会代表、省立律师公会代表、省市总工会代表、省市银行钱业公会代表,属于“法团程度皆较高”,“皆代表社会上相当的权力,故最合宜于做预选机关”。*胡适:《国民参政会应该如何组织》,《独立评论》第34号(1933年1月8日),第2-5页。
与此相应的,对“文治势力”的培养,也构成胡适思考“社会重心”的枢机所在。1930年胡适《我们走那条路》这篇文字引发梁漱溟的意见,胡适在答书中就明确表示其确信,“只有充分养成文治势力”,方能“造成治安和平的局面”。他还具体说明:“当北洋军人势力正大的时候,北京学生奋臂一呼而武人仓皇失措,这便是文治势力的明例。今日文治势力所以失其作用者,文治势力大都已走狗化,自身已失掉其依据,只靠做官或造标语吃饭,故不能澄清政治,镇压军人了。”*胡适:《答梁漱溟书》(1930年7月29日),《胡适全集》第24卷,第48-49页。稍后胡适在日记中对此也有所阐述:
今日所要者,第一,在这中央权力未造成的时候,要明了分权的必要,在分治上或可逐渐筑成一个统一国家。第二,要明了文治势力是制裁武力的唯一武器,须充分培养文治势力。第三,要明了一个“国家政策”比一切“民族主义”都更重要。当尽力造成一些全国的整个国家的机关与制度。*《日记》,“1930年9月25日”,《胡适全集》第30卷,第342页。
胡适所谓的“文治势力”,还包括国民政府中的一些力量。如他对孙科的建言贯彻的即是他所主张的“文治精神”,他始终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大病在于文人无气节,无肩膀,“武人之横行,皆是文人无气节所致”,所以他强调中国政治要上轨道,必须走这三步:第一文治,第二法治,第三民治。*《日记》,“1934年2月5日”,《胡适全集》第32卷,第299-300页。这是立足于当下立言。而从长远看,胡适仍坚守这样的认知: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的进步,国家的力量也靠这个人那个人的力量,“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工夫”。*胡适:《为学生运动进一言》,《独立评论》第182号(1935年12月22日),第4-7页。本文原刊《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12月15日。职是之故,对于“社会重心”的培养,胡适看重的仍然是读书人。在《领袖人才的来源》这篇文字中,胡适便直截了当指出过去的“士大夫”就是“领袖人物”,而今日要充当“领袖人物”不比古代容易,“在今日的中国,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种资格的养成,在今日的社会,除了学校,别无他途”。*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独立评论》第12号(1932年8月7日),第2-5页。这也是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蒋廷黻就写道:“九一八以后,因为大局的危急,国人对知识阶级的期望和责备就更深了。我们靠知识生活的人也有许多觉得救国的责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我们不负起这个重担来,好像就无人愿负而又能负了。”孟森更是试图通过为“士大夫集传”的方式,“使人知士大夫之共有真谛”,并以此唤醒“士大夫”的角色担当,“以自然人为国负责,行事有权,败事有罪,无神圣之保障,为诛殛所可加者也”。参见蒋廷黻:《知识阶级与政治》,《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第15页;孟森:《论士大夫》,《独立评论》第12号(1932年8月7日),第6页。
也正是围绕这些问题的思考,1932年胡适将中国问题的症结归结于“社会重心”的阙失,亦即是本文开篇所提及的一幕。这里可稍加补充的是,胡适不仅将创造“社会重心”作为“民族自救运动”的关键所在,而且对于“这个重心应该向哪里去寻求”,他也给出具体意见,指明这个重心须具有的条件:第一,必不是任何个人,而是一个大的团结;第二,必不是一个阶级,而是拥有各种社会阶级的同情的团体;第三,必须能吸收容纳国中的优秀人才;第四,必须有一个能号召全国多数人民的感情与意志的大目标;第五,必须有事功上的成绩使人民信任;第六,必须有制度化的组织使其可以有持续性。无论如何,胡适所要试图阐明的是:“我们要御外侮,要救国,要复兴中华民族,这都不是在这个一盘散沙的社会组织上所能做到的事业。”*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11-13页。有必要说明的是,对于“社会重心”的建构,其他读书人也不乏关注,只是着眼点有所差异。傅斯年即从“第三权力”对此有所说明。在其看来,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的根本不同处在于,中国社会之中坚分子不过是作为统治者贵族阶级工具的士人,而欧洲社会之中坚分子是各种职业中人。欧洲中世纪以来也有一个知识阶级——僧侣(clerical),但并非统治阶级的伺候者,且这个阶级还自成一个最有组织的社会。尤其是在中世纪的大城市还有不少“自由人”,以其技能自成一社会。相应的,在贵族之“无常权力”(temporal power)、僧侣之“精神权力”(spiritual power)之外,产生了一种“第三权力”。参见傅斯年:《教育崩溃之原因》,《独立评论》第9号(1932年7月17日),第2-6页。
结语:“社会”作为力量的浮现
以胡适为个案,结合“社会”概念在中国世界的浮现,以及不同时期针对此进行的思考,可以明确的是,近代中国的读书人与“社会”之关联,确实发生了颇大的变化,这同样可视作“三千年来所未有之变局”。当然,与“社会”的关联往往依托于不同的“媒介”,不同时代相应烙上不同的印痕。晚清以后新型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即改变了普通人沟通“社会”的“媒介”。以印刷书刊来说,往往确立“取重于社会”的目标,也构成那个时代读书人通向社会之阶梯,全面影响到读书人基本的生活。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即曾将其参与组织《新社会》旬刊视作其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6页。关于此的分析可参见章清:《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新型传播媒介的浮现与读书人新的生活形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关键尤在于,“社会”一词不仅构成近代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动的写照,还构成读书人思考问题新的方向,那就是关注“社会”各种力量的成长,并且追求基于“社会”的变革。
相应的,此一时期种种社会运动也颇为引人瞩目。举例来说,“启发社会的力量”,就成为推动乡村建设的重心所在。*《朝话——启发社会的力量》,《乡村建设》第4卷第7、8期合刊(1934年10月11日),第1页。内中阐明:“我们的事业,就是启发社会的力量,使死的散漫的变成活的团聚的社会,没有力量变成有力量。要让社会有力量,须打通地方上有力量的人的心。”梁漱溟表达了这样的用心:“乡村建设运动必始终保持其社会运动的立场,而不变为国家的或地方的一种行政,乃得完成使命。”*梁漱溟:《广西国民基础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国民基础教育丛讯》第1号(1935年3月),第37-38页。这与胡适基于对当政者善意期待所规划的方案,适成对照。之所以如此,缘于在梁那里,“中国此刻最高唯一的国家权力尚未树立起来”,故此,地方自治,“实非政府所能力,天然是一社会文化运动”。*梁漱溟:《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原刊《山东民众教育月刊》第4卷第9期(1933年11月25日),此据《梁漱溟全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45页。在1937年出版《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中,梁也是据此提出其设想:“假令中国社会将来开出一个新组织构造的路子来,一定不是从国家定一种制度所能成功的,而是从社会自己试探着走路走出来的,或者也可叫做一种教育家的社会运动,或也可说社会运动者走教育的路开出的新构造。”换言之,“乡约组织不可以借政治的力量来推行,至少他是私人的提倡或社会团体的提倡,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来推行,政府只能站在一个不妨碍或间接帮助的地位,必不可以政府的力量来推行”。*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9、167页。
勾画胡适作为“社会”中个体的代表,也揭示出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读书人对于“社会”的认知。可以明确的是,胡适在30年代提出对“社会重心”的思考,构成其思考“社会”问题的结晶。但相比于其他方面的言说,胡适对“社会”的论述并不算多。对于胡适较少涉及“社会”之论述,自有其逻辑在。那就是胡适认定中国当务之急乃“建国问题”,“国家有了生存的能力,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有渐渐救济解决的办法”。当外患侵入,国家陷入了不能自存的地步,“一切社会革命的试验也只能和现存的一切政制同受敌人铁蹄的蹂躏”。因此,在逻辑上他也认为“社会”问题还难以提上日程:“欧洲人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这个建立国家的大问题,因为他们的国家都是早已成立的了。因此他们能有余力来讨论他们的社会问题、生产问题、分配问题等等。然而在我们这国内,国家还不成个国家,政府还不成个政府;好像一个破帐篷在狂风暴雨里,挡不住风,遮不得雨;这时候我们那里配谈什么生产分配制度的根本改造。”*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第2-7页。如果说晚清之际梁启超在其所译介的各种价值中确立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优先性,在胡适活跃的年代,以“建国”为优先,可谓“同调”。然而,正是这种基于优先性的选择,却导致自由、平等的价值不能得到充分肯定,社会力量的培养也难以受到重视。
问题的关键还体现在,胡适对于“社会重心”的培育也是缺乏信心的。1928年4月高梦旦因为不堪商务印书馆内部的矛盾纠纷离开商务,他对胡适说:“我们只配摆小摊头,不配开大公司。”此语也引来胡适好一阵感叹:“此语真是说尽一切中国大组织的历史。”他也表示,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纯粹个人主义的民族,只能人自为战,人自为谋,而不能组织大规模的事业。考试是人自为战的制度,故行之千余年而不废;政党是大规模的组织,需要服从与纪律,故旧式的政党(如复社)与新式的政党(如国民党)都不能维持下去。岂但不能组织大公司而已?简直不能组织小团体,“我们只配作‘小国寡民’的政治,而运会所趋却使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我们只配开豆腐店,而时势的需要却使我们不能不组织大公司——这便是今日中国种种使人失望的事实的一个解释”。*《日记》,“1928年4月4日”,《胡适全集》第31卷,第23-24页。
因此,胡适对“社会重心”的关注,恰表明对于中国社会的变革,其所思所想仍立足于上层展开。他既把批评时政视作像他那样的读书人应尽的社会责任,也同样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当政者身上,并善意地期待当政者能倾听读书人发出的声音。除了公开的议政外,通过与上层人物的接触以实现图谋,也构成其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并沉醉于“君以国士待我,我必国士报之”。*此处无法展开,对于胡适参与政治的检讨,笔者在其他文字中已有所讨论。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修订本),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既然如此,胡适所期许的“社会重心”的建设,也难以取得真正的成效;读书人也难以在“社会重心”的建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实际情形恰如费孝通在40年代末针对读书人所表达的感叹:“以整个中国历史说,从没有一个时期,在社会上处于领导地位的知识阶级曾像现在一般这样无能,在决定中国运命上这样无足轻重的。”*费孝通:《论知识阶级——“从社会结构看中国”之二》,《观察》第3卷第8期(1947年10月18日),第15页。究其原因,正可归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一老生常谈。关乎此,已涉及对近代中国建构“社会”各种力量的评说,并且当结合国家-社会的架构思考这样的基本问题:在国家政权建设中是否推动着“社会力量”的成长;抑或是“社会力量”在国家政权建设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或许需要在别的文字中再详加论述。
(责任编辑:史云鹏)
“Creating New Causes”: Hu Shi's Reflections on Constructing“the Focus of Society”
Zhang Qing
“Society” as a key concept in understan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of the early 20thcentury has been drawing the attention of many researchers. On the one hand, it is important to grasp terms like “society”, and its reception depends on how we understand it. On the other hand,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other sense of “society”, that is, the “great change” it reflects, the pivot from which we can underst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 the exploration of this concept casts light on our re-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nd people in that period.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cholars of that time, Hu Shi and his use of “society”, his planning of role as social member, his analysis of basic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etc.,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dimension from which the concept of society can be revealed.
society, the focus of society, fitting into community, provincial borders, various professions
章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 200433)
K26
A
1006-0766(2017)03-00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