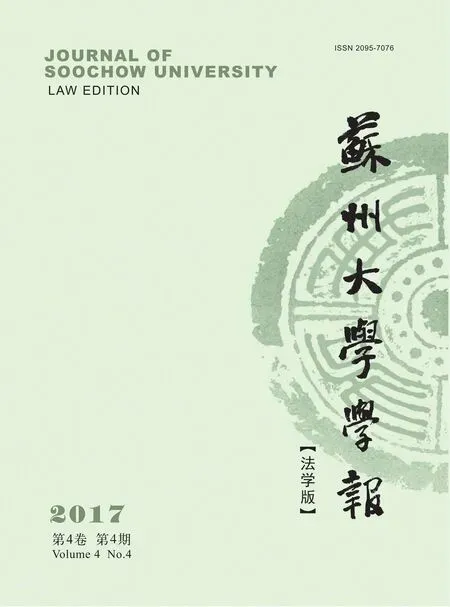不作为犯的成立要件*
[日]桥爪隆 著 王昭武 * 译
不作为犯的成立要件*
[日]桥爪隆**著 王昭武***译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要件,尤其是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是学界争论焦点。首先,作为成立要件,如果存在作为可能性与结果避免可能性,就不必再重复探讨“构成要件上的等价性”。其次,要认定作为义务,必须存在结果的避免实质性地取决于行为人这一状况,即存在对结果原因的支配;而且,另外还有必要考虑那些应该将制约行为人的自由、赋予其一定的作为义务予以正当化的因素,例如,先行行为等危险创造行为、同居在一起的亲子关系、行为人的地位或者职责等。
不作为犯;不真正不作为犯;先行行为;作为义务;结果避免可能性
一、引言
“杀人的”(《刑法》第199条),以杀人罪处罚。对此,一般的理解是:这里所谓“杀人”,不仅是指以作为方式杀害他人的情形,还包括怠于进行必要的保护等,以不作为的方式招致死亡结果的情形。①原本对于这种理解本身就提出质疑的,参见松宮孝明:《刑法総論講義〔第4版〕》,成文堂2009年版,第88页以下;井上宜裕:《不真正不作為犯と罪刑法定主義》,载《立命館法学》第327、328合并号(2009年),第115页;等等。这样,对于杀人罪、放火罪等一定的犯罪类型,判例、通说承认可以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但对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要件,尤其是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各种观点相互对立,呈现出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尽可能地明确学说之间的对立点,并据此提出笔者的一点思考。
二、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要件
(一)与作为义务的等价性的关系
在探讨作为义务之前,首先想就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要件的全貌,简单做些确认。对于不真正不作为犯,一直以来普遍认为,仅限于与该当于该构成要件的作为犯相比,能够被评价为,在构成要件上具有等价值的情形,才能认定该不作为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等价性要件)。另一方面,对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也不是针对所有人的不作为,而是只有那些负有作为义务的人(保障人)的不作为,才该当于构成要件。对于这种等价性要件与作为义务的关系,既往的多数学说是将二者作为不同的要件来理解的。亦即,首先要肯定具有作为义务,在此基础上还要求,对于违反作为义务的不作为,能评价为与作为形式的构成要件该当行为具有相等价值。①持这种理解的学者,参见内藤謙:《刑法講義総論(上)》,有斐閣1983年版,第234页;大谷實:《刑法講義総論〔新版第4版〕》,成文堂2012年版,第140页;曽根威彦:《刑法総論〔第4版〕》,弘文堂2008年版,第204页;川端博:《刑法総論講義〔第3版〕》,成文堂2013年版,第235页;等等。并且,我们也可以说,有关作为义务的“形式的三分说”,就正是以这种体系性理解为前提而主张的。传统的通说观点一直是将法令、契约、条理(包括先行行为)作为产生作为义务的根据来理解的。然而,如果原样适用这种理解,对于能认定具有民法上的扶养义务、契约上的安全考虑义务等义务的情形,就会极为宽泛地科以作为义务。为此,为了适当地限定处罚范围,就通过“构成要件上的等价性”这一要件来进一步予以限缩。
不过,本文倒以为,鲜有进行这种二阶段的限定(二重限定)之必要。这是因为,之所以有必要通过“构成要件上的等价性”来限定处罚范围,原本就是因为,“形式的三分说”宽泛地认定了作为义务。然而,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应该是起始便实质性地判断是否存在作为义务,仅限于那些能认定具有“构成要件上的等价性”的情形,才认定具有作为义务,这样即可。因而鲜有勉强采取这种二阶段的判断之必要。②与之相对,佐久间修则认为,在确定存在刑法上的作为义务违反的基础之上(作为外部界限的不作为),另外再研究是否与该状况之下的作为犯具有同价值性(等价值性),这样就相对更能限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性。参见佐久間修:《刑法総論》,成文堂2009年版,第80页。当然,这终究不过是一种体系上的整理方法而已,即便分开探讨作为义务与等价性,也许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认为,等价性是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实质,那么,不考虑是否具有等价性,而要从其他视角来划定作为义务的内容,显然是困难的。“构成要件上的等价性”不是作为义务之外的其他要件,毋宁说,应该将其理解为,作为义务的实质性产生根据。③持这种理解的学者,参见大塚仁:《刑法概説(総論)》,有斐閣2008年版,第157页注14;林幹人:《刑法総論》,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版,第158页;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84页;松原芳博:《刑法総論》,日本評論社2013年版,第89页;等等。而且,这意味着:不应通过法令、契约、条理来宽泛地承认作为义务,而是应该从实质性角度来限定那些被科以作为义务的情形。
另外,对于等价性要件,有观点指出,其具有作为构成要件之区别标准的意义。④参见萩野貴史:《不真正不作為犯における構成要件的同価値性の要件について(3)》,载《名古屋学院大学論集》第51卷第4号(2015年),第230页以下。这种观点特别设想的情形是,不作为的杀人罪与保护责任者遗弃(不保护)致死罪之间的区别。⑤本文无法就此问题展开详细探讨,但就一般性案件而言,两罪的区别应取决于是否存在杀人罪的故意(参见后述最决平成17年〔2005年〕7月4日刑集59卷6号403页)。例如,即便是不保护被害人而致其死亡的情形,如果该不作为不具有可以对应于作为形式的杀人行为的危险性,就应该以不具有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上的等价性”为理由,否定成立杀人罪,而止于成立保护责任者遗弃致死罪。这就是该观点之典型主张。⑥持这种旨趣的主张,参见大谷實:《刑法講義総論〔新版第4版〕》,成文堂2012年版,第142页;等等。的确,这种情形也并非不能想象:要成立不作为的杀人罪,一般认为,作为处罚的前提,以存在被害人死亡的具体危险性为必要,因此,在虽能认定存在针对生命的抽象的危险性,但具体危险性并不充分的状况下,就不成立不作为的杀人罪,而是成立保护责任者遗弃致死罪。⑦例如,虽然只有针对生命的抽象的危险,但由于其后介入了各种各样的情况(介入因素),最终发展至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并且,能认定当初的不作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对于这种情形,也只要作为作为义务的内容来加以说明即可:杀人罪中的作为义务,是为了避免针对生命的具体危险性而科处;保护责任者遗弃致死罪中的作为义务,是为了避免较之相对要低的危险性而科处。为此,对于此类情形下,完全没有必要特意提出“构成要件上的等价性”这一要件。①主张通过等价值性来区别二罪的观点,也许是以相当宽泛地承认保护责任者遗弃罪中的作为义务为其前提的(例如,对于将被害人丢在现场放任不管的逃逸案犯,也承认存在作为义务),但这种前提本身原本就是存在疑问的。就此问题,参见佐伯仁志:《遺棄罪》,载《法学教室》第359号(2010年),第102页。
(二)结果避免可能性的意义
这样,在不真正不作为犯中,违反作为义务的不作为,被评价为实行行为。并且,要对这种不作为认定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理所当然以不作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必要。就作为犯而言,若实行行为的危险性实现于结果,就认定存在因果关系,但在不作为犯的场合,由于不作为本身并未创造出引起结果的危险,因而其实现危险的样态也多少有些不同。所谓不作为的危险,就在于行为人没有避免原本可以避免的危险,因此,应该避免的危险未能避免,反而实现于结果的场合,就能认定存在“危险实现的关系”。②例如,对于若放任不管就有死亡的危险的伤者,负有将其送往医院予以救护之义务的行为人,没有救护伤者,导致伤者就此死亡的,在该场合下,行为人应该避免的针对生命的危险,由于行为人的不作为而未能解消,反而是原样实现于结果,因而能认定这种不作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进一步而言,作为这种“危险实现的关系”的前提,应该要求存在结果避免可能性。③例如,在注释(10)的案例中,如果是虽然立即将伤者送往了医院,但也未能挽救伤者的生命,那么,对此也并非不可能评价为,行为人未解消的危险在结果中得到了实现(实现于结果)。在此意义上,作为不同于“危险的现实化”的另外的要件,要求存在结果避免可能性(条件关系),作为对于要件的整理来说,可能更为适当。关于这一点,参见山口厚:《刑法〔第3版〕》,有斐閣2015年版,第47页注24。例如,被告人对被害少女注射了兴奋剂,被害少女由此陷入错乱状态,被告人将被害少女扔在宾馆房间自行离开,结果导致被害少女死亡,对此,最高裁判所认为,“如果被告人立即请求急救医疗……该少女十有八九有可能得救”,因此,“该女的得救是切实的,达到了超过合理怀疑的程度”,并以此为理由,判定本案的置之不管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认定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适当的”(最决平成元年〔1989年〕12月15日刑集43卷13号879页)。正如反复指出的那样,④例如,山口厚:《刑法総論〔第2版〕》,有斐閣2007年版,第79页。所谓“十有八九”,其含义并不是如文字所示的80%至90%,而是作为一种习惯表述,是“切实性达到了超过合理怀疑的程度”的另一种表述。⑤参见原田国男:《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元年度),法曹会1991年版,第385页。为此,就应该理解为:作为实体法上的要件,要求的是“原本是有可能得救的”,也就是,要求的是死亡结果原本是有可能避免的这样一个事实,而且,其证明程度达到了“超过合理怀疑的程度”。⑥更为详细一点说的话,这里想指出的是,在最高裁判所平成元年(1989年)的案件中,问题不在于与“延续生命”之间,而在于与“得救”之间探讨避免可能性。对于死亡结果,应该根据那个时点那个样态来具体把握,因此,在作为因果关系的问题来把握的场合,通过请求急救治疗(即便最终很难得救)而得以延续数日生命的,在该情形下,以此为根据认定存在因果关系,也并非不可能(在作为犯的场合,即便没有改变死因,而只是有意识地提前了被害人死期的,当然也能肯定因果关系)。尽管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但在本文看来,毋宁说,这并非因果关系的问题,而是“在仅仅只是有望延续生命的场合,就对行为人赋予作为义务,这一点能否得以正当化”这一视角的问题。而且,如果认为,只要探讨与“延续生命”之间的避免可能性的问题即可,那么,几乎所有场合都能认定存在结果避免可能性,在结论上也是不妥当的。
这样,在采取“作为实体法上的要件,以结果避免可能性为必要”这种观点的场合,例如,负有作为义务者虽然预见到死亡结果,却怠于采取必要的急救措施,结果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对于此类案件,在即便立即请求急救治疗,也不能说切实能够得救的场合,就不成立不作为的杀人罪。那么,这种场合是否也不成立杀人罪未遂呢?对于这一点,西田典之教授认为,既然我们根本就无法想象出能够避免结果的作为,那么,也就不能认定存在作为实行行为的“不作为”,自然也不能成立未遂犯。⑦参见西田典之:《不作為犯論》,载芝原邦爾等编:《刑法理論の現代的展開 総論Ⅰ》,日本評論社1988年版,第74页。然而,所谓未遂犯,只要存在构成要件该当事实被现实化的危险,就得以成立,因此,即便不能认定因果关系,也并非就此直接否定未遂犯的成立。①参见山口厚:《刑法総論〔第2版〕》,有斐閣2007年版,第79页注21。也许西田教授的意图在于:在不能防止结果的场合,就是对行为人科以了作为义务,那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结果避免可能性不仅仅是因果关系的内容,还应该作为作为义务的前提要件而发挥功能。不过,即便是从事后来看,属于根本无法避免结果的情形,但是,在进行事前判断之时,对于那些能认定具有避免结果之一定盖然性的情形,不管怎样,首先赋予其采取能减少结果发生之危险的结果避免措施,还是有其充分的合理性的。②关于这一问题,参见仲道祐樹:《不作為における「可能性」》,载高橋則夫等著:《理論刑法学入門》,日本評論社2014年版,第51页以下。按照这种理解,如果存在能够避免结果的一定的盖然性,就以此为前提,被科以作为义务,因此,怠于履行该义务的场合,就有成立未遂犯的余地。对于这种“一定的盖然性”的判断材料、判断标准等,最终会归结于如何区别未遂犯与不能犯的问题。③针对这一点的探讨,参见奥村正雄:《不作為犯における結果回避可能性》,载《同志社法学》第62卷第3号(2010年),第14页以下。另外,按照这种理解,对于前述最高裁判所平成元年(1989年)的案件,尽管不能说,如果立即请求急救医疗,就能够切实地避免死亡结果,但如果存在避免结果的一定的希望,那么,就可以成立保护责任者遗弃罪等犯罪;反之,如果在被害人陷入错乱状态的阶段,就已经无计可施,已经几乎没有得救的可能性,那么,原本就不能认定存在保护责任。
(三)作为可能性
在具体状况下,即便被科以了作为义务,但如果行为人没有作为可能性,仍然不成立不作为犯。对于结果避免可能性与作为可能性,时常看到混同二者的情况,但实际上,我们应该这样定位:二者属于不同的要件。例如,负有救助溺水小孩之作为义务者,没有实施救助行为,小孩最终溺水身亡,在该场合下,如果行为人原本就不会游泳,而且,也很难立即请求他人实施救助,则没有作为可能性,不成立不作为犯。相反,如果即便实施救助行为,也不能说,能够切实地避免死亡结果,那么,就不具有结果避免可能性,但(如前所述,如果处于存在成功得救的一定盖然性的状况之下)留有成立未遂犯的余地。为此,在分析具体的案件时,如果能认定行为人具有作为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作为行为人被赋予的作为义务,我们能够设想到,是存在具有避免结果之希望的结果避免措施的,那么,通过假定这一点——即,作为行为人的作为义务,行为人可以采取有避免结果之希望的结果避免措施——就能认定存在结果避免可能性。
另外,与作为可能性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就是作为义务的内容的问题。例如,在上述小孩溺水身亡的案件中,负有救助义务的父亲,虽然一定程度上会游泳,但游泳能力并未达到可以救助他人的程度,如果跳入水中救助小孩,也存在针对自己的生命、身体的危险。这种情形下,应如何处理呢?赋予作为义务不应该达到让行为人承受重大危险的程度,因此,在该场合下,大多应否定父亲存在作为可能性。但是,显然也不能说,甚至到了父亲基本无需承受危险的程度。即便存在诸如患上感冒、腿部受伤等多少会伤害身体的危险,有时候还是应该优先保护小孩的生命。对此,我们无法提出一般性标准,只能是通过考虑针对被害人的法益侵害的程度与危险、伴随于救助行为的危险性的内容、结果避免可能性、是否存在替代手段、作为义务的强弱程度等因素,个别地进行判断。④学界多将这种考虑表述为“作为的容易性”(即“作为的难易程度”——译者注)。不过,虽然不过是表述的问题,但不应该认为:只要稍微伴有困难或者危险,就不成立不作为犯。另外,杉本一敏将这种考虑定位于“负担的要求可能性”这一视角之下。参见杉本一敏:《不作為犯の結果回避可能性》,载高橋則夫等著:《理論刑法学入門》,日本評論社2014年版,第44页以下。
该问题凸显于这样的场合:存在数个大致具有避免结果之希望的措施,但与各个具体的措施相伴的危险或者困难也有所不同。例如,被告人带着自己的小孩B与A同居在一起,在A殴打B之际,被告人没有加以制止而是放任不管,结果B被A殴打致死,对此,札幌高判平成12年(2000年)3月16日判时1711号170页判定,被告人成立伤害致死罪的不作为方式的帮助犯。在该场合下,被告人可以采取的措施有:(1)接近A与B,为了让A不再对B实施暴力而进行监视;(2)用语言制止A的暴力;(3)挺身而出制止A的暴力。该判决具体分析了这三种行为所具有的避免结果的盖然性程度,以及各种行为可能伴有的针对被告人的不利益,这种做法是值得参考的。既往学说的关注点原本仅限于,是否会发生(原本应被赋予实施某种作为的义务的)作为义务,但在解决具体案件之时,确定该作为义务的具体内容,也是很重要的。①这一点与过失犯的情形是相通的:在过失犯中,不仅仅是注意义务的存在与否的问题,具体分析被科以了何种义务,这一点也很重要。
(四)小结
有关上述探讨的结论,下面简单地做些归纳:
在行为人被科以避免法益侵害之作为义务的状况之下,就有必要在那些具有避免结果之盖然性的措施之中,考虑可能给行为人造成的不利益的程度、危险性(作为可能性),明确应科以其何种作为义务。并且,要将法益侵害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在实施了应被赋予义务的作为的场合,还要求存在能够切实避免法益侵害结果这种关系(结果避免可能性)。如果满足了这些要件,就没有必要重复探讨“构成要件上的等价性”。
另外,还有一点想特别予以确认:对于不真正不作为犯,不得无视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不避免结果的不作为,有必要在该日语表述本身的语意的可能性范围之内,为法条的用语所包摄。例如,明知被害人正感到恐惧,却对被害人置之不管,要将其评价为不作为的胁迫,作为“胁迫”这一用语的解释来说,是很难做到的。②当然,言行等举动本身有时候也能被评价为“胁迫”,但那应该被评价为作为方式的胁迫。参见冨高彩:《強盗罪における不作為構成(2·完)》,载《上智法学論集》第54卷第3=4号(2011年),第76页以下。判例中,不真正不作为犯成为问题的案件,限于杀人罪、保护责任者遗弃罪、放火罪、诈骗罪等特定犯罪类型,这也是因为受到了这种法条用语的文理解释的制约。③有关判例的概要,参见西田典之等编:《注釈刑法(1)》,有斐閣2010年版,第292页以下(佐伯仁志执笔)。在此意义上,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解释也具有作为各论问题的一面。
在这种前提之下,下面再具体探讨最为重要的问题即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问题。
三、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
(一)探讨的展开
传统学说一直以法令、契约、条理这三种类型作为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如前所述,这种观点的前提是:通过“构成要件上的等价值性”来限缩处罚范围。在其后的学说中,毋宁说,下述主张更为有力:明确那些能认定具有“构成要件上的等价值性”的具体情形,仅限于这些情形才承认具有作为义务。这里重视的是,尽可能地排除规范性考虑,从事实的视角,并且,根据一元的标准,来明确作为义务的根据。④有关相关学说的展开,参见塩見淳:《作為義務の成立根拠》,载塩見淳:《刑法の道しるべ》,有斐閣2015年版,第30页以下。
作为事实的视角,首先重视的是先行行为。日高义博教授认为:对于不作为犯,要认定具有“构成要件上的等价值性”,有必要跨越不作为本身并不具有原因力这种结构上的鸿沟(gap),为此,限于“能认定(不作为者事先)设定了原因的场合”,亦即,事先通过自己的先行行为“自己设定了指向法益侵害的因果进程的场合”,才有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之可能。⑤参见日高義博:《不真正不作為犯の理論》,慶応通信1979年版,第154页。针对日高义博教授的这种观点的批判是:(1)不过是先行行为自己设定因果进程,仅此还无法认定不作为与作为之间具有等价性;(2)一方面,只要存在先行行为就总是存在作为义务,这样会使得不作为犯的成立范围过宽,另一方面,没有先行行为就不成立不作为犯,又会使得处罚范围过窄。①例如,中森喜彦:《保障人説》,载《現代刑事法》第41号(2002年),第6页;西田典之:《不作為犯論》,载芝原邦爾等编:《刑法理論の現代的展開 総論Ⅰ》,日本評論社1988年版,第87页;山口厚:《刑法総論〔第2版〕》,有斐閣2007年版,第87页;等等。不过,“自己创造出危险者负有消除该危险的义务”这种感觉本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考虑也会影响到此后的学说。
此后,受到重视的事实的要素是“保护的接受”。按照堀内捷三教授的观点,父母之所以负有保护子女(小孩)的生命的作为义务,是因为通过“保护的事实上的接受”(亦即,事实上接受了对于被害人的保护——译者注),子女(小孩)的生命依存于父母的保护。具体而言,根据(1)用以维护、存续法益的行为的开始,(2)该行为的反复、持续,以及(3)排他性的确保,就能肯定作为义务。②参见堀内捷三:《不作為犯論》,青林書院1978年版,第254页。同样重视“事实上的接受”的观点,参见浅田和茂:《刑法総論〔補正版〕》,成文堂2007年版,第159页。对于堀内教授的这种观点的批判是:如果“法益的保护依存于行为人”这一点是重要的,那么,就不应该限于实施了“保护的接受”的场合。③例如,将因交通事故而受伤的被害人安置在自己的汽车内,被害人的生命由此就依存于行为人,其时,这种法益的依存关系,不会因为行为人是意图保护被害人还是打算将被害人遗弃在某处而有所不同。参见西田典之:《不作為犯論》,载芝原邦爾等编:《刑法理論の現代的展開 総論Ⅰ》,日本評論社1988年版,第89页;山口厚:《刑法総論〔第2版〕》,有斐閣2007年版,第87页。不过,这种观点重视“行为人若不予保护,就无法维持、存续法益”这种依存关系,这一点为此后的排他性支配说所承继。而且,在其后的理论研究中,对于“保护的接受”这一视角的研究也有所深入,已经意识到这种行为在属于保护法益的行为的同时,也属于创造针对法益的(潜在的)危险的行为。例如,行为人将倒在马路上的被害人安置在自己家中予以保护,在该阶段实施的是保护法益的行为,但与此同时,如果就此放任不管,那么,该行为同时又属于创造危险的行为。这是因为,明明存在第三者实施救助的可能性,行为人却通过将被害人安置在自己家中,而事实上排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人予以救助、保护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保护的接受”的意义不限于对法益的保护,还具有与先行行为一样,属于创造出针对法益之(潜在的)危险性的行为的一面。④重视这一视角的观点,参见佐伯仁志:《保障人的地位の発生根拠について》,载内藤謙等编:《香川達夫博士古稀祝賀·刑事法学の課題と展望》,成文堂1996年版,第108页以下。
(二)排他性支配说
学界现在的有力观点是所谓排他性支配说。按照西田典之教授的观点,要认定不作为与作为具有相等价值,就以“不作为者将指向结果的因果进程置于掌握之中,亦即,具体地、现实地支配着因果进程”为必要。⑤参见西田典之:《不作為犯論》,载芝原邦爾等编:《刑法理論の現代的展開 総論Ⅰ》,日本評論社1988年版,第90页。基本上持相同旨趣者,参见松原芳博:《刑法総論》,日本評論社2013年版,第91页。按照这种立场,法益的保护依存于行为人的状态,也就是,行为人是否实施保护直接左右着法益的维持、存续这种关系(排他性支配),就成为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
排他性支配说属于从事实的视角合理地限定不真正不作为犯之成立范围的观点,为其后的学说广泛接受。⑥对于以存在排他性支配这种关系为必要这一点,井田良认为,“这是观点基本一致的地方”。参见井田良:《刑法総論の理論構造》,成文堂2005年版,第41页以下。不过,如果将这种观点贯彻到底的话,例如,将与独自居住的行为人毫无关系的乳儿遗弃在行为人家中的,由于除了行为人之外再无其他能保护该幼儿的人,因而难免连这种情形也要认定存在排他性支配,行为人承担作为义务。但是,学界一般认为,这种情形显然不能认定存在作为义务。当然,也许会有这样的理解:在该场合下,只要给警察或者救护机构打一通电话,幼儿就能得到保护,因而考虑到幼儿生命这种法益的重大性,赋予行为人这种程度的义务也未尝不可。⑦明确提出这种理解者,参见井田良:《刑法総論の理論構造》,成文堂2005年版,第43页。但是,人应该享有自由行动的可能性,因而要限制其自由、赋予其一定的作为义务,就必须存在某种实质性根据。仅凭(违反本人意志)偶尔取得了针对“完全毫无关系的他人”的排他性支配,还不应该赋予这种作为义务。①进一步而言,这里的前提性理解是:即便科以行为人向警察等通报的义务,但对于不履行这种义务的不作为,也不应该将其作为与作为方式的杀人罪等之间具有等价性的行为,而予以处罚。为此,多数说认为,即便基于这种理解,排他性支配具有重要意义,但仅此尚不足以成为赋予作为义务的根据,在此之外,还另外需要某种“附加要件”。②参见島田聡一郎:《不作為犯》,载《法学教室》第263号(2002年),第113页。并且,西田教授本人也在考虑这种“附加要件”,试图由此限定那些能认定具有作为义务的范围。也就是,(1)不作为者基于自己的意思设定了排他性支配的场合,能认定存在作为义务,(2)但对于那些非基于自己的意思而出现排他性支配的场合,则仅限于诸如亲子、建筑物的所有人或管理者等那样,基于特定身份关系、社会性地位,而在社会生活上持续性地负有保护义务的情形,才被科以作为义务。③参见西田典之:《不作為犯論》,载芝原邦爾等编:《刑法理論の現代的展開 総論Ⅰ》,日本評論社1988年版,第91页。对于这两种情形,西田教授将第(2)种情形称之为“支配领域性”,以区别于第(1)种情形(事实上的排他性支配)。与之相对,林干人教授则主张以自己设定了排他性支配作为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参见林幹人:《刑法総論》,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版,第156页。针对这种观点,有学者提出了疑问:尽管通过区分为两类,可以广泛地涵盖那些应肯定作为义务的案件,然而,这种观点立足的是,就作为义务的存在与否应重视事实的视角这样一个出发点,但对于第(2)种类型,最终却是从规范性的视角来划定处罚的界限。④例如,佐伯仁志:《保障人的地位の発生根拠について》,载内藤謙等编:《香川達夫博士古稀祝賀·刑事法学の課題と展望》,成文堂1996年版,第106页。
如果以这种学说的展开为前提,那么,下述观点的登场就是必然的事情:以排他性支配说为前提,同时从“附加要件”的角度,另外还要求存在,以先行行为作为其典型情形的创造危险。按照佐伯仁志教授的观点,要认定与作为具有“构成要件上的等价性”,从指向引起结果的因果性支配这一视角,要求存在排他性支配,并且,作为能例外地将赋予作为义务予以正当化的要素(从保障自由的视角),还要求事先的危险创造(事先创造出了危险),那么,在同时满足了这两者之时,就肯定具有作为义务。⑤参见佐伯仁志:《保障人的地位の発生根拠について》,载内藤謙等编:《香川達夫博士古稀祝賀·刑事法学の課題と展望》,成文堂1996年版,第109页以下;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89页以下。这里所谓危险创造行为,除了诸如先行行为那样积极地引起危险的行为之外,还包括像危险的接受那样,“排除第三者实施救助的可能性,形成自己之外的其他人无法实施保护的状况”。为此,按照该观点,由西田教授加以类型化的“基于自己的意思设定了排他性支配”,就是同时满足“创造危险”与“排他性支配”的要件。
由上可见,在排他性支配说的理论中,(1)对于应该以“指向结果发生的排他性支配”作为必要条件这一点,观点是一致的;不过,(2)围绕还进一步需要的“附加要件”的具体内容,则存在观点之间的对立。并且,学界的批判也正是针对这两点而展开。也就是,(1)作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要件,原本来说,需要排他性支配吗?而且,(2)另外还需要作为附加要件的危险创造行为吗?或者说,对于附加要件,原本来说,能够一元地理解吗?对于这两点,下文想做些探讨。
(三)排他性支配的要否及其内容
排他性支配说作为限制不作为犯的处罚范围的理论,就其出发点来说,当然包含着正当的内容。然而,在本文看来,作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要件,严格要求存在排他性支配,是存在以下问题的:
首先是与作为犯之间的“构成要件上的等价性”。如上所述,在西田教授看来,通过排他性地支配直至结果发生的因果进程,就能认定与作为犯之间具有等价性。然而,如果因果进程的排他性支配能够为等价性奠定基础,理应仅此就能肯定作为义务,鲜有另外再要求诸如“基于自己意思的设定这种附加要件”之必要。⑥关于这一点的分析,另见鎮目征樹:《刑事製造物責任における不作為犯論の意義と展開》,载《本郷法政紀要》第8号(1999年),第349页。可以说,不得不另外要求附加要件,这正好表明,仅凭排他性支配这一点,尚不足以为等价性提供根据。
并且,若严格要求排他性支配,作为义务的认定范围就会受到过度限制。如果我们完全从字面含义来解读排他性支配说,那么,就完全是以存在“排除他人”这种关系为必要,因而必须是,能够避免结果的,只有行为人一人。但是,父亲误将自己的孩子掉入水中,如果周边没有任何他人,父亲当然负有作为义务,但如果现场另有几名毫无关系的他人,父亲则不承担作为义务,这种理解想必是不恰当的。①镇目征树教授也指出了这一点,参见鎮目征樹:《刑事製造物責任における不作為犯論の意義と展開》,载《本郷法政紀要》第8号(1999年),第350页。另外,镇目教授认为,(1)行为人属于能最有效率地采取结果避免措施的主体,并且,(2)可以视为,行为人本人事先选择了处于这种地位,那么,在该场合下,就能肯定作为义务(参见鎮目征樹:《刑事製造物責任における不作為犯論の意義と展開》,载《本郷法政紀要》第8号〔1999年〕,第354页)。对于镇目教授所说的第(1)个要件,可以评价为,是从其他角度来重新把握那些能认定存在支配或者接受的类型。原本来说,在作为犯中,单独正犯的个数也并非总是限定为一人,有时候也有可能认定为同时犯,因此,就是在作为犯中,也没有要求达到因果进程的“排他性”支配的程度。②对于这一点,参见山口厚:《新判例から見た刑法〔第3版〕》,有斐閣2015年版,第40页以下。例如,像“大阪南港事件”(最决平成2年〔1990年〕11月20日刑集44卷8号837页)那样的案件中,即便实施第1暴力的被告人承担伤害致死罪的罪责,对于实施第2暴力有意提前被害人死期的行为人,仍有认定成立伤害致死罪的余地。这是因为,作为的正犯并非总是限于1人。“大阪南港事件”的概要大致如下:被害人因被告人的暴力而陷入昏厥,在被害人昏迷期间,第三人再次施加暴力而致其死亡。在该案中,第1暴力(被告人的暴力)已造成被害人颅内出血,这属于致命伤,第2暴力(第三人的暴力)也许因加剧了颅内出血而稍微提前了被害人的死亡时点(但这只是一种假定,事实上,判决书中也并未认定该事实)。对此,最高裁判所认为,“在犯人的暴力已造成属于被害人死因的伤害之时,即便其后第三者的暴力提早了被害人的死期,仍可肯定犯人的暴力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原判判定本案构成伤害致死罪是正确的”。本案的最高裁判所调查官在判例解说中进一步指出,就相当性说应如何处理这种异常的介入情况,判决并未予以明确,但相当性说是以因果进程的通常性为基准,而实务界是以行为对结果的贡献程度为中心而具体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属于二种不同的思考方法,进而由此引出了“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危机”这一问题。—译者注这样的话,仅限于对不作为犯要求具有排他性,就鲜有此必要。
凸显这一问题的,是过失不作为犯的情形。一直以来,我们探讨不真正不作为犯的问题,脑海中大多考虑的是故意犯的案件,但对于过失犯,当然也能想象出(观念到)不作为犯的问题。③对于这一点,也有观点认为,对过失不作为犯来说,那完全是注意义务的问题,作为义务不会成为问题(参见稲垣悠一:《刑事過失責任と不作為犯論》,载《専修大学法学研究所紀要》第40号〔2015年〕,第6页;等等)。但是,在过失不作为犯中,对于过失犯的结果避免义务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事实上是同时进行判断的。关于这一点,详见橋爪隆:《過失犯の構造》,载《法学教室》第409号(2014年),第117页(译文参见桥爪隆:《过失犯的构造》,王昭武译,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年第1期,第117页以下。—译者注)。并且,对于过失犯罪,也广泛承认过失犯重叠竞合的情形,例如,最典型就是那些监督过失成为问题的情形。④关于这一点,详见橋爪隆:《過失犯における回避義務の判断について》,载《法学教室》第410号(2014年),第146页以下(译文参见桥爪隆:《过失犯中结果避免义务的判断》,王昭武译,载《东方法学》2016年第5期,第144页以下。—译者注)。这里设想的是这样的情形:为了切实地避免法益侵害结果,地位、状况不尽相同的数个参与者,与各自的地位相适应,重叠性地负有作为义务。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不能严格要求因果进程的排他性支配,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⑤其他指出这一点的学者,参见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94页以下;斎藤信治:《不真正不作為犯と作為義務の統一的根拠その他》,载《法学新報》第112卷第11=12号(2006年),第284页;丸山雅夫:《不真正不作為犯の限定原理》,载丸山雅夫:《刑法の論点と解釈》,成文堂2014年版,第15页以下;等等。另外,作为主张不需要排他性支配的观点,参见高山佳奈子:《不真正不作為犯》,载山口厚编著:《クローズアップ刑法総論》,成文堂2003年版,第50页以下(认为那不过是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材料之一)。在直至结果发生的因果系列之中,存在几个有可能左右结果发生或者不发生的要因。对于有关不作为犯的支配性,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在这些有可能发展至结果发生的要因之中,只要达到能够实质性地支配其中的某一个要因的程度即可。作为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山口厚教授认为,问题在于有无“对结果原因的支配”,⑥参见山口厚:《刑法総論〔第2版〕》,有斐閣2007年版,第89页。应该说,在这一意义上,山口教授的这一观点是能够得到支持的。
这样,基于将“对于那些可能发展至结果发生的原因的支配”作为问题的立场,不仅仅是支配特定的被害人(例如,同居在一起的乳儿)的情形,对于管理、支配那些有可能侵害第三者的法益的原因(危险源)的情形,也能肯定作为义务。尽管未必确切,但既往的排他性支配说存在这样一种倾向:研究问题时,头脑中考虑的仅仅是前一种情形。的确,在针对特定的被害人,危险迫近的状况之下,很多时候只要研究是否负有保护该被害人的义务这一问题即可。然而,例如,在没有切实管理猛犬的场合,具体的被害人并未显现出来。但是,对于猛犬逃出咬死咬伤第三者的情形,即便在猛犬实际咬住第三人的阶段没有作为可能性,但仍应该以事前没有切实管理这种不作为作为问题而追究刑事责任。为了切实解决此类案件,对于危险源的管理者、支配者,也应该认定作为义务。①按照这种理解,在当下的学界,将作为义务的内容类型化为法益保护义务与危险源管理义务的观点很有影响(例如,山中敬一:《刑法総論〔第2版〕》,成文堂2008年版,第234页以下;高橋則夫:《刑法総論〔第2版〕》,成文堂2013年版,第157页以下;等等)。不过,这些不过是事实上的类型化,而没有表明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而且,按照这种理解,例如,就制造物、药品等而言,对于那些掌握着有关其危险性的相关信息的人而言,就有从情报(信息)的视角,认定其存在针对危险源的支配、管理的余地。②在所谓“药害艾滋病事件旧厚生省路径事件”(最决平成20年〔2008年〕3月3日刑集62卷4号567页)中,由于有关非加热试剂的危险性的认识,并未在相关人员之间得到充分共享,因而是对于担任生物制剂科长的掌握该信息的被告人科以结果避免义务,肯定成立过失犯。对于该案,主张承认排他性支配的观点也有很多(例如,林幹人:《判例刑法》,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版,第22页;等等),但仅仅是掌握着信息(情报),就肯定具有“排他性”,似乎属于过度的规范化。对于这一点,参见塩見淳:《作為義務の成立根拠》,载塩見淳:《刑法の道しるべ》,有斐閣2015年版,第41页以下;鎮目征樹:《公務員の刑法上の作為義務》,载《研修》第730号(2009年),第13页以下;等等。
另外,岛田聪一郎教授认为,排他性支配并非不作为犯的固有要件,而是将其定位于作为犯、不作为犯的共通要件。也就是,按照该立场,支配着发展至结果发生的因果进程这种支配关系,是(作为犯与不作为犯共通的)单独正犯的成立要件,因此,排他性支配不是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既往学说作为“附加要件”处理的危险创造、保护的有意识的接受,原本才是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③参见島田聡一郎:《不作為犯》,载《法学教室》第263号(2002年),第114页以下、第117页。持基本相同旨趣的观点,参见小林憲太郎:《不作為による関与》,载《判例時報》第2249号(2015年),第4页以下。至少对于那些不作为的单独正犯成为问题的情形,即便作为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而要求存在(以缓和了排他性的形式)排他性支配,而且,即便将其定位于单独正犯性的要件,具体结论也不会有什么不同。问题是不作为的共犯的情形。例如,在不作为的帮助成为问题的场合,按照岛田教授的理解,由于不存在正犯性要件的问题,因而也不会要求排他性支配。④关于这一点,参见島田聡一郎:《不作為による共犯について(2·完)》,载《立教法学》第65号(2004年),第222页以下。但是,例如,白天在周边有很多游客的公园,同居男友向自己的孩子实施暴力的,在这种情形下,该母亲是否应承担伤害罪的不作为的帮助的罪责呢?当然,认定成立帮助犯也没什么问题,也可能有学者持这种观点,但在本文看来,连这种情形也要认定成立不作为犯,就做过头了。对于共犯,我们当然不应该要求其具备与单独正犯相同的支配性要件,但即便如此,还是应该要求存在这样的关系:事实上很难由行为人(共犯)之外的第三者来阻止正犯的犯罪。
(四)科以作为义务的正当化
下面继续探讨“附加要件”的意义。如前所述,即便能认定排他性支配,仅此还不能科以作为义务。对行为人科以作为义务,即赋予其实施一定作为的义务,对于违反该义务的行为人予以处罚,要将这一点予以正当化,就必须存在能够将这种负担予以正当化的某种情况。⑤荻野贵史认为,对于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并未要求负担的正当化,进而以此为理由,对正文中的这种理解提出了疑问(萩野貴史:《刑法学における自由主義と不作為処罰》,载《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法研論集》第132号〔2009年〕,第301页)。尽管尚需进一步探讨,但对于真正的不作为犯,下面这种理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在真正的不作为犯中,对于那些能够将科以作为义务予以正当化的情况,是在将其予以一般性地类型化的基础之上,作为独立的构成要件而规定的。按照这种理解,要求“事前的危险创造”的观点,在学界得到有力主张。⑥参见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90页以下;島田聡一郎:《不作為犯》,载《法学教室》第263号(2002年),第116页以下;小林憲太郎:《不作為による関与》,载《判例時報》第2249号(2015年),第4页以下;等等。对于那些自己创造出针对法益的危险的人,赋予其采取一定的避免措施的义务,以使得该危险不被实现,应当说,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而且,对于“保护的接受”,只要该行为存在行为人通过接受保护,而事前排除第三者实施救助的可能性的一面,那么,(在如果行为人放弃保护的意思,就会转化为危险这一意义上)就可谓之为创造潜在的危险的行为,因此,将该行为评价为危险创造行为的一种类型,也是有可能的。
问题在于,对某人科以作为义务能得以正当化的情形,是否应该限定于这种危险创造行为呢?这里,事前创造了危险这一事实,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毋宁说,这里拷问的是,对于那些对被害法益或者危险源具有一定支配的行为人,科以其采取结果避免措施这种负担的正当性根据。按照这种“负担的正当化”的视角,能够为这种负担提供根据的情形,就不限于危险创造行为。①关于这一点,参见平山幹子:《保障人的地位について》,载川端博等编:《理論刑法学の探求⑤》,成文堂2012年版,第169页以下。按照这种理解,即便没有事前的危险创造行为或者保护的接受行为,通过考虑一定的身份关系或者社会的、法的关系,将科处义务予以正当化,也并非不可能。
典型情况是,父母对年少子女的保护义务。当然,通常情况下,大多能认定存在针对小孩的“保护的接受”。并且,母亲自始就不打算抚养,却生出小孩的,对于这种产子行为,要求危险创造的论者的解释是:明明如此却在家中偷偷产子的行为,就相当于(针对出生的婴儿的)危险创造行为。②参见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93页。然而,在这种情形下,同样自始不打算抚养的父亲是否就不负有作为义务呢?或者说,父母放弃抚养,同居在一起的祖父母代为保护小孩,此后,祖父母将小孩留在家中自己外出,且不再回家的,父母是否又不承担作为义务呢?③对于这些问题的提出,参见十河太朗:《不真正不作為犯の実行行為性について》,载《同志社法学》第56卷6号(2005年),第715页以下、721页。对于此类案件,从危险创造的视角,也许是存在解释的余地的,但与随意地稀释危险创造这一概念,试图一元地解释所有案件相比,直接指出同居的亲子关系有时候会成为承担作为义务的根据,这种解释要更为合适。④如果涉及所有同居在一起的亲子关系,想必过于宽泛。年少的子女、高龄的父母等法益相对脆弱,因而还是应该限于需要得到其他亲属保护的情形(当然,从危险创造或者保护接受这种视角而科以作为义务的情形,则另当别论)。
作为赋予作为义务的前提,要求实施了危险创造行为的观点,是从事实的要素,并且是一元地解释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应该说,这是一种极富魅力的观点。然而,应该对行为人科以义务的情况极其复杂,试图对此全部从危险创造这一视角来一元地予以正当化,想必是有些勉强的。正是基于这个前提,在本文中,以危险创造行为(或者保护的接受)作为应该对行为人科以义务的典型情形,同时又认为,还例外地存在因亲子关系、行为人的地位或者职责等规范性要素而被赋予义务的情形。不过,对于本文这种以事实的要素为中心,同时考虑规范的要素的立场,无论从其他哪一种立场,都有可能提出批判。今后还想就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五)小结
基于本文立场,对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可以进行如下整理:
要认定作为义务,必须存在结果的避免实质性地取决于行为人这一状况,也就是,以存在实质性地支配着那些左右结果之发生或者不发生的要因(之一)这种关系(结果原因的支配)为必要。如果在一定的局面之下,行为人具有左右结果之发生或者不发生的可能性,而且,行为人之外的第三者也不太容易介入该局面,对于这种状况,就应该理解为满足了该要件。为此,不必达到“除了行为人之外,别无其他能够保护法益者”这种意义上的排他性支配的程度。例如,事实性地保护着被害人、掌握着用于保护法益的信息(情报),以及管理着危险的设备等,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这种结果原因的支配之外,另外还有必要加上这样的视角:应该将制约行为人的自由、赋予其一定的作为这一点予以正当化的视角。最典型的就是先行行为等危险创造行为、保护的有意识的接受等,除此之外,还能想到通过考虑同居在一起的亲子关系、行为人的地位或者职责等情况,而应该将科以义务予以正当化的情形。同时满足这两点,由此就能对行为人科以作为义务。
这里想以这种理解为前提,对于几个具体案例,展现这种观点的问题解决思路。首先是前几年的一个最高裁判所判例(最决平成17年〔2005年〕7月4日刑集59卷6号403页)。本案被告人号称自己能进行所谓“瞎鼓捣①所谓“瞎鼓捣”,这是音译,是被告人给自己的所谓医术的命名,并无实际意义。——译者注。”这种民间独特疗法(“瞎鼓捣治疗”),由此来聚集信奉者。A因颅内出血而入院治疗,被告人受A的儿子B的委托,答应给A实施“瞎鼓捣治疗”,并无视主治医师的警告等,命令B等人将处于必须入院治疗这一状态之下的A带出医院,转入被告人所在的宾馆之中。并且,被告人明知如果自己接受B等人之托在宾馆对A实施“瞎鼓捣治疗”而不是让其住院治疗,这样存在死亡的危险,却仍然不让A接受维持其生命所必须的治疗,而是进行所谓的“瞎鼓捣治疗”,最终导致A死亡。对于该案,最高裁判所认为,“被告人因应该归于自己之责的事由而给患者的生命造成了具体的危险,亦即,在患者A被转入宾馆期间,患者亲属B等人因信奉被告人而将A的治疗完全交给了被告人,因而可以认定,被告人处于全面受托治疗重病患者A的地位”,进而以此为理由,认定被告人负有作为义务(最终判定构成不作为的杀人罪)。
对于本案,最高裁判所重视的是:(1)由“应该归于被告人之责的事由”创造了针对被害人的危险;(2)处于“全面受托”保护患者的立场。显然,前者指的是由先行行为创造出危险这一要件,而后者考虑的是排他性支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本决定仅止于指出,能认定该案中存在第(1)、(2)点这两点情况,而并未判定,作为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这两点属于必须具备的要件。②参见藤井敏明:《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17年度),法曹会2008年版,第203页。
按照本文的理解,对于为作为义务提供根据来说,像第(1)点那样,通过指示B而自己创造危险的行为,也不能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即便是因B的专断而将A带出医院,转入被告人所在的宾馆,如果被告人接受了实施“瞎鼓捣治疗”这种委托,同样有认定作为义务的余地。而且,就第(2)点来说,在该案中,相关人员以及A的家属可以自由出入宾馆,并不属于能认定存在“排他性”关系的案件,③作为提出这一点的观点,参见鎮目征樹:《判批》,载山口厚、佐伯仁志编:《刑法判例百選Ⅰ総論〔第7版〕》,有斐閣2014年版,第15页。但即便如此,也足以认定存在“对结果原因的支配关系”。进一步而言,例如,即便A被转入的地方是教团的道场,属于众多信徒一起生活的空间,如果考虑到被告人在该信仰中的地位、支配力等,也完全有可能作为难以由第三者避免结果的情况,而认定存在作为义务。
最后,还想简单谈谈肇事逃逸的有关问题。在肇事逃逸的场合,正是由先行的驾驶行为创造了针对被害人生命的危险性,当然能肯定危险创造要件。但是,在现在的审判实务中,对于将被害人放置在现场自行逃走的这种单纯肇事逃逸,并没有认定成立不作为的杀人罪或者保护责任者遗弃致死罪。④在该场合下,成立驾车过失致死伤罪(《有关因驾车而致人死伤的行为等的处罚的法律》第5条)与违反救护义务罪(《道路交通法》第117条第2款),两罪属于并合罪。东京地判昭和40年(1965年)9月30日下刑集7卷9号1828页虽然判定成立不作为的杀人罪,但其案情是:行为人过失引起车祸,造成被害人重伤,然后出于将被害人送往医院的目的,将被害人搬上副驾驶座,但途中放弃了将被害人送往医院的意图,转而打算将被害人遗弃在适当场所,最终导致被害人在移动过程中死于车内。本文以为,在本案中,除了由先行行为创造危险之外,作为作为义务的产生根据,该案重视的是,将被害人搬入自己车内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⑤另外,对于保护责任者遗弃致死罪,最判昭和34年(1959年)7月24日刑集13卷8号1163页判定,在因过失肇事造成被害人重伤,致使其无法行走的场合,汽车驾驶者就属于保护责任者。但该案也是将被害人搬上自己的车辆之后离开事故现场,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将被害人放下而顾自逃走的案件,而非单纯的肇事逃逸的案件。不过,作为作为义务的一般性要件,判例是否要求“支配的设定”,这一点并不确定。这是因为,对于单纯的肇事逃逸,按照道路交通法上的违反救护义务罪就能予以处罚,因而对于刑法上的不作为犯,就完全有可能仅限于那些较之更为恶劣的案件才予以处罚。按照本文的理解也会认为,即便不必达到排他的程度,但确保对于被害人的支配,这一点对于不作为犯的处罚来说,也是必要的。①在本案中,即便被告人自始便没有将被害人送往医院的意思,而是出于遗弃在适当场所的目的,将被害人搬入自己的车内的,也应该肯定作为义务。不过,没有必要的要求是,将被害人支配在汽车内部这一特定空间之内,因此,如果是在极少有其他车辆或者行为人通过的场所,造成被害人重伤,而后就此逃离的,对于这种单纯肇事逃逸的案件,也有认定作为义务的余地。②肯定这一点的观点,参见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91页;島田聡一郎:《不作為犯》,载《法学教室》第263号(2002年),第115页;等等。进一步而言,由先行行为创造危险,这并非不可或缺的要件,因此,即便是偶尔路过现场的第三者谎称送往医院,而将被害人搬入自己的车辆的,也有肯定作为义务之可能。
另外,行为人过失引起事故,致使被害人身受重伤,将被害人抬入自己车内,然后在严寒的深夜将被害人拽下车,扔在难以被其他人发现的地方,对此,东京高判昭和46年(1971年)3月4日高刑集24卷1号168页判定成立不作为的杀人罪(未遂)。③由于被害人是被偶尔路过的相关人员救助,从而得以挽回生命,因而是否成立杀人罪未遂也成为问题。在本案中,能认定行为人实施了将被害人拽下车的行为,因而也并非没有将该行为评价为作为的实行行为的余地。实际上,例如,如果是在下大雪的深夜,将身负重伤的被害人放在雪中不管不顾,也有可能将该行为本身评价为作为的杀人罪的实行行为。不过在本案中,尚不能评价为,是通过将被害人扔在路边不管的行为而创造了指向死亡结果的新的危险,因而该作为方式的行为并未满足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为此,是否成立不作为犯才成为问题。如前所述,将被害人拽下车之后,被告人并未在空间上支配被害人,但如果被告人之外的其他人难以发现被害人,就能够理解为,满足了支配性要件。再者,在被告人将被害人抬入自己车内的阶段,就已经满足了支配性要件,在车内也已经发生了针对被害人生命的具体危险,并且,如果能认定被告人具有杀人犯意,那么,将汽车运送过程中的不作为也一并作为处罚对象,也是完全有可能的。逆言之,如果本案被告人将被害人放在过往路人很多的地方之后逃离,那么,在放下被害人之后就失去了支配性要件,因此,就会仅以汽车运送过程中的不作为作为处罚对象。
Establishment of Elements of Crime of Omission
[Japan]Hashizume Takashi(Author) Wang Zhao-wu(Translator)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untypical crime of omission,especially the basis for the duty of action,are the backbone of contention in academic society. First,as essentials of establishment,it’s not necessary to discuss the equivalency of constitutive elements repeatedly,if the possibility of action and possibility of avoiding result exist. Second,the affirmation of duty of action must be based on the condition that the avoidance of result depends on the actor substantially,namely,the domination of the cause of the result.What’s more,it’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ose factors that legalize the restriction on the freedom of actor and the infliction of certain duty of action. Examples are danger-creating behaviors such as antecedent acts,parenthood of living together,the status or responsibility of actor,and so on.
Crime of Omission;Untypical Crime of Omission;Antecedent Act;the Duty of Action ;Possibility of Avoiding Result
D924
A
2095-7076(2017)04-0131-12
10.19563/j.cnki.sdfx.2017.04.013
*本文原载于日本《法学教室》2015年第10号(总第421号)。
**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
***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