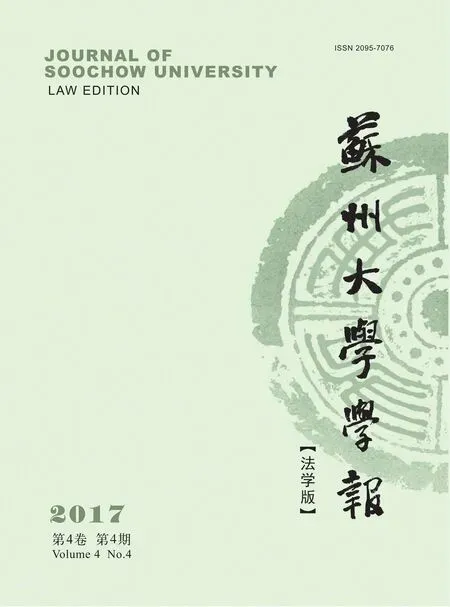监察委员会留置措施研究
秦前红 石泽华
监察委员会留置措施研究
秦前红*石泽华**
对比分析三个试点省市公布之案情和制定的有关规范可以发现,其都集中于批准、备案、执行、期限、权益和衔接等具体问题的探索,这对应留置措施的监督、实施、权益保障和外部衔接,与留置权性质共同构成留置措施的五大关键问题。试点探索透露出全面改革顶层设计或将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严格拆分,若如此,监察委留置措施与逮捕措施和纪检措施之间的工作衔接机制乃至《国家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联动互补,将成为未来立法重点。留置期限可基于科学考量之后适当限缩,借鉴刑事羁押设置一般期限和最长期限。即便调查活动不受《刑事诉讼法》规制,亦须在《国家监察法》中明确“辩护”和“陈述申辩”之差异,并且律师介入当为应有之义;与此同时,留置措施很可能严重影响当事人职务工作,所以构建完整的错案追究机制和救济机制势在必行;留置措施宜加入申诉渠道,此外职级恢复、财产归还和国家赔偿问题亦值得深思。本轮监察体制改革应尽快通过恰当的程序法来规制留置措施。
留置权;留置措施;备案审查;衔接机制;辩护
根据2016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决定,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有权采取留置措施。留置措施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等权益,可以说极为严厉,兹事体大,需从试点地区探索实践之比较出发,逐一分析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3月以来,杭州市上城区监察委、北京市通州区监察委和山西省监察委分别采取了各自试点改革以来第一起留置措施。此外,三个试点省市均制定了专门文件以规范留置措施的有关事项。但各地探索不约而同地回避或未言明留置权之性质,而多从留置措施的批准、备案、执行、期限、权益保护和外部衔接机制等具体问题切入,这些对应留置措施的监督、实施、权益保护和外部衔接,这四个方面又与留置权性质组成留置措施的五个关键问题。试点地区诸多探索绝非无的放矢,可从中探析留置权的性质,并可发现全面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线索。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以留置取代‘双规’措施。”显然,留置措施将成为监察委员会的重要职权,亟待予以规范和规制。在国家监察法制定之际①2017年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草案第41条对留置措施作了初步的规定。,回顾、剖析三个试点省市采用留置措施的情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留置措施的审批和备案
留置措施的审查模式主要是事前审批和事后备案,二者从源头和末端两处根本上影响留置个案正当性。①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羁押为例,第8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事前审查即对“决定适用”的必要性审查,事后审查即对“羁押决定正当性”以及“继续羁押”的必要性审查。参见钱列阳:《羁押必要性审查及律师参与》,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从审查对象看,主要有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要件,前者指根据一定原则规定或标准,若判定符合事先规定的法定情形和情节,则得采取(或者延长、解除)一定期限的留置措施;后者即实施留置的过程应符合程序性规定。事前审批或因留置尚未实施而限于实体审查,事后备案则有可能实现双重审查。从审查本身看,还涉及审查主体(如审查机关和级别等)和审查具体操作问题(如审查期限、文书和驳回后果等)。
(一)留置措施的批准条件和情形
审批制度是留置措施的先期把关程序,必须有严格的批准条件。以山西省留置首案为例,表述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党纪检机关对用语表述普遍严格,采用这一表述者结果多是“对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类比可见采取留置措施一般需要涉嫌犯罪并达到一定证据标准,“涉嫌犯罪”和“一定证据标准”就是情形条件和认定办法。
但笔者认为试点地区监察措施审批制度在批准条件上有两处待改进:第一,法定情形情节须明确。首先,法定情形须明确,如浙江省制定了《浙江省监察留置措施操作指南》,规定的条件是“已立案并且案件具有重大、复杂等四种情形”,但究竟包括哪些情形并不明确;其次,立法表述须客观,避免“可能”“认为”等主观性较浓的表达。第二,原则规则标准须明确。三个试点省市均未明确提及对情节情形的判定办法,所谓“情形”,究竟怎样判断属于这些情形,有没有判断的原则或标准?什么是“情节严重”,如何判断“情节严重”?
(二)留置措施的审批机关和层级
1.试点地区的探索
试点地区就留置措施的审批主体多已有详细规定,如审批机关及其层级等。浙江省留置首案经省委专门指示后由区委书记审批,而《浙江省监察留置措施操作指南》作了更全面的规定,“凡采取留置措施的,需监察委领导人员集体研究、主任批准后报上一级监察委批准,涉及同级党委管理对象的,还需报同级党委书记签批”。北京市留置首案同样是由区委书记批准,《北京市调查措施使用规范》明确规定采取留置措施需“报同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批准,予以立案审查(调查)”,“市纪委市监察委机关对局级或相当于局级的监察对象采取留置措施的,还需报市委主要领导批准”,“区级纪检监察机关对处级或相当于处级的监察对象采取留置措施的,还需报区委主要领导批准”。山西省留置首案由山西省监察委自行决定,在经山西省监察委批准后,运城市监察委采取了留置措施。《山西省纪委监察委机关审查措施使用规范》第八章规定,山西省监察委确需采取留置措施的,应提交省监察委执纪审查专题会议研究决定。
从以上的试点工作,不难归纳以下三点:第一,实践探索大致有自行决定和提请其他机关批准两条路径。山西省探索的路径是省级监察委员会决定自己或批准下级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不过还难以确定县级监察委采取留置措施应经市级还是省级监察委批准。北京市和浙江省探索的是党委审批制度,前者可直接概括为“报同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批准”;后者可抽象为区分对待原则和双重审批制,“普通留置”和“特殊留置”区分对待原则(区分标准为是否“涉及同级党委管理对象”),前者由监察机关自行决定、上提一个级别;后者则须在前一程序基础上再经同级党委书记批准。第二,在非民主决策过程中级别最高的程序通常直接决定了最终结果,故此,浙江省试点探索的留置措施“双重审批制”至少在针对“同级党委管理对象”时,实际上归为党委书记审批制。第三,北京试点公开资料未提及对更低级别公职人员的批准程序,从“还需”表述看,很大可能亦为区分对待原则。可见,北京和浙江两地探索路径基本趋同,差异在于“同级党委管理对象”和“同级党委主要负责人”等具体表述,但从党内组织级别实践来看,前者一般为下一级别公职人员,后者一般为同级党委书记。
2.留置措施的审批机关
北京留置首案公布后,一度引发热议。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员彭新林曾在采访中分析并提出党委书记审批是按程序执行,有助于实现对监察委的监督制约,是对留置措施审批权限、工作流程和方式方法的积极探索;①参见高鑫:《北京“留置首案”释放哪些反腐新动向?》,载《京华时报》2017年6月5日第03版。湘潭大学吴建雄教授认为,留置首案采取党委书记审批乃“改革试点之责任担当”,只是一个特例,有一定实质正当性,但背离了职权法定原则;②参见吴建雄:《北京首例留置案件的法理评析》,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MzEzOTQ4NA==&mid=2654375787&idx=2&sn=0b925fc55daf30d9291eeb2eb202149c&chksm=f2b3b998c5c4308ed37a94e2fe8e36c3cb98b248677493683184a2d0dfb4729068f2d4c15cbb&m pshare=1&scene=23&srcid=0608NJ5mXMIQq2gOSfuEjDIz#rd,上传时间:2017年6月7日,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6月21日。郭相宏教授则以逮捕为参照,援引《宪法》第37条和《刑事诉讼法》第78条,提出将留置的批准权和执行权相分离,分别交由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以实现对监察委员会的有力监督和制约。③参见郭相宏:《对留置措施的使用,批准权和执行权应分离》,载《南方都市报》2017年6月15日第AA15版。
未来较适宜的方案是监察委员会内部决定(批准)或交由司法机关批准,不宜由同级党委书记审批留置措施。摒斥同级党委书记审批制度,并不意味着党领导监察工作的缺失,恰恰相反,党对方针、政策而非个案的领导,是党的执政方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有利于维护党的权威、把握监察工作主动权。一方面,如果检察院决定不起诉或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将导致该案留置合法性存疑、党委审批被质疑,最终损害党的权威④就司法工作而言,如果二审法院改判了一审经过县级或地市党委政法委协调的案件,实际上是使党委政法委陷于被动,会损害党的威信。参见李雅云:《中国法治建设里程碑式的党的文件——纪念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25周年》,载《法学》2004年第9期。;另一方面,建国后曾有一段时期,党委书记审批个案制度盛行,在特定历史时期内造成了大量冤案错案,因此1979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后来被誉为政法领域“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明确提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做法”。⑤余敏声主编:《中国法制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273页。
党委书记审批一定程度上是对领导职能和执法职能的混淆,“在传统纪检监察向现代国家监察转型之后,在党纪委与监察委的关系上,则应坚持‘业务上以监察委员会为主’的原则”⑥李红勃:《迈向监察委员会:权力监督中国模式的法治化转型》,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党纪委和监察委“合署办公”无法回避二者权源和运作机制上的差异:纪委行使监督执纪权,监察委员会行使国家监督权;党的纪律监察委员会由同级党代会产生,监察委员会由同级人大产生。合署办公的科学模式应当是两个委员会“分别产生、领导人员相互交叉、办事机构合并设立和运行”。与党委政法委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应限于方针、政策而非个案的领导一样,党委纪委对监察工作的领导同样应基于一定限度,这个限度就是国家监督执法工作乃国家监察委员会依法独立行使之职权,同级党委不得以个案干预代替原则性指导。
3.留置措施的审批层级
基于国家监察立法定位和原则,试点地区探索的监察委内部决定(批准)留置措施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但须辅以严格的批准机制。
第一,市级及以下监察委员会的留置措施,少有人赞成“自行决定”,多认为应“上提一级批准”或“统归省级监察委批准”。两种方案各有优劣,前者或可提高工作效率,后者则处于对公民基本权利之谨慎处置。大多数学者认为二者必须择其一,我们以为区分对待“采取留置措施”和“延长留置期限”两种情况不失为良计:经上一级监察委员会批准,可采取留置措施;特殊情况需延长留置期限的,经省级监察委员会批准,可延长一次。
第二,省级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是否需中央层级批准?从保证监察效率出发,我们认为省级监察委员会应该有权自行采取留置措施。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第41条规定:“省级以下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应当由监察机关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决定,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省级监察机关决定采取留置措施,应当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备案。”
第三,国家级监察委员当然亦可自行决定采取留置措施。但是,回到备案制度的话题,省级监察委采取留置措施可向国家监察委备案,那么国家监察委采取留置措施是否需要备案呢?否则又如何对其调查活动进行个案规制呢?
4.“集体研究”表述需更加具体
山西省和浙江省在规定有关审批留置措施时,采用了“集体研究”的表述。这一表述比较模糊,可以从三个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首先,所谓“集体研究”的“集体”指谁?是只有正主任和副主任,还是也包括监察委委员?或者是是主任会议还是委员会议?或者未来有没有可能新增类似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集体”?
其次,“集体”全体成员有没有人数底限?比如说如果是主任会议,若是1正4副的配置则是5人,但是他们都有专业经验吗?都熟悉具体案情吗?如果恰好此时副主任职务空缺甚至主任空缺怎么办?
再次,开会到场人数有没有底限或者比例限制?比如说需不需要二分之一以上到场?还有,投票按照什么原则?是一票否决还是普通多数?
(三)备案审查制度有待发挥实效
备案制度是留置措施的最后关卡,为可能的失误提供最后补救机会。根据已有资料来看,试点各地确有考虑监察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如探索执纪监督和执纪审查分设以及监察措施监督问题。浙江省就规定了“对留置宣布、留置调查、留置交接等整个执行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还制定了《关于对说情、过问实行记录、报告制度》,但都限于内部横向监督或者自我约束,未走出同体监督窠臼。就留置而言,本可发挥实效的备案制度却有流于形式之虞。浙江省规定的是“凡使用、延长、解除留置措施的,市县两级监察机关都须报省级监察机关备案,而省监察委则需报中央纪委备案”;山西省规定的是“由案件监督管理室报中央纪委备案”。从表述看,似乎被框定为一种存档流程。
“备案”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向主管机关报告事由,存案以备查考”,有学者归纳指出备案有许可、监督、立法、登记、告知、审批和行政行为七种理论探讨②参见朱最新、曹延亮:《行政备案的法理界说》,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4期。。留置备案制度的争议在于:备案仅作存档之用,抑或备案必然伴随审查?③随着《立法法》的出台和2004年5月全国人大法工委法规审查备案室的成立,备案已经从一种程序性的登记制度演变为一种对立法的审查方式,即“备案审查”。但是,备案机关并无“审查权”,立案备案审查性质也比较模糊。参见王锴:《我国备案审查制度的若干缺陷及其完善——兼与法国的事先审查制相比较》,载《政法论丛》2006年第2期。单纯的备案可能使其价值限缩于“使其知晓”,而难发挥监督实效。从法律正当程序出发,留置措施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单纯备案是不够的(至少就留置而言),所以应当对报送的留置案件进行实体且程序性的审查,对不符合留置条件或违反留置程序性规定的案件及时补救。
留置措施备案制度的比较对象,应该是具体而不是抽象行为的备案制度。有人指出重大具体行政行为备案审查制度蕴含着规范行政权行使的意旨,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面临许多规范层面的难题。①参见陈鹏:《重大具体行政行为备案审查制度的规范阐释》,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5期。留置备案若要发挥审查实效,这些问题值得重视。一个重要问题是:审查发现实体条件不合格或程序缺陷时应当如何补救?这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符合留置条件,但过程程序有缺陷;第二,过程程序无误,但不符合留置条件;第三,不符合留置条件,且过程程序有缺陷。联系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至少在不符合留置条件而被采取该措施时公民可寻求救济。
(四)增设留置特别程序
我国宪法和代表法等对人大代表被拘留和逮捕等问题,规定了人大许可制度和报告制度。人大代表的人身特别保护,是人大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所需的保障之一。我国人大代表不仅是国家公职人员,一般还兼任其他公共职务,囊括于监察委员会“全覆盖”对象之内。留置措施在限制人身自由方面的程度类似于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很可能影响人大代表履行代表职务。未来应修改《代表法》第32条之规定,增设对人大代表采取留置措施的特别保护。但是,这一保护之评判标准,应当为“是否影响人大代表履行代表职务”,而非简单的“是否担任人大代表”;其许可应基于“对逮捕理由依据等进行实质性审查”,而非仅仅是“形式上的一种同意程序”。②参见李莉:《对我国人大代表不受逮捕权的几个问题的探讨》,载《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3期。
由此追问:对于监察委员会委员及其一般工作人员,如何开展监督、是否需要人身特别保障?郑贤君教授借引台湾地区规定,提出他们同为公职人员故亦需接受监督和调查。③参见郑贤君:《试论监察委员会之调查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如果认为监察委员会是类似人民代表大会的民意机关,或者有类似的民意性,基于保障监察委员之履职,其人身当然需要特别保障;至于监察委员会一般工作人员,则无需作此考虑。实际上,对比我国人大代表、法官、检察官的选任程序,在我国选民直接选举下产生的仅有县级及以下人大代表,其余人大代表由下级人大代表间接选举产生;各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系由相应级别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余则由院长、检察长提请相应级别人大常委会任免。我们看到,现状是具有人身特别保障的只有人大代表,不包括法官、检察官。由此,对于监察委员采取留置措施究竟适用何种程序,一方面要从国家反腐效能和监察立法层面进行全盘考虑,另一方面还要基于监察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之属性和身份作仔细思量。
此外,审查留置措施的具体操作问题亦当重视。现有办法集中在审批文书等方面,对于提请采取(延长或解除)留置措施的审批期限、驳回后果,乃至备案审查不合格的后果等,都应考虑到位。
二、留置措施的期限和权限
留置措施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其具体实施可能直接影响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留置措施的实施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分别对应留置期限和权限:期限主要是一般期限、最长(延长)期限和折抵刑期三个层面;权限则主要涉及留置执行过程。借此亦可分析留置措施的性质问题。
(一)适当限缩留置期限
1.留置与其他措施期限比较
《山西省纪委监察委机关审查措施使用规范》第八章规定,使用留置措施时间不得超过90日,特殊情况下经批准可延长一次,时间不得超过90日。《行政监察法》未规定“双指”期限,但在第33条规定行政监察机关的调查期限是6个月,特殊原因延长的不得超过1年;《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28条第2款规定纪委机关的审查时间是90天,经上级纪检机关批准可以延长90天。《人民警察法》第9条规定留置盘查措施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刑事诉讼法》规定拘传不得超过24小时且不得连续拘传,取保候审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不得超过6个月,刑事拘留不得超过37日,逮捕一般不得超过2个月,不同特殊情形可经批准延长1个月、2个月或更长。排除性质显著不同的民法留置、行政拘留和自由刑①“留置”主要是民法而非行政法或刑诉概念,行政拘留是行政处罚、只能类比监察委员会的“处置”权,判处“自由刑”乃人民法院审判权范畴,与监察委员会留置措施从性质上显著不同,故可直接排除之。,可能与留置措施类似的有留置盘查、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和“双规”(“双指”)等五种措施。有一种说法,留置措施从办案实效性考量更可能是用于取代“双规”“双指”的羁押举措,而不同于《人民警察法》第9条规定的留置盘查的临时措施。②参见施鹏鹏:《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侦查权及其限制》,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联系山西省的探索,从留置期限来看,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依据的。
但是,正如陈光中教授指出,一方面“双规”是和《行政监察法》第20条规定的“两指”结合实施的,另一方面《行政监察法》第20条规定“两指”的实施“不得对其实行拘留或者变相拘留”,然而“双规”实际操作通常对被调查人实行近似拘禁长达3个月之久,故而与《行政监察法》冲突。由此其提出,“双规”法治化是用“留置”来代替,还是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结合起来,尚需要作进一步研究。③参见陈光中:《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几点看法》,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可见,“双规”措施具有正当性缺陷,监察委员会的“留置”措施之设置初衷,即很可能为代替“双规”。但是,从“双规”出发进而认知“留置”措施的性质及其合法性,这一认知路径的理论基础尚难自证正当,无法借此对“留置”做出合理评价。④参见秦前红、石泽华:《目的、原则与规则: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法律规制体系初构》,载《求是学刊》2017年第5期。
2.设置“一般期限”和“最长期限”
观察试点探索和以往“双规”“双指”,“双90天”的规定似乎饱受青睐。本文以为,初次留置措施应更注重对公民人身权利之尊重和保障,况且并非所有职务犯罪案件都需如此长期限制自由。不妨参照当前《刑事诉讼法》类似的羁押措施,对留置期限加以限缩,并设置一般和最长期限。
可尝试从刑事拘留和逮捕中汲取有益内核。假设将留置看作逮捕的先行程序,则“刑事拘留”相较于其他强制措施,基于更大程度保障公民实际基本权利之考量,从决定(批准)、执行方式、司法程序衔接乃至对公民权利的限制程度等来看,都与留置措施十分类似。但是,观察试点探索和立法动态,未来留置和逮捕很可能是由监察委员会和人民检察院分别采取的、区分先后顺序的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措施,如此则“刑事拘留”作为一种临时措施与留置还有一定差异,一般期限14日,最长期限37日的设定也恐难为监察立法所采纳。“逮捕”则一般不得超过2个月,不同特殊情形可经批准延长1个月、2个月或更长。
具体规定必须重点考量审批层级、批准情形和条件以及可延长次数等。可作如下规定:经上一级监察委员会批准,可对本级监察对象采取留置措施,一般期限为30天。符合法定延长情形者,经上一级监察委员会批准,可以延长一次30天;经省级监察委员会批准或决定,可以延长一次60天;非经国家监察委员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不得继续延期。就一般案件而言,120天最长留置期限或许是可行的。⑤目前,《监察法(草案)》第41条规定:“留置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采取留置措施的监察机关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一次,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
(二)留置措施的刑期折抵问题
对于刑期折抵问题,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党的纪检机关对党员采取“双规”措施无法折抵刑期。就“双指”而言,根据《行政监察法》第20条规定,合法“双指”措施不包括“拘禁或者变相拘禁”(暂不论具体操作和实践情况),自然也不折抵刑期。彭新林研究员认为:“留置措施限制了被调查人的人身自由,当然应当折抵刑期。可参考刑拘,留置一日折抵刑期一日。”①高鑫:《北京“留置首案”释放哪些反腐新动向?》,载《京华时报》2017年6月5日第03版。有关报道指出山西政法委指导山西省高院制定的《职务犯罪案件证据收集指引(试行)》明确规定了该问题,不过公开资料未透露具体规定。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74条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留置措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程度至少不会低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折抵刑期当属应有之义,后续立法应明确折抵计算方式。基于留置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实际程度,我们认为留置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是合理的。②《监察法(草案)》规定:留置一日折抵管制二日,折抵拘役、有期徒刑一日。
(三)留置措施的执行问题
从试点改革公开资料来看,留置措施执行的探索集中在场所、主体和流程等问题。各地探索涉及的执行流程比较多,如规范流程内容、强制录音录像、安全问题、保密问题和被留置人生活起居等问题。
1.留置措施的执行场所
在执行场所方面,山西省“指定的专门场所”表述稍显含糊,未明确看守所还是纪检委常用的“规定地点”。今年年初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第35条规定“未经批准并办理相关手续,不得将被审查人或者其他谈话调查对象带离规定的谈话场所”,保留了“规定的谈话场所”之表述。该文件发布于监察体制试点改革启动之后,且根据2017年5月2日全国人大网站公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和6月底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家监察法之草案拟定乃“协同配合”中央纪委,可见立法动态更倾向“特定场所”。实际上,只要场所之决定由纪委监察委自行决定,“特定场所”一词的存留并无大的影响——监察委员会自行决定在看守所执行显然可能性极小。问题也正于此:究竟自行决定,还是请公安机关决定?
2.留置措施的执行主体
留置措施是自行执行还是协助执行?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浙江省制度探索中,规定“采取搜查、技术调查、限制出境等涉及人身权利的措施,必须经监察委主任批准,请公安机关协助执行”。我猜想,这种批准和执行分置的探索,出发点可能是这三项措施涉及限制人身权利③狭义的人身自由是指身体活动自由,包括积极作为的自由和消极不作为的自由;广义的人身自由还包括居住和迁徙自由、出入境自由等。我国宪法第37条、第38条、第39条和第40条规定表明,不论是狭义的人身自由还是广义的人身自由,都是我国宪法保护的对象。参见汪进元:《人身自由的构成与限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童之伟:《从若干起冤案看人身自由的宪法保护》,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5期。而纳入监察委和司法机关分工制约机制。这表明,不仅逮捕,公权力机关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权利的其他措施,亦应接受正当程序规制④现行宪法第37条仿效前苏联的突出司法机关的主体模式,过于强调逮捕而忽视其他剥夺人身自由的方式。参见周伟:《保护人身自由条款比较研究——兼论宪法第37条之修改》,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4期。。《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亦作呼应,其第28条规定“审查组可以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提请有关机关采取技术调查、限制出境等措施”。
上述“协助执行”之立法原意,可能有保障基本权利和便于高效执行这两种解释。从第一种解释出发,假如设置留置措施之初衷是用作取代“双规”“双指”的羁押举措,其目的可能是从法律正当程序出发赋予它以更大合法性,而非平白替换之。联系浙江省的制度探索,连限制人身权利严厉程度尚不如留置措施的搜查、技术调查和限制出境等措施,都需要公安机关协助执行,那么,留置措施亦由公安机关协助执行可能更加恰当。如果是基于第二种解释,技术调查、限制出境等措施确实由公安机关执行更加高效,那么留置措施究竟由谁来执行,可能要基于更多因素的考量。
此外,留置执行人员和流程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明确。比如,留置有无通知或类似程序?是否需要两名工作人员在场?是否需要见证人?是否需要出示证件和批文以及如何出示?还有,是否有家属通知程序?是否有告知陈述、申辩、辩护或申请律师的权利等程序?再有,留置期间录音录像的操作者是谁,是否需有律师在场?有程序缺陷的留置措施可否以及如何补正?
三、留置措施的辩护和救济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始终应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价值和目标。留置措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之程度极为严厉,除保证生命健康和人道主义待遇以外,程序性权利亦当重视。一方面留置的行使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正当程序;另一方面还需对包括被留置人在内的当事人之程序性权利进行特殊考虑。所以在国家监察立法中应以专门条款规定当事人权益问题。
(一)贯彻平等原则,保障程序权利
监察程序期间(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之前),程序性权利不应受到任何限制。我国《宪法》第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有罪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中指出“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是人人完全平等地享有的一种最低限度的保证。①《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大会第2200A(XXI)号决议。可见,其一,作为我国公民享有的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权利,在“法庭审判之前”,不因其接受了任何调查或侦查而产生丝毫影响;其二,如果严格区分监察程序和司法程序,从时间顺序看,留置程序还在刑事强制措施之前,故监察程序期间的人权保障程度至少还应在刑事强制措施期间之上,且不因接受监察委员会之调查或可能有职务违纪违法行为或涉嫌职务犯罪,而有丝毫影响。
如童之伟教授指出,我国若干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宪法》保护公民人身自由的程序性条款较多缺失,各法治国家宪法都确认的一些原则我国《宪法》并未确认。②参见童之伟:《从若干起冤案看人身自由的宪法保护》,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5期。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这些问题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后,立法对监察活动尤其是留置措施中保护公民人身自由的程序性条款更应重视。
(二)调查期间的权利保障
1.试点地区的探索
试点地区为保障被留置人权益已探索一系列措施,如保证留置安全等基本成为各地共识,浙江省还探索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这一点从确保证据合法性和保障被留置人权益来看都是必要的,也为当前《刑事诉讼法》所规定;山西省则为被留置人“制定了合理的日常起居计划,严格按计划进行调查和讯问,充分保障了郭海的饮食和必需的休息时间”,一定程度体现了其“依纪依法、保障权利”的基本原则。稍有不足的是,如山西省所称严格维护被留置人“申辩权”,现有信息还不多。
2.监察立法须区分“辩护”和“陈述申辩”
对于已被剥夺人身自由的被留置人,实际保障其获得辩护的权利,才可能有效防止职务犯罪领域冤假错案。观察国家监察立法动态,很可能独立于《刑事诉讼法》而另立监察法律体系。即便留置措施不受刑事诉讼法规制,亦须在国家监察法中明确律师辩护问题。
试点探索的表述采取的是“申辩权”而不是“辩护”。我们猜测这种表述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宪法》第125条有权获得辩护的背景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二是虽然《刑事诉讼法》以专门整章规定辩护与代理事宜,但从目前改革动向来看,很可能将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严格拆分,另设一套法律体系以规制监察程序,由此原有刑事辩护的规定将不适用于留置。在留置措施排除于刑事诉讼程序之外的基础上,回避“辩护”这一刑事诉讼领域的概念是有理由的,但采用“申辩”这一行政法领域的概念明显也不合适,何况申辩可能获取的程序性保护相对于严厉限制人身权利的留置措施来说实在杯水车薪。
3.律师可介入调查程序
无论采纳何种外在形式或语词表达,在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侦查)权系由人民检察院转隶而享有的背景下,既然当前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即可介入,无理由未来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阶段律师不得介入。即便职务犯罪调查活动不接受《刑事诉讼法》规制,未来监察立法亦须明确该问题。借鉴《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当事人自被监察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留置措施之日起,有权申请律师介入;律师应当可以为被留置人提供当前《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41条、第46条和第47条所列举的帮助内容并享有第37条规定之律师权利。①《刑事诉讼法》“辩护与代理”章节有关辩护权益的条款有8条,其中,第38条和第39条是在审查起诉之后,故“侦查”期间涉及辩护权益的有6条。明确提及“侦查”的有3条,分别是第33条、第36条和第37条,规定了申请律师介入的时间限定、帮助内容和辩护律师权利等;间接涉及或仅可能涉及“侦查”的有3条,第41条规定了收集有关材料、申请收集和调取证据、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第46条规定了保密权及其限制,第47条规定了申诉和控告的权利。此外,被留置人的亲属或利益相关人是否得为其申请律师介入,是否可与当事人见面等问题亦须进一步明确。
此外,当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回避制度、通知程序,亦有必要在监察法中延续。考虑到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尤其是牵连的广泛性,主动回避制度具备一定价值;留置的通知制度可以有“例外情况”,但必须严格规定法定条件和判定标准,避免出现“可能”“或”等主观色彩浓厚的表述。
(三)监察措施的事后救济
监察委员会不仅可以在调查活动中采取极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还有处置之职权。有学者提出救济是权利实现的必要条件,所谓“无救济即无权利”和“有权利必有救济”差别主要在因果顺序②参见孙笑侠:《西方法谚精选:法,权利和司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5页。;还有一种说法,基于裁判请求权、提起申诉和控告权、取得国家赔偿或补偿权,公民在宪法权利受到损害或侵犯时,有“权利救济权”③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231页。。总之,如何构建有效的错案纠正和救济机制,是监察立法的重要方向。这需要着重考量纠正的渠道、程序以及救济的方式和标准等问题。
1.规范申诉制度,保障渠道畅通
首先,哪些情况下可以申诉,申诉的方式、机关和层级,都必须规定清楚,要让申诉人有路可走,避免大量案件积压在信访部门;其次,监察委处置职能直接关乎当事人的工作、职务和财产等问题,当然可以通过申诉制度寻求救济;进一步讲,对于调查活动中留置等强制措施,尽管没有直接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但限制或剥夺了公民人身和财产等实际基本权利,同样需要有合适的救济途径。
2.职级恢复、财产归还和国家赔偿
职级恢复、财产归还和国家赔偿是职务犯罪错案救济的重要手段。从“处置”来看,性质类似行政处罚,且直接对当事人的工作、名誉、职务和财产等作出处置,有时执行力甚至比法院判决更高效,若经证实为错案,不可避免涉及被处置人的原有职级恢复、财产归还和国家赔偿问题。从“调查”来看,调查期间监察委员会可采取的强制措施——尤其是留置措施——极为严厉,虽尚未处罚,但不可避免严重影响当事人职务和工作,至少涉及职务恢复和国家赔偿等问题,有时还涉及财产归还等。
“职级恢复”方面,如果案后当事人原有职务已被任命,或当事人身体和精神状态已不适宜继续任原领导职务,应当作何安排?“财产归还”方面,如果原有财产已作他用,如何归还?“国家赔偿”方面,处置和调查强制措施之救济究竟是否适用国家赔偿?如果适用,是否适用《国家赔偿法》?损害填补方式和计算方式标准有无特殊规定?
四、留置措施和司法的衔接
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活动不可避免涉及外部衔接问题,这主要是留置和以逮捕为主的刑事强制措施之间的程序衔接设计。如果监察程序期间不存在监察委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之情况,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严格拆分可能成为未来监察立法的重要原则。从留置措施来看,这至少包括以下两重意味:
第一,司法程序期间不涉及任何监察措施且不受监察机关影响。1.衔接转换标志问题。首先,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之间将存在一个显著程序作为衔接转换标志,该标志一旦发生,案件立即转入司法程序;其次,衔接转换标志乃人民检察院“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非监察委“移送司法机关”;再次,作为衔接转换标志的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与监察委员会无直接关联。2.司法程序不受监察之影响。其一,不论人民检察院采取何种强制措施,甚至不采取强制措施,既然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则除非人民检察院“退回补充调查”或“决定不起诉”,否则案件仍处于司法程序;其二,只要在司法程序期间,案件将与监察委员会无直接关联。
第二,监察程序期间不涉及任何刑事强制措施且不受法律监督机关、司法审判机关影响。1.只要在监察程序期间,案件与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无直接关联,二者均无权决定(批准)留置措施,至于谁来决定(批准)留置措施此处不作讨论;2.至于留置措施由监察委自行执行还是请公安机关协助执行,有待后续明确;3.只要在监察程序期间,都无关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4.一旦人民检察院采取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案件立即转入司法程序。
留置措施和司法程序的具体衔接,主要表现于留置和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这至少涉及三个问题:
第一,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标志正式进入司法程序。首先,从杭州上城区留置案来看,监察程序和司法程序衔接转换的标志应是检察院“决定逮捕”,而不是监察委“移送司法机关”,由此实现二者时间上无缝衔接。其次,人民检察院采取其他刑事强制措施亦标志转入司法程序。实际上,人民检察院不仅可以“决定逮捕”,也可以选择不逮捕而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甚至未逮捕,直接退回补充调查或不起诉决定,都是可能的。
第二,进入司法程序后“留置”自动解除。假如人民检察院不决定逮捕而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留置”是否自动解除?假如人民检察院不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留置”是否仍自动解除?实践中,前一情况可能比例不大,后一情况几乎很少发生,仍不妨碍作理论探讨。笔者以为,只要人民检察院作出某一决定,程序则自动转入司法程序,“留置”当然地自动解除。其一,“以人民检察院采取强制措施为衔接转换标志”并不考虑人民检察院采取的是逮捕还是其他强制措施;其二,即便人民检察院未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仍不妨碍案件材料已移送司法机关且案件程序已走入司法程序。至于后续事项一应由人民检察院决定,与监察委员会无直接关联。
第三,逮捕措施由人民检察院决定、公安机关执行。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若现行宪法该规定不作修改,绝难从中透析出“人民检察院执行逮捕”之意蕴。由此,当职务案件程序走入逮捕,与监察委员会无直接关联,逮捕之决定权归人民检察院,执行权归公安机关。
五、结语
留置措施的批准和备案从源头和末端两处根本上影响个案正当性,但备案制度有待真正发挥实效。期限和执行从过程中控制个案发展并直接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可在科学考量之后适当限缩留置期限,并设置一般期限和最长期限。当事人权利保障应贯穿监察工作之始终,一方面要保障被留置人程序性权利,区分“辩护”和“陈述申辩”,允许律师介入;另一方面留置措施应纳入职务案件错案纠正和救济机制之内,职级恢复、财产归还和国家赔偿是值得深思的三大问题。以上问题对应留置措施的监督、实施、权益保障和外部衔接,从中亦可探析留置权的性质。
基于试点探索比较和监察立法动态,未来改革和立法中,有关留置措施的重点和难点如下:第一,如何构建留置措施的监督机制,包括完善的事前批准体系以及涵盖审查功能的备案制度;第二,初次留置期限限缩问题和延长留置期限的批准问题;第三,被留置人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的保护问题,立法有无必要以专门条款规定?若调查活动不受刑事诉讼法规制,怎样确保当事人辩护权利和律师介入问题?第四,怎样实现留置措施与检察程序之间乃至审判程序之间的合理衔接?与纪检监察程序是否有衔接需要?盼望正式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能对留置措施作出更详细、更科学合理、更符合宪法精神的规范和规制。总之,只要构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受到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制,故长远来看,尽快制定恰当程序法①法律体系内部中,同一个子系统中由于调整对象的差异,也存在分工不同。关于国家监察立法,应当有专门的组织法和行为规范,二者在性质上有明显差别,不宜混在一部法律之中。参见马岭:《关于监察制度立法问题的探讨》,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以规制留置等强制措施,应是本轮监察体制改革应有之义。
A Study on the Detention Measures of Supervision Committee
Qin Qian-hong Shi Ze-hua
The cases and related normative documents of detention measures in the pilot areas mainly focus on the approval,filing,execution,term,equity and connection. These can be summarized as supervision,implementation,infringement prevention,and external connection,which constitute the essence of detention measures together with the issue of its nature. The examination of the pilot experiences reveals that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may strictly distinguish the supervision process and the judicial process. In that case,the cohesion between detention arrest and discipline inspection,as well as the complement between the supervision law and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s would be the focus of future legislative work. The detention time could be appropriately shortened after scientific considerations,and could design a general term and a maximum term with reference to criminal detention. Even if investigation activities are not be regulated by criminal procedure laws,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efense” and “statement of pleadings” should be clarified,and the lawyers’ rights of intervention during the deten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written in the act. In addition,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the correction mechanism of misjudged cases and the remedy mechanism of rights due to that fact that misjudged detention could have serious impacts on duty performance. An appeal channel should also be provided for detention measures. The restoration of those people’s position,the restitution of thei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compensation need to be taken seriously. Appropriate procedural laws should be provided as soon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regulate detention measures.
Detention Power;Detention Measures;Filing Review System;Cohesive Mechanisms;Right of Defense
D911
A
2095-7076(2017)04-0009-11
10.19563/j.cnki.sdfx.2017.04.002
*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4JZD00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上官丕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