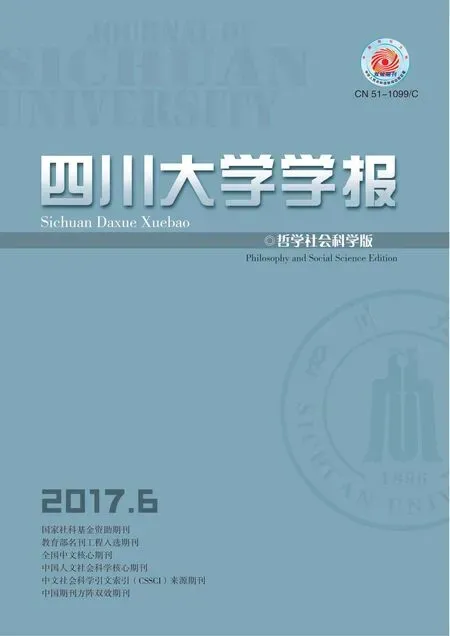苏轼七言古诗中的对仗艺术
——兼论古体诗“律化”的问题
张 淘
§宋文化研究§
苏轼七言古诗中的对仗艺术
——兼论古体诗“律化”的问题
张 淘
古体诗并不要求对仗,苏轼在杜甫的基础上使古体与律诗一样达到了艺术上的审美并重,用韵和句式都越来越接近律诗,这种创作态度与欧阳修趋向保守相比更为大胆。追溯对仗手法在七古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可以发现苏轼的七古在宋代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来自他对初唐以及杜诗的继承,尤其是面对可视为其座师的欧阳修继承李白诗风时,他能够开辟新路径,在宋人诗歌当以意为主的观念下发挥自身才华,形成了一种瑰伟绝特的“似律古体诗”。
苏轼;七言古诗;对仗;古体诗律化
对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一种重要艺术手法,体现了古人的平衡美学观。古体诗并不要求对仗,即便使用也不讲求精致工整,王力先生曾指出,“自杜、韩以后,一韵到底的七古总以完全不用对仗为原则。至于五古和转韵七古,就有些地方是对仗的了”。*王力:《汉语诗律学·古体诗的对仗》,《王力全集》第十七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96页。对仗艺术是在律诗形成过程中逐步得到提高的,*关于对偶与律诗产生的关系,可参考钱志熙:《唐诗近体源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古体诗大量使用工整对仗会模糊古律体之间的界线。七言古诗的常体是偶尔用对仗,而杜甫的七古中较为频繁地使用对仗,苏轼在杜甫的基础上使古体与律诗一样达到了艺术上的审美并重,用韵和句式都越来越接近律诗,甚至导致后人有时将他的拗体七律与七古相混淆。这种创作态度与欧阳修趋向保守相比更为大胆。近人陈衍认为“东坡五七古遇端庄题目,不能用禅语、恢谐语者,则以对偶排奡出之”,*《宋诗精华录》卷二,陈衍选评、曹中孚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215页。善谑和善比拟是苏轼诗风的重要因素,而对仗的作用不亚于二者。清代李重华认为苏诗“各体中七古尤阔视横行、雄迈无敌”,*李重华:《贞一斋诗说》,《清诗话》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61页。说明这一诗体在苏轼作品中的地位。但目前关于苏轼古诗的研究多从结构、声律入手,*张智华:《苏轼七言古诗的结构艺术》,《安徽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任正霞:《浅析苏轼七言古诗艺术风格——以〈凤翔八观〉为例》,《铜仁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等。本文从清人一则材料出发,通过追溯对仗手法在七古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分析苏轼七古创作风格的形成,以期深入探索七古的内在规律。
一、苏轼七言古诗中的对仗
苏轼古诗约867首,七古约361首,*本文讨论的主要是齐言七古的对仗使用情况,这也是宋元人概念中的七言古诗,但方便起见,在统计时也将杂言体七古以及歌行体、七言乐府等包括在内,但不包括骚体七言诗。占三分之一强。*刘尚荣《〈新编东坡先生诗集〉考辨》(载《苏轼著作版本论丛》,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103页)一文中提到上海中华书局图书馆收藏的一部十九卷本《新编东坡先生诗集》是唯一按诗体分类编次的苏诗传本,据卷首目录,此书共收四言诗4首,五言绝句75首,六言诗32首,七言绝句493首,五言律诗114首,七言律诗501首,五言排律39首,七言排律5首,五言古诗530首,七言古诗337首;另附乐府词34首。但笔者无缘得见,在统计时利用的是清人冯应榴辑注的《苏轼诗集合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卷四七至卷五十的他集互见诗和补编诗未计入在内。七古中完全不使用对仗的约184首,使用一两联*古体诗中本无“联”之说,但欧阳修已使用“联”来称呼古诗对仗(见本文第三节),故此袭用。对仗的约128首,使用三联对仗的23首,这在比例上与欧阳修、王安石等人集中七古使用对仗的频率(详见第三节)大体类似;但是苏诗中大量使用对仗的约有26首,这个数字形成了一种新的创作模式,尤其是那些首尾皆对的作品。对此,清初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一有云:
颜、谢以后,古诗多有对偶终篇者。入唐遂以有声病者为律,无声病者为古。至于七言古体,亦时一有之。若少陵之“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子规夜啼山竹裂,王母昼下云旗翻”;昌黎之“大蛇中断丧前王,群马南渡开新主”、“何人有酒身无事,谁家种竹门可款”,硬语排奡,视唐初四子及元、白诸家之宛然律调者,不可同日语也。若其自首至尾无句不对,无对不瑰伟绝特,则惟轼集中有之,实为创格。*曾枣庄编:《苏诗汇评》,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37、138页。
其中提及的杜甫、韩愈的七古将在第二节中细论,先来看苏轼七古中对仗的使用。这里提到他有“自首至尾无句不对”的作品,实际上数量并不多,笔者统计出的26首大量使用对仗的作品标准更宽,可分为四种类型:A.长韵(大于10韵)而对仗比重过半的作品;B.全诗10韵而中间8韵全用对仗的作品,此类数量最多;C.并非长韵但是对仗比重过半的作品;D.对仗比重未过半但超过三联的作品。下面以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中的卷次顺序(此书编年排列,注出卷数,不再一一注出创作时间,但注出押平韵、仄韵,或是换韵),对这些作品进行分析。
嘉祐年间在凤翔所作的《石鼓歌》(卷四、A、平韵)是苏轼初次尝试大量使用对仗,也成为其七古的代表作之一,共30韵15联对仗,语言上学习前代韦应物、韩愈、梅尧臣、刘敞的石鼓歌,但形式上打破了以上作品的局限。*唐宋时期石鼓歌在结构、内容、风格上的流变,可参考李娟:《由唐入宋石鼓诗之流变》,《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如用对句叙述:“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钳在口”“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籀史变蝌蚪”“欲寻年岁无甲乙,岂有文字记谁某”;用对句议论:“厌乱人方思圣贤,中兴天为生耆耈”“遂因鼓鼙思将帅,岂为考击烦蒙瞍”“勋劳至大不矜伐,文武未远犹忠厚”“扫除诗书诵法律,投弃俎豆陈鞭杻”“暴君纵欲穷人力,神物义不污秦垢”“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用对句刻画:“模糊半已隐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东征徐虏阚虓虎,北伐犬戎随指嗾”“象胥杂沓贡狼鹿,方召联翩赐圭卣”。叙述时重视上下句的逻辑关系,议论时上下句间存在意识流动的同时又有逻辑跳跃,如“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上追轩颉相唯诺,下揖冰斯同鷇鹁”。这种变化与跳跃在对仗中形成了独特的张力。
《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卷四、B、仄韵)除最后两句外整首诗几乎全为对仗。“横槎晚渡碧涧口,骑马夜入南山谷”同样用对仗句叙述;“谷中暗水响泷泷,岭上疏星明煜煜”描述所见风景;“寺藏岩底千万仞,路转山腰三百曲”,笔峰陡转,写出寺庙所在地的险峭,“千万仞”对“三百曲”,既造成了数字上的悬殊对立又是一种夸张描述,气势横放。“风生饥虎啸空林,月黑惊麏窜修竹”,“风生”对“月黑”不够工整,是作者为了突出夜晚山林中的险象采取的妥协。“入门突兀见深殿,照佛青荧有残烛”,上句叙述,下句描写进门第一眼见到的景象,不露刻意痕迹。“愧无酒食待游人,旋斫杉松煮溪蔌”写僧人招待自己的举动,“愧无”对“旋斫”属粗对却起到紧密联系上下句的作用。“板阁独眠惊旅枕,木鱼晓动随僧粥”从游人的角度来写,“起观万瓦郁参差,目乱千岩散红绿”是平常写景,“门前商贾负椒荈,山后咫尺连巴蜀”,以“商贾”对“咫尺”,以“椒荈”对“巴蜀”,灵活多变。最后归结为“何时归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飞鹄”。汪师韩评此诗:“其中写景处,语刻画而句浑成,读之可怖可喜,笔力奇绝”。指的便是其中对仗的地方既用心又不留痕迹,能够使读者忘却对仗这种形式,通过多重角度的叙述达到浑然天成的效果。
《渼陂鱼》(卷五、B、仄韵)10韵中8联对仗。其中,“携来虽远鬣尚动,烹不待熟指先染”用熟典而意义与典无涉,有趣生动,“携来虽远”对“烹不待熟”增加叙述的时间跨度。苏轼擅长在对仗中加入趣味因素,如“坐客相看为解颜,香粳饱送如填堑”用曹植《与吴季重书》“食若填巨壑”语,却用“解颜”来对,妙趣横生。
《送任伋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卷六、C、仄韵)8韵4联对仗。前两句领起之后连用对仗,从“无媒自进谁识之”至“见贤不荐谁当耻”,叙述友人生平及仕途不显的状况,夹杂议论一气呵成。
《再游径山》(卷十、A、仄韵)也是除首尾联外中间全用对仗。相对而言这首的对仗显得稳重谨慎,如数字对“日三竿”对“天一握”,专名对“含晖亭”对“凌霄峰”,重字对“丝杉翠丝乱”对“玉芝红玉琢”。其中也有几处巧思,如以“忆钦”对“征璞”。这种工稳可能与此时作者的写作心态有关,重在描写僧人行迹与学禅理想,议论较少。
《大风留金山两日》(卷十八、C、仄韵)6韵4联对仗:“朝来白浪打苍崖,倒射轩窗作飞雨。龙骧万斛不敢过,渔舟一叶从掀舞。细思城市有底忙,却笑蛟龙为谁怒。无事久留童仆怪,此风聊得妻孥许。”自由奔放,写出大风大浪的情形以及人物心理,与前首形成鲜明对比。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次韵前篇》(皆卷二十、B、仄韵)两诗,前者除首两句外都是对仗,刻画细腻,尤其从“已惊弱柳万丝垂”至“但恐欢意年年谢”,句意几经转折。“自知醉耳爱松风”对“会拣霜林结茅舍”打破了全诗的严整,从逻辑关系上来属对。最后两句用“妻子”对“嘲骂”也十分风趣幽默。后者前四句采用排比句式:“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如果纯用对仗则显得板滞,故而修改语句顺序,这种做法多见于唐人七古。又用“万事如花不可期,余年似酒那禁泻” 一联包含妙喻的对仗来总结。接着回忆往昔连用5联对仗,从“长江衮衮空自流”至“忧患已空犹梦怕”,纯是议论。结句才又归到赏花饮酒之事上。
《上巳日与二三子携酒出游随所见辄作数句明日集之为诗故辞无伦次》(卷二二、D、仄韵)20韵8韵对仗。如诗题所称,此诗各句间逻辑关系不强,对仗位置也显得零乱,但是延续了苏轼一贯不羁的风格。
《龟山辩才师》(卷二四、C、仄韵)8韵6联对仗,跳跃性也比较大:用“古人宴坐虹梁南”对“新河巧出龟山背”写河上桥梁,接着“木鱼呼客振林莽,铁凤横空飞彩绘。忽惊堂宇变雄深,坐觉风雷生謦欬”写寺庙颂经声与屋檐上的装饰物,属粗对,“呼”字想象奇特,“横”气势排奡,“堂宇”和“謦欬”主语位置变换,句法灵活。“羡师游戏浮沤间”等四句对仗工整。“千里孤帆又独来,五年一梦谁相对”用两个当句对,同时又是半成品对仗,前句虚写,后句实写。
《蔡景繁官舍小阁》(卷二四,C、仄韵)亦8韵6联对仗:“戏嘲王叟短辕车,肯为徐郎书纸尾”属粗对,但都用史书中语。“三年弭节江湖上,千首放怀风月里”对仗工整。“手开西阁坐虚明,目净东溪照清泚”,“手”“东溪”是主语,“虚明”是虚景,“清泚”是实景,句式灵活。“素琴浊酒容一榻,落霞孤鹜供千里”用熟语和当句对加强诗歌容量。“大舫何时系门柳,小诗屡欲书窗纸”,思维跳跃。“文昌新构满鹓鸾,都邑正喧收杞梓”用比喻而构思精巧。
《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卷二四、A、仄韵)11韵6联对仗,全诗前一部分写王巩经过贬谪后诗思更佳,“十年冰蘖战膏粱,万里烟波濯纨绮”想象奇特用语新颖。中间部分写其归来后的心态:“逝将桂浦撷兰荪,不记槐堂收剑履。却思庾岭今何在,更说彭城真梦耳。君知先竭是甘井,我愿得全如苦李。妄心不复九回肠,至道终当三洗髓。”前四句用虚词将意思连贯起来,后四句上下句意同语不同,反复说明哲理。诗中还将佛经语化用为对仗:“心通岂复问云何,印可聊须答如是。”
《用前韵答西掖诸公见和》(卷二七、B、仄韵)也是中间全用对仗的作品,而且首尾两联接近对仗:“双猊蟠础龙缠栋,金井辘轳鸣晓瓮”“借君妙语发春容,顾我风琴不成弄”。此诗所次韵的《送陈睦知潭州》只有一联对仗,次韵之作则变换形式来写,除“羡君”两句外都是工对。
《送表弟程六知楚州》(卷二七、C、仄韵)10韵5联对仗,《次前韵送程六表弟》(卷三十、C、仄韵)10韵6联对仗。加上前诗中用到的隔句对“子方得郡古山阳,老手生风谢刀笔。我正含毫紫微阁,病眼昏花困书檄”,两首中的对仗都占了过半的份量。两诗第一联对仗中都提到了刺史,且用典故写送其赴任之事(前诗送知楚州,后诗送漕江西):“里人下道避鸠杖,刺史迎门倒凫舃”“竹使犹分刺史符,上方行赐尚书舄”。随后两诗都忆往昔伤今时,一从儿时写起,一从前年写起,前诗用到的对仗如“健如黄犊不可恃,隙过白驹那暇惜。醴泉寺古垂桔柚,石头山高暗松栎”等,后诗用到的对仗有“前年持节发仓廪,到处卖刀收茧栗”“君才不用如涧松,我老得全犹杜栎”等。
《兴龙节侍宴前一日微雪与子由同访王定国……》(卷三十、B、平韵)10韵而中间全用对仗,与之前同类作品相比显得成熟了许多,从容不迫又游刃有余。《同正辅表兄游白水山》(卷三九、A、仄韵)12韵10联对仗,且有不少当句对,如“攫土抟沙”“金沙玉砾”“古镜宝奁”。所有对仗上下句几乎没有句意重复。《送江公著知吉州》(卷三三、C、仄韵)8韵中间6联全为对仗。《庞公》(卷三三、C、仄韵)6韵中间4联全为对仗。 除中间全用对仗的作品外,《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作诗远和之皆粲然可观子由有诗相庆也因用其韵赋篇并寄诸子侄》(卷四二、D、仄韵)10韵4联对仗;《西湖秋涸东池鱼窘甚因会客呼网师迁之西池为一笑之乐夜归被酒不能寐戏作放鱼一首》(卷三四、C、仄韵)8韵5联对仗;《聚星堂雪》(卷三四、C、仄韵)10韵6联对仗;《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卷三八、A、平韵)12韵6联对仗;绍圣二年惠州作《游博罗香积寺》(卷三九、C、平韵)10韵7联对仗;《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卷三九、D、平韵)20韵9联对仗;《欧阳晦夫遗接篱琴枕戏作此诗谢之》(卷四三、D、仄韵)11韵4联对仗等等。这些作品中不乏佳作,尤其是B类作品中的《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往往被编入各种选本为人熟知,故而给人留下了七古好用对仗的印象。不过苏轼善于作对确是宋人的普遍评价,如惠洪《冷斋夜话》中载:
东坡曰:世间之物,未有无的对者,皆自然生成之象,虽文字之语亦然,但学者不思耳。如因事,当时为之语曰“刘蕡下第,我辈登科”,则其前有“雍齿且侯,吾属何患”。太宗曰“我见魏征常妩媚”,则德宗乃曰:“人言卢杞是奸邪”。
苏轼属对不仅从自然界中汲取各种成对的现象,还吸收典籍中的语言,学问是他用对仗的基础。他学习了陶渊明五言诗对仗的自然流利,不讲究精致工整,而重在意贯其中,通畅有余韵。如《冷斋夜话》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东坡尝曰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霭霭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不知者困疲精力,至死不之悟,而俗人亦谓之佳。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万军声半夜潮”。又曰:“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皆如寒乞相,一览便尽。初如秀整,熟视无神气,以其字露也。东坡作对则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严》已不看”之类,更无龃龉之态。细味对甚的,而字不露,此其得渊明遗意耳。*以上引文参见惠洪:《冷斋夜话》卷一,陈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3页。
惠洪在这里批评晚唐诗人赵嘏、崔涂、杜牧的诗为寒乞相,是指两句之中只出一意,所谓“字露”是就读者观感而言,读后使人留意的只在字句。而苏轼却不同,惠洪所举苏轼的对仗,用“老宿”对“楞严”,故意打破工整性,且两句之中意思流动,从而转移了人们对于对仗的关注。
苏轼作对不爱用熟语,在运用典故时注意意思的连贯,大量运用流水对的方式,并且故意造成一种不平衡感。如“《复斋漫录》云:韩子苍言,作语不可太熟,亦须令生。近人论文,一味忌语生,往往不佳。东坡作《聚远楼》诗,本合用‘青山绿水’对‘野草闲花’,以此太熟,故易以‘云山烟水’,此深知诗病者。予然后知陈无己所谓‘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之语为可信”。*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七,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03页。从中显示出苏轼在对仗上的用心。又如《王直方诗话》所云:
对句法,人不过以事以意,出处备具,谓之妙。荆公曰:平昔离愁宽带眼,迄今归思满琴心。又曰:欲寄荒寒无善画,赖传悲壮有能琴。不如东坡特奇,如曰:见说骑鲸游汗漫,亦曾扪虱话酸辛。又曰:龙骧万斛不敢过,渔舟一叶从掀舞。以鲸为虱对,龙骧为渔舟对,大小气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谓之秀杰之气,终不可没。*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3页。此段话又见《冷斋夜话》卷四,个别字有异。
通过大小不同、品种各异的物体相对,以达到一种奇倔排奡的效果,*不仅古诗如此,宋人认为律诗也要遵循这一原则:“古人律诗,亦是一片文章,语或似无伦次,而意若贯珠。”参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七引《诗眼》,第43页。这是苏轼的经验之谈,也使得他能够把对仗更好地融入到古体诗的创作中去。
从宋代人的七古创作来看,苏轼的对仗使用也是具有鲜明特点的。对此,可以通过回顾七古中对仗的使用历史,分析杜甫、韩愈等人的创作可能对苏轼产生的影响,并以苏轼之前的宋代七古创作大家欧阳修、王安石等作为参照,来考察苏轼在七古中使用对仗究竟有怎样的突破。
二、作用力分析:从柏梁体到老杜体
现存最早的七言诗据传是汉武帝等人的《柏梁诗》,*关于七言古诗的研究,除明清诗话等作品中有所涉及外,现代研究主要有王锡九的系列专著:《唐代的七言古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宋代的七言古诗(北宋卷)》《宋代的七言古诗(南宋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1996年;《金元的七言古诗》,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其中只有“郡国吏功差次之,乘舆御物主治之”一联近似对仗,汉代其他七言诗中也没有对仗,直至魏文帝的《燕歌行》,七言都是句句为韵,每句各叙一事,不宜对仗。正如宋代范温对建安诗歌特点的评价:“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其言直致而少对偶,指事情而绮丽,得风雅骚人之气骨,最为近古者也。”*范温:《潜溪诗眼》,郭绍虞:《宋诗话辑佚》,第315页。这类七古诗成为典型高古之作,后世也称为柏梁体、燕歌行体。到刘宋颜延之、谢灵运时,五言诗开始有对仗终篇的诗作,即如严羽所评价:“灵运之诗,已是彻首尾成对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58页。而七言中的对仗则相对滞后一些,“白纻”系统的歌、辞、曲都只有当句对,*宋洪迈《容斋续笔》三:“唐人诗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对偶,谓之当句对,盖起于楚辞‘蕙烝兰藉,桂酒椒浆’、‘桂棹兰枻,斲冰积雪’。自齐、梁以来,江文通、庾子山诸人亦如此。” (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48页)实际上,谢灵运和谢惠连的《燕歌行》、鲍照的《代白纻舞歌词四首》、刘铄的《白纻曲》、汤惠休的《白纻歌三首》、王俭的《齐白纻辞五首》、萧衍的《白纻辞二首》、沈约的《四时白纻歌五首》、谢庄的《怀园引》等作都有当句对,鲍照诗中更是有大量存在,如:纤罗雾縠、含商咀征、车怠马烦、桂宫柏寝、朱爵文窗、象床瑶席,等等。参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510-1527页。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开始有对仗:“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其一,全诗共10句)、“璇闺玉墀上椒阁,文窗绣户垂罗幕”(其三,共10句)、“朝悲惨惨遂成滴,暮思遶遶最伤心”(其十二,共14句),这些已是隔句用韵或换韵的作品。*清代王士禛认为七古换韵法“起于陈、隋,初唐四杰辈沿之,盛唐王右丞、高常侍、李东川尚然,李、杜始大变其格”(郎廷槐:《师友诗传录》,《清诗话》上,第139页)。然而陈代之前已有换韵之作,此说不确。因此,七言中出现对仗应该与押韵从句句用韵,发展到隔句用韵甚至换韵有关。这种多用句中对、偶尔掺杂一至四联对仗的样式,可以看作是押平韵七古的常式,故而有人认为七古成于鲍照。*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七古自晋世乐府以后,成于鲍参军,盛于李、杜,畅于韩、苏,凡此俱属正锋。”参见《清诗话》下,第959页。南朝时期的七言呈现出系统性、模仿创作的特点,如南齐释宝月和梁吴均、费昶的《行路难》或者有句子接近对仗,或者有一两联对仗,*释宝月《行路难》:“空城客子心肠断,幽闺思妇气欲绝。凝霜夜下拂罗衣,浮云中断开明月。夜夜遥遥徒相相思,年年望望情不歇”句式接近对仗。吴均《行路难五首》其一:“白璧规心学明月,珊瑚映面作风花”“年年月月对君子,遥遥夜夜宿未央”,后两句也可以看出与宝月之作的关系。其二:“摩顶至足买片言,开胸沥胆取一顾”“吾丘寿王始得意,司马相如适被甲”。其四:“丹梁翠柱飞流苏,香薪桂火炊雕胡”。费昶《行路难二首》其一:“玉阑金井牵辘轳,丹梁翠柱飞流苏”。其二:“朝踰金梯上凤楼,暮下琼钩息鸾殿”“既逢阴后不自专,复值程姬有所避”。完全使用吴均的句子,更用其他对句。参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第1480、1727、1728、2083页。与鲍照之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继承关系。即使押韵规则改变,同题作品往往在形式上也具有相似之处,不过用韵开始从多变转向成熟。萧衍的《河中之水歌》《东风伯劳歌》能熟练地换韵,音节和谐,但还停留在使用当句对的阶段;张率的《白纻歌九首》其一也开始出现了一联对仗;王融的《努力门诗》《回向门诗》隔句用韵且全诗对仗;*参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为行文方便,以下将各诗中对仗的联数与总共韵数用分数表示。萧子显、萧绎、王褒、庾信的《燕歌行》都是换韵且用对仗的形式(7/12、3/11、4/13、7/14),七言新的题材越来越多,对仗的运用也更自如,如萧纲和庾信的《乌夜啼》都是七言(3/4),萧纲《和萧侍中子显春别诗四首》其二和萧绎《春别应令诗四首》其二皆6句且全对仗,沈君攸的《薄暮动弦歌》(4/6)《羽觞飞上苑》(6/8)《桂檝泛河中》(8/9)格式接近七言排律。七古的成熟大概是在梁陈时期,江总的对仗运用既多且工整。隋至初唐的七古创作不多,如卢照邻的七古保存下来的只有5首(其中2首骚体),骆宾王共6首七古,*本文卢照邻诗统计据祝尚书:《卢照邻集笺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另,五古14首、五律30首、五排21首、五绝10首、七绝3首。骆宾王诗统计据《骆丞集》,《丛书集成初编》本。而他们的近体诗创作远远占据上风。不过七古对仗的比重不小,如卢照邻的《失群雁》(6/12)、《行路难》(6/20),尤其是《长安古意》(23/34),基本上都是对句形式。此外,骆宾王的《帝京篇》等也有大量对仗,而王勃的《秋夜长》《采莲曲》《江南弄》等只有当句对和半成品的对仗,间有对仗的有《滕王阁》(1/4)。
七古的繁荣期在盛唐,李白集中乐府和歌吟占了绝大部分,然而多用杂言体(故亦有人称之为长短句),有时故意用“之”“兮”“于”等字来加强诗歌的文章偏向,对仗以一至两联为主,*本文统计据《李太白全集》,王琦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一联对仗的有:《战城南》(总11韵,下仅注数字)、《胡无人》(9)、《阳春歌》(5)、《双燕离》(6)、《白头吟》(15)、《采莲曲》(4)、《司马将军歌》(10)、《少年行》(15)、《长相思》(5)、《扶风豪士歌》(14)、《金陵城西楼月下吟》(4)、《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8)、《赠郭将军》(4)、《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8)、《上李邕》(4)、《流夜郎赠辛判官》(7)、《江夏赠韦南陵冰》(17)、《对雪醉后赠王历阳》(7)、《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31)、《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10)、《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14)、《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6)、《别山僧》(5)、《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7)、《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筒》(3)、《醉后答丁十八以诗讥予搥碎黄鹤楼》(7)、《鹦鹉洲》(4)、《下途归石门旧居》(9)、《万愤词投魏郎中》(19)、《观元丹丘坐巫山屏风》(9)、《寄远十二首》其八(6)、《代美人愁镜二首》其二(5)等;两联对仗的有:《凤笙歌》(8)、《江上吟》(6)、《草书歌行》(13)、《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4)、《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20)等。另,《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3/16)、《行路难》(4/7)、《捣衣篇》(4/13)、《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5/10)、《猛虎行》(6/22)有多联对仗。尤其是他的《白纻辞三首》亦是杂言不带对仗,从这点来说,李白的七古与齐梁时代的作品有天壤之别。王维的古体诗共150首,其中七古21首,施补华《岘佣说诗》评价说,“摩诘七古,格整而气敛,虽纵横变化不及李、杜,然使事典雅,属对工稳,极可为后人学步”,*《清诗话》下,第1019页。清代钱良择《唐音审体·古诗七言论》(《清诗话》下,第809页)中也提及:“七言始于汉歌行,盛于梁。梁元帝为《燕歌行》,群下和之,自是作者迭出,唐初诸家皆效之。陈拾遗创五言古诗,变齐、梁之格,未及七言也。开元中,其体渐变。然王右丞尚有通篇用偶句者。旋乾转坤,断以李、杜为歌行之祖。李、杜出,而后之作者不复以骈俪为能事矣。”本文王维的古体诗统计据《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而《老将行》《燕支行》《桃源行》《洛阳女儿行》《同崔傅答贤弟》《同比部杨员外十五夜游有怀静者系》《故人张諲工诗善易卜兼能丹青草隶顷以诗见赠聊获酬之》《送崔五太守》《不遇咏》中皆有大量对仗,不过大多属歌行体。*虽然歌行体也可以归入七言古诗,但唐人眼中的歌行体与七古是有区别的,如吴融《禅月集序》(四部丛刊本《禅月集》前附)中有提及:“且歌与诗其道一也。然诗之所拘悉无之。足得放意取非常语、非常意又尽,则为善矣。”杜甫则在文人七古中大量加入对仗,而且避免工整以求一种张力。据统计,杜甫的七古共119首,其中运用对仗的72首,接近三分之二。*韩晓光:《整中寓变 拙中见巧——杜甫七言古诗中的对仗句例析》,《杜甫研究学刊》2010年第2期。如《古柏行》以武侯祠前的古柏为描述对象,24句中对仗达到了16句,旨在形容刻画对象,其以“四十围”对“二千尺”曾在宋人诗话中形成了争议,而以“子规”对“王母”为则借对,子规诗中意指杜鹃鸟,又有望帝之意。韩愈集中以五古居多,李汉《昌黎先生集序》称“古诗二百一十、联句十一、律诗一百六十”,*参见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本文统计据此书。其五古亦有时故意不用对仗,如《唐子西文录》中云:“韩退之作古诗,有故避属对者,‘淮之水舒舒,楚山直丛丛’是也。”此两句出自《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朱彝尊曰:“添一之字,故避对,乃更古健。然《秋怀》诗何尝不对。此要看上下调法如何。” 参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96页。笔者统计出七古共54首,多用单行或者当句对,有时是在故意回避使用对仗句。如《鸣雁》中“风霜酸苦稻粱微,毛羽摧落身不肥。徘徊反顾群侣违,哀鸣欲下洲渚非”,接近对仗却有几个字不完全相对,当句对较多,如:穷秋南去春北归、去寒就暖、天长地阔、江南水阔朔云多、草长沙软、闲飞静集、违忧怀惠等。《山石》中亦有当句对,如:山石荦确行径微、升堂坐阶、芭蕉叶大支子肥、铺床拂席、清月出岭光入扉、山红涧碧等;《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此诗被翟翚评曰:“纯用古调,无一联是律者。”参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三,第263页。中:清风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声影绝、洞庭连天九疑高等等,《华山女》等作亦是如此。清代黄钺曾称韩愈七言古诗间用对句者唯《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赠崔立之评事》《桃源图》三篇而已,前两首对仗所占比例分别为:5/20、6/25,第三首虽然俞旸称“公七言古诗,少用对句。此篇诸对,亦甚奇伟”,*参见黄钺:《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俞旸:《桃源图》,《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916、568页。但实际上只有一联对仗:“大蛇中断丧前王,群马南渡开新主”,因此黄钺、俞旸所说的对句应该是指其中的当句对,如:流水盘回山百转、驾岩凿谷开宫室、接屋连墙、嬴颠刘蹶、地坼天分、听终辞绝、礼数不同罇俎异、骨冷魂清等。韩愈以矫正时文之弊以自任,这是其七古不大用对仗的原因。
汪师韩认为杜、韩诗“视唐初四子及元、白诸家之宛然律调者,不可同日语也”,但在使用对仗上两人仍有区别,如施补华所云:“少陵七古,多用对偶;退之七古,多用单行。退之笔力雄劲,单行亦不嫌弱,终觉钤束处太少。”*施补华:《岘佣说诗》,《清诗话》下,第1023页。苏轼七古多使用对仗学自杜甫,甚至被人称为老杜体:
老杜自我作古,其诗体不一,在人所喜取而用之,如东坡在岭外《游博罗香积寺》、《同正辅游白水山》、《闻正辅将至以诗迎之》,皆古诗,而终篇对属精切,语意贯穿,此亦是老杜体,如《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入衡州奉赠李八丈判官》、《晚登瀼上堂》之类,概可见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七,第319-320页。
“终篇对属精切,语意贯穿”是老杜体的特点。张耒《明道杂志》中记载了苏轼评价杜、韩诗:“子瞻说吏部古诗,凡七言者,则觉上六字为韵设,五言则上四字为韵设,如‘君不强起时难更’,‘持一念万漏’之类是也。不若老杜语韵浑然天成,无牵强之迹”。*张耒:《明道杂志》,《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页。此段话标点笔者有所改动。“持”当作“挂”。下引同页。苏轼学习杜甫古诗的韵,一是指其押韵,二是指使用律句对句。而他在语言提炼和结构布置则学韩。韩愈的心思似乎都放在语言、用韵和单句句法上,刘熙载《艺概》曾评价说,“昌黎七古,出于《招隐士》,当于意思刻画、音节遒劲处求之。使第谓出于《柏梁》,犹未之尽”,*王气中:《艺概笺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7页。认为其语言结构的创新打破了诗歌对仗的句式。*张耒《明道杂志》曰:“韩退之穷文之变,每不循轨辙。古今人作七言诗,其句脉多上四字而以下三字成之。如‘老人清晨梳白头’、‘先帝天马玉花骢’之类。而退之乃变句脉,以上三下四。如‘落以斧斤引纆徽’、‘虽欲悔舌不可扪’之类是也。”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7页)中提及此问题,并称这打破了对句规则。汪师韩对韩愈“大蛇中断丧前王,群马南渡开新主”“何人有酒身无事,谁家种竹门可款” 两句诗的“硬语排奡”的评价,也是从语言上而言的。苏轼曾说“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苏轼语,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4页。所谓“规矩”大概包括了对仗一类具体可学的做法。
三、参照系:欧、王的七古创作及理论
宋初首先大量创作古体诗并且注意到对仗这种手法对于古诗创作有重要意义的是欧阳修,他曾经教人作诗,说过“但古诗中时复要一联对属,尤见工夫”。*苏轼:《跋陈氏欧帖》,《苏轼文集》卷六十九,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86页。对此,诗话中也有相似记载,如吴可《藏海诗话》中有“欧公云:古诗时为一对,则体格峭健”;*吴可:《藏海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第335页。陈善《扪虱新话》上集卷一有“欧公尝言,古诗中时作一两联属对,尤见工夫”,*陈善:《扪虱新话》,《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页。此说在当时应该产生了一些影响。欧阳修提出的方法是“一联对属”(或“一两联属对”),偶尔为之,这与李白的七古创作不谋而合,而事实上欧诗的七古的确有学习李白的一面。欧阳修的古体诗共229首,其中七古106首,约占二分之一。七古中全诗无一对仗的约有69首,占了多数;其次是仅有一两联对仗的,约有28首;三联的有3首,为《归田四时乐春夏二首》《奉送原甫侍读出守永兴》,集中用对仗最多的两例为《千叶红梨花》和《伏日赠徐焦二生》。*本文统计据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对仗位置不固定,有在句首发挥领起作用的,也有在句中为叙事服务的,可见欧阳修对于对仗的使用功能还没有进行定位。由此推测他的基本观点是:古诗当中不应该使用对仗,使用一两联对仗只是偶尔现象,或者说他有变换风格的目的,是他所做的尝试。但是这部分作品并没有达到预期的“体格峭健”,反而那些打破对仗的诗歌往往能够达成这点,如《盆池》诗中除“余波拗怒犹涵澹,奔涛击浪常喧豗”接近对仗外,看不出诗人有任何打算使用对仗的意图。但读此诗仍然能感觉到长江支流贡水(西江)是如何波澜壮阔,诗人从西江水脉悠长联想到灨石,又提到夜登滕王阁所见景象,随之写到古时神话中的老蛟,一气泻下又不断变换描写对象,结尾以盆池中鱼类与自我对比来收束。全诗主要靠出奇不意的章法、雄健奇瑰的意象和思深意远的议论取胜。
欧阳修的七古意在议论,刻画的地方少,甚至用意太过而似古文,他的《鬼车》都可以等同于文章。缺少对仗会使得其古诗较少形象刻画,容易气弱,但是欧诗中特别喜爱使用当句对,仅举《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一诗,其中便使用了诸如:洪涛巨浪、云消风止、泊舟登岸、千岩万壑、悬崖巨石、仙翁释子、丹霞翠壁、晨钟暮鼓、幽花野草、幽寻远去、买田筑室、青衫白首、宠荣声利、青云白石等当句对,都是熟语,增加了形式美,这可能是出于对全诗质朴平淡风格的一种补救。有些诗使用了接近对仗的句子,如《希真堂东手种菊花十月始开》“清泉白石对斟酌,岩花野鸟为交朋”“煌煌正色秀可餐,蔼蔼清香寒愈峭”、《食糟民》“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尔之饥”、《寄圣俞》“万钱方丈饱则止,一瓢饮水乐可涯”、《盘车图》“妍媸向背各有态,远近分毫皆可辨”、《送公期得假归绛》“山行马瘦春泥滑,野饭天寒饧粥香”、《啼鸟》“宫花正好愁雨来,暖日方催花乱发”等,只需改变一二字或调整字词顺序便可称为对仗,这让人不得不怀疑作者是在刻意回避使用对仗。还有一些诗使用了隔句对,如《鹎鵊词》“一声两声人渐起,金井辘轳闻汲水。三声四声促严妆,红靴玉带奉君王”。欧诗与韩诗同样多用当句对,但在用语上有差异,苏轼在语言上更接近韩愈。
如果欧诗的上述特征与他本人不喜杜诗有关,*《后山诗话》中云“欧阳永叔不好杜诗”(《历代诗话》,第303页)。宋代第一个学杜的有可能是石延年,范仲淹《祭石学士文》中云:“曼卿之诗,气雄而奇,大爱杜甫,独能嗣之。”参见《范仲淹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36页。那么宋代另一位古体诗的创作大家王安石则积极学杜,其集中共439首古诗,七古132首,约占三分之一。*本文统计据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高克勤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其中完全不使用对仗的101首;使用一两联对仗的约18首,多用于写景刻画,如《光宅寺》共8句一联对仗,“千秋钟梵已变响,十亩桑竹空成阴”描述该寺所处环境;《移桃花示俞秀老》17句一联对仗,“山前邂逅武陵客,水际仿佛秦人逃”用与桃花相关的典故;《秋热》18句一联对仗,“金流玉熠何足怪,鸟焚鱼烂为可哀”夸张性描述秋热程度。三联对仗的有《九井》《寄题众乐亭》《寄平甫弟衢州道中》。四联对仗如《同王浚贤良赋龟得升字》,迭用多重典故且对仗工整,不过全诗52句中仅有此4联对仗;《次韵欧阳永叔端溪石枕蕲竹簟》36句中亦有4联对仗,“端溪琢枕绿玉色,蕲水织簟黄金纹”于句首起领起开篇作用,“形骸直欲坐弃忘,冠带安能强修饰”“笛材平莹家故藏,砚璞坳清此新得”置中间,一为议论一为叙事,“心于万事久萧然,身寄一官真偶尔”于诗末抒怀,位置分散。值得注意的是《独山梅花》《忆鄞县东吴太白山水》两首押平韵而中间对仗,但全诗整体不符合平仄,应该算是七古。押仄韵的七古中有两首平仄使用较多的作品:一为《和王乐道烘虱》,16韵12联对仗;一为《次韵和中甫兄春日有感》,10韵8联对仗,虽然从总数上说不如欧阳修,但王安石更注重艺术手法,而不是前后诗句意思连贯,他讲究字词,诗中加入不少儒经佛典、诸子小说中语,以语言和哲理的差别,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且使用当句对要少于欧诗。如《王直方诗话》中载:“荆公云:凡人作诗,不可泥于对属,如欧阳公作《泥滑滑》云:画帘阴阴隔宫烛,禁漏杳杳深千门。千字不可以对宫字,若当时作朱门,虽可以对,而句力便弱耳。”*郭绍虞:《宋诗话辑佚》,第90页。《泥滑滑》为古体诗,可见王安石也是注意到了欧阳修喜欢使用当句对做法,关于此点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尽管没能对唐宋七古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分析,从以上对七古产生之初至宋代的一些大家作品的考察来看,苏轼的七古在其时代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来自他对初唐以及杜诗的继承、对韩愈诗歌语言的学习,尤其是他在可视为座师的欧阳修继承李白诗风的面前能够独辟蹊径,遂使后世将其七古与杜、韩作品并列。当然,欧诗重逻辑和王诗重语言对苏轼也有所影响,他在宋人诗歌当以意为主的观念下发挥自身才华,形成了一种瑰伟绝特的“似律古体诗”。
四、代结语:七言古诗“律化”的问题
古体诗“律化”大概从初唐时期开始。律诗出现以后,诗人在创作押平韵七古时往往避免使用对仗,有意识地将古、近体区分开来。经过韩愈、白居易等人对古诗律化的反拨,直至北宋初期,曾围绕古、近体诗产生过分歧,西昆体、台阁体以近体为主,欧阳修等人则大力提倡古体诗,尤其是七古呈现出“反律化”的倾向,而苏轼则援古入律(以古为律),*刘占召曾在《中国古代诗学中“以古为律”思想的演进》(《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以古为律”是中唐以来出现的一个重要的诗学观念,即律诗在创作过程中借鉴古诗的修辞技巧、篇章结构、表现功能、审美趣味和创作精神。其相关论文还有《“以古为律”与杜甫七律艺术的革新》,《安徽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其古体诗也借鉴了律诗的创作手法,纠正了韩、欧等人的矫枉过正。
宋代李之仪《谢人寄诗并问诗中格目小纸》中曾提到近体诗的形成过程:“近体见于唐初,赋平声为韵,而平侧协其律,亦曰律诗。由有近体,遂分往体,就以赋侧声为韵,从而别之,亦曰古诗。格如律,半格铺叙抑扬,间作俪句,如老杜《古柏行》者。”*李之仪:《姑溪居士全集》卷一六,《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9页。这段话可以代表当时一般宋人的理解,即古诗只能偶尔出现俪句(对仗)。此后张戒《岁寒堂诗话》在比较唐人古律诗的创作时说:“韦苏州律诗似古,刘随州古诗似律,大抵下李、杜、韩退之一等,便不能兼。”*《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60页。这说明张戒认为律诗似古或古诗似律并不能算作杰作。而苏轼在古诗中加入对仗是一种反常规的做法,*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64页)中指出:“真正的好诗不在于结构的工整规则,而在于合常规与反常规、合形式与非形式等多种对立因素的辩证统一,如杜甫诗一样,‘稳顺’而‘奇特’。具体说来,在律诗当用对仗处,出之以散体,在绝句不当用对仗处,又出之以骈体。”他舍弃了李白、欧阳修的七古熟调,对作诗难度进行挑战,结果是他的古诗既有形式美,又能达到流变健拔的风格。另外据《岁寒堂诗话》的记载,苏轼似认为古诗免不了使用律句:“东坡评文勋篆云:世人篆字,隶体不除,如浙人语,终老带吴音。安国用笔,意在隶前,汲冢鲁壁,周鼓泰山。东坡此语,不特篆字法,亦古诗法也。世人作篆字,不除隶体,作古诗不免律句,要须意在律前,乃可名古诗耳。”*《历代诗话续编》,第454页。郭绍虞《清诗话前言》中曾指出,写古诗而讲究声调,自赵执信《声调谱》始,但赵氏作《谱》之动机实受王士禛的启发。而本文认为,苏轼实际上已经注意到此问题。
明代有人提出“古不可涉律”的看法,如李东阳就认为“古诗与律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然律犹可间出古意,古不可涉律”。*李东阳:《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第1369页。清代王士禛更是将押平韵的古诗使用律句视为大忌,他指出“古诗要辨音节。音节须响,万不可入律句”,并曾多次表达这一见解:“七言古自有平仄。若平韵到底者,断不可杂以律句”,“七言古平仄相间换韵者,多用对仗,间似律句无妨。若平韵到底者,断不可杂以律句。大抵通篇平韵,贵飞扬;通篇仄韵,贵矫健。皆要顿挫,切忌平衍”。*引文分别参见何世璂:《然镫记闻》、王士禛《王文简古诗平仄论》、郎廷槐:《师友诗传录》,《清诗话》上,第121、230、137页。翁方纲批评了这种论断:“古诗之兴也,在律诗之前,虽七言古诗大家多出于唐后,而六朝以上,已具有之,岂其预知后世有律体而先为此体以别之耶?是古诗体无‘别律句’之说审矣。”*王士禛:《王文简古诗平仄论》,《清诗话》上,第235页。翁氏抓住了王士禛论七古总是以唐宋大家等人的作品为例,其实从整体概观诗歌发展过程来说,平韵古诗是逐渐律化的,所以翁氏的批评更有道理。事实上,苏轼不仅在押仄韵和篇中换韵的古诗中大量使用律句,其押平韵的诗作亦使用律句,如上面提及的《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一诗,亦可称为古律。清代更有作者有意在押仄韵或转韵的七古中加入律句,如深受王士禛平仄论影响的梁章钜就提出:“七古有仄韵到底者,则不妨以律句参错其间,以用仄韵,已别于近体,故间用律句,不至落调”,“其篇中换韵者,亦可用律句,如少陵之《丹青引》,东坡之《往富阳新城》皆是。而王右丞之《桃源行》,凡三十二句,律句至二十三见。此皆唐宋大家可据为典要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二十二,《二思堂丛书》,光绪元年刊本。因此,郭绍虞在《清诗话前言》中提出了中和之论:“声律之论,古调律调确有分别。古调乃自然之音调,律调则人为的声律。所以古调以语言的气势为主,而律调则以文字的平仄为主。”*郭绍虞:《清诗话前言》,《清诗话》上,第20页。
前人评价七古往往用纵横阖辟、抑扬顿挫、气势雄健等语,创作七古时“拟古”的意愿可能比创作五古时更淡薄,但从柏梁体以来,古体诗审美或以意象奇瑰为高,或以叙事酣畅为美,如胡应麟《诗薮》所云:“古诗之妙,专求意象;歌行之畅,必由才气;近体之攻,务先法律;绝句之构,独主风神。”*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页。从对仗这条线索或许可以探索出七古的内在规律,这正是本文目的所在。
(责任编辑:庞 礴)
TheAntithesisinSuShi'sSeven-CharacterAncientVerse—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Use of Tonal and Rhyme Patterns in the Ancient Poetry
Zhang Tao
The pre-Tang poetry does not require the use of antithesis. Based on the poems from Du Fu, Su Shi promoted the pre-Tang style to the same high level aslushi, the rhymed poetry. In addition, the rhythms and patterns of Su Shi's poetry are very close to those of thelushi. This attitude of creation is much bolder than Ouyang Xiu's conservative view.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ole and status of antithesis techniques in the Seven-Character ancient verses, it can be found that Su Shi's Seven-Character ancient verse has certain particularity in the Song Dynasty. Su Shi inherited the style of the poetry of early Tang poets and Du Fu and created a new style, while he found his chief examiner, Ouyang Xiu, inherited the style of Li Bai. Su Shi exerted his talents among poets of Song dynasty focusing on the meaning of the poem, and formed a great and special style that is called “ancient poetry similar tolushi”.
Su Shi,the Seven-Character Ancient Verse,antithesis,the ancient poetry similar tolushi
I207.22
A
1006-0766(2017)06-0028-10
张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成都 610064)
2015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中日两国对宋代文学的接受”(2082704184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