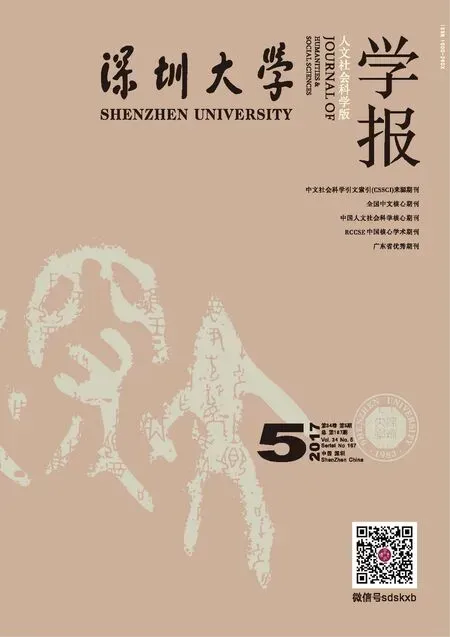中国话语建设的新路径
——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的对话
曹顺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中国话语建设的新路径
——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的对话
曹顺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在中国学术界,由于对西方学术话语和西方文论的过分依赖使得中国文学理论脱离了现实文化的土壤,陷入长达数十年的“失语”困境。随着新时期文论30年的发展,我们也开始逐步反思当前中国文论的现状,并积极探索话语重建的有效方案。中国话语的重建应以实际的生存经验为基础,充分利用好当下现有的文论学术资源,实现对中西文论的整合,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的对话就是促成中国话语建设的新路径。古代文论是中国传统的话语资源,西方文论又是当代主要的言说语境,两者的对话对于中国文论的重建和今后的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文论话语可从中西对话的当下语境、理论支点、对话的话题与言说方式等方面着手深入建设。
中国话语建设;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论;当代西方文论;对话;重建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已经习惯套用西方理论,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殊不知如果不把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文化土壤相结合而盲目地套用,这么做是会出问题的。季羡林先生很有感触的指出:“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1]。中国当代,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其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1995年,我提出了中国学术与中国文论的失语现象:“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等的表达、沟通、交流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我们没有一套自己的学术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学术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进行学术研究。本文认为,我们在引进及应用西方理论的時候,不应该把它当作绝对的真理,而应该加强对话,注意它的适用性,注意西方理论的中国化,注意其异质性与变异性。
习近平主席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2]
怎样改变中国文论的失语现状?怎样建设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本文认为,加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对话,应当是中国话语建设的一条新路径。
笔者认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学术资源,大致有三个传统,一是中国古代文论,二是俄苏文论,三是西方文论。从历史源流上来看,古代文论是我们自己的文论资源,但“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后,再难找到其言说语境,一直举步维艰;俄苏文论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我国文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改革开放以后,逐步从人们的话语中淡去,成为一种历史记忆;西方文论虽然在“五四”时就有所接触,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蜂拥而入,成为当今文论的重要话语资源。
西方文论自有其深厚的发展传统,有其产生的文化根源和背景,而我们的引入却基本上是一种共时性、平面化的引入。第一是拿来,从柏拉图到德里达,几千年的演变浓缩到几十年内来吸收。一时间风起云涌,云遮雾障,各式各样的西方思潮都在中国的学术界演练了一遍。呐喊厮杀声中都是西方文论话语的硝烟,而中国文论却哑然失语。
改革开放已经30年,新时期文论也已经走过了30年。斗转星移,尘埃渐定,我们逐步开始分析和思考,在拿来的基础上甄别与挑选,在失语的困惑中转换与重建。不论是西方文论的研究还是古代文论的阐发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从总体上看,现当代中国文论还是隐而不彰,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没有一个大体的轮廓,没有一个明晰的面貌,没有呈现出自己独立成熟的理论形态和话语系统。
我们究竟要重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文论?这是面对现实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首先,有一个方向是清楚的,那就是整合中西文论,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其次,如何创新,怎样创新?中国文论的发展迟迟没有突破,就是在这个关节点上我们的思考还不深入。
首先,我们不能指望创造一个包打天下的文论。这种情况在人类认识的早期出现过,如先秦的“诗言志”,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摹仿”。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书写性灵和现实的文学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而复杂化,千姿百态,面目各异,不可能服从某一条定律。我们不可能再创造出一种文论能囊括古今文学的阐释。所以说,我们未来的文论肯定是多元的。不同的理论交杂共呈,提供不同的思路对文学进行多视角多维度的阐释。因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应是文学理论的常态。
其次,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的完成中国文论的建设。我们的文论总是在不断的言说之中,不断的建构之中。中国文论的建设成功不在于提供一个本质的答案,而在于能给出对文学及其现象的有力阐释或是独到见解。因为文学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本质,如果有,那也是我们建构出来的,而且一直在我们的构建之中。虽然文学理论一直有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言说,或者说各个流派各种言说都试图揭示文学的本质,但都只是从一个方向,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每一种揭示也远非定论,它只是文论构建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3]文学理论也是这样。它的构建一方面指向文学的本质的揭示,一方面指向当下的生存体验。因此它一方面固守传统,在言说中不断追溯先贤;一方面随着社会思潮的变迁而变迁,参与甚至引领着社会思潮的发展。在构建变动中有历史传承,在历史传承中有当代气息,因此,它的发展永无止境。也就是说,我们未来的文论是动态的。
再次,多元言说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它们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各说各的,百花齐放,各论一隅,各持其论,各得其情,流派分明,各有千秋。当代西方文论流派纷呈,犹如春秋战国时期之百家争鸣,各家学说蜂拥而出,形成一个又一个学术高峰;还有一种就是冲突、碰撞、对话,最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面目各异的情景。如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学说的结合所产生的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都类似于此。
综上所述,创新也就有两条路径,一是在百花齐放中再绽一枝的原创。这种情况比较罕见,它不但依靠特定历史环境的孕育,也依靠特立独行天才的发现,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福科的知识考古学,这确实是前人所未思考过的角度,所未探索过的方向。他们的发现打通了一堵墙,后继者在他们的启发下继续往前挖掘,往往所获甚丰,逐渐形成一个流派,也形成思想史上再也无法忽略的资源。
还有一种就是在对话中激发,在继承中创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进一步,积微渐进,局部创新。面对古今文论丰富的学术资源,这是我们比较可行的扎实的创新路径。在对话的过程中,更加深入的理解前人的言说,在前人的激发下有一点自己的独得之见,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之于陆机的《文赋》,荣格之于弗洛伊德;或者是能够让不同的言说在同一个场景里呈现,拼接出新的面貌,如海德格尔之于胡塞尔现象学和老庄道家思想的融合。中西文论对话采取的就是这后一种方式,相互交流,深入沟通,在前人的基础上试图有所发明。这也是积极稳妥地重建中国文论的道路。
一、西方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对话
对话与研究不同,研究的对象我们称作材料,它是冷静而客观的,而在对话里却没有客体的概念,对话双方都是以主体的姿态呈现。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谁和谁对话?其次是他们如何展开辩论的?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如同观赏一场精彩的球赛。因而,对话的价值就在于主体性的张扬。如果说研究如同写剧本,那对话就把这场戏搬上了舞台。
巴赫金说:“思考它们,就意味着和它们说话,否则的话,它们立即会以客体的一面转向我们。”[4]我们一直在讲中西融合,仿佛这些思想是客体的资源可供我们驱使。然而,在对话的场景里面,它们不再是被动的客体,它们成为了主体。它们是活跃的思想家,是游说的政治家,是激动的辩论家,总之它们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们在不断的言说,言说它们的立场主张。思想的活力和生命在于传播。不论是西方的还是古代的文论,都只有从书本文字中站起来,寻找到知音,产生共鸣;寻找到对手,产生论辩,那才能成为鲜活的思想。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在时间上跨越了传统与现在,在空间上联接了中国与西方,使得他们之间的对话成为了中西文论对话中的重头戏。西方文论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必须在中国本土找到话语支撑,古代文论要实现现代化转换,必须要在当代找到言说语境。古代文论是中国传统的话语资源,西方文论是当代主要的言说语境,两者的对话和磨合对于我们重建中国文论至关重要。
(一)当下语境:当代西方文论
中西文论对话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促进我国的文论事业的发展,解决我们当下的困惑和实际的问题。随着现代化程度的加深,我们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近,他们曾经的遭遇和困惑很多也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类似的病症使我们把求诊的目光投向西方现代话语资源。他们走过的弯路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取得的经验值得我们吸取。而流派纷呈的西方当代文论,各领风骚数十年,在西方急剧变化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反思,不断批判,一路披荆斩棘走过来,有很多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可以说,当代西方文论已经超越了文学理论的专业领域,与西方当代哲学一起,直接参与了西方当代价值理念的建设而纵横天下。
当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条线索,都和当代西方文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从人本主义一条线来看,这是文论的原初领域。尼采的哲学也是尼采的散文,萨特的小说也是萨特的哲学,更为重要的是,对人的关怀,是哲学的本分,也是文学的本分。对于人本主义哲学来说,文学所提供的社会范本是再好不过的人性分析范本,而他们的研究肯定要影响到文学理论。因此,人本主义哲学流派和文论流派它们自然而然的走到了一起,很多思想家同时也是文论家,如海德格尔、弗洛伊德,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的思想家们,等等。
现代科技的发展形成现代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使得科学理性成为当代主导性力量,逻辑分析的方法渗入到各门学科,包括“非其族类”的人文学科。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当代西方文论开辟了科学主义一条战线,使当代西方文论在研究文学自身的问题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古希腊哲学试图认识世界的本质;而笛卡尔、康德却追问这个认识何以可能,回到人自身及其认识能力;而现代哲学则进一步思考这个认识的工具——语言本身如何可能。因此,哲学家开始分析语言、分析形式:区分所指与能指、语言与言语,历时与共时、转喻与换喻,分析层次、功能、模式、结构,分析世界是如何被叙述被构建出来的,这些分析促使了文学理论转向自身内部,做精细的科学研究与分析,形成了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一批影响深远的流派。
没有哪个世纪的文学理论有20世纪西方文论那样丰富多彩,也没有哪个世纪的文学理论象20世纪西方文论那样掀起全球性的风暴,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它们也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思想风暴,成为当今学界所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因此,当代西方文论成为我们所选择的对话主体之一。
(二)理论支点:中国古代文论
对话不是独白,它要求对话双方各自有各自独立的话语,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平等有效的对话。对话西方当代文论,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的理论支点,这就是古代文论。这一方面是现当代文论罹患失语症的无奈。回首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历程,“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救亡压倒一切,启蒙与革命使文艺成为宣传;解放以来,苏联文论随着苏联模式红遍社会主义阵营。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论的引进开拓了我们的视野,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但是,不自觉的又一头陷入西方文论的藩篱。直到如今,失语症仍然是现当代文论界最明显的病征。如陈伯海先生说:“中国现代文论话语之所以不能当作本根,还因为从总体上看,它尚未建成成熟的理论形态,不足以支撑起一套新的话语系统。”[5]
我们认为:“进行异质文论的对话首先应该掌握‘话语独立’和‘平等对话’两条基本原则。 ”[6](P138)现当代中国文论深受西方文论侵染,无法脱离西方文论的言说,未曾独立,也就谈不上什么平等。而古代文论是在中华文明中孕育出来的独立的话语系统,有自己的根脉和体系,有自己的话语规则和言说方式:“一是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二是儒家‘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解经’话语模式。这两条主线生成又派生出众多的附属生成规则,如言不尽意、立象尽意、微言大义等等,支撑起枝繁叶茂的中国学术。”[7](P8)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规则独具特色,与西方文论有着从根子上就截然不同的异质性。这形成了她与西方文论对话的天然条件。
另一方面在于古代文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理解古代文论,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我们自身,才能在传统与现代的过渡中回旋转身。和西方当代文论不断深入批判当下西方社会中的种种问题相反,我们近百年来批判的目标不是指向当下,而是指向过去,指向传统,从“反帝反封建”到“破四旧”等不一而足。总以为是传统思想束缚了我们的发展,造成我们的落后。百年来的批判割裂了我们的传统,对于古代文论我们也产生了隔膜。在当今西方话语盛行的时代,听听古代文论的言说,能唤起我们的集体无意识,唤起我们的民族记忆。也是在西方文论的参照下,我们能冷静地审视我们的文化传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特质。张首映先生认为:“西方20世纪文论还有一种‘小处精细,大处迷茫’的小家子气倾向。”[8]西方文论新锐犀利,但常常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深刻与偏见共存,启示与迷茫同在。传统深厚的理论资源,历经岁月千年的淘洗锤炼,它的浑厚和大气正好作为西方当代文论的参照。这种参照也许能在《庄子》中找到隐喻: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人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徐无鬼》)
郢人与匠人,一个大智若愚,一个大巧若莽,二者截然不同,然而却相得益彰,相互为质,相互成就。庄惠之交,濠梁之辩(《庄子·秋水》),中西文论对话亦有似于此。审美的庄子有艺术家的气质,认知的惠子有逻辑家的辩才,截然不同的个性成就了他们的辩论与友谊。批判的西方当代文论与审美的中国古代文论截然不同的异质性,他们的交锋也定是颇为精彩。
二、对话的话题与言说语境
当代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走到了一起,讨论些什么呢?如何开展交流、沟通与对话呢?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讲:“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从第六篇《明诗》开始,细论各类文体,基本是按照这个程式进行的。我们便依古人之例,略加变通,改造成中西文论对话的方法,或许可行。论述路径如下:
(一)原始以表末:西方文论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
原始以表末,对西方当代文论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情况做一个历时性的梳理。理清西方文论传入中国的来龙去脉,了解现有研究状况,是构建对话语境的基础。
从历史上来看,当代西方文论传入中国主要有两个时期,第一次是“五四”前后,以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鲁迅等对西方思潮的译介和传播为代表,打开了国人的眼界。这次引进在解放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而归于沉寂,但也有暗潮涌动。第二是改革开放后的全面引进,波澜壮阔,目不暇接,而又与时代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时代步伐中,引进西方文论,破除僵化思想,激发了人们极大的学习讨论热情。 1985 年人称“方法年”、“批评年”、“文化年”,人们争相用西方当代文论的各式方法理论解构长期盘踞的阶级思维专断模式。从90年代初到20世纪末,学术上少了些冲动,更多了些反思,西方文论的引进也进入了更高一层的消化研究阶段。尤以1996年“失语症”和“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为热点,回到重建中国文论的道路上来,更为理性地对待西方文论。而从21世纪初到现在,全球化浪潮加速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脚步,我们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几乎形成了同步共振的态势。
而在大体的演变过程中,西方文论各流派在中国的境遇也不尽相同,这或多或少取决于中国社会的接受程度。比如80年代,初登陆的新批评、结构主义在中国热极一时,对文学形式研究的重视实际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驳。而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女性主义批评、殖民主义批评等后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直到90年代以后,当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也遭遇西方后现代式的精神危机的时候,才逐步热起来。因而,“原始以表末”,在历时的流变中梳理每个流派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遭遇以及它与中国问题的契合度与关联度,它在中国接受的深度与广度,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二)释名以章义:同题共论中西观点
展开中西文论的画卷,对比强烈的色差使我们不得不首先找寻它们的共同点以寻求沟通的可能。不同话语共同话题、不同路径共同走向、不同规则共同规律都是可供切入的交汇点。在这些交汇点上,所谓“释名以章义”,就是在对话的过程中敞开各自的阐释和立场,揭示各自的角度和观点,搭建对话沟通的话语平台。这种讨论不是一定要得出什么结果,而是聆听双方的声音,彰显双方的释义。
1.不同话语共同话题
《在对话中建设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论中西文论对话的基本原则及其途径》一文中,曹顺庆、支宇先生就提出“不同话语与共同话题”作为中西异质文论对话的具体途径之一[6]。展开异质文论的对话,掌握好原则和途径[9],共同话题是一个很好的切入方式,也是最常用的切入方式。早在1988年,国内第一本比较诗学著作《中西比较诗学》[10]就将艺术本质、艺术起源、艺术思维、艺术风格、艺术鉴赏等五个话题作为中西对话的基本单元,然后在每个话题下展开中西文论的相关论述,使他们在各自的言说中揭示出中西艺术共同的规律。
当代西方文论流派纷呈,每一个流派都有它的侧重点。他们往往在一个问题上深入下去,将其推到极致,形成一种“片面的深刻”,然后掉头,又开发另一块处女地。它的新意和深刻在于立场和角度的不同,但话题往往还是古老的话题。比如说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陆机讲“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文赋》),刘勰在《体性》中列“新奇”一门:“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韩愈说“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都有与之相通之处。再如接受理论从读者的角度切入文论,刘勰也曾在 《文心》中专列《知音》一篇,提出“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讨论读者的偏好与作品的接受问题。同一处风景或许在中西画家笔下风采各异,但他们毕竟画的都是同一棵树、同一座桥。因此,虽然时空迥异,但中西文论都有共同关心的话题,可以就此基础上展开讨论。
2.不同路径共同走向
不同的路径如同登山,前山后山的风景不同,但山顶是共同的目标。中国的内陆型文明与西方海洋性文明起源虽然迥然不同,都展开了对宇宙人生的思考。虽然各自的路径不同,古希腊的“逻格斯”,中国的“道”,一可说一不可说,但都指向以语言为阶梯的对宇宙规律的揭示。而文学本是人学,中西文学和文论其实都绕不开人性的探索。精神分析的压抑说和古代文论的发愤著书说,一个从性压抑的角度进行潜意识分析,一个从历尽磨难奋发图强的人生态度上分析,路径虽然有所不同,但都从作家心理寻找创作动机,得出“病蚌成珠”的结论。
3.不同规则共同规律
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都是根植在各自文化传统中,有着各自不同的话语规则。熟悉古代文论的中国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伊瑟尔提出的“文本的召唤结构”和传统“意境”理论的“虚实相生”、“韵味无穷”有着类似之处。然而,“‘意境’的范畴成熟虽晚,但是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庄子的言不尽意、‘得意而忘言’,到钟嵘的‘滋味’说、司空图的‘韵味’说、严羽的‘兴趣’说,直至王国维的‘境界’说,我们可以看到仿佛有一条隐约的红线贯穿始终,这就是深藏在范畴后面的文化规则。”[7](P7)意境后面是深于体味领悟的“道”不可言的中国文化规则,而“召唤结构”后面却是西方式的剥笋抽茧式的逻辑演绎文化规则。伊瑟尔从文本与读者两极的关系出发,对文学作品如何调动读者的能动作用,以及文本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了怎样的预结构提出设问。这种预结构从空白、填空、追问、召唤中一点点的揭示出来,体现了逻辑清晰追求真理的西方文化规则。“召唤结构”与意境理论殊途同归,说明从不同的学术规则出发,我们也能探寻到文学艺术的共同规律。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11]。
(三)探源以辨异:类似论述不同根源
中西文论对话的价值,一方面在于寻求文学的共同规律,一方面还在于对于各自异质性的确证。“所谓异质性,是指从根本质地上相异的东西。就中国与西方文论而言,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文明,在基本文化机制、知识体系和文论话语上是从根子上就相异的(而西方各国文论则是同根的文明)。 ”[12](P26)所谓探源以辨异,就是不仅仅看到表面上的同,还要进一步深究其根源上的不同。这也是中西文论对话进行之后更深层次的要求。在引发对话、展开对话、活跃对话的愿望下,对话双方“求同存异”,尽量就某些共识交流意见,如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都是这类著作。这样的对话能促进双方的交流,但真正牢固的友谊还应该建立在进一步理解的基础上。因此,更深层次的对话一定会涉及到双方异质性的探讨,也是在对异质性根源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双方能互以为质,在对比中更加深入地认识自己。
1.类似现象不同成因
中西文论成长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之下,有些观点和论述不谋而合,但细加咀嚼,就会发现它们后面的结构背景、文化支撑其实是不同的。例如,西方现象学文论传到中国,引起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乃是由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与中国传统思维颇为类似之故。但其实二者之间有着绝大的不同。胡塞尔的“本质直观”是科学分析式的,它通过加括号的方式悬搁了经验主义的态度,这和古代文论的目击道存的顿感领悟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思维路径。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在批判西方传统的主客体两分的思维模式下产生的。他通过“意向性”这个关照动作将“意向性主体”和“意向性客体”融合到一体,这和中国向来不分主客体的浑然思维又有一致之处,但实际上胡塞尔的意向性是针对个体的、有确定对象的,与中国的浑融完全不同。中国的天人合一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并没有确指的。在这些类似现象的背后,我们加以深入的辨别与分析,就可以看到中西文论类似的说法后面有着非常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思维模式和出发点。
2.类似结论不同指向
“慧子曰:狂者东走,逐者亦东走,其东走则同,其所以东走之为则异。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审察也。”(《韩非子·说林上》)同是东走,一奔一逐,貌同而神异。西方当代文论是在对西方文化的批判过程中发展而来,都有着现实的内在意义。如俄国的形式主义标立“文学性”及其名言:“艺术永远独立于生活,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其实只要听听他们的宣言,看看他们兴起和零落的年代,我们就知道它其实以标榜形式逃避和反抗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政治话语。新批评在美国兴起,摈弃文学的外部研究而着力于文学的内部研究,其实和美国这个新兴国家没有多少历史可供外部研究也有关系。而同样是对形式的重视,李清照的词“乃知别是一家”(李清照《词论》),是对苏轼等“学际天人”以文入词的不满,为词争取一个独立的地位,和当时的政治没有什么深刻的联系。
因此,在中西文论对话的时候,不仅要听它们说了些什么,要辨析它们言说的思路和根源(也就是异质性),更要比较思考各自言说的目的和指向,也就是它们的话语试图达成的力量。这样才能吸收双方思想精华为我所用,而不是我为其用。
3.杂花生树范畴共生
对话寻求的是理解,不是争个谁是谁非,不是一方压制另一方,也不是强势话语的一家独白。杂花生树、范畴共生让异质性话语都有言说的空间,互证互识,共存共生。“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并处理中西文论的异质性,则很可能会促使异质性的相互遮蔽,并最终导致其中一种异质性的失落。”[12](P26-27)异质性最好的保护就是保持其原生态,异质共生,保持其独立的品格,形成真正的“和而不同”。“江南三月,暮春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丘迟《与陈伯之书》)西方文论争奇斗艳,古代文论枯木逢春,杂花生树春满园,范畴共生百花开。
[1]季羡林.东方文论选·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2.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D/OL].http://www.xinhuanet.com.2016-05-18.
[3](意)B.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J].田时纲译.世界哲学,2002,(6):6-22.
[4]朱立元,李钧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86.
[5]陈伯海.“原创性”自何而来——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构建之我思[J].文史哲,2008,(5):13-21.
[6]曹顺庆,支宇.在对话中建设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论中西文论对话的基本原则及其具体途径 [J].社会科学研究,2003,(4):138-143.
[7]曹顺庆,王庆.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重建[J].文史哲,2008,(5):5-12.
[8]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3.
[9]曹顺庆.跨文明文论的异质性、变异性及他国化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2).
[10]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11]张隆溪.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A].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92.
[12]曹顺庆.中国文论的“异质性”笔谈——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文论的异质性[J].文学评论,2006,(6):26-29.
【责任编辑:向博】
【】【】
New Method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Dialogues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CAO Shun-q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4)
Among Chinese academics,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s detached from reality and falls into the dilemma of“aphasia”for dozens of years as academics rely too much on western academic discour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theory for recent thirty years,we begin to reflect on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and explore feasible way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ory discourse.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should be based on practical survival experience.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existing academic resources to integrate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and be innovative on the basis of inherited traditions.The dialogues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re new method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Ancient literary theory is China’s traditional discourse resources,whil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represents current context.The dialogues between them are significant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literary theory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To construct Chinese literary discourse,we should start with current context and theory fulcrums of the dialogu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and topics of dialogues and way of communication.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literary theory;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dialogue;reconstruction
I 0
A
1000-260X(2017)05-0118-06
2017-09-12
曹顺庆,四川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