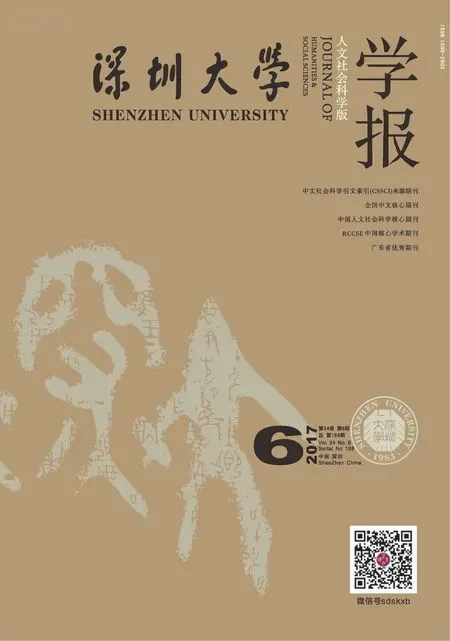论社会资本的社区公共空间向度
张勇
(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论社会资本的社区公共空间向度
张勇
(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社会资本理论是解释社会现象的重要分析框架,尽管学界对其内涵与外延有着多元化的理解,但一般认为社会网络、信任和互惠性规范等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和“公共性”等属性特征。作为社会关系发生场域的空间与社会资本之间有着内在的“互生关系”,社区公共空间因其所具有的特殊“公共”空间属性,在作为社会资本承载体的同时,也“创生”着社区社会资本。社区公共空间通过居民行为活动、心理思维习惯等中介,对社区居民的社会交往网络的范围与交往密度、社区居民彼此间信任的基础与强度、社区规范的内容与互惠性程度、社区文化的载体形式与功能发挥等都产生重要的制约与影响,进而塑造着具体而多样化的社区社会资本。而社区社会资本在社区空间内创生和生长的过程,也是社会资本在社区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内渗透和呈现的过程,也塑造和改变着社区公共空间的存在形式与功能利用。
社区空间;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社会资本;社区规范;社区文化
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一种理论解释分析框架,以其深刻而且不断丰富着的内涵,对当前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解释,彰显着雄厚而神奇的解释力;作为一种实体性社会实践目标,社会资本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投资,是保障一个公民社会的重要公共资产,是构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一个决定性方面。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社会资本“使在不求助于利维坦之极端强制力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允许集体行为和合作的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成为可能。”[1]对于社会“细胞”的最基本单元——城市社区而言,社会资本是社区发展的核心要素。然而,一定的地域空间是社区的重要要素,特别是在我国“社区建设”或“社区治理”话语体系中,对社区作为“行政性社区”的表达中,社区是作为行政管理或权力覆盖的对象而存在,更具有行政管辖意义上的“地域空间”属性与色彩。作为社区空间特别形式的社区公共空间,以其特殊形式和存在发挥着特殊的功能,于是,我们要问的是,社会资本和社区公共空间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联?或者说,社区公共空间是如何影响和制约社区社会资本生长或培育的?这是本文所关切和力图解释的问题。
一、社会资本内涵及主要分歧
社会资本是一源于“经济资本”但又超越“经济资本”的概念。20世纪50年代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在经济学意义上首次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相区别[2],在此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后期,格伦·卢里(Glenn.Loury)首次提出了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对应的“社会资本”概念,在此,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已跨进了社会学的门槛。本文所言的社会资本主要限于社会学视角,但既使在社会学领域,对社会资本的理解也历经了不同的阶段,不同学者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既有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和林南(Lin Nan)从社会网络及其拥有社会资源视角[3]的研究,也有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对其“制度化的持久关系网络”的解读,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对“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体制化、持久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种“体制化网络关系”是与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获得这种身份就为个体赢得“声望”,进而为获得物质或象征的利益提供保证。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S.Coleman)对社会资本进行功能性的社会结构分析,认为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是一个共同体之内的行为主体在长期交往、合作、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的网络,这些网络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4](P337-345)。 而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对社会资本进行“特征性”描述,将社会资本概念高度概括为 “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并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4](P197)。除此之外,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的“获取资源能力”说[5](P29-143)、福山的“信任-繁荣”模式分析[6]、斯蒂格里茨(Joseph E.Stiglitz )的“非正式制度与市场”探讨[7],克拉克对于“社会资本支持经济福利”的论证、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对“自主治理体系的社会资本”研究等等都从不同视角和层面对社会资本进行过解释的努力。当然,最为经典的莫过于皮埃尔·布迪厄、詹姆斯·科尔曼和罗伯特·帕特南的解释。
可见社会资本内涵有着差异化的理解,导致其差异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部分来源于各自的学科视角及强调侧重点不同所致,学界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或利用主要体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三大领域,每个学科都有着自身的学科侧重点、研究范式和规范,使之对社会资本有着不同的理解;一部分来源于学者采取的不同分析层面所致,如周红云研究员认为在三种经典的社会资本定义当中,布迪厄定义可谓微观定义;科尔曼的定义属于中观范畴;而帕特南的定义则是宏观层面的定义[8]。托马斯·福特·布朗(Thomas Ford Brown)从系统主义视角对社会资本进行微观、中观和宏观分析,力图对社会资本概括出一个理论化的定义。他认为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是一种嵌入自我的观点,关注的是个体通过他所嵌入的网络来调配资源的潜在能力;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研究采取的是一种结构观点,侧重于网络的形成、集体的行动和成员间义务与权利的分配;宏观层面上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则持的是一种嵌入结构的观点,主要考虑社会资本在其中运作的网络是如何嵌入到更大的政治经济或文化规范体系中去的[9]。
二、社会资本内涵的学界共识
众多学科之间理解虽然有差异,但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在“社会资本”这个节点上进行了汇合,“在社会资本身上,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决策者以及各个领域‘内’的各阵营,又一次找到了一种存在于公开的和建设性的争论中的共同语言”[10],这恰恰体现了“社会资本”概念作为一种解释框架所具有的深厚解释力。总的来看,不论是布尔迪厄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社会网络,还是林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或者科尔曼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便利于行动者的隐藏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还有普特南强调的社会资本是一种规则、网络与信任,应该说都有着一定程度的相通、相似或相关性,特别是在社会学领域,学界对社会资本的内涵和特征已取得一定共识。
(一)社会网络、信任和互惠性规范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
上述对社会资本概念的梳理中,尽管皮埃尔·布尔迪厄、科尔曼、罗伯特·帕特南等对社会资本有着差异化的理解,但其共识也逐渐显现,从帕特南开始,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是观测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厄普赫夫(Norman Uphoff)将社会资本归分为结构社会资本和文化社会资本两种紧密联系的社会资本,并认为文化社会资本主要指规范、价值、态度、信仰、信任、互惠等心理过程[11];福山(Fukuyama)也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5](P72)。我国的杨雪冬研究员认为“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上的)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沉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规范”[12]。从上述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对社会资本进行结构性的理解、功能性的解读,还是特征性的描述,尽管对社会资本的本质是结构、资源还是能力存在着不同理解,但其内在要素都与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紧密相关,因而,作为一种解释框架或分析范式,网络、规范和信任是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或分析的主要进路或向度,也是观察和测量社会资本的主要观测点,于是,社会的信任度、行为规范特征和连接网络的紧密程度成为衡量社会资本的重要依据。
(二)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
所谓社会资本的“生产性”包含两个层面含义:一是指社会资本具有“正”的社会作用或功能,有利于个人、团体的发展,能够促进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进步,突出的体现在促进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增长”上;二是指社会资本本身在“创造”生产着新的社会资源或社会关系,“创造”生产着新的社会结构或者称之为社会资本自身的“生产”,体现在社会资本自身的拓展与变迁。20世纪70年代初,格兰诺维特研究发现求职者所具有关系网络与求职是否成功之间有直接关系[13],我国边燕杰的研究结论尽管和格兰诺维特的结论相反,但也认为社会网络关系的强弱与社会资源的获得和行为目的的实现具有相关性[14]。林南认为社会资本可以使个人更好地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能够“为成员获得物质或象征的利益提供保证”,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15],波茨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作为家庭支持的来源、作为通过家庭外的网络获得的收益来源”三项正功能[5](P129-143)。 上述对社会资本“生产性”理解的两个层面实则为同一过程,社会资本在促使人们在社会结构中利用所处的特殊位置而具有了获取利益的能力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着人们间的交流和相互关系,带来社会关系的产生或转型;社会资本在提高社会的效率和社会整合度,促进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将网络中的主体置于更丰富、更广泛的关系网络中,从而为其获得更多的资源提供了可能。社会资本发挥“生产性”功能的关键在于其对资源的产生及配置发生作用,而其背后,则在于社会资本促使主体所处和所能够利用的社会网络扩大而且有效,促使主体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和强化,促成交换规则的形成和有效运行。
(三)社会资本具有“公共性”
从社会资本的直观存在状态和来源来看,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中,产生于持续的人际互动交往过程中,从布迪厄开始,理论界多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于群体之中,存在于群体关系网络中,社会资本的存在及其发挥作用具有相互依赖性,在一定意义上,社会资本更具有集体特性而不是个人的特性,虽然群体中的个人可以利用社会资本以获取资源或以此具备某种能力,但这种社会资本形式的获取与占有并不完全受个人支配,个人对社会资本的获取与利用,实则必须依赖于他人。不论是社会网络还是信任,都是双方或多方主体的范畴,单个人无法形成网络,信任也是双方或多方才能存在,而互惠性规范的形成,既然是互惠性,自然是彼此相互协商而成。因此,社会资本具有公共性,只能为一个群体所获取,不可能仅靠个人的力量来获得。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品特征是社会资本和其他形式资本最基本的差别”[16],而所谓公共品特征,其中最为直接的体现之一就是其功能的“外溢性”或“外部性”,即群体中的社会资本一旦形成,其网络中的成员或主体,因其具备该群体的成员身份,都可以通过相应的“关系”或“联系”来利用该网络并获取相应的资源,不论之前其是否是积极的参与到该社会资本生产。于是,社会资本的存在也给该网络成员提供了“搭便车”的可能,这种社会资本的“外部性”给社会资本的延续和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和冲击,也是在实践中应该努力避免的。
三、社区公共空间及其生产性
根据社区空间的开放程度,可以将社区空间分为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公共空间指那些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常见的包括街道、广场、居住区户外场地、公园、体育场地等,是居民参与、交流与互动的重要交往场所;半公共空间具有两种形式:一种半公共空间是指几个群落共同构筑的,属于这些住宅群落居民共同拥有的街坊、居住小区或居住区外部空间;另一种半公共空间是指那种产权归属私人,却向公众开放的空间,如城市的戏院、茶馆、商场等等。而私密空间一般指为保护个人隐私性、具有很强的排外性的私人空间,如家庭。本文所论及的社区公共空间包括社区公共空间和社区半公共空间。社区公共空间最大的属性特点是功能上的“公共性”和空间上的“开放性”,二者紧密相关。空间上的“开放性”意味着对一定范围内的所有人开放,所有人都有进入的机会与可能;功能上的“公共性”意味着该空间是居民开展公共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居民公共性培育和生长的重要空间。
社区公共空间首先是一个物理空间或地域空间的客观存在,社区公共性的物理空间不仅是居民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承载体,也“创生”着社区的“社会空间”及其社会关系,列斐伏尔称之为 “社会空间生产”。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生活领域、社会生活层面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构成了社会空间的基本意蕴,社会空间的“生产”以物理空间为客观基础,人们在进行社区物理空间“生产”的同时,也改造着自身和自身的精神世界,创生着各种社会关系,“生产”着新的社会生活领域和社会生活层面,居民生活方式、精神世界也在实践中发生着或明显或潜在的变化,社区文化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迁。人类在空间中的实践活动是一个从“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生产”的实践过程,人类生存空间在实践中日益扩大的过程也就是空间生产过程[17]。社区公共空间影响和制约着社区社会空间生产,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一方面,社区物理空间是社区社会空间“生产”的基础和前提,社区物理空间“框定”着社区社会空间生产的空间范围和领域,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空间“生产”的形式、路径与结果;另一方面,社区公共空间制约和影响着社区居民的行为方式,对居民活动具有前置性制约作用,特别是对居民的行为方式与心理产生直接重大影响。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面对不同社区空间的“框定”,居民都会“适应性”的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便更好的在空间生活,这种“适应性”过程往往最初是一种“被动”反射性行为,进而逐渐成为“习惯”行为,最后演变为“主动”行为。社区空间在型塑着居民行为的同时,也影响着居民的思维和心理,只是居民自身往往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或没有“有意识”地去主动“意识”这种现象,而社区外的观察者,特别是带着“研究目的”的观察者,往往能清晰地感知或发现社区居民的思维观念与心理特征都打上了或多或少的社区空间的烙印。也正是因为如此,一个社区中的居民行为与心理习惯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或共性,进而形成各自独特的社区文化,这也正是“此社区”区别于“彼社区”的重要依据和标识。总之,“一定的社区空间型塑该社区居民的日常行为方式和规律,型塑着居民的思维习惯和心理特征”[18]。
四、社会资本的社区公共空间向度
在城市社区这一微空间中,社区空间对社区社会资本的生长有着重要影响,A&M University的Bin Kang博士通过对美国及中国社区将近五年时间的长期跟踪和研究,认为城市社区的户外公共空间及公共空间中人的活动对社会资本有重要影响[19]。社区本质上是居民社会生活共同体,而“社区共同体的营建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这种良性互动必须依托于公共空间的平台才能得以实现”[20]。该“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特殊属性在于其“生活性”。社区空间是居民日常生活活动的空间,因社区公共空间具有“开放性”和“无门槛性”特点,社区公共空间成为居民休闲娱乐、锻炼、聊天交往、开展文化活动的重要空间,也是居民开展群体性公共活动的最佳选择场所,进而也是居民社交网络建立的重要平台。在此类公共空间中的居民活动,具有日常性、频繁性、利益无涉性等特点,是社区社会资本培育和积累的重要途径。
(一)社区公共空间与居民社交网络
社区空间是居民生活交往的基本空间平台,是居民社交网络形成及存在的重要制约和影响因素,社区空间对社区居民的社交对象、社交范围、社交形式和社交关系紧密性程度等都产生重要影响或制约,从而影响着社区社会资本的生长。
首先,社区公共空间影响着居民社会交往的内容和方式。居民社会交往的内容和方式多种多样,但社区公共空间是居民“日常生活性”交往活动的主要空间。所谓“日常生活性”交往是个人为了满足基本的日常生活需要而发生的交往活动,不仅是个人交往行为中最基础的部分,也是满足居民交往需求的最重要部分,同时,还是社区空间内居民交往活动的主要形式。居民“日常生活性”交往具有日常性、持久性和非正式性等特征,主要体现为居民的娱乐、聊天、生活互助等活动。也正是因为此类交往行为的日常性、频繁性特点,有利于居民交往行为的深入和彼此关系的紧密;同时,社区公共空间的“日常性”交往行为,多具有利益无涉性、目的一致性等特点,使居民间关系不易因相互利益冲突而破裂,使居民社交网络具有坚韧性。当然,“日常生活性”交往网络中个体之间的关系最初可能处在格兰诺维特所言的 “弱关系”层面,但随着交往的频繁和持久,存在由“弱关系”逐渐转化为“强关系”的可能,其实,不论是“强关系网络”还是“弱关系网络”,均是社会资本生长的重要来源。由于居民交往内容的“日常性”,所以,也多是以“非正式”的、“面对面”直接交往的方式进行,具有交往“直接性”的特点。
其次,社区空间制约着居民社交网络范围与交往对象。特别是居民间“日常生活性”的交往活动多囿于社区内发生,其交往的对象也多是社区内生活的居民。科尔曼认为网络锁定与闭合是社会资本生成的一个重要组织特征,并构建了一个著名的 “闭合”模型[21]。社交网络的“封闭性”或“闭合性”是保持社会网络稳定性和社会关系稳定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而影响着社会资本的产生。社区空间范围是社区居民交往网络“闭合性”或相对“闭合性”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社区居民交往对象的相对固定,彼此间更容易熟悉,也更容易增加彼此信任度。这是社会资本生长的重要促进因素。当然,“流动性”和“开放性”是时代主流,居民社交网络边界得以空前扩展和向外延伸,居民交往对象日益复杂,使居民对社区内交往的依赖感减弱,在一定程度上冲淡着社区内社交网络的紧密性,但这种“跨越”社区空间边界的交往多是因居民为达到或实现某一具体目的而进行的“偶然性”或“间断性”社交行为,该社交活动是居民社会交往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实则是扩大社会交往网络范围、丰富社交网络的重要途径,有利于产生和积累更丰富的社会资本。
最后,社区公共空间影响着居民参与的形式、强度及其效果。居民参与是居民参与社会交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殊形式。与一般“日常性”社会交往不同,居民参与侧重于指社区居民通过一定的途径和形式参与社区公共性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表现为各主体在互动中所采取的制度化、合法化的参与方法和策略。一般说来,居民参与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社区层面上的政治参与;第二,社区公共管理中的参与;第三,有关社区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参与[22]。一方面,社区公共空间为社区居民参与提供了重要空间场所,甚至某些类似于“社区礼堂”的公共空间在原初意义上正是为居民参与而设。社区公共空间的大小、区位、设计及其设施配置,直接影响到居民参与的方式和效果,特别是传统的“面对面”形式的居民参与,更对社区公共空间有着特别要求;另一方面,居民参与是社区居民本着公共精神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监督和管理,在社区公共空间内开展居民参与活动,有利于居民参与行为的“公共性”发挥,公共空间逐渐获得了“公共性”的象征意义,有利于良好的居民参与网络的建立。
(二)社区公共空间与居民信任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甚至有学者将信任等同于社会资本,不论是林南认为社会资本影响信任的生成,还是福山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结果,信任和社会资本有差别,但二者存在内在的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的关系。梅西克和克雷默认为信任是个体基于对他人行为是否会遵守或破坏道德标准所作的一种反馈行为,也被认为是施信者对他人可能行为的一种积极性的预期。卢曼将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人际信任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23]。这里所言的居民信任,主要指社区居民基于前述社区居民交往活动及居民行为规范的基础上形成的各主体相互间的信任,社区公共空间影响和制约着社区居民信任的产生及作用。人际信任产生于自然人之间的情感关系纽带,常发生于首要群体和次要群体中;而制度信任发生于更抽象的关系之中,依赖于制度环境 (如法律、政治、经济等相关制度)。社区在最初“生活共同体”意义中,其与“社会”相区别之一就在于社区内人际关系的情感纽带及道德规范,凸显社区内居民间的相互信任与相互关爱,而社区公共空间通过为居民交往提供空间,进而促进居民交往并以深度的方式生产着社区内的情感纽带,增进社区的情感信任;而现代社区居民间的信任更多地来源于认知信任,建立在知识和个体经历基础上的认知能力是认知信任发生的基础,而社区公共空间内的居民交往和互动,是促进居民彼此认知和熟悉的重要场所。同时,社区空间边界是促成社区内部成员产生团体意识和社区归属情感的重要因素,而这种团体意识和归属情感是增强社区内居民个人间信任的重要影响因素,而社区公共空间往往是社区团体意识和社区归属感的重要“演练场“和“培育场”,甚至是社区的“标识”,成为社区凝聚力与社区精神的承载物或体现,在祖克尔“背景式预期”理论中,当个体感知自己和他人拥有相同的符号、文化和对世界的解释系统等信息时,个体间更容易持有信任[24]。另外,信任作为一种对他人的积极预期,而这种积极预期信任建立在居民个人对他人信息的了解和掌握基础之上,通过掌握的有关信息来判断他者是否可信或在哪些方面可信。“施信者可直接从与被信任者的互动中获取有关信息,也可通过自身经历以及其他交往人员那里获得与被信任对象相关的信息”[25]。而社区公共空间多是居民相聚与交流的空间,也是信息的聚集空间,而且因公共空间内居民交往关系的多元性和交错性,使社区公共空间内的信息量丰富而多元,因而,社区公共空间成为居民彼此相互获得他人相关信息的重要场所和渠道,而且这种获得他人信息的方式在具有“近距离”或“直接性”特点的同时,也具有“丰富性”和“多元性”的特点。丰富而多元信息的获取为居民间信任提供重要基础。
(三)社区公共空间与社区规范
尽管学界对社会资本理解有别,但都认为 “规范”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要素,而且这种规范往往具有互惠性和非正式性。总体而言,社区居民行为规范包括制度性行为规范和非制度行为规范两大部分,前者既包括法律法规、政策等具有普遍效力、国家强制性的规范,也包括形成于社区内部、作用限于社区内的类似于村规民约的“居民公约”;后者主要包括融入社区文化中(也是社区文化重要表现形式)约定俗成的社区风俗习惯或社区惯例,虽然不具有国家强制性,但对居民具有道德约束力。而社区公共空间与居民行为规范特别是涉及社区公共利益的公共性规范紧密相关。首先,社区公共空间是社区公共公共性规范适用的重要空间或场所。社区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维护,离不开制度性或非制度性的社区规范,而社区公共利益或公共秩序之所以具有其 “公共性”,往往正是因为其在社区公共空间中存在,或其与社区公共空间紧密相关。而且,不论是制度性规范还是非制度性规范,其适用均要保持社区规范与公共空间之间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适性”,因而,社区公共空间的属性与特征影响和制约着社区规范的内容和特征。其次,社区公共空间是居民活动的重要空间或场所,特别是社区居民开展自治活动、互惠性活动,更是多集中于社区公共空间中进行,因此,社区公共空间不仅直接影响着社区自治活动、互惠性活动的开展及其效果,而且,居民自治规范或互惠性规范往往正是在多次的自治活动或互惠性活动中产生,所以,在社区公共空间中开展活动更彰显“自治”或“互惠”色彩,社区公共空间最终也影响着社区居民自治规范和互惠性规范的形成。
(四)社区公共空间与社区文化
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文化二者有着内在的内容上的相通性,社区社会资本是社区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体现;而社区文化影响和制约着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厄普赫夫甚至将社会资本归分为结构社会资本和文化社会资本两种紧密联系的社会资本形式,足见社区社会资本具有强烈的“文化”内核和特色。
因“文化”之概念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之多元分野,加上研究视角及领域的差异,社区文化概念之内涵与外延也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的社区文化,指社区居民在特定区域内长期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狭义的社区文化,是指社区居民在特定区域内长期活动过程中形成起来的,具有鲜明个性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等文化现象的总和”[26]。这里所言的社区文化是广义的社区文化,主要包括“社区物质文化(如社区文化公共设施、社区物质文化遗迹、文化机构、文化产业等)、社区行为文化(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社区制度文化(社区的制度、规范、习俗、惯例及仪式性文化活动等)、社区精神文化(社区文化价值观、社区精神等)[27],也包括“社区团体、组织等内容”[28]。社区文化与社区公共空间紧密相关。首先,社区公共空间本身是社区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内容呈现。不同的社区公共空间往往体现着不同的社区文化,甚至社区公共空间成为社区文化的象征或标志,如上海的“东方明珠塔”俨然成为上海的象征和名片,广州的“小蛮腰广州塔”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进步与繁荣的象征,“东方明珠塔”与“小蛮腰广州塔”在很多人的脑海意象中,已经成为上海和广州这两个城市的符号记忆。其次,社区公共空间是开展社区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社区文化活动特别是文化娱乐活动,具有“公共参与性”的特点,其理想的场所非社区公共空间莫属,社区公共空间不仅保证了居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性”,还扩大了社区文化活动的影响力。社区公共空间狭小或不足,成为制约社区文化活动开展的重要因素。再次,社区公共空间影响和诠释着社区精神文化。社区精神是社区的内核,是社区长期发展过程中精神文化积累的结果,而社区精神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物质载体才能存在,社区精神也正是通过物质载体得以彰显和传承。一方面,社区公共空间中象征社区精神的“象征物”是一个社区的精神的凝聚和呈现,社区精神“象征物”赋予社区公共空间特殊的精神和文化功能;一方面,社区公共空间及其内的居民交往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居民的价值观、思维观念与方式。最后,社区公共空间承载着社区居民的历史记忆与情怀。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自我认同是社区之“共同体”属性的重要基础和体现,也是社区精神的重要内容。而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历史记忆和情怀是促进居民社区认同的重要方面,也是居民社区认同的重要体现,同时,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历史记忆和情怀本身是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体现。
五、余 论
综上可知,社区公共空间对社区社会资本产生重要的制约和影响,但在新时期和新的技术条件下,“空间”的存在方式发生着变化,人们行为、社会交往方式和心理也发生巨大变化,这都要求我们在理论上进行积极回应。如,在互联网时代,大量的网络虚拟空间出现,早已打破传统的空间边界,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中,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探讨虚拟空间中人与人交往的方式、路径及网络有着何种特殊性,我们面临着虚拟空间又是如何创生和影响社会资本的问题。又如,因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居民社交网络得以空前的扩展和向外延伸,但也正是因为居民大量社交行为超出社区边界而向外延伸和扩展,从而使居民对社区内交往的依赖感减弱,在一定程度上也冲淡着社区内社交网络的紧密性程度。但同时,我们看到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但居民社会网络的紧密性程度也并非必然随着空间距离上的拉近而变得更加紧密,甚至因空间狭小和资源有限而带来相互间的竞争和排斥。所以,出现了社区空间和社会关系紧密程度的悖论,这种悖论在社会资本空间向度的视角上,我们又该如何解释?特别是对这种悖论中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和实证量化研究显得尤为迫切。还如,社会资本的消极性不容回避,有可能对网络以外的成员带来消极后果,波茨认为社会资本的消极后果包括:排斥或禁止圈外人获得收益,或者造成部分团体为了寻求他们自己团体利益而牺牲或损害更大团体的利益;团体壁垒带来团体成员义务增多,引发搭便车现象;社群或团体的规范可能限制成员的个人自由;用规范消除秀异,往往使获得社会资本的人受到社会环境中的规则的限制,并阻止其作出各种变革和创新等[5](P129-143)。甚至斯蒂格利茨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与市场这种正式制度相比有可能是缺乏效率的,并可能被挤出市场制度,特别是在解决道德陷阱和激励问题时,实际上会令事情更糟[7]。对于这些消极性,我们又该如何从社区公共空间角度进行理解?又该如何在利用公共空间的实践过程中进行回避?这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1]王华.中国社会资本的重构[J].思想战线,2004,30(4):5-10.
[2][美]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吴珠华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132.
[3]赵延东.“社会资本”理论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1998,21(3):18-21.
[4][美]罗伯特·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5][美]亚里山德罗·波茨.社会资本:现代社会学中的缘起和应用[A].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美]弗朗西斯·福山.公民社会与发展[A].曹荣湘.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72.
[7][美]J·斯蒂格利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A].曹荣湘.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115.
[8]周红云.社会资本及其在中国的研究与应用[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111(2):135-144.
[9][美]托马斯·福特·布朗.社会资本理论综述[A].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77-100。
[10][美]迈克尔·伍考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一种力量的综合和政治构架[A].郗卫东译.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01.
[11]Norman.Uphoff.Understanding social capital:learning from the analysis and 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on[A].P Dasgupta and I Serageldin (eds.).Social Capital: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C].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1999.215-249.
[12]杨雪冬.社会资本:对一种新解释范式的探索[A].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6.
[13]Granovetter.M.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6):1360-1380.
[14]Bian.Y.J.Bring Strong Ties Back in:Indirect Ties,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7,63(3):366-385.
[15]李惠斌.什么是社会资本[A].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
[16][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349.
[17]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 Smith.Oxford UK:BlackwellLtd,1991.24
[18]何艳玲,张勇.论城市社区治理的空间面向[J].新视野,2017,202(4):84-91.
[19]杨力,邱灿,红康彬.基于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城市社区空间规划研究[J].山西建筑,2008,(11):27-28.
[20]龚建华,李永华.“良性互动”视野下的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3(2):146-150.
[21]张广利,桂勇.社会资本:渊源·理论·局限[J].河北学刊,2003,23(3):17-22.
[22]王敬尧.参与式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2-14.
[23]E.M.Uslaner and R.S.Conley.Civic Engagement and Particularized Trust[J].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2003,(4):331-360.
[24]L.Zucker.Production of Trust: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1840-1920[J].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1986,(8):53-111.
[25]邹宇春,敖丹,李建栋.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格局及社会资本影响——以广州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2,(5):131-148.
[26]奚从清.社区研究、社区建设、社区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93.
[27]杨敏.历史视域下的社区文化建设新趋势[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54(5):29-37.
[28]刘庆龙,冯杰.论社区文化及其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7(5):19-24.
On Community Public Space Dimension of Social Capital
ZHANG Yong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Zhanjiang,Guangdong,524048)
Social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plain social phenomena.Although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its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social networks,trust and reciprocity norms are the core elements of social capital,and that social capital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productive” and “public”.There is an inherently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social capital.As community public space has special attributes of“public” space,it is the carrier of social capital,and at the same time create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Community public space has important impact and restriction on the foundation and degree of trust among residents,content of community norms and their reciprocity degree,and the carrier and function of community culture through the residents’behaviors,activities,and psychological thinking habits,and shape specific and diverse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s.The creation and growth of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in community is the process for social capital to penetrate and present itself into communities.This process also shapes and changes 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community public space.
community space;urban community;public space;social capital;community’s regulation;community’s culture
C 912
A
1000-260X(2017)06-0153-08
2017-09-10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精细化研究”(GD16CSH02);广东省宣传文化人才专项资金项目“完善城乡基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机制研究”(粤财教[2015]465号)
张勇,博士,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岭南师范学院农村社工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成员,主要从事城乡基层治理与社区建设研究。
【责任编辑:周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