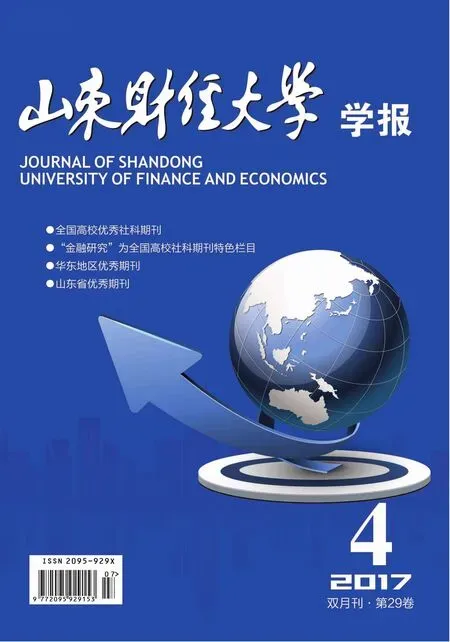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原因及限制性因素研究
康传坤,柴国俊,李 粉
(1.山东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山东济南 250014;2.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61;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原因及限制性因素研究
康传坤1,柴国俊2,李 粉3
(1.山东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山东济南 250014;2.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61;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由于“少生优生”生育观念的深入人心、孩子养育成本的增加及育龄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已大为降低。同时,二孩生育激励和补偿措施不完善,使得生育行为的正外部性并没有被很好地补偿,进一步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再考虑到生育行为的不确定性,实际生育水平将会更低。因此,文章认为:为了“全面二孩”政策顺利达到预期效果,政府必须从修订和调整不适合二孩生育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二孩生育的激励和补偿措施、调整政策宣传方向等多方面入手,营造良好的生育环境。笔者通过引入生育行为的外部性及不确定性新视角构建“全面二孩”政策背后的逻辑框架,试图给出相关部门人口治理的新思路。
全面二孩;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外部性;生育行为不确定性
0 引 言
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建议,之后“十三五规划纲要”正式决定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原因和明确的政策目的,正如《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里所述,放开生育二孩的目的在于通过“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和“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以“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标志着中国人口政策的转型,是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人口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势必对经济社会各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尽管如此,“全面二孩”政策能否如预期的那样提高生育水平顺利实现政策目标莫衷一是。有学者对此持乐观态度,认为“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可以明显改善人口增长趋势,增加劳动力资源供给,并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1]。不过,多数学者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问题,难以从根本上扭转中国人口发展的长期低生育率趋势[2-4]。之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全面二孩”政策难以实现预期效果,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解释:一是二孩生育意愿低下,背后原因包括孩子养育成本的增加、育龄人群生育观念的改变及育龄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3-4];二是基于“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经验[2,4-5];三是“全面二孩”政策覆盖人群有限,二孩生育主体“80后”和“90后”已多被“单独二孩”政策所覆盖[4]。实际上,无论是“单独二孩”政策的遇冷,还是生育政策对目标人群约束力的减弱,本质上反映的还是生育意愿下降的问题。当然,考虑到各种生育行为的促进性或抑制性因素,生育意愿降低并不必然导致实际生育水平降低[6]。不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都呈现出下降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7]。
根据现有研究,如果将生育过程划分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两个阶段的话,那么令人遗憾的是,国内现有人口学、经济学文献多集中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方面。在分析差异时,以往研究虽然考虑了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但是很少考虑生育行为的外部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而且关于生育行为本身不确定性的考察甚少。
基于此,在考察生育观念变化、妇女教育水平、孩子养育成本等因素对生育意愿影响的基础上,本文引入经济学中生育行为外部性理论,考察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同时,借鉴医学领域研究成果,考察生育行为本身的不确定性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试图构建顺利推行“全面二孩”政策的逻辑框架。
1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原因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医疗卫生技术水平的进步,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持续下降,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导致中国人口的迅速老化。始于19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又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使我国在2000年左右便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①国际上通常把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16.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5%,分别比2000年上升2.93和1.91个百分点②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到来,给我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带来了巨大冲击,其中最明显、最直接的冲击莫过于养老负担加重和劳动人口的减少。同时,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及“单独二孩”政策的“遇冷”加速了“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
1.1 养老金缺口增大
我国的现行养老金制度主要有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及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三种。尽管随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推进,三种制度都是统一到了“统账结合”模式,但由于个人账户空账运转,实际上仍是现收现付制,即退休老人的养老金来源于同期在职人员的缴费。老龄化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老人增多,领取年限变长,而缴费的在职人员减少,这一增一减就增加了养老金收支压力。另外,再考虑到养老金制度转轨时的历史欠账,其收支压力可想而知。有学者预测,在假定未来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方式为养老保险体系融资的情况下,2010-2050年养老保险资金缺口所形成的隐性债务折现到2010年,总额将达到575 000亿元,相当于2010年GDP的143%[8]。
当然,为了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政府已出台或即将出台一些对策,如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渐进延迟退休年龄以及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等。不过,所有上述政策只能暂时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不能治本,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来要有充足的缴费人口进行缴费。要实现未来充足的缴费人口,就要放宽生育限制,增加人口数量。最近有研究显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将会有效缓解养老金缺口[9]。
1.2 劳动力供给减少
2004年左右,部分沿海地区就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种“民工荒”现象被认为是劳动力短缺在局部地区的显示[10],甚至被看作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11]。随着“民工荒”问题愈演愈烈,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格局正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向局部短缺甚至全面短缺演变[12]。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民工荒”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短缺,而是由制度缺陷导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畅[13],或者仅是部分特定年龄和性别农村劳动力短缺现象[14]。尽管如此,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及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不争的事实,而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又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数据显示,经过数年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9.41亿人的峰值,然后出现连续下降。截至2015年末,劳动年龄人口降到9.11亿人,比2014年年末减少487万人,劳动参与率为66.3%,较2014年又下降了0.7个百分点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1-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这是2012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第4年绝对量下降。
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理论表明,劳动力作为增长和发展的一种关键要素,对储蓄、资本积累及创新等具有重要影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将会导致储蓄减少,进而资本存量不足,当然也会阻碍创新水平和消费水平提升。因而,有学者认为中国2012年后的经济增长乏力以及日本近20年的“迷失”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结果。正是因为拥有数量巨大的劳动年龄人口资源,中国才得以享有“人口红利”实现30多年的高速发展,并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理论和经验共同表明,充足的、充满活力的劳动年龄人口才是保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前提,也是经济持续增长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
1.3 男女性别比失衡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开始出现了出生性别比例失衡问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08.47,超出102~107的正常范围。随后,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2004年达到121.18的历史最高水平,2005-2008年处于高位震荡状态,直到2009年才开始出现明显下降趋势。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出生性别比已降到113.51,这是自2009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连续第7年下降。尽管如此,当前的出生性别比依然较高,失衡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扭转,仍需持续关注性别失衡治理[15]。
当然,出生性别比失衡并非中国独有,印度、韩国等都存在此问题,但是中国却表现得最为严重。之所以我国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出生性别比例失衡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偏好男孩的传统文化影响,而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数量的挤压以及性别鉴定及流产技术的普及又加剧了这一影响[16]。实际上,我国性别比例的失衡已经导致了婚姻挤压、人口拐卖、性犯罪、婚外恋、同性恋等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并威胁到社会的和谐稳定。近年来出现的“光棍危机”就是明证。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影响极为深远且令人担忧,已经成为当前需要应对的全局性重大挑战[17]。因此,全面放开二孩生育限制有利于缓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对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1.4 “单独二孩”政策遇冷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次年初,“单独二孩”政策便相继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具体实施。其行动之迅速,出乎意料。不过,从政策实施的效果来看并不理想,甚至远低于预期[18]。截止到2014年12月,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条件的1 100万对夫妇中,申请生育二孩的仅有106.9万对夫妇,不到预计年出生200万对的二分之一[18]。从二孩的生育意愿来看,全国及各地多种抽样调查数据都表明二孩生育意愿普遍较低。基于2012-2014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张丽萍等[2]发现全部育龄人群的二孩终身生育意愿稳定在55%左右,而“单独”育龄夫妇的二孩生育意愿不到30%,明确打算不生二孩的“单独”育龄妇女超过40%。风笑天等[19]基于全国12城市1 487名符合二孩生育条件者的调查数据,发现符合“双独二孩”与“单独二孩”政策的城市育龄人群中,只有14%的人提出了二孩生育申请。诸多调查研究表明,2013年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遇冷。
2 实施“全面二孩”的限制性因素
上文的分析表明,尽管“全面二孩”政策有着明确的经济社会目的及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全面放开二孩生育限制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大幅增加人口数量,并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及出生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单独二孩”政策实践表明,许多限制性因素的存在弱化了政策的效果。这些限制性因素同样适用于“全面二孩”政策效果的分析,因为“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理想子女数基本相同[20]。这为我们如下分析提供了参考。
2.1 生育意愿的改变
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史表明,生育率呈现出随经济社会发展不断降低的趋势[21]。生育率的降低意味着意愿生育数量的降低,这源于生育观念改变、妇女受教育水平及孩子养育成本的提高等因素[3]。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巨大化,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多子多福等传统的生育观念已经弱化[22]。特别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降低了人们对养老的担心,从而降低了生育意愿或数量[23]。少生优生已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生育观念[24]。
研究表明,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会降低意愿生育水平[3,7]。一方面,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往往意味着其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妇女收入水平提高又意味着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加。当面临生育决策时,育龄妇女会在劳动参与和家庭再生产之间做出抉择,从而可能减少生育孩子的意愿数量。特别是在生育导致女性收入降低时,妇女生育需求进一步降低[25]。另一方面,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同时也意味着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独立性增强,能够提升其在家庭中的生育选择、决策权和议价能力[26],从而不愿意再被束缚在养育子女的家庭活动中。
近年来,随着生活成本的提高,孩子养育成本增加越来越成为影响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3]。孩子养育成本的增加,加上人们对自己生活质量的看重、对子女成长环境的重视及对子女教育程度的预期等都降低了人们对生育数量的要求,对那些打算生育二孩的低收入人群来说更是如此[27]。
当然,生育意愿并不等于生育行为,更不等于实际生育水平,但过去几十年生育意愿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7]。除此之外,不同出生队列人群的意愿生育水平还表现出随年龄的减小而递减的趋势,在低年龄组出生队列人群意愿生育水平将来不发生显著提高的情况下,中国未来的意愿生育水平还可能进一步降低[6]。
2.2 生育的外部性
生育决策由家庭做出。每个家庭在进行生育决策时考虑的仅是各自家庭的成本和收益,很少甚至从不关心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这就容易导致家庭最优生育数量与理想的宏观人口规模的偏离[28-29]。当实际人口数量高于理想的宏观人口规模时,容易导致过快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破环等严重问题,此即生育行为的负外部性;反之,当实际人口数量低于理想宏观人口规模时,增加人口数量则会优化人口结构并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有利的影响,即生育的正外部性[30]。不过,现有研究往往强调生育行为的负外部性,而忽略了生育行为的正外部性[30-31]。实际上,生育行为的正外部性一直都存在,只是在特定的资源环境和人口结构下其表现不如负外部性明显,再加上国内相关研究缺乏,因而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和人口结构差异,外部性可表现为不同形式。从19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庞大的人口数量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承载了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孩子多意味着资源占用、消耗多,就不能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因而多生孩子被认为是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行为。在此背景下,“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是被提倡和鼓励的符合生育政策的行为,而超生则要支付数额巨大的罚款或面临降职、失业等隐性惩罚。超生行为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即为生育行为的负外部性,只不过由超生带来的惩罚使生育行为的负外部性被内部化,因而并未显现出来。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情况则大为不同。由生育率下降及预期生命延长等因素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已经严重威胁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老龄化加剧的严峻形势下,劳动力供给短缺一方面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另一方面又造成养老保险支付危机,这最终都会威胁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为了提高生育率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政府放松了对生育数量的限制,实施了“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全面二孩”政策下,人口不再被强调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负担,而是可利用的巨大资源。多生孩子不仅有利于人口的均衡发展,更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正是生育的正外部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表现。相对于那些由于各种原因选择不生或少生孩子的家庭来说,选择多生育孩子的家庭实际上是在通过提高生育率方式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同时他们为养育孩子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成本,理应从国家和全社会那里得到补偿。这也是不少国家通过生育补贴政策鼓励生育的原因所在。
不过,出于对高生育率反弹的担心,制定并完善针对生育二孩家庭的相应激励和补偿措施并未引起中国政府的足够重视。那些多生孩子的家庭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反而还要独自承担大量的养育成本。如果生育行为的正外部性得不到合理、有效补偿,将会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从而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生育的这种正外部性在现收现付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下表现得更为明显,不少国外学者对此曾作过出色的研究[32-34]。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一个家庭生育孩子或多生孩子将意味着未来更多的养老保险缴费来源,有利于养老金制度的持续运转;从社会角度来说,一个家庭生育孩子或多生孩子实际上是为那些不生或少生孩子的家庭养老。无论基于国家还是社会角度,生育都存在正的外部性。许多国外研究表明,正是这种生育的正外部性使得许多家庭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除非国家或社会对其进行补贴[33-34]。
2.3 生育的不确定性
生育行为的不确定性是指从受孕到分娩的生育过程中,由夫妻双方的生理、心理因素及外界环境因素等所导致的风险。其中,最为普遍的风险就是不孕不育现象。不孕症已成为影响人类发展与健康的一个全球性医学和社会学问题,它不仅是反映家庭幸福与否、生活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是衡量这个国家和地区生殖健康水平、医疗服务水平等多方面情况的重要指标[35]。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报道,发展中国家不孕症患病率高达8%~12%,即5 000~8 000万对夫妇患有不孕症[36]。近年来,由于年轻人受工作压力大、饮食不健康、过度晚婚晚育、未婚性行为等因素影响,我国不孕不育现象明显增加。2012年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我国不孕不育患者目前已超过4 000万,占育龄人口的12.5%,不孕不育患者中25~30岁最多,而导致男性和女性不孕不育的主要原因分别是少精、弱精、无精和妇科炎症。如果把婚姻也看作是生育的一部分,那么还应考虑婚姻的不确定性。一个人的身体状况、经济条件、甚至人品相貌等都可能导致婚姻困难,在男女出生性别比例失衡的当今更是如此。
当然,不孕不育问题涉及个人和家庭隐私,更多属于个人和家庭层面要考虑的问题,不过要实现预期的人口政策目标,政府政策层面对此也应予以充分考虑。
2.4 “全面二孩”政策的新增受惠群体有限
虽然“全面二孩”政策表面上看起来覆盖了所有希望生育二孩的人群,但是这些人群中很大一部分是独生子女人群。即使不是独生子女,通过和独生子女结婚也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另外,在农村如果第一孩是女孩,也可以再生一个,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更为宽松。除去上述本就可以生育二孩的人群,剩下的想生育二孩但受政策限制的人群才是“全面二孩”政策的新增覆盖人群。显然,这部分人群不会太多,主要集中在“70后”“80后”“90后”人群。由于“80后”“90后”基本都属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出生的人群,大部分已满足“双独二孩”和“单独二孩”政策,所以“全面二孩”的新增覆盖人群主体应是“70后”[20]。
不过,即使整个“70后”育龄妇女都满足“全面二孩”政策,也未必有生育的意愿和生育能力,这是因为随着育龄妇女的年龄增加,二孩生育意愿降低,且流产风险增加,生育能力也急速下滑[37,38]。
3 “全面二孩”政策治理措施
上述分析表明,尽管“全面二孩”政策使得更多家庭受益,但是实际受益人群增量并不会太多。再考虑到生育观念变化、养育成本增加、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等因素导致的二孩生育意愿的降低,以及生育行为的外部性、不确定性导致生育结果不确定,进一步削弱了政策效果。这一点,“单独二孩”政策的“遇冷”已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参考。因此,为了实现二孩政策的预期目标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相关部门必须出台鼓励生育的配套政策[3,39,40]。
第一,修订和调整一切不利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规章制度及条文。当初在执行严格“一孩政策”时,为了达到控制生育的目的,政府所制定的一整套配套激励或限制性政策安排都应根据需要进行适时修订和调整,以利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
第二,对生育二孩进行激励。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法国、俄罗斯等许多生育率较低的国家在产假、生育补贴、子女养育等环节制定了经济或非经济的多形式鼓励生育政策,尤其是法国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对于中国来说,首先应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生育二孩的妇女及配偶在产假、生育津贴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激励;其次,对生育二孩的家庭减免部分养老金缴费并对子女教育投资进行补贴。无论是养老金缴费减免还是教育投资补贴都是对家庭生育外部性的补偿。
第三,减少生育的不确定性。不孕不育是生育行为不确定的主要来源,而不孕不育又跟人的健康密切相关。因此,年轻人口尤其是那些想要孩子的生育人群更应该从饮食、居住环境、生活习惯等多个方面注意健康问题,而且应经常进行体检。医疗卫生机构应为生育人群的相关医疗服务需求提供便利。政府应在胎儿性别鉴及人工流产方面制定更为严厉的限制政策。
第四,调整政策宣传方向。尽管历史上的“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及“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等口号为缓解我国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发挥过积极作用,这些耳熟能详的“一孩政策”时期所大力宣传的生育观念已深入人心,当前看已对生育率的提高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要实现“全面二孩”政策的预期效果,调整政策宣传方向、重塑人们的生育观念显得十分必要。例如,不应再对晚婚晚育进行激励和倡导,甚至可以考虑适当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实际上,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法定结婚年龄都低于我国。这些国家中,法定结婚年龄最高的为美国(男21岁,女18岁)①美国法定结婚年龄各州有所差异,一般为男15~21岁,女14~18岁。,最低的为西班牙(男12岁,女10岁),其他各国的法定结婚年龄都在此之间。我国目前的法定结婚年龄为男22岁,女20岁,相比于其他各国而言有较大的降低空间。
[1]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2014,38(2):3-17.
[2]张丽萍,王广州.中国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5(6):43-51.
[3]宋健.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政策环境与政策目标[J].人口与经济,2016(4):121-126.
[4]彭希哲.实现全面二孩政策目标需要整体性的配套[J].探索,2016(1):71-74.
[5]彭希哲,李贽,宋靓珺,等.上海市“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实施的初步评估及展望[J].中国人口科学,2015(4):2-13.
[6]王军,王广州.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J].人口学刊,2016,38(2):5-17.
[7]侯佳伟,黄四林,辛自强,等.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J].中国社会科学,2014(4):78-97.
[8]刘学良.中国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和可持续性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4(9):25-37.
[9]袁磊,尹秀,王君.“全面二孩”、生育率假设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资金缺口[J].山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28(2):10-20.
[10]蔡昉,王美艳.“民工荒”现象的经济学分析——珠江三角洲调查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05(2):5-10.
[11]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4-13.
[12]辜胜阻,李华.以“用工荒”为契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J].中国人口科学,2011(4):2-10.
[13]简新华,张建伟.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度分析[J].人口研究,2005,29(2):49-55.
[14]章铮.民工供给量的统计分析——兼论“民工荒”[J].中国农村经济,2005(1):17-25.
[15]胡莹,李树茁.中国当代女性跨省婚姻迁移模式变迁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15(1):20-27.
[16]杨菊花,李红娟.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四要素:一个省级层面的纵向分析[J].学术研究,2015(5):44-54.
[17]翟振武,杨凡.中国出生性别比水平与数据质量研究[J].人口学刊,2009(4):3-10.
[18]马小红,顾宝昌.单独二孩申请遇冷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54(2):20-26.
[19]风笑天,李芬.生不生二孩?城市一孩育龄人群生育抉择及影响因素[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1):94-101.
[20]张晓青,黄彩虹,张强,等.“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J].人口研究,2016,40(1):87-97.
[21]尹文耀,姚引妹,李芬.生育水平评估与生育政策调整——基于中国大陆分省生育水平现状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3(6):109-128.
[22]郑真真.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4(5):73-78.
[23]何亚丽,林燕,张黎阳.教育及社保投入对生育率和教育水平的影响[J].南开经济研究,2016(3):133-153.
[24]郑秉文.从“高龄少子”到“全面二孩”:人口均衡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人口转变”的国际比较[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24-35.
[25]贾男,甘犁,张劼.工资率、“生育陷阱”与不可观测类型[J].经济研究,2013(5):61-72.
[26]ANDERSON S,ESWARAN M.What Determines Female Autonomy?Evidence from Banglades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9,90(2):179-191.
[27]郑真真,李玉柱,廖少宏.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来自江苏省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09(2):93-102.
[28]李小平.外部性与过度生育——关于过剩人口成因的制度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0(6):18-28.
[29]王学思.生育行为的经济学解析[J].人口学刊,2002(4):14-19.
[30]邱红,王晓峰.生育外部性及生育成本分析[J].西北人口,2010,31(5):113-119.
[31]吕昭河.人口行为外部性及外部性内在化的经济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0(4):16-21.
[32]VAN G B,LEERS T,MEIJDAM L.Social Security and Endogenous Fertility:Pensions and Child Allowances as Siamese Twins[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3,87(2):233-251.
[33]FENGE R,MEIER V.Are Family Allowances and Fertility-related Pensions Perfect Substitute?[J].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2009,16(2):137-163.
[34]YASUOKA M,GOTO N.Pensions and Child Care Policies with Endogenous Fertility[J].Economic Modeling,2011,28(6):2478-2482.
[35]杨菁,张燕.不孕症研究概况[J].国外医学妇幼保健分册,2005,16(4):232-235.
[36]黄荷凤,王波,朱依敏.不孕症的规范化诊疗[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13(9):688-690.
[37]石智雷,杨云彦.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J].人口研究,2014,38(5):27-40.
[38]韩雷,田龙鹏.“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基于2014年湘潭市调研数据的分析[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0(1):51-56.
[39]易富贤,苏剑.从单独二孩实践看生育意愿和人口政策:2015-2080年中国人口形势展望[J].中国发展观察,2014(12):58-67.
[40]吕红平,崔红威,杨鑫.“全面两孩”后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走向[J].人口研究,2016,40(3):82-89.
Reasons and Restrictive Factors for"Comprehensive Two-child"Policy Implementation
KANG Chuankun1, CHAI Guojun2, LI Fen3
(1.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2.School of Business,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3.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The fertility desires of reproductive women have been greatly reduced because of the deeply-rooted concept of"fewer births and better births",increased cost of child rearing,and the improved educational level of reproductive women.Meanwhile,the positive externalities of reproductive behavior have not been well compensated since the incentive and compensation measures for two-child fertility are imperfect,which further reduces reproductive women's fertility desire.The actual fertility level will be even lower if the uncertainty of fertility behavior i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Therefore,this paper states that in order to build a good birth environment and achieve the expected effects of"two-child"policy,the government must start with revising and adjusting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which are not suitable for the two-child birth,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the incentive and compensation measures for two-child births, and adjusting policy publicity direction.And the author, through constructing the logical framework behind the"comprehensive two-child"policy by introducing the new perspectives of externality and uncertainty,tries to give a new idea of population governance for related departments.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 fertility desire; fertility behavior externality; fertility behavior uncertainty
F120.2
A
2095-929X(2017)04-0072-08
(责任编辑时明芝)
2017-02-24
康传坤,男,山东菏泽人,博士,山东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Email:kangchuankun526@163.com;柴国俊,男,内蒙古凉城人,博士,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李粉,女,山东济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性别失衡、人口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