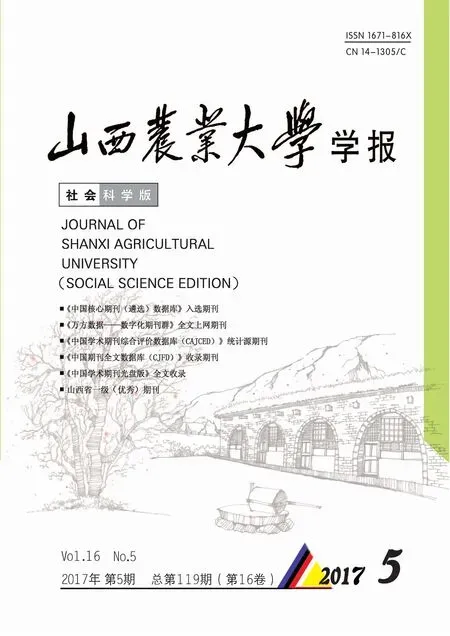《礼运》中的大同与小康
李静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礼运》中的大同与小康
李静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
大同小康之名源出《礼运》,今人大多单论二者的时代意义,却鲜有人去梳理它们在文本脉络中的意义。在《礼运》中,大同与小康只是礼运行过程的一个部分,不能独立开来,它们的意义也只有在礼的整体运转中才能得到确切的理解。《礼运》明确描绘了礼的四个运转阶段,除了大同与小康,还包括周衰礼坏与大顺。大同与小康述说了五帝三王相变易的过程,这是一个下降的过程,而从周衰礼坏到大顺又是一个上升的过程。下降与上升朝着不同的方向,目的却一致,旨在表达礼的阴阳转旋之道。在礼的阴阳转旋过程中,大同、小康既道明了过去历史之实,又树立了未来礼义大顺的标尺,百世不易。
大同;小康;周衰礼坏;大顺
近世以来,大同小康之名广泛流传,它们或与公羊三世说相连,或与现实政治改革相关,极大地影响了世人的生活。无论与公羊三世说相连,还是与现实政治革新相关,大同与小康都被植入线性时间之中,从现在开始,遥指未来——其中,或以小康为现在,以大同为未来,又或依次把小康、大同皆安放于未来。大同与小康对世人的意义已无可置疑,然它们的内涵却并非显而易见。众所周知,大同与小康之名同出于《礼运》,但却鲜有人去梳理它们在《礼运》篇章脉络之中的意义,而无论做理论的勾连还是现实的革新,都得以它们的原初涵义为本。要弄清它们的原初内涵,我们需得转入《礼运》,在礼的具体运转中理解大同与小康的意义。
常言中国为礼仪之邦,礼之名固由来已久。什么是礼?经史子集之文,加上百姓日用之实,无不或明或隐述说着礼,故而,我们多少对礼的“什么”有所理解,然则,礼从何而来,最终又如何运用于日常生活而经久不衰?要回答这个“如何”,我们便得把目光投向传统的经典文本《礼运》,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礼”原始反终的过程。
今本《礼记》(指《小戴礼记》)总共四十九篇,《礼运》位列第九。“礼运”此名,重点不在解释某种“礼”,而旨在阐释礼的运转。郑玄云:“名曰《礼运》者,以其记五帝三王相变易、阴阳转旋之道。”[1]何谓礼的阴阳转旋,它与五帝三王的变易有什么关系?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先了解《礼运》的脉络。
一、《礼运》的文本梳理
《礼运》采用传统的对话体,它是孔子与其弟子子游间的一场对话,这场对话包括三个问答,相应地分为三个部分,都由子游提问,孔子回答。“君子何叹”这个问题提供了对话的具体场景,开启关于“礼”的对话;“如此乎礼之急也”沿着前面的场景,进一步谈礼的重要性;“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孔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占据对话绝大部分篇幅,详细讲解礼之始终。沿着子游的询问,孔子前后提到四种不同的社会状态,即大同、小康、周衰礼坏以及对话末尾的大顺,这四种社会状态从不同层面反映出礼的不同状况。它们先后有序、依次转化,它们之间的变易,将会给我们展示礼如何转旋。
(一)大同
对话以孔子之叹开头,孔子参加完鲁国的腊祭后“喟然长叹”,子游问“君子何叹”,孔子于是谈到那段著名的大同小康之言。在此孔子没有直接说明自己为何叹气,但下文却有回应:“於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禘,非礼也。”看来,问题出在鲁国坏礼上。此乃整篇对话的语境。在周衰礼坏的背景下,孔子谈起大同小康之道,感叹自己“未之逮,而有志”。孔子有志的大同是一幅美好的生活图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
大同即大道运行之时。同者,和也,平也,平即平和,而非平等,大同因此就是率土皆然的大和。这里的“和”不能仅仅理解为“和平”,《中庸》有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2]大和的大同境界因而就是“中节”的大道。大同的特点很明显:“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为公天下;“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为兼爱;“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为各得其所;“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讲的是货力不私;“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则说和平无争。大同处处体现“公而不私”的德性,更难得地是,这种“公而无私”自然而然,不带丝毫强制的痕迹——甚至可以说,在大道的层面,根本没有公私之分,公即私,私即公,如同忠恕之道,修己与成人,其义一也。大同之世,人之货力慈爱不囿于己,成己而能达人,正可谓爱人之仁,因而大道通行天下,其“公”德的核心在仁,见诸行事便是让。[3]
历代注疏家都把“大同”解为五帝之时,这在对话前后时有映照,比如,下文所说的“先王”之初,“后圣”之作当是此时。五帝之道之所以不同于后世,关键就在于其德浩大。《白虎通》云:“德合天地者称帝”,天道无声无息,化育万物,帝道法天地生化之仁德,象天则地,抚教万民。黄帝、帝颛顼与帝喾“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顺天之义,知民之急”,“执中而遍天下”[4-5],其德化所披,日月所照,莫不相从,正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帝道见于具体行事便是让,上古禅让之德流传已久,这便是天下为公。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2]帝尧把天下禅让给舜,舜又让于尧之子丹朱,诸侯朝觐舜而不理丹朱,舜于是乎有天下。同样,帝舜授禹天下,禹让于舜之子商均,天下归禹而不支持商均,禹于是有天下。上行下效,居上位之人行仁讲让,百姓自然相从,大同之世,上下相通,共同成就“广大而不偏私”的大道。
(二)小康
大道隐去之后,便是小康之世,此为第二个社会状态。孔子继续谈道:“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1]
世易时移,小康之世的景况已然不同:天下为公的时代过去,转而为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是为亲亲;货力为己是为私己;“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等级森严的礼义由此兴起;“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显示盗贼兴起、争斗开始;争斗既起,便不得不尊崇勇知,六君子顺时而出,在谋、兵迭起的情况下,不得不立“礼义”为纲纪,“著其义以导其行,考其信以杜其欺,著有过以惩其罪,法仁恩以厚其性,讲逊让以防其争”[6],以此给百姓定下常法。康者,安也,小康居于“安”,较之大道之“和”,只得称“小”。
孔子描述小康时,三次提到“礼”,可见“礼”是小康的根本。小康之世,“礼”泾渭分明:传承天下以家为准,诸侯传位也以家为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等级有差,六君子明确以仁、义、礼、知、信、勇为尊。三代之时,风气不如五帝时淳朴,各亲其亲,货力为己,私心一起,权谋、战争相继而来,三代的英杰,尤其是六君子,不得不衣戎衣而平天下,然后用“天下为家”、“大人世及”来稳定社会秩序,以免再起争夺。小康之世靠着这些清楚分明的礼义制度,才得以去除纷争,保持安定的局面,正因如此,在小康之世里,百姓刑仁讲让便显得不如大同之世那么自如,甚至有些迫不得已——“刑仁讲让”得靠三代之英引导强调,这表明让德已失。我们注意到,孔子在“小康”里三次重复“礼”,谈到“大同”时,却只字未提“礼”,这是否证实了某种解读,即礼只不过是小康的纲纪,而与大同无缘呢?[7]
当子游问“礼之急”时,孔子如此回答:“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人要是不依礼而行,还不如早些死去,既如此,便很难想象孔子所向往的大同社会里没有礼。就此,孙希旦以为,礼与天地并,由来已久,五帝同样以礼义治天下,只不过与三代的气象广狭不同。[6]倘如此,五帝大道之礼与三王小康之礼究竟有何不同?
郑康成注曰:“大道之人以礼,于忠信为薄,言小安者失之,则贼乱将作矣。”孔颖达疏中也谈到“五帝以大道为纪,而三王则用礼义为纪也。”[1]陈澔见此,便称“有老氏意”。[8]《老子》下篇开头云:“大道废,有仁义”,“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9]就此,五帝时的大道效法的便是不可道之“道”,三代之时则据于德;若以德言,五帝大同之道则居于“上德”,以无为要、无为而为,三代小康则据于“下德”,为之而有为。
名曰“五帝”与“三王”,本身就分别了不同的功德。《白虎通》云:“帝王者何?号也。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号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10]帝与王统统据于德,法天地无为者为帝,是为“上德”,礼义为纪者当王,居于“下德”。五帝之时百姓性情敦厚、民风淳朴,大道之时非但有“礼”,而且这礼浑然天成,与三代井然有序的礼义殊为不同。《礼记·乐记》云:“大礼与天地同节”,我们可以借此称帝道之礼为大礼。大礼法天地生化万物之德,无为而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君子笃恭而天下平”[2],帝道所谓“德合天地”,便当如此。大道效法天地之生物载物,无声无息之间,万物化育。由此,我们似可理解孔子为何谈到大同时只字不提“礼”:“大礼”不言,“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正是大同。大同与小康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状态从不同的层面昭示着礼的成就,可以说,大同与小康体现着判然有别的两种礼的状态,是圣王在不同时代根据不同时机对礼的不同安排。
(三)周衰礼坏
孔子说得礼者生,失礼者死,得知礼如此重要,子游不由得想知道礼的始终,孔子于是谈起礼的成型过程。礼的出现,始于人的饮食(养生),看重送死,历经先王后圣的努力,“承天之祜”、“合莫”、“大祥”等礼仪逐渐成型,礼也因此大成。
作为人君之“大柄”,礼可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帮助国君治政安邦,相应地,人君也当以政治为本,法天地高下不同颁行命令:降命于神社,是为殽地;降命于祖庙,兴起仁义,远者尊而为义,近者亲而仁;降命于山川,便可利用山川之材制作器物,法五祀行动便成就制度,各有法度。君王一旦参照天时、地利,能够厚人伦、施教化,便可立于不败之地,如同日月星辰之神,“辉光于外,而形体不见”。[1]
对话到此,突然来了个转折,一下子从守礼的三代转到无礼甚至无法的春秋时代。孔子观礼之时,礼制已经大不如前。周道从幽王、厉王开始有缺,厉王失正,百姓“道路以目”,幽王失礼,烽火戏诸侯,终惨死于骊山之下,二人几乎废掉先王基业;不仅如此,连夏殷二王遗法也不见于杞宋,即便那有周公遗风的鲁国,情况也大为不妙:《春秋》刺隐公观鱼于棠,非其鬼而祭之,尚算轻微失礼,而到了桓公弑隐公,“舍鲁何适”也只能变成伤叹。就此,孔子把败坏礼法的情况分列七类:君臣弃用古礼,藏于宗祝之家,是为“幽国”;诸侯僭用王器,是为“僭君”;大夫私藏冕弁兵革,这是“胁君”,大夫造祭器,僭用声乐,便是“乱国”;君臣无分尊卑,平等相处,是为“君与臣同国”;天子到诸侯国去,不住在诸侯祖庙,就是“天子坏法乱纪”;而诸侯除了问疾吊丧,随意去臣下家里串门,便是“君臣同谑”。凡此种种,无不昭示着周衰礼坏,而礼坏的结局便是“疵国”。
常言“礼不下庶人”,一旦君王、各国诸侯、卿大夫这些本该守礼之人带头坏法,乱便随之而起。正所谓“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弊,则法无常,法无常而礼无列,礼无列则士不事也。刑肃而俗弊,则民弗归也”。政事坏于无礼,礼崩乐坏之后,旧俗不足以约束人,刑法更新越发无常,百姓没办法适应不断更新的刑法,更加没法忍受苛政,便不会归顺。没有民心的国家国将不国。
至此,对话已经给我们展示了礼的三种状态:大同,小康以及周衰礼坏,相比五帝与三王六君子时期,周衰礼坏之时当属孔子所处的的春秋五霸时代。就孔子所列的败礼之举,要么君王带头坏法,要么臣下僭起争心,这样的风气,“争”自然会取代“让”,成为时代主流,礼崩乐坏在所难免。《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趋。三王驰,五伯骛。”[10]陈立疏曰:“世愈降,德愈卑,政愈促也。”从五帝时代的让德到三代六君子时让隐礼显,最后到春秋五霸之争,世风日下,不用赘言。这三种社会形态,大同之世自不必说,三代小康之世虽然不如大道时美好,毕竟有谨慎依礼的六君子,尚能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五霸之时则不然。霸者,伯也,迫也。五霸一方面“行方伯之职”,另一方面却“迫胁诸侯,把持王政”[10],《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争心一起,即便五霸有向“义”之心,终究难敌私心,不能持久,难怪孔子会有“呜呼哀哉”之叹。孔子的喟然之叹不仅昭示着周道衰缺与礼崩乐坏,同时也预示着圣人拨乱反正的必要。
(四)大顺
自五帝三王再到春秋,世越降德越卑,最后竟到达疵国的境地,圣人怀不忍之心,天下有道不与易,于是起身于危乱,拨乱反之正,重述先王礼法,最后到达美好的大顺之境。不过,圣人述礼法,并非立于人世之外,想当然以某一理想社会制度强加于世人,而是立足人之性情,再缘人情制作礼法。
解释人的性情也即在回答“何为人”。圣人不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也不说人是劳动的动物,而把人视为连接天地的生灵,看作天地之心:“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说的是气和性。天地之德、阴阳之交,说的是气,其中,阴阳为气,天地为形;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指的是性。天高地阔,人在其中,因此人是天地的心脏,又披天地五行之秀气而生,感通天地,为五行之首,故而又能通晓仁义礼智信五常。
“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10],人禀天地阴阳秀气而生,不仅有性,还有情。“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概括而言,人情无外乎欲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死亡贫苦,人之大恶。人皆喜好饮食男女,害怕死亡贫苦,然四时循环往复、旦暮有时,各有所节,饮食男女之事若不加限制,死亡贫苦之态若不加引导,必生争乱,甚至人人自危。因此,圣人便要缘人的性与情立法,这便是礼。
《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礼也如此,可以“上下察”。人既为天地之心,相应地,礼也当本天效地,依四时的变化行政、施教,四时有孟、仲、季之先后,长幼于是井然有序,春秋教授《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礼不但上与天地相通,还要下达于日常生活,通达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财货劳动依礼而行,饮食有节,冠礼成人,婚礼节男女之情,丧祭重送死之意,射、御、朝、聘无不有礼。
圣人“修礼”、“陈义”、“讲学”、“本仁”、“播乐”,使礼通达于上下,最后到达大顺之境。大顺之时,“人肥”、“家肥”、“国肥”延展而“天下肥”,此所谓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四体既正,肤革充盈”,此为身修;“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是为家齐;“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此为国治;“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此为天下平。仁生于中,引而未发,发而为顺,顺为成物之效,达到大顺之境。王中心无为,往下扩展,养生送死事鬼神,各得其所。圣人依从天道,顺着人情,用礼来治理百姓,事情无论大小、深茂,无不相与并行,各不相悖。
大顺之境天地人合一。人效法天地,遵照阴阳四时五行,应时而动,顺人性,笃人情,如此,天地也会有所感应,不私藏其道,不私藏其宝:“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大顺之时,阴阳调和,天人相感,有感必有应,膏露、醴泉、河图、凤凰、麒麟,各个都是祥瑞之物,唐尧时刑仁讲让,上行下效,百姓和睦,龙马负图而出,虞舜之时,四海之内,莫不拥戴,于是凤凰来翔,天人相感早有前例。
与前三种社会状态不同,大顺不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社会状态,而是圣人通过言辞上立法达到的美好状态。饶有兴味地是,对话末尾的大顺一时像大同,一时又似小康,它似与对话开头的大同小康有着某种渊源。它究竟与大同相应,还是与小康相合,或者,它自成一体?
一方面,大顺处处以礼为则,讲究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讲求仁义礼智信,礼制极其完备,如此与小康相类。另一方面,大顺之礼又效法天地之德、阴阳之气、五行之运转,这与处处合于天地之义的五帝之道暗暗相应;不仅如此,大同的特点在“让”,小康则多以“私”为前提,大顺之世礼乐并置、讲信修睦、礼行于货力辞让,又似乎对应着大同之“让”,“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似乎正是“男有分,女有归”以及“选贤与能”的具体安排;此外,大顺最后能达到“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实,人不爱其情”这样一个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小康似还不能比拟。因此可以说,大顺自成一体,部分与大同相似,又部分与小康相合,它似乎是二者的某种综合。照前人所疏,大顺类似于大同,但它不是大同,也不可能成为大同,因为五帝时的大同之世奠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以敦厚朴实的民风为起点,又加上生而知之的先圣,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才能成就大道。后代时势不同,机运不再,很难再复制一个大同之世。按照对话的语境,这样的解释甚为合理。大顺既然是圣人在礼崩乐坏时期的某种重述,准确地说,是复古更化,它便只是一种言辞中的理想状态,在现实社会中没有对应的实物,当然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五帝的大同,也不可能是三代的小康。
二、礼的运转
(一)阴阳转旋
纵观整篇对话,孔子前后给我们展示了大同、小康、周衰礼坏以及大顺四种社会状态,它们分别昭示着礼的四种状态,这四种状态各有特色,又井然有序:从大同到小康,再到周衰礼坏,礼逐渐下降,到达否隔不通的境地,而后,从周衰礼坏到大顺,礼逐渐上升,最终否极泰来。礼的运转大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既可以说是五帝三王之道相变易的实际历史过程,同时,它也是礼原始反终的常道,经久不衰。把它理解成历史实际运转的过程,对于前三个社会状态似乎并不难,但需要合理解释大顺的存在。而若把这个过程视为礼变易的常道,意义似乎更大:孔子用这样一个由治到乱,再由乱到治的过程,展示了礼运转的根本大法。然则,礼的运行与阴阳转旋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偏偏要把礼的运转理解为阴阳转旋?对话里,孔子自述曾到杞国和宋国去观古礼,由于文献不足而没法了解详情,只得到《夏时》和《坤乾》两本书,以此来推演古代的礼。《夏时》是一本记载四时的书,而《坤乾》讲的是阴阳之道,如此看来,礼的运转与阴阳四时之道实密切相关。
何谓礼的阴阳转旋之道?
孙希旦这样解释礼的运行:“盖自礼之本于天地者言之,四时五行,亭独流播,秩然燦然,而礼制已自然运行于两间矣。”[6]孙氏的理解,大概渊源于对话第三部分孔子所述礼之终始:“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人得天地五行之秀气,性承天地之德,情顺天地之宜,为人所特有的礼因此也要顺天道应人情,故而礼有“上下察”的能力,它上可通于天地阴阳,往下达致百姓的具体生活,运用在“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等各个方面。因而,礼的运转指的就是礼从太一混沌状态,经过一系列转化,最后融入万事万物的过程。
太初而太极,分而为两仪,气有清浊,清者上行,浊者下降,阳爱动,阴好静,二气交感而生人。两仪生四象,由阴阳二气的升降而成,变而为四时,即春夏秋冬,清浊之间的为中气,这便是土,居于中。[11]东方阳气初生,生发万物,故曰仁;南方阳气在上,阴在下,尊卑有序,故为礼;西方阴气出动,有肃杀之气,故曰义;北方为水,阴气在上,水利万物而不争,圆润融通,是为知;居中为土,土广大厚实,能载万物,是为信。在传统视野里,自然万事万物不是一个与人隔离,站在人外面的客体,而是活生生与人事闇合的生灵。不论人还是其他生物,统统都是由阴阳之气变化而成。阴阳有尊卑高下,相应地,自然万物也有各自的德性。
人在各种生灵中极其特别,能与五行之气相感通,圣人尤其如此,能根据不同的象效法不同的德性,成就仁义礼智信五常。天高地阔,人居其中,感通天地之德,言辞行动与天地相应,“天地有人,如人腹内有心,动静应人”[1],因此说人是“天地之心”。人作为天地的心脏,又是“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因此,人的食、声、色都与天地阴阳五行相合。五音宫商角徵羽、五味酸苦辛咸甘、五色青赤黄白黑,各自对应四时五行,循环往复,相继为本。这样一个阴阳变化的过程既是天地生人之性的过程,同时又是礼的运转过程,各自对应着不同的德性:阴阳变换,天尊而地卑,四时循环,便有了仁义礼智四德,转而为五行,于是五常具备,再下行到达人事各个方面,于是有了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人的一言一动,甚至在没有言语行动自己独处的时候——君子慎独,礼也无声无息地存在着。人与礼名为二,实是一,圣人因此说人不可以没有礼。由此,礼的阴阳造化流通就是礼沟通天地与人事的过程,其中,圣人承担着桥梁作用,因此说“礼之待圣人而后运行”。[6]然则,郑玄所谓“五帝三王相变易”又如何理解?帝道无声无臭,德行隆厚,为什么最终还是不能避免转为小康王道,甚至走向礼崩乐坏?
(二)帝王变易
“盖五帝之时,风气方厚,而圣人之治乘其盛,三代之时,风气渐薄,而圣人之治扶其衰,故其气象之广狭稍有不同者,非圣人之德有所不足也,时为之也。”[6]按孙氏的理解,大同之道转向小康,关键在于时运不同。《礼器》云:“礼者,时为大,顺次之”,礼与义相与并行,礼为义的定制,是常法,而义又随时势而变,因此孔子在对话里说,只要敬顺天道人情,即便先王时没有的礼制,也可以应时而变,加以创制,这便是“协诸义而协”。五帝与三王时代,时势不同,礼也由大礼转而为纲常之礼,然则,我们如何理解“时”所带来的变易呢?
“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礼器》),文与质要相互配合,才能达到文质彬彬。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质彬彬指的是文与质的协和,这不能理解为严格的数学比例,文一半,质一半,文质的协和尤其要把握时运,质美之时文不必多,质损之时文定要补,最终达到中和之道。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五帝之时,民风厚实,不需要太过精细的礼仪威仪,因此礼的具体制度没有后世那么细致。五帝之道即大道,同即和,因此大道便是大和的中道,大道以忠信为本,讲信修睦,中正无邪,《乐记》云:“中正无邪,礼之质也”,五帝所行的大道质美而正,五帝之道之所以质正,根子在于心诚,美质之人稍加引导,便自然中正,根本不需要繁复的礼节画蛇添足,因此大同之道恰恰文质彬彬。文质彬彬的从容中道对应地便是合天地的大德。
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文质而言,“天质地文”[10],质偏于阳,而文偏于阴,文质彬彬因此就是阴阳调调。“乐者,阳也。动作倡始,故言作。礼者,阴也。系制于阳,故言制。乐象阳也,礼法阴也。”[10]乐者,乐也,大同之世其乐融融,乐以发和,大同之世正是大和,阳盛而阴藏,乐出而礼藏。《乐记》云:“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主阳,礼主阴,就阴阳而言,无所谓纯阴与纯阳,总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礼乐如此,仁义也如此。乐中有礼,仁中有义,因此孔夫子说“仁者爱仁恶不仁”;礼中有乐,义中有仁,正是对话中“仁者,义之本”之意,因此,大礼中仁义并举,义藏在仁中,阴藏于下。大同的气象之所以更为广大,不仅因为有阴有阳,而且在于常中有纲,这便是阳主阴随。一般而言,人情莫不喜阳而恶阴,爱饮食男女而恶死亡贫苦,阳为常中之纲,大同之为“同”,相较于小康,则义通过仁显现,礼通过乐显现,因此大同之道阳显而阴藏。
世易时移,大道不再,转为三代。夏殷二代质盛,礼文不备,质盛则亲亲,亲己之亲太过便不免失尊,因此说质胜文,弊端在野,继而周代沿革,礼文大备,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总的说来,三代之制是一个礼文逐渐完备的过程,文备则阴盛,此即对话中孔子所述礼制的成型。小康之制虽然礼文具备,和乐却不足,人独亲其亲倘若不能扩展为恕之道,显然不如不独亲不独子那么融洽,气象随之转狭。
一阴一阳,一柔一刚,刚柔相济而生变化,阳极则阴动,大道隐去,实则阴出而阳藏。大道转为小康,道理如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则少阳,阳气初生,夏则老阳,阳极,秋则少阴,阴气生,冬则老阴,阴极阳欲动。三代之时阳极而阴生,转而为小康,不得不礼义以为纪,正君臣父子夫妇之纲,至此,则阳藏而阴稍显,礼显而乐藏,仁藏于义。
到了周末,终于走到文胜质的境地,其失在史,春秋之世,周文疲惫,君臣上下内心无诚无信,言语行事当然无法笃于仁义,正是文胜于质的弊端。这便来到否革不通的境地。正如大同之道最终会转为小康,周衰礼坏也不能持久,道之理穷则变,变则通,阴极阳欲动,因此,周衰礼坏之后,终会有大顺。
文胜质则史,失在薄,穷则反本,又需质来救助。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不但质不正,文也疲惫,阴阳两损,圣人依着天地之象,参赞天地之序,因以制礼,顺着人情之实,玩民之所乐,修礼陈义讲学播乐,使民各得其乐,最后到达乐中有礼、阴阳调和、天地人合一之境,“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最后“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人不独亲,货力不为己。大顺与大同,文不同而实同,大同永远在那美好的五帝时代,然而大道却可以效法,圣人与先王一样,效法天地人情,最后同样可以达到大和的境地,朱子解释大顺曰:“信是实理,顺得和气,体信是致中,达顺是致和”[8],大顺与大同,都是文质彬彬的大和之道。
从大同到小康,再到礼崩乐坏,从周衰礼坏到大顺,礼由盛而衰,再由衰到治,礼运转的过程当然首先合于时势的变易,另一方面,也同德性的盛衰一脉相承,礼衰便是德坏,礼治便是德兴,只有诚于中的圣人,淳朴的民人,外加远在星辰外的好时运,才能通达大同之道。礼的运转,上由太一、阴阳下至人事,就具体人事运转来看,又体现为五帝三王的礼乐因革,因而可以说,五帝三王相变易之道同时也就是阴阳转旋之道,二者不可分离。然则,孔子在对话中仅仅陈述了四种社会状态,这能够完全概括礼的运转吗?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从大同到大顺,穷极而返本,周而复始,道在此,百世亦在此中。
三、结语
从《礼运》的篇章脉络出发,从礼的阴阳转旋细查,我们逐渐理清了大同与小康的历史涵义与现实意义。它们曾在历史上真实的出现过,它们是五帝与三王时代的现实总结,此为历史涵义。另一方面,它们又不仅仅是历史,经过周衰礼坏,它们又与大顺藕断丝连,大顺为圣人言辞中的未来,大同与小康也可能成为未来,成为现实,此为它们的现实意义。大同与小康成为未来的现实,不是亦步亦趋重复过去的五帝三王时代,如同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过去发生的事也不会再次发生。但它们却可能发生,而且是以大顺的名义出现——在此,我们理解了为何大顺既像大同,又类小康。在《礼运》之中,大同和小康的意义旨在述说礼的运转,它们是过去,也是未来,因为它们以人情人性为根基。倘若把大同和小康放在一起,那么它们与周衰礼坏以及大顺一道,在理论上描绘了一个类似公羊学三世说的三步走路线,但却是以类似三统循环的方式述说,而非西方的进化论方式。在现实生活运作中,大同与小康也的确可以作为现在与未来的蓝本,因为按照礼的阴阳转旋,它们不仅过去存在,未来也定当再现。
[1]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56,658-659,660-661,660,683,699.
[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8,107,40.
[3]姜义华,张荣华.康有为全集(第五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54-555.
[4][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117-121.
[5][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14.
[6][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9:584,583,581,581,584.
[7][清]康有为.礼运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238.
[8][元]陈澔注.礼记集说[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169-170,184.
[9][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98.
[10][清]陈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43,45,62-63,381,365,98-99.
[11][清]黄元御.四圣心源[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1-2.
(编辑:牛晓霞)
Great harmony and well-off society in theBookofRites
Li Jing
(CollegeofPublicAdministration,ShanxiAgriculturalUniversity,Taigu030801,China)
Great Harmony and Well-off society are two social formations in theBookofRites, whose contemporary meanings are discussed most but their text meanings are ignored. Actually, they are indispensable part of ritual operation and we can understand their proper meanings in the real operation. TheBookofRitesdescribes the four stages of Rites as the Great Harmony, the Well-off society, the collapse of Rites in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and Da-Shun. The declining change from the Five Emperors to the Three Kings in the Great Harmony and the Well-off society and the rising process from the collapse of Rites in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to Da-Shun have the same goal of explaining the waxing and waning of Yin and Yang in the ritual oper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the Great Harmony and the Well-off society have explained both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 future tendency which continues through generations.
Great Harmony; Well-off society; Collapse of Rites in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Da-Shun
2017-01-20
李静(1986-),女(汉),重庆巴南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西方政治哲学、法哲学方面的研究。
2016—2017年山西省社科联重点项目(SSKLZDKT2016083)
B21
A
1671-816X(2017)05-005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