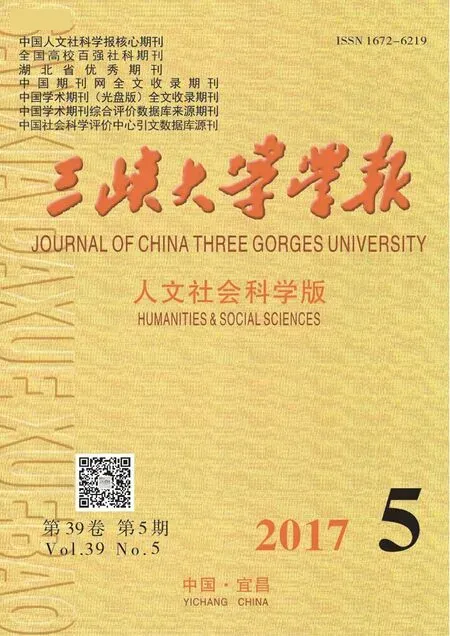民国新记《大公报》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形象探析
曹明臣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民国新记《大公报》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形象探析
曹明臣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在民国新记《大公报》的记述中,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经历了“洪水猛兽”之“国际党”、“对国家犯重大之罪”之“匪”、抗日之共产党、“以兵争政”之“第二大党”、代表人民的中国共产党等五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形象变化的过程反映了该报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变化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艰难发展过程。
新记《大公报》; 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
本文立足于民国时期民间大报之新记《大公报》,梳理该报视野下中国共产党形象变化的基本过程,借以反映该报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变化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艰难发展过程。
一、“洪水猛兽”之“国际党”
国共合作北伐时期与国民党反共清党时期,是新记《大公报》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该报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洪水猛兽”之“国际党”。在《大公报》看来,共产党的名称就不好:“就‘共产’二字释其义,则有类于夺人之产以为己有,故共产公妻,相提并论。”因此,共产党“如洪水猛兽”;此外,“共产党为国际党,易言之,为国际革命党。”由此视共产党等于“卖国”[1]。
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之“国际党”,与该报的反对赤化之立场不无关系。1926年9月4日,该报的社评《回头是岸》就正式亮出了反对赤化的底牌。该文认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国民党之标明‘以党治国’,以国际共产党之入党,与夫亲俄色彩之浓,宣传工潮学潮之烈,此皆吾人所反对者”[2]。该报在1928年的《岁首辞》中更是进一步表示:“吾人之根本旨趣”为“非复古,亦非俄化”[3]。该报甚至直言,“中国有赤化问题之发生,中国之耻也。”并具体列举了“耻”的五种表现[4]。
该报虽然反对赤化,却不赞同国民党反共清党时期屠杀共产党的政策。该报认为新国家之建设,须依赖全国有志青年之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到,对于国民党“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5]此外该报还有文章指出:“上海广州大清党之时,杀人殊多,犹可诿为非常之变。今历时数月,而恐怖未减。上海特务处,常有刑人之事。所犯罪状,概不宣布,杀者何人,亦秘不宣。共党诚与宁政府大不利,然凡共党是否俱应处死?……解释清党之义,不过驱跨党分子而出耳,何以动辄死之?……此诚国民党治最大污点矣。”[6]
在反对屠杀共产党的同时,该报提出了反共的具体办法:一是反共须研究“马学”。“马学”即共产主义理论。该报认为:“主义之事实发生,政府应予以严惩,主义之思想讨论,政府应予放任,或且进而提倡之,期是非之明确,免社会之盲从也。”[7]二是要改善社会环境。该报认为近年赤化运动发生,原因在于政治不良、经济困难,“今日反共第一条件,在改善社会环境,釜底抽薪,消弭隐患,若纯恃高压,恐徒为共产党添宣传资料耳。”[8]
二、“对国家犯重大之罪”之“匪”
1927至1937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土地革命战争,而国民党在此时期的一项主要工作便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剿匪”。对于国民党的“剿匪”,《大公报》态度非常积极,相关报道与评论非常多。在报道与评论中,该报对中国共产党的称呼较多,如“中共”、“共产党”、“共党”、“共”、“赤”、“赤匪”、“共匪”、“匪”等,但多数时候称“匪”。
早在1929年,该报就对东南省份之“共匪之祸”进行了分析:“东南共匪,纯为无赖亡命之徒,裹胁溃兵,与夫赤化不可救药之青年男女,以烧杀泄怨毒,以窜扰求生存,有流寇之势,而激烈凶残过之,此辈所过,城邑皆墟,失业贫民,随处尽是,其无可逃无可生者,则皆折入于匪,以冀旦夕苟活,是以朱毛贺龙,以败残小股,而窜扰四五省,历时三四年而不灭者,一以军队之进剿不力,一因随处裹胁,新陈代谢而无穷也。”该文主张:“政府为巩固长江一带治安之计,应视剿共为紧急事业,与其宣称准备十万兵赴东北国境,毋宁先简选中央劲旅足资信任者二三师之众,特派一二总指挥,专任鄂湘赣一带剿共之事,临之以法,激之以赏,务期于最短期内肃清焉,庶几乎不至为大害矣。”[9]这恐怕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最早提倡了。
《大公报》对中国共产党“匪”的称呼,以及关于“剿匪”的叫喊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才停止。但直到抗战爆发前,该报对中国共产党依然抱有极深的偏见,如1937年初的社评《对西安负责者之最后警告》就对中国共产党予以指责:“共产党者,第一须自忏过去十年来对国家民族所犯之大罪。夫自江西暴动起,迄最近止,以赤色恐怖蹂躏及十余省。江西人口,为之减数百万,如鄂如豫如皖,凡其盘踞较久之地皆一空。……要之共产多年穷凶嗜杀,谋推翻整个社会,而自己又绝无对国际对国内之一贯认识,害国家、害民族、害自己,辗转战争,由东南而西北,以至于今日。粗略计之,国军损失不下数十万,费财数万万,至于共产所杀害及其部队灭亡支数,更不可胜计,此诚可谓对国家犯重大之罪矣。”[10]不可否认,该报对中国共产党也作过一些客观的报道。从1935年11月起,《大公报》连续刊载了记者范长江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第一次向国人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部分真相,这对人们正确了解中国共产党,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起了重要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大公报》认中国共产党为“匪”的基本判断发生变化。吴廷俊就指出,“《大公报》史上的这一光辉点至多只能算‘四不’方针的一个表现。”[11]164
三、抗日之共产党
《大公报》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态度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的国共“和平交涉”过程中开始转变。中国共产党在该报中也褪去了“匪”的形象,而逐渐转为较正面的形象。尤其是对于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该报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作用:“中国今天,是整个团结了,共产党这样捐弃成见,共同奋斗,是加强这团结的。”[12]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促成了中国的整个团结,成为中国国民党的合作对象,是中华民族抗战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作战。对于八路军取得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大公报》发表文章指出,“这一战更可特别庆贺”[13]。太原会战期间,《大公报》刊载了数篇对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访谈。这些访谈不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也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言行举止,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良好的媒体形象。如该报于1937年10月21日刊载了一篇对八路军正副总指挥朱德与彭德怀的访谈,详细记录了朱彭二人平易近人的形象[14]。1937年12月20日,又刊发了对毛泽东的访谈,详细记载了毛泽东的忙碌与朴素形象[15]。此时期,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共产党经常通过新闻媒体主动报捷,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很注意塑造自己良好的抗战形象,借以扩大影响,博得社会公众的赞赏与支持。
从抗战初期《大公报》的报道与评论中可以发现,该报已经改变以往对中国共产党所持的排斥、批评与指摘态度,转而对其认可、赞赏与褒奖①。此时,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了“匪”的媒体形象,完全以一种新的抗战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当然,受自身立场的影响,该报在对一些重要事件的评述中,仍体现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偏见。在皖南事变发生后,该报先后发表《关于新四军事件》与《关于共产党问题》两篇社评,认为事变发生至为不幸,但就军纪军令而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并进一步指出中共军队,在理论与事实上,与其他军队同为国军,除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其背后就不能另外再有一个军令系统,“军队的统一,军令的尊严,无论如何,必须维持与贯彻”[16]。这无疑是指责中国共产党破坏军令统一。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该报撰文要求中国共产党来一个所谓的“转变”,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不分彼此,不分阶级,团结一致,切实遵奉“国家至上”、“胜利第一”的原则,其实质是要求中国共产党无条件地拥护和服从蒋介石国民政府这一“国家中心”。1944年8月5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延安参观的感想》,对6至7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访问团参观延安一事进行评论。该文对延安在党政军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的做法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既不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符合中国的立国主义;该社评还指出:“我们拥护国家统一,我们爱护国家中心,政府若有缺点,应该促其改善,政府若有失败,应该促其纠正,但绝不可轻谋另起炉灶。”[17]这无疑是指责中国共产党破坏了“国家中心”,是“另起炉灶”。
四、“以兵争政”之“第二大党”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认为“共产党是第二大党”,国家政局的好坏关键在于国共两党是否团结合作[18]。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由美国大使赫尔利及张治中陪同飞抵重庆,参与国共谈判。对于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及国共谈判,《大公报》发表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认为这是一件大喜事:“在抗战已告胜利,盟友业已结成,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19]并指出此举“关系目前与今后的国运极其远大”,因此“目前的团结商谈,必须成功,而绝对不允许其失败。成功了,是国家的大幸,民族的大福;假使失败了,那不但是抗战胜利与外交成功要打大大的折扣,甚至依然把国家弄的乱七八糟。”[20]这无疑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但直到解放战争最后阶段到来之前,该报依然是坚决维护蒋介石政府这一“国家中心”,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以兵争政”之“第二大党”。例如,在“双十协定”签订不久出现的国共摩擦,该报发表题为《质中共》的社评,错误地断言是中国共产党挑起了战争:“今天局面的演成,从文献上寻索,日本宣布请降之初延安总部发布的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是一个根源。……及至毛先生返回延安,广大的北方到处起了砍杀之战。”因此,该文呼吁中国共产党放下军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可能博得众人的同情,我们所最不敢同情的,是以兵争政。……希望共产党放下军队,为天下政党不拥军队之倡,放下局部的特殊政权,以争全国的政权。与其争城争地驱民死,如何兵气销为日月光?”[21]
1946年4月14日,苏军撤离长春,此后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争夺长春的战争。《大公报》于15日在要闻版刊登了题为《长春苏军昨已撤去,共军攻击接踵而来》的新闻,次日又发表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指出:“苏军刚刚迈步走去,国军接防立脚未稳,中共的部队四面八方打来了,且已攻入市区。多难的长春,军民又在喋血……中国人想想吧!这可耻不可耻?”这无疑是认定由于中共军队的进攻导致军民喋血;社评还利用国民党方面制造的谣言,污蔑中共军队“常常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堆地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称这是“最伤天害理”,“残忍到极点”,“可耻到极点”[22]。
五、代表人民的中国共产党
由于解放战争后期的形势所致,《大公报》各馆之间彼此失去联络,总管理处对各分馆不能进行言论方针的指导。1948年11月10日,港版宣布转变;1949年1月16日,津版停刊,后改名为《进步日报》;6月17日,沪版宣言新生;9月18日,沪版被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温和接管”[11]448-449。《大公报》各版言论立场由此出现较大差别,没有以前那样统一的言论方针。
1948年11月10日,《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在香港版发表社评《和平无望》,抨击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支持中国共产党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以赢得真实而持久的和平:“违逆了人民大众的生存轨道,必无治,摧折人民大众的求生欲望,必乱。……看目前中国的乱局,人民真是痛苦极了,目前纵然和平无望,人民大众终将会走上合理生存之路。我们挥泪跋涉,总希望这条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之路已不在远!”[23]218社评的发表,标志了港版《大公报》的立场开始发生质变,这种质变无疑会影响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判断。遗憾的是,内地各版并未同时刊载此文。
1949年元旦,《大公报》香港版又刊登王芸生撰写的社评《展望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文章满怀激情地断言:“今天东方一亮,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就到了,三十七年就过去了。这到来的是新的到来,那过去的是旧的过去。……那过去的是战争的痛苦,人民的磨难;是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的战争痛苦,两千多年专制封主高压下人民的磨难。这到来的应该是和平、民主、自由、平等、进步与繁荣的新中国。”[12]219这里,该文肯定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文章又指出:“用人民的新胜利,彻底而干净地结束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历史。……展望中华民国三十八年,这源远流长的内战应该在人民胜利的面前结束了。”[23]220这里,中国共产党无疑又是代表人民的。
《大公报》的这种言论,并非吹捧,而是有实际体验的。这在《〈大公报〉新生宣言》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该文是王芸生在回到刚刚解放的上海后写的。该文指出,在这短短的二十几天中,上海600万市民全体获得解放,他们不再受国民党匪帮的压榨、剥削、抢掠、凌辱,以至抓杀屠戮,开始享受自由。“看了人民解放军的严明纪律,谁不衷心感叹这才是我们人民自己的军队;看了人民政府的朴素认真的作风,谁不衷心感叹这才是我们人民自己的政府。……上海的解放,实际是国民党匪帮的反动政权彻头彻尾的灭亡,是全中国获得新生。在这重大时候,大公报也获得了新生”[23]222,该文最后断言:“中共毛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质上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23]225
六、结语
新记《大公报》是民国时期的重要报纸,被称为“舆论重镇”,在当时社会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著名新闻学家方汉奇教授指出:“解放前的《大公报》,作为一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报纸,就是中间势力的舆论代表。”[24]前言20中间势力所具有的两面性特点,很好地反映在了该报的言论中。该报在续刊之初就坚决反对赤化,在国民党反共清党时期,赞成国民党的清党政策,但又严厉谴责国民党对共产党及革命群众的屠杀行为;在国民党“剿共”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抱有极深的偏见,配合国民党进行积极的“剿共”宣传,污蔑中国共产党为“匪”,但又发表了一些能客观反映中国共产党实际情况的新闻通讯,对如何“剿共”也有与国民党不一致的言论主张;在抗日战争时期,既存有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希望中国共产党进行“转变”,拥护“国家中心”,又有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客观报道;在解放战争时期,既承认中国共产党是第二大党,国家政局的好坏关键在于国共两党是否团结合作,又指责中国共产党是“以兵争政”,直到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大势已去,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时候,才最终转变了立场,谴责国民党祸国殃民,承认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讲,媒体形象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一个重要表现,中国共产党媒体形象的变化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艰难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成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25]67。这应该是《大公报》称共产党为国际党,视共产党等于卖国的基本原因。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战争。作为以推翻国民党政权为目标、以武装暴动为手段的革命党,力图塑造“国家中心”的《大公报》当然会视之以“匪”。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积极投入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战争中去。此时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形象当然会从“匪”转变成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力量。对于这一点,对中国共产党仍存偏见的《大公报》也不否认。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中国的第二大政党。由于中国共产党掌握一定的武装力量,更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内战再次爆发。此时对于坚持“国家中心”的《大公报》而言,中国共产党就是“以兵争政”。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终于丧失了民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最终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自然恢复了其代表人民利益的本来面貌。
注释:
① 其他报纸所持立场与此基本一致。例如,《申报》在报道平型关大捷时,专门配发了一张标题为“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照片,以示敬意;王少桐的《晋北前线朱彭会见记》不仅在《大公报》上刊载,也刊登在《申报》、《中央日报》等其他大报上。
[1] 社评:共产党在华失败之批判[N].大公报,1927-07-01(1).
[2] 社评:回头是岸[N].大公报,1926-09-04(1).
[3] 岁首辞[N].大公报,1928-01-01(1).
[4] 社评:明耻[N].大公报,1927-01-06(1).
[5] 社评:党祸[N].大公报,1927-04-29(1).
[6] 社评:党治与人权[N].大公报,1927-07-03(1).
[7] 社评:反共须知[N].大公报,1927-11-27(1).
[8] 社评:联俄与反共[N].大公报,1927-07-08(1).
[9] 社评:剿共清匪之亟务[N].大公报,1929-08-27(2).
[10] 社评:对西安负责者之最后警告[N].大公报,1937-01-22(2).
[11] 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第2版)[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
[12] 社评:读蒋委员长谈话[N].大公报,1937-09-25(1).
[13] 短评:晋北大胜[N].大公报,1937-09-25(3).
[14] 王少桐.晋北前线朱彭会见记[N].大公报,1937-10-21(3).
[15] 陆 诒.毛泽东谈抗战前途,拥护最高领袖抗战到底[N].大公报,1937-12-20(3).
[16] 社评:关于共产党问题[N].大公报,1941-03-10(2).
[17] 社评:延安视察的感想[N].大公报,1944-08-05(2).
[18] 社评: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就[N].大公报,1946-02-03(2).
[19] 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N].大公报,1945-08-29(2).
[20] 社评:政府可以先做一件事[N].大公报,1945-09-01(2).
[21] 社评:质中共[N].大公报,1945-11-20(2).
[22] 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N].大公报,1946-04-17(2).
[23] 《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编委会.大公报一百年社评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4] 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刘自兵]
D 231
A
1672-6219(2017)05-0109-04
2017-04-13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记《大公报》视野中的中共媒体形象研究”(AHSKQ2015D11)。
曹明臣,男,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10.13393/j.cnki.1672-6219.2017.05.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