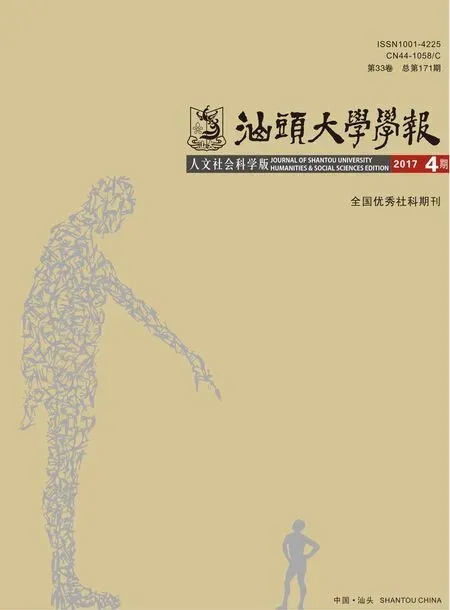潮州“关戏童”与潮剧戏神田元帅信仰考
——兼驳“关戏童”为潮剧鼻祖说
陈志勇
(中山大学中文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275)
潮州“关戏童”与潮剧戏神田元帅信仰考
——兼驳“关戏童”为潮剧鼻祖说
陈志勇
(中山大学中文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275)
“关戏童”是潮州的巫术仪式,它通过戏神田元帅降神附体于戏童进行歌舞及戏剧表演,具有一定的娱人功能。萧遥天《潮州戏剧音乐志》认为“关戏童”是潮剧的鼻祖,吴真《潮剧童伶制探源》主张“关戏童”是潮剧童伶制的源头;事实上,就“关戏童”的戏神田元帅和所表演“戏”的来源看,从关戏童班到潮音戏的演进之路难通。但“关戏童”作为一种具有巫术色彩的仪式演剧,考察其与潮剧的关系,不失为反思巫术仪式向戏剧演化路径论证的绝佳例案。
关戏童;巫术;仪式演剧;潮剧;田元帅
1947年饶宗颐先生总纂《潮州志》时设有“戏剧音乐志”一门,由萧遥天先生执笔,可惜初稿方成而修志工作已然停顿,故《潮州戏剧音乐志》当时并未刊行。1957年萧先生侨居新加坡时对原稿重新整理,题为《民间戏剧丛考》正式出版。书中,萧先生认为潮州“关戏童”是潮音戏的鼻祖。2000年吴真发表《潮剧童伶制探源》论文,论证原始巫术“关戏童”是潮剧童伶制的源头[1],捍卫了萧先生的观点。由于萧先生在撰写《潮州戏剧音乐志》时,“明代潮州戏文五种”尚未出土或庋藏于国外不曾寓目,其对潮音戏艺术来源的研判似有可商;而吴真认为潮剧戏神田元帅源自关戏童的论断亦有可疑之处,故笔者在此再作些探讨,求教于同好。
一、“关戏童”:潮州的原始巫术与仪式
“关戏童”是潮州、汕尾一带的“关神”巫术仪式,潮汕人称神灵附体为“关神”。潮州关神有多种,妇女玩的有“关篮畚姑”“关脚神”“关箸神”“关葵笠神”等,男人玩的有“关戏童”“关蛤蟆神”“转木椅”等,五花八门,各地略有分别。关神时,要按请神、催神、退神几个环节分别唱《请神曲》《催神曲》《退神曲》。神的身份各异,所唱曲子也有所不同。[2]368
对于“关戏童”的历史样态,我们不妨从“受术者”“施术者”及所表演的“戏”三个层面来考察。
1.受术者。“关戏童”的“童”,是指降神附体的对象——“童身”。潮籍学者萧遥天说:潮人信神,每逢赛会,必有一人为神降附于其身。口宣神话,不省人事,俗呼之为“童身”[3]63,也谓“同身”。其实,潮语称巫觋为“童魕”“童身”[3]63。当被巫觋请降的神祇附着于童身,他就进入特定时空中人神合一的“同身”状态。神的意志通过“童身”得以传达和表现。
“关戏童”中,“童身”必为男童。个中原因,陈历明先生指出:“儿童纯洁无瑕,易受艺术感染而接受教育。潮州民间的‘关戏童’活动,正是利用儿童的这一特点,以儿歌‘牵引’,将儿童曾经观听的已输入头脑的艺术讯息反馈出来,演唱为戏。”在陈先生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儿童纯洁,更符合神的圣洁标准。”[4]192
2.施术者。“关戏童”仪式活动中,请神、催神和送神的主持人却是成年人,而且多是巫师,如潮州彩塘乡关戏童班,它的施术者吴振源,是雷神爷庙(震天庙)的庙祝,其关戏童术是自幼家传,庙祝也是世传之职。[5]22巫师是“关戏童”的组织者,掌控着整个活动的行进节奏和场面。其中有三个关键的环节,显现出巫师的重要性。一是请神,需要巫师念诵咒语。潮阳关戏童的咒语是:“关咧关戏童,搬山过岭来相逢,相逢也相邀,呢哺英,田元帅,李家生,急急如律令。”又有“田师爷,骑马吱吱声。头壳戴顶金帽仔,带阮同身去游行。”[6]19这些咒语在萧遥天看来“俚俗可笑”[3]54,却带有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二是送神,同样需要巫师念诵咒语解除神祇附体。三是巫师最为核心的职司,即将请来的神灵附着于“童身”。萧遥天记述潮安浮洋的关戏童:施术者初把一根写满符箓的木棒挂中台中,并陈管弦伶乐,部绪既定,乃召童子到棒边,默默为他诵咒,须臾,昏迷扑地。[3]54“写满符箓的木棒”是施术巫师重要的道具,潮州彩塘的“关戏童”巫术,此时戏童还要手触木棒,实现人、神的联通。某种意义上,被巫师施以法术的“木棒”成为了“童身”接受神体的触媒。
3.“戏”的表演。降神附体的“童身”在施术者的引导下,不自觉地表演一些舞蹈和戏剧动作,就具有很强的神秘性和娱乐性,故又被称为“土风戏”(原始戏剧样式)。萧遥天记述潮安浮洋的“关戏童”巫术,处于昏迷状态的“童身”,在乐工弹丝吹管、伶工清唱的音乐下,依声作态,关目情节,处处扣合,如牵傀儡,如演双簧。[3]由于“童身”在台上闭目表演,且所表演的剧目为观众临时选择或后台安排。[7]3653更重要的是,小时候曾参加过这种神奇游戏的陈天国记述:这些“同身”所演唱的曲目,原先他们也并无学过,但演唱起来,唱做兼工,像真正的演员一样,真是不可思议。[8]85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关戏童”在受术后就处于昏迷状态,只做不唱,海陆丰地区的“关戏童”(又名“关蛤仔”)在受术后既唱也做。当授术者突然大喝一声“蛤仔跳”,这时,多数受术者就会手舞足蹈,唱一轮“蛤仔婆”的歌谣。[9]37所以,萧遥天指出:“当外来各种戏剧未入潮境以前,关戏童所唱的尽是畲歌蛋歌。”[3]54
其实,“关戏童”仪式过程中的戏剧娱乐性,还体现在施术者也有表演。如汕尾地区的“关戏童”,施术者在请神的过程中,念诵咒语后唱一轮“蛤仔婆”(当地歌谣)。在神灵附体的“童身”做戏后,授术者还会表演喷火、角抵、变脸等傩舞、百戏。[10]6
可见,粤东地区的“关戏童”很好地将原始巫术与巫舞融合到仪式过程中,在施术者(巫师)和受术者(童身)的表演中,展现较强的可观赏性和娱乐性,实现巫术、巫舞向戏剧表演的转化。我们注意到,潮汕地区的“关戏童”多是中秋前后的夜晚表演,当“关戏童班”的出现,则将这种节日性的巫术仪式表演常态化,从而强化了“关戏童”的娱乐功能。
二、田元帅:“关戏童”请降神只的身份信息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粤东地区的“关戏童”请降的是什么神?这“神”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外来迁入的呢?
笼统而言,关戏童所“关”之神,是戏神。从逻辑上看,因为戏神附体,“童身”们才会“做”他们不曾排演的戏目。这可从巫师咒语获得证明:“关呀关,关戏神,戏神(猛猛)来显身,神来演老爹,神来演老爷……”[10]6。在潮州的很多地区,“关戏童”请降的戏神就是指田元帅,如潮阳的请戏神咒语就有“田元帅,李家生,急急如律令”、“田师爷……头壳戴顶金帽仔”[6]19等语词。潮州称神为“老爷”“老爹”,行业祖师也有称“师爷”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探悉哪些关于这位戏神田元帅的身份信息呢?萧遥天说:“据老伶工的报告,最初教戏的祖师化为青蛙而隐,那么,田元帅原来是青蛙神。”[3]5吴真也认为关戏童祀奉的田元帅就是青蛙神。[1]我们注意到,南中国种植水稻的地区都有青蛙神信仰习俗,而且潮州的“关戏童”开始前,都由主持者到田里捧回一块土置于香炉中拜之[8]85;或是到田里拔回一株带泥的水稻来奉祭[9]37。这些信息表明:潮州“关戏童”所请的田土或田禾,就是田元帅的象征物,是一种田祖信仰的表现形式。但令人疑惑的是,“关戏童”仪式过程中并没有出现青蛙崇拜的任何信息。
其实,在紧邻潮州的福建,田元帅信仰中也含蕴着丰富的田祖崇拜元素。福建民间流传着田元帅诞生的传说:玉皇太子投胎杭州铁板桥,桥边有块大田,便取“田”为姓,名清源。[11]117这则传说不仅将戏神与“田”相关,而且直接与戏曲行业祖师神清源真君扯上关系。此外,该地区还流传田元帅母亲苏小姐郊游,吮吸田中稻浆而孕,被迫弃子于田边,为田蟹所救。[12]470甚至《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风火院田元帅”的插图,田元帅嘴上还画有螃蟹的涎迹,这与流传于福建一带的田元帅传说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凡此种种,戏神田元帅的诞生充满着“田地”意象和大地孕育的文化意味。正因如此,以叶明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戏神田元帅当来源于民间农业神“田祖”信仰。[13]181-198
然而,对农业神“田祖”或青蛙神的信仰,如何演变为戏曲行业内部祖师的崇拜,叶明生、萧遥天及吴真等学者缺乏中间的逻辑论证。我们断不能因为“田公”信仰体系中包含有一些农耕文化信息(如青蛙、蟹、田土、禾苗、稻穗、繁衍生殖等),就将田元帅信仰的来源归之上古时期的“田祖”信仰。笔者认为,潮音戏的行业神信仰来源于邻省福建的田元帅信仰。
首先,从有关文献记载和历史遗迹来看,福建的田元帅信仰远比潮州要早。元撰明刻的《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收录了带有傀儡戏特征的神只田元帅,因未指明其发源地和流传区域,还不足以证明田元帅信仰文化的中心在福建,但闽地的一些遗迹却无声地证明田元帅信仰文化的悠久。坐落于福建莆田瑞云祖庙供奉田公元帅,此庙始建于明朝初年[14]138,万历三年(1575)、康熙五十二年(1713)两次被伶人重修、扩建,这说明田公元帅信仰至迟在明朝已经扎根于莆田。据《中国戏曲志·福建卷》介绍,瑞云庙尚存乾隆二十七年(1762)莆田32个戏班镌刻的《志德碑》(碑文有拓录)。[15]556正因田公元帅信仰在福建的孳盛,乾隆年间人汪鹏特意指出:“习梨园者共构相公庙,相公之传自闽人始”[16]271。
其次,从历史面貌来看,福建的田元帅信仰远比潮州要繁盛。除莆田外,道光年刊《厦门志》也记载厦门的俗众祭祀雷海青,“上元前后,香火尤盛”[17];施鸿保《闽杂记》卷五“五代元帅”条记载:“福州俗敬五代元帅”[18]79;《福建通志·坛庙志》记载福州府侯官县也建有田元帅庙。[19]16事实上,当今在福建全省田元帅庙多达千座以上(大多是作为俗信,并非完全是戏神庙),其中有一些历史久远的祖庙明显具有戏神庙宇性质。当地的民众赋予了戏神田元帅更多的世俗神职功能,如生殖、祛灾、除病、驱邪等等,田元帅越出戏曲行业成为信仰广泛的地方神只。相对而言,潮州关于戏神田元帅的历史记载比较晚,而且数量远没有福建的多。有鉴于此,潮州戏曲行业的田元帅信仰很大可能是从福建传入。
我们知道,田元帅是南戏的戏神,除了福建,浙江的温州高腔、乱弹等戏班也是信奉的田元帅。[20]325同样,在粤东的潮汕地区,“田元帅”不但是正字戏、潮音戏、纸影戏的戏神,而且后来的“外江戏”(广东汉剧的前身)也改奉它为自己的祖师神,本地的秧歌舞、关戏童也同样尊奉其为戏神。潮州市昔有一座田元帅庙,原称庆喜庵,始建于何时不详,清咸丰九年(1859)重建。该庙正殿三龛,中供金身田元帅像,头戴纱帽,帽翅作两手掌状,十指合拢,嘴角刻有蟹形涎迹,旁有二童像侍立,一持竹板,一持小册,下供穿袍田元帅小像。像前立一神牌,署“玉封九天风火院都元帅神位”。龛前有磬一口,铭文记载光绪十六年(1890)冬月“外江戏”福顺班、新天彩、老三多、老新天香所立,说明外江班也改祀戏神田元帅。正殿壁嵌有石碑一方,记录了咸丰十年(1860)召开梨园会议,正音班、西秦班、潮音班重修祖庙,缴纳捐银的情况,并规定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田元帅诞辰,必演影戏隆重祭祀。[21]17-18
除潮州城外,粤东各地也建有田元帅庙,如海陆丰地区乡间即建有神庙,奉祀戏神田元帅,平时戏班、戏倌有神龛供奉[9]36-37,专门放置戏神牌位和供具的戏箱称为“老爷笼”。每到一处演出,装台完毕,便将牌位悬挂在底幕背面的正中处,香火日夜不断。还有专司供奉的“香公”,由一名相应角色的二等老生担任。[22]107潮阳司马浦乡也有戏神庙,关戏童者必须到那里请神奉拜。[6]19
“关戏童”由原来去田间请来田土或禾苗,改变为直接去戏神庙中恭请田元帅降临附体,显示田元帅在潮州戏曲行业神信仰地位的确立,同时也隐含着伶人群体“戏祖授艺”的集体心理。《潮阳戏剧简志》说:潮阳俗传田元帅是唐代人,姓雷名万春,教人以戏曲,故艺人称为戏神;当施术者念动咒语请田元帅出神,点角色、唱戏。[6]19前揭所引萧遥天从老伶工处访谈来的,戏祖田元帅化为青蛙来教授“童身”戏曲一说,同样折射出戏曲艺人“艺由神授”的群体心态。
其实,不仅关戏童,即便一般的潮音戏伶人他们的内心深处同样弥漫充斥着戏神田元帅(田老爷)授艺护佑的心态。如上文所述,潮州城田元帅庙中的田元帅塑像左右各一童伶,持竹板及书卷,[23]237这一塑像传达出潮音戏童伶受戏祖田元帅护佑的意涵。这种涵义还体现在平常的心态中,如潮音戏班下乡或过点,步行的童伶队列前头,擎着一支灯笼,名日“天地灯”,也称“老爷灯”。据说有“老爷”引领,就可一路平安。[24]718当然,田元帅在潮音戏童伶的心目中,不总是一副慈爱护佑的形象,有时戏班也借着他的神圣与权威来管教“子弟脚”(童伶)。戏谚谓:“老爷姓雷,戏仔着捶”,“着捶”便是要严厉打骂管教。旧时童伶入班,必先在戏神牌位前举行授教仪式;童伶学艺过程倘有犯规或失误,常被罚到戏神前长跪悔罪。
总之,“关戏童”游戏在潮州盛行的时候,戏神田元帅信仰已经在以潮州为中心的粤东地区伶人群体中确立起来。戏曲行业中“田元帅”信仰已经介入到“关戏童”巫术的表演环节,田元帅的伎艺通过“童身”进行展演,其祖师神的威严和神秘得以强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关戏童”因为戏神田元帅的降临,“神戏”通过田元帅的附体就实现了向人戏的转化呢?
三、源头误判:从关戏童班到潮音戏的演进之路难通
萧遥天在《潮州戏剧音乐志》“潮音戏与关戏童的关系”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潮州的关戏童,乃承接古代侏儒倡优的旧规,潮音戏的鼻祖就是关戏童”[3]58。在“关戏童”一节中再次强调:“潮州的关戏童,是潮音戏的胚胎”[3]55。论证“关戏童”与潮音戏的源流关系,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厘清:一是萧遥天认为潮音戏的戏神田元帅是从“关戏童”而来;二是吴真认为“关戏童”进化为潮音戏存在关戏童班这一中间环节。下面就这两个观点作些辨析。
(一)从戏神田元帅论证潮音戏源自“关戏童”,于理难通
萧遥天从戏神的角度论证潮剧信奉的田元帅是从关戏童而来,为“潮音戏的鼻祖是关戏童”的论断张目。他说:
潮音戏班所祀的神都称田元帅,或田师爷,史无可考,询之老伶工,所言很诡异,那是一段神怪的故事。他们说,田元帅是戏师,相传是最初教戏者,教曲甫成,化为青蛙而隐。干脆地说,田元帅是青蛙神。凡潮音戏开班,必祀此神。初就田野间拾取田土一枚,归盛香炉中,奉牲果香烛虔诚祷祭,这叫“请元帅”。按此神是关戏童先祀的神,故关戏童一称“关田元帅”,后来潮州的秧歌戏也同样祀它。所以,我的观察,必由关戏童传给秧歌戏,再传给潮音戏,一脉相承,可以看清楚同出一源的迹象。[3]3-4
尽管潮州“关神”的巫术可能追溯上古,但“关戏童”仪式所“关”的是戏神田元帅(上文已论),而又据笔者考证,戏神信仰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宋代[25],那么“关戏童”产生时间不会早于宋代。也就是说,潮州“关青蛙神”之类巫术或会较早,然“关田元帅”的巫术游戏必是在戏曲行业“田元帅”信仰产生和流行之后的产物。我们知道,戏神信仰的确立,是以戏曲艺术处于成熟阶段、从业人数众多为前提的。同理,流行于东南沿海一带的南戏戏神田元帅信仰文化,也一定是在南戏艺术相对成熟和发达时的表征。依照这个前提,潮州的“关神”巫术引入戏神田元帅,必是南戏处于成熟阶段之后的事情。若此,潮州的“关戏神”所表演的“戏”,应该不单是原始巫觋的表演艺术(巫歌巫舞),更有成熟的戏曲表演。这一推论其实萧遥天也是认可的,他说:“当外来各种戏剧未入潮境以前,关戏童所唱的尽是畲歌蛋歌”,而当外来各种戏剧入潮境后,“关戏童”就改演它们了。[3]5潮州的戏神田元帅信仰文化也正是随着南戏从福建等周边省份同时流入,“关戏童”的戏神田元帅崇拜也源于此。因此,不说戏神田元帅是从入潮南戏承传给潮剧,反而讲是由“关戏童”传给潮剧,就于理难通。
(二)从关戏童班到潮音戏的艺术演进之路难通
吴真论述“关戏童”与潮音戏之间的演进关系,是以潮剧童伶制为考察中心。她认为潮剧童伶制的起源可能与潮州古以有之的巫术“关戏童”有关,而关戏童班是古之巫术关戏童向潮音戏转化的中间环节。[1]这样,吴真的论文实际上将萧遥天“关戏童”是潮音戏源头的论断发扬光大了。
关戏童班作为戏班,进行商业演出,实现了“关戏童”巫术表演的常态化,展演的时间由局限于中秋前后的月夜变为全天候,表演人员由随机松散变为固定组班。遗憾的是,潮州的关戏童班已消失半个多世纪了,关于其班社组织形态和表演特征,只能通过亲历人员的回忆文字获得了解。据潮州《彩塘镇志》记载,彩塘曾有“关戏童班”[26]349-350,“关戏童班的演出脚色及舞台布设与同时期的潮剧戏班基本相同,戏文、唱腔、乐器伴奏也大致一样,只是人数比潮剧戏班多;关戏童班的演员们虽双目紧闭,却能自动地出台演戏,其亮相、台步、做样等,与一般潮剧无异,只是念唱由后台专人代替而已。”[8]87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关戏童班”基本的样貌:(1)排场布设、唱腔伴奏完全仿照潮剧戏班;(2)剧目来自潮剧戏班;(3)表演保留了“关戏童”巫术的原貌,但唱、演分离,后台职司唱念,“童身”前台表演。某种程度上,关戏童就是傀儡。“关戏童”演化为关戏童班,实现了巫术巫舞表演向娱乐性展演的转变,也被注入了一些商业演出的元素。
从“关戏童”巫术表演向关戏童班展演的衍进路径,比较容易理解;而关戏童班向成熟的潮音戏转化,其中间环节就令人费思。对此,吴真是这样阐释的:
巫舞型的关戏童已经发展到这两种巫术所难以企及的巫术与戏剧的过渡形态——关戏童班。关戏童班的表演超越了“请华光”和“关月”的单纯形体表演,它演的是“戏”,有情节有戏剧冲突,有化妆,有弦乐伴奏,有科介,有剧本,已经包括了戏剧的多种因素。它与戏剧的区别仅在于:戏剧是有意识地进行角色扮演,关戏童班则表现为神灵附体后的不自觉的角色转换。可以想见,当“同身”的扮演从“不自觉”演变到“自觉”时,关戏童也就从巫术演变为一种戏剧。关戏童班的表演已经具有这种从巫术转换为戏剧的态势,让演员开口唱戏,睁眼演戏,这样的转变是完全有可能的。[1]
吴真认为当“同身”的扮演从“不自觉”演变到“自觉”,他开口唱戏、睁眼演戏时,关戏童也就从巫术演变为一种戏剧。对此,我们不禁产生疑问:这个“转换”又是怎样实现的呢?
潮州的“关戏童”是典型的“降神附体”巫术。关戏童在巫师施法后,“出台亮相,顿时倒地,双眼紧闭,昏睡如醉”[7]3653,以致有人怀疑所施巫术为催眠术,戏童昏迷状态下的“依声表演,类似傀儡戏”[27]65。关戏童“无意识”下的表演,实际上是戏神在演出,“童身”仅仅作为躯壳供戏神所役使。
“关戏童”类似于北方民族的民间宗教信仰萨满。萨满在昏迷时也会呈现出超越普通人能力的“神格”,但一旦解除“凭灵”,就完成了由神向人的转换,不再具有超人的神格。[28]102姚周辉在专门研究中国民间各种“降神附体”事象后,也没有发现“退神返魂”后的巫师或乩童延续了附体精灵的神力。[29]9-50同样,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关戏童因为戏神田元帅的附体而获得戏目的灌注,并会在“退神”之后将不曾习得的剧目表演技能保留在记忆中。换言之,“关戏童”表演是在昏迷的“不自觉”所为,一旦醒来,能演戏目和伎艺自然消失,他又回复为原来的那个“懵懂”的童孩。
要描绘关戏童班向成熟的潮音戏转化路径,不能不关注“童身”未附体前艺术修养状况。尽管根据有限的文献记载,我们已经很难还原关戏童班中童伶所具艺术修养的实际情况;但不外乎存在这样两种可能:一种是关戏童班中童伶本身就有演出潮剧(或其他成熟戏曲)的经验,当他们退出“关神”仪式,他们自然能以真身演戏。这种情况的话,他本身就是潮剧艺人,在此就无需讨论了。另一种可能是,参与“关戏童”降神演出的童伶“一张白纸”,没有演出戏曲(如潮剧)的基础,当他们退出“关戏童”仪式后若仍能演戏,那问题就来了。既然只要通过“关戏童”巫术及其仪式,童伶就能以戏神附体的形式遍习新戏,等他“退神”后就掌握了演技,那么潮剧的童伶科班无需存在了。显然,这种情形并不存在。既然“关戏童班”的童伶“退神”后,也无迹象能显示“童身”因为参与“关戏童”而额外获得演戏的经验,会演的仍然会演,不会演的依旧不会演;也就是说,巫术还是巫术,戏曲还是戏曲,二者并不融通,只是在同一载体下各自表演。那么,推断“童身”在“自觉”意识下开口唱戏、睁眼演戏时,关戏童也就从巫术演变为一种戏剧的论断,根本就站不住脚。
笔者认为,“关戏童班”本质上就是“关戏童”巫术与潮剧表演的结合体(或称混合体),而不是如吴真所言是二者的中间状态。也就是说,不存在关戏童-关戏童班-潮剧在艺术上一脉演进的逻辑次序,反而是关戏童班吸收潮剧(或其他成熟戏剧)的表演艺术而呈现于舞台。关戏童班的消失,不是因为它转化为潮剧了,而是由于艺术的简陋或其他外部因素(如以“迷信”名义被禁)遭到观众和历史的淘汰。
康保成、詹双晖先生曾深入研究潮州戏剧形成轨迹后认为,潮州包括“关戏童”在内的“原始戏剧样式没有直接衍变为白字戏”[30]。詹双晖在《白字戏研究》一书中也认为萧遥天描绘的关戏童仪式中,“点定戏目,令之演唱”、“所唱戏目,皆非受术者所熟悉”、“所奉祀之神也即正音戏的戏神,其演唱有仿‘正音’,也有‘潮音’之腔调”之说,则为后世潮音戏、正字戏盛行之象,而非蕴含戏剧萌芽状态之关戏童。[31]70詹双晖进一步指出:在我们“无法知道最早的关戏童班起于何时,所扮何种角色,演唱内容又是什么,对早期关戏童以及关戏童班的艺术特征缺乏认识的条件下,贸然认为潮音戏、白字戏就是由关戏童发展而来,显然有失粗率。”[30]71这样的结论无疑是审慎的,对于我们客观认识潮州“关戏童”的表演形态及其与潮剧之间的艺术渊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潮音戏的艺术来源,固然有潮州乡土艺术的基因,但主要源头还是从福建泉州等地传入的南戏。[31]同样,潮州戏曲行业神田元帅也当是从福建传入的南戏戏神。[32]这两个问题已有学者详细论述,限于篇幅不再展开,但要指出的是,其实吴真在《潮剧童伶制探源》中已经注意到潮剧可能受到福建梨园戏的影响,但遗憾的是未予深究,反而太过执着于探寻潮剧童伶制与“关戏童”之间的内在关联,忽视了潮剧及“关戏童”周边的其他信息。
四、反思:巫术仪式向戏剧演化路径的学理性论证
萧遥天《潮州戏剧音乐志》在论述“关戏童是潮音戏的鼻祖”观点时,引用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中关于戏剧起源于巫优的论点,以此来印证他潮州“关戏童”为潮音戏鼻祖的论断。同样,吴真也主张作为巫术仪式的“关戏童”,其扮演由“不自觉”转化为“自觉”时,就进化为潮剧了。这表明,王国维戏剧起源于巫觋说的学术立场得到了研究潮州“关戏童”学者的充分重视和借鉴。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描述由上古巫术发展为成熟戏剧的理路是极为清晰的:中国戏剧起源于巫觋、歌舞,继而巫觋分化出娱人的俳优,接着是汉魏六朝及隋唐宋金时期的以歌舞演故事的雏形戏剧(有学者概括为“泛戏剧形态”[33]),再继之是以成熟戏剧面目出现的宋元戏曲。故而,王国维戏剧起源于巫觋说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中外学者的重视和认可;当然也有歧见,如有学者就指出:“我们无法假想,从巫师傩神的狂魔乱舞中可以产生一个高雅端庄的梅兰芳!”[34]378这样的话多少让人感觉到其中的个人意气,但平心而论,话语之中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祭祀仪式(巫术表演)是如何演化为成熟戏剧的?
确然,将原始巫术仪式向戏剧衍化的路径问题从学理层面阐释清楚,是主张戏剧起源巫觋的学者必须面对的共同任务。我们不应单单专注于宗教祭祀、巫术仪式中蕴含的戏剧因素,以及这些戏剧因素与后天成熟戏剧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更要厘清并描画出从宗教仪式演化为成熟戏剧的进路。日本学者田仲一成先生一直专注于祭祀仪式与中国戏剧之间联系的研究,在中国本土也有学者从遗存巫术印记的剧种来研究仪式与戏剧之间的演进问题,如蒙光朝《壮师剧概论》描绘广西的师公戏演进的历史轨迹:“开始是师公跳神,后来又跳神发展到面具舞,再发展到一个多角的唱故事(曲艺),再由唱故事发展到分角色演唱的壮师剧”[35]1。康保成先生一直从戏剧形态的角度来寻找这条“潜流”,《傩戏艺术源流》《中国古代戏剧形态与佛教》就是还原宗教仪式到戏剧形式之间模糊地带的重要成果。
潮州“关戏童”与潮剧的关系,同样存在这样的“模糊地带”,如何将这节点的演进路径讲清楚,就成为立论的关键所在。上文中已经详细驳斥了“关戏童”由关戏童班演化至潮剧的发展路线图,尽管萧遥天等学人提出的“关戏童”为潮剧鼻祖的观点不能成立,却给我们研究巫术仪式向成熟戏剧转化问题提供两点启示:
其一,不是所有的巫术表演或祭祀仪式都会向成熟的戏剧转化。只有当巫术仪式中出现角色扮演和“戏”的表演,并不断强化娱人功能时,巫向优的角色转化,才可能实现仪式向成熟戏剧的演进与转化。
其二,我们在考察祭祀仪式向成熟戏剧演进轨迹时,更要秉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来甄别近世成熟戏剧反哺仪式展演的样貌,切莫把宋元之后成熟戏剧表演艺术反渗、反哺仪式展演的状态,视为仪式向戏剧演进的中间环节。若如此,必会在演进路径的描画和论证中头绪不清、擎肘难书,甚至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
综上所论,潮州“关戏童”尽管只是中国民间林林总总巫术仪式中的一个例案,但它与戏神田元帅信仰及潮剧艺术源头的历史渊源,值得我们做深入的探究。揭示“关戏童”所含蕴的丰富民俗事象和文化符号信息,可为学界探讨巫术仪式(宗教祭祀)向成熟戏剧演进轨迹提供参考。
[1]吴真.潮剧童伶制探源[J].文艺研究,2000(2).
[2]叶春生,施爱东.广东民俗大典[M].第2版.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萧遥天.民间戏剧丛考[M].新加坡:南国出版社,1957.
[4]陈历明.潮州出土戏文珍本《金钗记》[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5]陈小庚.潮韵绕梁 广东潮剧[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3.
[6]马庆忠,陈创义.潮阳戏剧简志[M]//广东省潮阳县文化局编.潮阳戏剧史话.内部资料,1985.
[7]蒋宝德,李鑫生.中国地域文化(下册)“潮汕卷”[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7.
[8]陈汉初.潮州风土戏关戏童[C]//潮俗丛谭.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
[9]蔡锦华.海陆丰地方戏曲文化面面观[M],广东省海丰县文化局油印本,1990.
[10]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广东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7.
[11]刘晓迎.永安市黄景山万福堂大腔傀儡戏与还愿仪式[J].民俗曲艺,2002(3):135.
[12]黄锡钧.泉州提线木偶戏神相公爷[C]//南戏论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
[13]叶明生.一把打开戏神田公迷宫的钥匙——《大出苏》[C]//南戏遗响.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
[14]廖必琦等修.莆田县志[M]//光绪五年(1879)潘文凤补刊本.1926年重印本.
[15]中国戏曲志·福建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
[16]汪鹏.袖海编[M]//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
[17]厦门志[M].卷二“祠庙”.道光十九年(1839)刊本.
[18]周亮工,施鸿保.闽小记·闽杂记[M].来新夏校点.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19]陈衍修纂.福建通志(第十五册)[M].铅印本,1938.
[20]刘念兹.南戏新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1]林淳钧.潮剧闻见录[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
[22]胡幸福.趣闻广东[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9.
[23]沈丽华,邵一飞.广东神源初探[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
[24]刘志文.广东民俗大观(上卷)[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7.
[25]陈志勇.论民间戏神信仰的源起与发展[J].文化遗产,2010(4).
[26]彩塘镇志办公室.彩塘镇志[M].内部印刷,1992.
[27]陈俊粦,王次阳.潮州胜概[M].“风情篇”.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28]郭淑云.中国北方民族萨满出神现象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29]姚周辉.神秘的幻术——降神附体风俗研究[M].修订版.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
[30]康保成,詹双辉.从南戏到正字戏、白字戏——潮州戏剧形成轨迹初探[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1).
[31]詹双晖.白字戏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32]陈志勇.南戏戏神田公元帅信仰变迁考[J].文化遗产,2013(2).
[33]黄竹三.论泛戏剧形态[J].文学遗产,1996(4).
[34]解玉峰.献疑于另类的中国戏剧史——读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C]//胡忌主编.戏史辨(第4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378.
[35]蒙光朝.壮师剧概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李金龙)
G127;K89
A
1001-4225(2017)04-0024-07
2016-11-22
陈志勇(1975-),男,湖北嘉鱼人,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文化遗产传承与数字化保护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明代杂剧传奇文献整理与研究”(16wkjc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