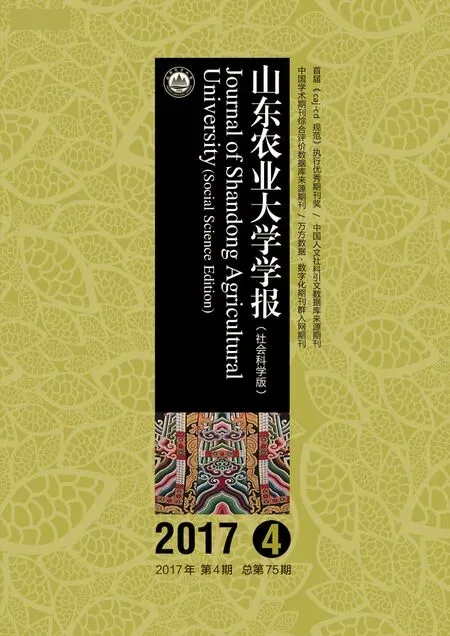中华海洋文明与世界海洋文明的互动及贡献
□郭奇林
中华海洋文明与世界海洋文明的互动及贡献
□郭奇林
中华海洋文明是世界海洋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3000多年来,中华海洋文明以其特有的物质和文化形态与世界海洋文明不断地进行着交流和互动。通过自己的方式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将中国先进的耕作技术和文化理念传向附近国家,将先进的科技和知识通过行经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同国家的商人传递到四面八方。其与西方长期互动的历史,也为当今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的世界和平发展模式,提供了文化和历史的借鉴。
中华海洋文明;世界;互动;贡献
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写道:“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学习东罗马帝国。”[1]世界历史就是一部不同文化元素组成的各具特色的文明之间的互动历程。在这一历程中,作为中华文明多元组成中的海洋文明,在与世界海洋文明的互动中,以其特有的形式和内容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回溯历史,着眼未来。值我国致力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规划和建设之际,对东西方海洋文明互动史做一综合性的梳理,一方面通过历史的参照汲取经验,另一方面也为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伟大的建设征程提供思想文化支撑。
一、古代中华海洋文明对世界文明的积极影响
海洋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依靠很早就与人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但在造船和航海能力上“突破大海隔离和束缚”“有走向海洋的进取意识,同时获得与外部族群接触联系和文化交流的机遇”,[2]则是最近几千年才具备的能力。这也是人类海洋文明的开端。它在发展中不断充实和丰富着自己的内涵,从区域走向全球,从全球走向立体。[3]中华祖先在石器文化时代就开
始在大河流域(长江和黄河流域)、渤海、黄海以及东南沿海区域进行生产和生活,他们种植水稻、谷物,泛海捕鱼,陆地和沿海居民相互间进行着必要的交换,为中华多元文明的开创营造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中华海洋文明就起源于这种滨海与岛屿先民的渔捞生活,这些濒海聚落在进入文明时代后逐步发展为港口(或者是海洋族群建立的早期国家的国都),“他们通过大海沟通环中国海不同区域的联系,并将文明传播到西、南太平洋的岛屿。”[2]
据文字记载推断,中华先民在春秋战国之前已经与海外世界有了接触。如,“大九州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认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益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九者,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文献描述了一个被海洋环绕的世界,有如中国这样的州还有很多。九州说反映了中华先民以中国为中心观察世界的一种朴素的海洋观。《竹书纪年》中有夏帝王芒“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鱼”,也就是说4000多年前中国已经有了辽阔的海疆,狩海经营的海洋意识。《诗经·商颂》载:“肇于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祈祈”,反映了从海上来商朝交往和朝拜的盛况。上世纪20年代,殷墟出土了大量海贝、鲸鱼骨、龟甲,说明中原地区与沿海很早就有贸易往来,中华民族的疆界达到了东南沿海。周代时期已经可以制造战船,进行海上作战,如《诗经·大雅》载:“畀彼泾舟,蒸徒楫之,文王于迈,六师及之。”而这一海上作战实力也使周朝对周边区域产生了影响,《诗经·周颂》记曰:“周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被到荒,至于海邦,淮夷同来。”东南沿海地区以及长江下游地区均成为周的番属。这些记载充分说明,早在公元前1000多年,中国已经开启了海洋文明之旅。
在这之后的两千多年间,中国率先建立了封建制度,铁农具广泛使用,农耕和栽培技术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象形文字和文化礼仪精深成熟,“辐辏四夷”,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均有了质的飞跃,中国的海船开始了有目的的探索。这一过程中,中国发现了日本、南洋诸国、西亚国家、非洲国家以及欧洲国家,不仅扩大了对异域世界的了解,也获得了一些国家的臣服和朝贡。这一时期,“中华海洋文明是东亚海洋文明系统中的中心系统。”[2]
中国海洋文明之旅的足迹首先出现在东亚近邻朝鲜和日本。据《山海经》记载:“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山海经·海经·海内北经》)这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中华百科全书精确地指明了朝鲜的位置,同时也显示人们已经到达了朝鲜的南部,“韩雁在海中,都州南。”韩雁就是古代韩国的国名。有关日本的记载:“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相关研究显示:中国北方沿海居民在春秋战国时期,经朝鲜半岛渡海至日本列岛,并带去先进的金属文化与水稻种植技术,使处于石器时代过着原始渔猎生活的日本,开始了从绳文式文化缓慢发展中脱离出来,向着金属工具和水稻种植的弥生式文化飞跃转变。[4]对于日本的影响不能不谈到徐福,徐福是日本古代的人文始祖,对日本文明的形成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史记·始皇本纪》有徐福东渡的记载:“始皇东行郡县,……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的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据孙光圻分析,徐福航行线路可能是:起点是琅邪(山东胶南),第一段航路是琅邪—成山头—芝罘港;第二段是芝罘—蓬莱头—庙岛群岛—老铁山;第三段航路是老铁山—鸭绿江口—朝鲜西海岸—朝鲜南部海岸;第四段航路是朝鲜南部海岸—对马岛—冲岛—大岛—九州海岸。[5]此后日本与中国的交往增多,据《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载:“倭人在带方大海中,以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来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日本通过朝见,从中国获得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带回华夏文化,对于开发和建设日本产生了重大历史作用。在东亚文明系统中,南洋与中国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密切,这一方面由于唐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沿海港口(广州为最)成为中外货物交易的汇集地;另一方面南洋岛国特殊地理位置,成为沟通东西大洋的中转港口。中华海洋文明与南洋的互动,集中体现在郑和下西洋。从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至宣德六年(1433年)郑和死于古里国(今印度卡利卡特),28年间中国出使西洋的船队每次人数均在27 000人左右,行程经过南洋、西亚、东非、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赤道以南,遍及亚非海岸,逾15 000英里。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和平的国际之旅,它展示了古代中国海洋文明精神的和平内涵,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声望,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中外了解和交流。时至今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仍流传着有关郑和的各种故事,留下了以其名号命名的遗址和祭祀堂,如,印尼的爪哇岛有三宝垅、三宝港、三宝洞、三保井、三宝公庙,苏门答腊岛有三宝庙,马来亚的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城、三宝井,泰国有三宝港、三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三宝寺塔等。[4]
连通古代中华海洋文明与世界海洋文明的要归功于海上丝绸之路。对此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从中国的南部沿海出发沿越南中南半岛入南海,过马六甲进印度洋到西方的路线;二是从地中海、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出发往印度到中国的航线。据《汉书·地理志》对这一海上线路的记载:“自日南(今越南)障塞、徐闻(广东雷州半岛南端徐闻县)、合浦(广西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马来半岛东南);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缅甸南部);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一带);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缅甸太公城)。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印度南部泰米尔的康契普拉姆)……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说明在汉朝,中国的海船已经能航行到印度南部了。[6]唐朝从广州出发最远到达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西南端亚丁,也就是当时的大食王国。另一条线路是从西向东航行来到中国。公元一世纪,定居在埃及的希腊商人在其著作《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中,对这一航路有过描写:经红海和印度洋,经马六甲和印度支那沿中国海岸北上,一直到达秦那(China)。在印度港口会看到中国的丝绸,还有来自中国的皮货、胡椒、桂皮、香料、金属、染料和药品等也在那儿装船。这种航行要利用季风,八个月往返一次。但运输者不会走完全程,都是在中途接换。[7]随着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后,阿拉伯商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中介。罗马、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从海上来到中国,他们的船停泊在广州、泉州或是明州(宁波),他们在这里出卖来自西方或是南洋的各种货物,包括皮货、香料、海货、金银等,又将中国的瓷器、丝绸、漆器、铁器、茶叶、纸张装运上船。
这一时期中国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均领先于世界。唐代中国已能制造大型的海船。据慧林在《一切经音义中》描述一种叫“苍舶”的大船,长二十丈,可载六七百人。南宋周去非写的《岭外代答》中讲到宋代南海中中国的巨舟,“帆若垂天之云,柁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8]。导航技术上从罗盘开始向指南针过渡,出现了天文定位技术。唐开元年间,高僧一行发明了一种可以测量维度的仪器“复矩”,用一把有刻度的尺,手持该尺,使刻度起点与地平线对齐,目测北极星在刻度尺上的高度,可大略计算出测量者所在的维度。这与现代的测量仪器“六分仪”原理是一样的。
纵览历史可以看到,古代中国至少在商周以前就与世界海洋文明不断地进行着交流和互动,并通过自己的方式为世界海洋文明做出了特有的贡献。其特点是:第一,当中华先民可以走出近海的时候,他们将中国先进的耕作技术和文化理念传向附近的岛屿邦国,使这些地区及早摆脱了原始氏族的生产状态,并积极地加入到汲取中华文明的行列,这样也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区域海洋文明圈。它与欧洲地中海为中心的区域海洋文明既相似又不同,在物品交换的相似背景下,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海洋文明圈更强调政治的归附和思想上的和谐,利益因素不占主要地位。在宗教问题上则更显现出包容和多元。
第二,这一时期中国海洋文明呈现出巨大的辐射状,它的影响通过行经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同国家的商人传递到四面八方。这种影响惠及了世界各个民族。如,中国的手工产品,丝绸、瓷器、漆器、铁器、纸张等,引领了时尚,丰富了各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科学技术上,造船、造纸、印刷等技术,先是为阿拉伯人学习,之后又传入欧洲。其中造船技术对欧洲影响相对较晚,但作用巨大。
第三,由于古代中国先民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早熟与发展,尤其是科技上的优势,造成16世纪之前中国与世界海洋文明的互动总体表现出向外播散的、甚至是单向型(如对东亚国家)的态势。这也使得中国成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和国际舞台的主角。这期间,汉唐开创、宋元时期达到高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对沿线国家经济文化的繁荣产生了巨大作用。优秀的外来文化亦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丰富和滋养、延续和传承本土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使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古文明绵延至今[9]。
二、16世纪以来中华海洋文明与世界的互动
16世纪世界进入大航海时期,此后的两百年间,中西海洋文明交流形成了第一次高潮。在世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东亚朝贡体系开始走向解体。与汉唐宋元时期不同的是,明清时期中国海洋文明呈现出收缩的态势,与西方海洋文明的进取形成了强烈对比。尽管中国的商品和物产依然广受欢迎,但在工具器物应用方面尤其是对宇宙和世界的了解方面,中国第一次发现还有比自己更先进和高明的知识群体。这一时期,中国无论经济还是军事方面与欧洲国家相比依然具备自信和实力,初期的欧洲殖民者亦尽量遵守中国的制度并以委婉的形式去打开与中国接触的大门。从此,中华海洋文明的视眼开始从东亚区域移向欧洲并最终融入全球海洋文明的世界。特点是:唐宋以来活跃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阿拉伯商人此时已经落寂,泛海而来的欧洲传教士群体则成为这一交流互动的新的媒介。
1582年利玛窦入华传教,将西方的科技知识,天文、物理、数学、地理、医学等全面传入中国。诸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远西奇器图说》《火攻揭要》,这些书籍的翻译和传入,冲击了明朝空疏的学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在传教士的帮助下,修纂了《崇祯历书》,并对西洋火炮进行了仿造,开启了西学东传的大门。明亡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做了整理然后呈献给清政府,即《时宪历》,中国从此开始使用西历。康熙时,采用了经纬图法、梯形投影等先进方法,中国制成了当时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地图《皇舆图》,是近代中国地理版图的一个蓝本。西方科技知识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影响,出现了一批会通中西的人士,以梅文鼎、王锡阐最为突出,梅文鼎作了《梅氏丛书辑要》,王锡阐作了《晓庵新法》,两部著作均介绍了西方天文学数学知识,在一些方面还提出创新的见解。梅珏成等人编成了《数理精蕴》,集合了当时西学中数学的主要成就,成为学习和研究西方数学的教科书。耶稣会士受到重视,并主持清朝钦天监事务,从利玛窦、汤若望,到南怀仁、张诚等,长期担任这一职务,促进了中西天文学的交流和合作。雍正时期,开始全面禁教,中西交流局面日趋衰落。由于罗马教廷禁止中国天主教信徒尊孔祭祖,雍正帝的答复是将他们驱逐出境,只留少数懂天文历法的传教士在京城。1824年担任钦天监监正的传教士福文高去世,道光帝再未任命其他传教士担任该职务,自汤若望以来一百多年间天主教士担任钦天监职务的局面结束了。[10]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传教士带入的钟表,逐渐为中国人所熟悉并接受。与中国传统计时使用的水漏、更鼓和梆子相比,钟表更加精密和小巧。钟表的引进和普及,正值近代中国城市社会转型时期,它对城市系统各种活动的时间规范,人们的时间意识、效率意识的提高,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另一个向度上,中国文明亦通过传教士走进欧洲的千家万户,欧洲开始全面认识和了解中国,是为“东学西传”。1615年由利玛窦撰写,耶稣会士金尼阁增修《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出版,一时引起欧洲人对中国的极大兴趣。1735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根据传教士的书简、札记、日记等材料,编写成《中华帝国全志》,这是涉及中国各个方面的一部百科全书,是当时欧洲人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必读书。此间,传教士据见闻和各种在华记录出版了有关中国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研究著作,如,1642年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中华帝国史》,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叙述。于1776-181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艺术、习俗史》,由法国传教士韩国英和另一法国传教士所写,是第一部从社会角度来介绍中国的史书。传教士冯秉正依据朱熹的《文献通考》写成《中国通史》,成了在欧洲刊布的中国通史的楷模。之后格鲁贤(Grosier)作了《中国自然史》,为这部通史作了补充和完善。地理学方面,1656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中国新图》,对中国15个省的地理、人口、经济等做了介绍。传教士把中国儒家经典也传到了欧洲。利玛窦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将“五经”译为拉丁文。柏应理、恩里格等人所著的《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1687年用拉丁文刊行,其中包括《论语》译本。以及《大学》拉丁文译本(西文版名称为《中国之智慧》)、《中庸》(西文版名称为《中国政治道德学》)和《易经》等,均开始在欧洲发行,这些译著极大地增进了欧洲对中国的了解,还形成了一股“中国热”。而中国的哲学思想则对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耶稣会士们的著作,孔子智慧格言和治国思想为人传颂,当时最杰出的思想家也不能摆脱它的影响。传教士历史观也发生了变化,1658年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i)在所著《中国上古史》中就提请学术界注意,中国历史具有不可思议的古老性,其可靠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圣经》记载的世界历史之前,甚至远远超出这一时间。[7]
由于新航路的开辟,西方的科技和人文知识传入中国,一方面极大地冲击了中国“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也促进了中国知识界的近代转变;另一方面,欧洲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与东方有了直接的接触,16~18世纪成为欧洲对中国的再发现时期,也成为欧洲经济和思想发展的转折点。这个时期中国依然是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中心,巨大而繁盛的贸易市场,琳琅满目的商品都是欧洲急需却又无法自己生产的。新兴的欧洲像一个饥饿的年轻人,充满激情但又缺乏营养,依靠新大陆的开辟,葡萄牙、西班牙率先用美洲和非洲的金银打开了一条东西方贸易的捷径,欧洲用“他山之石攻玉”,走上了马克思所说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原始资本积累之路。由于从亚洲港口停泊的东方船舶中获得启发,葡萄牙、西班牙最早开始制造出多桅帆船,欧洲造船技术密封技术获得了改进,速度和容量有了突破,这使得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快船更具效率优势。在这种往来中,原产自中国的各种作物园艺技术也开始传入西方,如水稻、茶叶、柑橘、桃树、杏树、桑蚕等的培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对近代世界海洋文明走向全球发挥了特殊的推动作用。如,造纸和印刷术传入欧洲,对打破教会对知识和教育的垄断,知识的大众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马可·波罗旅行记》(拉丁文版名称《世界珍异记》)就是这个时候为大多数欧洲人所了解。借助印刷术提高,价格低廉的纸质书籍开始普及到普通人,哥伦布就有一本1485-1486年间在安特卫普出版的马可·波罗《世界珍异记》,并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火药和火器在13世纪后通过中亚传入欧洲,欧洲进行了改进,发明了威力更多的火枪和火炮,近代将火器安装在船舰上,这极大地改变了中西方的力量对比,成为西方殖民时期对外掠夺和扩张主要优势工具。指南针则帮助达·伽马和麦哲伦找到了通向东方的新航路,第一次以实证的形式宣告了近代科学的胜利,托勒密的“地圆说”不再是假设,从世界的任何一点出发沿着一个方向前进都可以回到原点成为现实,人类开始走向全球海洋文明。
地理大发现之后,东西方实现了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尤其在商业经济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圈为欧洲资本主义近代的起步和发展,从商品、原料到市场均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正如弗兰克在他的著作《白银资本》所描述的:近代早期世界并非由欧洲推动的,而是由一个早已运转着的世界经济体系所塑造的。那就是中国,它的发展悠关当时的全球经济。欧洲通过加入亚洲贸易,从比他们更具生产力、更富裕的亚洲经济中获得了好处[11]。思想文化上,中国古老的历史则打乱了欧洲人止步《圣经》的历史观念,汉语无与伦比的结构,亦使欧洲学者开始用全新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言语。莱布尼茨从中国《易经》中发现了二进制原理,他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是神学和自然结合的典范,从那里“造成基督教徒们分裂的纠纷原因,都会在它面前最终消失。”他甚至建议,如同欧洲向中国派遣文人一样,可以从中国请来一些文人,以这种手段而得到西方所没有的那种普遍真理。[7]
这种可谓平等意义上的交流,最终在东西方的实力对比中被打破。1840年后,收缩的中国在极其被动中被卷入了西方海洋强国构建的世界殖民体系。此后,近代西方海洋文明开始大规模向中国传播,这一方面导致东西方在政治、军事和文化各方面的严重对峙和碰撞,西方通过不平等条约建立起条约体系来压榨和奴役中国人民,使中华民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政治文化的思潮,并与推翻帝国主义殖民奴役的社会运动一道,形成20世纪上半期拯救民族危亡的民族解放浪潮。其中,从1860-1890年代,主要是学习西方工艺技术为主的洋务运动,其成就是在工业、教育和军事等方面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刺激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甲午战后,随着西方维新思想和进化论的传播,“维新变法”和“民主共和”的思想先后掀起中国社会变革的浪潮,它促成辛亥革命的爆发,最终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革新迈出了关键一步。此后,在西方“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下开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则对封建旧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从思想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三、结语
汤因比说过,“文明是一种运动,而不是一种状态模式,是航行而不是停泊”[12]。新的世纪,“随着海洋开发的立体推进及西方扩张性海洋文明发展模式的难以为继,世界海洋文明正在转型”[2]。而告别近代之痛的中华民族,一方面需要通过积极地历史审视进行总结,另一方面也可从曾创造过辉煌的古代中华海洋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有益的价值元素,为我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文化和历史的借鉴。概如:
其一,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国家间要合作、文明间要交流,这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必然。3 000年来东西方海洋文明的互动历史形象地诠释了这一点,而当前“一带一路”的倡议也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规律的积极作为。它借助我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着力于推动开放、合作、发展与和平的国际海洋文明秩序,这与汉唐以来搭建起东西方文明互动桥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其二,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源远流长,但它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殖民扩张,而是靠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和吸引力。这一历史经验对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拓展并构建新型的东西方海洋文明的互动模式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其三,中国文明是一个融合多种文化与文明一体的熔炉,“善于在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寻求均衡”。在人类迈向真正有效的全球治理过程中,这种包容性的价值观弥足珍贵。在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价值观面临巨大危机的今天,中国文明的这种开放胸襟正契合了当代全球社会的价值追求。[13]
总之,中华海洋文明与世界海洋文明的互动之路,是一条充分尊重他国国情、“和而不同”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历史上,它以其独特的方式泽惠于世界文明的同时,也从文化上、心理上拉近了与沿线国家间的距离。今天,随着我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平发展方案的出台与实施,在如何超越西方模式、化解新的国际政治、经济“零和博弈”困境与危机面前,这一路径仍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为全球良性治理的实践,提供一方具有深厚历史与文化渊薮的根基。
[1] 罗素.中国问题[M].秦悦,译.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146.
[2] 杨国桢.中华海洋文明论发凡[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4):43-56.
[3] 杨国桢.中华海洋文明的时代划分[J].海洋史研究,2014,(01):3-13.
[4] 杨金森.中国海洋战略研究文集[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6,7,13.
[5] 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103.
[6] 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19-20.
[7] 雅克·布罗斯著.发现中国[M].耿昇,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5,79,88.
[8] 许海燕.中西文化交流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6.
[9] 徐梦龙.历史学家刘迎胜:”汲取丝绸之路滋养用文化自信推动‘一带一路’建设”[EB/OL].(2017-05-12)[2017-06-07].http://www.thereport.cn/newsDetail_forward_13383.htm.
[10] 李喜所,林延清,李梦芝.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二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2-7.
[11]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3-14.
[12]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M].沈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47.
[13] 杜德斌,马亚华.一带一路——开启全球治理新模式[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6-01(01).
K203
A
1008-8091(2017)04-0001-06
2017-03-16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通识教育部,福建 漳州,363105
郭奇林(1974- ),男,汉族,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