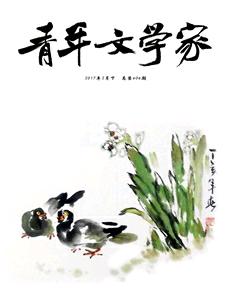《活着》的电影改编研究
葛晓刚
摘 要:《活着》作为小说是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作品,作为电影也是一部佳作,它们以悲悯而又带有黑色幽默的基调大跨度地再现了中国现当代史。电影除了对小说进行正常的情节筛选之外,对小说许多关键部分又有一定的变动。本文将对电影与小说的异同进行探讨,基于两种艺术形式的特点,寻找出这部电影成功的自我原因。
关键词:悲剧色彩;荒诞;苦难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2
电影和小说在情节的引入方式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小说以作者本人作为故事的引入者,读者顺着作者的经历将视角定格于自然质朴的乡下,直到遇到一位名叫福贵的老人,随着老人的讲述才展开了以福贵为主人公的主体情节。第三方即作者的介入,巧妙地将作者与小说融合起来,把自己作为老人的听众与读者一并倾耳而听,无疑增添了小说的亲近感。同时乡下浓厚的土地气息又顺其自然的为老人一生经历的讲述增添了历史厚重感。小说的末尾从故事再次回到老人放牛的场景,乡下恬静之美再次映入眼帘,表明老人从过去回到当下的一种超脱淡然之态,也意味着将读者从故事带回现实,引发读者对现世人生的深刻思考。余华的这种处理是值得称赞的,而张艺谋对情节开门见山的简单处理也未尝不可,电影受时间所限,需要观众更早的融入到情节中来,所以若照搬原著未免显得过于拖沓,而对于原著引入情节为读者带来的情感铺垫,电影完全可以依靠其画面载体,声音载体还有演员生动传神的表演等这些小说所不具备的特点来对其加以弥补。
《活着》小说与电影所展现的这种蕴意基本是一致的,如余华所说:“《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活着。”活着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词语,却给予我们生命中最沉重最顽强的精神力量,而当其与苦难不期而遇时,就成为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但又是世世代代,芸芸众生所无法真正领悟的人生哲学——命运之苦难。[1]张艺谋则依照自己的理解对小说进行了大胆的再创造。从叙事方式上来说,小说所塑造的故事场景更具有荒诞性,例如有庆的死就十分不可思议,县长夫人产后大出血,有庆与其血型相符,成为献血的第一人选,可谁又想到有庆这一个单纯的孩子就是这样在医院里抽血过多而死的。这情节的荒诞性可想而知,现在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医院能够发生这种事情。有庆就是这样被官僚主义和庸医所害死的,这就是整个时代的悲哀,也彰显了当时社会的荒诞,冷漠,压抑。而在电影中对于这种荒诞性是有所弱化的,将有庆改为县长开车撞墙导致事故而死,显然这是更容易理解与接受的死亡情节。
张艺谋在作品中更加崇尚真实,采用各种时代符号去彰显时代特征,站在整个社会历史的角度审视时代历程。努力的做到了将小说的主观倾向大幅度减弱,还原给观众一个更为客观的生活图景,是是非非由观众自我体悟,将观众的思想空间扩大化,寻觅自己想要的精神体验,同样把这种接受美学很好地展现出来。
从作品的气氛渲染上来说,两者是具有明显差别的。余华的《活着》着重渲染這种悲凉,阴森,低沉的气氛,全篇少有温馨场景,几乎没有清新亮丽之感,让读者在悲悯中品味全文。而张艺谋对此再次创新,虽然电影依旧采用贯穿整体的冷色调,但在其中却刻画了许多温馨的场面,部分背景音乐的运用也使得影片中一度充满希望。而展现这种希望的最为巧妙之处就是影片中对幽默感的运用,虽然黑色幽默居多,但丝毫不影响其对整体压抑气氛的减弱作用。影片中福贵这一角色有着大量的俏皮台词和喜剧化的表演,在葛优的演绎下使气氛显得较为轻松欢快。还有一些喜剧化的情节,例如有庆家珍对福贵的恶作剧,福贵幽默精彩的皮影表演,都大大降低了影片的悲剧化色彩。
从福贵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电影则将小说中的福贵性格刻画的更加尖锐化。我觉得影片的开头便有所体现,将背福贵少爷回家的肥胖妓女夸张化,不仅是增加喜剧色彩,同时也预示着福贵前后两期的扁形人物特征将更为明显。验证最为显著的便是福贵因龙二的枪决而被惊吓到尿裤子这一情节,着重的突出了福贵的小人物特征,面对逆境的逆来顺受,面对死亡的胆小与恐惧,从生存夹缝中寻求一丝快乐的卑微心态。这些都在电影中有了更为夸大化的表现,从戏剧的角度来说这是对小说的一种升华,戏剧正是需要一种夸大效果对观众内心带来的震撼。
从反映历史现实的着重点来分析,小说对福贵一生所经历的历史事件进行了均衡化的描绘,并非有明显的侧重点。而电影则不太一样,将侧重点放在了文革这一历史重大事件之上,而且在这一部分的描绘中,所呈现的社会混乱感甚至大幅度地超越了小说。对这一中国历史禁忌话题的大胆展现无遗是值得敬佩的,这或许就是当年这部影片被禁播的原因。凤霞的死正是荒诞性的极致体现,小说并未对其死亡的细节做太多描述,而电影凤霞产后大出血没能救回的根本原因则是因为医院内没有好医生,好的医生因为文革被批斗了,在找到这位医生准备救人的时候,医生却因为饥饿过度,在吃一个馒头的时候噎死了。其实说来荒诞但也并非荒诞,这种情况其实当时的社会现实,真正的人才都被迫害,而当人民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发现缺少了他们的社会无法正常运转了,整个社会都在腐化,变质。时代的可怕性在观众心理留下了深深印记。所以即使这样小说与电影依旧是遵从现实主义的,没有依靠幻想虚构社会以及人生。电影中的最主要道具皮影盒子的象征意义并非只是寓意着福贵的人生历程和家庭观念,同时后期没有皮影的盒子又象征着建国后尤其是文革时期社会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摧残。而余华本人最为擅长的就是对文革的描写,几部优秀作品中都有涉及文革,张艺谋选取这部分突出刻画是非常明智的。
最后,电影照比小说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变化就是故事的结局。小说中福贵的外孙子苦根吃豆子噎死了,代表着福贵最后的一位亲人也离他而去了。而电影的最终画面定格在福贵喂苦根吃饭的场景,也就是说电影的结局苦根并没有死。这是张艺谋想要弱化作品悲剧意识的点睛之笔,给了观众更多的希望,而不是余华想要带给读者在经历苦难以后的一种淡然,也可以说是一种麻木。而在这一差别中苦根已经是一个象征符号了,是继续以常人姿态活下去的救命绳索。而失去了苦根的小说中我们看得出福贵老人已经是以不谙世事的心态来活着了,或者说,活在自己的记忆中。余华曾自我剖析到:“长期以来,我一直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而到写作《活着》时,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开始认识到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种高尚是对于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2]可见福贵最后向我们展现的是一种以平和接受痛苦的高尚力量。
对于小说的结局而言,这种一无所有对心灵的穿透力显然要更为强烈,完全触发了人类对活着的哲思,对人生的哲思,对珍惜的哲思。不过从现实的角度看,活着,总是好的,我想在这里张艺谋绝对加入了自己对福贵的一种人性关怀,一种主观同情。对于刻画人生的艺术作品,作为有情感有灵魂的人类,是做不到真正的理性与冷静的。
小说与电影都广阔的再现了深刻而又真挚的人生哲理,死亡的不可抗拒性,仇恨在困境面前被同情所化解,社会现实对人生的无情囚禁等等。如果说活着是一场虚无一场绝望,这种人生的尴尬就应该用“顽强不屈的人生实践创造一个充实欢乐的人生过程。这,既是人生的态度,同时也是人生的意义。[3]我们在读完一部好小说之后总会期待电影作品的出现,可往往改编出的电影作品会让我们大失所望。但《活着》所改编的电影所带给我的失望感是微乎其微,许多方面又绽放着与小说不同的风采,绝对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
参考文献:
[1](德)叔本华,任立等译,自然界中的意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
[2]程戈,对余华小说一种存在主义的解读[J].社会科学战线,2004,(4):56.
[3]胡山林,文学与人生[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