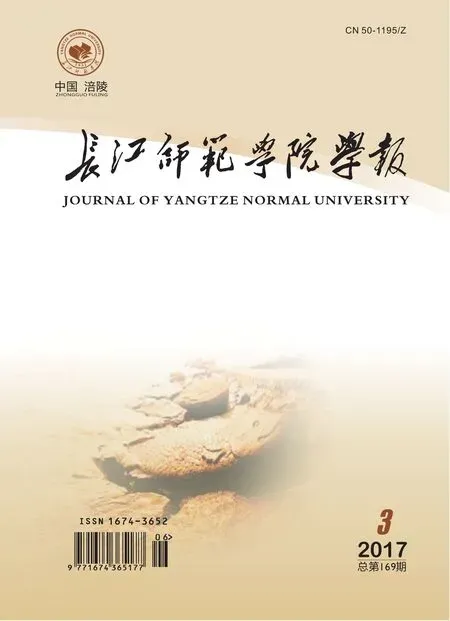城镇化进程中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赵冬菊,黎 光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重庆 404100)
城镇化进程中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赵冬菊,黎 光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重庆 404100)
历史文化是民族之根,文化之魂。在我们今天的城镇化进程中,却存在着对历史文化认识不到位、保护不到位,甚至严重破坏等现象。做好城镇化进程中的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应将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纳入城镇化建设的规划、纳入城镇化建设的衡量标尺、纳入地方政府和相关领导的实绩考核之中,做到保护和利用相结合。
城镇化;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中国历史悠久,历史文化丰富厚重,这些厚重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内涵深邃,不仅记录着我们祖先生活的历史,延续着我们先人的血脉,传承着我们优秀的文化基因,而且孕育着浓厚的人文情怀,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涵盖着至高的人生境界,释放着无穷的光芒。因此,历史文化不仅在历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而且在我们今天的城镇化进程中,在提高城镇影响力、辐射力和吸引力等方面也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时下传统文化热和城镇化热都倍受关注的背景下,有必要就历史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保护和传承做一探讨,以期在城镇化进程中能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建设更有文化底蕴和文化特色的新型城镇。
一、历史文化中流淌着中国人的血脉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大国,在这样一个积淀深厚的国家里,我们的祖先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诸如石器、陶器、青铜器等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文物——物质文化遗产,而且也留下了诸如先秦散文、周朝礼制、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和各种诗词歌赋、曲艺杂耍、习俗禁忌、技能技艺等精神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遗产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内涵博大精深,形式丰富多彩,其优秀的文化因子深深植根于中国人民的血脉与情感之中,是中国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动力,是中国辉煌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催化剂,是中国人民克服各种困难、战胜各种灾难的力量源泉。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使三岁就丧父的孔子把对母亲的孝道延及对社会、对天下的关爱——博爱、大爱,并对当时动荡的时局、前途与未来进行了认真的思考,继而推出用“仁”来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新主张。其“仁”学所包含的“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文化便由此诞生。
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形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的亲善友好的人际观、“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不学礼,无以立”的仪礼观、“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的诚信观,以及“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情怀。
东晋南北朝时期,由道家发展而来的道教,也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对昆虫、草木、鸟兽、山川河流、日月天地的爱戴;对崇山峻岭、登高望远,如入“仙境”环境的追求;对“道法自然”哲学思想的膜拜;对“天人合一”宇宙观的精解;对贵己重生、尊重生命的人生态度……既是信众的精神支柱,也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教科书,因而在中国拥有深厚的土壤和众多的信众。
中国古代文物考古所揭示的我国悠远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遗产,无不连接着中国人的情感与血脉。正是历史文化的这种情感和血脉所凝聚的伟大力量使中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贫穷到富裕、由受欺凌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作用和意义不可小觑。
二、城镇化离不开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2003年9月26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其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其二是中国的城市化。斯蒂格利茨关于中国城市化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并呈加速推进之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16年底,我国城镇人口已近8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为57.35%,中国仅用了30年就基本实现了城镇化。中国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惊人。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持续进行的新型城镇化,将为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从农村走向城市、走向更高水平的生活创造新空间。”2016年,他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电视电话会上指出:“要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2]我国城镇化的目的在于给人民谋取福祉,使人民更加幸福。而人民的幸福和福祉与历史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第一,城镇化建设本身即是对人民的造福运动。我国城镇化建设的目标是城镇化质量的稳步提升、城镇化格局更加优化、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城市生活和谐宜人、城镇化机制不断完善,其根本目的在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作为我国当前重大战略任务的城镇化建设活动,实际上就是一场造福人民的运动,“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3]。
第二,城镇化必须有历史文化才能维系其情感与根脉。我国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即最关注的是人民,尤其是农村的人口。在城镇化过程中,将有几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这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尤其是中老年人,要适应城镇的生活,需要有过去邻里乡亲礼尚往来的交流、三五成群的聚会、逢年过节的拜访等,否则,他们对新城镇的陌生感、疏远感、失落感便会油然而生,有的甚至会产生“打道回府”的念头。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注重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让记忆留住,让乡愁留住,才能使新城镇的人们爱上这座城镇。
第三,城镇化建设有历史文化的内涵才有特色。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民族和人口众多的国家。要在这样一个国家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必须与各地各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习俗与风尚、心理与审美等结合起来,必须与历史建筑、街道、习俗、风尚等不同的历史文化特色或个性结合起来,才能使我国的新型城镇成为有特色、有影响力、有吸引力、有辐射力的新型城镇。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对于新型城镇文化的打造、对历史的缅怀……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三、城镇化进程中文化保护与利用的问题与成因
城镇化是我国当下的重大发展战略,正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向前推进。我国城镇化的目标,主要是调整经济和社会结构,推动区域发展,提高人民的福祉,并以此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过度城镇化”所带来的部分城镇的“重表面,轻地下;重形象,轻设施;重短期,轻长远;重政府,轻民生;重新区,轻老城”[4]导致了种种的“城镇化病”。此种“城镇化病”看似由城镇中的产业、资金、设施、设备等硬件所造成,但我们细究其根源,其根本的致命原因是历史文化的被忽略与漠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对历史文化的忽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和文明为支撑的。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管仲就十分重视历史文化对国家的作用,他把礼义廉耻提高到国家兴亡的高度:“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古人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可见一斑。在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也对历史文化给予了高度重视。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北京大学汤一介对历史文化有深刻的理解,他说:“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博大精深,不仅通过个体表现为强烈的道德主义、积极的社会关怀、稳健的中庸精神、严肃的自我修养,也表现为人道主义和理性态度,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直到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5]从古到今,人们都对历史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可在我们当今的城镇化建设中,历史文化却有重视不够、认识不到位之嫌。
以重庆为例,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由于过分强调城镇化率和进度、速度,致使急功近利、不按程序建设和开发的现象不乏存在。重庆江北区铁山坪,本是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的一块宝地,可由于过分强调其开发效应而忽略了历史文化等人文生态的保护而使其部分人文资源被破坏,原有的文化遗迹遗物,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未能得到充分的保护和传承。在巴南区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城镇化过程中不但存在着工程施工单位不按程序报文物相关部门勘测、发掘和不按国家相关规定支付文物保护经费就施工的现象,而且也存在着文化基础设施滞后、一些传承传统文化活动无法开展等问题。产生种种问题核心原因归结起来只有一个,即对历史文化保护认识不到位或重视不够、重视不力。
其二是建新城,推旧城,不注意对旧城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人们失去了历史的归属感。我们先后到重庆两江新区、巴南区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重庆在城镇化进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旧城镇及其文物古迹的破坏。一些旧的城镇、街道、楼宇遭到“建设性破坏”,不少文化遗产被“商业化”和“城镇化”。渝北区的舒家镇原有的穿斗式建筑古香古色,别具一格,可现在已基本上被拆毁而不复存在,场镇淡出;龙兴镇虽然是重庆市历史文化名镇,古街风貌基本上被保存了下来,但由于其地理环境和人为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渝北天梁寺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但早已被毁;含盖渝北乃至重庆历史和文化的两座古桥梁——白银桥和苏家桥于2013年被废弃。建于东汉时期,号称有“九宫十八庙”和37处院落的江北城被成片破坏掉。江北区在1987年进行全国第2次文物普查时有文物点600多处,但在后来的第3次文物普查时仅存120多处。过去沿江均为成排吊脚楼的传统民居现在已基本上找不到踪迹。一二十年前这里街头巷尾讲故事、讲神话、唱民间歌谣、吹拉弹唱的人比比皆是,但现在这样的民间文化传承人十分稀少,民间故事、神话、歌谣、曲艺等失传严重,以至于像江北一带原来文化资源十分富集的地方,现在普查出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仅有1项(江北评书),区级的也仅11项。北碚区的63个77处抗战遗址中,已消失32个。另有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央警卫署、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暨滑翔机修造所、江苏医学院、峡防局旧址(文昌宫)、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旧址、逊敏书院、军令部中央军需学校重庆旧址、北川铁路—绞车梭槽遗址、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检查署行政法院等遗址损毁严重[6]。巴南区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但部分也处于破坏或处于危险状态。巴南区文物管理所是承担该区文物保护的机构,但却因库房设施简陋而使文物存放处于极其危险之中;由于经费短缺,国家每年给的业务经费不足以文物管理部门维持基本的业务开支,大量的文物不能及时征集和保存而不乏破坏和被损毁……这些历史文化的被破坏,不仅使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受到毁灭性的损失,同时也使生活其中的人民看不到对往事的记忆,中断了他们对历史的情感。保护和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迫在眉睫。
其三是对农村历史文化的破坏。在城镇化进程中,因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到城镇而至农村的大批历史文化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被荒废、废弃、遗失、散落、焚毁,大量的乡风民俗、民间技能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淡忘、蔑视、失传。我们在武陵山区调研中发现,大量的土家族、苗族吊脚楼要么处于无人管理而空置所致的自然性损毁,要么因成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仅留置老人小孩所致的安全意识不强而导致火灾和具有民族特色的房屋被烧毁,要么因建设新房而拆除旧房被整体毁灭,要么因搬进新家而将过去使用过的民俗文物予以丢弃,要么因进入城镇后认为原来的建筑和民间习俗、技能技艺等的落伍而予以蔑视,致使农村的大量历史文化遗产被破坏和遗失。2016年8月,武陵山区一个200余年的土家族吊脚楼四合院因用柴火熏炕玉米导致全部烧毁。在武陵山区一个村,非常具有苗族特色的一个村寨因大量人口外出而仅剩不足20人的老弱病残在此守候,这些人员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防范意识极差,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整个村寨都可能被一场大火毁之殆尽。至于传统的生产、生活、信仰等过程中使用的工具、器皿等被废弃、丢弃、遗失的,可谓不计其数。
其四是盲目城镇化,丢弃传统的习俗风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传统习俗对人们的教化作用。《荀子·王霸》载:“无国而不有美俗。”民间有不少美俗。美俗有巨大的正能量,古人就明白“夫风俗盛衰之故系于人心,正人心厚风俗存乎教化”“故欲振国势,必先挽颓风,挽颓风必先从社会着手”[7]的深刻道理。可在我们今天的城镇化进程中,对民俗的认识和作用的发挥很不够。例如,过去民间端午、重阳等传统节日里的祭祀活动及伴随而来的走亲访友、相互往来的习俗渐为今天放一天假或旅游一天所代替,真正意义上的传统节俗几近消逝;连接着无数家庭、无限情感和亲情的大年是我国几千年历史的沉淀。过去,人们不管路有多远,物资有多匮乏,家里有多贫穷,但也得聚在一起亲自煮一煮年饭,吃一餐象征来年美好的团年饭,可今天则正在被在酒店过年、在外地旅游所取代,由此使得进入城镇中的人,尤其是中老年人,没有了昨天的历史和今天亲情的对话,甚至本应得到颐养天年、养老送终的最基本的人伦关怀也难以满足,让他们倍感失落与凄凉。传统习俗对人们良好品德的教化作用正在消解。
其五是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体育、文艺消逝严重。重庆在历史上曾有不少民间体育和文艺,如打陀螺、跳山羊、打老钱、打水枪、打毽子(毽球)等民间体育和陪歌(坐歌堂,土家族地区为“哭嫁”)、吹打、薅草锣鼓、山歌、龙灯等民间文艺,都异常丰富,这些传统的体育和文艺是我们前辈创造的文化,是先人们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情感基础和文化基因,它体现的是我们民族的根,塑造的是民族的魂,有着活跃文化生活、再现历史、联络情感、塑造灵魂、提升素质和培养乡情民情等方面的功能。但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伴随乡村城镇化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加上老者作古,年轻人不愿传承,几近人亡艺绝。秀山花灯是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重要民间表演艺术,它集歌舞、宗教、民族、民俗、说唱、杂技、连响、腰鼓、纸扎等多种技能于一体,一直受到人们的青睐。然而,在市民化、现代化等城镇化过程中,花灯老艺人已离世不少,60岁以上的老艺人离世已达70%,仅剩几个70多岁的老艺人在艰难地维持。川江号子在现今洋歌洋舞和现代城市流的冲击下,重庆境内能唱川江号子的船工仅剩下数十人[8]。重庆其他民间体育和文艺遭破坏的也不在少数,均面临着传承堪忧的问题。
四、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建议
(一)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担当
历史文化在城镇化中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上至政府,下至民众都应重视的问题。这种重视,除了通过宣传提高民众的自觉参与和自觉保护意识以外,更多的责任赋予了政府。因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建高楼、修广场、扩马路,而是需要凝聚历史积淀的古城古镇古街风貌、传统建筑特色、不同的宗教与信仰、不同的乡风民俗、不同的风味小吃,以及适宜人们生产生活的生态环境等在内的多样化的历史与传统文化,才能使一个城镇成为富有历史与文脉、富有根基与灵魂,能连接记忆与情感,既有历史乡土气息又有现代元素的和谐城镇,继而发挥历史文化的润滑、示范和引领及对人们的凝聚和辐射、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和影响作用,使人们从这里找得到归属感、认同感、自豪感,使历史文化成为链接历史与未来、老人与孩子、本地与它地、人文与自然的一座桥梁。而这些造福社会的公益性工作是需要地方政府的规划、实施、监督……地方政府必须承担起主导性作用,在提升对历史文化保护意识、改进保护措施的同时,政府要积极引导民众与社会组织参与到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中来。
(二)严格落实《规划》精神,将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纳入各地城镇化建设的规划之中
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在诸多方面都提到了历史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和利用问题。但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我国是一个地域复杂、人口和民族众多、发展程度迥异的大国,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国家政策的落实并非易事。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部分基层政府,为了追逐城镇化速度和GDP效应,在《规划》等文件政策的执行上敷衍了事。2017年1月2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些精神落实各地城镇化建设的相关措施时,应将历史文化的内容切实纳入各地的城镇化规划之中。
(三)将历史文化纳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衡量标尺
国情和地情的复杂,使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千差万别,城镇化建设的内涵和风格各异。城镇化建设的内涵、风格或形式虽然不同,但我们衡量新型城镇文化建设成效时应该有一个标尺,那就是历史文化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视程度、保护程度、应用程度、传承程度,以及人口素质的文明程度等。
在今天的城镇化进程中,无论我们建设的城镇处于什么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中,无论它规模的大小,人口的多寡,也无论它经济实力的强弱,都需要历史文化的注入和渗透。如果把我们新建的城镇建筑物、桥梁、公路、街道、公园、超市,以及行驶在其中的车辆比作城镇的物质文明或城镇硬实力的话,那么涵盖其中的古建筑、古村落、古院落、古街道、古桥梁、古庙宇、古神像、古祠堂、古家谱,以及流传其中的神话故事、诗词楹联、风俗习惯、习俗风尚、民间信仰等历史文化,则是城镇的软实力,它是这座城镇聪颖与明智、灵魂与气魄、胸襟与气质、格调与品位的聚合体,是城镇中的灵与魂,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一个城镇,拥有了这些,这个城镇的人口素质会提高,品位和形象会提升,文化底蕴会增厚,吸引力和影响力会增强。因此,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不但应重视历史文化在其中的作用,而且更应将其作为衡量城镇化建设的一个标尺和硬指标。通过历史文化保护和传承,把我们的城镇打造成具有不同民族和地域特色的特色城镇。
(四)用“活”的方式保护和传承地方历史文化遗产
农村的历史文化建筑因人员外迁和无人看管与修缮而至破败,因缺乏防火意识和防火设施而遭火灾,因山区山势陡峭和夏季洪水泛滥而至传统建筑被洪水卷走,因不明宗教建筑价值而被人为破坏,因建新房拆旧房而至旧有建筑被摧毁,因搬家搬迁的搬运负重而致旧有生工具(器具)等设施、设备的遗弃,因农村人口不明民俗文物的价值和重要性而低价被文物商贩收购,因缺乏保护保养措施而致受到自然性破坏加剧……如此等等,都使农村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破坏严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武陵地区的一些农村,由于不少人外出而至老家房屋无人管理而破败不堪,因图搬迁省事而丢弃风车、磊子、磨子、碓窝、筛子、簸箕、麻蓝等几乎可以建若干个博物馆的藏品。原来不少典型的四合院吊脚楼院落因不少人以现代水泥建筑的改造而至老式历史建筑的风貌被改变。一个两百多年的木质吊脚楼建筑小院,因安全意识淡薄和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在一场火灾中吞灭了。一户吊脚楼因修建于陡峭的山坡而在一场洪水中连人带房地被洪水卷走。二三十年前在家家户户都能见到的绣花鞋、绣花帽、绣花枕头、绣花肚兜和老人头上包裹的帕子、身上穿的土家族苗族服饰,等等,因人为丢弃和自然的流失而今看不见踪影。在四川夹江古镇,2017年除夕夜晚的一场火灾,使得百年老屋被烧成空架……这种破坏势头仍在加剧,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果不及时予以遏制,不到10年,农村的历史文化遗产将被消灭殆尽,不复存在。先辈给我们留下的这笔文化财富将被消失在浩淼的历史中,掩埋在现代人的城镇化进程中,这不仅是我们对祖先的不敬,而且我们也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因此,保护好农村的不可移动的历史、建筑和可移动的各种民间文物和“活态”文化,使其发挥文物收藏、艺术鉴赏、乡村旅游、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作用,吸引城里人到乡下旅游、观光、体验,在使用中保护和传承,这不失为保护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为此,政府应首先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宣传,让百姓明确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作用,使百姓形成一种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自觉、自信和自律。其次,政府应对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做出保护的规划和措施,包括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规划和措施,以此形成一种有序的管理、保护与传承的机制。最后是积极调动和鼓励百姓参与。通过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而发挥其在旅游中的经济价值,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作用的发挥与百姓的利益结合起来,发挥联合保护效应。
(五)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我国有包括民俗、戏曲、歌舞、神话、故事、谚语、谜语等在内的极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内涵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护,但保护和传承的力度和成效仍待进一步加强。2016年8月,我们到重庆秀山县调研发现,有能歌善舞的古稀老人未被普查到的,有一些乡间民俗和神话故事未能被收录。在其中一个村里,能唱出几十个民间歌曲、利用民间中草药为民治病的老苗医的以及会刺绣的绣花老艺人等都未能被发现都收录。这些人的年龄均在七八十岁以上,如果不及时保护和抢救,他们身上所携带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必将随着老艺人的作古而消逝。
(六)积极开展传统文体活动,在使用中保护和传承
不少传统文体活动也是历史文化遗产,但因从业、从艺老艺人年事已高或已作古而中断,因外出、外迁人口的增多,留在本地的人口越来越少而使活动越来越少。同时,因青少年的“现代化”而嫌弃传统文体活动的“土气”而使相关活动的参与者越来越少,因现代各种体育和文艺产品的增多及媒体的快速传播而至传统文体项目被越来越多地遗忘……因此,建议政府从全方位的视角,在现有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就这些传统的民间文体项目出台较为细化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并使政策细化和落地。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间文艺——喊山歌、说唱、傩戏、阳戏、南戏、三棒鼓、吹唢呐……历史传承下来的民间体育——打陀螺(打得螺)、踢毽(毽球)、跷跷板、滑滑板、跳房子(跳飞机)……都是历史上流行的文体娱乐项目,这些项目至今仍然在民间有一定的传承和影响。这些项目仍然是人们交友、娱乐、健身的活动方式,受到人们的青睐追捧,发挥着健身、鉴赏、增进友谊、凝聚人心和促进和谐的种种功能。在今天人们快节奏生活余暇的企盼和返璞归真中,更需要这些传统习俗与活动的浸润和滋养。因此,政府应将其保护和传承纳入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中,纳入地方政府和干部的绩效考核中,纳入文化创意产业和乡村旅游的规划和建设中,使之成为地方的文化名片。
[1][战国]孟轲.孟子[M].四库全书本.
[2]习近平.习近平对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 促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6-02-24.
[3]新华社.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EB/OL].http://www.gzny.gov.cn/tbgz/2014-03-19/24502.html.
[4]城市中心解析城镇化之三:改革的难点[EB/OL].http://www.jinxiang.gov.cn/art/2013/1/25/art_2625_38676.html.
[5]找回民族力量之所在——访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EB/OL].http://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shzt/ctc/core/200410210784.htm.
[6]北碚区抗战遗址汇报材料[EB/OL].http://wenku.baidu.com/view/fcbc59c75fbfc77da269b156.html.
[7]萧放.中国传统风俗观的历史研究与当代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31-40.
[8]王予谦.重庆民间文化艺术陷入尴尬 人亡艺绝难传承[N].重庆时报,2009-05-21.
[9]抓好文化建设领导重视是关键[N].重庆时报,2009-07-01.
[责任编辑:庆 来]
G127
A
1674-3652(2017)03-0047-06
2017-03-20
2016年重庆市科委课题“城镇化进程中的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cstc2016jccxA0068)。
赵冬菊,女,湖北利川人。教授,主要从事民族文化研究;黎光,男,湖北恩施人。经济师,主要从事文化管理研究。
——围棋